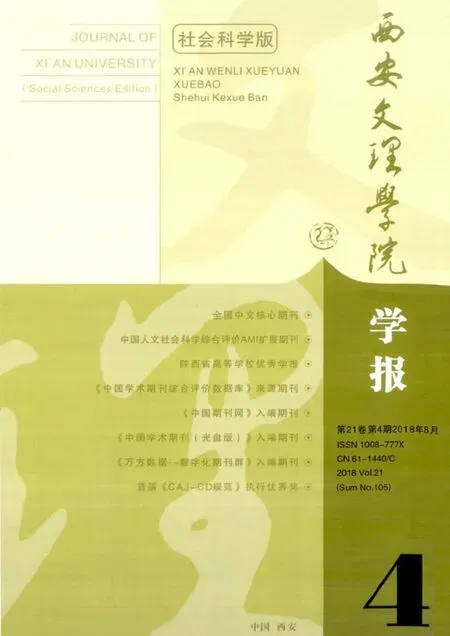论武则天时代的大赦与刑狱
王 艳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滥赦”与“淫刑”一向是后世诟病武则天统治的常用之词,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本文所言武则天时代[注]关于武则天统治的时间跨度,学界有不同观点。以往多认为自高宗显庆始,长达近半个世纪,其依据是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的记载。据赵文润在《唐高宗“昏懦”说质疑》(《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唐高宗再评价》(《唐史论丛》第七辑,1988年)等文中的考证,武则天在高宗去世前仅是高宗在政治上的助手,“参预国事”,是高宗政治意愿的执行者而非主导者。而高宗崩后,虽遗诏“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但从中宗即位后对人事多加调动、并大力扶植韦氏势力,且扬言“我以天下与韦玄贞有何不可”可知此时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中宗手中,其并非“傀儡皇帝”。直至光宅元年(684)二月,“废中宗为庐陵王”,随后“立雍州牧豫王旦为皇帝。政事决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武则天方完全掌握政权。始自光宅元年(684)二月,终于张柬之等“兵谏”的神龙元年(705)正月,在此期间政令完全出自于武则天的意愿,反映了其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目前学界涉及这一时期的大赦和刑狱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注]既有在对整个有唐一代的赦宥研究中提及武则天时代的成果,如禹成旼《唐代赦文颁布的演变》(《唐史论丛》第八辑,2006年)、魏斌《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与大赦职能的变化》(《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等,也有专门针对武则天时期的研究,如印娟《武则天时期的大赦》(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雒晓辉《论武则天当政时期的大赦问题》(《乾陵文化研究》第十一辑,2017年)等,涉及武则天时期赦书内容的扩展、颁赦形式的演变、频繁大赦的原因及其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等各个方面。而关于此期刑狱的研究多集中于“酷吏”,如胡戟《酷吏政治与五王政变》(《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王双怀《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唐都学刊》1999年第1期)等。此外,赵文润在其《武则天与法制》(王双怀、梁咏涛主编《武则天与广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一文中批驳了长期以来认为武则天时期无法制的观点,对本文写作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刑狱是践行国家法律制度的自然结果,大赦是皇帝权力意志对司法的干涉,二者有天然矛盾之处,又同为一个时代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武则天时代对大赦及刑狱的运用,以窥其治国理政思想。
一、武则天时代的大赦
唐代的赦,有大赦、曲赦、别赦等不同种类,相对于针对特定地区的“曲赦”和针对特定个人的“别赦”,“大赦”因其赦免对象范围包括天下臣民,影响最广、意义最大,也最能代表统治者的政治选择和主张。
从光宅元年(684)临朝称制,至神龙元年(705)被迫退位,武则天在其统治的22年间,共发布大赦26次,大赦原因除传统的登基、平乱、立太子等外,还增加了加尊号、祀南郊、建明堂等,甚至连“齿落更生”都要大赦,无怪乎被盖上“滥赦”标签。但考察其诸次大赦的时间及前后史实发现,虽大赦频繁发布、名目众多,但绝非所谓“多是因帝王的一己之私”[1],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且在其称制、称帝等不同的统治阶段,大赦动机和特点亦存在差异。
1.以大赦消弭改革的障碍并最终达到“革命”的目的(684—690)
从光宅元年(684)二月武则天临朝称制至天授元年(690)九月改唐为周,这一时期的大赦往往都伴随着一定的改革措施。
光宅元年(684)二月,“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为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2]6533李成器为睿宗长子,立其为太子即是为了巩固此前代中宗为帝的睿宗的地位。光宅元年(684)九月,赦天下,改元光宅,同时宣布改易旗帜、服色、官职名号等。垂拱四年(688),“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名‘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拜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刍牧。”[2]6564除以祥瑞“宝图”证明自己是天命之主外,还封洛水、嵩山,明显意在提高其驻跸地洛阳的地位,以洛阳代长安,正是以周代唐的前奏。永昌元年(689),“春,正月,乙卯朔,大享万象神宫,太后服衮冕,搢大圭,执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太后御则天门楼,赦天下,改元。”[2]6571此次大享,武则天“服衮冕,搢大圭,执镇圭为初献”,所行均为天子礼,可以说是将自己的欲望及所处地位正式昭告天下。选择这个时机,想必与此前武则天借豫、博叛乱大诛李唐皇室,扫清自己称帝的最大障碍有关。“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3]120在讲究“天人感应”的古代社会,历法是一个王朝的象征,故每一个新王朝建立都要颁行历法以示“正朔”,而武则天行用“周正”,其心昭昭。天授元年(690),“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赐脯七日。乙酉,加尊号曰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3]121即正式改唐为周。
以上六次大赦都伴有重要的改革措施,占这一时期九次大赦的2/3。其余三次大赦虽未伴有大的政治动作,但均有利于提高武则天的个人权威。“垂拱元年春正月,以敬业平,大赦天下,改元。”[3]117这种平乱赦,多有先例,目的就是宣扬皇帝的武功、仁爱,恩威并济,以震慑肖小,安定平民。垂拱二年(686),“春正月,皇太后下诏,复政于皇帝。以皇太后既非实意,乃固让。皇太后依旧临朝称制,大赦天下。”[3]118此次复政是武则天对皇帝的试探,也是给朝野看的一次表演。其后的大赦是武则天掌握实权的最好证明。垂拱四年(688)十二月,明堂成,“宴赐群臣,赦天下,纵民入观。”[2]6570明堂为武周政治的象征,且此前一直存在于文献记载中,高宗欲建明堂未成功,却在武则天治下建成了。明堂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武则天权威的最好歌颂。
这一时期的大赦多伴有改革措施,也可以说此期改革措施多伴随着大赦一同发布。为什么要将二者并行呢?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借助大赦消弭改革的反对之声。唐代大赦一般包括三种元素,即“对罪囚的赦宥、对官人的赏赐、对百姓的恩惠”[4]2。以光宅元年九月的赦文为例,“自九月五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皆赦除之”[5]16,对罪囚的赦宥范围不可谓不广、力度不可谓不大。“诸年八十以上,各赐粟二石、绵帛二段,九十以上,赐粟三石、绵帛三段,百岁已上,赐粟五石、绵帛五段。并依旧例版授,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咸表门闾,鳏寡惸独、笃疾之徒、不能自存者,并加赈恤”[5]17,此即对百姓的恩惠。另外,虽此赦文中未明确规定“对官人的赏赐”,但据天册万岁元年(695)刘知几的奏疏,“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2]6616。也就是说,每逢大赦,朝野臣民皆有益处。改革自然难以避免地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大赦则在最大范围内使臣民受益。武则天正是以大赦为契机,一步步完成了改易国家机器、行天子祭祀、颁行新历法等诸多改革,最终革李唐之命为武周。此外,大赦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伴随着赦书而发布的改革措施自然也能快速而广泛地深入民心。
此外,大赦也是皇帝与普通百姓沟通关联的重要方式。俗话说“天高皇帝远”,朝堂争斗、皇位兴替在多数情况下对平民百姓的生活影响甚微。但大赦同一般诏令不同,其涉及范围为天下臣民,皇帝的恩惠伴随着赦书传播到全国各地,百姓自然对大赦发布者的“皇恩浩荡”感恩戴德。故大赦在争取民心、提高皇帝权威方面功不可没。上述“平乱赦”“建明堂赦”等即是着重体现了这一点。而在武则天成功“革命”进入新的统治阶段之后,为了稳定民心、巩固帝位,大赦的这一职能更加突出。
2.以大赦提高个人权威并行恩惠以巩固统治(690—698)
从天授元年(690)九月改唐为周至圣历元年(698)九月立庐陵王为太子,此期大赦最为频繁,多为提高武则天个人权威、巩固新王朝的统治而赦。
长寿元年(692),“四月,大赦天下,改元为如意,禁断天下屠杀。”[3]122此举或与此前天授二年(691)四月“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2]6587有关。李唐自立国以来,便以道教为三教之首,更尊道教始祖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以提高皇室的“神性”。而武则天改唐为周,也要为自己寻找一个能与李唐所尊道教相抗衡的思想上的靠山,故其提高释教地位。为了增强说服力,其遵从佛教教义,禁断屠杀,在天下臣民面前树立“仁君”形象。大赦天下,也是为了减少推行此诏令的障碍。从久视元年(700)凤阁舍人崔融上言求开屠禁,言“贫贱之人,仰屠为生,日戮一人,终不能绝”[2]6670,可知此诏令推行之难。
同年九月,“敕以齿落更生”赦天下[2]6602,如此带有强烈而奇特的个人色彩的赦,史无前例,是武则天被盖上“滥赦”标签的有力论据。然值得注意的是,“齿落更生”从生理角度本就少见,更遑论皇帝晚年的“齿落更生”,足可算作祥瑞之兆。武则天通过大赦将此“祥瑞”广告于天下,意在向臣民宣扬其“天命之主”的特异性,提高个人权威。
长寿二年(693),“秋九月,上加金轮圣神皇帝号,大赦天下”[3]123;延载元年(694),“五月,魏王承嗣等二万六千余人上尊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甲午,御则天门楼受尊号,赦天下”[2]6609;天册万岁元年(695),“正月,辛巳朔,太后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赦天下”[2]6613,“秋九月,亲祀南郊,加尊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天册万岁,大辟罪已下及犯十恶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大脯九日”[3]124。这一时期的大赦均为上尊号赦,其核心为加“金轮”之号。[注]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孙英刚《转轮王与皇帝:佛教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武则天的七宝——佛教转轮王的图像、符号及其政治意涵》等研究。《释迦方志》云:“凡人极位,名曰轮王。……又轮王有四王,约统四洲。金轮王者则通四有;银轮三方,除北一洲;铜轮二方,除西北方;铁轮在南,除于三方。”[6]也就是说,金轮是佛教“四大轮宝”中最为殊胜的一种,为金轮王者,即为万国共尊之主。武则天加“金轮”尊号,即是自比金轮王,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权威,以巩固统治。
其后的万岁通天元年(696)腊月以“封神岳”而赦[2]6619,四月因“新明堂成”赦[2]6620,神功元年(697)九月“以契丹李尽灭等平,大赦天下,改元为神功”[3]126,圣历元年(698)正月“亲享明堂,大赦天下”[3]127。这些大赦前后并无重大举措,可算作传统的为宣扬国家强盛及帝王恩赐黎民而赦。
纵观这一时期的大赦有如下特点:(1)十分频繁。短短8年期间,大赦11次,除天授二年(691)外,每岁必赦,甚至多次一岁两赦,这在重视大赦、提倡“慎赦”的古代社会是十分罕见的。究其原因当与政权初立有关,然更重要的是由于武周政权之来源不当。武则天以太后之尊篡其子之帝位,其名不正,自然多受诟病,故以频繁颁布恩赦的方式来换取臣民的支持。(2)大赦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多次大赦的因缘都与帝王个人直接相关,如“齿落更生”、加尊号等。这一点则与武则天的“女主”身份不无关系,武则天虽以女主之身君临天下,但却改变不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和思想观念。在这种环境下,她只能竭力提高个人权威,强调自己并非一般的女子,而是“金轮王”转世的天命之主。(3)大赦伴有赐脯。除长寿元年(692)四月赦外,每赦均有赐脯。少则三五日,多至七九日,所费弥广,但不可否认的是,赐脯是最直观展示国家昌盛并让臣民受益的活动。可以说,此期频繁大赦并伴有赐脯的用意,正是在于让人民最直观感受到新政权的益处,从而支持其统治。
3.大赦频率降低且具有恢复唐制的妥协色彩(698—705)
从立庐陵王为太子的圣历元年(698)九月至被迫退位的神龙元年(705)正月,大赦的频率降低,且具有回归李唐王朝统治轨道的妥协色彩。
圣历二年(699)腊月,“赐太子姓武氏;赦天下”[2]6655,但武则天亦心知这只是表面工程,自己百年之后江山依然是李氏的江山,甚或无武氏容身之地,故其随后“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2]6656,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李、武之间的矛盾。
久视元年(700)五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视;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2]6662;久视元年(700)十月,“制复以正月为十一月,一月为正月。赦天下”[2]6669;长安元年(701)“冬十月,幸京师,大赦天下,改元为长安”[3]130;长安二年(702)十一月,“亲祀南郊,大赦天下”[3]131;神龙元年(705)“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明以来得罪者,非扬、豫、博三州及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2]6695。伴随着以上大赦,武则天一步步去尊号、恢复李唐历法、将统治中心迁回长安、赦宥政治犯,将国家机器又恢复到李唐统治的轨道上来。
在这一阶段的7年间共颁布大赦6次,与第一阶段的7年9赦、第二阶段的8年11赦相比,频率大大降低,且明显带有回归李唐统治的色彩。或许是因为此期武则天已然年迈,预料到身后之事且无力改变,故不再作奋力改革或维护革命成果的无望之争,转而与朝野妥协,恢复李唐王朝的统治秩序。
4.大赦中的“赐脯”及“御楼”问题
武则天时期频繁大赦饱受诟病的重要原因除破坏国家正常司法秩序外,还有所费繁多,增加财政负担。大赦增加财政负担主要体现在赐脯上。从玄宗先天二年发布的《禁断大脯广费敕》中“赐脯合宴,正欲与人同欢,广为聚敛,故非取乐之意……自今已后,两京及天下脯宴,所作山车、旱船、结彩楼阁、宝车等无用之物,并宜禁断”[5]562可知,武则天时期的赐脯,除所赐宴饮花费本身外,还有所作山车、旱船等费用,真可谓“所费弥广”。赐脯以外还有“御楼”,“唐制:凡御楼肆赦,六军十二卫皆有恩赉”[2]8068,亦是国家财政的一种负担。但应当指出的是,武则天时期的“赐脯”并非贯穿始终,而是集中于垂拱四年(688)至圣历元年(698)之间,即称帝前两年与政权建立初期。圣历元年(698)立太子之后的大赦中仅有久视元年五月赦“大脯五日”[3]129。而三次“御则天门楼”,也集中在新政权建立前后的永昌元年、天授元年和长寿二年。也就是说,武则天的“赐脯”和“御楼”有着为称帝作准备和巩固新政权的深层目的,通过这些手段最直接地给予官民恩惠从而换取他们对新政权的支持。
至于作为例外的久视元年(700)五月的“赐脯”,联系此次大赦的契机即武则天疾病少愈可以推测,或是出于为自己祈福的目的。从长孙皇后大病不愈,太子承乾言“医药备尽,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3]2166可知,唐人认为恩赦可以积福助疾。另外,1982年在嵩山发现的《武则天除罪金简》上书:“上言:大周圀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七月庚子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注]金简现藏河南博物院。文献引自赵文润《武则天与法制》一文。
金简上的“小使臣胡超”应是为其合药的僧人胡超,“太岁庚子”年亦正是久视元年(700)。此年五月的“大赦”是赦他人之罪,而两个月后的七月投放“金简”是为了“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有理由认为武则天此次大赦天下并久违地“大脯五日”,极可能是通过恩赦臣民来为自己积福赎罪。
综上所述,武则天时代的大赦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不同统治时期的大赦特点和动机存在差异,归根结底与其在各个时期的处境及需要息息相关。即使是因给国家财政带来负担而饱受诟病的“赐脯”等问题,也是出于特定阶段的统治需要而进行的阶段性活动,不宜一概而论。
二、武则天时代的刑狱
武则天时代的刑狱,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和统治需要,亦呈现出阶段性特点。这一点前辈学者已有论述。胡戟在《酷吏政治与五王政变》一文中,就将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政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光宅元年(684)武则天临朝称制到天授元年(690)九月正式称帝,其特点是大开告密之门,重用酷吏大肆诛杀宗室大臣,“打击面大而且刑法酷重”[7]4。第二阶段是从天授元年(690)九月至圣历元年(698)九月立庐陵王为太子止,“这时的打击对象集中于文武官员”,但处罚力度有所减轻,且“以如意元年(692)七月严善思打击‘罗织之党’为标志,滥刑开始有所收敛”[7]4。从圣历元年(698)九月立太子到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退位为第三阶段,此时期武则天帝位已基本巩固,逐渐宽省刑法,弃用酷吏,并采纳臣子建议,数次为之前得罪者平反。
“酷吏政治”是武则天时期司法理刑的最重要特点,故以上关于“酷吏政治”的阶段性划分基本与此期治理刑狱的阶段性特征相一致,但仍有一些地方值得注意。《旧唐书·刑法志》云:“则天严于用刑,属徐敬业作乱,及豫、博兵起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3]2143即武则天重用酷吏的原因在于“恐人心动摇”,即《资治通鉴》所言“疑天下人多图己”[2]6553,故“欲以威制天下”。而在武则天大开告密、任用酷吏之时,麟台正字陈子昂上书劝其以亡隋为鉴,“务玄默以救疲人”,莫要“任威刑以失其望”,武则天虽“不听”,但也没有加罪于陈,或因其心知陈子昂所言有理,但此时代唐的脚步已经迈开,必须重威行打击政敌以巩固统治,故而不能用其言。[2]6555-6556另外,武则天在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的同时,又重用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等治案公正宽仁的直吏,天授元年(705)徐有功为周兴所陷免官,武则天又“复起为侍御史”,甚至罔顾其辞官之愿,“固授之”[2]6584-6585。
天授二年(691),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纵横上疏,武则天虽不听其言,但却在同年诛杀周兴等,并着手逐渐清除酷吏,“以慰人望”[2]6587。长寿元年(692),“右补阙新郑朱敬则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异议,今既革命,众心已定,宜省刑尚宽,乃上疏……太后善之,赐帛三百段。”[2]6600-6601侍御史周矩上疏劝武则天“缓刑用仁”,武则天亦“颇采其言,制狱稍衰”[2]6601-6602。此前陈子昂等上疏武则天皆不听,此时却善朱敬则等言,并非其性情善变或年老宽仁,而是为了迎合不同阶段的统治需要。长寿二年(693),“或告岭南流人谋反,太后遣司刑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就按之”,随后“更遣六翊卫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威卫兵曹参军屈贞筠皆摄监察御史,诣诸道按流人”,“其远年杂犯流人亦与之俱毙”,但其后“国俊等亦相继死,或得罪流窜”[2]6606-6607。这是武周时期最后一次酷吏按狱,大加诛杀,也是为了将可能的“谋反”扼杀在摇篮里,迎合其巩固统治的需要,一旦没有“谋反”威胁,即清除酷吏。其后,万岁登封元年(696)颁布《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敕》,因“万岁初元,肇开昌历,九章恒宪,甫释严苛”,故裁司刑之丞,废秋官之狱,可见此时刑法已略宽省。[5]473万岁通天元年(696)因与契丹战败,下制发“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骁勇者”以击契丹,陈子昂上疏言“比来刑狱久清,罪人全少”,罪人少一方面是连年大赦的缘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此期刑法大省。[2]6622-6623而圣历元年(698)立太子之后,武则天更是不断颁布诏令,平理冤狱。
武则天时期的刑狱与大赦相同,亦存在阶段性特点,且呈现逐渐宽省的趋势,并不能以“淫刑”概之。而即使是刑法最为“枉滥”的临朝称制时期,武则天在重用酷吏、大肆诛杀的同时,亦注意起用治狱宽仁的直吏。武则天并非真正的“淫刑之主”,“威刑”只是为了迎合特定时期的统治需要而采取的“非常之法”而已。另外,大赦对罪囚的赦宥自然是对刑狱的破坏,但结合武则天统治不同时期的大赦与刑狱的消长情况来看,二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反而基本呈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在武周代唐和武则天称帝初期,武则天重用酷吏,刑法酷滥,同时大赦也十分频繁;而在其统治后期,刑法逐渐宽省,大赦频率也明显降低。个中原因当是为了保持国家司法体系的平衡和社会稳定。武则天统治前期,政局动荡,刑法酷滥,社会矛盾尖锐,大赦是最简单有效地缓解矛盾的手段。至后期政局逐渐稳定,刑法逐渐宽省,继续频繁大赦,使违法之徒逃避惩罚,反而会对国家司法和社会稳定造成破坏,故恩赦频率自然降低。总而言之,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大赦与刑狱,均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且各个阶段大赦与刑狱的频率和程度均相互制衡,从而使社会的司法状况达到微妙平衡,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三、武则天时代大赦对刑狱的影响
刑法酷滥与大赦频繁并存是武则天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故具体研究此二者的共存状态,是了解武周政治必不可少的一环。
天册万岁元年(695),彭城刘知几上表:“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惜,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于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寇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望陛下而今而后,颇节于赦,使黎氓知禁,奸宄肃清。”[2]6616
以往研究武则天时期的大赦者多据此批评武则天时期频繁大赦,使违法者逃避惩罚,对国家司法秩序造成了极大破坏。笔者试从大赦下的政治犯和大赦下的一般刑狱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真如是言。
1.大赦下的政治犯
如前所述,武则天重用酷吏主要是为了诛杀政敌,为称帝扫清障碍,因此政治性案件是此期刑狱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在频繁大赦之下,这些政治犯的处境如何?有没有因为大赦就推翻了原有刑狱处分而被赦免呢?
目前所存武则天统治时期发布的大赦赦文有二,即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三的《改元光宅诏》及载于同书卷四的《改元载初赦》。二者关于赦令范围的规定如下:“可大赦天下,改文明元年为光宅元年。自九月五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皆赦除之。流人未达前所者、放还。其犯十恶、官人枉法受财、监临主守自盗、所监临却杀人、故杀人、谋杀人、反逆缘坐、并军将临戎挫威丧律、镇遏失所、亏损师徒、及常赦所不免者,并不在赦例。亡官失爵、量加收叙。”[5]16-17(《改元光宅诏》)“自载初元年正月一日子时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皆赦除之。其叛逆缘坐、及子孙杀祖父母父母、部曲容奸、奴婢杀主,不在赦限。其与敬业虺冲并与诸虺友往来、其魁首已伏诛、其支党事未发者,并特从原免,不得更相言告。”[5]19(《改元载初赦》)
两条大赦规定的不赦内容虽有差别,然“反逆缘坐”条均不在赦列。而武则天时期的政治犯多数是因“谋反”获罪,扬、豫、博等坐实谋反者且不论,还有诸多因反对其以周代唐或为其政敌申理而被诬谋反者,如裴炎、程务挺等,这些政治犯及被其牵连的家族等当然不在赦列。此外,还有一些政治犯虽不因“反逆”获罪,但最终也不免死亡的命运。如因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而被赐死于家的刘祎之、因周兴构言“太后老矣,须复皇嗣”[3]2853而被赐死的魏玄同等,这种官僚的非正常死亡在武则天时代比比皆是。究其原因,或因这些人罪因法不足致死且处唐律规定的可议减之列,若再遇赦即有免罪可能,故武则天选择动用帝王权力直接将其处死。
从以上两条赦文可以推测其余年份发布的赦文内容,其所赦范围应当无大差别。唯有天册万岁元年(695)发布的赦文,规定“大辟罪已下及犯十恶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3]124,因此特殊性而被载入《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那么,在此赦文下,政治犯是否就得到赦宥了呢?应当注意的是,在此大赦发布前的长寿二年(693),武则天曾因担心流人谋反而派遣六道使“诣诸道按流人”,六道使大肆屠杀流人,使“远年杂犯流人亦与之俱毙”,在诸道流人中因政治案件而流的人必然是谋反的最突出怀疑对象,也必然在此次事件中受创最重。如因上书言武氏“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而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被流于岭外的江陵人俞文俊就是被六道使所杀。[2]6557从此次事件后武则天发布的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属皆听还乡里”,就可以推测此次六道使屠杀之滥。经过这一浩劫,众多政治犯已经无命活到两年后的颁赦了。
另外,圣历二年(699),凤阁舍人韦嗣立因“向时酷吏所诬陷者,其亲友流离,未获原宥”而上疏:“自扬(徐敬业叛乱)、豫(越王贞起兵)以来,制狱渐繁,酷吏乘间,专欲杀人以求进。赖陛下圣明,周、丘、王、来相继诛殛,朝野庆泰,若再覩阳和。……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广雷雨之施,自垂拱以来,罪无轻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复官爵,生者听还乡里。如此,则天下知昔之枉滥,非陛下之意,皆狱吏之辜,幽明欢欣,感通和气。太后不能从。”[2]6659

2.大赦对一般刑狱的影响
考察大赦对一般刑狱的影响,即是考察赦令执行的范围及力度。关于这一点,台湾学者陈俊强在《述论唐代大赦的内容和效力》一文中已对唐代大赦执行的时间、涉及的范围、对不同刑法的影响程度等诸多方面做了详细考证。据陈氏考证: “徒刑算是较轻微的刑罚,一般都会因大赦而放免。流刑犯若未发遣或程内在道,都因大赦而得到放免。但是,已经抵达配所的流刑犯,除非是程内遇赦,否则仍不可返回原籍。死刑犯方面,由于唐代审判手续以及‘待时而决’的限制,再加上频繁的大赦,最终恐怕有超过三成的死囚会逃过一劫。”[4]28且陈氏认为,三成只是有唐一代的平均概率,在肆赦的盛唐,死囚被赦免的概率更高,如平均九个月一次大赦的武则天时期,可能会达到四成以上。但笔者不以为然。
首先,大赦效力之强大毋庸置疑,但唐代仍有一些罪行虽赦仍不免,主要有三类:一是“常赦所不原者”,二是“知有赦而故犯”,三是“以赦前事相告言”。其中牵连最广且最易受当政者影响的当属“常赦所不原者”。武则天时期频繁大赦,但赦文载入《则天皇后本纪》者,仅天册万岁元年(695)“大辟罪已下及犯十恶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一条,说明此次大赦情况特殊故录入,也就是说,往年大赦“犯十恶常赦所不原者”并不在赦列。这一点从上文所引两条现存赦文中也能得到印证,故可知“常赦所不原者”在武则天时代往往是得不到赦宥的。
其次,武则天时期大赦对刑狱的影响力受到酷吏政治的影响。《资治通鉴》记载:“每有赦令,俊臣辙令狱卒先杀重囚,然后宣示。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2]6555往者多以此条批判酷吏政治,认为其所杀重囚多为武则天的政敌。而由前文论述可知,武则天对其政敌一般采取两种处置方式:一是使诬其谋反,而坐“谋反”者不在赦列,无需先杀然后颁赦。二是由武则天直接下令赐死,则更无赦宥可能。故此处所说的“重囚”,可能多是一般刑狱中的重犯。武则天为了谋取帝位及巩固统治,不得不以频繁大赦拉拢人心,但其必定心知频繁大赦会对司法理狱造成破坏。来俊臣正是揣摩到了武则天的这种心理,故每有赦令先杀重囚然后宣示,“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也正是对其行为表示支持。而就武周时期酷吏们的一贯行事作风来看,这种支持必然会促进其他酷吏的效仿,虽史书无明确记载,但可以推测每有赦令先杀重囚者绝不止来俊臣一人。
最后,武则天时代特殊的政治局势亦会对一般刑狱造成影响。武则天在天授中和长寿二年,两次派遣诸道使按“流人”,死者甚众。虽其初衷是为了打击政治犯,但也难免殃及其他流人。陈子昂所上《为朝官及岳牧贺慈竹再生表》云:“日者王德寿等承使失旨,虐滥无辜,灾感蝗虫,毒痡慈竹。宁岁为之饥馑,甿庶以之流离。”[8]王德寿即长寿二年所遣“六道使”之一。
综上所述,武则天时期频繁颁布大赦必然使一些“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逃脱惩罚,对国家司法造成破坏,但并非所有罪犯都在赦列,尤其犯“十恶”等重罪者很难得到赦宥。且由于其时政局动荡、重刑制狱,还使得一些罪犯不仅没能得到赦宥,反而可能受到政治局势牵连而亡命。
四、结语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特殊的一个时期。从司法角度来说,这一时期既重刑威杀又频繁大赦,对这一矛盾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时的社会状况和武则天的治国理念。这一时期大赦虽然频繁,但并非一般认为的因帝王一己私利“滥赦”,而是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且根据不同时期的统治需要大赦也呈现出阶段性特点。而因给国家财政带来负担而饱受诟病的“赐脯”等问题,也是在特定的统治阶段为了最直接地换取民众支持而为之的手段。刑法虽然严酷,但武则天也并非所谓的“淫刑之主”,刑狱只是维护统治的一种非常手段,且这种手段的张弛程度也因不同时期社会环境和统治需要的不同而不断调整。结合武则天统治时期各个阶段大赦和刑狱的特点可知,二者的关系并非此消彼长,反而是“荣损与俱”,相互制衡,从而使社会的司法状况达到微妙平衡。此外,频繁大赦不可避免地对国家司法产生破坏,但这一时期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重刑制狱又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这种破坏性。总而言之,大赦与刑狱都是武则天治政的重要武器,其根据不同时期的统治需要调整策略,不同程度地使用这两种武器,恩威并济,以达到自身的目的。而无论是频繁大赦还是重用酷吏威刑制狱,都带有浓厚的君主个人主张的皇权色彩,武则天时代之所以会呈现出这种特点,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其女主临朝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