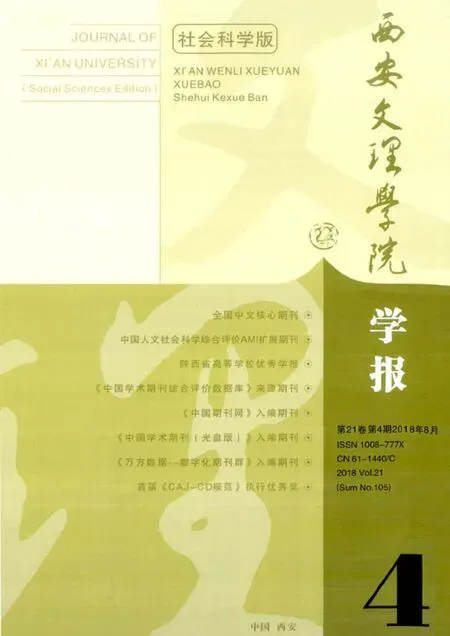探寻自我的历程
——浅析《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的主题意蕴
张 瑶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西安 710119)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是 20 世纪最富盛名的意大利作家,被誉为“最有魅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他巧妙地游走于幻想与现实之间,运用轻逸的笔法、精确的描述、凝练的语言,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又一个光怪陆离而又妙趣横生的世界,塑造了诸多个性鲜明、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作为其寓言式小说的代表作,意欲通过三个主人公追求自我的行动,向读者展示人类对于自我意识追寻的历程。三部曲在寻求自我意识的觉醒,树立自我意识的例证,进行自我意识的思考的过程中,向人们诉说着“人如何实现自我的经验”[1]102,并借此展现了作者对于人类反抗消极现实,走出异化困境乐观而执着的追求。
一、完整与分裂
《分成两半的子爵》是《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最先完成的一部作品。小说以17世纪末基督教徒与土耳其人之间的战争为背景, 隐喻了现代人所面临的怪诞荒谬的处境,文中说:“荒凉的原野上散布着一堆堆人的躯壳”,“秃鹫的残骸同他们混合在一起”,“只见男女尸体都赤身裸体,被瘟疫害得变了形还长出了羽毛”,“仿佛从他们瘦骨嶙峋的胳膊和胸脯上生出了翅膀”。[1]2而也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不谙世事的梅达尔多子爵满怀热情地“骑马穿越波西米亚平原,直奔基督教军队的宿营地”[1]1,他踌躇满志,心中“没有怀念,没有忧伤,没有疑虑”[1]6,对人生充满了信心与渴望。但是,头一天与敌人交锋,他就不幸被土耳其军队的炮弹打中,身体也随之被分裂成了两半。右边的一半变成了恶魔的代言人,回到家乡后,偏执地将他所见到的一切都分裂成两半,并以近乎疯狂的残忍,为非作歹,干着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杀死父亲精心训练的伯劳鸟,唆使木匠打造冤杀平民的绞刑架,将养育自己的奶妈驱逐到麻风病村,强迫牧女帕梅拉嫁给自己等等。而就在泰拉尔巴地区的人们慑于右半边子爵的淫威而感到彷徨无助的时候,作为圣徒化身的善良的左半边子爵,也来到了这里,与邪恶的子爵相反,他充满温情地对待着被另一半所践踏过的土地,用基督式的忍耐和一系列善行,试图使得泰拉尔巴由地狱变回天堂。然而,圣徒与恶魔毕竟同在,两个被分裂的半边人在自己所表征的理论体系中,不断地产生对抗与冲突,人们也在“仁爱与恐怖之间”[1]66,在“不近人情的邪恶与道德之间而感到茫然失措”[1]78。最终,善恶两个子爵在为追求帕梅拉而进行的爱情决斗中,被对方分别削开了各自的旧伤口,他们的血肉也因此得以再一次黏连成一体,在古怪疯癫的特里劳尼医生的缝合下,子爵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既不坏也不好的完整的人。
实际上,作者并无意通过这个奇谲诡异的故事来展现人类在善与恶之间艰难的抉择,因为善良的子爵虽然诚实可敬、宅心仁厚,但其行为有时也不免显得迂腐不堪、不近人情,令人心生厌恶。如他曾异想天开地劝说视劳动为教规的胡格诺派教徒无条件地降低裸麦的价格;又曾在以及时行乐为人生准则的麻风病村,进行不合时宜的道德说教,也难怪作为叙事者的“我”开始埋怨子爵的考虑“走得太远了”,甚至还有人因此而感慨:“在这两个半边之中,好人比恶人更糟。”[1]78由此可见,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在这里并不具有崇高的道德意义,作者只是“采用了一种众所周知的叙事的对立”来向读者呈示出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分裂与异化。诚如卡尔维诺在《后记》中所言:“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古老的和谐状态丧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1]94
那么,在被大炮分裂之前的子爵难道就不是完整的存在吗?其实,那时的子爵虽然在表面上具有完整的形体,但却是“无定型的”,“没有个性也没有面容”[1]96,“一切情感全都处于模糊的冲动状态”[1]2。而受难才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追求和谐的欲望来自对内心挣扎的认知”[4]173。我们会发现,“两个非人的相反形象”,反而“表现得更具人性”[1]96。肉体的丧失虽然让他们承受了巨大的苦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分裂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重新审视自我及其周遭环境的崭新的眼光,获得了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和明晰的价值观念。在文中,邪恶的右半边子爵曾对帕梅拉感慨道:“我原来是完整的人。那时什么东西在我看来都是自然而混乱的,像空气一样简单。我以为什么都已看清,其实只看到皮毛而已。” “假如你将变成你自己一半的话”,“你便会了解用整个头脑的普通智力所不能了解的东西。”[1]40善良的左半边子爵也曾有过类似的言论:“这就是做半个人的好处:理解世界上每个人由于自我不完整而感到的痛苦,理解每一事物由于自身不完全而形成的缺陷。”[1]62也就是说,一个不受摧残的完整的自我,并不在于其自身是否具有一个完备的形式,而在于他是否对自我行为有着明确的认知,是否为自己确立了坚定的行为准则。所以,在经过分裂而重新恢复完整之后的子爵反而比之前变得更加幸福和明智。然而,小说在子爵重归完整后便戛然而止,作者并没有继续铺陈子爵对自我意识坚守的过程。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在《树上的男爵》中找寻到一个真正完整的人物形象。
二、融合与反叛
作者将《树上的男爵》的故事架构在遥远的18至19世纪之交,这同样是一个纷繁复杂、动乱不堪的时代,贵族体制与民主共和思想在进行尖锐的斗争,“时局的动荡也让某些人蠢蠢欲动”。故事的主人公柯希莫男爵便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中。柯希莫的父亲是一个旧时代的贵族遗老,他的生活被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主宰着,“他一心考虑的只是家谱、继承权以及同远近的权贵们的斗争和联合”[2]3。而他的母亲虽然是将军之后,但也只能将自己尚武的热情倾注在传统的女红上,虚张声势地以“女将军”的身份去经营家庭,是她获得精神解脱的唯一途径。在积怨深重的家庭里,作为感情交流地的饭桌也成为暴露他们之间“一切对立和互不相容的场所”[2]4。于是,埋藏已久的矛盾终于在1767年6月15日这一天得以爆发。12岁的柯希莫因拒绝吃由姐姐以残忍的手段所烹饪的蜗牛而与父亲发生了争吵,并在一气之下,愤然出走,爬到了树上。令人惊奇的是,在懵懂地上树之后,他便在树上终其一生,再也没有从上面下来,而是渐渐适应并喜欢上了树上的生活,并在树上开辟了属于自己的王国。从表面上看,柯希莫的行为显得过激而幼稚,但其实他所作的一切既意味着他要同压抑和束缚自身天性的家庭与社会进行抗争,也意味着他要在反叛中拒斥平庸,找寻独属于自我的个性和始终如一的处世原则,并将其持之以恒地保持和贯彻下去,直至生命腐朽。
那么,柯希莫男爵在逃离地面之后,是否就成为一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世外高人呢?事实上,如同卡尔维诺自己所言:“那样就太肤浅和无聊了”。[2]273深入文本,我们会发现,柯希莫在爬到树上之后,并没有与外在世界脱离联系,进而使自己变成一个仅仅会在树上跳跃活动的“野人”,相反,他在开拓树上生活空间的同时,也开始全面积极地参与到翁布罗萨地区的生活中去,并与地上的人们实现了和谐融洽的往来。如他曾为防止森林起火,与叔叔律师骑士一起研究如何修建蓄水池,并为此组建了一支消防队;他还曾勇敢地带领民众与摩尔海盗进行殊死抗争;甚至他还在博览群书之后,为翁布罗萨地区的居民们讲解政治新闻和时事事件,以促使其思想启蒙等等。“可以说他越是坚决地躲进他的树枝里”,越是能深切地感觉到自己有要“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的必要”[2]229。也无怪乎柯希莫在随热气球升入天空之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如下字样:“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2]263然而,吊诡之处便在于柯西莫对于大地深沉的热爱,对于人们的亲近与融合,却是在与其反叛和疏离的基础上完成的,就像他弟弟所说的那样:“我哥哥认为”,“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2]173这似乎也印证了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所宣示的文学观:“我不是说要逃避到幻想与非理性的世界中去,而是说我应该改变方法, 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5]7总之,柯希莫虽然生活在树上,但他却并不是一个“厌世者”,而是在此过程中成为“一个不断为众人谋利益的男子汉”[2]273,他成功地借助于树上的空间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专属于自我的生活形式,为自己找到了在他人与自我之间游走的恰当的平衡点。而也正因如此,柯希莫才避免了像子爵般被分裂的命运。
另外,我们还应注意到,为了凸显柯希莫坚持自我意识的主动性和恒久性,作者还有意安排了另一类在树上生活的人,以便与其进行参照。他们是西班牙的贵族,因被王室流放而被迫选择在树上生存,所以,当王室的赦令下达后,他们便欣喜若狂,迅速回到了地上。男爵虽然与他们缔结了深厚的友谊,乃至与亲王的女儿乌苏拉产生了美妙的爱情,但当亲王邀请柯希莫与他们一起返回故乡格拉纳达时,他却宁愿选择牺牲爱情,也不愿放弃抵抗,踏上土地,重回牢笼。也就是说,他的反叛是出自于内心的志趣,“当不存在任何外部理由时,他仍然(选择)留在树上。”[2]273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柯希莫与薇莪拉的交往中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当他与幼时朋友薇莪拉再次相遇时,便迅速坠入爱河,而薇莪拉是一个在情感上极度自我而又贪婪的女人,她想要柯希莫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想法,但柯希莫却说:“如果不充满力量地保持自我,就不可能有爱情。”[2]213就这样,柯西莫在树上孤独地度过了余生,在树上体验了人能体验到的一切的生活的滋味,他如同第一个走出洞穴的智者,享受着孤独之美,但也承受着不被外人所理解的苦痛。无论如何,柯希莫用一生的时光创建了只能容纳他一个人的理想国,在反叛和抵抗中实现了他的自由选择,并用实际行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始至终坚守自我意识的完美的例证。然而,卡尔维诺也深知,这个人物形象毕竟只能存在于童话中,他在小说的结尾无奈地写道:“翁布罗萨不复存在了。”“纠结解开了,线拉直了,最后把理想、梦想挽成一串无意义的话语,这就算是写完了。”[2]264由此可见,单纯地追求精神自由是远远不够的,卡尔维诺在《不存在的骑士》中便将对自我意识的思考进一步推向了形而上的层面,而《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也随之接近了尾声。
三、迷失与寻找
《不存在的骑士》是《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最后发表的一部作品,但作者却觉得“它更可以被认为是序曲而不是尾声”,[3]133因为它所讲述的故事涉及“人该如何存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同前两部小说一样,《不存在的骑士》依然充溢着奇特的寓言色彩和传奇的浪漫情调。故事发生在更为遥远的查理大帝时代,而在那时,人们所处的环境则更为荒唐不堪,文中说:“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世事尚为混乱,名不副实的事情并不罕见,名字、思想、形式、制度莫不如此。而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上又充斥着许多既无名称又无特征的东西、现象和人。”[3]28而作为故事主角的阿季卢尔福骑士,却在这混沌未开的世界中显得鹤立鸡群,卓越不凡。虽然在他雪白锃亮的盔甲背后没有一具完整实在的形体,但他却是一个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勇敢的斗士和尽职的军官”[3]14。他诚实自律、恪尽职守,对工作一丝不苟,熟悉一切规章制度并按照规范严格执行,不容有丝毫懈怠和差错,乃至有时显得机械死板、不近人情,如他曾在宴会中极力揭露将军们用于夸耀战功所编造的不实之词,这也使得将军们感到尴尬难看。总之,他是一个拥有独立意识却并不怎么合群的骑士。而也正因为没有肉体,所以他对自己所感受的东西没有清晰的概念,并且每到夜晚他常常感到寂寞萧索,害怕被不确实而又模糊不清的黑暗所包围。另外,他还对“人们所特有的睡觉的本领心怀嫉妒”。[3]8或许阿季卢尔福也就只能在对“数”的精确推算和对“图形”的整齐排列中,派遣孤独,缓解焦虑。
那么,作者是要有意塑造一个细致严苛而又寂寥落寞的人来表现现代人在世俗生活中的无助与不安吗?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笔者看来,与其把阿季卢尔福骑士当作是一个只会机械完成工作任务的“机构人”,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在畸形的社会中难能可贵地集聚自我意识的“精神象征”。卡尔维诺就曾在文中明确指出:“生存的自觉意识、顽强追求个人影响以及同一切现存事物相抵触的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普遍流行开来,由于许多人无所事事——因为贫穷或无知,或者因为他们很知足——因此相当一部分意志消散在空气里”[3]28,而阿季卢尔福也正是以这种意志集合体的身份出现的。并且,为了突出这一点,作者还有意使用了二元对立的手法,在阿季卢尔福身边设置了古尔杜鲁这样一个“活着但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人”作为对比。[3]23他是一个没有主体意识的存在,已经迷失在客观世界中。他看见鸭子,就认为自己是鸭子,学着鸭子的样子跟着鸭群扑进水塘;看见青蛙,又认为自己是青蛙,跟着青蛙一起跳跃;甚至在埋葬死人的时候,自己也随之跳进了坑里,想让死人来埋葬自己。并且,古尔杜鲁只是他众多的名字中的一个,“可以说,名字只是在他身上滑过,从来不能粘住。对于他来说,无论怎么样称呼他都是一回事”[3]23。由此可见,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个有趣的组合看作是堂吉诃德与桑丘在“现代寓言”中戏仿式的翻版,他们两个最大的区别便在于“一个没有生理个性,一个没有意识个性”[3]133。
而也正是由于阿季卢尔福表征了自我意识的原型,所以,他能够为在迷失中想要寻求突破的人们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指引,而也只有他能够用纯粹精神性的力量带给放荡成性的普丽希拉一种前所未有的美的享受,并捕获她的芳心。而同样是作为骑士的郎巴尔多则更是以阿季卢尔福为榜样,迫切希望与他相逢,因为在他心中,始终萦绕着诸如“明日夕照时我将是什么样呢? 我将经受住考验吗?我将证实自己是一个男子汉吗? 我将在走过的大地上留下自己的一道痕迹吗?”[3]41等类似的困扰。他想要借助于阿季卢尔福的存在,在实践中追求生存的证明,确立自身的意义。并且,就连受人追捧的女骑士布拉达曼泰也出于对骑士精神的景仰,渐渐爱上了阿季卢尔福,而对郎巴尔多热烈的追求采取一种视而不见、不管不顾的态度。但虽然如此,阿季卢尔福毕竟是一个没有肉体依托的空洞存在,强烈的自我意识一旦脱离了具体的生命本体,很有可能因被任意的攻讦而引发自我毁灭。正如裴亚莉教授所言:“生命的实质以及命运的塑造是包括身体的建构和思想意识的建构两方面的,作为入世的人,既不能忽视身体的欲求,也不能全然保持出世。”[4]44所以,阿季卢尔福在寻求骑士名誉合法性的过程中,以将自己的盔甲委托给朗巴尔多的方式完成了精神与肉体的和谐与统一,完成了身体和思想意识两方面的建构。
结语
至此,我们通过对《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的细致梳理,为三部作品勾勒出了一条贯穿于其中的完整线索,卡尔维诺通过描写这三个主人公异乎寻常的经历,始终关心着人类生存的本质问题,思考着个体自我如何在荒谬的处境中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并进而协调灵与肉的复杂关系,就像卡尔维诺所指出的那样:“凡让我们放弃我们自己一部分的必是负面的”[5],无论这三个人物形象的最终结局如何,他们都是最先尝试抵抗异化,寻求完整的先驱,他们的努力并不是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突破原有生活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以别样视角观照人生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