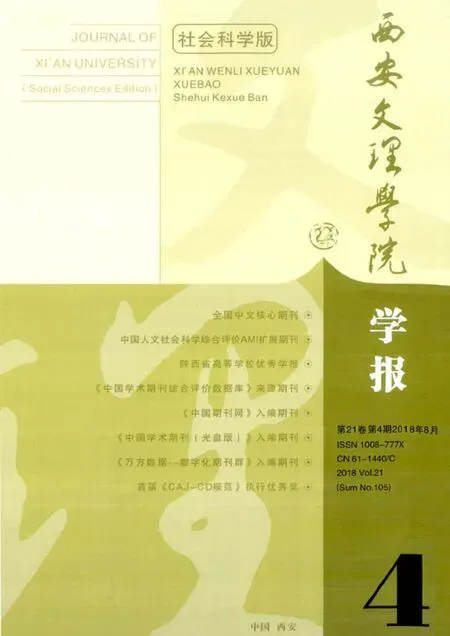唐代官吏奸罪之考察
林晓炜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性行为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正如《孟子·告子》所言:“食、色,性也。”[1]但人类社会的性行为必须受到道德、法律等社会规范的合理规制。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府官员的不当性行为若不受法律的强力约束,对于国家、社会与人民都将贻害无穷。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对传统中国之官吏性犯罪与反腐败问题进行分析,能为当代刑法打击公职人员性犯罪、保障民众的根本利益与维护国家政权的廉洁性提供有力的镜鉴。
一、唐以前官吏奸罪之嬗变
“奸罪”实为性行为犯罪,传统中国之可考律令都有关于男女非法交合之规制条款。例《唐律·杂律》有如下条文:“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者,各加一等。”[2]530但需注意的是,秦汉律及唐律中也有部分条文将“奸”字定义为非法或罪恶的行径,例如诈伪、劫掠等。秦《法律答问》中有“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的说法;《唐律·卫禁》亦载:“诸缘边城戍,有外奸内入,(谓非众成师旅者)内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觉,徒一年半;主司,徒一年”[2]194。显然这里的“奸”并非指男女奸淫问题,这与后世所通识之“奸罪”并不相符。溯源“奸”字之意涵,据《释名·言语》载:“姦,奸也,言奸正法也”;《集韵·删韵》云:“奸,犯淫也”;《说文解字》:“私逸也,通作淫”;《尔雅·释言》:“逸,过也”;《广雅·释言》:“逸,失也”[3]。据段玉裁解释,古语中“奸” 与“姦”字本意不同,“奸”是指“放逸”,即放纵之失;从《释名·言语》可以看出,“姦”字本身表示的是“违法”“罪恶”之意,实际是名词,换句话说,凡违反一定社会秩序之行为皆可谓“姦”。当然,无论是“奸”还是“姦”,其本质上都是非法行为,因此两字的含义也逐渐趋同。实际上,现在汉语中“内奸”“奸诈”等词显然与性犯罪无涉,因此研究性犯罪问题,还须对“奸”字做限缩性解释,明确其为男女间不正当性行为。
按照冨谷至先生的观点,秦汉时期的法律对于男女间性行为的规制限于四种:强奸已婚妇女或与之和奸,居父母丧时犯奸,近亲之间的性交,庶人与奴婢或主、奴之间的性交。[4]汉律并未将未婚者的通奸行为视为奸罪。汉以后随着法律儒家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人们对于涉奸犯罪的看法与观念才发生了变化,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对男女越界交合的容忍度愈来愈低。但囿于成文法典的散佚,对于掌握国家政权的官吏群体违犯“奸淫”条文该当如何处置,其与常人犯之入罪、处刑有何差异,从唐以前历代史料中尚无法清晰辨明,故有必要将研究视角投至中华法系的精华——唐律。《唐律疏议·杂律》明确区分了不同的犯罪主体、犯罪行为、犯罪情节乃至共同犯罪等构成性要件,以及免责条件等违法阻却事由,也规定了各主体违犯奸罪的处罚细则。因此对于官吏奸罪问题便藉由下文进行探究。
二、唐代官吏犯奸之罪与罚
(一)犯奸之罪
1.监守内奸罪
本罪之刑名及法律后果自唐时乃见诸史料,唐律中规定:“诸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妇女以凡奸论。”[2]534
(1)犯罪主体:本条罪名中的犯罪主体为“监临”“主守”者,那么何为“监临”“主守”?对此,《唐律疏议·卫禁》明确论述:“诸称‘监临’者,统摄案验为监临。”其疏议曰:“统摄者,谓内外诸司长官统摄所部者。案验,谓诸司判官判断其事者是也。”[2]150谓“统摄”者,乃一部内总管组织、人事之政务官,如掌中央六部之尚书或地方州刺史、县令等,亦可谓“官吏”词中之“官”;称“案验”者,乃主管某事之事务官,如尚书省侍郎、郎中等;县之县丞、主簿等,亦可谓“官吏”词中之“吏”。此外,“谓州、县、镇戍折冲府判官以上,统为监临。”[2]150无论是“统摄”还是“案验”皆为一定人群之监临官。同时,律文载明“临时监主”违犯本罪则视同“监临之官”。此处“临时监主”是对特定的行政事务与特定人群进行管理的人员。何为“主守”,疏议曰:“主守,谓行案典吏,专主掌其事及守当仓库、狱囚、杂物之类。虽职非统典者,谓非管摄之司,临时被遣监主者,亦是。”[2]151-152换言之,主守即亲自主掌其事之典吏。该级别的官吏在唐代的行政体系中已享有一定的职官权力,可以便捷地利用职权徇私枉法,因此唐律将此类监临官纳入规制范围。
(2)犯罪客观方面:本罪的犯罪对象为“良人”,即监临官统辖范围内的良家百姓。若监临主守者在任职期间奸部民便成立本罪。由此也可以看出,若官吏与部民和奸或强奸行为发生在其任职期间外,虽然已构成奸罪,但可不加奸罪一等,以示内外有别,为量刑提供依据。
2.监临娶所监临女为妾罪
在婚姻的合法性层面上,唐代特别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官于所统属官亦同。其订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5]律曰:“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女家不坐。”其疏议曰:“‘监临之官’,谓职当临统、案验者,娶所部人女为妾者,杖一百。为妾属娶者,亦合杖一百。亲属,调本服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既是监临之官为娶,亲属不坐。若亲属与监临官同情强娶,或恐喝娶者,即以本律首从科之,皆以监临为首,娶者为从。‘其在官非监临者’,谓在所部任官而职非统摄案验,而娶所部之女及与亲戚娶之,各减监临官一等。女家,并不合坐。其职非统摄,临时监主而娶者亦同。仍各离之。”[2]289本条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1)犯罪主体:本罪的犯罪主体一为“监临之官”, 如前文所述,即为“监临”“主守”者。一为“在官非监临者”。区分“监临之官”与“在官非监临者”的主要意义在于量刑,而不在于确认犯罪是否成立。但本罪的一大特点便是增加了针对“为亲属娶者”的规定,因此需要对 “亲属”之范围进行界定。唐律中之“亲属”概念显然来源于魏晋律中之“准五服以制罪”条,尤其是西晋《泰始律》中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6],根据“五服”概念推知,亲属指缌麻以上亲和大功以上姻亲之家。于本律,亲属指斩衰、期、大功、小功、缌麻五服之内亲;斩衰、期、大功三服内亲结亲的婚姻之家与外祖父等外亲。由此可以看出,唐律本罪所划定的犯罪主体范围十分广泛,从监临官本人到其斩衰、期、大功、小功、缌麻五服之内亲,牵连甚广。除此之外,本罪的行为主体还涵盖了“行求者”、主婚者、媒人等关系人。
(2)犯罪客观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唐律针对监临官娶部民女为妾设置了不同的犯罪形态。首先,从法律文本上看,“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妇为妾”可根据字面解释为一般语义下的“娶”。该情形中双方相互达成合意,与“和奸”有类似之处。随后疏议进一步阐述:若监临官及其亲属强娶或恐吓,则“以本律首从科之”,说明此时监临官对于女性施加了暴力或恐吓行为,因此女性对于与监临官之间的男女关系已无法选择,监临官实施该行为则视为“强奸”。其次本律还有文:“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即区分“枉法”与“不枉法”,主要意义也在于量刑。此外,唐律对于官吏娶部属妻、妾及女者,仅要求官吏以“枉法”为目的便构成本罪,而不考察官吏是否确实进行了枉法裁判。
(二)犯奸之罚
1.监守内奸罪
疏议曰:“监临主守之人,于所监守内奸良人,加凡奸一等……若奸无夫妇女,徒二年;奸有夫妇女,徒二年半。”[2]534而凡奸的量刑规定为:“诸奸者,徒一年半;……强者,各加一等,折伤者,各加斗折伤罪一等。”[2]530-531综上,监临主守于内和奸所监临女徒二年,若强奸更加一等,徒二年半。令人惊讶的是,《唐律疏议·名例》中有如下规定:“其杂犯死罪,谓非上文十恶、故杀人、反逆缘坐、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中死罪者。”[2]54可见,官吏犯监守内奸之罪最高可判处死刑,当然此针对的必是强奸情形而非和奸,但足以证明唐律对本罪的量刑之重。
唐律对于官吏犯奸行为的规制远不止于此。自汉末魏晋以来,随着大儒阶层逐步掌握政权,传统形式法律观向实质法律观再向新形式法律观的转型,士大夫群体的政治地位在此过程中有了极大提高。有学者指出:“六朝贵族的自立性很强,并不依附于王朝权力,这一倾向可以说十分浓厚,难以否定。”[7]唐律将议、请、减、赎当作为法律适用的重要规则,享有应请、应减特权的官吏,犯罪多可减一等处理,然而犯监守内奸者不得减等。“流罪以下,减一等。其犯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律”[2]38;对于涉案妇女而言,律条亦作相应调整:“妇女以凡奸论”[2]534,即比照奸罪“和奸无妇女罪名”条中“强者,妇女不坐”[2]533论。官吏若对妇女实施“强奸”,则妇女无疑是被害人,对预防犯罪结果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自然不应受到惩罚;但若官吏对妇女“和奸”,说明此时妇女对于官吏的犯奸行为也提供了物质或心理上的推动力,因此可谓奸罪“共犯”,这时妇女是要受到惩罚的。
2.监临娶所监临女为妾罪
违犯该罪所适用的规范如下:“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其在官非监临者,减一等。女家不坐。其疏议曰:‘监临之官’,谓职当临统、案验者,娶所部人女为妾者,杖一百。为妾属娶者,亦合杖一百。”[2]289根据法条,该罪之打击范围还包括监临官之缌麻以上亲和大功以上姻亲之家,与现行刑法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本条罪状系为预防监临官因收受性贿赂而枉法擅权而设,就渎职行为而言重在事前预防。故对官吏之量刑较监守内奸为轻,对女方家长也无处罚。
本罪还对“行求者”、主婚者、媒人等明确了量刑规则,律曰:“行求者,各减二等”。这是在“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的基础上减二等处刑。同时,对涉案妇女的规定往往是免于处罚,即便为“和”娶,“妻妾及女理不自由,故并不坐”[2]289-290,但此时的犯罪结果已经发生,虽然是否追究妇女的刑事责任有待考察,但对于已经造成的危害结果必须予以矫正,即男女各“离之”。
从涉案妇女角度而言,这样的法条亦可谓“衡平”,若官吏采取“强”的手段,不论其违法行为涉及的是“娶”或“奸”,妇女皆“不坐”。而若是“和奸”行为,对于同案妇女要追究刑事责任;但若是“和娶”,则女方可免予处罚,只惩治主婚者、媒人等。
由此观之,唐律对于监临官员的性腐败行为规定细密、处罚颇重,而对妇女实行惩免也充分体现了唐代立法技术的高超。
三、唐代惩处官吏奸罪的法制实践考察
(一)赵孝信监守内奸案
“赵孝信妻张,有安昌郡君告身。其夫犯奸除名,主爵追妻告身。张云:‘夫主行奸,元不知委,不服夺告身事。……且赵孝信身任折卫,爵班通贵,朝仪国范,顺亦应知。自可志励冰霜,心齐水镜。岂得监临之内,恣彼奔。无存秉烛之仁,独守抱梁之信,贞清莫着,秽浊斯彰,败俗伤风,此而尤甚。但奸源已露,罪合除名,除名官爵悉除,资荫理从斯尽。’”[8]本例中赵孝信犯监守内奸之罪,按律当“除名”,即削夺其全部官职与爵位。由于赵孝信已然成为白丁,其妻张氏的郡君告身乃受荫而来,因此其资格也应被剥夺,夫妻二人的所有告身均被追毁。
(二)郡守求娶部内之女案
“得甲为郡守,部下渔色。御史将责之。辞云:‘未授官已前纳采。’”判词如下:“诸侯不下,用戒淫风;君子好求,未乖婚义。甲既荣为郡,且念宜家,礼未及于结褵,责已加于执宪。求娶于本部之内,虽处嫌疑;定婚于授官之前,未为纵欲。况礼先纳采,足明嬿娩之求;聘则为妻,殊非强暴之政。宜听隼旟之诉,难科渔色之辜。”[9]本例引自唐白居易之《百道判》集,材料所称某郡守因涉嫌于其任职期间求娶部内之女而遭御史弹劾。因为该郡守虽在其任职区域内娶妻,然而其娶妻的事实发生在任职之前,故该郡守渔色之举 “难科渔色之辜”。
以上两例涉及唐代官吏监守内奸、求娶部内之女两项罪名,前者为以敦煌出土文献为代表的唐代判例集,该类出土文献中对官吏奸罪的记载比较明确,案件事实、法律适用及分析基本得到完整的呈现。后者虽非出于实际史料,但在社会生活中亦必然有所反映。限于篇幅,各类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官吏犯奸罪之案件无法一一列明,但涉及官吏奸罪的“文本中的法律”和“行动中的法律”相差不大。
四、唐代规制官员奸罪体现的时代特征
(一)明法治吏色彩浓郁
官吏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官吏队伍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便深刻阐释了吏治对于政权稳定的直接作用。至圣先师孔子曾对向其问政的季康子答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10]法家思想家韩非子亦认为:“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11]权色交易引发臣僚奸邪,而吏治腐败必祸及万民,进而易导致下层民众走上暴力反抗专制政权的道路。及至唐代,随着大一统国家体系的建立与社会经济的稳定,唐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逐步成型并走向成熟,目睹隋朝统治因吏治腐败而崩溃的唐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济之民,吏也。故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驰而败矣”[12]。通过法制手段强化吏治,通过吏治清明以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专制君主的统治效能便成为当时主导的立法理念与司法原则。因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盛唐统治者大力整饬吏治、激浊扬清,于是“官吏多自清谨”。
(二)纳礼入律的政制观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礼教思想逐步成为历代王朝正统的治国理念与立法的指导思想。特别是汉末以来,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力量得到了极大加强。[13]而儒家法律观的本质即是礼法观,法律儒家化在很大意义上也就是引礼入法,因此在魏晋至隋唐的立法活动中掀起的引礼入律新高潮便不难理解。法律儒家化自两汉时起步,经魏晋南北朝诸如“准五服以制罪”“八议”“官当”等制度得到强化,到唐代最终完成“出礼入刑”,儒法结合。《唐律疏议》卷首中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处的“德礼”指的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即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名教观念与道德准则。“儒家的纲常名教与伦理道德渗透到《唐律》条文中甚至洋溢在疏议的字里行间,使整部《唐律》及疏议弥漫着宗法伦理色彩。”[14]唐代立法者严格约束官员的性犯罪行为,除了要求官吏遵纪守法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儒家伦理道德,特别是圣人对于家庭伦理的要求。《唐律》对于官员犯奸行为的定罪、量刑皆比照纲常名教犯罪,而非常规的职务犯罪条文,便深刻说明《唐律》“一准乎礼”的形式特征。
五、唐律惩治官吏犯奸行为的价值分析
(一)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官吏的性腐败行为
在吸收秦、汉、魏、晋等中原王朝及部分游牧民族政权法律的基础上,唐律体系化地规范了官吏并加大了对官吏奸罪的打击力度,对于官吏借用手中权力对妇女实行犯罪进行严厉打击,并根据犯罪情节、对象、后果等给予科学的惩处。这一规定对监临官吏的言行起到很大的约束,众所周知,监临官吏对于其部内之人事掌握着政治、经济等各项特权,无论是打击监守内奸还是禁止官吏娶部内之女,都能有力地防止监临官员因贪图女色而滥用职权、因人设法、损害政府的廉洁性与制度的严肃性。官吏的腐败与滥用职权行为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对于社会风气的净化极有好处,在传统中国漫长的人治时代中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唐律重惩官吏犯奸行为,也弘扬了“明法治吏”“存百姓”等古圣先贤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之理念,使民众得享宽闲,对于饱受监临官吏欺压的下层民众而言,即使不说安居乐业,至少也能享受一定的承平之治,这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缓和阶级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进一步完善了唐代法律规范体系
随着唐王朝的发展步入正轨及相关案件的爆发,为满足高层统治者加强对官吏的控制、维稳的需要,加大对官吏及其他特殊主体犯奸的打击力度势在必行。这就需要立法者通盘考虑不同的性犯罪情形,有针对性地制定惩处措施,例如根据犯罪的主体、动机、情节、后果、主观恶性大小等情形来给予犯罪者相应的处罚,实现对各特殊主体涉奸犯罪的“精确打击”,有针对性地惩处各级官员的犯奸行为,真正实现预防职务犯罪的价值取向与保障妇女的性权益并进而消弭人民群众对于帝制反抗的有机统一。为此,以长孙无忌为首的“立法委员会”针对奸罪问题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法规,进一步完善了唐代刑法规范,推动了唐代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也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统治秩序和统治环境,促进治吏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对后世相关法律规范的制定产生了极大的借鉴意义。历史已然证明,传统中国法于唐以后之宋、明、清,历千载之演进,然于官吏奸罪之科条可谓一脉相承,这也充分展现了“性腐败”入刑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总之,以唐律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法对官吏犯奸科条完备,意即“完”;量刑适中,可称“善”。以此观之,中国古代立法对惩治性腐败的规定、制度呈现出体系完善之特点。而此种种,皆为现今性腐败立法提供了一个较完美的“工作规则”。
六、结语——“以法止过”优于“口诛笔伐”
唐律对于官吏性腐败的罪与罚,远比当代中国刑法针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行为的调整范围大得多。当前,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官员的腐败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案件当事人“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字眼屡见报端。相较于传统的权钱交易,性腐败往往为人所忽视,事实上,所谓“贪污”,既有牟利之义亦有牟色之义。古往今来,贪色者必贪财以供养美色,两者恶性循环,密不可分。因此,凡惩治腐败者,防色之贪尤为重要,对官员的性腐败行为严加防范、防微杜渐,正是预防与惩治腐败的关键。
总之,唐律对于官员性犯罪行为的规制,无论是调整范围还是行为结构,抑或是法律后果,都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学术与现实价值。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在法治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不仅要积极探索和创新,更要对过往经验进行总结思考。这正是当代中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