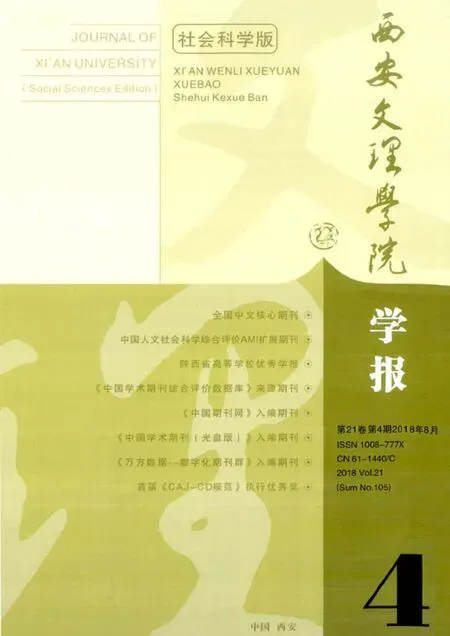再论弗洛伊德影响下的张爱玲创作
高莉娜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西安 710119)
赵学勇先生曾指出:“张爱玲作为一个传奇的女作家,她的传奇决不仅仅是对古典文学中‘传奇’传统的简单吸收和截取,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精神的演绎。传奇中蕴含的‘不奇’——永恒的人生和人性,才是她作品真正的指向所在。”[1]张爱玲的作品标新立异,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的疯狂与变态,男主人公的卑怯与伪劣,无不充斥着情欲和性本能的气息,在《对照记》中张爱玲有过这样的感慨:“其实是个弗洛伊德(以下简称弗氏)式的错误。‘心理分析宗师弗氏认为世上没有失误或偶尔说错的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2]潜意识学说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部分,张爱玲注重借鉴哲学理论尤其是精神分析学的运用,其创作呈现出浓郁的精神分析学的色调。
一
弗氏的欲望说中介绍了人的欲望是在潜意识里隐蔽,它不会赤裸裸地显现出来,而是通过人的无意识的动作间接暗示。所以在弗氏看来没有所谓的口误和失态,这些看似反常的表现正是人潜藏内心里最真实的诉求。纵观张爱玲的作品,就可以发现她惯用的修辞手法主要是隐喻和象征,一贯的文风是苍凉悲情,正所谓“文如其人”,作家的创作风格与自身的品性格调有莫大的关联,性情幽闭的张爱玲不喜繁华与热闹,忠于阴冷与灰暗,所以她以参差不齐的对照手法选择具有丰富蕴含的意象来抒心中之块垒。
中国诗学一向重视“意”与“象”的关系,酷爱中国传统诗歌的张爱玲,在文学创作中将这一关系处理得恰如其分。月亮,在日常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一旦被赋予一种情感,它就显得朦胧而不可捉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亮的意象往往是一种对相思之情或思乡之情的美好感情的寄托,也是一种女性阴柔美的象征,但西方文化的意蕴中月亮更多的却是不洁的寓意。西蒙娜·德·波伏瓦曾说:“女人的月经周期奇怪地与月亮运行周期一致,于是月亮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反复无常的。”[3]从张爱玲的小说中关于月亮这一意象来看,她对月亮有个人的理解。因为她表现的月亮就如西蒙娜所言的,带有冷酷和死亡的色调。
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月亮并非单单是朦胧情感的象征,在同为抬头看月亮的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内心却汹涌着不同的情感激流。范柳原是情感至上,在月光隐约的映照下打电话挑逗流苏,想打探对方心意是否与己相投,而这边的流苏表面上是用理智在克制自己,但在潜意识中知道自己是喜欢他的,然而她已经不是怀春少女,她的喜欢是以结婚为前提的,所以不能轻易给出答复。重重顾虑让她看不清真切的月亮,只是感觉到一股散发着寒气的有着绿光的月亮,她感觉到自己在惘惘中受到了威胁。再次写到月亮是在流苏与范柳原快要分开时,在船上,二人在月光之下的两人暗自较劲,身体的距离永远消除不了两颗心的隔阂,柳原首先在心里为自己筑起了一道墙,他不仅能抵得住天边的那抹月色,而且一定也可以抗拒甲板上的“月色”。想爱不敢爱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衡量对方是否值得,因此在这里就造成了某种抵制与压制。月亮在文中的作用虽然微妙,但却是二人在无声中与自己的情欲和无意识作斗争的最好见证。月亮虽不明媚,却足以照出他们藏在内心深处的阴暗与懦弱,参透他们步步为营之下的精明的谋算与诡计。
张爱玲笔下的月亮的蕴意是多重的,在流苏和范柳原的世界里月亮是情欲的化身,但在《金锁记》中它冒着一股冷酷绝望的杀气。意象的整个基调是与文章协调一致的,这里的七巧是人格缺陷的不完整的,所以文中的月亮也是被吞噬了的,故事给人以沉闷压抑的气氛,阴森森的月亮更增加了一层恐怖感,就如雷雨为了映衬繁漪狂风暴雨般情绪,窗外阴森恐怖的鬼一样的月亮是七巧的再现。紧接着在月亮的刺目灼烈的照耀下,芝寿再也受不了这非人的魔窟,于是在这冷酷阴森的月亮下,以上吊来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月亮是七巧的化身,它的被蚀导致了其对亲人疯狂的报复,所以在月亮的张望下也即七巧的残酷迫害下,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被活活扼杀。
至此,张爱玲对月亮这一意象的大胆呈现,既可以与代表情爱的欲望相关联,亦可以赋予死亡的特殊含义。对于月亮这一系列怪诞却又不失真的寓意是张爱玲结合西方美学的独创,是对弗氏欲望说的独到运用。除此,张爱玲对色彩和绘画有异常的天赋和敏锐的感知,她经常赋予普通平常的“象”以某种象征性的意义,从而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和命运的“意”。张爱玲笔下的意象巧妙地结合了客观物的“形”与“色”,既要求尽力表现鲜明的“色”上,又要达到“形”的独特。
在弗氏精神分析法看来,红色是欲望的涌动色,往往是富有激情、诱惑、情欲的代表,而花朵则是女性的象征。更进一步讲,弗氏对于花这一形象的理解更为大胆和奇异,说它是女性阴槲的隐喻。红花的艳丽醒目的“红”与形状独特的“花”二者完美的合结,就像是一根无形的线在暗中牵动着人的情欲。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用这一意象来暗示恋人之间的情欲涌动,黑夜里,流白苏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的直觉告诉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4]65,此时,再也不可压抑的情欲有喷薄而出之势。这里用红得过分、红得怕人的花儿表现了貌似理智和深沉的两个人不能阻挡情欲来袭的洪水,内心真实的痕迹通过外在的物象表达得真真切切,让人感觉到了一股本能欲望的勃发。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张爱玲更是直接用“红”和“白”来表示两类女人,对此,有学者认为:“张爱玲以红白玫瑰分别代表着热烈的、不道德的女性和圣洁的、道德的女性。”[5]这无形中契合了弗氏关于“红”与“花”的阐释和寄寓。在这部小说里,张爱玲不仅以鲜明而有深意的红白玫瑰作为文章的题目,在文中更是蓄意地安排了名为“玫瑰”的华侨女子和朋友之妻“王娇蕊”出现在振保寂寞空虚的情感世界里。
总之,张爱玲通过色彩与形象的完美搭配,再现了并非单纯意义层面的红花,用弗氏的精神分析法来暗指人对自己原始欲望的诉求,是性本能所要投射的象征,潜意识里红花是男性幻想的对象,是极具魅力的女性的化身。所以,在张爱玲的意象里,红花的出现是人对性本能需求的一种寄托和慰藉。
二
与弗氏学说重视心理分析的指向相似,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流露出对人物内心的透析和洞察。通过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法相结合,来表现人物的心理特征及其变化甚至变态。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写道:“微温的水就像有一根热空的管子,龙头里挂下一股子水一扭一扭流下来,一寸寸都是活的。”[6]非常简短的一句话,三两个词语就将振保内心深层隐秘的情欲骚动和潜意识心理完整地体现出来。随后振保竟对溅在手背上的肥皂沫紧绷绷的感觉留恋不已,又在浴室里拣起娇蕊的头发并下意识地装进裤袋里,这一切使他变态的意淫起来。只觉得自己浑身躁热,血脉偾张,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可笑,就将那团头发赶快丢进垃圾桶里。这又一次展示了振保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也证明了面对娇艳的女人,他难掩自己的性本能的冲动。
弗氏精神分析法认为人的强烈的性欲在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他就会将这种情形转移到物上,亦即“恋物癖”。振保极力压制眼前的诱惑,但是在潜意识里有一股难以遏止的力量在寻找出口,所以他就借与自己性幻想的对象有关的东西来间接表达自己的情欲。张爱玲通过佟振保在娇蕊浴室里的一系列动作间接折射出他的内心活动,表现了人的非理智以及潜意识对人的无形的控制力,人物本身的内心活动的流露将人性中本能的欲望表现出来。
此外,《倾城之恋》中,张爱玲以她独特的艺术手法将流苏的心理转机以及潜意识里的对情欲渴望刻画得逼真而传神。当流苏站在镜子面前傲娇地端详自己娇小的面孔时,她的心里是窃喜的,她不觉得自己是年过三十离过婚的女人,因为她还是美丽的,所以在心里她有信心把自己嫁出去而且还会嫁得好。对于家人对她的嘲讽,她表现出鄙夷和不屑,因为在自己妹妹的相亲舞会上,她一展风采便赢得别人嫉妒又羡慕的眼光。就算抢了原本是妹妹的对象她也不觉有愧,她要追求的是自己的幸福,旁人是顾不得的,内心的自私阴暗暴露无遗。这正是弗氏精神分析法中的人格论中“本我”的浮现,流苏以自己的幸福快乐为原则,无视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为求得个人生存,流苏的本我面目在此暴露无遗。文本中四爷那古老的胡琴对于心驰神往的流苏是听不进去的,对她而言殿堂舞曲才能紧扣她的心,力求摆逃传统古琴的藩篱,追逐新时代女性的步伐是流苏的内心呼唤,最后终于阴阴一笑明白了自己的归处。这里的胡琴也好、节义也罢,都在流苏阴阴的一笑中消失殆尽,她不想再被所谓的伦理道德所绑架,不愿违背内心的意愿去遵从所谓的忠孝节义。
“自我”是主体面对周围的客观坏境和外在规范约束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人,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传统的宗族礼法能约制流苏在他人面前的行为举止,却无法鞭及她作为一个自然人最本真的内心渴求。正如孟子所言:“食、色,性也。”[7]孔子也认为凡是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流苏作为一个健康而美丽的女性,她有正常人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的要求。所以她决定作真实的自我,大胆地响应内心的呼吁,此时流苏的“本我”压倒了“自我”,这既揭示了流苏当时所处的不得不为自己寻谋出路的艰难困境,也是张爱玲对弗氏人格理论的形象化和传神化。
由此视之,张爱玲通过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的感受,披露了人生存的困境以及人性险恶的一面,这与弗氏在人类心理层面的开掘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
弗洛伊德认为生的本能可以使生命获得新生, 使人类能代代繁衍,生生不息, 但是在精神上,人类有追求永生的欲望,这就会导致心理失衡。张爱玲的作品大都浸染着一股浓郁的感伤,她以犀利的笔锋和敏锐的目光洞察人性,审视人生,这些作品都透露着人如何摆脱人格面具而又无法回归自我,最终迷失自我的感伤。
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8]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正体现了这一点。她笔下的人物“人不人,鬼不鬼”的,从母亲到儿女再到兄弟没有一个是温情的,都好像疯了似的。相爱的人不敢用真心,即使情意绵绵也只是以有所附丽为筹码。在她的世界里亲情是冰冷的,而爱情则是谎言,但这两种情感却是我们人生中最珍重和宝贵的东西,却被这样无情地撕毁。张爱玲悲剧的魅力就在于悲剧的情节契合了人类内心深处与欲望进行无休止的博弈状态。人是很难摆脱这样的情形的,所以我们在欣赏悲剧的时候,也是一种求同性的审美,并在文学作品悲剧人物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其实人活着就会感到痛苦,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能安于现状,永远都有尚未企及的梦想”[9],除非人禁欲或者否定了生命的追逐,也就是所谓的“死亡本能”——人接受命运安排好的一切,不再进行徒劳的挣扎,不再苦苦寻求出路。
张爱玲虽与鲁迅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倾向,但她与鲁迅一样,对世界对人性的看法也是绝望的,只是与鲁迅热烈且悲壮的深情不同,张爱玲显示的是同情的理解和苍凉的启示。
在弗氏看来,“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是人类的两大基本本能。生本能,它富于建设性,它的“目标就在于不断建立更大的统一体,并极力地维护它们”,死本能,它富于破坏性,“目标是取消联结,故而带来毁灭”[10]。生本能与死本能二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人类的生存和延展需要生本能与死本能是同存同行的。《半生缘》中顾曼璐的求生本能促使她不择手段地牺牲妹妹,千方百计地破坏曼桢的美好爱情,她甚至让自己的丈夫强暴曼桢,为了自己的利益,曼璐丧失了良知,牺牲了亲情,而结果非但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相反,自己却一步步走进了绝境,终于一切都是空。还有白流苏、曹七巧等都是为了生存,人的本性之恶竞相迸发,仿佛要用尽毕生的精明与算计,为自己编织一个安稳的黄金梦抑或是爱情梦,然而结果是在惘惘的威胁中明白了一切的挣扎到最后都归于零,人的命运始于激情没于凄凉。
张爱玲用冷静淡漠的语言将人的两大本能缓缓道来,人这种生物扣合了生命本性发出的爱恨情仇后终归回到虚无蛮荒的空寂中来。张爱玲笔下的故事往往保持了一致的冷漠的语言和苍凉的韵味,从而使整个篇章都浸染在一股淡漠阴郁的哀伤中。比如《金锁记》结尾:“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4]45“沉”“死”都是对一种事物或生命的终结。正如张爱玲对胡兰成曾倾心相付却终遭离弃的凄清与悲凉,彼时的张爱玲虽未以死明志,一句“我将只是萎谢了”其实比死更甚,她的生命已失却了原始的冲动和前驱,当生命的精力被内在无尽的欲望消耗殆尽时,生本能就悄无声息地退隐于死本能的身后。
显然在张爱玲的各式悲剧中,让我们体会到了人生的冲突和痛苦,看到了欲望的悲剧,从而对大千世界避之不及,于是不再有欲望。这与弗氏的死亡本能是一致的。弗氏认为,人类欣赏悲剧是出于死亡本能,死的本能是人回到一种无生命的状态,无欲无求,是一种非存在的形态。但是,张爱玲的悲剧色彩与弗氏的死的本能并非要人放弃对生命中美好东西的追求,虽然人活着就会与各种欲望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但也恰是这样不屈服于命运的顽强精神才造就了人类的今天,才有可能继续开创文明的长河,这是张爱玲对悲剧与人生独特的审美方式。
结语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受到弗洛伊德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张爱玲所表现出来的家庭亲情的消解、恋人的猜忌与背叛、人性的变态等可以理解为她本人生活经历留下的阴影所致。但从更宽广的一面来说是张爱玲大量地接触西方文化,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并根据个人的审美眼光选择了一种审美表达,而此时正处于五四高潮的弗氏精神分析法的审美情绪是张爱玲的不二选择。她感情的闸门由此打开,一方面是用文学创作来弥补心理的创伤,另一方面以她独特的视角来审视社会,并直面人生,触及人的灵魂。她不仅囿于个人情感的宣泄,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超越与升华,运用精神分析来剖析特定社会历史情形下普遍的变态的心理与畸形的人伦关系,进而探索人性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