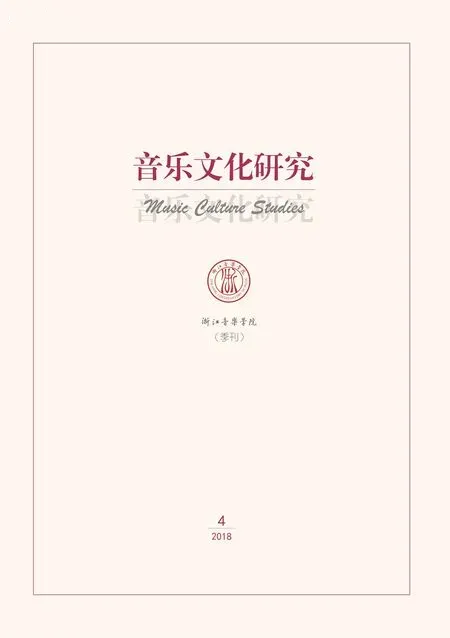敦煌壁画中所见鼗鼓与鸡娄鼓兼奏图论考*
刘文荣
内容提要:鼗鼓本中原之器,鸡娄鼓源出西域。在莫高窟中,鼗鼓的绘制始出于北周石窟,鸡娄鼓始出于初唐石窟,二鼓本不兼奏。随着初唐九部乐、十部乐的设置以及大量西域胡乐的进献,左手播鼗,左臂腕托鸡娄鼓,右手拍击或持杖而击的兼奏形式在敦煌初唐窟以来得到了大量的表现,其出现的背后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二鼓在莫高窟中的兼奏始于初唐,兴于盛唐,盛于中唐,终于晚唐,共绘制五十余幅,使莫高窟成为保存有全国乃至全世界鼗鼓与鸡娄鼓兼奏最多的地方。本文以图证史,对莫高窟中出现的鼗鼓与鸡娄鼓兼奏图,从其演奏形态、莫高窟各时期的表现情况、龟兹乐的影响,以及与克孜尔石窟兼奏情形的比较出发,溯源探流、明本释末,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考论。
敦煌莫高窟本佛教石窟,在约492个石窟,四万五千多平方米的壁画中绘制了大量反映佛教因缘、本行、经变及佛经说法的图像。乐舞在佛经中被视为是礼佛的第九类供养,①故敦煌壁画中有大量反映乐舞内容的乐器图像。莫高窟鼗鼓图像始见于北周290窟东壁上部飞天伎乐中(图1),直至西夏、宋窟中仍有见于鼗鼓。鼗鼓乃中原汉器,具有悠久的历史。鸡娄鼓乃西域传来之乐器,非华夏旧器。莫高窟自初唐窟始,见鼗鼓及鸡娄鼓的兼奏,亦大量见于有盛大乐器组合及反映唐九部乐、十部乐信息的大型经变画中。以下结合相关典史文献记载,将鼗鼓与鸡娄鼓兼奏的历史背景及与莫高窟的图像印证作详细的考证。不揣浅陋,求教于方家。

图1 莫高窟290窟东壁上部北起第二身中的鼗鼓
一、莫高窟北周前的鼗鼓及演奏形态
莫高窟北周前未出现鼗鼓,但鼗鼓在中原汉乐中却早已兴盛,为了全面认识鼗鼓在莫高窟中的表现情况,在此,先对鼗鼓形象在进入莫高窟前的历史情况加以考释如下。
鼗鼓本华夏之器,史载早在远古帝喾高辛氏时,即有鼗的乐器。如《吕氏春秋·古乐》云:“帝喾命有倕作为鼙、鼓、钟、磬……鼗。”②且多以盲瞽乐师来演奏鼓鼗,如《周礼·春官·乐师》云:“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③被周代所奉为歌颂上德的六大雅乐舞中已使用了鼗鼓。如据《周礼春官》的记载,《云门》使用了雷鼗,《咸池》使用了灵鼗,《九韶》使用了路鼗。④
鼗亦是宫廷雅乐中较重要的乐器,见于《礼记·月令》载:“仲夏之月……命乐师脩鼗鞞鼓,均琴瑟管箫……自鼗鞞至柷敔皆作曰盛乐。”⑤并且周天子常赐贵爵们以鼗乐,如《礼记·王制》:“天子赐伯、子、男乐,则以鼗将之。”⑥
鼗鼓其器,即是今民间俗称“拨浪鼓”的前身。唐孔颖达疏“鼗鼓”曰:“鼗如小鼓,长柄,旁有耳,摇之使自击。”⑦鼗鼓从南宋时已成为货郎“吟叫百端”⑧的叫卖乐器了。(图2)

图2 南宋李嵩《货郎图》中的鼗鼓
关于鼗鼓的演奏形式,既可独奏,也可合奏,但更多的是与其他乐器合而奏之。在先秦雅乐中,鼗鼓常与磬一起演奏,如《仪礼·大射礼第七》载:“鼗倚于颂磬两纮。郑玄注:‘鼗,如鼓而小,有柄。宾至摇之,以奏乐也。纮,编磬绳也。设鼗于磬西,倚于纮也。’”⑨这在《诗·周颂·有瞽》所言“应田县鼓,磬鼗柷圉”⑩中也得到了印证。
鼗乐演奏的重要性一直影响并延续到后世宫廷雅乐中去,鼗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常常在乐始和乐终演奏。《文献通考》引陈旸《乐书·雅部》云:“景祐中,太宗诏太常,凡祀天神、地祇、享宗庙,宫架每奏降神四曲,送神一曲:先播鼗……凡乐终,播鼗、戛敔,散鼓相间三击而止。”⑪

图3 南阳石桥东关汉画像石中的播鼗吹箫图
至汉代,鼗鼓常与箫⑫一起演奏,这是莫高窟中大量表现鼗鼓与鸡娄鼓兼奏前鼗鼓最后一种呈稳定的合奏方式。在出土的汉画像石中,鼗鼓与箫的合奏有大量的体现。如南阳市石桥东关汉墓出土的画像砖(图3),图像中左侧二乐人正击建鼓而舞,鼓上饰有羽葆,右起第一个和第三个乐伎左手持箫,右手播鼗二鼓。唐河县湖阳辛店汉墓中也出现了右手播鼗、左手吹箫图。南阳卧龙岗崔庄汉画像石中亦有右手播鼗、左手吹箫图像(图4)。此外,南阳李相公庄汉墓许阿翟墓志画像石,以及山东济宁汉画像石砖,山东嘉祥、山东梁山、山东邹城、山东滕州、江苏沛县、江苏徐州、江苏睢宁、江苏铜山、河南新野、湖北当阳等,都出现了鼗鼓与箫兼奏的图像,并以河南南阳和山东最多。可见,鼗鼓与箫及其合奏是鼗鼓与鸡娄鼓兼奏前最常见的一种合奏方式,乃真正汉中原之乐。

图4 南阳卧龙岗崔庄汉画像石中的播鼗吹箫图

图5 《三才图会》 中的鼗鼓
莫高窟自北凉272窟起,有大量的西域乐器见于壁画的绘制中。北周290窟东壁上部北起第一身和第二身中虽出现了鼗鼓,但并不见与汉风式的箫合奏,而是与打击鼓类乐器合奏。北周290窟的鼗鼓为一柄一枚鼓,这与《三才图会》中的一柄鼗鼓形制类同(图5)。《三才图会·器用三卷》“鼗”条云:“小鼓以木贯之,有两耳还自击。鼓以节之。鼗以兆之八音,兆于革音,则鼗所以兆奏鼓也。”⑬北周窟的一柄鼗鼓还没有发展到与鸡娄鼓兼奏的二鼓鼗和三鼓鼗。虽然莫高窟初唐窟前有见鼗鼓的单奏形态,但是,更多的是鼗鼓与其他鼓类乐器的合奏,这体现了一定的西域龟兹风格。《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⑭

图6 莫高窟290窟中的鼗鼓
二、莫高窟初唐窟始——西域鸡娄鼓的东进
莫高窟自初唐窟始,直至盛唐、中唐、晚唐,鼗鼓不全是独奏了,而是大量与鸡娄鼓兼奏,常见的演奏形态是左手持鼗而播,左腋下夹或左臂弯夹鸡娄鼓体,右手或拍而击之(如图7、图8),或持杖而击之(如图9、图10)。此正是史籍所载“后世教坊奏龟兹曲用鸡娄鼓,左手持鼗牢,腋挟此鼓,右手击之,以为节焉”⑮出于敦煌莫高窟的图像印证。

图7 中唐112窟南壁东乐池中的鼗鼓与鸡娄鼓兼奏图

图8 晚唐85窟北壁东侧思益梵天问经变中的兼奏图
莫高窟中有大量此类鸡娄鼓与鼗鼓的兼奏(以下皆简称兼奏图)形态的表现,据笔者统计,多达五十余幅。(见表1)正因为龟兹乐部中鼗鼓与鸡娄鼓通常由一人兼奏,就连盛唐172窟、晚唐9窟壁画中“不鼓而鸣、自翔于天”的不鼓自鸣乐器中,鼗鼓与鸡娄鼓也绘制在一起组合成兼奏的形态(图11)。统表如下:

图9 盛唐45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中的兼奏图

图10 盛唐148窟东壁北侧药师经变南乐池中的兼奏图

表1

年代 窟号 位置 经变 备注中唐 201 主室南壁 观无量寿经变主室南壁 观无量寿经变中唐 231主室北壁 药师经变中唐 240 主室北壁 药师经变中唐 258 主室南壁 报恩经变中唐 359 主室南壁 阿弥陀经变中唐⑯ 386 主室南壁 阿弥陀经变晚唐 9 主室窟顶东披 弥勒经变 “不鼓自鸣”主室窟顶南披 观无量寿经变晚唐 12主室南壁 观无量寿经变北壁东侧 天请问经变晚唐 18 主室南壁 观无量寿经变主室窟顶北披 华严经变南壁东起 报恩经变、阿弥陀经变、金刚经变各经变1幅,共3幅晚唐 85北壁中铺 药师经变 上下乐池各1幅,共两幅北壁东起第一铺 思益梵天问经变主室南壁 金刚经变晚唐 138北壁西起 金光明经变、药师经变各经变1幅,共2幅晚唐 147 北壁西起 药师经变、金刚经变各经变1幅,共2幅晚唐 156 主室南壁西起 思益梵天问经变、阿弥陀经变各经变1幅,共2幅晚唐 161 主室窟顶南披晚唐 177 主室西壁 观无量寿经变主室南壁 阿弥陀经变晚唐 192主室北壁 药师经变主室南壁 阿弥陀经变晚唐 196主室北壁 药师经变
鼗鼓与鸡娄鼓的兼奏是鼗鼓与排箫兼奏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兼奏形态,莫高窟中保存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多的鼗鼓与鸡娄鼓兼奏图,也成为莫高窟壁画中最典型的乐器组合。兼奏图起于初唐,含三窟共有三幅,一窟一幅。盛唐稍兴,含五窟共六幅,其中148窟东壁南、北两侧均有,一窟两幅。中唐大兴,十一窟共十四幅,其中,112窟南壁、北壁,180窟东壁、南壁,231窟南壁、北壁均有,三窟含六幅。且中唐180窟与盛唐148窟皆是观无量寿经变与药师经变。兼奏图在晚唐走向极盛,十一窟共二十五幅。其中,147窟、156窟、192窟与196窟均一窟两幅;12窟与138窟一窟三幅;而85窟一窟7幅,为莫高窟中含鸡娄鼓与鼗鼓演奏最多的洞窟,除窟顶外,南壁共有报恩经变、阿弥陀经变、金刚经变,三幅经变中皆绘有兼奏图,且北壁药师经变中上下乐池汇有两幅,为历窟之最,鼗鼓与鸡娄鼓兼奏的兴盛令人叹为观止。

图11 盛唐172窟北壁不鼓自鸣鼗鼓与鸡娄鼓
兼奏图在莫高窟中的大量表现有其必然的历史背景。鼗鼓与鸡娄鼓的兼奏为西域胡乐的表现形式,西域音乐大肆集中进入中原朝廷,主要在初唐前的隋代。这与隋室喜好西域胡乐有极大的关系。隋虽历二世,但王室皆好西域音乐。文帝喜欢胡乐,“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⑰,文帝也常“龙潜时,颇好音乐,常倚琵琶作歌二首”⑱,文帝作歌所倚琵琶其实已为曲项四弦梨形琵琶,此正是史籍所载西域式的胡琵琶,龟兹克孜尔等石窟有大量绘制,莫高窟隋代洞窟中也有大量的西域式曲项四弦梨形琵琶。隋炀帝对西域胡乐更是极度痴迷,可谓穷奢极欲。《隋书·西域传》载:“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⑲另外,《隋书·音乐志》载:“(炀帝)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⑳而且“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管以上,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㉑。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河西走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披绵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迎候道左”㉒。可见,西域音乐在进入中原隋廷前,在敦煌河西等地已有大量流传。故此,莫高窟隋窟中有大量的西域乐器,且隋一朝在敦煌修建的七十余个洞窟中,其中与音乐有关的洞窟就有52个之多。隋室开放并蓄,积极接纳外族散乐的态度,使隋代在其短暂的执政时间里,音乐文化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也直接导致隋开皇初,始置了“七部乐”㉓,炀帝增设了“九部乐”㉔,至此,龟兹、疏勒等西域音乐大演于中原隋廷。
隋七部乐、九部乐之龟兹、疏勒乐的演奏中,已出现了鸡娄鼓,且隋七部乐中始设龟兹乐,疏勒乐为七部乐之外的杂乐。至隋大业年间,疏勒乐正式成为隋九部乐中的一部,不再是杂乐。《隋书·音乐志》载:“龟兹……其乐器有竖箜篌……鸡娄鼓、铜钹、贝等十五种。”㉕并且,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闬”㉖。
在隋九部乐中的疏勒乐中也出现了鸡娄鼓。《隋书·音乐志》载:“疏勒……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鸡娄鼓等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㉗疏勒乐中除笙、毛员鼓、都昙鼓、铜拔、贝乐器外,其余与龟兹乐皆同。
唐初,乐承隋制,至开元中,太宗增设十部乐,西域之高昌乐始设其中。《旧唐书·音乐志》载:“高昌乐……乐用答腊鼓一,腰鼓一,鸡娄鼓一……”㉘可以看出,在初唐始设入宫廷伎部的高昌乐中,亦使用鸡娄鼓。至此,史籍所载凡使用鸡娄鼓者,只见于西域来乐,且是龟兹、疏勒与高昌三乐,非为它乐所有。《文献通考·乐考九》恰有云:“鸡娄鼓,其形正而圆,首尾所击之处,平可数寸,龟兹、疏勒、高昌之器也。”㉙并且,《文献通考》是将鸡娄鼓列于“革之属胡部”乐器之下。可见,鸡娄鼓其鼓面平小,形器规整,乃圆而正之小鼓,专用于龟兹、疏勒、高昌之胡乐。

图12 初唐321窟北壁不鼓自鸣鼗鼓

图13 初唐341窟南壁西侧不鼓自鸣鸡娄鼓
不为兼奏的鸡娄鼓单只图像多见于不鼓自鸣乐器的表现中,如初唐71窟、初唐321窟(图12)、初唐335窟、初唐341窟(图13)、盛唐103窟、盛唐117窟、盛唐172窟、盛唐217窟、盛唐225窟、中唐236窟、晚唐9窟、晚唐85窟、晚唐156窟等。其中,除321窟、172窟与9窟鸡娄鼓与鼗鼓共同出现外,其余多为单只鸡娄鼓的不鼓自鸣。敦煌壁画中,单只鸡娄鼓在乐队中的实际演奏中则极不多见。换言之,敦煌壁画鸡娄鼓或以不鼓自鸣乐器形式表现,或以实际演奏中与鼗鼓的兼奏来表现。龟兹石窟的单只鸡娄鼓演奏也多见不鼓自鸣中,如阿艾石窟正壁有不鼓自鸣的鸡娄鼓,库木吐拉石窟68窟主室券顶有不鼓自鸣的鸡娄鼓,单只鸡娄鼓的实际演奏在龟兹石窟中亦不多见。

图14 初唐321窟北壁不鼓自鸣鼗牢
另外,莫高窟初唐321窟北壁绘制了14种乐器,为莫高窟单幅壁画中绘制乐器最多的洞窟,表达了盛大的天宫不鼓自鸣伎乐。14种乐器仅西来乐器就有8种之多。这14种乐器分别是竖箜篌、五弦琵琶、笙、横笛、箫、筚篥、毛圆鼓、都昙鼓、答腊鼓、鸡娄鼓、铜钹、鼗牢、筝、竖笛。与《旧唐书·音乐志二》载“龟兹乐……乐用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横笛一、箫一、筚篥一、毛圆鼓一、都昙鼓一,答腊鼓一,羯鼓一,鸡娄鼓一,铜钹一,贝一”㉚的史籍所载相印证。可见,明显为西域龟兹乐的乐器。另外该窟出现了莫高窟不多见的以不鼓自鸣形式表现的鼗牢(图14)。该鼗牢一柄叠二枚,且画师非常细致的是绘制的鼗牢上鼓槌正在击奏鼓面,音乐动态十足。该窟北壁大型的不鼓自鸣天乐正是《阿弥陀经变》的表现内容。唐窥基撰《阿弥陀经疏》云:“无量乐器常悬在天,不鼓自鸣。又随物有处,或舍或林皆悬乐器,悉自和鸣,随众生意,皆奏法音无非法声。人天闻者,俱发道意。”㉛再如,初唐335窟南壁共绘制13件乐器,西域答蜡鼓5件,鸡娄鼓2件,印证了初唐兼容并蓄,积极接纳西域音乐的史实。
龟兹、疏勒、高昌之乐进入汉地及中原皇廷多是由西域通向敦煌河西等地,即鸡娄鼓等西域音乐在敦煌河西繁衍兴盛并吸纳本土音乐后,再进入中原。故莫高窟中多有西域胡乐器的绘制。且多起自五凉、魏周占统河西时,其使有来供其器伎,㉜或征伐得其艺伎,㉝;遂获其乐。再如《通典》载:“又有新声自河西至者,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诸乐咸为之少寝。”㉞且“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㉟另外,唐边塞诗也记载了河西胡乐的繁盛。如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云:“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云:“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云:“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可见,鸡娄鼓等胡乐在敦煌河西的兴盛。
鸡娄鼓一词称语明显是汉语对西域乐器的音译词,龟兹老维吾尔语中音有与鸡娄极似者,是为朱砂颜色之意,鸡娄鼓很有可能为以朱砂漆于鼓体而命名。克孜尔8窟、184窟及186窟中鸡娄鼓鼓体的绘制皆呈朱红状。《文献通考》“革之属胡部”对西域胡鼓常据“漆”字来命名,如“檐鼓”条云:“状如瓮而小,先冒以革而漆之,是其制也。”㊱“齐鼓”条云:“状如漆桶,一头差大。”㊲“羯鼓”条云:“其状如漆桶,下承以牙床。”㊳莫高窟鸡娄鼓雕漆彩绘,也以红色居多。近世依存的形似鸡娄鼓的腰鼓,鼓体常漆以红色。
三、鼗鼓与鸡娄鼓的兼奏由西域龟兹传入
鼗鼓乃中原旧器,鸡娄鼓于初唐进入莫高窟,然鼗鼓与鸡娄鼓兼奏的演奏形态系西域鸡娄鼓传入汉地与鼗鼓的合奏呢?还是西域本已有与鼗鼓的合奏?换言之,鼗鼓与鸡娄鼓之兼奏的演奏形式是西域固有风格还是汉化之后的风格,亦即所谓胡风还是汉风?细考如下。
其一,从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仅三乐含鸡娄鼓的演奏以及宫廷始设乐部来看,自隋七部乐起有龟兹乐,隋九部乐起有疏勒乐,初唐十部乐起有高昌乐,含有西域胡风的鸡娄鼓遂进入河西、中原及汉乐的领地。且隋唐时期,龟兹乐尤其是龟兹鼓乐在中原汉地极为流行。《唐会要·宴乐》载:“武德初,未暇改作,每宴享,因隋旧制……自长寿以下,皆用龟兹乐。”㊴《旧唐书·音乐志》亦载:“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㊵《太平御览·乐部》载:“自安乐以后,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乐,声震百里,并立奏之。”㊶《文献通考·乐考十八》云:“唐安乐、太平、破阵、庆善、大定、上元、圣寿、光圣等舞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皆立奏之,乐府谓之立部伎也。自长寿、天授、鸟歌万岁、龙池、小破阵等舞皆同龟兹乐。”㊷据《新唐书》所载,唐立部有八伎,㊸皆奏之以龟兹乐。唐坐部伎有六,㊹除燕乐外,自第二伎长寿乐下,五伎皆以奏龟兹乐。而含有鸡娄鼓的龟兹乐,“自周、隋以来……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㊺并且,唐乐未暇修改,多袭隋制。可见,含鸡娄鼓演奏的龟兹乐影响极广。这在唐德宗时,云南王弟朝贺朝廷后,朝廷遣使复号“南诏”时,云南王以玄宗曾赐其“龟兹乐”以款享滋等来使㊻可以印证。可见,玄宗时曾以国礼遣南诏以龟兹乐,龟兹乐的风靡可窥一斑。亦可看出,包含鸡娄鼓在内的龟兹鼓乐进入汉地后在汉乐中的流行及对汉乐的影响。
其二,鼗鼓乃中原之器,鼗鼓自中原传入西域极有可能在汉代。汉代之前,中原与西域鲜有往来。再如前文所述,汉代鼗鼓极为流行,从出土的大量汉画像石上可见一斑。鼗鼓由中原传入西域或即在汉宣帝时期。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龟兹王绛宾携乌孙公主第史去长安拜贺,汉宣帝赐其鼓吹乐伎数十人。《汉书·西域传》是云:“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增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激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㊼清徐松撰《汉书·西域传补注》中引刘昭《续汉书·百官志注》云:“大将军赐官骑三十人,在鼓吹……鼓吹者,横吹也。”㊽横吹为马上军乐,鼗鼓亦用为马上之乐。如《阵纪·技用》有云:“军中响器,则有铜鼓、桡鼓、鼙鼓、杖鼓、鼛鼓、鼗鼓、鼍鼓之类,用虽不同,大抵壮逢隆之势,彰震天之威。”㊾
可见,鼗鼓极大可能在汉地传入西域龟兹等地。龟兹克孜尔石窟第8窟券顶(图15)和第184窟、186窟正壁菱格图中绘有一柄叠二枚的鼗鼓,表现的是“小儿播鼗踊戏”的因缘故事。“小儿播鼗踊戏”原出自《六度集经》,《六度集经》本由三国时吴康居国沙门康僧会译出,时为公元3世纪中下叶。据汤用彤先生考证:“僧会译经中,现存有《六度集经》。文辞典雅、颇援引中国理论……审其内容,决为会所自制,非译自胡本……深受华化。译经尚文雅,遂常掇拾中华名辞与理论,羼入译本。”㊿可见,康僧会对汉文汉事颇有精通,以致汉之鼗鼓撰入经中。并且,也可以看出,龟兹地区《六度集经》也极为流行,根据三国时译经的《六度集经》因缘本事故事而绘于龟兹克孜尔石窟中的鼗鼓,亦可能在三国前的汉代在龟兹等地亦已为流行。

图15 克孜尔石窟第8窟券顶鼗鼓与鸡娄鼓兼奏
其三,鼗鼓虽本汉来乐器,然一柄叠二枚或叠三枚的鼗鼓则在西域加工完成,并与鸡娄鼓合于兼奏。《文献通考》有“鞉(鼗)牢,龟兹部乐也,形如路鞉,而一柄叠三枚焉。古人尝谓左手播鞉牢,右手击鸡娄鼓是也”之云。敦煌,既是龟兹乐的传播之地,同时也是中原汉乐的盛演之地。鼗鼓虽是中原汉族传来的乐器之一,然莫高窟中的汉风鼗鼓多是一柄一鼓,如290窟的鼗鼓。鼗鼓自汉传自龟兹后,多是一柄二鼓或一柄三鼓。故在莫高窟及克孜尔石窟中看到的一柄叠二枚或一柄叠三枚的鼗鼓多系龟兹之风,且多与鸡娄鼓兼而奏之。中原传入西域的乐器,不断进行改造和新制,变成了西域的乐器,这并不鲜见。如同是鼗鼓,由中原传入西域后,在鼗鼓上张弦,即所谓的弦鼗而鼓之,并且在两弦之间轧以竹片而奏之,遂成了奚琴,号为胡乐。如陈旸《乐书》有言:“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形制亦类焉。”

图16 库车苏巴什出土舍利盒

图17 苏巴什出土舍利盒中的鼗鼓鸡娄鼓兼奏图

图18 库木吐拉46窟所见舍利盒
其四,鸡娄鼓与鼗鼓的兼奏在龟兹形成,是以整体形式由龟兹传入汉地。鸡娄鼓与鼗鼓的兼奏在龟兹的形成不完于5世纪,传入汉地不晚于7世纪。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库车苏巴什古寺遗址出土有一件舍利盒(图16),在该盒盒身上绘有摇鼗鼓兼奏鸡娄鼓的图形(图17),表达了龟兹乐舞的场面。据日本学者熊谷宣夫的研究,这只舍利盒的时间“是5世纪以后至7世纪的产物”。无独有偶,中国最早记载的建塔供奉佛舍利,亦于三国时的康僧会有关。库木吐拉第46窟后甬道正壁“八王分舍利图”中有一王所奉舍利盒与库车苏巴什出土舍利盒极为相似(图18)。并且在该窟主室正壁龛上方听法菩萨亦手持排箫、琵琶等乐器,其乐器种类及形制与苏巴什出土舍利盒乐舞演奏情形极为相似。可见,一则由于库车苏巴什舍利盒在20世纪出土,库木吐拉46窟所见舍利盒乃约5世纪所绘,不存在库木吐拉舍利盒图袭仿苏巴什出土舍利盒之模状,说明这种圆锥形舍利形器在龟兹地区曾极为流行;二则,库木吐拉第46窟,有龟兹姓名的供养人题记,供养人均着龟兹装束,系库木吐拉龟兹风石窟,并且与舍利盒图同在的后甬道正壁中。该窟“与克孜尔石窟第三、四阶段的特征十分相近”,壁画中有“一武士装人,身穿盔甲,手举狼纛对骑马争战……这种狼纛图像的出现时间应与突厥人活动在古龟兹国有着直接的关系”。46窟中壁画所见乐器亦也说明,突厥人进献乐器于长安宫廷亦含有龟兹乐器。这在史籍中亦能得到证明,《隋书·音乐志》载:“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此龟兹式的胡琵琶在46窟中亦有绘制。可见,绘有鸡娄鼓与鼗鼓兼奏图的龟兹舍利盒,时间可能在5世纪左右。如以舍利盒5世纪算,有明确纪年的含有鸡娄鼓与鼗鼓兼奏的220窟为贞观十六年(642年)算起,从时间来看,兼奏形态乃西域龟兹传入内地。霍旭初先生对鸡娄鼓与鼗鼓兼奏情况亦有考证,其认为“此种形式的形成,似在西域或即龟兹……鼗鼓与鸡娄鼓合为一起形成之始,可能在5-6世纪”。正因为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故在周、隋及唐宫廷乐部里,龟兹乐一直居西域诸乐部之首。说明鼗鼓鸡娄鼓兼奏乃本为龟兹地区所先有,后传至敦煌及中原地区。作为最早传入汉地的敦煌初唐窟才见鸡娄鼓与鼗鼓的结合。
其五,龟兹乐中鸡娄鼓与鼗鼓兼奏情形,亦最先见于龟兹克孜尔石窟第8窟、184窟及186窟。三窟中在佛身侧旁均绘有一小儿一手拨弄鼗鼓,一手击打腋下鸡娄鼓。在位于谷西区的第8窟主室右侧券腹菱格因缘中,因是表现小儿的播鼗踊戏,故小儿身材矮小,以半蹲状,左手持一柄叠二枚的路鼗,柄端上部小鼓颜色呈红色,下部呈白色,鼓面各为相反,呈两个“十字”方向链接。且右手拍击夹于左腋下和右腿上的鸡娄鼓,鸡娄鼓鼓体椭圆,呈红色,鼓面显白色,与鼗体小鼓鼓体颜色相同,小儿面向佛陀听其说法。位于谷东区的184窟主室东壁龛外及186窟主室东壁龛外的“小儿播鼗踊戏”,均在佛左侧,小儿形象绘制较大,右腿稍抬,出胯站立,左腋下亦夹鸡娄鼓,两只鸡娄鼓形体一致,绘制均同,首尾鼓面均呈白色,鼓体呈黑褐色(或因红色颜体蜕化而致),左手所持鼗亦均为一柄叠二枚的路鼗,柄端上部小鼓颜色呈黑褐色,下部呈白色。二窟小儿播鼗拍鼓形态绘制略似。以上三窟所见鼗鼓与鸡娄鼓的兼奏正是《文献通考》载“鞉(鼗)牢,龟兹部乐也,形如路鞉,而一柄叠三枚焉。古人尝谓左手播鞉牢,右手击鸡娄鼓是也”之云的印证。
其六,含鸡娄鼓演奏的龟兹乐、疏勒乐及高昌乐三乐中,龟兹乐为最早的影响。《旧唐书·音乐志二》载:“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北齐龟兹乐成了龟兹乐中的“齐朝龟兹”。《隋书·音乐志》载:北齐“杂乐有西凉舞,清乐、龟兹等”。《北齐书》亦载“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其帝家诸奴及胡人乐工叩窃贵幸,今亦出焉。”在河南安阳洪河屯村发现的北齐骠骑大将军墓中黄釉瓷扁壶中有龟兹乐舞表演的场面。河北响堂山北齐第七窟中亦有西域胡乐的表现。另《酉阳杂俎》有云:“玄宗常伺家诸王。宁王尝夏中挥汗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另外,与鸡娄鼓常一起在壁画中出现的筚篥,同出龟兹乐。《文献通考》将其归为“竹之属胡部”,其云:“筚篥,一名悲第、一名茄管,羌胡龟兹之乐也。”克孜尔38窟及库姆土拉13、16、24、46窟中都有筚篥的绘制。再且,同书卷一百三十一有云:“周文帝时,有龟兹人,曰苏袛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龟兹人苏袛婆在周、隋之期,其带来的西域乐调体系对汉族音乐影响极大。
其七,有鸡娄鼓演奏的高昌乐与疏勒乐中皆含龟兹因素。《隋书·音乐志》载:“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及天和六年,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由此可见,高昌伎本有龟兹之风,再且,从此乐伎所穿服饰看,“皂丝布头巾……锦袖,绯布袴,红抹额”,正是龟兹乐舞伎员所穿服饰。也可看出,龟兹乐对高昌乐的影响至大。另外,《新唐书》记录唐代龟兹乐乐器18种,记录高昌乐乐器11种,龟兹乐器大大多于高昌乐,且凡高昌乐器所有者,除铜角与羯鼓外,龟兹乐器皆有。可见,龟兹乐对高昌乐的影响很大。另外,鸡娄鼓乃龟兹地区所始有,并非自印度而来。唐天竺乐,据《新唐书》记载,乐器共10种,明显看出鸡娄鼓等不为天竺乐所有,鼓类乐器远远少于龟兹乐。另外,唐仍随隋制,虽高昌乐已进,然隋乐部里并不奏高昌乐,隋时,龟兹乐已经影响到了高昌乐。高昌早期石窟亦受龟兹艺术的影响。
高昌乐中使用的鼗鼓与鸡娄鼓的兼奏见于原出土于吐峪沟石窟现藏于日本西本愿寺中的绢画(图19),与高昌吐峪沟绢画兼奏图一起出土的化生童子乐伎图与龟兹苏巴什出土舍利盒盒顶人物极为相似,可见,鸡娄鼓是为源出龟兹。

图19 高昌吐峪沟出土绢画中的鼗鼓与鸡娄鼓兼奏图
疏勒乐中所奏鸡娄鼓,至今疏勒地区考古不见其遗迹或遗存。《隋书·音乐志》所载疏勒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除羯鼓外,其余乐器均与龟兹乐同。《隋书》无载疏勒乐乐伎服饰所用情况,《旧唐书·音乐志》载:“疏勒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白丝布袴,锦襟褾。舞二人,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与龟兹乐乐伎所穿服饰类同,但舞曲《疏勒盐》并不为疏勒乐所有,而为龟兹乐所有。并且,隋始设七部伎时,龟兹伎正式为七部伎之一,然疏勒伎仍为杂伎。亦见,鸡娄鼓源出龟兹属确凿。
总之,宫廷教坊中演奏鼗鼓与鸡娄鼓的兼奏,所用龟兹乐为多。因为疏勒乐、高昌乐影响较小,隋七部乐中未列疏勒乐,而是排在杂乐之中。隋七部乐、九部乐亦不见高昌乐,而龟兹乐夹中含高昌旧乐。唐贞观初才始设高昌乐。况且自周隋以来,而鼓舞曲多用龟兹乐。鼗鼓、鸡娄鼓皆革鼓乐器。自隋七部乐始设龟兹,至隋九部乐、唐九部乐和唐十部乐中,皆备龟兹乐。正如《文献通考》所云:“后世教坊奏龟兹曲用鸡娄鼓,左手持鼗牢,腋挟此鼓,右手击之,以为节焉。”大概“后世教坊”中疏勒乐与高昌乐已少见,而龟兹乐独兴之使然。可以肯定的是莫高窟中的兼奏图乃真正的龟兹乐所属,其兼奏之风系西域龟兹之地所传来。
四、鼗鼓与鸡娄鼓的兼奏——后世龟兹乐的影响及元后莫高窟外的记载
由前文可知,自初唐开始,含鸡娄鼓演奏的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皆作为宫廷之乐部,大兴于教坊及长安、中原汉地。所以,敦煌莫高窟自初唐窟始,至盛唐逐渐出现大量的合奏图。到中唐、晚唐时达到极盛。这种合奏图多出现于能表现唐十部乐大型乐队组合的经变画中,正是大唐气势所至。晚唐后,莫高窟不再有鼗鼓与鸡娄鼓合奏图,西域风格的大型乐队组合逐渐减少。如榆林第3窟中的西夏窟,在其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中,乐伎并不像唐窟一样出现在说法图下的乐池中,而是出现在如天宫伎乐般的阁廊中,乐队人员大幅减少,令人意外的是其东侧西起第一乐人左右手各持一枚鼗鼓,每枚叠三个小鼓,持鼗鼓者并不见与鸡娄鼓的兼奏,似乎所见大唐盛气已尽,另类民族特色的西夏之风异起。在莫高窟西夏353窟窟顶北坡及榆林窟宋15窟窟顶南坡中,也出现了飞天持鼗鼓的图像,鼗鼓均一枚叠二,花纹相同,且鼗鼓鼓面较大,西夏353窟更是左手持杖而击,与大唐风气截然不同。
宋元之后,莫高窟的兴建渐趋衰落,龟兹乐在莫高窟中的演奏绘制亦稀奇零落,然鼗鼓与鸡娄鼓的兼奏在他地仍有记录,可见,龟兹乐及鼗鼓与鸡娄鼓兼奏并没有随着元后莫高窟的冷落而沉寂萧条。
莫高窟之外的五代前蜀国开国皇帝王建(847─918年)的陵墓中亦可见龟兹乐的强烈影响。在王建墓棺床石刻东侧南起第八人就有鼗鼓与鸡娄鼓的兼奏(图20)。我们从图可看,左手播一柄叠三枚的灵鼗,左腋夹鸡娄鼓,右手持杖演奏。此演奏状态,正是《文献通考》中所云的龟兹部使用的一柄叠三枚的“鞉牢”。再且,王建墓中出现乐器图像以毛员鼓、齐鼓、答腊鼓、鸡娄鼓等西域鼓类乐器为主,可以看出,其所含龟兹乐因素十分突出。

图20 五代前蜀王建墓棺床石刻中的鼗鼓与鸡娄鼓兼奏
在后晋,龟兹乐同样繁盛。《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九云:“礼毕,高祖大悦,赐棁金帛,群臣左右睹者皆嗟叹。然礼乐废久,而制作简缪,又继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参乱雅音。其乐工舞郎,多教坊伶人。”后晋用龟兹乐,虽无图像可存,然透过史籍记载,不难看出在礼乐废陋的后晋时期,诸乐不存,唯龟兹乐以其影响而独兴,能担当习奏之。
另外,鼗鼓与鸡娄鼓的兼奏在宋代仍存,宋沈辽有诗名曰《龟兹舞》,其云:“龟兹舞……衣冠尽得画图看,乐器多因西域取。红绿裀结坐后部,长笛短箫形制古。鸡娄楷鼓旧所识,饶贝流苏分白羽。”可见,宋史龟兹乐中鸡娄鼓仍在奏响。见于北宋初的开封繁塔伎乐砖中有鼗鼓与鸡娄鼓兼奏的情形。(图21)。在该繁塔二层内壁中嵌有20块刻有伎乐演奏的方砖,其中有两伎左手持鼗,左臂夹有鸡娄鼓,右手持杖在演奏,其左臂间夹奏鸡娄鼓,与莫高窟极为相似。在繁塔其他的刻砖中,乐器种类多见拍板、横笛、筚篥、排箫、笙等乐器,亦呈现了明显的龟兹乐舞场面。可见龟兹乐舞在宋代也极为流行。这和史书记载亦相符。《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有云:“自唐季之乱,礼乐制度亡失已久……高祖会朝崇元殿,廷设宫悬,二舞在北,登歌在上……又继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可见,在礼乐已废的唐末五代,龟兹乐部仍由旧时教坊伶人在传习着,充分说明其在唐时的盛行。

图21 开封繁塔伎乐砖中的鼗鼓与鸡娄鼓兼奏图

图22 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碾伎乐狮纹白玉带中的鸡娄鼓鼗鼓兼奏
在唐代莫高窟壁画记录之外,鸡娄鼓与鼗鼓的兼奏亦不乏所见。位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碾伎乐狮纹白玉带,玉带中九件刻有胡伎奏乐图,其中一件可见胡人乐伎席地坐于毯上,左腿起立,鸡娄鼓置于左膝与左臂间,左手播一柄二枚的路鼗,右手持杖正在敲击(图22),其演奏情形与莫高窟极似。在其余方上出现有筚篥、横笛、排箫、琵琶、羯鼓、答腊鼓、毛员鼓,表现的正是西域龟兹胡乐的演奏情形,恐为使朝进贡所献。
龙门石窟龙华寺洞窟开凿于唐代,其北壁有鼗鼓与鸡娄鼓兼奏的形象(图23)。乐伎左手持鼗,腋夹鸡娄鼓,右手持杖欲击。

图23 龙门石窟龙华寺洞窟鼗鼓与鸡娄鼓
另外,原出土于克孜尔石窟,今藏于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编号为“MIKⅢ8136”的一件木雕,也正是表现了左腋夹鸡娄鼓,盘腿而居的演奏状态,虽然右臂已残,但其生动可人的击鸡娄鼓表演状态活灵活现,在云冈石窟2窟、6窟、12窟前室北壁上部窗楣中、内蒙古敖汉旗萨力巴乡水泉一号辽墓出土的玉带中、西安西郊关庙小学出土有唐玉带中,龙门石窟唐代石刻及大足北山唐代石刻中皆可见鸡娄鼓与鼗鼓的兼奏情形。正如清乾隆年间王芑孙记述西域风土人情的《西陬牧唱词》,对鸡娄鼓描写的那样,“小雅诗传考牧篇,僸偶有唱谱新编,阿谁惯打鸡娄鼓,与我同绉马尾弦。”可见,莫高窟外,随着龟兹乐的兴盛及佛教在全国各地的发展,云冈等佛教壁画乐舞礼佛供养的绘制中鸡娄鼓与鼗鼓兼奏的情形频频出现。有龟兹乐影响的地方,方物及墓葬中亦多见鸡娄鼓与鼗鼓兼奏的情形。以上可为莫高窟外鼗鼓与鸡娄鼓兼奏情形的延拓。
结 语
鼗鼓与鸡娄鼓兼奏图在莫高窟中自初唐窟始,终于晚唐窟。初唐窟前北周窟中有单奏的鼗鼓形象,晚唐窟后,直至西夏、宋窟中仍有单奏的鼗鼓,初唐窟前及晚唐窟后不见兼奏情形。
鼗鼓与鸡娄鼓兼奏图多出于经变画说法图下乐池中能表现大唐风气的九部乐、十部乐乐器使用中。从处在乐队中的位置看,兼奏者多有领奏或担当乐队指挥的用意所在。
鼗鼓本华夏旧器,鸡娄鼓出于西域,鼗鼓与鸡娄鼓兼奏源起于西域龟兹,克孜尔即见证。莫高窟中的鼗鼓与鸡娄鼓兼奏明显受西域龟兹之风的影响,亦是唐代嗜迷于龟兹乐,龟兹乐对中原汉乐影响的见证。
余 论
鸡娄鼓始见于初唐石窟中,龟兹乐、疏勒乐皆随胡女唐时进献中原,高昌乐虽在隋时有访,也进献乐器,然在隋时并未进入宫廷乐部伎,故隋窟中仍不见鸡娄鼓。且鸡娄鼓与鼗鼓合奏多出现在能表现唐七部九部乐、十部乐及立部、坐部等的大型经变乐器组合中。且初唐有表现经变的乐器组合,如322窟,虽在出现鸡娄鼓与鼗鼓合奏的初唐,然是表现粟特安国乐,故不出现鸡娄鼓。贞观十四年唐王朝起大兵平高昌,建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敦煌成为西域与中原衔接的重要驿站。河西及往来西域的道路复归通畅,西域文化陆续东传。故高昌文化介乎于龟兹与中原之间,但是,鼗鼓与鸡娄鼓的兼奏有可能是贞观十四年平顶高昌之后,陆续大规模在莫高窟中表现。我们发现,莫高窟大量图像亦能证实,莫高窟中的所有鸡娄鼓与鼗鼓兼奏图都是在贞观十四年之后出现的。或许与大唐贞观十四年平顶高昌一事有关。贞观十四年之后,随着大唐向西域征讨的逐渐平静,西域及长安风气艺术随之在莫高窟中极度凸显盛行起来,如建于贞观十六年艺术水平至高的220窟带有强烈的大唐中原风气,亦见鸡娄鼓的演奏。这可以看作是平高昌及唐重控西域后,唐西域音乐艺术首度在莫高窟中的精彩绽放。换言之,西域艺术继北朝以来再次在莫高窟中的进入,标志着唐的实力再次控制西域,亦即从另一个层面证实了唐王朝的高昌用兵,西域各权力的归附及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
注释:
①如《法华经·序品第一》有云:“诸天龙神,人及非人,香华伎乐,常以供养。”《法华经·法师品第十》记述的其他九种供养是“花、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及合掌”。原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合掌恭敬,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另《法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有云:“千万亿众,以一切华、香、璎珞、幡盖、伎乐,供养宝塔,恭敬、尊重、赞叹。”《法华经·分别功德品第十七》有云:“悬诸幡盖及众宝铃,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众鼓、伎乐,箫、笛、箜篌,种种舞戏,以妙音声、歌呗赞颂,则为于无量千万亿劫、作是供养已。”
②吕不韦等:《吕氏春秋·古乐》,载《诸子集成之六》,上海书店,1996,第52页。
③《周礼注疏》卷二十三,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3,第797页。
④《周礼·春官》载:“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征,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乐,函钟为宫,大簇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蔟为征,应钟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同②,第789-790页。
⑤《礼记正义》卷十六,载《十三经注疏》之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27页。
⑥陈戍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2006,第282页。
⑦同⑤,第234页。
⑧[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天晓诸入出市”,商务印书馆,1939,第115页。
⑨《仪礼注疏》卷十六,载《十三经注疏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89页。
⑩袁梅:《诗经译注》,齐鲁书社,1982,第565页。
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六“乐考九”,中华书局,1986,第1206页。
⑫古人谓箫,非今单管箫之形器,乃指多管之排箫。
⑬王圻:《三才图会·器用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125页。
⑭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中华书局,1975,1068页。
⑮同⑪,第1208页。
⑯ 386窟为初唐窟,主室南壁阿弥陀经变为中唐所绘,故南壁兼奏图归为中唐时期。
⑰[唐]魏徵:《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345页。
⑱同⑰,第347页。
⑲[唐]魏徵:《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中华书局,1973,第1844页。
⑳同⑰,第381页。
㉑同⑰,第381页。
㉒[唐]魏徵:《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第1580页。
㉓《隋书·音乐志》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同⑰,第376页。
㉔《隋书·音乐志》载:“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同⑰,第377页。
㉕同⑰,第378-379页。
㉖同⑰,第378页。
㉗同⑰,第380页。
㉘同⑭,第1070页。
㉙同⑪,第1208页。
㉚同⑭,第1071页。
㉛《大正藏》第37册《经疏部五》,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3,第320页。
㉜如高昌乐:“太祖(宇文泰)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中华书局,1973,第342页;“西魏与高昌通,始有高昌伎。我太宗平高昌,尽受其乐。”同⑭,第1069页。
㉝;如龟兹乐:“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同⑰,第378页。如疏勒乐:“疏勒……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同⑰,第380页。
㉞《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乐六”,岳麓书社,1995,第1964页。
㉟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十二》,中华书局,1975,第476—477页。
㊱同⑪,第1208页。
㊲同⑪,第1208页。
㊳同⑪,第1208页。
㊴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55,第609页。
㊵同⑭,第1059—1060页。
㊶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六八“乐部八·宴乐”,中华书局,1960,第2567页。
㊷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五“乐考十八”,中华书局,1986,第1208页。
㊸《新唐书》卷二十二云:“立部位八:一安舞,二太平乐,三破阵乐,四庆善乐,五大定乐,六上元乐,七圣寿乐,八光圣乐。”同㉟,第475页。
㊹《新唐书》卷二十二云:“坐部伎六:一燕乐,二长寿乐,三天授乐,四鸟歌万岁乐,五龙池乐,六小破阵乐。”同㉟,第475页。
㊺同⑭,第1068页。
㊻《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五有载:“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滋至其国,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百再拜,因与使者宴,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唯二人在耳。’”《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五《唐纪五十一·德宗贞元十年(甲戌,公元794)》,1956,第7561—7562页。
㊼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六十六下,中华书局,1962,第3196—3197页。
㊽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中华书局,1985,第79页。
㊾何良臣:《阵纪·技用》,中华书局,1985,第24页。
㊿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