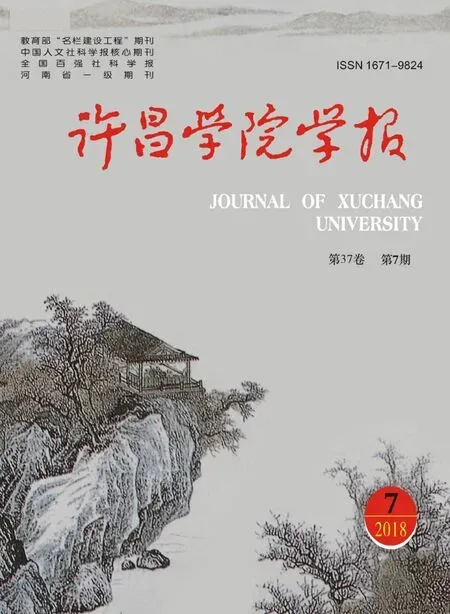政治视域下魏晋反玄学思潮析论
阎 秋 凤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3)
曹魏末年,皇权被要挟在两股庞大的政治势力中。这两大势力一为曹爽集团,主张改革,为名士新贵所拥护;一为司马集团,采取保守路线,为儒家大族所拥戴。两大势力此消彼长。在曹爽专权的正始年间,曹魏政权已呈衰颓之势,为巩固统治,曹爽集团的中枢人物夏侯玄、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提倡道家“贵无”的思想,主张“任自然”“无为”的治国方针,清简朝政,试图通过清静无为之治,达到以弱胜强、以一统众、以君统臣的目的。玄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携裹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发端于魏末的权力角逐中,也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注定了玄学从诞生起就处于一种对立的体制内,时刻遭受来自对方的纠举、批评、责难。
一、崇名教、尚有为,纠举“任自然”“无为”的政治模式
《晋书·王衍传》称: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1]1236
玄学的中心问题是有与无的问题,王弼“以无为本”的思想称为“贵无论”。王弼把有形名的具体事物称为“有”,把无形名的抽象本体称为“无”。在社会政治领域,礼仪制度、仁义原则是有,而礼仪制度、仁义原则背后的自然状态则是无。基于“贵无”的认识论,王弼提出了“以静制动”“无为而治”“崇本息末”的政治主张,并进一步把“崇本息末”的思想运用于汉魏之际社会中,强调因自然而立名教,名教本于自然。王弼在《老子注》中说:“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2]149他认为消除“邪淫盗讼”,不应使用严刑苛法,而应该“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察善;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存乎不尚,不在善听”[2]198,以自然无为的态度行有为之治,从而达到老子所谓“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的目的。
王弼以道家思想为中心提出“以无为主”的主张,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自然无为”思想体系,其目的是为了缓和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维护曹魏集团的政治统治,但却遭到了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如傅玄和裴頠等人的极力反对。
(一)魏晋之际傅玄的政治蓝图
在曹魏末年诡异多变的政局和政权角逐中,傅玄站在儒家大族的立场上与曹爽集团种下政治嫌隙,因此与曹爽集团中的中枢分子夏侯玄、何晏等人处于敌对状态,尤其与何晏结怨最深,据《晋书·列女·严氏传》载:“时玄与何晏、邓扬不穆,晏等每欲害之。”[1]2509而“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1]1317的傅玄对何晏表示了极大的厌恶,“魏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3]886面对何王为曹爽集团建构的“贵无”与“任自然”的政治模式,傅玄更是极力地予以抵制。
首先,傅玄主张国君“有为”,反对何王的“无为”说。
傅玄认为高明的治国策略应该是礼刑共用、德威兼济,其途径在于教化,不论是“立善防恶”,抑或是“禁非立是”,都需要通过礼法的实施来预防违法犯罪,而非“专任杀人”,同时又要求统治者通过刑罚的实施体现礼法本身的教化职能。傅玄于太始初上书晋武帝:
战国之际,弃德任威,竞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4]52
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惟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仪,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1]1317-1318
这是针对何晏、王弼所大力提倡的“无为”政纲而发的。王弼提出“从事于道者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绵绵若存,而物得其真”[2]58的执政之术和“不能以谦致物,物则不附”[2]456的谦和清静之政,以及“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3]179的“去刑”“去威”“无为之治”的御民之道,实际上是给曹爽政权提出一套重建伦理秩序的理论工具。而傅玄则以“有为”论说,起而纠之。傅玄尤其注重国君自身的修为,以黄帝、夏禹、周公等爱民恤民、勤于政事的国君为砥砺对象,期盼新朝君主加以效法。傅玄认为国君乃一国之主,其一举一动皆影响臣民的行为,进而影响着政风的好坏。
傅玄“有为”的政治思想,不仅是对何王“无为”政纲的反制,也为司马氏政权提供了治国政策和措施,使当时的统治者有了借鉴的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其次,傅玄主张“圣人设教”,反对何王“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
王弼认为封建体制的建立源于“自然”,为了证明“名教出于自然”之说,他提出:“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2]75“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长官,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2]82王弼借由自然法则的先天决定论,为人类社会阶级、贫富等的不平等现象寻求合理的论证,以重建社会秩序,使之回复于上下相安、尊卑有等的礼制,这样纷乱就不会再度发生,人民的安全与幸福才能获得永久保障。但傅玄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王弼巧妙地消融了存在于人类社会间的不平等现象,用一种消极、回避的态度观照实有的现象界。傅玄说:“上德之人,其济万物也,犹天之有春秋,时至自生,非德之力。”[5]511他不承认人世间有超越自然的主宰力量,即使“上德之人”也只能利用天时育成万物,并不能代替自然的作用。傅玄在《傅子》中进一步阐发了这种观点:
善为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况于人乎。尧水汤旱,而人无菜色,犹太平也,不亦美乎。晋饥吴懈,而为秦越禽,人且害之,而况于天地乎?[4]82
傅玄认为,人类间的尊卑上下等级的维护,是仰赖于执政者的明德教化的,只有以诚信对待所有的臣民,使百工以劝,贤才归集,透过后天的陶冶正身,使德化普博,才能使失序的体制恢复其和谐之序。
傅玄以建立务实有为的政府为目的,力主君主“有为”和“圣人设教”,以纠举何王君主无为、任自然的政治策略。
傅玄的观点开启了魏晋反玄思潮中君主“有为”和“圣人设教”言论的先河,西晋裴頠继承了他的观点。
(二)西晋裴頠的“崇有”为政观
裴頠出身儒学世家,其父裴秀“儒学洽闻,且留心政事……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朝廷多遵之”[1]1039-1040。裴頠本人“才德英茂,足以兴隆国嗣”[1]1041,裴頠官至侍中、尚书仆射,对当时的政治决策影响极大,是元康时期的实权人物之一。
裴頠所处的时代,正是魏晋玄学的鼎盛时期,清谈领袖王衍继承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高唱“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士人“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1]1992,不但无心于国事,反而崇尚无为之政,高旷、放达之风盛行,使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作为当权派,裴頠针对时俗放荡、儒术和礼法遭受贱鄙的情形,著《崇有论》予以回击。《崇有论》涵盖两方面的论述:政治上,以“名教本为圣人所创制”反对“名教出于自然”,倡导礼制教化,以纠正虚无的玄风;哲学上,以“虚无是不能创生实有物”为出发点,批判玄学家的虚假性,进而将哲学中的“有”转化为政治上的“有为”。
首先,裴頠以维护晋室统治为己任,认为当时迫切的任务为重视名教,名教源自圣人,而非源于自然。裴頠于《崇有论》中言道:
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1]1044
他理想中的圣人形象乃是“建厥极”“理群生”“训物垂范”之有为形象。因为圣人立处于世,洞悉了人之情性,知欲不可绝,也断绝不了,只有依缘此性,而以礼制之,以教化之,方能使“欲”之求,合乎节度,且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推溯王弼论圣人之情性说,《三国志·钟曾传》注引和劭《王弼传》已有论及: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6]795
王弼肯定圣人同于一般人的是皆具五情,但又承认圣人能体无,纵使有情有欲,亦无妨于其自然之性,却完全忽略了“牵累于物”的凡人。
有鉴于此,裴頠认为王弼所盛称的圣人,其所体认的“无”以及所信仰的“无为之政”,都是“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1]1047,“信以无为宗,则偏而害当矣”[1]1046,因而“济有者皆有也”[1]1047,唯有在现实社会中,深刻地观察世俗纷扰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以返归自然的和谐,而圣人则就此应运而生,将纷扰的群生统一起来,为其建立体制,进而使得人伦有序,事与而物理。
裴頠以此肯定圣人设置名教的贡献,驳难道家圣人对世俗责任的轻忽,因为圣人只在于“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2]77。如此无施无为,在儒家眼中是不能济世群生、通理万物的。裴頠从政治上分判儒道二家圣人境界的高低,试图确立儒圣的地位;同时肯定了圣人设教的价值与贡献,以维护名教之治。
其次,裴頠有感于当时老庄贵无被转化误用进而产生许多虚无弊病,因此列举了贵无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
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1]1044
这段文字立足于政治层面对当时“贵无”思想所产生之流弊进行批判,裴頠认为当时贵无论者看到简损之善,遂贵无而贱有,而这种“贱有”心态必将走向外形、遗制、忽防、忘礼这条路上,最终将无法推行政策,造成政务严重迟滞积案,故无以为政。其最终落脚点在于“无以为政”,即认为“贵无”“贱有”之说的最大弊端,是其将会对“政治秩序”造成极大之破坏。裴頠以是否有益于“政治秩序”作为评价标准,显示出其思想立场在于维护儒家之政教。为此,裴頠不得不纠举弃儒贱礼、随性妄为的世俗歪风:
是以立言借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凌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1]1045
正是在此贵无贱有的渐染下,“礼制弗存”成了事实。裴頠想通过纠举“虚玄贵无”之风来强调唯有重振礼法之制,建立长幼尊卑等级之序,唤醒世人的道德意识与责任感,国家、社会才有生机可言。其目的是从根本上着手,以礼制教化建立积极有为的政府。
二、废九品、罢中正,批驳腐败的门阀政治体制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是对西晋统治集团的形象描述,也是西晋政治腐败与颓放的真实写照。这种局面是通过两种途经形成的,一是“户调门选”的选才模式,二是晋初晋武帝卖官。这是两晋政治腐败的主因,然而这一不平等的世族政治体制,却得到了玄学家郭象的理论支持。郭象提出了“性各有分”“适性逍遥”的玄学思想,强制下层寒微之士承认“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终,而愚者抱愚以至死”[7]59的事实,并且接受此一不平等现象。在这种玄学思潮的影响下,两晋门阀世族沉溺在一片虚玄的“迹冥”理论与追逐中:“(王衍)居宰相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志在苟免,无忠蹇之操。”[1]1237“(谢鲲)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1]377“(乐广)清已中立,任诚保素。”[1]1245“(庾亮)爱容逃难,求食而已。”[1]1916在政治上,门阀世族形成了君臣“无心”(无处事意)“无为”(无所作为)、高谈玄妙的为政观。而经历过魏晋易代的名士群体,则为求自全,以退为守,苟且于名利,不因求名而害利,亦不因贪财而损名,形成“士当身名俱泰”的为政观。为此,晋武帝时期的刘毅著《请罢中正除九品》,提议废除九品中正制,以匡正举才之失,使政治回归开明之治。惠帝元康时期的王沈亦针对这一政治流弊著《释时论》予以鞭挞。
(一)王沈对“举才乖实”的指责
王沈是西晋文学家,《晋书·王沈传》记载:
王沈,字彦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于寒素,不能随俗沈浮,为时豪所抑。仕郡文学掾,郁郁不得志,乃作《释时论》。[1]2381
《释时论》强烈地指责了世族制度对人才的压抑,揭露了一批无德无才、欺世盗名之徒的可憎面目和卑劣用心。
虽然王沈生卒年不详,但根据现世文献推断,他大致生活在惠帝元康时期。面对“才与不才”皆无关系,“品德操守”亦是无关紧要的士族政治,王沈如是批判道:
至乃空嚣者以泓噌为雅量,琐慧者以浅利为枪枪,脢胎者以无检为弘旷,偻垢者以守意为坚贞,嘲哮者以粗发为高亮,韫蠢者以色厚为笃诚。[1]2382
晋初政坛上还存在着卖官鬻爵的现象,官职成了皇室、世族获利的工具,皇室、世族用其职权扩充家族势力,以巩固其政治地位。针对“姻党相扇,毁誉交纷”[1]2383的情况,王沈曰:“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官无大小,问是谁力。”[1]2383
基于先祖辈的功劳,世家大族的纨绔子弟高居显职,无须才智、修养和德行,纯依祖宗之门,坐享无尽之权力与财富,王沈深疾道:
多士丰于贵族,爵命不出闺庭。四门穆穆,绮襦是盈,仍叔之子,皆为老成。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肉食继踵于华屋,疏饭袭迹于耨耕。谈名位者以谄媚附势,举高誉者因资而随形。[1]2382
而寒素阶级的士子,因家门低下之故,难以突破门阀世族的盘根结错,在政治上往往空有一腔抱负。王沈《释时论》则论说了此一不平等的现象:
卿相起于匹夫,故有朝贱而夕贵,先卷而后舒。当斯时也,岂计门资之高卑,论势位之轻重乎!今则不然。上圣下明,时隆道宁,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门有公,卿门有卿。[1]2382
王沈的批评都是针对选举失实,唯门第是求造成的政治腐败现象而发的。针对选举之失这一根本问题,晋武帝之世的刘毅在《请罢中正除九品》一文中提出了批判与建议。
(二)刘毅对“九品中正制”的谴责
刘毅,西汉城阳王刘章的后代,曹魏及西晋官员。刘毅公正刚直,喜欢评论人物。
在门阀政治下,高门世族为巩固其政治势力于不坠之境,除了身居中正一职以操选举外,还以联姻方式,永享其高门之尊荣,而其子孙则取得了与生俱来的优势。针对“崔卢王谢子弟,生发未燥,已拜列侯,身未离襁褓,业被冠戴”的情形,刘毅曾上书:
今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1]1276
《晋书·段灼传》亦云:
今壹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1]1347
有感于晋世“公有公门,卿有卿门”截然二分的政治结构,刘毅以为其病源在于“中正”官员的主观情绪与偏袒心态上,其言:
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1]1273
为此,刘毅甚至提出了解决办法,他认为举才应需课试,都官也应以考课,这样才能杜绝世族势力的扩大及其观望无为的心态,其言:
昔在前圣之世……乡老其善献天子,司马论其能以官于职,有司考绩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浮华邪佞无所容厝。[1]1275-1276
综上所论,在王沈的批判与检讨中,在刘毅的强烈谴责声中,西晋政治的腐化与颓废已全面呈现。西晋政权的灭亡,实与玄学思潮、门阀政治密切相关。
三、“清谈误国”论对玄学清谈的政治责难
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根据清谈内容将其分为前后两期:“当魏末两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借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8]201事实上,魏晋前期,清谈与政治的关系除体现为清谈与士大夫的出处进退的关系外,还体现在王室贵要醉心于清谈而不事政务,以致政治效能和政治秩序无法保证,政局动荡,直至西晋灭亡。清谈领袖王衍在被石勒杀害之际,一语道破清谈对政治的破坏力:“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1]1238令人遗憾的是,王衍死前发自肺腑的悔叹,并没有引起东晋统治集团高层的充分重视。为稳定政权,王导作为宰辅,以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作为政治方针,“镇之以静,群情自安”[1]1751“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9]156。从而再次引发清谈盛况,如: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9]185
然而,东晋时期的清谈,正如陈先生所说,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意义,只是名士身份的装饰品而已。虽说有稳定江东的作用,但却无益于社会风气的改善与救治亡国之弊,玄学引起的弊端仍在东晋泛滥流行,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东晋王朝在政治、军事等各方面不会有大的起色,南渡士人收复失地的热情、统一全国的理想最终化为泡影。
即使这样,两晋的政治得失,仍牵动着士大夫的天下情怀。这个时期,一些政治家和文人却存在着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思想倾向,北伐雪耻、匡复失土的大志,仍在众多士人心头萦绕。对西晋亡国的检省与反思几乎成为东晋士人的第一要务,痛彻心扉的东晋士人,纷纷将此国难归罪于清谈玄虚以及由此引发的任诞放达之风,运用整个社会舆论的力量,各抒其忿,自此,清谈开始承担起误国的罪名。如《晋书·桓温传》记载桓温自江陵北伐途中的感叹:
于是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1]2573
《晋书·愍帝纪》文末论述西晋朝得失时,引用干宝的《晋纪总论》将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病及其原因归于清谈虚浮、放诞旷达之风:
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1]136
干宝这段文字概括地总结了玄谈之风对社会风气的败坏尤其对国家政治的消极影响。干宝是东晋人,“殷鉴不远”,西晋灭亡的惨痛教训,使干宝毫无顾忌地指出西晋之失。当然,干宝几乎把西晋的灭亡原因主要归之于玄谈所引发的弊端,未免有些夸大其词,说“清谈亡国”可能言过其实,然而说“清谈误国”应该是不刊之论,因为“清谈”毒化了社会风气,加重了社会混乱,加速了国势的衰微,从而最终加快了西晋的灭亡。
桓温、干宝之外,东晋当朝的反玄声浪更是风起云涌,“清谈误国”论作为政治性的责难再掀高潮。如应詹曾上疏元帝,力陈永嘉之弊是由“贱经尚道,玄虚宏放”[1]1858所导致;卞壸也认为中朝倾覆是贵游子弟颓唐放达、“悖礼伤教”[1]1871造成的;虞预也因胡虏遍于中国而“憎疾玄虚”[1]2147;范宁则把王弼、何晏二人作为玄虚风气的始作俑者,将士风的堕落,社稷的倾颓,一切历史的罪孽都归于王弼、何晏二人的“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1]1984,等等。这是遭受失国之痛的东晋士人在痛定思痛后的反省,是东晋士人集体焦虑之下,对清谈进行的强烈谴责!
四、结语
玄学思潮影响下,老庄清静无为之政及自然之化的治国之术,渗透在曹魏政治体制的建构中,贯穿于西晋的门阀政治体系内,弥漫于两晋名士的清谈之间。立足于儒家立场的傅玄,坚守礼教之治的裴頠,出身寒素、备受豪门世族压抑的王沈,公正刚直的刘毅,晋室南渡后痛定思痛的东晋士人等等,面对玄学引起的虚无和颓废,舍“虚”尚“实”,出“无”入“有”,以强烈的道德意识和入世担当的治世情怀,期待通过政治的运作建立纲纪有序、伦常和睦的大有为政府,在玄学思潮居主流地位的魏晋社会,以反玄学的姿态,处处彰显着为社会付出的关怀和努力。即使在国富民安的当代社会,这种力求作为、积极进取的务实精神,也仍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