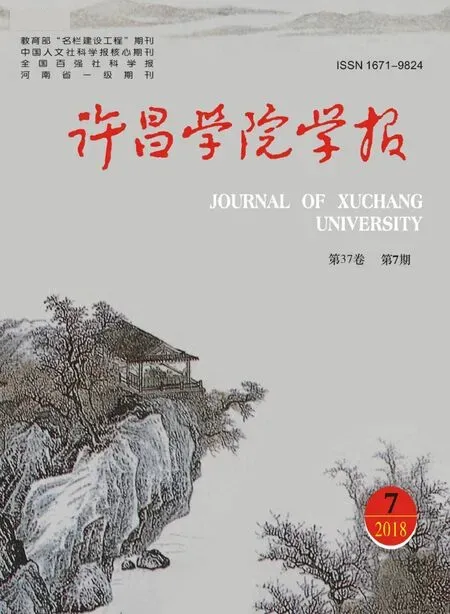北朝医者与政治
高 贝 贝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招生处,河南 许昌 461000)
医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既是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的技艺之士,又是保身全命的养生践行者。故世人常云,医,“精义也,重任也”[1]自序。即便医者拥有精专的医疗技艺和救死扶伤的强烈责任心与使命感,也无法泯灭其在世人心目中“方技(伎)”“艺术(术艺)”之士的社会身份和形象。不过医者却可以凭借其专业的医疗知识和技术进入上自君王贵胄、下至黎民百姓的私领域,为之治疗病痛,维持生命,延续香火,并可享有相当弹性的政治活动空间,有机会获得君王的特殊宠任而进入统治者的公领域,参与国家政务。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拥有着双重的身份与社会角色,其内心深处自然蕴蓄着一番精神向往与人生理想。那么,在南北朝时期医学权力被“门阀的医家”“山林的医家”所占有时*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医者群体又是如何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呢?本文试以北朝医者(即学人所说的“门阀的医家”)为中心,从史料中梳理出医者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就正于方家。
一、佐助新皇登基
在君主政治时代,帝王作为国家权力的实际载体,肩负着与生俱来的神圣使命:治国安邦,垂世济民。既然君主是天下万民仰赖的对象,统治者只有得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拥戴,方能位居尊位,治理天下。《魏书·礼志四》记: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与詹事王显,中庶子侯刚奉迎肃宗于东宫,入自万岁门,至显阳殿,哭踊久之,乃复。王显欲须明乃行即位之礼。崔光谓显曰:“天位不可暂旷,何待至明?”显曰:“须奏中宫。”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国之常典,何须中宫令也。”光与于忠使小黄门曲集奏置兼官行事。于是光兼太尉,黄门郎元昭兼侍中,显兼吏部尚书,中庶子裴俊兼吏部郎,中书舍人穆弼兼谒者仆射。光等请肃宗止哭,立于东序。于忠、元昭扶肃宗西面哭十数声,止,服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进玺绶,肃宗跽受,服皇帝衮冕服,御太极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阶,夜直群官于庭中北面稽首称万岁。[2]2806
倘若立国而无君,出现权力真空,则必然会出现混乱、动乱局势,乃至亡国。故宣武帝元恪驾崩后,医者王显等人拥护孝明帝元诩承袭皇位,临治天下。不过这次皇权交接过程中的斗争异常激烈,以王显为代表的外戚高肇集团同以于忠为代表的外戚于氏阵营展开殊死搏斗,其表现为即位时间之争。从王显、高肇系的利益角度来看,若元诩天明即位,王显等人就可以争取时机,把宣武帝驾崩的消息奏知中宫,让皇后高氏出面干预,出现太后临朝听政的局面,若此,王显等人既可继续享有既得权益,又有加官晋爵进一步扩大权势的无限可能。从于忠系的利益角度来说,迅速扶持元诩即位,他们就成为拥立新皇登基的最大功臣,既可把新皇作为他们的政治代表而牢牢控制手中,又可避免高后干预朝政,还可在今后同王显、高肇系的争斗中占据上风。两大阵营各有思量,其“计划体现了两种前景,王显的计划是导致太后临朝局面的出现,于忠等人的计划则是由未被顾命之权臣辅政并控制朝政”[3]10。最终,因高肇在外征伐,王显等人于朝中势力微薄,在元诩即位时间上败给于忠等人。
医者王显虽拥立新主即位有功,但在新朝尚未有所作为时就在同于忠的争斗中败阵而亡,“朝宰托以侍疗无效,执之禁中,诏削爵位。临执呼冤,直阁以刀镮撞其腋下,伤中吐血,至右卫府一宿死”[2]1969。同样是参与君王权位交接,医者王显被下狱削爵诛杀,而徐之才却驰骋官场,安然终老。《北齐书·徐之才传》载:
之才少解天文,兼图谶之学,共馆客宋景业参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启之。文宣闻而大悦。时自娄太后及勋贵臣,咸云关西既是劲敌,恐其有挟天子令诸侯之辞,不可先行禅代事。之才独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诸人咸息。须定大业。何容翻欲学人。”又援引证据,备有条目,帝从之。登祚后,弥见亲密。之才非唯医术自进,亦为首唱禅代,又戏谑滑稽,言无不至,于是大被狎昵。[4]445
医者徐之才、天文数术之士宋景业“运用自己所了解的那些天文知识,对天道规律进行夸大和神化,并将其运用到对人和社会的认识中来”[5]116,依凭高德政向高洋进言:顺应天道,取代东魏。毕竟天道“不仅富于理性色彩,代表着自然与万物的规律,而且也是国家的‘规范’,君主只有按照这些‘规范’行事,才能体现天道的意志”[5]119。最终,高洋篡夺东魏,接受天命。高洋虽然篡魏成功,登临宝座,在终结东魏国祚时得到了高德政、杨愔等汉族文官的大力支持,但却遭到了勋贵势力的强烈反对,更确切地说是遭到了晋阳军方勋贵的强烈反对[6]241-248,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高洋篡魏事件也包含有胡汉两集团冲突的意味[7]206。代魏成功后,医者徐之才因“首唱禅代,又戏谑滑稽”,甚得北齐各代君主宠幸,政治上既扶摇直上,生命上又正常谢幕。
二、参与君王重大决策
帝王要依赖群臣百官的辅佐,才能上情下达,治理国家,而后方可稳居高位,长掌大权。然而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帝王要想实现君权的有效统治,至少要具备独自裁决日常行政事务的能力,即“独断”的能力:“其一,君主在政治决策的时候,不为群臣左右,保持判断的独立性”;“其二,君主必须始终亲自把握最高决断权,在决策过程中保持绝对的主导地位”[5]236。帝王只有具备了“独断”的能力,才不至于遇事倍感压力,无所适从。《魏书·术艺·周澹传》云:
周澹,京兆鄠人也。为人多方术,尤善医药,为太医令。太宗尝苦风头眩,澹治得愈,由此见宠,位至特进,赐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师饥,朝议将迁都于邺。澹与博士祭酒崔浩进计,论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与朕意同也。”诏赐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袭,绢五十匹、绵五十斤。[2]1965
神瑞二年(415)京师暨并州地区发生严重饥荒,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太史令王亮、苏垣、华阴公主等人主张放弃平城而迁都邺城。迁都固然可解明元帝拓跋嗣的燃眉之急,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故崔浩、医者周澹二人提出定平城为京都的策略。他们的策略既符合拓跋统治者的需要,在当时又有切实可行的现实条件。第一,当时鲜卑军队以骑兵为主,于冲锋陷阵方面拥有很强的战斗力和威慑力;第二,平城位于畜牧业和农业交汇地带,可以为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第三,平城于军事方面有优越的战略位置;第四,定都平城,建立偌大且稳固的根据地是拓跋统治者早已有之的想法*参见严耀中:《从“定都策”说崔浩》,《许昌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明元帝拓跋嗣面对着这份理清言明的固守而非迁都的策略,甚感欣慰,最终拒绝了华阴公主等人的意见,采纳了周澹、崔浩二人的建议,分民就食山东三州,以解饥荒。
明元帝裁决是否迁都的理政举止符合“兼听独断”的模式。当君主做出重大决策时,要善于倾听多方谏言,之后再做出裁决,切忌轻信近臣,被他者左右判断,失去最终决断的主导权。《魏书·外戚·高肇传》曰:
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世宗初,六辅专政,后以咸阳王禧无事构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无亲族,颇结朋党,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详位居其上,构杀之。又说世宗防卫诸王,殆同囚禁。时顺皇后暴崩,世议言肇为之。皇子昌薨,佥谓王显失于医疗,承肇意旨。[2]1830
宣武帝重用外戚高肇,初衷在于集中君权,反而却助长高肇权势日渐膨胀,致使高肇相继对统治集团中妨碍其权力提升的恩幸、诸王、皇后于氏及其家族三股势力予以致命打击*参见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第8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医者王显党附于外戚高肇,极有可能利用医疗之便谋杀于皇后之子元昌,让于氏家族在权力斗争中失去重要筹码。皇子殒命,宣武帝竟不追责,似乎说明外戚权势过盛,已可专断皇权,实则不然,“高肇专权是宣武帝时期北魏皇权政治的体现,它适应了宣武帝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高肇权力的膨胀是臣下权力的高度发展,而不是对君主集权的离心倾向”[8]80,故外戚权力依旧在皇权约束之下,对国家政令的决策、执行都没有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宣武帝没有听从高肇建议把于忠逐出朝廷,即是保持判断独立性的明证。当然,君王作为最高统治者,在做出最后裁决之前,也会亲自调查,若情况属实,可听从百官言论,如情况不符,可全权否决,给出切实可行的方略,否则,其盲目裁决将会酿成悲剧。《北齐书·崔季舒传》记:
祖珽受委,奏季舒总监内作。珽被出,韩长鸾以为珽党,亦欲出之。属车驾将适晋阳,季舒与张雕议:以为寿春被围,大军出拒,信使往还,须禀节度;兼道路小人,或相惊恐,云大驾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启谏,必动人情。遂与从驾文官连名进谏。时贵臣赵彦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临时疑贰,季舒与争未决。长鸾遂奏云:“汉儿文官连名总署。声云谏止向并,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诛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张雕、刘逖、封孝琰、裴泽、郭遵等为首,并斩之殿庭。[4]512-513
祖珽与陆令萱之争,就其性质而言,至少有胡汉冲突说[9]92、内廷派系争斗说[6]383-392。暂且不论祖珽与陆令萱之争,就医术之士崔季舒等人谏阻后主大敌当前不可避难晋阳一事来看,其做法实属为国效力,冒死谏言,而韩长鸾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极尽诬陷之能事,怂恿后主屠戮崔季舒等人。最高统治者应该明白,“‘兼听独断’作为一种决策模式,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同时又维护了君主个人的绝对权威”[5]237,只可惜后主高纬没有领悟“兼听独断”的真谛,故在决策前没有广泛征集意见,没有切实把握全局,就对崔季舒等人痛下杀手,致使朝廷损失一批能人贤士。
三、涉入君臣权力之争
王权至上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在整个传统社会中几乎令人无法置疑。“全国一切的最高所有权属于王,臣民的一切是王恩赐的,这两种观念的结合,把王置于绝对的地位,为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10]223。这种理论自然得到统治者的普遍认可,其目的皆在于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维护帝王的绝对权威。《魏书·景穆十二王·阳平王新成附子衍传》载:
颐弟衍,字安乐,赐爵广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请假王,以崇威重。诏曰:“可谓无厌求也,所请不合。”转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传疗。疾差,成伯还,帝曰“卿定名医”,赉绢三千匹。成伯辞,请受一千。帝曰:“《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以是而言,岂惟三千匹乎?”其为帝所重如此。[2]442
这一君臣医疗救护事件的性质并不单纯。众所周知,在政治利益共同体当中,“群臣百官是协调君令民情的必要环节,是实现有效的君权统治的保障。如果臣的环节发生故障,则直接影响国事安危”[5]254,故君主必须依靠或利用群臣,有功则赏之,有罪则罚之,恩威并施,方能驾驭百官,进而维护君主的权威和实现有效的统治。反观元衍主动请封王爵一事,实属否定君主专制的理论,挑战帝王的至上权威,企图左右朝廷加官晋爵大事,遂遭请封不果而转调他州的责罚。元衍到徐州任上患病后虽得到孝文帝派遣医者前去疗疾的宠遇,但医者徐謇诊候救护的医疗实践背后蕴含着三层含义:皇亲罹疾,天子遣医前去救护,以示优宠;臣子请封不遂,难免心有不甘,由此与帝王结怨也不无可能,君王派医前往疗病,以期弥平君臣之间紧张的政治关系;最高统治者号令全国,大权在握,岂容他人染指,左右朝堂?皇帝遣医前去诊候,不无窥探臣子最新动向之用意。无论孝文帝出于何种心态,其派遣医者徐謇前去疗疾的行为都在于守护皇权,维护自己的权威。

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显摄疗有效,因是稍蒙眄识。又罢六辅之初,显为领军于烈间通规策,颇有密功。累迁游击将军,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营进御药,出入禁内。[2]1969
景明二年(501)正月宣武帝巧妙地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禁卫长官领军将军于烈的有力支持,在医者王显互通宫廷内外传递信息的忠心辅助下,成功地发起政变,夺取了孝文帝所设立的顾命大臣的政治权力,开始享有治国理民的最高统治权,并努力建构君主臣辅的权力再分配体系。
统治者既谙熟君臣关系处于一种经常性的主次位序互换状态中,又深知丢掉权力后的惨痛结局,故帝王们为了坐稳皇位,牢牢地把握手中的权力,永享治国理民的统治资格,都千方百计地防范他者觊觎皇位,侵夺至高无上的皇权。一旦出现窃取君权的政治势力,在位帝王为固守一己之利,即不惜大肆杀戮。《魏书·术艺·王显传》曰:
显每语人,言时旨已决,必为刺史。遂除平北将军、相州刺史。寻诏驰驿还京,复掌药,又遣还州。元愉作逆,显讨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2]1969
永平元年(508)皇弟京兆王元愉叛乱,僭号称帝,却因势单力薄,最终“在方镇监控体制和皇帝狡诈权谋的联合作用下战败身死,近属宗王与河北士族则广受株连”[12]。元愉之所以谋叛,敢于否定宣武帝的权威,自然“是对高肇专权、排挤宗室的政策不满”[8]181的正面回应,但双方冲突的实质在于宣武帝压制宗室和巩固皇权的策略,努力颠覆“前朝以近属宗王为藩屏的权力体系,倾力打造外戚、恩幸、疏族三位一体之新格局,从而实现皇权的最大化”[12]。不过宣武帝在伸张皇权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京兆王元愉的挑战,忠诚于王权至上的官员如相州刺史王显自觉或受命担负起平叛职责。医者王显虽然征讨元愉不利,却因是宣武帝心腹近臣而被调任中枢,任太府卿、御史中尉。值得注意的是,对各级官吏进行监督纠弹是御史中尉的基本职能,而在北魏时期“在发生反叛时御史中尉及其属官往往受命平叛”,“尤其对于地方长官的反叛,御史台官员参与或主持平叛,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对反叛者进行审理,纠出参与反叛的成员并绳之以法”[8]188。若再联系景明二年(501)宣武帝废黜顾命宰辅大臣,夺权亲政,王显参与其中颇有密功,就不难想见宣武帝此时委任王显为御史中臣,意在纠治叛党和宗室势力的政治用心。王显走马上任后,也没有辜负宣武帝重托,“及领宪台,多所弹劾,百僚肃然”[2]1969,尽力维护帝王的尊位和权威。《北齐书·斛律金附子羡传》记:
羡未诛前,忽令其在州诸子自伏护以下五六人,锁颈乘驴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门,日晚而归。吏民莫不惊异。行燕郡守马嗣明医术之士,为羡所钦爱,乃窃问之,答曰:“须有禳厌。”数日而有此变。[4]228
北齐后主高纬杀害斛律光,其弟斛律羡因受牵连而蒙难。斛律氏家族被杀事件,既与北周韦孝宽的离间计有关,又与内部祖珽、穆提婆等人联合陷害相涉,但关键在于“斛律光没有处理好与高齐皇族之间的婚姻关系,成为势力强大的外戚家族,功高震主,使北齐后主感受到潜在的威胁”,“双方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隔阂乃至矛盾,而这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激化,要解决矛盾最后只能是一方将一方罢免废除甚至将一方杀戮”,最后北齐后主高纬血洗斛律氏家族[13]。斛律羡被杀之前,曾行禳厌之术,希冀消灾祛祸,为友人马嗣明所知。医者马嗣明是否知晓斛律羡消灾祛祸为何事,是否卷入到后主高纬与斛律氏家族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来,都已较难寻踪觅迹,不过医者徐子范却亲自参与了后主高纬杀害宗室高长恭的政治斗争事件。《北齐书·文襄六王·兰陵武王孝瓘传》载:
芒山之捷,后主谓长恭曰:“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对曰:“家事亲切,不觉遂然。”帝嫌其称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阳,其属尉相愿谓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贪残?”长恭未答。相愿曰:“岂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见忌,欲自秽乎?”长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于此犯便当行罚,求福反以速祸。”长恭泣下,前膝请以安身术。相愿曰:“王前既有勋,今复告捷,威声太重,宜属疾在家,勿预事。”长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扰,恐复为将,叹曰:“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自是有疾不疗。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范饮以毒药。长恭谓妃郑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鸩也。”妃曰:“何不求见天颜。”长恭曰:“天颜何由可见。”遂饮药薨。[4]147
君主说臣子为国家征伐外敌为“家事”,是君对臣的客气话语;臣子称为国家驱敌是“家事”,在帝王看来就是大逆不道。高长恭军功卓著,却在后主高纬面前称驱敌征讨为“家事”,这就犯了大忌,深遭皇帝忌恨。段韶晚年病重,将军队指挥权交给高长恭,以致触到后主痛处,毕竟高长恭的兄弟高孝珩、高延宗同时参加过拥立高俨而废后主的政变,如若高长恭也有类似看法,那么,对于后主而言,手握兵权的高长恭自然是极其可怕的人物,势必除之而后快*参见王怡辰:《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故后主派遣医者徐子范前去毒杀高长恭,解除来自宗室内部的有力挑战,维护自己有效的统治,固守武成帝高湛一系的至高皇权。
四、伴驾外出
天子出行,或视察州郡,体察民情,推行教化,或征伐异己,扬威显盛,安境靖边,皆在于安邦治国,巩固皇权。不过对于古人而言,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而去较不熟悉或完全陌生的地方,都每生恐惧之心。这倒不是说“熟悉的地方,非无危险——来自同人或敌人,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然这宗危险,在或种程度内是已知的,可知的,能以应对的。陌生的地方却不同:那里不但是必有危险,这危险而且是更不知,更不可知,更难预料,更难解除的”,尤其那些怀有异心的人和自然灾害,“在僻静处,在黑暗时,伺隙而动,以捉弄我,恐吓我,伤害我,或致我于死地为莫上之乐”,故“古中国人把无论远近的出行认为一桩不寻常的事”[14]5。于是,君王要安然外出归来,其出行队伍中至少有医者随行伴驾,以备外来各种力量伤害营疗之需。《北史·艺术·马嗣明传》云:
武平末,从驾往晋阳,至辽阳山中,数处见榜,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购钱十万。又诸名医多寻榜至是人家,问疾状,俱不下手。唯嗣明为之疗。问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麦穗,即见一赤物长二尺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惊倒地。即觉手臂疼肿,月余日,渐及半身,肢节俱肿,痛不可忍,呻吟昼夜不绝。嗣明即为处方,令驰马往都市药,示其节度,前后服十剂汤,一剂散。比嗣明明年从驾还,此女平复如故。[15]2976
晋阳是北齐高氏一族隆兴发家之地,几代帝王多有自邺幸晋阳之举。武平末年,医者马嗣明伴驾至晋阳,途经辽阳山中,救疗患病之女,以显皇恩浩荡,关心民瘼。虽然上述材料中没有透露医者马嗣明在出行中救疗后主高纬的点滴信息,但从医者徐謇救护孝文帝元宏的医疗案例中可以找到医者陪王外出的用意和目的。《魏书·术艺·徐謇传》曰:
二十二年,高祖幸悬瓠,其疾大渐,乃驰驿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下治,果有大验。高祖体少瘳,内外称庆。九月,车驾发豫州,次于汝滨。乃大为謇设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陈肴觞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摄危笃振济之功,宜加酬赉。……从行至邺,高祖犹自发动,謇日夕左右。明年,从诣马圈,高祖疾势遂甚,戚戚不怡,每加切诮,又欲加之鞭捶,幸而获免。高祖崩,謇随梓宫还洛。[2]1967、1968
孝文帝把消灭南朝统一全国作为人生最大的政治志向,一共发起三次南伐战争,尤其第二次南伐战争将近一年半,“是孝文帝三次南伐中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成效最为突出的一次,南齐沔北五郡被划入北魏版图,保证了洛阳南大门的安全”[16]266。不过于第二次南伐战争中,孝文帝病重,急诏医者徐謇不远万里前来疗疾,尔后陪伴孝文帝北返,并一路悉心救护。至太和二十三年(499),南齐王朝试图挽回战场颓势,抱病在身的孝文帝带着医者徐謇再次南伐,虽然孝文帝在战场上“成功地阻止了南齐反攻的图谋,有效地巩固了迁都后南伐战争的成果,维持了南北朝之间重新形成的边境线”[16]303,却在身体健康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病情加重而亡于途中。医者徐謇也结束其随军诊候疗治孝文帝病痛的重大使命,随梓宫还洛。医者姚僧垣也有相似随军救护最高统治者的医疗实践,战后便与圣驾一起回京。《周书·艺术·姚僧垣传》记:
四年,高祖亲戎东讨,至河阴遇疾。口不能言;睑垂覆目,不复瞻视;一足短缩,又不得行。僧垣以为诸藏俱病,不可并治。军中之要,莫先于语。乃处方进药,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未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华州,帝已痊复。即除华州刺史,仍诏随入京,不令在镇。[17]842-843
建德四年(575)武帝宇文邕突然誓师大举伐齐,后罹疾退兵,无功而还。至于武帝罢兵理由,颇令吕思勉先生质疑:“是役也,周武帝谓有疾故退师,恐系托辞。或谓以浅攻尝之,亦未必然。以予观之,似以河阴距长安较远,应接非易,恐战或不捷,复为邙山之续,故宁知几而退也。”[18]666吕先生之说甚是。建德三年(574)以后北周在齐周对抗中虽已取得优势,但“北齐的精兵多置于西边,北齐对陈并未尽全力;但北齐之对北周则迥然不同,始终视之为头号大敌,全力以赴”[7]134,故北周想要吞灭北齐也绝非易事,在此次战争中无获而归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论齐周双方备军力量如何,也不管周武帝身体状况如何,医者姚僧垣随武帝宇文邕出征却是不争的事实,其职责自然是诊候疗治病者和伤员,尤其是救护御驾亲征的帝王,以确保君主生命周全,进而稳固军心,奋勇杀敌,或开疆拓土,或平乱安境。
五、受命疗治同僚
医者掌握着一定的医疗技术,又熟谙人身病理,再加上丰富的疗疾效验,往往在疾病疗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故统治者也往往运用太医属官或医药之事,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非常态性的医疗救护措施,进而达到化解潜在冲突与弥平紧张关系的目的*参见金仕起:《古代医者的角色——兼论其身分与地位》,《新史学》第6卷第1期,1995年,第21~24页。。如孝文帝元宏派遣徐謇前去探视疗治广陵侯元衍,即有弥平君臣之间紧张的政治关系的用意。前文已述,不再复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似偶发的、具有权宜色彩的医疗救护措施,实则为最高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政治艺术再现,目的在于协调君臣关系,守护皇权,传递一姓帝王基业。《魏书·术艺·李修传》载:
先是咸阳公高允虽年且百岁,而气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时令修诊视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气微,大命无远。未几果亡。[2]1966
咸阳公高允年事已高,勋绩卓著,孝文帝、文明太后时常向其咨询国家政事。当高允身体微恙时,孝文帝、文明太后派遣李修前去诊候疗疾,以示对老臣的优宠和礼遇。当然,最高统治者宠遇大臣的具体医护举止还有遣太医送方药,遣使存问、赐医药等。《魏书·程骏传》云:
初,骏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问其疾,敕御师徐謇诊视,赐以汤药。[2]1349-1350
《北齐书·儒林·张景仁传》曰:
景仁多疾,每遣徐之范等治疗,给药物珍羞,中使问疾,相望于道。[4]591
医者所固有的知识结构和技艺,就是驱除疾病和维护生命的知识和方法,尤其在医药不甚发达和医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统治者派遣名医前去悉心救护罹疾大臣,既可彰显君王优宠患病大臣之情,又可无形之中固化或升华大臣忠君报国之志。进而言之,君王遣医赐药疗护大臣的行为实则离不开情感的交融和利益分配,即“情感为其表,实利为其里”[5]259。
在方术伎巧之于用而往哲轻其艺的社会氛围中,北朝时期大多数医者本着治病疗伤的利人操守和高尚的医德情操,进入罹疾患病者的私领域,为之治疗病痛,维持生命,延续香火。医者凭借其专业的医药技能,因医疗实践之便而获得最高统治者的特殊宠任,进入君王的公领域,参与国家政务,或佐助新皇登基,或参与君王重大决策,或涉入君臣权力之争,或伴驾外出,或受命疗治同僚,从而在最高统治者的优宠下,在至上皇权的庇佑下,实现自身在官场上的政治价值。
———百年华诞同筑梦医者担当践初心
———百年华诞同筑梦医者担当践初心
——谨以此献给守护黑夜点亮生命曙光的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