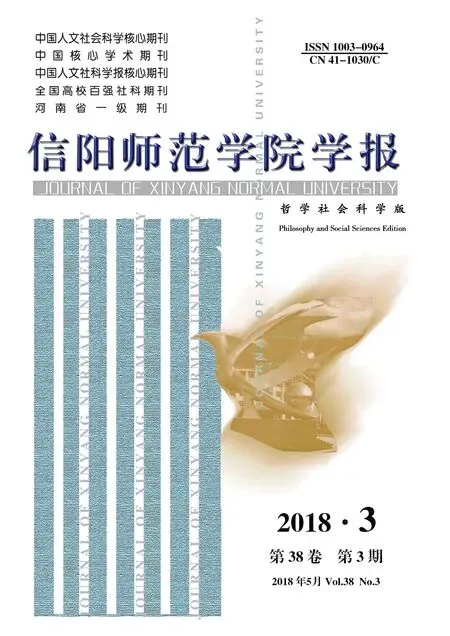刘咸炘的史表观
刘治立
(陇东学院 历史与地理学院,甘肃 庆阳745000)
史表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一种体例,以表格形式勾勒历史轮廓和历史线索,出自古代谱牒,在纪传体史书中是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可以补本纪、列传之不足。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曰:“应劭云:‘表者,录其事而见之。’案:《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曰:“表者,明也。明言事仪。”司马贞和张守节都强调表具有使事物线索明晰的作用。。清末民初学者刘咸炘在讨论史体时,对史表予以较多的关注,并就史表的功用、《史记》与《汉书》诸表的得失进行了分析,对刘知幾《史通·表历》中谬批史表提出驳议。刘咸炘的论断是对唐朝以来史表讨论的全面总结,表现出较高的史识。
一、论史表的功用
史表依历史时间先后将事件按照特定格式排列,使脉络贯通,既可避免遗漏,又能省去许多叙述文字。从司马迁开始,历代史学家撰写史书往往以史表来勾勒历史发展脉络,阐发历史见解。关于史表的功用,历来肯定者很多,牛运震说:“史之有年表,犹《地理志》之有图经,族谱之有世系也,昔人推之,以为史家本源冠冕,盖事繁变众,则年月必不能详;世积人多,则传载必不能备。年表者,所以较年月于列眉,画事迹于指掌,而补纪传书志所不及也。”[1]138刘咸炘在讨论史书体例时,对史表予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诸家之说于表之用犹未尽”[2]404,因此结合各种史书中表的得失展开论述。
首先,史表可以使史书的脉络更加清晰。史表依据时间先后顺序,将史事简明扼要地置于格内,使之脉络贯通,经纬分明。刘咸炘说:“表之为体最易明,而自来学者乃多不明,其所作多不成表,有经无纬,有纬无经,但将直行文字改作旁行而已,无所谓‘斜上’也。此章君所谓绩学之士不如胥吏者也。”[2]404对于几个政权并存的时代,史表更能够将历史线索梳理清楚,“凡一时数国并立者,必须有表,此理易明。《太史书·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始之,欧《五代史记·十国年表》沿之,《三国志》《晋书》、南北史皆当立而不立。万氏及周嘉猷补之,周氏《晋略》亦立表,是也”[2]392。刘咸炘不仅肯定史书中固有的表,如《史记》十表和《汉书》八表,而且对《三国志》等重要史书不立表感到惋惜,对于万斯同等学者所作的补表,也给予很高评价。史表“足明其盛衰相代之势”[2]410,强调史表能让读者更准确地认清历史的发展趋势,把握历朝的兴衰过程。方志乃一方之史,与国史的区别仅仅在于地域全体与一方之异,也需以表来廓清线索,其地理“沿革当作表”[2]446,特定区域的“职官沿革宜作表”[2]448。
其次,史表可以提要纪传,与纪传互为表里。万斯同说:“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3]683四库馆臣评论《后汉书》时说:“范蔚宗作《后汉书》,独阙斯制(指史表——引者),遂使东京典故,散缀于纪传之内,不能丝联绳贯,开帙厘然。”[4]405刘咸炘引用周济《晋略·甲子表序》认为“表本与纪同为纲目也”[2]410,以《史记》为例,“十表与十二本纪互为经纬,划分时代段落,展现天下大势,亦为全书纲纪”[5]156-157。史表可以与纪传互为出入,将纪传中的重要内容以清晰的线索表述,并使纪传部分无法体现的内容得以彰显,“表体之特异在纵横两叙,凡事有两三类,须分别循索者,用直行文字则冗复不明,用表则简而易检,表之为用专在于是,纪传之省,犹其副效耳”[2]404。赵翼曾经指出:“表多则传可省,此作史良法也。”[6]4刘咸炘认为,一些史书由于表的缺失,造成人物关系和历史事件的错乱,出现许多后人无法解决的矛盾,“三国无大事表,致多矛盾;魏收不知立氏族表,而又欲保存谱牒,致使列传芜冗,非不知立表之失也耶?”[2]379如果有了完整的史表,这些失误就可以避免。
再次,史表可以保存史料,网罗遗漏。“邵晋涵《四库提要稿》亦谓《宰相世系表》虽多附会,足备唐人之谱学”[2]410。作史表只有得当与不得当,而不存在须作与不须作的问题,“盖表之立有当与不当,无须与不须。凡其名事烦碎,入传则繁乱不明者,必须表乃明,所谓补纪传、合纪传实兼有之”[2]379。李景星说:“惟作表之法,以简明为贵。凡国家大事,固不容漏略。”[7]107史表似繁实省,“事之零碎无从叙,又不可弃者,则以表驭之;眉目既清,事实又备,实法之最便者也”[8]277。史表网罗遗漏,可以“提要钩玄,持类驭杂。使繁颐之物,归于简约;纠纷之事,达诸整齐”[9]31。当代学者指出《史记》“十表内容不仅表现天下大势,而且紧密地与本纪、列传互补,凡传之不胜传而事实又不容尽没的历史人物,则载之于表中。由于十表的特殊和文字简明,所以它容纳了大量的历史内容以资考证,并且是联系纪传的桥梁”[5]158,这些观点是对刘咸炘见解的继承和回应。
最后,人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刘咸炘强调说:“又有一表为前史所无而实不可不立者,曰人表。”[2]398《汉书》中有《古今人表》,历来受到非议,章学诚在《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中为班固《汉书·古今人表》辩解,认为通古之史不可无人表,“列传裁断所余,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则略者致讥挂漏,详者被谤偏徇,即后人读我之书,亦觉阙然少绳检矣。故班氏之《人表》,于古盖有所受,不可以轻议也”[10]284。不仅通史中需要有人表,就是断代为史,也需要人表,“专门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独断别裁;集众所长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参差同异;强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芜滥猥棼。故曰:断代之史,约计三门,皆不可以无人表也”[10]286。章学诚认为“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10]287。刘咸炘非常赞同章学诚的观点,“盖人之名字、邑里、官阶、履历,有表可检,志传仍可屈曲如事而少支赘隔越之文,此马、班所犹未能而章君特推极之者也”[2]410。刘咸炘提出,“倘立人表,以姓叙之,自可该彼之用。此当更宽于世族,不相妨也”[2]394,他认为在史书中立人表还可以发挥谥法的作用,“如元人之追谥,传中实不必详,但此不必别立一篇,人表立则可以该之矣”[2]394。
二、驳议《史通·表历》的观点
刘知幾自称“多讥往哲,喜述前非”[11]103。他在《史通·表历》中,对史表的起源、形式、用途进行说明,认为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11]16,总体评价很低,甚至反对在编纂史书时置表。刘知幾关于史表的见解过于偏颇,未能客观认识史表的价值,历代学者如郭孔延、胡应麟、朱彝尊、黄叔琳、纪昀、吕思勉等,均对此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刘咸炘在前人的基础上,采取分段评议的方式,对《史通·表历》篇中的具体言论逐条驳斥,所论多发前人所未发。
刘知幾认为史书编纂讲求简要,没有必要为周备而编纂与纪传内容重沓的表,“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11]15。刘咸炘反驳道:“无表则文史不豁,征考无从,史所以纪事,岂有任其偏略而自命为简要者哉?”[2]477简要固然很必要,但刻意追求简要而造成偏略,就会使著述纪事不豁亮,无从征考。
刘知幾说,由本纪、世家、列传等组成的纪传体史书已经足以缜密清晰地反映历史的相关内容,无需再立表。“观马迁《史记》则不然矣。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11]15-16对此,刘咸炘说:“祖孙昭穆,年月职官,传不能委曲周备,故以表补其阙,表之所有,传仅有其十三四,刘氏乃谓‘具有其说’,何也?”[2]477纪传不能详备地阐明历史,而史表则可补其阙漏,从《史记》诸表的内容看,能够在纪传中反映出来的仅占表的十之三四。
刘知幾根据多数读者对表“缄而不视”的现象,论证史表之无用,“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11]16刘咸炘说:“刘知幾谓表历当废,非也。”[2]378他引用万斯同、朱鹤龄和章学诚的观点予以批驳。许多人读史书时漠视史表,徐文靖在为《读<史记>十表》所作的序中已经指出,“后世读史者,于史表不甚省览,即览矣,孰是钩深索隐,心解神悟,多所征发者?大约以十表空格辽阔,文义错综,不耐寻讨,亦古今才学人之通病也”[12]4。四库馆臣认为,“史家之难,在于表志,而表文经纬相牵,或连或断,可以考证,而不可以诵读,学者往往不观。刘知幾考正史例至为详悉,而《史通》已有废表之论,则其他可知”[4]400。刘咸炘说:“读史不读表,乃陋儒徒取文辞之为,不足为读史。且表以备检,即不读,亦非无用。厌而不读,负作者之心,乃咎作者不当作,有是理邪。”[2]477他认为陋儒读史只取文辞,没有领会史家作表的意图,辜负了史家的良苦用心。
《汉书》《东观汉记》祖述《史记》之法立表,受到刘知幾的讥讽,认为是“迷而不悟,无异逐狂”[11]16。他进一步论证说:“必曲为铨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何者?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11]16刘知幾认为,《十二诸侯表》及《六国年表》将春秋战国时列国年代与周秦对照,使“诸国分年,一时尽见”,便于查考。他并不是对史表一概否定,而是分出不同的情况,当天下分割之时,线索繁杂,可以立表;而在四海统一的时代,不必有史表。刘咸炘指出,这种认识太片面,表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而“知幾止知表用于年数耳”[2]477。
刘知幾少年时读《汉书》,“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11]101。在《史通·表历》中,他再次质疑:“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11]16集中批评了班固品评人物的尺度问题。不止刘知幾批驳,刘咸炘也说:“此篇世多讥之,张晏首纠其列等错误,刘知幾讥其失断限及有古无今,凡三言之于《史通》。”[2]184刘知幾在《史通·杂说》篇中说:“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贤愚,激扬善恶为务尔。既非国家递袭,禄位相承,而亦复界重行,犹书细字。比于他表,殆非其类欤?盖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吝而不去,则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终于下下,并当明为标榜,显列科条,以种类为篇章,持优劣为次第。仍每于篇后云右若干品,凡若干人。”[11]162-163刘咸炘说:“按此止讥其体,其说亦苛。时纵品横,经纬已具,何云无以为表邪?若如刘说,先标品类,次列人名,则某人必注某代,反不若表之简明矣。且此安可作志,后世陋方志乃有人物志耳。”[2]187
刘知幾“明于纪传而暗于表志”[2]466,他一方面有废表之论,另一方面又肯定史表的长处。在《史通·二体》中称“表以谱列年爵”[11]8。对此,刘咸炘认为是看低了史表的作用,“表之为用不止列年爵”[2]472,“表已不止谱年爵”[2]470。刘知幾在《史通·杂说上》中分析了史表的作用,“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11]162。梁玉绳批评说:“以为烦费无用,妄加贬斥,不自知其矛盾也。”[13]281孙德谦《古书校读法》卷六指出,“《史通·杂说》篇云云,刘子元于《表历篇》常非之,于此乃以则曰:列行萦行以相属。再则曰:雁行有序,是极言表之旁行,于法最善也”[14]918。刘咸炘也注意到了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对其进行反驳,“《表历》篇言表可废,兹又言表善,殊矛盾”[2]498。
刘知幾对史表的论断,历来史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评论,但大都局限于对个别文句的质疑,刘咸炘逐条驳斥,其评断全面而深刻,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讨论的集大成者。
三、分析《史记》《汉书》诸表的得失
刘咸炘不仅对刘知幾的偏颇之见作了批驳,而且围绕《史记》与《汉书》诸表,于《史记知意》《汉书知意》和《史学述林》中详细论述了史表设立的利弊得失,他博涉诸先贤的论断,分析诸家见解的高下,阐发自己的观点。
(一)对《史记》十表的论断
《史记》自三代讫太初,有一个世表,八个年表,一个月表,共计十表。十表意在解决“并时异世,年差不明”[15]3319的问题,反映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几千年历史嬗变的大势,每表记述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事件及职官制度等,如《三代世表》“纪黄帝以来讫共和”,《十二诸侯年表》“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六国年表》“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
《史记》十表揭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历来有史家予以评断,甚至写出著作,如清朝汪越的《读史记十表》十卷“排比旧文,钩稽微义”“订讹砭漏,所得为多”“于史学之中可谓人略我详矣”[4]400。吕祖谦《大事记》称“《史记》十表,意义宏深”,郑樵《通志·序》中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于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更是对十表推崇备至。在《史记知意》中,刘咸炘对十表作了全面的探讨。
对于《三代世表》的论断,是结合对《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史记志疑》观点的分析体现出来。《史记索隐》认为,“三代代系长远,宜以名篇”。《史记正义》认为,“言代者,以五帝久古,传记少见,夏殷以来,乃有《尚书》略有年月,比于五帝事迹易明,故举三代为首表”。刘咸炘比较两家意见,认为《史记正义》的说法更符合实际,“按《正义》说是也。以三代尤详可考,寓考信六艺之意耳。仍从黄帝起者,犹之先经始事耳。《索隐》但以长远为说,甚陋”[2]48。桓谭概括史表的形式为“旁行斜上”,当代学人认为“旁行”即谓横行,即由右而左的左行,“旁行斜上”就是一种“表”与“谱”结合,亦即”二维结构”与“树形结构”完美融合的逻辑表达方式[16]162。梁玉绳认为《三代世表》“有旁行无斜上,久失其旧,则知帝泄以下之无属固因试析脱误,不能绵历无差,亦缘连叙殷、周之世于前,遂致乖绝。而列侯之属不相当,均是传写误耳”[13]281。刘咸炘认为梁玉绳的说法不正确,“旁行斜上即谓纵横维格,无属自因无考,非由脱误。此表本止以世次排列,不取其年相当”[2]49。
《史记》诸表的小序文字揭示历史演进的趋势,阐发见解,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刘咸炘认为:“古今之变,莫大于周、汉之际,《六国年表》序挈其大旨。”[2]24《六国年表》的小序追述了战国七雄的形成及最后为秦统一的过程,指出经过秦始皇焚书,六国史书尽毁,只有秦国的史书较为完备地保存下来,司马迁“因《秦记》,踵《春秋》之后”,编纂《六国年表》。司马迁对于秦的兴盛,感到无法解释,因此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14]685刘咸炘引吴汝纶的话说:“此乃反复推求,不得其所以并天下之故。”[2]51梁玉绳对于表中七国的排序,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则七国宜何以书?曰:周表之下晋为首,燕次之,楚次之,齐次之,秦次之;晋 、齐之灭,然后次韩(晋公族,故先之)、次赵,次魏于秦之下,次田氏于三晋之下,庶几得之”[13]388。刘咸炘认为六国表是根据《秦记》而作,秦为表主,当然不能居于末位。他说:“梁氏谓当作七国,且谓先书三晋为夺君与臣,当改为晋、燕、楚、齐、秦,此亦不读序之妄论。此表乃表战国,晋不过缘起耳,秦乃表主,岂可居末?”[2]51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的小序较其他诸表序为胜,李景星认为其撰写风格独特,“亦得体,亦得法,而辞气又极醇雅”[7]110。这主要是就文法而论。汪越在《读史记十表》卷五《读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中则主要探讨了小序的意旨,“太史公序形势二字,其主意也。侯国强则王室弱,侯国弱则王室强,故于诸侯先言其疆域之大,又言汉所有仅自三河至于内史,此形势在候国也。后言推恩分子弟国邑,历举诸国分裂之数,与天子支庶、王子支庶尊卑之等,其支郡山海咸纳于汉,与汉郡错诸侯间,此形势在王室也。一篇之中,反覆照应,而结之以仁义为本,与周尊尊亲劳同道,封建所以公天下,其义自见”[12]46。汪越的分析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刘咸炘没有再重复前人的认识,只是说:“封建改而为郡县,《诸侯王表序》言之。”[2]24表明了该小序的主旨是封建制转为郡县制的历史发展“形势”。
白寿彝称“《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17]75。刘咸炘评《秦楚之际月表》“案梁说固非,钱辨亦谬。是书乃通史,不以汉为主,表之用,所以齐不齐。秦统一时,本不须表,故附书《六国表》后,而不别立,秦末则须表,故立此表,名秦楚者,正以上接六国,下接汉兴耳。此乃事之自然,非有抑秦尊汉之意。钱氏所说,皆是支词。《自序》曰:‘八年之间,天下三嬗。’夫岂不以楚汉继秦乎?要之,史表所以明事势,非以褒贬,一切推测争论皆无为徒劳耳”[2]55-56。他强调《史记》诸表的要旨在于“明事势”,这种认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对《汉书》八表的论断
在讨论《汉书》八表时,刘咸炘结合《史记》诸表的相关内容展开。
《汉书》有《异姓诸侯王表》和《诸侯王表》,而在《史记》中无此区分。《史记评林》征引黄履翁的说法,认为《史记》的编次表明汉初亲疏相错之旨,而班固的分类编纂则无法体现天下大势。刘咸炘认为,这样的认识不符合历史实际,第一,《史记》和《汉书》分属通史和断代史,要求自然不同,“马书通史,宜略;班书断代,宜详。马书仅至孝武,班书直至莽篡,则分立宜也”[2]182。第二,《史记》年经国纬固然很好,“然汉初诸王国与后所分封之国,疆域不同,同在以纬,本不相当;且武帝以后,诸王衣食租税无事可书,年代绵久,徒多空格,班氏更为国经世纬,固得其宜矣”[2]182。时势各异,划出分列有其合理性。第三,《史记》与《汉书》所叙述的时间断限有别,期间分封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汉书》有异姓王,止是沿袭,何曾有亲疏相错之意?班氏分别为二,以示初有异姓,后乃尽为同姓,正足表大势之变耳”[2]182。黄履翁批评班固所作异姓和同姓诸侯王表不能反映历史大势,只是看到了表面,实质上两表相连很好地概括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特别是《诸侯王表》“述古过秦,抑扬不尽。高祖矫枉过正,卒折诸吕,景、武抑省诸侯,王莽诈谋始成,终始强弱,综括无遗”[2]182。
刘咸炘认为“黄氏之言,无一当也”[2]182。这不仅是针对黄履翁对异姓与同姓诸侯王表而言,而且针对其他几个表。如对《王子侯者表》(上)断限的论断,刘咸炘认为“非也”[2]182;而黄履翁对《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不能验证当时得失的认识,再次强调“此说亦非也”[2]183,刘咸炘云“班书若仍分立,则昭宣元成又当别立一篇矣。可并则并之,而得失固仍可见也。至于改年纬为世纬,亦有其故。《史记》于前二表,亦仅有朝代,武帝朝仍用纪元,班书合昭宣以后,若尽列纪元,则纸幅难容,徒多空格,若止用朝代,则亦与纪世次何殊,故悉用世次为纬,亦其宜也”[2]183。刘咸炘揣摸司马迁与班固作表的本意及遇到的技术问题,做出合理的推断。
“篇章博举,通于上下,略差名号,九品之叙”[18]4241。《汉书》的《古今人表》所列人物上起传说中的太昊,下迄秦末,收录人物近二千个。班固依据孔子分人以上智、中人、下愚三等的标准,把历史人物又细评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桀、纣,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于莘、崇侯与之为恶则行。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18]861。从中看出,班固不以人的政治地位作为划分等级的依据,而是以其功业和品格。班固排除了人物的国别、民族的界限,从人类道德发展的宏观角度分析人类社会的演变,通过道德的善、恶变化来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从而建构了一个道德古史系统。同时,《古今人表》把九黎、三苗、由余等都纳入统一体中,各民族生息、共存于统一体中,从而得出大一统历史观。
对于《汉书·古今人表》历来争议颇多,主要集中在所记述人物超越了西汉的界限和人物品级的划分上。有人认为其有古无今,不合体例。颜师古说:“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书未毕故也。”[18]861张晏对于表中人物品级划分提出质疑:“老子玄默,仲尼所师,虽不在圣,要为大贤,文伯之母达于礼典,动为圣人所叹,言为后世所则,而在第四。田单以即墨孤城复辟强齐之大,鲁连之博通,忽于荣利,蔺子申威秦王,退让廉颇,乃在第五。大姬巫怪,好祭鬼神,陈人化之,国多淫祀,寺人孟子违于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宫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嫪毐上烝,昏乱礼度,恶不忍闻,乃在第七。其余差违纷错不少,略举扬较,以起失谬。独驰骛于数千岁之中,旁观诸子,事业未究,而寻遇窦氏之难,使之然乎?”[18]862-863刘咸炘认为:“案班列次表,本以补马,犹唐撰《隋书》,因作《五代史志》,此史家特裁也。不及今人,自有其故。列等错谬,亦未可苛责。苛非精义之圣,孰能褒贬至当,传写又多伪邪?”[2]184由于这个问题“昔人辩之详矣”[2]184,刘咸炘就征引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梁玉绳《人表考》、章学诚《亳州志人物表例议》、蒋湘南《书古今人表后》、恽敬《大云山房集·古今人表书后》等的相关论断,来分析《古今人表》的问题,认为这些学者对《古今人表》出现的根源、分类的依据、表达的思想见解等方面的认识虽有所不同,但各有其道理。梁玉绳《人表考》说:“若表今人,则高祖诸帝,悉在优劣之中,岂孟坚所敢出哉!”[12]493这主要是从政治顾忌的角度考虑的。蒋湘南认为表未见汉朝帝王,是因为“今人表未出”,推断是书稿本身并未成完帙造成,与颜师古的观点相近。恽敬则提出,“孟坚于汉之君臣,不可差等,次古人,即以表今人”[2]186,这种带有猜测的说法尚有一些道理,但他进一步做出推论:“于身无事功而为弑与不弑被灭者列第九等,乃所以著哀、平、王莽之罪。齐桓列第五,秦始皇列第六,老子列第四,而高祖、文帝、武帝可推知。”[2]186-187却明显有穿凿臆断的成分,刘咸炘批评说:“此则大凿矣。”[2]187
历代学者讨论史表者很多,但像刘咸炘这样全面分析史表的并不多见。刘咸炘的史表论是其史体论的重要构成部分。无论是讨论史表的作用,还是表达自身的史表观,抑或是评论具体史书中的史表,刘咸炘都以史学发展的实际为依据,总结和吸收前任的成果,指陈得失,推进了对史表的研究,丰富了历史文献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1] 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历代名家评《史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 黄曙辉.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 爱新觉罗·永瑢,纪 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 安平秋,张大可,俞樟华.史记教程[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6] 赵 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评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 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9] 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 章学诚.文史通义[M].长沙:岳麓书社,1993.
[11] 刘知幾.史通[M].长沙:岳麓书社,1993.
[12] 梁玉绳,等.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 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 赵吕甫.史通新校注[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 赵 益.《史记·三代世表》“斜上”考[J].文献,2012(4):158-182.
[17]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8] 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