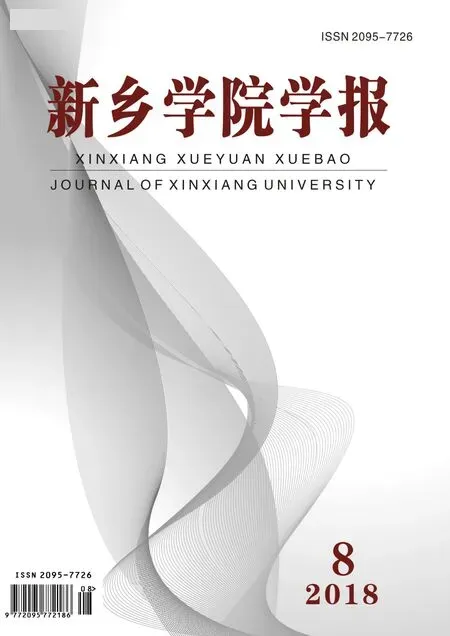从《受戒》看汪曾祺的佛教文化意识
赵文阁
(新乡学院 素质教育中心,河南 新乡453003)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佛教文化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受戒》虽描写佛教僧众的生活场景,但却别出心裁地把重点放在了对佛教世俗化的描写上。
一、《受戒》中描写的佛教文化
(一)和尚的称谓
《受戒》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明子出家前后发生的故事。明子当和尚是他小时候家里决定了的事情。因为家里田少,几个哥哥就能把地里的活儿干完,而明子恰巧又有一个当和尚的舅舅,明子的母亲便和明子舅舅商议,要让明子去当和尚。舅舅先给明子相面,确定明子符合条件后,约定了接明子出家的日期。
关于明子要当和尚这件事,《受戒》是这样描述的:“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1]2这说明当和尚也是需要很多条件的,比如,和尚要学习经文,就必须认字,认字就成了一个重要条件,所以明子的父母就让明子去读了几年书,读书期间取了个学名叫“明海”。
明子要出家,先要取个法名。所谓法名,便是一个僧人准备出家修行时取的名字。一般来说,同一个人,出家和在家的名字是有差别的,《受戒》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明子刚准备入荸荠庵当和尚的时候,因为舅舅说“明海”这个名字无需再改,所以明子就直接用“明海”这个名字当了法名。在荸荠庵里,除了明子之外,其他和尚都另取了自己的法名:最年长的那位是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和尚,法号普照,明子的舅舅一般称他为师叔;明海的舅舅法号仁山,人称大师父或者山师父;另外两个与仁山同辈的和尚分别叫仁海和仁渡,有人称仁海为二师父或者海师父,对仁渡却直接称呼其法名仁渡。无论如何称呼,荸荠庵的每一个和尚都有起法名的意识。
出家人六根清净,自然也没有亲情的牵绊,在佛教生活中没有辈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听到的许多僧人法号里有同一个字,并不是像世俗家族中同一辈分的人名字里有同一个字,而是为了把法脉延续下去,让人们知道他们是同属于一支法脉的传人。
佛教僧众的身份不同,他们所受的戒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把这当成区别他们身份的标志。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影视里听到人们提到“师叔”“师伯”等对僧人的称呼,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称呼并不准确,因为佛教没有我们常人所说的辈分问题。然而,他们却可以相互称对方为“师兄”“师弟”,毕竟,佛教观念是众生平等,所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在这里是可以借用的。比如《受戒》中的仁山、仁海和仁渡,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仁”字,可以看出,他们是同属于一支法脉的传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受戒》对佛徒辈分和法名的描写还是很写实的,荸荠庵里这些和尚的名字起得很有讲究,由此可知汪曾祺先生是有一定佛教知识储备的。
(二)佛教习俗
荸荠庵里的和尚拥有一项用来谋生的本领,那就是受邀去附近的农户家里做法事。一般来说,他们做法事采用的形式就是放焰口。这一带的村子里,哪一家如果有人故去,便会去荸荠庵里请和尚来家中做法事。《受戒》中写道,如果是做冥寿,因为现场氛围不是特别伤感,所以通常不是按照最悲戚的那种形式,而是依据主家要求来做,有时候就会放花焰口。焰口,即饿鬼,因生前鄙吝而投为没有福报的鬼,由于业报的关系,即使遇到可口的食物也无福享用。人们根据它们的形象,即口中喷出烈焰,给它们取名字叫“焰口”。放焰口主要的照顾对象就是它们。放焰口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些沦为饿鬼道的鬼怪吃上一顿饱饭,让活着的人显示他们的孝心。做法的和尚念很多真言神咒,让饿鬼道的大小鬼怪们可以不受饥饿的折磨,吃到做过法事的食物。放焰口不只是为了召请饿鬼前来饱餐一顿,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宣扬佛法,让饿鬼道的那些鬼怪们转变自己的心性,甚至永远脱离饿鬼道的种种折磨。和尚放焰口,是佛家慈悲心的体现,荸荠庵的和尚很明显也保留了这一传统。
在《受戒》中,汪曾祺用了很多的笔墨来写明子去受戒这件事情。受了戒会在受戒者头顶上留下戒疤。戒疤还有一种叫法,即香疤,它一般是佛教僧众为了保持自己内心的纯净而在身上燃香留下的痕迹。这种在僧众身体上留下疤痕的现象最早起源于佛教中的 “舍身供养”这一思想,是佛教僧众为了割舍掉自己内心的固执和念想而体现在身体上的一种虔诚的行为。以前僧人受戒的时候,依据头顶上所点的戒疤的数目分为六种形式。在这六种戒律中,公认最受人尊敬的是“菩萨戒”。受戒者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家的佛教信徒,另一种是在寺庙中当和尚的人。相传烧戒疤始于元朝,后来,逐渐演变成每个和尚都要遵守的规矩,以至于后世佛教徒都以烧戒疤的形式表达对佛主的虔诚。
所谓受戒,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通过参加一种仪式来获得可以表明自己是合格和尚的一种凭证。受戒需要到一个专门的地方,受戒后会在受戒者头上留下戒疤。《受戒》对明子受戒的场景有比较详尽的描写。明子要到善因寺去受戒,到了善因寺,他先去报名办事。受戒之所以选在夜里,是因为烧戒疤的时候是不让别人观看的。文中还介绍了烧戒疤之前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先请手艺精湛、技法熟练的师傅来剃头发,然后再用枣泥在头皮上做好标记,即画上圆圆的点。烧了戒疤之后要喝蘑菇汤,再用“不停的走”这种形式散戒。
《受戒》对佛教文化的细致描写,反映了汪曾祺有着深厚的佛教知识,因此他才能准确地描写荸荠庵和尚的生活,这与他青年时期在庵中避难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二、《受戒》中僧众生活的世俗化
(一)关于称谓
明子为了达到当和尚的标准,在进荸荠庵之前念了几年书,家里又给他起了“明海”这个学名。因为按照常理来说,出家人和在家人的名字应该是不同的。明海的舅舅却说这个名字不用改,导致“明海”这个名字既是学名又是法号。这样的随意拉近了僧俗两类人的关系。
庵里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和尚,是明子舅舅的师叔,明子喊他师爷爷。然而在佛教僧众中,是没有师爷爷这样的称呼的,甚至连“师叔”“师伯”这样的称呼都是逾越佛教制度的。从这样的称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荸荠庵中和尚浓厚的世俗化色彩。
(二)关于和尚娶亲
佛界本来定下了和尚不准与女人接触的规矩,可是《受戒》中的和尚却不遵守这个规矩:仁海作为荸荠庵的二师父,在家里是娶过亲的,而且他会在每一年的夏末秋初带他的妻子来荸荠庵里避暑。三师父是个有智慧又肯卖力气的和尚,他不但多才多艺、本领高强,而且精通经文和忏悔文。他的一场“飞铙”表演,使他出尽风头。和尚放过焰口后,有的大姑娘小媳妇会因仰慕和尚而跟他偷偷离家出走。有传言说,仁渡也有好几个关系暧昧的异性。
和尚有女人,荸荠庵并不是特例。善因寺一个名叫石桥的方丈,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个德高望重的和尚,也有传言说他有一个年仅十九岁的漂亮小媳妇,其他人自然更不必说。然而,“这里的破戒并不意味着低俗和沦落,而是象征了人性”[2]。
《受戒》的主人公明子,与他邻居家的女孩小英子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成天玩儿在一起。农忙时节,小英子常常去挖荸荠,还带明子一块儿挖,田地里的嬉戏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这正是明子和小英子两人之间恋情的萌发点。然而,即使这种懵懂纯真的情愫,也是不符合清规戒律的。《受戒》的结尾写道,明子受戒回来,小英子在船上和他说话。得知明子有机会当沙弥尾,即有机会当方丈之后,小英子感觉到自己的爱情可能会受到威胁,坦率地说出不想让明子当沙弥尾的话来,甚至许诺给明子当老婆。“《受戒》的最后结局是一种圆满,明海和英子过着幸福的日子。这种小说中所创造出的和谐,体现着一种圆融之美”[3]。
(三)其他世俗化生活
仁渡多才多艺,会放花焰口,还会唱小调、山歌。有些做冥寿的人家,或者是需要做法事的家庭中有些不是很正经的亲朋好友,就会提要求说要放花焰口。花焰口,简单来说,就是在做完正经的法事以后,让来做法事的和尚唱一些小调,类似于现在农村吹响器的形式。小说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有一次很多人在谷场上聚着聊天,仁渡被大家围着唱了一个安徽小调:“姐儿生的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1]9这种轻佻的言语,从一个和尚口中说出来的,实在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佛教有一条戒律:“不捉持金银戒。”[4]字面来看,就是不使用钱币。我们再看《受戒》里的和尚,不但有三本账,还把放焰口当营生。仁山是荸荠庵当家的,桌子上放着三个账本,分别是经、租和债三种账。荸荠庵里的和尚把平日里放焰口得到的收入记在经账本子上。庵的附近有几十亩田地是属于荸荠庵的财产,和尚们自己种不了那么多,就出租给周边的农户,当然这些都是要收取租金的,自然记在租账上。此外,庵里还放债,这些账目也记在了债账上。荸荠庵活脱脱就是一家生意店。
荸荠庵里的和尚闲暇的娱乐方式和在家人也极为相似,无非斗纸牌、搓麻将。“桌子一放好,仁山就从他的方丈里把筹码拿出来,哗啦一声倒在桌上”[1]10。 《受戒》在描写三师父仁渡时,提到他脑子聪明,打牌经常赢,所以别人找他玩牌的时候常客气地说:“想送两个钱给你。”从“筹码”和“送两个钱给你”可以看出,他们不止是单纯地斗牌,还有筹码小赌一下,以至于输了就骂粗话。
荸荠庵的和尚不但行为是世俗化的,甚至连思想也是充满世俗色彩的。从描写受戒的文字中,我们看到,受戒人主要关注的是受戒的好处:受了戒就是正经和尚了,即使到别的寺庙去也同样受人尊敬,还能做更多的法事,挣更多的钱。明子是这样理解的,也是这样对小英子说的,明子有这样的想法,自然得益于庵里的其他和尚——尤其是明子的舅舅的教导。
《受戒》对佛教生活做了许多与众不同的描写。汪曾祺先生在完成《受戒》这部作品后明确地说过:“发表《受戒》是需要勇气的。”[5]这表明汪曾祺自己是知道《受戒》的独特性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本人也是愿意追求这种异质性的。
三、结语
汪曾祺从小就生活于佛教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中,他的祖父、祖母、继母及家里的佣女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这种潜移默化的感染也体现在他的小说的创作中。在汪曾祺的文学作品中,传统意义上的佛教价值观被消解殆尽,读者看到的是对佛教清规的漠视,充满了世俗文化。尤其是《受戒》这部作品,最为明显地体现出汪曾祺独特的佛教文化意识。这种风格是他与其他作家最明显的差异,也是汪曾祺小说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