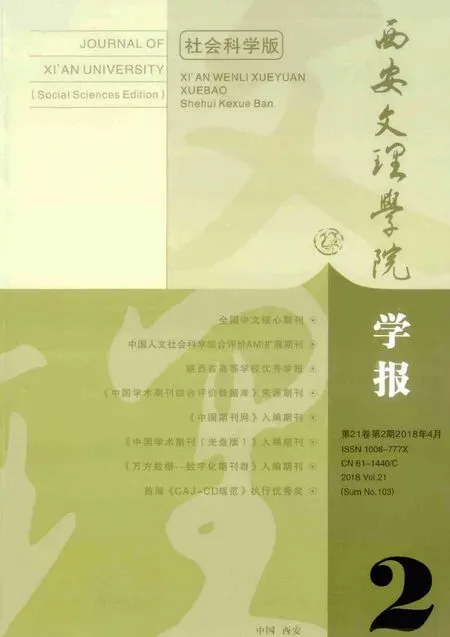宋代地方官赴任探析
宁欧阳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宋承唐末五代之乱而建立,实行“右文”政策。在科举取士数量逐渐增加的基础上,恩荫制在宋代也呈现了“数额冗滥、范围甚广”等特点,[1]这使宋代官僚队伍一直居高不下。宋代统治者在人事政策上继承了前代“三年任期”制,但随着官僚队伍的逐渐扩大,“三年任期”制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出现了两年一任、甚至不足一年一任的情况。[2]频繁的官位调动,使得地方官赴任成为宋政府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宋政府对地方官赴任问题投入了足够多的精力,不仅会在路途中给予赴任官员各式各样的帮助,并且对地方官赴任前后程序、赴任期限、家属携带等问题做了详细规定。赴任者本人在面对经济困境和安全威胁时,也会想尽办法解决。目前学术界对宋代地方官赴任问题虽有涉及,但并不充分。*详见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7页;张聪著,李文锋译:《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3~104页;王福鑫:《宋代旅游研究》,河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3~53页,187~204页;刘馨珺:《从墓志铭谈宋代地方官的赴任》,《东吴历史学报》2004年12期,第159~196页;苗书梅:《朝见与朝辞——宋朝知州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方式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期,第112~119页;黄纯艳:《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以欧阳修于役志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1期,第21~28页;赵碧云:《清代地方官赴任研究》,《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9期,第57~60页;李永卉:《试论南宋地方官员的离任审计法律》,《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4期,第18~25页。本文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该问题作相对系统全面的梳理,不仅可以从侧面了解宋代官吏管理制度,还能部分地反映官员生活中的面相。不当之处,还望方家多多指正。
一、官员启程赴任前的准备工作
地方官到新州县任职前,需获得一系列的文凭与印章,且向皇帝、宰相、御史台长官辞别谢恩。
(一)文凭与印章
赴任前,吏部会将告身发放给官员,告身是证明自己职务与官阶的凭证,官员领取告身时,往往要缴纳一笔费用(绫纸钱)。如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五月诏:“百官为父有(母?)官,先曾降麻制授官者,纳钱五千。”[3]3347又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诏:“官告院应选人注官,令纳朱胶、绫纸钱,许选人情愿就便送纳。”[3]3350但对于官职低微、收入较少的官员,宋政府也会减免所需缴纳的绫纸钱。至道元年(995)二月,“应中书除授幕职州县官,陵纸并令赐予,不更纳钱。”[3]3347这表明幕职州县官在此前是需要缴纳绫纸钱的。宋代统治者对告身的制作和发放可谓达到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4]382的程度,为防止不良之人伪造告身或告身被冒用的情况发生,告身除了注明官员职务和官阶外,还会记录此人岁数和形貌特征。如云:“长身品,紫棠色,有髭髯,大眼,面有若干痕记”,或云“短小,无髭,眼小,面瘢痕”之类。非常遗憾的是,元丰改制废除了在告身上书写体貌特征的制度,导致南渡后“承袭伪冒,盗名字者多矣”的局面。[5]25因此,到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有官员建议告身应写明三代、乡贯、年甲,并得到了采用。[3]3356
除了告身外,宋政府还会颁发给赴任官员一种叫“历子”的文凭,是由官员的直接上司负责填写,用于记述官员政绩功过以备考课升降之用的本子。史载:“先是,诸州掾曹及县令、簿、尉,皆户(吏?)部南曹给印纸历子,俾州郡长吏书其绩用愆过,秩满,送有司差其殿最。”[6]3758在得到“告身”“历子”后,官员就可以领取官印了。官印的获取通常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在礼部领取,另一种是到所任职之地进行官印交割。《宋史》载:“礼部掌国之礼乐、祭祀……若印记、图书标疏之事,皆掌焉。”[4]3851又熙宁五年(1072)诏:“内外官及谿洞官合赐牌印,并令少府监铸造,送礼部给付。”[4]3592可知官印的发放由礼部负责。在任官员任期结束后,有时会把官印留在当地,“诸守臣因事罢黜指挥已到,就当日将牌印交以次官,批罢离任”[7]56。只有因犯罪而被罢免之官须立刻把官印交给临时代职官,然后由代职官转交给新任官员。
(二)辞谢
在获得文凭与印章后,还需要履行一系列辞谢仪式。新任官员要上殿向皇帝表示感谢并辞别,称为“朝辞”。史载:“先是,京朝官授远地及缘边知州、通判,朝辞日,许升殿。”后来因为官员多汇报无关紧要的事,故咸平四年(1001)规定:“始令奏听朝旨,得报,乃许升殿。”[4]1064南宋时,朝辞得到了更加严格地执行。乾道六年(1170)八月诏:“应今后文武知州军、诸路厘务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见辞,并令上殿,批入料钱文历,如托避免对,并不得差除赴任。委台谏、监司常切按察,以违制论。”[8]可知,不仅扩大了朝辞人员的规模,而且禁止“托避”不朝辞的官员赴任,并处以“违制”罪名。除了向皇帝进行辞谢外,还需到宰执和御史台处辞谢,分别称为“堂谢”和“台谢”。史载:“授官职朝谢毕,谢宰执。”[9]91说明在“朝辞”结束后,需要到宰相处进行谢别。关于台谢,北宋时规定:“故事,通直郎以上迁官,皆赴台谢,惟两省侍从官则否。”[10]1241可知台谢的范围限于通直郎以上的官员,但两省侍从官除外。南宋时,台谢范围扩大,所有在京除授的官员都得到了台谢机会,“所有在京除授及转官,合赴台谢,或赴外任,亦合台辞,并照例给关子付本官。”[3]4512通过“朝辞”“堂谢”和“台谢”三条与地方官员直接交流的途径,中央高层领导者(皇帝、宰执和御史中丞)不仅可以树立自己的权威,了解官员的品行才干,还可以获知基层民情和地方政绩。
二、官员赴任的花费问题
宋代交通欠发达,官员花费在赴任途中的时间多以月计算。另外,多数官员赴任并非只身一人。因此,官员准备启程赴任前,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应付赴任途中的花费。考据史料发现,官员赴任费用主要由两部分构成:自我筹集和官方资助。
(一)自我筹集
现存史料反映了宋代某些官员的经济状况,《燕翼诒谋录》载:“国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迎送。小官到罢,多芒履策杖以行,妇女乘驴已为过矣。”[11]9小官因贫困,赴任甚至需要步行。陆游曾论及自己的经济状况时说道:“贫不自支,食粥已逾于数月。”[12]197又如何坦离任后“无以振其行李,县之士民哀其穷而为之裹囊以饯之”[13]。虽然赴任费用对于一些清贫官员来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科举难、改官难”[14]的现实状况促使他们格外看重赴任机会,会通过各种途径解决费用问题。
1.亲友资助
咸平二年(999),王禹偁被贬谪到黄州,毕士安“亦罢职守潞州,人皆咎禹偁。公曰:‘元之家贫,安能遽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两赆禹偁,禹偁乃能为黄州之行”[15]。王禹偁被贬黄州之前的职务为知制诰(阶官为刑部郎中),[4]896-901知制诰这样的官员,仍需朋友的资助才能赴任,对于那些职微俸薄的中下级官员,其赴任艰难可想而知。陆游曾讲道:“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阴。以贫悴逐禄于夔。其行也,故时交友醵缗钱以遣之。”[12]334此条史料固然有“哭穷”的嫌疑,但大体是可以相信的。为了支持赴任,地方官的妻子甚至抵卖妆奁帮助丈夫。如:“自大司马使西鄙,奏君为其属。君顾太夫人春秋高,将辞不行,夫人曰:‘行矣,妾在侧,君奚忧?’于是尽斥奁中之藏,具滫髓滑甘,以时进馈。”[16]由此可见,亲友资助是赴任费用的重要来源之一。
2.借贷
宋代也存在官员赴任借贷的情况,为了防止赴任借贷可能造成的官员腐败,宋政府很早就对赴任借贷做出了限定。大中祥符元年(1008),“新及第授官人,无得以富家权钱,倍出利息。至任所偿还,所在察举之。”[4]1544但实施效果并不是很好,赴任借贷仍时有发生。章惇“初宰信州玉山县,以忧去。服除,再知玉山县,带京债八百千赴任”[17]。又绍兴二十四年(1154),“保义郎李琦监和州东关镇税,家颇丰赡。有高指使者,赴官舒州,与其妻来谒,愿贷钱五万为行装,约终任偿倍息,李如其数假之。”[18]这种情况迫使南宋政府不得不加大对赴任举债行为的惩罚力度,“诸命官举债而约以任所尝者记本过五十贯,徒两年”。[7]902但考虑到一些官员的俸禄并不足以支撑家庭支出,故赴任举债情况屡禁不止。
(二)政府资助
宋代官员赴任费用除了自我筹集,还能获得来自政府的资助。
1.公使库资助,或预支俸钱
宋政府考虑到官员赴任的经济困难,宋太祖年间就设立了公使库,以资助官员赴任,“太祖即废藩镇,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于是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馔,欲使人无旅寓之叹”[5]42。《燕翼诒谋录》对公使库做了更加详细的记载:“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所馈之厚薄,随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损有余补不足、周急不继富之意也。”[11]29可知设置公使库就是为了资助官员赴任,且根据官品高低、家属多寡,资助程度也不同。同时,公使钱的设置也可以避免赴任官员的扰民行为,减轻百姓负担。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盖祖宗之时,以前代牧伯皆敛于民,以佐厨传,是以制公使钱以给其费,惧及民也。”[19]
另外,宋政府还允许赴任官员提前预支俸禄,根据赴任地距京师的远近预支不同的数额。大中祥符三年(1010),“幕职、州县官,除广南、福建路已令预借俸钱外,江浙、荆湖远地,麟、府等州,河北、河东缘边州军,自今并许预借两月俸,余近地一月。”[4]1666但政策落实到实际运行中,总会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宝元二年(1039)十二月,“夏竦乞预借月俸以办行李,诏特借一季”[4]2888。破坏了远地两月、近地一月的俸禄预支规定。
2.驿劵
在宋代,驿劵是官员入驿食宿的凭证。宋初“内外文武官,下至吏卒,所给劵皆未有定例,又或多少不同”。为了解决这种混乱无序的局面,嘉祐四年(1059)正月,张方平进献“驿劵则例”,赐名为《嘉祐驿令》:“并取宣敕、令文专为驿劵立文者,附益删改为七十四条,总上、中、下三卷,以颁行天下”[4]4548。对驿劵规定之详细可想而知,遗憾的是《嘉祐驿令》未能流传至今。值得注意的是,宋政府还会根据赴任地区的不同发放不同类型的劵。史载:“京府按视畿内,幕职、州县出境比较钱谷,覆按刑狱,并给劵。其赴川峡者,给驿劵,赴福建、广南者,所过给仓劵,入本路给驿劵,皆至任则止。”[6]4145官僚队伍的快速增长,给宋代财政带来了较大压力,熙宁八年(1075)权发遣河东转运范子奇言:“近年非次朝旨差官时暂勾当,于俸给外增驿劵,举天下言之,耗费不少,乞自今已有本俸给者,罢给驿劵。”[4]6607故于次月下诏:“自今差官出外,已支赐者毋给驿劵,愿请驿劵者不支赐。”[4]6623就是说,官员赴任时只能获得“支赐”或“驿劵”的其中一种。
3.随行吏卒配给
宋政府为提高赴任效率和安全,给官员们配备了数量不等的吏卒。随行吏卒人数配给经历了至道三年(997)、天圣七年(1029)、熙宁七年(1074)[3]2373-2375三次调整,形成了从幕职州县官到知判州府使相20个不同等级,所差人数从7人到550人不等的规定。南宋时,《庆元条法事类》对配给吏卒做了更加详细明确的规定。[7]186-190为保证赴任安全,宋政府还会派军士护送,康定元年(1040)七月诏:“臣僚赴官、罢任所过山险之处,量差军士防送,毋得过迎送人数之半。”[4]3025宋政府甚至对随行吏卒的使用时间做出了限制,“诸接送人已到本处,过十五日无故不起发,及不遣回者,计所过日并依私役兵防律,缘路无故稽留通计过十驿程之半者,罪亦如之。”[7]182对于过期使用吏卒之官,处以法律上的罪名。宋政府对吏卒接送距离也有限定,且水路与陆路的标准不同。嘉祐三年(1058)诏:“臣僚赴任益、梓、利、夔,其远接人陆路止于京师,水路止于荆南,若路不由京师,即计其地里,无得过六十驿,若旧制不及者,止于旧制。”[3]2374对随行吏卒做时间和接送距离上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赴任地方官对吏卒的滥用,节约行政成本。
三、赴任期限与违限惩罚
宋政府非常重视赴任效率,针对不同地区给予了不同的赴任期限,且对赴任违限做出了惩罚规定。
(一)赴任期限
为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及时的权力交接显得尤为重要,故宋政府对赴任期限做了规定。北宋时,“诸之官,川、广、福建路,限六十日,余路,三十日。下班祗应事干急速放朝辞者,限五日到。以上并除程,在京以朝辞日,在外以授敕告、宣札日,待阙者以阙满日,非次阙以得报日为始。”*此条史料来源于谢深甫于嘉泰三年(1203)成书的《庆元条法事类》。此条史料并未注明该法律产生于何时,但可以推测应该产生于北宋。因为该条史料讲福建路的时限为60日,而同书54页淳熙三年的一条史料:“福建路之官,除程限依余路作三十日”,并解释:“本所看详上件指挥,系为日。今行在去福建不为远地,难以冲改旧法,止合编节存留,为申明照用”。说明制定“旧法”时,京城是离福建较远的,因此,此京城只能是指开封。故此史料颁布时间为北宋时期。[7]53可知,宋政府不仅对不同地区做了不同的时限规定,还对时限的起始期做了具体说明。至南宋,行在临安距福建路较近,故赴任福建的时限由六十日改为三十日,“福建路之官,除程限依余路作三十日”[7]54。当然上述赴任时限只适用于正常时期,特殊时期则有特殊规定。宝元二年(1039)正处于宋夏剑拔弩张之时,二月壬午诏:“新除近边知州军臣僚,并令乘递马赴任,限三月十日以前到。”[4]2896赴任时限只有短短二十天。为鼓励官员到边远地区赴任,措施之一就是延长赴任时限,太平兴国(976—983)初年诏:“川峡、岭南、福建注授,计程外给两月期。”[6]3721另《宋大诏令集》载:“广南官并春夏季内定差,许至秋冬到任。”[20]为了更好地协调离任官员与赴任官员的时间差,宋政府规定:“应官员赴任川、广、福建于半年前,荆湖南路于一季前,荆湖北路、江南西路于两月前,江东、淮南、两浙路于一月前,其不及千里州军于入半月,并为见阙,全差合破船数。”[3]11182根据赴任地距京城的远近确定赴任官员提前启程的早晚,有助于保证赴任效率。
(二)违限惩罚
宋政府对于限满不赴、无故稽留之官有处罚措施。北宋时,“诸之官限满不赴者,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即代到不还,减二等。”[21]南宋时期有所改变,“诸之官,限满无故不赴者,罪止杖一百。”武官赴任违限惩罚力度明显更大,“诸下班祗应之官无故违限者,一日杖六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7]52此外,为防止官员托疾延迟赴任,还制订了监督机制。大中祥符七年(1013)诏:“在京授差遣及外州移任文武官,除驿程外,在道属疾者,所至遣官验视,给公据,俟达本任,委长吏验问。如设诈妄满百日者,不得放上,具名以闻,并用违制论。当任远官托故不赴者,从本法。”[4]1869通过“验视”“验问”,既能给予赴任官员帮助,也能起到监督作用。对限满不赴任的情况,宋政府也制订了解决办法,“诸之官限满不赴,每月终州委通判,帅司、监司委属官,实封差人赍申尚书吏部,当厅投下。仍令所委官置籍销注,帅守、监司常切检察。”[7]53通判、监司等官会将限满不赴情况及时报知吏部,吏部可以较快做出补救措施。史料中存在因赴任违限而被惩罚的事例:大中祥符九年(1016)七月,殿直王素被任命为钦州咄步寨寨主,“素以地多瘴毒,不欲行,托疾,在道二百余日,至襄州,又称病甚求免,故黜之。”[4]1998王素因害怕瘴毒,故意滞留不赴,受到了黜贬,但此类例子并不多见。与之相反,许多赴任违限官员并未受到惩罚,如欧阳修在《于役志》[22]1005-1010中记载其从开封到夷陵,历时达三个半月。陆游在其《入蜀记》[23]1-21中记载从山阴到夔州,历时接近五个月。他们在赴任途中,走亲访友、观光游览,丝毫看不出因害怕违反期限而匆匆赴任的情景。
四、赴任途中的危险及应对
赴任途中的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途患病,二是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
(一)疾病与死亡
官员在赴任途中长时间奔波劳累,对身体状况是极大的考验。范成大在赴任成都后感叹:“成大止存四茎骨头,乌皮包裹其不仆于道涂者,天也。”[24]赴任之艰难可想而知。赴任官员在途中患病的情况时有发生,范仲淹讲道:“赴任耀州,以炎热之期历涉山险,旧疾遂作。近日颇加头目昏沉,食物减少,举动无力,勉强稍难见于永兴军,请医官看治次”[25]。有的官员因赴任途中患病,影响到了以后的生活,张方平言:“臣自熙宁三年赴任陈州,于路得疾。面日徧急,后医治虽痊损。然终不复旧,至今语謇涩,心多悸易忘,时昏眩”[26]。对于赴任途中可能遇到的疾病,宋人有事先的防备。《作邑自箴》记载了官员旅行途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如“犯寒不宜早洗面”“胃热以冷水洗面,则生疮瘰”“中暍已不省人事者,与冷水喫即死。但且急去衣服,令仰卧头高,以日中沙土或温温炉灶中灰壅之。复以稍热汤蘸手巾,熨腹胁间,良久苏醒”[27]100-103。这些内容是对赴任途中可能遇到疾病的预防和应对,此书也成为宋代颇受重视的书籍之一。除个人防范、治疗外,宋政府也会帮助赴任途中的患病官员,如上文提到的“请医官看治次”及“在道属疾者,所至遣官验视”。对于赴任途中死亡的官员,宋政府会给予其家属一定的抚恤,包括允许家属按照官员生前的资序乘官船归乡、[28]给予家属一定仓劵、[4]11697恩补官员子孙一定官职[4]7952等。
(二)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
除了疾病与死亡外,充满危险的水路交通、贼盗、瘴气等也对赴任安全造成了威胁。作为水路大动脉的长江,其危险指数令人咋舌。史载:“镇江府旁临扬子大江,舟楫往来,每遇风涛,无港河容泊。以故三年之间溺舟船凡五百余艘,人命当十倍其数。”[3]6166在水流相对平缓的长江下游,每三年尚溺船五百余艘,溺亡五千余人,上游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范成大的《吴船录》为我们描述了其过三峡时的状况:“独滟滪之顶,犹涡纹瀺灂,舟柫其上以过,揺橹者汗手死心,皆面无人色。”[29]其危险指数使经验丰富的揺橹者在经过时也必须万分小心,以至“面无人色”。在长江航行,还可能遇到贼盗的袭劫,如“两岸皆葭苇弥望,谓之百里荒……平时行舟,多于此遇盗。通济巡检持兵来警逻,不寐达旦”[23]42。宋政府需要派兵于百里荒进行昼夜巡逻,可知此地贼盗十分猖獗。面对水路上的危险,宋政府除了派兵昼夜巡逻外,还会于险恶的津渡置船救溺,“乞于津渡险恶处官置小船十数只,差水手乘驾,专切救应,其诸路江河险恶处,亦乞勘会施行。从之”[3]9535。对于赴任官员本人来讲,面对危险时还多会求助于神灵。陆游在进入三峡之前“舟人杀猪十余口祭神,谓之开头”[23]48。又如经过江西一座龙王庙时,“士大夫及商旅过者,无不杀生以祭,大者羊豕,小者鸡鹅。”[30]对于陆路可能遇到的危险,宋政府会“量差军士防送”,且《作邑自箴》也提醒赴任官员们“投宿先顾屋壁欹损,并视后床下及僻处”[27]100。赴任安全与气候也有关系,岭南地区“瘴烟,季春为甚”[31],为了保证赴任官员的安全,宋政府下诏:“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6]133通过调节赴任时间,来确保赴任官员的安全,这也从反面证明瘴烟对赴任官员的健康威胁之重。
五、赴任家属问题及官员到任后的程序
(一)家属问题
考虑到宋代官员多非只身一人,故到地方赴任时,是否允许携带家属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北宋初年,天下初安,离京师较远的地方,多不许赴任官员携带家属。之后,允许赴任携带家属的区域越来越广。端拱元年(988)四月,“先是,江南、两浙、荆湖州郡所差京朝官、幕职州县官等,咸不得家族行,如闻中外物情甚郁,今海内宁一,愿携家者听之。”[32]天禧三年(1019)七月诏:“河东路不许携家赴任,州军有官员挈属在彼者,并令发遣离任。”[4]2159但此诏令制定不久就被废除,同年十一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天下,诏:“河北、河东、陕西缘边监当、京朝官,使臣,幕职、州县官自今并许携家赴任”[4]2171。景祐元年(1034),允许携带家属的区域继续扩大,此年正月诏:“幕职、州县官任川峡路者听搬家,京朝官如无亲属可侍者,亦听之”[4]2660。此后,未见过不许携带家属赴任的规定。
北宋初期,对不携带家属赴任的官员,不仅有物资上的补助措施,还有升迁考课方面的优待政策。大中祥符二年(1009)诏:“外任官不得挈家属赴任者,许分添给钱赡本家。添给:羊,凡外任给羊有二十口至二口凡六等;给米有二十石至二石凡七等;给麦有三十石至二石凡七等;傔从有二十人至二人凡七等;马有十匹至一匹凡六等。”[6]4134天禧四年(1020)六月陈尧咨言:“旧制,河北、河东缘边幕职州县官不许挈家赴任,代还日免其守选。”[4]2199-2200通过物资和考课上的优待措施,激励官员更好地服务地方。当然,考虑到赴任途中的花费以及赴任途中可能遇到的危险,并不是所有官员赴任时都选择携带家属,如“王均、李顺之乱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17]110。对于因罪而贬的官员,如果家属不欲同行,也得到了许可。[3]8450
(二)官员到任后的程序
官员到达任地后,要履行一系列程序,赴任才算最终完成。到任后,官员需到上司处进行参拜,称为“公参”。“小官赴任,诣长贰公参讫,衙前听候三日,方敢退归本职。”[9]76应该是在公参之时,上级官员会对新任官员进行身份核对,并支发俸禄,“诸命官赴任,委长吏限当日照验,初补及见任付身别无伪冒,听上。仍于十日内取索出身以来文字,长吏辨验讫,批上印纸,方许放行请给”[7]55-56。公参顺利进行,象征着新任官员得到上级的认可,是权力交接的一个重要环节。
另外,官员到任后一般需要到当地祠庙进行参谒。“故事,守令始至,则郡县之祠庙悉诣之。恭于神,训于民,政之本也。”[33]在崇文抑武的宋代,孔庙比其他祠庙更具优势地位,故官员到任后参谒孔庙多是其不可或缺的工作。绍兴十四年(1143)十月诏:“州县文臣初至官,诣学,祗谒先圣,乃许视事……后遂著为令。”[10]2878使赴任官员到孔庙参谒成为一种制度。通过参谒孔庙等祠庙,一方面表达了以文治国的施政方针以及希望得到当地神祇的庇佑,另一方面也借此向民众宣告上任。
最后,新任官员还必须上表谢皇帝恩。宋人文集中有大量谢表流传至今,为我们了解谢表的内容和格式提供了方便。[22]1412,[34]谢表有固定格式,多会说明自己何时得到任命文书、何时启程赴任、何时到任。通过“愚昧”“不才”等词汇表达自己的卑微,然后感谢君主的知遇之恩,并保证尽忠朝廷、造福百姓等。
六、结语
官员赴任问题作为官吏管理制度的一部分,宋政府对其投入了较多精力。“告身”“历子”“印章”的制作与发放,体现了官吏管理的成熟;“朝辞”“堂谢”“台谢”的施行,为中央统治者了解赴任官员品行和获知地方民情提供了渠道;公使库、预支俸钱、驿劵、随行吏卒,为赴任官员提供了经济和安全上的帮助;依据赴任距离的远近确定不同时限,并对违限官员做出处罚规定,保障了赴任效率;家属携带问题和官员途中死亡后家属抚恤问题,体现了宋政府的人文关怀。如果仅从制度层面去研究,可以发现宋政府对官员赴任问题的设计非常完备。但是,一旦制度落实到实践层面,或多或少地都会发生扭曲变质。正如我们看到的,欧阳修、陆游在赴任期间花费的时间远超过了规定,而他们却依然走亲访友、观山游景。就整个宋代来讲,也没能节制住官员赴任借贷问题。因此,制度史研究不仅要关注“死”的制度规定,还要关注制度实际运行的“过程”、制度之间的“关系”和所处的“空间”,[35]即走向“活”的制度史。
另外,通过研究地方官赴任,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宋代官员的生活状况。如一些官员的生活并不富裕,在面对赴任花费的压力下不得不向亲友或他人借贷;在赴任地不安全或被贬斥时,多选择不携带家属;面对赴任旅途中的危险,除了依靠人力外,还会求助于神灵。对于这些情况的了解有助于多维度反映官员生活的面相,使研究者对宋代官员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赴任,宋代官员也获得了验证所学、增长见识的机会,是“知”与“行”的有效合一。
[参考文献]
[1] 金旭东.试论宋代的恩荫制度[J].云南社会科学,1985,(3):82-83.
[2] 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262.
[3] 徐松辑,刘琳点校.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 王明清.挥麈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6]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7] 谢深甫撰,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8] 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M].北京:中华书局,2016:2025.
[9] 赵升撰,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1]王栐撰,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陆游.渭南文集[M]∥钱仲联,马亚中主编,涂小马校注.陆游全集校注,第9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13]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2.
[14]王瑞来.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J].史学集刊,2015(4):76-78.
[15]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宋代传记资料丛刊,第16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233.
[16]陆游.渭南文集[M]∥钱仲联,马亚中主编,涂小马校注.陆游全集校注,第10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312.
[17]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0.
[18]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645.
[19]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394.
[20]佚名编,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609.
[21]窦仪撰,吴翊如点校.宋刑统[M].北京:中华书局,1984:148.
[2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23]陆游.入蜀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岳珂.宝真斋法书赞[M].北京:中华书局,1985:394.
[25]范仲淹撰,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文正公文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397.
[26]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469.
[27]李元弼.作邑自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28]赵抃.赵清献公文集:宋集珍本丛刊[M].北京:线装书局,2004:787.
[29]范成大.吴船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
[30]方勺撰,许沛藻,杨立扬点校.泊宅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83.
[31]楼钥.攻媿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53.
[32]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582.
[33]文彦博.潞公文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130.
[34]洪迈撰,穆公点校.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530-531.
[35]邓小南.过程·空间——宋代政治史再探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序言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