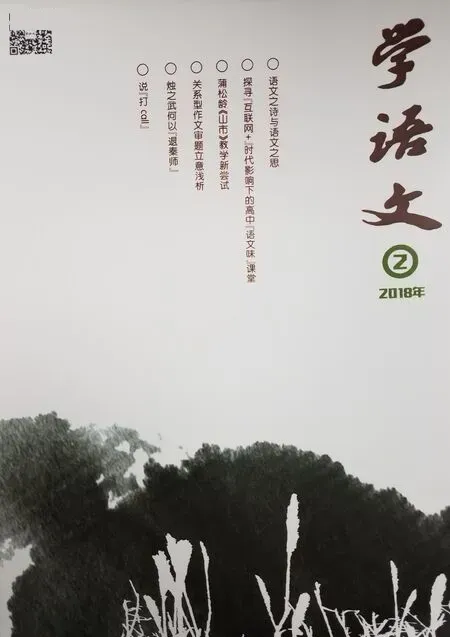囚绿之举,求绿之心
陆蠡的《囚绿记》一文,曾不止一次出现于语文教科书中,例如语文版的九年级上册、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都可见其身影,其教育价值不言而喻,影响了诸多学生。通常情况下,它都戴着顶“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的帽子出现,应试教育中此类标签式的套话屡见不鲜。
但这篇文章真的只是因家仇国恨交织而产生烦忧并由此决心反抗吗?起码笔者不论第几次阅读,兴奋的初感都并不如此。
文中扑面而来的,是陆蠡对于“绿”的浓烈感情。他总在不住地呼唤着:
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
我好像发现了一种“生的欢喜”,超过了任何种的喜悦。
陆蠡确实生活在战火纷飞,内忧外患最激烈的时代,但是创作背景不能被简单的当做作品的主题,解读鉴赏应立足于作家在文字中留下的生活真实上。
所以,迈出传统教参的禁锢,去贴近陆蠡的内心告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他早在《囚绿记·序》中就说到了:“这集子就是我的一些吞吐的内心的呼声”,“这是心灵起伏的痕迹,我用文字的彩衣给它穿扮起来。”[1]他说得明白,《囚绿记》这部散文集子不过是写他的心灵故事与生命事件,承载着他最纯粹的感情而已。
照理说,潮湿的房间能有阳光的直射最好不过,可偏偏在这里,阳光是“可畏”的——融入了主观感情色彩的阳光,并非一般意义上温暖的状态了,它产生了异变。那么,什么样的感情会把阳光称为“可畏”呢?我们可以联系平日里人人都有过的体会来理解:当心理内向、悲伤难过的时候,是否更宁愿呆在阴晦的房间,借昏暗将自我掩饰,求得一丝安全感呢?而过量的阳光照射,好似一枚聚光灯,个体一下子被抛入最敞亮之地,通透得反而无所遁形、无所适从了。
就是这样一间房间,陆蠡却只因为瞥见了一抹绿影,那喜悦的感情竟逼他毫不犹豫住下。“瞥见”,说明时间短,仅刹那的目光交汇。但这一眼,便一见钟情了!世间百般事物,能一见钟情的不过八九,所以,能称心这个“情”,在本身应是有潜在模型的,客体恰巧满足主体的所思所盼。也就是说,作者应该先是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深埋内心,但是这抹绿影却勾引起了作者内心的渴望。
为什么绿色有那么大的魔力呢?就性质而言,绿色不过是一种颜色,出身江浙地带的陆蠡应打小见惯了的,他大可去追求“实用价值”,选择其他好一点儿的房间。但正是陆蠡放弃了实用价值,不实用的审美价值才愈发地被凸显了。
当公寓中一切都是“南方少见的”时,绿色就不再是一种单薄的颜色,它变得立体起来,首当其冲的就因俏似故乡童年生命中的绿而宝贵,透过绿,似乎能看见背后家乡的模样。
我怀念着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我急不暇择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绿也视同至宝。
文章中陆蠡用了很多的字句宣扬着对于绿的情感,似乎生怕他人不知。孙绍振先生曾道,过于直接的抒情若放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则不能不显单薄,因为诗歌总是尽可能发挥着超现实的形而上的空寂理想,一览无余容易将意境之美消解。但这是散文,其叙事与描写都是具体的,一切以指向作者情感为表现目的。
显然陆蠡对于绿已是近乎狂热,没有万叠青,仅一枝“野绿”都将其捧在手心中。那么,这就不单单是对故乡的喜爱了,陆蠡的感情转折,在文章的第二层意脉开始显现。
《囚绿记》的真实发生时间 “是去年夏间的事情”,去年夏天之时,陆蠡于北平见这株绿色,由此怀念起故乡来;然而离开了北平,又怀念起那抹绿影,所以,“绿”在陆蠡的生命中一直影响着他,小小的绿特别到一年过去了陆蠡依旧念念不忘,并为此写了一篇文章用以回忆。刘西渭在《陆蠡的散文》中曾说过:“老实人,到了寂寞的时候,便从过去寻找温暖。”[2]回忆是个好东西,能够用以逃避寂寞,回归心灵。
大家听了刘少奇的分析,无不眼前一亮:原来路就在脚下,办法就在彼此之间。于是,造船修船、疏通河流、建立白区据点、联络各地商户等等办法都提了出来。一场讨论会圆满结束,效果超出预期。更重要的是,这些办法付诸实践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还锻炼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斗争灵活性。
之所以如此,这里有必要补充了解作者彼时的生活境地:1935年,陆蠡任上海生活出版社编辑,在上海沦为“孤岛”后,仍坚守上海主持工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他与广大文化战士隔离了开来。这使‘我’感到‘孤独’”[3]。这也便难怪“门虽是常开着,可没人来打扰我,因为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这样的孤独,不仅仅缘于身处异乡,更因为心灵上的形单影只,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隔离后的那种寂寞。所以,正是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于绿的渴望,驱使着陆蠡做出“非理性的选择”:常春藤本在窗外天地中自由快乐地生长,通常而言,一个有爱心、有人性的人,是不会对其随意攀折的。但陆蠡却这样做了,即便是动作和缓地将柔条牵进屋子,也是一种平日看来不符合爱护花草之美德的事情。
不过,偏偏因为不讲“道理”——情感与理性拉开了距离,才更突显了作者对精神与情感的审美追求:
我拿绿色来装饰我这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喻猗郁的年华。
作者内心孤寂在绿色的到来后表现得淋漓尽致,绿能予“我”光明及自由的安慰,缓解因时局造成的囚禁生命的令人憎恶之感。所以,即便面对常春藤依旧向窗外攀缘、渐渐青黄病损,作者都不愿放它回归本位,无理得仿佛故意在蹂躏这株绿色。
这般看来,囚绿,其实也是求绿,不单单是求绿色,而是求一种生的欢喜。“我”之爱“绿”,实是“我”爱那自然饱满的生命理想与激情。
被囚禁的常春藤,在文中,作者称它为被“幽囚的‘绿友’”,仿佛二者都是监狱中的囚徒,“我”囚绿的同时,亦是被囚的对象,二者内在的主观情感有了契合点。于是,这里的意脉又有了变化:“绿”不仅是外在自然对于内在心灵的慰安了,当作者审视被囚的常春藤、凝视被隔离的自己这样一对具有相似生命关系的“难友”时,情感上更易对“绿”生发出惺惺相怜相惜的移情之感。
“我永远是胆小的孩子,说出心事来总有几分羞怯”[4],《囚绿记·序》中陆蠡自我剖析道。内向沉寂的性子,使他往往“借重文采的衣裳”来掩饰自己的内心,以求不被一目了然的微微心安。很明显,文中“绿”这个意象,便是他所着意刻画的文采衣裳,常春藤之绿之美,并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而在于将自我的感情渗入到其中,使那株常春藤成为陆蠡生命的化身,“我了解自然无声的语言,正如它了解我的语言一样”。这仿若是在说陆蠡自己,长于自然,本性向阳,即使在困索中也追寻着光明与自由一般。
参考文献:
[1]陆蠡:《囚绿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2]李健吾著,张大明编:《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
[3]刘一新:《热爱生活,追求光明——陆蠡的〈囚绿记〉赏析》,《名作欣赏》1987年第5期。
[4]陆蠡:《囚绿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