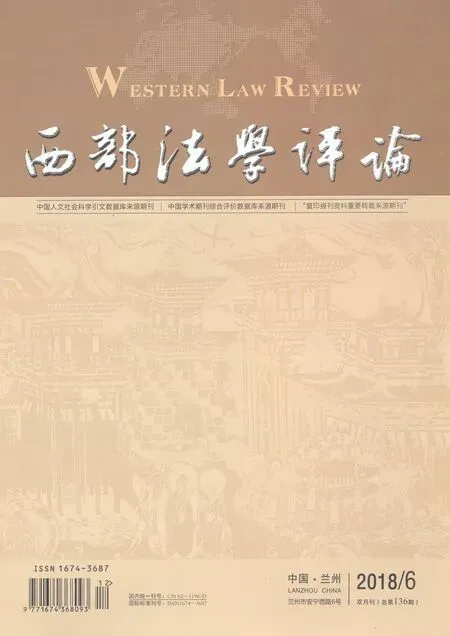体系的思考方法下的参加理论
李瑞杰
一、 基于“体系的思考方法”的参加理论
建构参加理论[注]严格意义上,“Teilnahme”指的是狭义共犯(参与),“Beteiligung”指的是广义共犯(参加)。这样,晚近我国刑法学中的“犯罪参与体系”,准确的理解应该是“犯罪参加体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即区分制与单一制。区分制为德国、日本刑法所采,其学说——“共犯从属性说”,亦流行于德日刑法学界。原本,我国刑法学界无人讨论我国刑法参加规范的体系归属,但是近年来,很有力的观点认为,鉴于单一制有其不足,有必要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去解释我国刑法中的参加规范。然而,如果运用“体系的思考方法”就不难发现,这些观点未必妥当。[注]如果为了“问题”部分放弃“体系”,无疑任何理论都将具有相当合理性,理论更迭亦无必要。
例如,有学者为了将共犯从属性说植入中国刑法典,苦心孤诣地提出了“以违法与责任为中心,先判断参加人在客观违法层面上的作用大小,以此区分共犯与正犯,在具备多个正犯即共同正犯的场合,再根据主观责任的大小进一步区分出主犯与从犯”[注]周啸天:《正犯与主犯关系辨正》,载《法学》2016年第6期。的观点——即“正犯主犯递进关系论”。但是,区分客观违法与主观责任,是采取(限制的)共犯从属性说所赖以存在的理论根基。这意味着,区分正犯与共犯,是在不考虑主观责任的情况下就能够且必须做出来的。犯罪参加的成立,不限于“共同不法且有责”,而仅仅是“共同不法”,那么,参加论是不法论的组成部分,以责任的大小区分共同正犯中的主犯与从犯,实属自相矛盾。
论者明确表示“正犯与共犯属于不法层面上的区分”后,又说,对于共同正犯,“要根据责任的大小来进一步筛选出主犯、从犯,而仅将责任大者作为主犯处罚。”然而,当共同正犯中只有一个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时,不知道该将其认定为主犯还是从犯?一律以主犯或从犯对待,不尽合理。如欲“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又存在“责任不存在,大小更不用谈”的尴尬境地(在我国,“无主犯的从犯”是不可思议的)。同样的情形是,其一方面认为,“我们应当修正已往的观点,秉承教唆者应当是共犯,从而是从犯,被教唆者才是主犯的理念”,另一方面又说,我国《刑法》第29条第1款前段中的“其中作用大的情况仅指第二句话中的教唆未成年人的场合”,并补充道,“‘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人已经不是教唆犯,而应当是共同正犯。”既然区分制中,分担实行行为的人肯定属于正犯,那么,即使认为此时的“教唆人”是共同正犯,但就共同的“法益侵害”的结果而言,为什么共同正犯之间还会出现量刑上的差异?这一挣脱不法理论的羁束而在责任领域也谈论参加理论的观点,就犯了散在的思考方法的错误。
“正犯主犯递进关系论”只是一个缩影,类似观点其实不少。在根本上,这些观点都是因为没有运用“体系的思考方法”去建构参加理论。对于“散在的思考方法”,德国学者费尔巴哈曾给予了这样的批评:“任何混乱以及不协调都是对理性的侮辱,理性的最高使命是协调与统一。”[注]参见[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刑法的体系构成》,黄笑岩译,载梁根林、[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主编:《刑法体系与客观归责: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刑法体系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外在体系(刑法典规则体系),即对刑法规范和构成要件所进行的概念上的梳理、解释和阐明;另一个是内在体系(犯罪论理论体系),即贯通和支配整个刑法的精神理念、基本原则以及它们之间的实质联系。因此,如果我们承认体系的思考方法有其必要性,那么就应当坚持学术立场的一贯性,同时,重视罪刑规范的国别性,立足于中国刑法,研究参加理论。就此而言,本文认为,运用体系的思考方法深化参加理论,进而形成参加理论的中国话语与中国表达,至少可在如下方面展开:
其一,近来有些学者,将“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中的“犯罪”解释为“不法”,同时,又将我国刑法上的“教唆他人犯罪的”人解释为德日刑法上的“教唆他人使之实行犯罪的”人,并具体考察被利用人实际上是否具有“规范意识”。这或有不妥。我国刑法采取的是单一制,不能将中国刑法上的教唆犯与德日刑法上的教唆犯做相同的理解。“教唆他人犯罪的”中的“犯罪”,不限于“实行行为”。而且,就实现“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的规范目的而言,推不出界分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的必要性,也不用进行“规范意识”有无的考察。
其二,如果认为共同犯罪的实质是共同不法,那么不法理论就应包容参加理论。坚持结果无价值论,同时又批判单一正犯体系的做法[注]例如,陈兴良教授“旗帜鲜明地主张将故意作为责任要素而非构成要件要素”(李世阳、崔涵:《第四届中德刑法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成功举办》,来源于http://www.ghls.zju.edu.cn/chinese/redir.php?catalog_id=55&object_id=353055,2018年4月4日访问),又认为应当运用限制从属性说的观念解释刑法总则编第二章第三节,参见陈兴良:《走向共犯的教义学——一个学术史的考察》,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7页。,难言合理。只有行为无价值论才能与共犯从属性说相结合:如果不承认构成要件故意,不承认构成要件的个别化机能,不承认共犯行为对主行为故意的从属[注]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页。,不承认参加类型之间“质”的不同,那么,就不能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于参加人,无法在不法阶层区分参加形态,对于不法范围的认定也将过于宽泛。这都与共犯从属性说相冲突。区分制只适用于共同故意犯罪场合;限制从属性说要求在不法阶层就区分出正犯与共犯;保证构成要件的定型性与正犯不法重于共犯不法,要求共犯的成立必须具备“双重故意”,必须坚持共犯对主行为故意之从属;采取限制的正犯概念,就必须舍弃间接正犯概念。此外,即使认为我国采取了区分制,但是,依据第25条规定,成立共同犯罪要求“共同故意”,所以,也不宜运用结果无价值论去解说相关参加规范。
其三,单一制作为构成要件实质化中的重要一环,是实质刑法观、功能刑法观在参加理论中的重要体现。如果将实质构成要件论、实质正犯论等“贯彻到底”,必然会导出单一制。而且,较之区分制,其更有助于保护法益。罪责以不法作为基础,罪责独立也只能建立在不法独立的前提之下。区分制将“行为”局限于与人直接相关的身体动静,认为狭义共犯只存在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没有将“共动现象”结合在一起分析,因此,既不符合刑法中的“行为”概念,也无法为追究共犯的刑事责任提供有力的根据。
二、“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之解释
近年来,有些学者为了贯彻共犯从属性说,对于如何理解“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钱叶六教授认为,在教唆或者帮助有规范意识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场合,传统通说会不当扩张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从而导致轻罪重判。如果被教唆的人虽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但实际上具备规范意识时,就不能将教唆犯评价为支配被教唆的人实行犯罪的人(间接正犯)。将教唆犯一律评价为正犯,忽视了其成立从犯的可能性,无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注]钱叶六:《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阶层化及共同犯罪的认定》,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2期。杨金彪教授基本上也是这种观点:“把本来应当属于教唆犯的背后教唆者作为间接正犯处理,使本来应当作为教唆犯受到较轻处罚的背后者却作为正犯处罚,造成处罚上的不公平。”[注]杨金彪:《刑法共犯规定对共犯从属性说的贯彻》,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4期。付立庆教授则认为,既然这一规定属于刑法“共同犯罪”这一章的内容,那么“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理应构成共同犯罪”。在无法肯定被教唆者完全沦为教唆者的利用工具[注]为便利行文,本文未如付文等那样严格区分“教唆”与“利用”,而一概称之为“利用”。的时候,通说将难以合理解释,教唆者没有亲手实行犯罪的情况下,其构成相关犯罪的单独实行犯的原因。[注]付立庆:《犯罪概念的分层含义与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再宣扬——以“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规范理解为切入》,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2期。最近,付立庆教授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其表示,判断“规范意识”的标准虽然模糊,但是仍具有合理性。在模糊之处,应该本着“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按照间接正犯处理。尤需注意,其将“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从重处罚”的根据,归结为“其制造出了一个违法意义上的犯罪人(违法共犯论),并据此引起了法益侵害,从报应和预防的角度都有较之单独犯罪人从重处罚的必要;而在后者(即间接正犯——引者注)的场合,行为人仅仅是通过自己‘手的延伸’而实现了法益侵害,被利用者在法律评价上完全是中性、无辜的,因此,无论从报应还是预防的角度讲,对行为人都只需要按照普通的单独犯罪人予以处罚。就此而言,两者场合的差别对待并非是造成了不均衡,其背后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因此是一种合理的、值得肯定的差别。”[注]付立庆:《违法意义上犯罪概念的实践展开》,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5期。
就前两位学者的观点而言,至少存在这一问题:通说诚然会使得事实上成立教唆犯的情形被一律评价为间接正犯,但是未必一律导致“轻罪重判”。在德国、日本,教唆犯比照正犯处罚,而如果将我国刑法中的主犯理解为正犯的话,那么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的处罚也应当一样。如果还进一步考虑到第29条第1款后段,反而还要从重处罚教唆犯。也就是说,同样教唆一个13岁的孩子去杀人,在孩子有规范意识的时候,教唆人被评价为间接正犯,适用第26条;在孩子没有规范意识的时候,教唆人被评价为教唆犯,进而比照使用第26条——认为主犯即正犯时,还考虑第29条第1款后段,必然造成教唆犯重于间接正犯的局面。
因为付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条文的内在结构,说理比其他人更为深入,并且,其论说也是日本结果无价值论在参加理论中的必然延伸,下面重点分析:
第一,我国不应当承认“间接正犯”这一概念。首先,共同犯罪是不法形态,共犯论先于罪责论,结合结果无价值论否定构成要件主观要素的主张,就应当认为,间接正犯只是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的一种。其次,中国刑法与日本刑法对“间接正犯”都缺乏明确规定,如果运用这一概念去认定犯罪,无疑违反罪刑法定。否则,德国刑法不会规定“间接正犯”的可罚性,晚近日本的有力学说亦不会否定“间接正犯”概念了。最后,采取从属性说,在身份犯的场合,认为正犯只能由具有身份的人构成,可能会使得第29条第1款后段得不到适用。
第二,在德日刑法中,“教唆犯的对象仅限于实行犯,而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在我国刑法中教唆他人犯罪的为教唆犯,这里的教唆他人就不限于教唆实行犯”。[注]何荣功:《共犯的分类研讨述评——以中日刑法的比较为中心》,载马克昌、莫洪宪主编:《中日共同犯罪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刑法第29条第1款,既然包括了教唆他人去实施帮助行为或连环教唆的情况,那么就可以认为,我国刑法不存在区分制的存在空间。[注]蔡桂生;《构成要件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4页。并且,我国刑法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以次数等个人行为要素作为入罪门槛。例如,“多次盗窃的”、“敲诈勒索多次的”。尤其是广泛存在诸如“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注]第2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前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一)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二)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类似的情况下,如果共犯合乎次数而正犯不合乎,将造成不能处罚共犯的荒唐局面——正犯行为不符合构成要件。此外,教唆他人,不用要求教唆未成年人去亲自实行犯罪,教唆未成年人去教唆他人实行犯罪、教唆未成年人去帮助他人实行犯罪等也可以,例如,哥哥教唆17岁的高中生表弟,给屋子里正在强奸妇女的族弟放风,也应当从重处罚哥哥。理解第29条时,采取区分制的解释路径,行不通。
第三,如果承认构成要件故意,或许就不能还提出所谓的“规范意识”概念以区分间接正犯与教唆犯。例如,爸爸拿出一把东西,告诉(1)八岁的孩子,或者(2)十三岁的孩子,“这是毒药,倒进隔壁王大爷的茶杯中去”。很难说,前者没有“规范意识”,后者就有“规范意识”。即使认为前者没有“规范意识”,进而爸爸不成立间接正犯,但是以“规范意识”之有无,区分教唆犯与间接正犯,只是日本学界的主流界分标准,并不为德国学界所采。依据区分制的原理,只要行为人具备实现构成要件的“知”与“欲”,行为人就具备正犯性。但是论者却认为,精神病人不可能具备规范意识,因此,不可能被教唆,只能被利用,不能成立正犯。[注]同前引[11]。这与阶层理论抵牾。精神病人只能在罪责阶层才能排除犯罪性,他也具有构成要件故意,其行为也符合构成要件。[注]否则,在帮助犯的场合,将无法处罚之。例如,精神病人疾病发作,要别人给他一把刀去杀人,旁边的人也就应允给了他一把刀,如果认为精神病人没有规范意识(依据付立庆的观点),那么不符合构成要件,将无法处罚那个递刀的人。并且,依据德国犯罪事实支配论、日本共谋共同正犯论,即使被利用人具备“规范意识”,利用人也有成立正犯的可能——即“正犯背后的正犯”。在事实支配论中,间接正犯人的成立,虽然也需要意志支配,但并不排除“台上人”也构成正犯的可能性,而只要求行为人必须利用自己的意志力量。例如,强制、被利用人的错误、优势的事实认知、组织性的权力机器等,完全支配了犯罪行为的因果流程。[注]Vgl.Roxin,Tä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8.Aufl.,Walter de Gruyter&Co.,2006,S.126ff.而且,按照日本学界通说,如果无法确定被利用人是否具有“规范意识”,进而对利用人是否实际支配了被利用人存疑时,考虑到教唆犯是比间接正犯更低的不法形态,间接正犯故意只能降格评价为教唆犯故意——而不是相反[注]这就好比行为人犯盗窃罪、诈骗罪,前罪应当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后罪应当判处半年拘役,由于拘役不再执行,法官不能“转过头”将诈骗罪判处一年管制。,利用人只能被论以教唆犯。但是,在我国被“降格”评价为教唆犯后,反而会“从重处罚之”,导致一方面,对成立间接正犯存疑而成立教唆犯可以确定时,将行为人评价为教唆犯;另一方面,将行为人评价为教唆犯后,又会被“从重处罚”。论者认为,当被利用人是否具有“规范意识”存疑时,对利用人论以间接正犯,但是这违背了共犯从属性说的基本理念。此外,依据学者的上述观点,接续区分制的一贯逻辑,在教唆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去帮助他人实行犯罪时,也应当考察儿童的“规范意识”。[注]例如,甲为教唆乙杀人,请丙代为传递信件,如果(1)丙只有十岁时,或者(2)丙有十三岁时,奇怪的是,这些学者却不去区分丙有没有“规范意识”,进而主张存在“规范意识”时,对甲从重处罚。笔者尚未听到这样的观点。
第四,在处罚根据上,间接正犯与直接正犯并无不同。对此,无论单一制还是区分制都不否认。但是,共犯的处罚根据论,经历了从“罪责共犯论”到“不法共犯论”再到“因果共犯论”(纯粹惹起说、修正惹起说和混合惹起说)的不小变化。纯粹惹起说与混合惹起说是行为无价值的产物,如果采取结果无价值势必采取修正惹起说,但是该说的具体结论与共犯从属性说抵触。[注]大概也是因为这一原因,我国采取共犯从属性说的结果无价值论者,在共犯处罚根据上,有的采取“混合惹起说”(例如,张明楷、陈洪兵),有的采取“修正惹起说”(例如,黎宏、杨金彪)。付文一方面表示,在共犯处罚根据上,其支持的是“修正惹起说”[注]同前引[10]。,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之所以只对“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从重处罚,是因为“其制造出了一个违法意义上的犯罪人(违法共犯论)”,而间接正犯没有。但是,为什么一方面采取因果共犯论一方面又采取违法共犯论?间接正犯同样可能也“制造出了一个违法意义上的犯罪人(违法共犯论)”,例如前述“集团犯罪”中的“组织支配”。[注]德国实务中,法官为了解决在聚众性犯罪(Massenverbrechen)中,采取“主观说”,将导致直接实行者与背后组织者都因为缺少正犯意思被认定为帮助犯的局面,以及,对在冷战期间,命令那些警察射杀出逃民主德国的人的领导人,按照间接正犯予以处罚,司法实务又采取了以组织控制地位为依据的间接正犯结构学说(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如果认为说法不同时,“后法优于前法”,那么,首先,即使认为教唆犯制造了犯罪人,教唆成年人也可谓制造出来“一个违法意义上的犯罪人”。而且,依据客观不法论,不论被利用的人有没有故意,其行为都属于不法。即使按照德国通说,成立不法,需要被利用人存在故意或过失,不过,依据反对解释,付文却认为,被利用人有故意也不成立不法,只有在有故意也有“规范意识”的时候,才成立不法——才“被卷入”。其次,集团犯罪中的“幕后人”与“台前人”,“柏林墙”案件中的民主德国领导人与射击士兵,都是正犯,但在“台前人”、射击士兵不满十八周岁的时候,不从重处罚教唆他的人的话,显然不合理。最后,将教唆犯的处罚根据归结为制造了不法行为人的说法,早已被德、日刑法学界所抛弃,因为其不合责任主义与“法益侵害说”。在德国学界,即使被教唆人具备“规范意识”时,教唆他的人是否一律成立教唆犯——而不会是间接正犯,也有很大的争论。耶赛克等人认为,对于教唆者来说,“如果该无责任能力的幕前人事实上能够认识其行为的不法性并按规范行为的,同样为间接正犯”,并举出了一个例子论说之:“例如,行为人让一名伶俐的男孩纵火。即使该男孩对其行为违法性‘有足够的认识’并主动地实施了纵火行为,构成间接正犯”。[注]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下),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l7年版,第905页。与之类似,意大利刑法第112条,存在着与我国刑法第29条第1款后段类似的规定,但是据笔者了解,该国学界基本上都不存在“规范意识”这一概念。
第五,付文认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不可能存在规范意识,并且,实际上也不可能具备规范意识——否则,就不属于“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其还指出,对于被教唆时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来说,“没有认识能力不行,虽有认识能力但没有现实的认识也不行,仅在既有认识能力又有现实认识的情况下,才能肯定上述的互动关系,才能肯定‘被教唆者’的地位。”[注]同前引[10]。那就应当认为,生活中固然存在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际上已经具备规范意识的情况,但是不能认为他们具有规范意识,因为这是立法“不可反驳”的推定,否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深层次而言,根据我国刑法,“欠缺责任能力,就不可能具备规范意义上的故意和过失”。[注]丁胜明:《正当化事由的事实前提错误——基于故意论系统思考的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页。刑法第14条第1款,没有将事实意义上的、作为心理要素的故意,与责难意义上、作为评价要素的不法意识[注]与我国大陆地区将不法意识(违法性认识)理解为违反法律的认识的做法不同,在德国、日本与我国台湾,不少学者认为,不法意识即是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社会危害性)的意识。德国联邦法院也认为,只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违反法律秩序、有害于社会共同体就够了(Vgl.BGHSt 40,241.)。相区分。犯罪故意不仅是行为能力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还是“思想非价”的表现形式与实际载体。这就决定了,虽然“社会危害性认识”等同于“违法性认识”的概念内涵,但是因为彼此的功能地位不同——与本国刑法中“犯罪故意”的关系不同,我国刑法中的“故意”不能等同于德日刑法中的“故意”。因此说,我国刑法规定了一种不同于德国、日本刑法的实质的故意概念。在德国“现行法律条文中是区分故意(第16条)和不法意识(第17条)的,故意说(指犯罪故意包含不法意识的观点——引者注)并不符合法律上的这种规定”。[注][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第六版),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8页。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故意概念,包含了非难可能性,蔡桂生博士就曾指出,“我国《刑法》第14条中规定的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乃是不法意识,它有别于事实性故意”[注]同前引[13],第245页。,进而排除了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具备“故意”与“过失”的可能性。同理,只要我国刑法第25条第1款没有修改,共同犯罪是“共同故意犯罪”,那么就不能将共同犯罪仅仅理解为共同不法。
三、结果无价值论与共犯从属性说相冲突
探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标准、共犯的成立条件,是共犯从属性说不能回避的两大问题。采取实行从属性说与限制从属性说,要求在不法阶层即区分出正犯与共犯、讨论共犯的成立与否。构成要件故意决定了不法行为的方向与目标,是个人行为不法的核心要素,也是“法益侵害”得以主观归责的基础[注]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只有先确定存在“故意”,才可能探讨是否存在“参加”。而且,刑法第25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共同犯罪中每个行为人都必须具备犯罪故意。即使认为这里的“犯罪”可以理解为违法意义上的“犯罪”,根据形式逻辑,教唆犯与帮助犯如若成为共同犯罪人,它们的成立必须要求主行为人具备了犯罪故意。[注]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主行为,对教唆犯与帮助犯一律不处罚。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已经明确肯定了未遂教唆的刑事可罚性。由于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如果被帮助的人没有犯被帮助的罪”的处罚规则,可以借鉴学界对奥地利刑法第15条的解说方式,即我国刑法排除了未遂帮助的可罚性。因此,结果无价值论否定共犯对主行为故意之从属,乃至于将犯罪参加扩展到“过失共犯+过失正犯”“过失共犯+故意正犯”“故意共犯+过失正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一)行为无价值论与共犯从属性说的适用
德国刑法区分不法与罪责的时间,晚于采取共犯从属性说的时间,所以,原先都是在不法—罪责“一体论”的视角下讨论区分制的。这种做法,导致共犯从属性说在要素从属性的要求上,采取了极端从属性说。由于在罪责阶层的考察中,罪责能力先于罪责形式,这样就会导致教唆犯、帮助犯会由于无从依附正犯而难以得到处罚。而且,这也违背了罪责原则。“为了回避这样的问题,李斯特和贝林以区别违法性和责任为基础,提出了三阶层的古典犯罪论体系。”[注]王充:《论德国古典犯罪论体系——以贝林的构成要件理论为对象》,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6期。紧接着,迈耶阐释了四种从属性,并认为,参加的成立,采取以正犯违法地满足了构成要件为前提的限制从属性说,最为妥当。[注]Mayer,Der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Strafrechts.2.Aufl.,Carl Winters Universitätsbuchhanglung,1923,S.391.从属性说只在故意地参加故意犯罪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在提出限制从属性说时,还没有普遍承认构成要件故意,所以存在适用范围上的危机:犯罪故意摆在后面,认定参加却在前面。而韦尔策尔巧妙地化解了这一危机,为限制从属性说稳住了阵脚。实行区分制的德国,就在刑法第27条第2款、第28条、第29条明确表示,在数人共同过失犯罪的场合,不用区分过失正犯与过失共犯。因为过失犯只有正犯可言,所以事实上采取了单一正犯体系。就审查步骤而言,德国学者也指出,先审查客观的构成要件,然后是构成要件故意。接下来研究是否存在犯罪参加。如果存在犯罪参加,又是需要讨论客观的正犯要件或者共犯要件,然后考察每一个参加人是否认识到了该情形。[注]Vgl.Roxin(Fn.19),S.330.由此可见,只有在主行为人的犯罪故意得到确认后,我们才会去考虑是否属于犯罪参加乃至适用共犯从属性说的问题。“选择限制从属说,意味着认可构成要件故意。”[注]同前引[13],第383页。如果贯彻结果无价值论,难免使得从属性说的适用范围不明晰,乃至于将“过失共犯+故意正犯”、“故意共犯+过失正犯”等夹杂其中,愈发混乱。而且,不考察犯罪参加人之间的主观交流与意思联络,是难以认定犯罪参加是否成立的,还使得“参与犯”与“同时犯”不易区别。
结果无价值论者注重“法益保护”,轻视行为类型与意思联络,这种理念的直接后果就是采取行为共同说与片面参与的扩大化。行为共同说将不能够归属于行为人的结果也归属给了行为人。例如,三个人分别以伤害的故意、杀人的故意、强奸的故意共同对被害人施以暴力,在被害人死亡却无法查明是哪一个行为人的行为致其死亡的时候,草率地将其分别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故意杀人(既遂)、强奸致人死亡。这种做法非法倒置了证明责任,或许违背罪责原则。不管怎么对我国刑法第25条第1款那几个字如何解释,问题是,上述案例中存在“罪过”,已经逾越了从属性说探讨的范围,应当变换理论学说——考察单个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是否具有“犯罪过失”。相同的情况,出现在“片面的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之中。结果无价值论,全面承认片面的帮助犯、片面的教唆犯、片面的共同正犯。[注]同前引[6],第392—393页。值得补充,李瑞杰新近的一篇论文(李瑞杰:《从单一正犯视角看片面共犯论》,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首次从单一正犯视角对片面共犯理论进行了批评性研究,或许能给人以一定启发。在强调共同意思联络的德国刑法学界那里,只承认片面帮助,难以想象其他两种片面共犯的存在。
此外,共犯从属性说坚持“限制的正犯概念”,这是其根本立论所在。因此正犯行为与共犯行为存在类型上的区分,具有“质”的不同,每一种举止都具有其独特的负价值:“如果立法机关没有赋予亲自实现构成要件以外的人以刑事可罚性,那么即使一个人按住被害人、教唆行为人为谋杀行为甚至为他提供枪支,都不能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注]Roxin/Arzt/Tidemann,Einführung in des Strafrecht und Strafprozeβrecht,4.Aufl.,C.F.Müller Verlag,2003,S.23f.这意味着,从属性说不是以“法益侵害”为思考起点的,而是十分重视刑法分则对构成要件的预先规定。这就与不重视“行为样态”本身的危险性,同时也不强调通过“行为样态”来区分不同犯罪的结果无价值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结果无价值论者即使承认正犯行为与共犯行为存在不同,也只是承认存在“量”的不同。这显然与从属性说冲突。例如,行为人出于教唆的故意,由于他人本来已经有了行为决意——只是行为人不知道而已,使得“教唆行为”只产生了心理帮助的后果,论者会认为,对行为人论以帮助犯,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间接正犯(未遂)与教唆犯(既遂)竞合的场合。因此,如果只看到参加人都是“侵害法益”的行为人,无视构成要件的类型性,显然已经背离了从属性说,与单一正犯体系相去不远了。检视日本的刑事审判实践,98%的犯罪参加人最后都被评价为了共同正犯,大抵可以说日本采取的是一种顶着区分制名义的单一正犯体系。[注]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第二版),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91页。参加体系是犯罪论体系的试金石,结果无价值论无法在共犯从属性说之中“一以贯之”,它在德国日渐式微也是理所当然的。可以说,我国不少结果无价值论者对单一正犯体系的批评,同样适用于自己所持的“共犯从属性说”,即仅依靠因果关系的条件判断来认定共犯,进而,大量地将本不该评价为共犯的人评价为共犯,将本不该评价为共同正犯的人评价为共同正犯,简化了构成要件的类型功能,等等。
(二)不承认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难以准确认定正犯
在区分制中,“正犯”是共同犯罪的“核心人物”与“主角”,“共犯”是共同犯罪的“边缘人物”或“配角”。共犯由于没有亲手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位于犯罪事实边缘,对于犯罪事实不具有支配性、不具有特别义务,是相对于正犯的次要概念。因此,只有在存在着某个实现构成要件的主行为的时候,才能显示出核心角色(正犯),边缘角色共犯才能有所依附。显然,此时必须发展出能够合理区分“正犯”与“共犯”的理论。而且,采取限制从属性说,意味着在不法阶层就需要妥善地区分出二者。
德国审判实践中,在正犯理论上出现过多种学说,但总体上倾向于综合主观意思与客观情状进行认定。例如,判例“猫王案”(Katzenkönigfall)[注]BGHSt 35,353.中,就采取了“限定的主观说”,在考虑行为人对结果利益的态度的同时,结合行为人对参加犯罪的妇女的控制程度、行为人对犯罪支配的意志,实现整体评判。有学者认为,“对犯罪事实的支配,并不以行为人具有犯罪的故意为前提”。[注]同前引[6],第357页。这将事实支配理论与客观实质的正犯理论简单等同了。其实,是否成立犯罪支配,需要综合行为人主观上的操纵意思与客观上的参加分量进行判断。[注]Vgl.Jescheck/Weigend,Lehrbuch des Strafrechts,Allgemeiner Teil,5.Aufl.,Duncker&Humblot,1996,S.652.
犯罪支配,只能理解为行为人在具备构成要件的故意的前提下,排他性地操纵了构成要件的实现。“只有使故意进入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才能使犯罪的参加形态在不法阶段即得以区分性地描述,而在不法阶段就区分出正犯和参与,正是支持限制从属性说的前提。”[注]同前引[14],第383页。例如,如果没有意识联络的两个行为人,不约而同地向同一被害人开枪,被害人身中一枪死亡却无法查明的时候,显然都只能论以故意杀人罪(未遂)。但是,如果存在意思联络,则被论以故意杀人罪(既遂)。如果不考察主观状态,就难以认定是否存在犯罪支配,存在哪一种犯罪支配,具体此案而言,则是行为支配(单独正犯)还是功能支配(共同正犯)。而且,上述学者的观点,将导致支配行为人是过失犯而参与行为人是故意犯的情况。对此,罗克辛教授说,“如果认为某一个人‘在客观上’支配了犯罪行为而因为欠缺故意,只是不知道而已,这种意义上的‘客观’的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显然是一种‘修饰语上的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o)。就如同我们说过失行为是一个‘客观的故意行为’一样,这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将故意从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中剔除出去,人们将发现,客观上找不出可以成立犯罪事实支配的东西”。[注]Vgl.Roxin(Fn.19),S.331.又如,在行为人出于间接正犯的故意的场合,如果不考察直接实现构成要件的人是否具备规范意识,不考察被利用者的主观认知,将使得教唆犯与间接正犯混为一谈。同理,部分结果无价值论者将间接正犯一概归入教唆犯(诚然,这是结果无价值论否认构成要件故意的必然归结),也不值得赞同。一律以教唆犯论处,将会出现,如果承认构成要件故意,正犯将可能不具备构成要件,从而共犯无从依附一个“故意地违法行为”(zu dessen vorsätzlich begangener rechtswidriger Tat)得以成罪的局面,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塚仁教授指出,“间接正犯具有与共犯从属性原则共存亡的名义”。[注][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其实,如果将结果无价值论否认“人的不法论”的观点贯彻到底,甚至会得出人与动物、植物可以共同犯罪的荒谬结论。
(三)不承认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难以准确认定共犯
共犯的成立需要具备“双重故意”。教唆故意包括,完成一个确定的故意地违法的主行为,和使主行为人萌生行为决意。帮助故意包括,实施并使得一个特定的故意地违法的主行为实现既遂,和自己提供帮助。[注]同前引[29],第443页、第458页。由于刑法总则为共犯行为单独设置了特殊的构成要件,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同单独犯一样,共犯人成立不法需要具备构成要件故意,只是说,共犯行为的构成要件故意是“双重故意”。如果不在构成要件符合性层面,就讨论狭义共犯的主观状态,难免会使得所有与结果具备因果性联系的行为人,都被认定为不法共犯人。虽然可以在罪责阶层考察“双重故意”之有无——最终也不会论以犯罪,但是这来得太晚了。这种做法,导致不法的范围过于浮滥,使得刑法丧失安定性。而且,如果像某些结果无价值论者完全不考虑主观要素来确定不法,并坚持对不法行为可以科处保安处分[注]参见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以下。,人权保障水平可能会下滑。将行为评价为不法,意味着行为侵害了法益,行为不具备正当性,是有害于社会的。一旦脱离了主观故意去认定共犯行为,则对于特定行为的不法评价将是“强人所难”——不法意味着行为人应当“不该那样做”。更为重要的是,不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是否属于以及属于何种帮助行为、教唆行为。例如,甲在屋内盗窃财物,乙在屋外走动并四处观望,如果甲与乙之间没有意思联络,乙是自发地“帮忙”(片面帮助),如果不纳入乙对甲的盗窃行为有认知,显然很难说乙“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的行为侵害了什么法益,顶多是“打望”而已。又如,某一个毒贩要租房子,边住着边制毒、贩毒。如果房东知道他是一个毒贩子,在他来租房子的时候爽快地出租了,或许可能属于帮助犯。如果房东不知道这些事,即使事后知道了,原先的出租行为显然属于日常行为,很难说侵害了什么法益。
同理,如果不承认共犯人对主行为故意之从属,也难以贯彻区分制。诚然,否定共犯人对主行为故意之从属,不会造成处罚漏洞[注]例如,行为人出于故意帮助行为人,但是主行为人有过失但没有故意的时候,由于德国刑法只有处罚未遂教唆的规定,这将导致处罚上的漏洞。,结论也更具有合理性[注]例如,主行为人只是过失,而策动者认为有故意行为,只能够以未遂教唆(versuchte anstiftung)论处。否定故意之从属的观点,会认为这是故意犯罪(既遂)——德国结果无价值论者也是持此说(Vgl.Baumann/Weber/Mitsch,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11.Aufl.,Verlag Ernst und Werner Gieseking,2003,§30,Rn.26.)。但是主流观点都是持否定态度,因为上述观点明显漠视了客观流程与主观状态的对应理论,违背了责任主义(Vgl.Jakobs,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2.Aufl.,Walter de Gruyter&Co.,1991,§22,Rn.18.)。,但是这瓦解了共犯从属性说。参加无故意主行为的“共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犯”,而只是肇因者。[注]Vgl.Welzel,Das deutsche Strafrecht,11.Aufl.,Walter de Gruyter&Co.,1969,S.114.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德国新刑法改变了旧刑法没有要求共犯对主行为故意之从属的做法,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议[注]Vgl.Schmidhäuser,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2.Aufl.,J.C.B.Mohr(Paul Siebeck),1975,§14,Rn.94.,但是并未改变立法的进程。因为相较于全面舍弃主观构成要件要素,所带来的不法范围过于宽泛、共犯处罚范围无限扩张而言,容忍误认为“他人会有故意”的帮助人逃脱刑事制裁,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认为,成立参加,不以正犯故意犯罪为必要,那么在正犯出于过失甚至意外的时候,教唆犯与帮助犯将无从比附。例如,正犯出于过失,(故意的)教唆犯是不可能比照他所处的犯罪参加中的正犯处罚的。采取共犯从属性说的刑法典,其实都已经预设了正犯不法高于共犯不法,教唆不法高于帮助不法。如果不承认他们的不法程度有高低之分,认为凡是“侵害法益”的行为都是不法行为——不论行为人是否具备故意或过失,由于诸位参加人都具备故意罪责——故意罪责之间没有高低之分,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正犯的刑罚重于共犯的刑罚了。更深层次,否定共犯人对主行为故意之从属,在正犯出于过失时,对于(故意的)共犯人的处理方式,必然将与单一正犯体系的处理方式一样:每一个行为人的参加形式与不法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法官依据每一个行为人的行为贡献大小,分别裁量刑罚。
四、单一正犯体系与刑法目的理性
由于区分制不断地修正了自己的“正犯理论”,尤其是在德国学者罗克辛提出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之后,致力于将“正犯主犯化”,加上不少采取区分制的刑法典——例如《德国刑法典》《瑞士刑法典》,原本就处罚未遂教唆[注]中国学界历来将“未遂教唆”理解为“未遂的教唆犯”,值得检讨。德语中的“未遂”有“尝试、力图”的意思,“未遂教唆”就是努力去教唆但是还是失败了。(versuchte anstiftung),目前两种参加理论的差异正在不断缩小。继续停留于罪刑法定原则层面批评单一正犯体系,或许难言合理。过于抽象的理念指摘,已经不能适应理论探讨的要求,也容易产生“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
在三阶层逐渐被二阶层所取代的大背景下,构成要件本身也在进行实质化的改造。从最初中性、无色的构成要件论,到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发现,再到全面承认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社会相当性理论的提出,以及新进的客观归属论,被害人合意(Einverständnis)、被害人承诺(Einwilligung)一元论,都成为了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的“阻却事由”。置身于宏大体系,较易准确检验个别认知。观察变动中的刑法思想,不难发现,单一正犯体系契合了构成要件实质化的潮流,满足了刑法体系的功能性思考与实质化导向。对于单一制,刑法学理上最常见的批评是,其“在构成要件上网罗所有对法益侵害历程有贡献的行为人,容易使构成要件遭到浮滥适用”[注]许泽天:《主行为故意对共犯从属的意义》,载林维主编:《共犯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页。,或者说,该理论将行为构成的满足简化为因果性,就会导致刑事可罚性发生不可容忍的扩张。[注]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王世洲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然而,这或是误解:
首先,在正犯着手实行犯罪后,对于参加人的处罚范围,单一制与区分制并无不同。随着近年来德日的有力学说将参加人的处罚范围,扩大到正犯预备阶段,两种体系的不同仅在于,后者对侵害“法益”的行为方式进行了分类。其实,共犯从属性说一面主张“限制的正犯概念”,一面又将刑罚扩张到共犯身上,无非也是尊重了刑法目的的结果。反而我们可以质疑:强调每个参加者侵害“法益”的方式、手段的不同,真的合理?是否是一个未经检验的想当然的做法?就侵害“法益”而言,不管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之,其实都不重要。区分制的发源地,意大利与奥地利已采取了单一正犯体系,而且,这两个国家以及其他的采取单一制的国家或地区,如挪威、丹麦,乃至英美法系的所有法域,在人权保障力度上,较之于德国、日本,没有多少可以惭愧的地方。依据德国学界通常的说法,行为刑法概念,作为一种法定的规则,意味着惩罚仅仅表现为对单个行为(或者可能情况下的多个行为)的反应,而不是表现为对行为人整体生活导向的反应。[注]同前引[52],第105—106页。从属性说论者时常将单一正犯体系与共犯独立性说做等同理解,或许不是一种严谨科学的研究态度。毕竟,单一正犯体系从来没有将刑罚的根据归结为人身危险性为由。正如区分制之中,“不论是对扮演正犯,还是扮演共犯的行为人,其处罚理由都在其行为破坏各罪构成要件所保护的法益,而非在使其他人陷入成为犯罪人的境地”。[注]同前引[51],第238页。在单一正犯视角下,也只可能将那些事实上已经侵害到了“法益”的行为认定为犯罪。
其次,德国、日本司法实务中,大量扩大共同正犯的范围,使得正犯与共犯的界限模糊不清。而且,限制的正犯概念,同样无法给出共犯行为的成立条件,使得法官在无法确定行为人是否为共犯时,可能将其全部认定为共犯,也有造成刑罚过度浮滥,进而损害法的安定性的危险。作为从属性说立论根基的限制正犯概念,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从构成要件的形成关系来看,共犯行为既然不属于实行行为,那么必然产生如下疑问:在何种条件下的共犯行为可以被涵盖到刑法判断的范围之中成立帮助犯与教唆犯?换言之,在何种情况下,加功于正犯行为之人才可以被视为共犯?既往所有的从属性说对此避而不问。在每一个持从属性说的教科书上都很容易地找到“正犯和参与的界限”“正犯与共犯之区别”“正犯理论”等相关内容,但是很少看到“参与行为与中立行为的界限”“共犯理论”等相关内容。如果只有确认正犯的理论,却欠缺确认共犯的理论,仅仅论以从属性的关系显然仍无法消除何以形成共犯的疑虑。只有存在充分的共犯形成的判断基础,才能进一步检讨从属性问题。在无法判断“加功程度”的认定关系时,直接切入从属性的检讨,给人以思维上的跳跃与论理上的急躁之感。此种不当,要么造成处罚漏洞,要么造成刑罚滥用。相对的,单一制直接思考该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在构成要件阶段确定谁可罚,也需要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再次,不论是针对什么样的犯罪行为科处刑罚,都必须具有刑事政策上的正当性。一般认为,如果想要让刑法能够起到保护法益的效果,刑法就只能够针对未来的、尚未发生的事件发挥作用。这也就是学理上的“以积极地一般预防为导向的法益保护”或者“通过规范的预防性法益保护”。[注]参见蔡圣伟:《刑法问题研究(一)》,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80页。共犯原理与行为无价值二元论的结合,导致刑事归责的类型的实质性重构,使得结果归责的范围较之于严格的实行从属性说宽松很多。未遂教唆、未遂帮助都具有可罚性,只要进行了教唆、提供了帮助,即使对结果的出现没有现实的助益,也可以进行处罚。[注]参见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148页。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行为是否现实地侵害了法益,不能够进行纯粹事实性的理解,否则,“将会使法益和违法性理论流失其规范刑法学的基本内涵,而成为纯事实性概念”。[注]参见刘艳红:《实质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如果某一行为的重演,可能会侵害法益,那么,就应当认为,这一个行为是值得处罚的。即使在采取区分制的德国,也没有一概认为,在正犯没有实行犯罪的时候,就坚决不能处罚共犯。反而顺应复杂多变的生活事实,出现了某种“从属性的松动”(Akzessorietätslockerung)。[注]Vgl.Krey/Esser,Deutsche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5.Aufl.,Verlag W.Kohlhammer,2012,Rn.1011ff.《德国刑法典》第30条第1款规定,“力图确定或者教唆他人实施重罪(根据同法第12条第1款的规定,重罪是指,最低刑为一年以上(含一年)自由刑的违法行为),依照重罪的力图的规定加以处罚”。第2款规定,“就实施或者教唆某一重罪而言,自愿声明、接受他人的请求或者与他人约定者,同样处罚”。尤需注意,《德国刑法典》分则中的实质预备罪很少,但是通过第30条第2款的规定,就将所有的重罪的共谋行为纳入了刑事制裁的范围。对此,德国学者是这样论述的,若干参加人的犯罪预备与单独犯的犯罪预备更加危险,单个行为人可能无法掌握犯罪的进程,而且,这使得犯罪更容易得逞,也很难出现犯罪中止与犯罪脱离,此外,在彼此之间对共同实施重罪的交流沟通,本身也质疑了相应罪刑规范的法律效力。[注]Vgl.Frister,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Verlag C.H.Beck,2009,S.407.另有德国学者也说,这一规定“意在阻止阴谋性质的意志形成,从这样的意志形成中产生的法益威胁,要比那些可以随时推翻和很容易再次放弃的单个决意中产生的明显要大”。[注]参见[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柯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64页。这对于盛行结果无价值论的日本刑法学界来说,可能难以想象。但是,德国不少法官认为,教唆者教唆了他人去实施一个有可能发展为既遂的重罪时,教唆行为本身就蕴含了一种可能使得事态“失控”(Einflussverlust)的抽象性危险,而共谋约定尤其会使得各个参加者将难以从犯罪中撤出来。例如,一个人书写了一封要求证人作伪证的信件,即使这封信在送信路上被警察截获,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是认定其构成了伪证罪。
最后,贯穿参加理论始终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从构成要件层面考察,何种行为才具有刑事可罚性,即犯罪参加的类型问题;二是从刑罚裁量层面判定,各个参加者应科处的刑罚量,即犯罪参加的程度问题。区分制混淆了参加类型与参加程度的关系,舍弃刑罚个别化,进而导致刑罚上共犯必然要轻于正犯的不当结论。在区分制下,只有确认正犯的理论,没有确认共犯的理论,共犯的处罚根据也只是证成了共犯必须处罚,中立的共犯行为自始至终都没有建立系统的理论予以归纳,是否应当绝对排除过失的共犯也含糊不清。因此,前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后一个问题似乎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是,问题的解决,却建立在突破自己原有的正犯理论的基础之上:将参加活动中作用较大,但是又完全没有该当任何构成要件的行为人也纳入正犯。而且,依旧的遗憾是,“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人恒属于正犯”,可能在幕后操纵者发挥作用更大时——亦即是操纵指挥行为比实行行为的危险更甚时,二者却同等视之的不公正现象。
相反,在单一制中,前一个问题表现为参加人与非参加人的区别,即可罚性的外部区别;后一个问题表现为各参加人内部的作用大小的认定,直接交给量刑解决。不容忽视,早期的单一行为人概念,从因果关系的条件说出发,认为凡是对不法构成要件的实现有贡献的人都是正犯(单一行为人概念),而不论其贡献的程度大小。现代的单一正犯体系,强调“共同合作的二重性”:在构成要件阶段确定谁可罚;在量刑阶段根据参加人的不法、责任确定个别化的刑罚。参加形态并不重要,对于刑罚裁量起作用的仅仅是参加人的贡献力度。
五、从单一正犯视角看构成要件行为
在参加理论中,“体系的思考方法”与“散在的思考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是从共同犯罪行为的存在意义出发,还是从共同犯罪行为的规范意义出发,去理解“共动现象”。诚如德国学者雅科布斯所言,必须依据刑法的任务,而不是根据其他刑法以外的主张建构刑法体系。刑法中的概念也必须进行规范化的理解与诠释。[注]Vgl.Jakobs(Fn.49),S.V,Ⅶ.对于犯罪行为的表现形态,不能仅仅凭借存在论上的差异,就断然声称它们必须在规范论上予以区分对待。解决参加问题的思路,必须完成从事实性与存在论到机能性与规范论的转变。
共犯从属性说原先认为,正犯仅指直接实现构成要件的人,间接实现构成要件的人只能是共犯。后来认为,以自己犯罪之意思,间接实现构成要件的人也可以为正犯。晚近的德国学者更是明确指出,正犯是“操纵犯罪行为的核心人物(die Zentralgestalt des konkreten Hundlungsgeschehens)”[注]Vgl.Roxin(Fn.19),S.529.。显然,这一定义,并不是通过演绎逻辑得出的必然推论,而只是一种事实性的描述,或可谓是一种经验式的总结,已经完全否定了以前从构成要件的形式侧面建立标准,以区分出正犯与共犯的各种努力。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只将正犯认为是支配犯罪发生的人,其实毋宁说,任何犯罪的成立,都需要行为人对于结果的原因具有支配力。犯罪不是简单的因果流程,而是经由行为“体现的行为人对导致法益侵害的整体事件过程的支配力”。[注][德]许乃曼:《不纯正不作为犯及以不作为实施犯罪之形式》,载梁根林主编:《刑法体系与犯罪构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8页。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否认共犯行为也是犯罪行为的话,那么,正犯与共犯都支配了犯罪结果的发生:缺了哪一个人,犯罪都可能最后“不是这个样子”。仅有的区别,也只在于各自的支配程度不同,而与实行与否关系不大。在这一意义上,分工分类法已经逐渐向作用分类法靠拢了。
如前所述,共犯行为与正犯行为一样,都需要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都需要进行结果归责:都需要将结果归责给对引起结果的原因具有支配力的人。这是单一制与区分制“共同的底线”。但是由于各自采取的路径不尽相同,因而对于刑法基本原则的贯彻以及说理充分程度存在着差异。共犯从属性说认为,犯罪参加是“数个人犯一个罪”,共犯人只能依附于实行犯才构成犯罪。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正犯行为会产生正犯、共犯的几个刑事责任,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正犯举止可能导致正犯与共犯之间存在不同的犯罪形态,不能说明为什么部分行为要负全部责任——尤其是教唆犯的最终“待遇”与正犯没有什么差别。这些目前解释参加现象的各种理论,存在着法理与情理的“悖离”。在法理上,处罚共犯行为“不符合”刑法基本理论:首先,刑法只能处罚构成要件行为,不能处罚构成要件以外的行为;其次,依据以往的行为理论,共犯人的身体动静不符合构成要件;最后,罪责自负原则要求不能处罚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在情理上,不处罚共犯有悖于民众的基本感情。
而根据单一正犯体系,犯罪参加无非是这样一种共动现象:以其他人的行为,作为控制条件的行为形式。每个参加人,都以其他参加人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组成部分(狭义共犯人在犯罪参加中的行为不仅包括共犯行为,也包括利用行为)。行为人利用他人作为自己追求不法利益的工具,每一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各自独立地构成犯罪。从而,按照每个共犯人的罪过内容及其实现程度来定罪,按照每个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来量刑(在其中,利用他人最为充分的就是主犯)。任何人只对也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直接杀人的人,应当对其不法且有责的行为负责;教唆杀人的人、帮助杀人的人,也应当对其不法且有责的行为负责。如果认为正犯的“作品”也是共犯的“作品”,正犯侵害“法益”的结果也能归属于共犯人,那么基于“无行为即无犯罪”的刑法准则,就必须承认,正犯行为在共犯行为的延长线上。基于存在论的角度,共犯行为迥异于正犯行为,但是,“从最终受罚的只是单个参加者的现象来看,其不过是利用了和他人一起行为的契机,实现自己犯罪目的的一种类型而已,和一个人单打独斗的单独犯之间没有什么两样”。[注]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5页。不难看出,相较于从属性说,单一正犯体系的说理更为透彻充分。例如,共同正犯的“归责依据”有所谓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共同正犯是指两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因此必须存在共同实行的事实,而所谓共谋共同正犯,认为没有实施实行行为的人也成立共同正犯。”[注]陈家林:《外国刑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但是仅仅依靠一个“犯意联络”就可以对行为人不充足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进行“补强”吗?而且,如果共同正犯人中的其中一个就已经负担了“全部责任”,那么,按理来说,其他人将无责任可负。
在共同犯罪未遂时,对诸行为人可以科处刑罚,区分制论者对此并无异议。有分歧的仅仅是,一个人想去共同犯罪而未能遂意(参加的未遂),是否可以处罚。诚然,当时《德国刑法典》的立法者有意识地将力图帮助(versuchte Beihife)、对重罪约定的帮助和对重罪帮助的单纯承诺,排除刑事可罚性。[注]同前引[60],第319页。但这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之中公民对社会秩序的合理期待了。对于被教唆的人或被帮助的人没有犯罪的情况,坚持实行从属性说,显然是不能处罚教唆人与帮助人的。但这不尽合理。如果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本身已经逾越了刑法所能够容忍的程度,刑罚就必须出面,否则,基本的法律制度将陷入崩溃的境地。有学者曾发出来这样的感叹:“很难理解,为什么行为人出自真意的教唆或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必须依赖他人是否进行有效的侵害行为,才有刑罚性。”[注]李圣杰:《共犯从属性的光与影》,载前引[51],林维主编书,第291页。如果坚持实行从属性说,必然就会产生,行为人可能由于自己无法控制的某个偶然因素,而得以挣脱刑事制裁的奇怪现象。如果对所有的未遂教唆与未遂帮助放任自流,显然无助于保护法益。因为这无非是在传递这样一种信号:你可以肆意教唆与帮助一个人去犯罪,只要他不去犯罪,你还可逍遥法外!勇于尝试实现不法的行为,需要给予刑罚回应,毕竟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保证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还有这样的运气,下一次行为人的行为依旧停留于这样的境地——而不可能是犯罪既遂!“如果它停留在我想要教唆他人犯罪,这没有问题,不用处罚,因为这只是思想,可是他讲出来了,他人也接收到了,这个时候的处罚绝不是建立在思想刑法上面。”[注]此系陈志辉教授的会议发言。参见《高级论坛实况》,载前引[51],林维主编书,第625页。因此,处罚未遂教唆与未遂帮助,与思想刑法、行为人刑法无涉,而恰恰是行为刑法的表现,坚持了“法益侵害说”,体现了“一般预防论”,处罚的就是行为人的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本身,而不是处罚其“未遂”。
教唆犯开始了教唆、帮助犯开始了帮助,可谓是一种“预备行为”。如果正犯接受了教唆与帮助,但尚未着手实行,共犯仍然至多只能评价为“犯罪预备”。所以说,在单一制中,共犯(利用人)的“着手”也依赖于正犯(被利用人)的“着手”。这就好似区分制中,间接正犯“着手”的成立是在被利用人“着手”时,具备正犯性的共谋共同正犯“着手”的成立也是在直接实行人“着手”时。不同的是,单一制中的“共犯并非因为对于他人行为的挹注(即加功——引者注)而受处罚,而是因为自己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之不法而负责,至于对于正犯的从属,只不过是纯粹事实的性质(rein faktischer Natur)”。[注]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此外,对于参加人彼此之间的刑罚轻重,区分制在定罪层面加以解决,其依赖的是参加的形态;单一制留待量刑阶段进行考虑,其依赖的是参加的贡献。于单一制而言,在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微弱时,或者主观罪责不大时,完全可以排除犯罪性。即使结果属于行为人的意志所控制或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也还要考察是否具备社会影响上的重大性——行为的危害是否严重。单一正犯视角下,行为人(Beteiligung)不可以被理解为那个引起了“法益”侵害结果发生的人,而是那个可以对“法益”侵害结果负责的人。也就是说,认定参加者,需要区分结果的造成与对结果的归责。诚然,以往的单一正犯体系通过“条件说”过分扩张了不法的范围,将所有对构成要件的实现存在原因性贡献的人都视为正犯——正如客观归属理论提出来之前的刑法理论一般,虽然也可以在罪责阶层排除很大一部分行为的参加性,但是这毕竟“来得太迟了”。欣慰的是,如今的单一制已经经过了规范性的“改造”,运用客观归属论去判断“正犯行为”——主要是“不典型的构成要件行为”的边界:“根据对构成要件性的结果在客观上的可以预见性和可以避免性,根据人的行为对因果发生的可以避免性,以及根据由行为人制造的或者加重的对出现危害的风险性的实现情况,来确定归责终止的界限。”[注]同前引[60],第106页。
结 语
我国刑法的参加规范,为单一制提供了法律语境,实质上使得加功于构成要件实现的每个参加人都取得了平等的地位。对于近来学界运用区分制理论,解释我国刑法相关规定的做法,台湾学者曾说:“对于大陆刑法学界在此犯罪参与议题中跳离立法(‘窠臼’)的学术现象,或可称为当代中国刑法学的特色。”[注]参见前引[51],许泽天文,第256页。好在晚近刑法学界已经认识到,我国的参加规范归属于单一制,其操作便利,还揭示了一个荫蔽已久的“真理”:参加形态与支配程度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呼吁实质刑法观、功能刑法观的今天,单一制迎合了构成要件理论的演化进程,我们应当肯定并坚持下来。这也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就合理性而言,单一正犯体系,作为19世纪从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角度理解刑法概念的对立面,反映了人们试图从价值和规范上把握刑法思潮的努力。区分制与单一制的争论,接续的是学理上有关存在论与规范论、描述性与规范性的立场争论,体认的是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这两种不同的学术旨趣。综观德日参加理论近两百年的演进史,可以肯定,形式刑法观下的共犯论基本上已破产。只有贯彻实质刑法观,才符合实质正义和客观主义。就合法性而言:(1)第13条规定了犯罪行为的内涵,这种普遍式的定义,在比较法上属于很少见的做法,对此,存在批评意见,也存在正面评价。不可质疑的是,此处“危害社会依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包括了所有的参加行为;(2)第25条给予所有参加犯罪的人以“共同犯罪人”的待遇,显然,“共同故意犯罪”中的“犯罪”,不仅包含“实行行为”,也包含“帮助行为”“教唆行为”乃至“组织行为”;(3)第26条中的主犯不仅包括实行犯,也包括组织犯;第27条中的从犯不仅包括“起次要作用”的实行犯和教唆犯,也包括“起辅助作用”的帮助犯和教唆犯;(4)第28条中的胁从犯也不是帮助犯的特殊类型,既可能是被胁迫去实行犯罪的人,也可能是被胁迫去帮助犯罪、被胁迫去教唆犯罪的人;(5)第29条第1款,没有把教唆犯限定为“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的人,还可能包括连环教唆、教唆帮助等情形,更没有一律赋予教唆犯以“准正犯”的待遇,而且,在处罚上,教唆犯可能比正犯重,可能比正犯轻,也可能和正犯一样;(6)第29条第2款,直白肯定了“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时,教唆犯的刑事可罚性,赋予了教唆犯以独立的归责地位,其成立与否不依附于(正犯的)实行行为甚至预备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