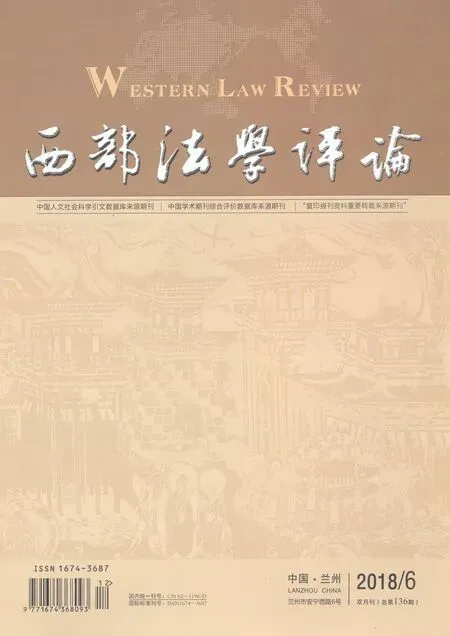渐进主义视野中环境权利的发展路径
杨 曦
一、问题的提出
人权有三代之说。第一代人权是以自由权为核心的消极人权,即一种不受侵犯的权利;第二代人权是以生存权为核心的积极人权,即主张国家承担保障义务的权利;第三代人权是环境权、发展权为核心的自得权利。[注]徐祥民:《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环境权源于人权,“人权”的概念源于自然权利,而“自然权利”的概念又源于自然法,即“环境权”这个概念追根溯源是自然法的产物。相比之下,“自然权利”侧重于以人性为基础,而“人权”则强调人的道德性,以“人权”作为基本权利的研究起点,更加侧重于人的理性。[注]钟丽娟:《自然权利的制度化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总体上,无论是从“人权”还是“自然权利”基本概念出发都会有意无意地迈入理性主义的思维之中,这是因为在自然法的观念中,一直存在着一种理性主义的倾向,自然法一直都密切地跟“自然理性”之作用连接在一起,而且被视同于人之尊严与能力,即在自然法的观念中人类可以运用人的理性去发现规则。[注]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李日章等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55—58页。因此,环境权从诞生之初,就带有“理性主义”的色彩,强调自上而下的在宪法之中预设环境权,而后在各个部门法中设置“环境权”以达到对于环境利益的全面保护。[注]周训芳:《环境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这种应然的角度设计环境权,显然使得环境权理论过于理想化。现在自然法的任务不是给我们一批理想的普遍立法,而是给我们一种对实在法中的理想成分的鉴定。[注][美] 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页。同时,作为理性主义的延续,抽象概念的研究方法会使得人们进行“是”或“否”的绝对两分,“多”或“少”的近似思考是严格排除在外。[注]方新军:《权利客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146页。由此,环境权的否定者得出结论:环境权“主观权利化”既没有理论基础,又缺少司法实践。[注]陈海嵩:《环境权实证效力之考察:以宪法环境权为中心》,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类型概念与抽象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类型是以评价观点为其构建因素,而抽象概念则是以用来表达概念特征的语言符号的“可能的意义范围”为其构建要素。[注]同前引[6],第147页。环境权更应当从类型概念思考出发,法官与立法者将环境权纳入考量时本质上应体现一种价值判断,是在环境利益与其他利益之间做出衡量。
目前我国的立法中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多为义务性的条款,通过限制的手法间接地保护了环境权利。这种立法模式结合概念法学的思考,使得环境权学者在研究环境权利时,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公法权利的范式之中[注]基于社会风险预防的考量,侧重于环境参与权的构建。参见张恩典:《“司法中心”环境权理论之批判》,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通过公众参与解决城市空间分配纠纷的,参见陈国栋:《公法权利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利益争端及其解决》,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 年第2期。基于公法上的请求权的视角,参见张震:《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从理论到实践》,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等。,或是过分强调环境义务对环境权利的间接保障效果[注]这种观点主要来自于义务本位论的环境权理论,强调了环境利益的公共性,通过促进环境义务来保护环境。参见徐以祥:《环境权利理论、环境义务理论及其融合》,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参见刘卫先:《环境法学中的环境利益:识别、本质及其意义》,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3期等。,又或是专注于国家权力对环境的保护[注]史玉成:《环境利益、环境权利与环境权力的分层建构》,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5期。何佩佩:《环境法本位的反思及环境法多元化保障手段》,载《政法论丛》2017年第3期等。。这种研究趋势忽视了环境权利自身发展的形态,使得环境公民权利始终无法顺利具象化,在应然与实然之间有一层很微妙的隔阂。
二、渐进主义原则及方法的导入
在公共决策的方法论中理性主义也称为“理性——全面”主义,其对立方法是渐进主义。这种方法系统地在公共决策中出现:一方面公共决策与立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甚至两者在政治方面具有重合部分;另一方面由于公共决策影响着立法,尤其是在环境政策方面,例如196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的第一篇第3条规定了“享受健康的环境”的权利。因此,在方法上法学与公共政策学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另一层面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相对,而渐进主义正是基于经验主义作出的判断[注]杨涛:《间断—平衡模型:长期政策变迁的非线性解释》,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 年第2期。。当代这种思维也向着法学领域延展,在宏观的法治引入上,马长山教授在《法治的平衡取向与渐进主义法治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国法治进程不能靠西方化、模式化的制度设计和理想主义、激进主义的权利诉求来推进,而是应当采用渐进主义的法治道路进行。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有学者认为当下无法实现最优选择的情况下,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将成为推进某些制度的次优路径。[注]参见赵骏、吕成龙:《〈反海外腐败法〉管辖权扩张的启示——兼论渐进主义视域下的中国路径》,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在新型权利的立法顺序上,一般为个案裁判——法律解释——法律普遍化的渐进思路。[注]参见王庆廷:《新兴权利渐进入法的路径探析》,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因此,从环境权利的实现也可以尝试通过渐进主义的方式进行。
(一)“渐进主义”的流源与释义
当下,渐进主义的概念逐渐被法学所吸收与借鉴。法理学中的渐进主义主要是由于:1.法治源于西方,但是需要注意到西方法律的非模块化、流动性,以及注意到非西方国家法治发展的多元性与地方性。2.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需要互动平衡。因此,我国在法律移植与构建法律体系时,应当:(1)国家权力与多元社会权利之间的平衡。(2)立足于社会承受力,推进权利与权利、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3)保持法律制度与多元规则的适度并存。[注]参见马长山:《法治的平衡取向与渐进主义法治道路》,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当然,此处的法治发展是更具有宏观的色彩,但是与公共决策中的渐进主义仍具有相似之处,例如在注重多元化、非模块化以及注重动态的平衡等观点上基本是一致的,可以说两者都传承了渐进发展的思路。在具体制度构架上,渐进主义要求法律的实施是逐层推进、步步展开,以点带面地将制度予以完善。
(二)导入“渐进主义”的必要性
首先,来源于西方的人权思想。环境权主要源于西方人权思想,同时英美法系通过公共信托加以改造进入权利谱系。环境权的概念被引入中国是1982年蔡守秋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刊载的《环境权初探》一文,由此揭开了环境权理论研究的序幕。我国的环境权理论研究虽然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但是仍未成体系,在很多基本问题上尚存争议。因此环境权这个概念在从西方国家引进之时,仍旧需要注意其抽象性,以及当作为权利进入法律视野中时,需要考虑到本国的社会承受力。在非西方国家,日本环境权理论陷入了存无的争论之中。在国会的讨论中,支持者认为环境权可以视为国家政策或者以国家义务的形式体现,反对者则认为环境权主体、内容不明、定位不清等原因,倘若作为私权入法有挂标签的嫌疑,属于多余的概念。但是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主张把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直接写入宪法。[注]参见徐祥民,宋宁而:《日本环境权说的困境及其原因》,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3期。虽然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发布,从1976葡萄牙开始至2012年,已有92个国家在宪法中承认了环境保护的宪法权利。[注]See David R.Boyd,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2). 5—6.但是目前而言环境权理论仍旧处于争议之中,这种从无到有,再到内容、属性的反复的争论体现了环境权理论的流变性、非模块性、多元化以及地方性特点。因此,环境权理论作为舶来品,更加需要通过渐进方式进行本土化的操作。
其次,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长期处于失衡状态。环境权实质是法律对环境利益的保护。所谓利益,就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性情和思想使自身的幸福观与之联系的东西。换句话说,利益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人认为对自己的幸福是必要的东西。[注][法]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71页。庞德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其中公共利益是指从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需要和愿望。[注][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页。这种三分说受到了广泛的引用,但是目前学界逐渐开始反思这种学说的正确性。“从利益主体的角度,可以把利益分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公共利益表现为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私人利益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注]赵震江、付子堂:《现代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而所谓的环境利益,根据环境因素而取得的幸福。环境利益可以区分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的法律保护方式一般是环境权利,而公共利益上法律的保护手段则是环境义务,这也是环境权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之争的由来。在环境领域,即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在部分之上体现为一致性,但是公共利益的范围还是要比个人利益更加庞大。针对整体的环境法规范而言,环境义务所涵盖的内容要大大宽于权利的内容,即要大量的规范设定了相应的主体的义务,却并无权利与之对应。[注]徐以祥:《环境权利理论、环境义务理论及其融合》,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因此,环境权理论中环境义务与环境权利处于一种非平衡状态,这种非平衡的状态会使得环境权力与权利之间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之中。为了同时满足个人和公众环境利益,环境权的研究必然需要向着互动平衡的角度逐步发展。
最后,环境权理论中“权利本位论”的发展是依托于自然法中天赋人权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很难容纳“社会性环境权利”或“国家环境权利”,并且“权利本位论”过于追求从应然法到权利的设置,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但是这种基于“理性主义”的判断,显然过于理想化了,[注]王小钢:《义务本位论、权利本位论和环境公共利益——以乌托邦现实主义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2期。有学者甚至直接指出环境权不是自然权,其权利的幅度与确认依赖于国家的认可。[注]李启家:《环境法领域利益冲突的识别与衡平》,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6期。抽象概念的研究,使得环境权模糊不清。这种无所不包的理论反倒成为了进入法律的阻碍,而且在论证时往往难以自圆其说。环境权中公民权利的发展必然需要从经验主义出发,通过类型概念逐步发现环境权利的内涵与外延。
总之,环境权的实现既需要通过“客观秩序”(义务层面)的形式实现,同时也需要从保护私主体的利益的目的出发,需要通过循序渐进的方法将环境利益逐渐转变为权利,并且需要让权利与义务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的关系。因而,以环境权理论为背景的权利研究必然适用渐进主义。
(三)导入“渐进主义”具体方法:利益法学对“环境权论”的修正
环境权理论的目标与利益说具有一致性。宏观上,利益说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但是功利主义却不是一种个人主义,而是追求公利。[注]参见方新军:《权利客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127页。在特定的环境下,客观的正当的行为将能产生最大的整体幸福。[注]参见[英]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来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8页。这与环境权理论中公益与私益的一致性是相似的。
权利的利益说认为权利是法律所承认和保护的利益。许多利益是可以直接上升为权利的,但是利益与权利是不能完全等同的,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一,从目的与手段上看,利益往往是权利的目的,权利往往是获得利益的手段。第二,从价值论上看,权利具有道德价值,利益具有功利或经济价值,因而权利属于道德的范畴,利益属于经济的范畴。第三,从主体上看,权利主体并非利益的主体,反之亦然。[注]范进学:《权利政治论:一种宪政民主理论的阐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根据利益说,可以将环境权利与环境利益的关系总结为:首先,环境权利是实现环境利益的手段。其次,环境利益具有经济属性,环境权利是在伦理认可的基础上产生的法律权利。最后,环境利益与环境权利的主体存在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在环境权利中主要体现为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的不一致性。
但与这两年的风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茅台酱香系列酒的过往却有些“默默无闻”:从1999年茅台推出茅台王子酒,到2000年推出了茅台迎宾酒,之后又陆续推出的其他酱香酒产品,十多年的时间里,系列酒的贡献率一直比较低,在茅台的营收占比中从来没有超过10%。即使是“黄金十年”顶峰期的2012年,系列酒在茅台营收中的占比也只有9.16%。毫不客气地说“黄金十年”期间“茅台在狂奔,系列酒在沉睡”。
在司法领域,利益衡量论是法解释论的一种形态,是对概念法学的修正,尤其是在当下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法院面对新的问题与案件类型,不能机械地适用法条解决。[注]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基于利益衡量论而产生的容忍限度学说曾经遭到了环境权学说的批判,环境权说对容忍限度论诟病之处在于容忍限度内后者偏袒了公害制造者,让大量受害者对于环境利益诉求,通过利益衡量的手法被排除于救济范围之外,使得危害正当化。或者仅通过支付补偿的手段,继续公害侵权行为。在此基础上,容忍限度论作出了修正,将权利滥用同样做违法性的判断依据,并且降低了一些因子在评价违法性时的作用。[注]张利春:《日本公害侵权中的“容忍限度论”述评——兼论对我国民法学研究的启示》,载《法商研究》2010 年第 3 期。事实上,两者是有互通性的,例如环境权说并不否认环境侵权中将容忍限度作为评价违法性的依据。既然容忍限度论可以吸收环境权说中对于环境保护的一些积极因子,那么为何环境权说不能借鉴容忍限度论中有关利益衡量的相关方法呢?其实当环境侵权的容忍限度变成“零容忍”或是即使在容忍限度内仍旧使用权利保护时,环境权说与容忍限度论即可达成统一。
从利益角度出发研究环境法必然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注]程多威:《环境法利益衡平的基本原则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当然对环境权论的修正,不仅存于司法的法解释论中,而且应存于立法之中。通过利益衡量,首先将一些重要的环境利益作为权利进行保护。其次在原有保护程度的基础上增加保护强度,最终达到环境权所倡导的绝对的权利保护。在同一层的权利之间发生冲突之时,凸显出环境利益的重要价值,侧重于保护环境权利,即有学者提出的“环境利益本位”[注]吴贤静:《环境权的本位:从支配环境到环境利益优势》,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在此情形之下,环境权不能被应然地视为一种权利,权利是达成环境利益保护的手段。通过渐进的保护路径,不断修正环境利益保护之中的缺失,最终达成环境权理论的目标。
三、渐进主义适用于环境利益权利化的次序
渐进主义具体而言是对之前修正方案的不断修正,具有动态的形成特点。具体到环境权利上,是不断将环境利益权利化保护的过程。人权之中的环境权是一种道德权利,上升为法律权利仍旧需要进行相应的价值考量,考量的对象是环境利益。因此,必须要将环境利益类型化之后作相应的排序,以保证这种环境利益权利化后的正当性。
(一)环境利益的类型化分析
环境权理念,尤其是基于公民权利的方向研究中,是将环境利益以权利的形式加以维护,从而使得环境利益在救济方面得到可视化的表达。环境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概念被提出,在公民权利方面必然具有独特性。环境权是基于第三代人权而产生的,不同于传统的人权理论,环境权的保障层面更高。健康权、生命权都是最低限度的保障,国家也仅承担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义务。[注]吕忠梅:《环境权入宪的理路与设想》,载《法学杂志》2018 年第1期。因此,环境利益蕴藏在传统的基本权利之中,但是环境权中的环境利益又高于传统权利的保护范围。有学者对环境权通过嫁接于人格权、物权和侵权责任得到体现。[注]张震:《民法典中环境权的规范构造》,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这种环境权确立的方法,实际上是环境利益注入于其他权利之中,而这些环境利益能否因此称之为“权利”或者说是否能够以权利的方式得到全方位的保护,仍旧是有待商榷的。但是这种以传统权利为依据,将环境利益进行嫁接的处理方式是值得借鉴的。但是不应将环境权作过于广义的理解[注]环境权的基本概念有三种代表性学说:1.最广义环境权说(个人环境权、单位法人环境权、国家环境权和人类环境权等);2.广义环境权说(环境使用权、自然资源财产权与环境参与权);3.狭义环境权说(环境权是一种对一定环境品质的享受权,是实体性的权利,不包括经济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载吴卫星:《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三十年之回顾、反思与前瞻》,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笔者认为环境利益可分为人身型、精神享受型与生态利益。
1.人身型。人身型环境权利主要嫁接于生命权、健康权之上,是较传统的生命权、健康权更高层级的保护形式。此类环境利益生成于生命权、健康权之中,但是已经不再遵循损害环境利益进而侵犯生命权、健康权直接的因果律。例如“顾某等29人诉江苏泰林工程构件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注]参见(2016)苏06民终4657号判决书。,法院就以“大型运输车辆通行所产生的噪声、扬尘等对道路周边居民正常生活造成一定影响”为由支持了顾某环境利益补偿的请求。本案中,环境利益的减少,并没有给生命或者健康带来直接的损失,或者说这种损失仍旧处于可以容忍的范围内,但是法院仍旧支持了补偿请求。此时,环境利益具有相当的经济属性,属于一种可交易的范围,但是生命权、健康权往往不具备可交易性。环境权具有独特的内涵与品格,应当从生存权中独立出来。[注]吴卫星:《公法视角的环境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不仅仅依附于传统权利之上,可以成为独立的权利。但是这类环境利益的损害,最终结果会有损生命、健康,所以笔者将其归为人身型环境利益。应当说,环境权利置于传统的基本权利之前,可以起着预防性保护的作用。诸如清洁水源、清新空气、采光、通风都是此类环境利益。
2.精神享受型。此种类型的环境利益是与人格权相关,但是此类环境利益受到法律保护更直观地体现为新型权利。例如视觉卫生权,在“黄某等诉无锡市锦江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无锡城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排除妨碍纠纷”案[注](2007)新民一初字第0695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眺望权、视觉卫生权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权利,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基于容忍义务等因素的考量,判决被告支付一定的补偿金。损害此类环境利益并不会直接影响生命、健康,更多地指向精神层面。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的精神损害的适用范围为9种人格权的损害,并不包含环境权利,但是实质上污水的恶臭、光污染带来的精神损害是巨大的。《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了环境污染纠纷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了环境侵权中受害者有“初步证明责任”,但是在污染物、干扰物并无国家标准的情况下,举证自己的精神上的损害是极为困难的。因此,这种精神享受型环境利益的保障是需要引入比例原则,以损害程度而定而非仅依据容忍限度。当然精神损害造成的损失,可能间接地影响生命、健康,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将这种损害做扩大化的解释。由此种环境利益生成的环境权利包括达滨、眺望、精神安宁等利益。这些环境利益大多可以进行经济衡量,具有经济属性。值得一提的是当有些人身型环境利益的范围扩大到一定范围,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神享受,例如采光、居住安宁的利益保护范围扩大到从生存、生活需求转变精神追求时,这些权利背后的利益便可能成为精神享受型利益。因此,在判断时仍旧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分析。
3.生态利益型。《宪法》之中规定“生态文明”,《民法总则》中规定的绿色原则,第9条明确规定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条款。但是生态利益的维护依靠的是国家制定法律义务,至于此种义务对应到个人是能够成为反射利益,抑或是公法权利是有待论证的问题。所有的对共同利益的保护必然保护了无数的个人利益,而不必创设主观权利。只有当个人意志对利益的存在范围的决定性被承认时,利益才转化为主观权利。[注]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公法权利的形成有三个层次:(1)确认原告主张系争处分违法所引据之法令规定——原告原则上须具体处分违反何等法令。(2)解释系争规定是否属于“保护规范”——该法规的规范目的,除保护公共利益外,是否兼及保护特定范围或可得特定范围之个人的利益。(3)判断原告是否属于系争法规的保护对象——系争规定除须具有保护规范之性质外,原告尚须为该保护规范所及。一般而言这种权利,原则上应取决于立法决定,除非属于人民生存“最低限度保障”,否则应委诸于立法者的政治决定及形成自由以决之,仅于一定范围内始存有公法上权利。[注]李建良:《行政法:第十二讲—公法上权利的概念、理由与运用》,载《月旦法学教室》2011年第1期。因此,生态利益能否上升为环境权利更多地需要立法者,而非司法者考量。生态利益一般可以通过程序性权利进行保护。究其原因是此类利益对应的权利多为社会权(在社会权利层面,环境权也是渐进发展的,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规定,社会权利的实现必须承担一种“逐渐实现”的义务),更多地指向客观秩序价值层面,其主观权利化需要立法者明确,司法可诉性较弱。因此,此类更多地是以公益诉讼的形式出现,但是当生态利益与个人利益重合时,生态利益可以适用私人司法救济的途径,例如《水法》第31条、第76条,《草原法》第6条,《水土保持法》第58条,《矿产资源法》第32条都属于生态利益的权利化。《民法典分则》(草案)侵权责任中也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纳入其中即是生态利益逐渐权利化的最佳佐证。
(二)环境利益的权利化次序
无论在司法对环境权利进行个案的保护,还是在立法上强调环境权利的普世性价值都必须在各种利益中进行衡量,即环境利益与所有利益一样,具有层次性。渐进地将环境利益权利化保护,必须明确哪些利益应当优先得到法律保护,哪些环境利益需要通过时代的发展,进而在一定的社会条件满足时,并且等待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以及对环境利益认可后方能予以保护。在此对比环境利益并由于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必须在各种利益之中作出选择。这种对比更多是立法机关将环境利益权利化时的渐进趋势,即在立法上,从重要性程度差异发掘环境利益权利化的进路。
首先,在人身型环境利益之间,需要考量环境利益对生命、健康等基础权利可能造成侵害的紧迫性。例如环境污染造成的对环境利益的侵犯必然优先于采光成为权利。在环境污染之中,关于重金属污染的危险程度显然高于扬尘污染。因此,前者比后者更加优先地成为权利。
其次,在人身型环境利益与精神享受型环境利益之间,人身型环境利益由于指向的是生命、健康,因而在价值层面上具有优先性。因此,基于生命、健康而产生的环境利益比景观利益、眺望利益在立法层面,更具有成为权利的潜质。在同一种环境利益之中,这种享受型、发展型的利益在价值评价上也是要低于生存利益的,例如享受型的采光在权利化的紧迫性方面肯定不如可能基于健康需要的采光。因此,保护的次序上,环境标准的制定永远是自下而上的,从宽至严,从粗到细的,从危险系数高的污染物到相对较低的污染物。
最后,基于生态利益而产生的权利更多地通过政策层面的诱导产生,生态利益作为公共利益,多以义务的形式存在。因此,这种利益多是反射利益。预想进入权利体系,更多地需要借助公法权利的方式,或者当公私利益一致时,通过私人救济完成公共规制。同时生态利益与其他类型的环境利益具有叠加效应。相比于个人利益,生态利益作为公共利益处于更高的位阶。因此,目前生态利益在制度层面,其权利化具有一定优先性。
在对利益进行衡量之时,环境利益不仅具有经济价值、人文价值,同时也具有制度价值,因此在衡量之时也需要综合考量,环境利益权利化推进过程中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不同时代的人民对环境利益的诉求亦不相同,不同时期对于环境利益的权利化需要考虑不同的因素。
四、渐进主义在环境利益保护强度上的运用
环境利益不同于环境消费利益,后者是人在消费(占有、使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价值,例如喝水解渴、开采矿产等系列行为,更多偏向于财产权的属性,前者作为法律需要维护的利益是通过从负环境利益到环境利益,例如清洁的水源、空气等环境的维持,即环境利益只有当被损害时才能显现出来。[注]徐祥民、朱雯:《环境利益的本质特征》,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6期。因此,从环境侵权的角度入手去探索环境利益的实现方式是极为有必要的。
(一)环境利益保护的强度:基于环境侵权案件的视角
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中明确指出了环境侵权案件不以国家制定的标准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也指出不能以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免责。在环境质量标准能否用于认定侵权责任的问题的答案上已经较为清晰了。但是在判断上无论是在学界与实务界都存在争议,那么为何仍旧存在争议呢?其中,肯定说认为污染行为只要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就构成侵权。[注]施志源:《环境标准的法律属性与制度构成》,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否定说认为即使符合强制性标准,依旧不能免除侵权责任。[注]谭启平:《符合强制性标准与侵权责任承担的关系》,载《中国法学》2017 年第4期。其实环境标准是容忍限度极为重要的参照。权利的边界与他人容忍义务的扩张与限缩成反向位移。而国家制定的环境标准对于司法机关在确定容忍限度时具有天然的诱惑力。《物权法》第90条之中对于邻地的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的排放同样是参考国家规定的。作为一种可明确参照的对象,一旦违反环境质量标准,在环境侵权上必然具有相当的过错。在许多情况下,容忍限度与环境标准之间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尤其是在对安宁权的侵犯上,一般适用国家标准。例如“陈永荣等诉南宁振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噪音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就以噪声夜间值高于《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的限值,构成环境噪声污染,判决排除妨碍。而在未超过噪声标准的情况下,法院更乐意双方达成补偿协议,而非通过排除妨碍、停止侵权等,[注]参见海中法环民终字第1号判决书。或者直接判决原告败诉。
其实,世界各国在环境侵权容忍限度的范围内,大抵如此。在日本,公法上的标准并不是环境侵权必须考虑的要素,仅仅是对企业和个人在污染排放上最低限度的规制,但是它的行为本身违背了公法的标准,那么自然具有违法性。在英国,在满足排除妨碍的要件之后,是否能够适用排除妨碍的诉请,需要在利益上进行衡平。由于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措施需要停止生产,需要付出极大的社会代价,因而在19世纪之前,法院不支持排除妨碍的请求,而仅支持精确损害赔偿的请求。[注]See Joel Franklin Brenner, Nuisance Law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3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03 (1974)p405-406.由于排除妨碍能够更好救济环境利益,排除妨碍这种救济模式在19世纪之后被更加广泛地应用。这种二阶段的利益保护机制,同样是从“利益平衡论”探索环境利益的法律保护机制。在德国,同样存在这种二阶段的利益衡平机制,《德国民法典》第902条第2款规定了土地使用人的容忍义务,在容忍义务之下,除非可以通过经济上的方式加以阻止,否则不适用妨碍排除的救济。[注]马强伟:《环境污染侵权中预防性请求权的解释与适用》,载《法学》2018年第3期。《德国联邦污染防治法》第14条在规定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可以采取金钱补偿的方式补救环境损害。具体言之,德国的不可量物侵害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是为维护共同发展所必要的绝对容忍义务,适用于侵害非属重大之情形;其二为了衡量补偿请求权之权利救济,适用于虽为重大侵害,但本于利益衡量而要求受害人加以忍受,但需以衡量补偿作为代价;其三为排除侵害请求权,适用于损害重大,而侵害活动又不具有补偿请求权成立之要件,以使其回复物权请求权。[注]邱聪智:《公害法原理》,三民书局1987年版,第33页。
综上,环境侵权案件中,在容忍限度内,一般可以以金钱补偿的方式救济无须停止侵害,或者不受法律保护。当超过容忍限度时,环境利益则一般以权利的形式进行绝对的保护,不仅可以请求赔偿也可以要求停止侵害。因此,对环境利益的保护以容忍限度为界,可以分为三个档次:1.不受法律保护的环境利益。2.受到法律保护,但只承担经济赔偿仍旧可以继续公害行为。3.受到全面保护,可以请求排除妨碍、停止侵权等。环境权的研究是一方面可以通过让容忍限度不断限缩,从而推动环境权利边界的移动,扩大环境利益的保护范围。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升环境利益的保护强度来实现。
(二)环境权利保护强度的渐进性增加
德国法用来区分利益的保护类型大致可以分为绝对权利、一般人格权利和利益。对于绝对权利一般不进行利益衡量,但是当绝对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也适用利益衡量进行取舍。一般人格权利作为框架性的权利,通过积极确定违法性的处理方法,同时也适用利益衡量。[注]蔡琳:《论 “利益”的解析与 “衡量”的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 年第1期。环境权利是通过环境权利抑制他人自由,是通过权利抑制权利的方式保护环境。将某些一般人格权利逐步提升为绝对权利,适用全面保护,适用无过错责任。有些仅未受法律保护的环境利益逐渐提升为一般人格权,与利益冲突时适用全面保护,在与权利冲突时,适用过错责任或者可以以经济补偿的形态替代停止侵害。
随着全社会在环境保护方面达成共识,环境利益的保护强度也随之增加。环境权利的保护强度由低层次向高层次保护递增,重要的环境利益可以优先适用绝对化的保护,生态利益可以优先作为保护对象,适用绝对权利保护,例如在生态保护区设置更为严苛的保护标准,通过公益诉讼或是私人诉讼,一旦触及到生态利益即可以通过停止侵权、排除妨碍的方式杜绝环境损害,并恢复原状。人身型环境权具有预防性的功能,在危险程度较高时,例如核电厂、垃圾场的设置,虽未超过容忍限度,但是可能造成相当危害威胁的情况下,即使在科学上没有完全确定某些因果联系,也应当采取预防性措施。在美国,基于这种“合理担心”的标准,即使未遭受实质损害仍旧具有原告资格。这种预防性原则的使用有助于防止那些必须证明因果相连的难题,同时避免民事诉讼进入法院时,简单地采用证明责任倒置的可以察觉的不公平或者武断。[注][英]蒂姆·海沃德:《宪法环境权》,周尚君、杨天江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在国内无烟诉讼第一案中,法院认为“当权利发生冲突时,需要考虑权利在法律价值体系中的位阶,旅客身体健康不受侵犯的权利高于吸烟者的吸烟权益。司法裁判需要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限制来实现社会利益的平衡”“设置吸烟区必然导致车内环境降低”,遂判令取消列车吸烟区标识及烟具。在精神享受型的环境权中,在未超过容忍限度却对生活产生影响时,可以用经济补偿的方式予以保护,采用一般人格权的形式保护。同一级别的利益之间发生冲突之时,给环境利益加权,提升其重要性。环境权利作为一种公民权利,不断地有学者批判其不具有独立性,是依托于人格权和财产权的。[注]徐祥民、张锋:《质疑公民环境权》,载《法学》2004年第2期。事实上,对于环境利益的法律保护不一定要独立地称之为环境权,正如对食品安全的保护也不需要创制食品权。即使环境权在名称上不用单独列出,通过财产、人格权利的形式保护环境利益也是可以的。重要的是如何扩大环境利益的保护范围与强度。
以上一方面需要《侵权责任法》第2条作扩大解释,另一方面需要在环境侵权的案件之中引入比例原则,而非仅仅是依据容忍限度或是利益的价值比较,并且在立法上完善环境权利的种类。在“吴某等50名居民与规划局纠纷案”中[注]参见(2012)通中行终字第0015号判决书。,法院认为“虽然规划许可对通风、采光、交通、环境利益等造成侵害,但是城市开发与其对通风采光等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矛盾,建筑物之间已满足了建筑设计规范及相关规划技术规定”,遂驳回了诉请。在此很明显法院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做了比较。但是本案中,法院是承认原告的利益受到侵害的,但是仍不作出补偿决定的重要原因是原告与实际侵权者之间达成过补偿协议。那么倘若未达成过补偿协议,规划局是否要负责呢?我们认为虽然在容忍限度内,基于比例原则侵犯的程度过大时,行政机关仍要承担补偿责任。这种从损害的程度考虑补偿的方式,尤其要运用于无数据可参照的精神享受型环境利益的保护之中。
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利益的保护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在1973年的“宾西法尼亚州政府诉国家盖茨堡战场瞭望塔公司案”中,法院认为环境权条款中“清洁空气”“清洁水”等用语过于模糊,根本无法作司法论断。[注]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但是,在1979年Payne v.Kassab案中,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通过将公共信托与环境权结合,间接地承认了环境权的存在。美国最高法院也开始承认审美、环境保护和休闲意义上的损害的原告资格。[注]397 U.S 123(1951)转引自[美] 理查德·J·皮尔斯:《行政法》(第五版),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097页。在1999年“美国蒙大拿环境信息中心诉环境质量局”案中,法院承认了健康、清洁环境权。[注]胡静:《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可诉性和具体化》,载《中国法学》2017 年第5期。可见环境利益是否被保护不在于是否在法律中确立,而在于环境利益在那个时代是否重要。环境权理论的意义在于如何提升环境利益的重要价值,以实现在各种权利冲突时,环境利益具有优先性,使国家承担更多的环境给付义务,并逐步达到环境权中绝对保护的目标。因此,环境权的研究不应当执着于概念的桎梏,而应当注重于如何以权利的方式提升环境利益的保护。
五、小结
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有代表就环境保护法中增写“公民环境权”提出议案。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也提及“赋予公民环境权”。学界对环境权入宪也在积极主张,但是在法律文本之中却未明确写入“环境权”。自上而下,从应然的角度分析环境权,并在各个部门法之中进行规定显然是不具有可操作性。即使规定于宪法之中,也无法达到环境权利绝对保护的目标,正如朱谦教授所言环境权即使进入宪法之中,也不应当视为一种实体的基本权利,而应该是揭示环境保护的政策、理念的宣示性条款。[注]朱谦:《环境权问题:一种新的探讨路径》,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在环境权内涵与外延并不明晰的情况下,立法者审慎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与其在理论上强调环境权入宪的重要性,不如使立法者逐渐意识到环境权入宪的可行性,这一过程显然是要通过大量案例与单个环境利益权利化的积累才能实现的。
在环境权理论下渐进地对环境利益进行保护。笔者认为在部门法之中不宜以“环境权利”的形式出现,而应当用单种环境利益权利化,例如采光权、安宁权、眺望权等进入民法典或是环境保护法。在修正环境权的保护范围的同时,强化已有的环境权利,最终使得环境权利得到绝对化的保护。当然并非所有的利益都应当绝对化的保护,通过修正的方式使得环境利益逐个权利化,保护程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趋于绝对化。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给立法者确立环境权的信心,最终将“环境权”写入宪法,这才是环境权渐进入法的路径。这种路径也是符合我国的法律制定的基本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