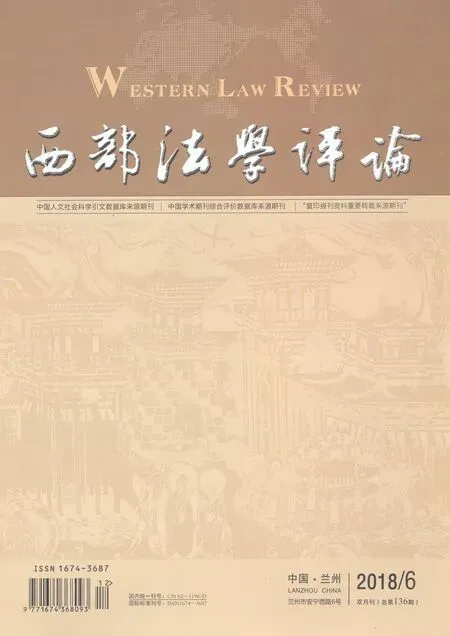论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平衡
——由《基本法》的双重属性展开
谢 宇
一、《基本法》: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关系的核心法律依据
2014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中央依法履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的全面管治权和宪制责任,有效管治香港特别行政区”,创造性地提出了“全面管治权”这一概念。党的十九大在阐述“一国两制”基本方略时进一步指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1月21日。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关系的论述,是处理港澳问题的基本思路,这意味着我们在实施“一国两制”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强调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任何片面强调其中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将与“一国两制“的基本方略相违背。然而,如何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实现两种权力的平衡仍是亟待解决的宪法问题。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统称《基本法》)规定了中央与特区的关系,既明确了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又赋予了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一国两制”法律化的集中体现,是处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关系的核心法律依据。如何理解并对待《基本法》,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近年来,人们在对待《基本法》时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以部分香港人士以及香港法院为代表,主张将《基本法》作为特区的“宪法”,混淆我国《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将《基本法》作为中央与特区的“社会契约”,淡化中央全面管治权;另一种倾向是过度强调《基本法》只是全国人大制定的一部基本法律,忽略了作为不易于被修改的特殊授权法性质,引发人们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担忧。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如果不得到及时纠正,将不利于正确理解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平衡关系,最终有损“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基于此,本文将分别对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和危害进行阐述,并通过阐明《基本法》的双重属性来理解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平衡关系。
二、对待《基本法》的两种错误倾向及负面影响
《基本法》被誉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但也正是因为这部法律的“创造性”,使其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和现成的法律可以参考和借鉴,加之内地与特区社会制度不同,因而早在1985年《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开启之初,人们围绕着《基本法》就已经产生了诸多分歧。[注]肖蔚云:《一部艰辛而有创造性的杰作——回顾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诞生》,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8期。《基本法》付诸实施以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于保持特区繁荣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对《基本法》的错误认识也时有发生。其中,对《基本法》属性的两种错误认识将对我们理解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一)将《基本法》作为特区宪法的倾向及负面影响
1.将《基本法》视为特区宪法的倾向
将《基本法》作为特区宪法的声音由来已久,这种倾向在香港特区以及西方学界尤为严重。早在中英谈判之初,香港就曾有人主张制定香港自己的宪法甚至赋予香港立法机关自主的修宪权,[注]The Legal System,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14 Hong Kong L.J. 137 (1984).《香港基本法》的构想提出以后,许多香港人士将《香港基本法》视为特区的宪法进行探讨,[注]See Yash Ghai, The Pas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s Constitution, 1991 China Q. 794 (1991);Jack Chan, Hong Kong's Role after 1997, 12 Loy. L.A.Int'l & Comp. L.J. 54 (1989); Benny Y. T. Tai, Basic Law, Basic Politics: The Constitutional Game of Hong Kong, 37 Hong Kong L.J. 503(2007).这种倾向也得到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支持,[注]John M. Rogers, Anticipating Hong Kong's Constitution from a U.S. Legal Perspective, 30 Vand. J. Transnat'l L. 449 (1997);Harriet Samuels,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in Hong Kong, 1993 Asia-Pac. Const. Y.B. 22 (1993).除此之外,还有人将《基本法》称为“小宪法”与我国《宪法》进行区分。[注]例如,香港特区第一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也曾经提到,“我们现在拥有一部成文小宪法——基本法”。梁爱诗:《飞鸿踏雪——香港基本法实践20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页。香港回归以来,这种将《基本法》视为特区宪法的倾向长期在香港得以延续。如果说学者将《基本法》作为宪法只是一种学术讨论的误区,那么,包括香港终审法院在内的香港法院则将这种错误的倾向引入了司法实践之中,从香港法院公布的判决书来看,香港法院自回归以来,多次在司法审判中将《基本法》视为特区宪法,试图构建起一套以《基本法》为根本大法的特区法律体系。仅以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书来看,早在1998年“THANG THIEU QUYEN及另六人对入境事务处处长及另一人案”中,香港终审法院就使用了“本地宪法《基本法》”一词。[注]THANG THIEU QUYEN 及另六人对入境事务处处长及另一人,FACV 2/1998,第110段。随后,在1999年“陈锦雅及另外80人对入境事务处处长案”中,香港终审法院在适用《基本法》时使用了“本港的宪法《基本法》”。[注]陈锦雅及另外80人对入境事务处处长 ,FACV 13,第6,28,33段。在此之后,香港终审法院长期在判决书中将《基本法》称为“本地宪法”、“本港的宪法”、“特区的宪法”。[注]吴嘉玲、吴丹丹诉入境事务处处长,FACV 14/1998,第10段。如果说仅仅在判决书中将《基本法》作为特区宪法可能是一种表述的便利,那么,依据《基本法》行使违反基本法审查权(香港人士称之为“违宪审查权”[注]陈弘毅:《香港终审法院关于〈基本法〉的司法判例评析》,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则显现出了香港终审法院的真实目的,即在特区构建起一套以《基本法》为根本大法的法律规范体系,赋予《基本法》在特区的最高法律地位。在陈锦雅案、吴嘉玲案、吴恭劭案[注]香港特别行政区诉吴恭劭及另一人,FACC 4/1999。等多个判决中,香港终审法院均将《基本法》作为香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典,多次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法例因违反《基本法》而“违宪”,进而宣告其中“违宪”的部分内容无效。香港终审法院甚至在吴嘉玲案中还指出,香港法院有权依据《基本法》裁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违反《基本法》的行为无效。[注]同前引[10]。
那么,香港法院基于何种理由将《基本法》视为特区宪法呢?通过对香港终审法院判决书进行梳理,可以看出,在香港终审法院将《基本法》视为“本港宪法”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1)从形式上看,《基本法》的效力和修改程序特殊。香港终审法院认为与一般的香港法例相比,《基本法》具有更高的效力,同时在修改程序上严于一般法律,具体体现在:第一,《基本法》的效力高于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立法会制定的任何法律。例如,在吴嘉玲案中,香港终审法院在考虑如何“解释基本法这样的宪法时”指出,“任何抵触《基本法》的法律均属无效并须作废”。第二,《基本法》的修改程序严于其他法律。例如,同样在吴嘉玲案中,终审法院指出,“《基本法》是为贯彻独一无二的‘一国两制’原则而制定的宪法性文件,具有不可轻易修改的地位。”[注]同前引[10],第 64,73段。(2)从实质上看,《基本法》所规定的内容特殊,其在内容上规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具备“宪法”实质上的特征,具体体现在:第一,《基本法》是贯彻“一国两制”、建立特别行政区的重要法律依据,是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例如,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及另四人案”中,香港终审法院指出,“《基本法》首个明显目标,是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及另四人,FACV 22/2005,第42段。此外,在吴嘉玲案中,香港终审法院也指出,“制定《基本法》的目的是按照《联合声明》所阐述及具体说明的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成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并实行高度自治。”[注]同前引[10],第75段。在刘港榕案中,香港终审法院指出,“《基本法》是按照‘一国两制’原则订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宪法。”[注]刘港榕及另外16人对入境事务处处长,FACV 10/1999,第157段。第二,《基本法》的主要内容是规范权力、保障基本权利与自由。香港终审法院在“吴嘉玲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诉吴恭劭及另一人案”中分别指出,“与其他宪法一样,《基本法》既分配权力,也界定权限,并且订明各项基本权利及自由”,[注]同前引[10],第64段。“《基本法》载有宪法性条文,保障香港这个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多项自由。”[注]同前引[12],第1段。香港终审法院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诉林光伟及另一人案”中指出,“《基本法》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提供了一部包含各项已确立权利和自由的现代宪法。”[注]香港特别行政区诉林光伟及另一人,FACC 4/2005。香港终审法院的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这也导致部分内地人士也一度将《基本法》称为特区的小宪法,[注]刘南平:《借鉴美国州宪法解决香港基本法的两大难题之探讨》,载《法学评论》1987年第4期。然而,这种将《基本法》视为特区宪法的倾向将在理论和实践中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
2.将《基本法》视为特区宪法的负面影响
将《基本法》视为特区宪法的观念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其本质是片面强调《基本法》而忽视我国《宪法》作为特区宪制基础的地位,片面强调特区高度自治权而忽视中央全面管治权,这种错误的认识如果不得到及时纠正,将对“一国两制”的正确实施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1)片面强调《基本法》作为特区的宪制基础,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我国《宪法》”)的宪制基础地位。我国《宪法》不仅与《基本法》共同构成了特区的宪制基础,而且我国《宪法》也是《基本法》的制定依据和宪制基础。我国《宪法》第31条为特区的设立和《基本法》制定提供了直接的宪法依据,《基本法》序言也开宗明义地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意图排除我国《宪法》特别是《宪法》第31条以外条款在特区适用的观点由来已久,早在《基本法》起草之初就有人提出我国《宪法》不应当适用于特区,但这种观点随即遭到《基本法》起草者的批评与否定。[注]肖蔚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将《基本法》作为特区宪法,而淡化甚至忽略我国《宪法》作为特区宪制基础的地位,其本质上仍然是延续了“我国《宪法》不适用于特区”的观点,目的在于将本应当适用于特区的宪法条款也一并排除在特区法律体系之外,实质上是将这些宪法条款中规定的中央全面管治权排除在特区之外,进而弱化中央全面管治权。(2)淡化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试图构建一种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进而强化特区高度自治权,而弱化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正当性。在单一制国家中,中央以法律授予地方权力,而联邦制国家一般在宪法中划分中央和地方权力,这是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注]王磊:《宪法的司法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通过《基本法》而非我国《宪法》授予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符合单一制国家的基本特征。然而,如果将《基本法》视为宪法,将淡化我国单一制特征,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混淆为联邦与州的关系。一旦这种错误的理念深入人心,这就意味着《基本法》会被视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分权法而非中央向特区的授权法,使人错误地认为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由宪法创制而非中央授予,那么,“一国两制”白皮书中认为高度自治权源于中央全面管治权并受中央监督的理念将丧失理论基础。
(二)忽视《基本法》特殊属性的倾向及负面影响
1.忽视《基本法》特殊属性的倾向
时至今日,为了正确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方略,中央对特区高度自治权始终秉承了尊重与维护的态度,在行使全面管治权时十分审慎,例如,至今从未行使过《基本法》修改权,在历次行使《基本法》解释权时也较为克制,[注]王磊、谢宇:《论〈香港基本法〉解释实践队人大释宪的启示》,载《行政法论丛》第19卷。这种审慎的态度为特区高度自治权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然而,随着“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实践的不断推进,在实践和理论中出现了另一种错误倾向,即仅将《基本法》视为全国人大的一般基本法律,而忽视《基本法》的特性,这种倾向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是不必要地担忧中央会滥用《基本法》的修改权或解释权侵犯特区高度自治权;[注]See Brian Z. Tamanaha, Post-1997 Hong Kong: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eaning of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20 Cal. W. Int'l L.J. (1989). Guiguo Wang; See Priscilla M. F. Leu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ory into Practice, 7 Pac. Rim. L. & Pol'y J. (1998).二是当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行使出现张力时,主张通过修改《基本法》等方式解决,而忽视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的稳定性。[注]例如,由于2000年香港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判决,使得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所生的中国公民也依照基本法享有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导致后来发生“双非孕妇风波”,在“双非孕妇风波”发生后,许多人士呼吁全国人大修改基本法。佳日思等:《居港权引发的宪法争议》,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曹旭东:《博弈、挣脱与民意:从“双非”风波回望“庄丰源案”》,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6期。
之所以有这种声音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仅认识到了《基本法》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一般特性,而忽视了《基本法》不同于其他基本法律的特性。根据《立法法》第7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法律体系,两部《基本法》确实均属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然而,有些人仅仅片面地强调《基本法》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性质,而忽视了《基本法》不同于其他基本法律的属性,即《基本法》是不易于被修改的特殊授权法,因此,这些人士或者不必要地担忧中央会滥用《基本法》修改权或解释权,或者在不必要的时候主张过度行使《基本法》修改权或解释权。
2.忽视《基本法》特殊属性的负面影响
相较于将《基本法》视为宪法,忽视《基本法》特殊属性的危害更加隐蔽,因为这种倾向表面上看更有利于维护“一国”和中央全面管治权,但事实上,这种忽视《基本法》的特殊属性,片面刻画出一种全面管治权异常强大而高度自治权异常脆弱的景象,将会引发诸多危害:(1)将引发对全面管治权侵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担忧,损害“一国两制”的核心内涵。过度强调《基本法》只是全国人大制定的一部基本法律,无视《基本法》的稳定性,忽略《基本法》在内容上是为了贯彻“一国两制”和我国《宪法》第31条专门制定的法律,其修改在内容上受到“一国两制”的限制并在程序上也有更为严格的限制,将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人们对于高度自治权的担忧。在许多人看来,《基本法》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核心法律保障,[注]See Anson Chan, Hong Kong's Basic Law: A Contract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1996 Inter Alia 31 (1996).如果《基本法》处于一种易于被修改的地位,那么,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将无法得以保障。事实上,为了打消人们的这种顾虑,中央围绕着《基本法》做了大量工作,一是通过合宪性审查,在通过两部《基本法》的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确认了两部《基本法》符合宪法,不会因为有违宪之虞而影响其稳定性;二是在起草《基本法》时,分别通过《香港基本法》第159条和《澳门基本法》第144条对两部《基本法》的修改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不仅设定了更为严格的修改程序,而且规定《基本法》的修改不得与对香港、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然而,片面地强调《基本法》仅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而忽视《基本法》不易于被修改的特性将违背设计《基本法》时的初衷,将引发对中央全面管治权侵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担忧。这种引发人们对高度自治权担忧的做法目前并未引起太多重视,但我们应当认识到,“一国两制”的独特智慧之处就在于通过“一国”与“两制”的平衡,[注]陈弘毅:《〈基本法〉与“一国两制”实施的回顾与反思》,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4卷。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平衡,以实现“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即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又要保持特区长期繁荣稳定,[注]饶戈平:《“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的启示》,载《中国人大》2017年第13期。这也是党的十九大强调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统一的深意。如果打破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平衡,忽视特区高度自治权,以致引发特区内部的广泛担忧,那么,“一国两制”这一基本方略必然会受到冲击,特区的繁荣稳定也将难以得到保障,最终将损害的还是中央的全面管治权。(2)导致法律体系内部出现矛盾。片面将《基本法》与全国人大制定的其他基本法律等同起来,会导致在《基本法》修改问题上出现法律体系内部的矛盾。以《香港基本法》为例,《香港基本法》第159条对该法的修改进行了特殊的规定,[注]《香港基本法》第159条规定,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法的修改提案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修改议案,须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分之二多数、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同意后,交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本法的修改议案在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程前,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意见。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实际上是对该法的修改加以了实体和程序上的限制,目的是赋予修改该法更高的门槛,以保障“一国两制”的稳定性。然而,对《基本法》的修改包括两种,一种是直接修改,即直接通过修法程序对《香港基本法》的文本进行修改,另一种是间接修改,即虽然不直接对《香港基本法》文本进行修改,但是利用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在全国人大新制定的基本法律中做出与《香港基本法》不一致的规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间接修改。[注]参见黄明涛:《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自足性——对基本法第11条第1款的一种解读》,载《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如果片面强调《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而忽视其与其他基本法律的不同,意味着全国人大可以摆脱《香港基本法》第159条的限制,通过制定新的基本法律的方式对《香港基本法》进行修改,其结果显然违背了《香港基本法》第159条的初衷,会导致法律体系内部出现矛盾。
三、正确对待《基本法》的双重属性
如何对待《基本法》的属性关系到如何实现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平衡,并最终关系到“一国两制”基本方略的实施。上文阐述了对待《基本法》的两种错误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当下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如果不加以纠正,将不利于正确理解中央全面管治权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平衡,并最终危及“一国两制”的基本方略。要有效维持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平衡,必须正确对待《基本法》的双重属性,即《基本法》既是宪法之下的基本法律,又是不易于被修改的特殊授权法:
(一)《基本法》是宪法之下的基本法律
将《基本法》置于我国整个法治体系之中进行考察,《基本法》的第一重属性将得以彰显,即《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位于宪法之下的基本法律,而非“特区的宪法”或“小宪法”,这一属性决定了全面管治权的内容及其与高度自治权的“原生—派生”关系。我国《宪法》第62条和《立法法》第7条规定,在我国法治体系中,《基本法》无论从内容还是程序上均属于我国《宪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这一属性包括以下几层内涵:
1.全面管治权的内容根本上是源自我国《宪法》规定,而非局限于《基本法》的规定。虽然我国《宪法》中部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的条款不在特区实施,但我国《宪法》作为主权的最高体现和法律表达,[注]韩大元:《论〈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过程中的左右》,载《现代法学》2017年第9期。其整体上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部领土,[注]肖蔚云: 《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94页。且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其同样也是特区的最高宪制基础。我国《宪法》中关于国家主权、国防、外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等规定均适用于特区,[注]参见肖蔚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这些规定均是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的直接法律依据。由于《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而非宪法,其效力高于法规、规章,但低于我国《宪法》,其无法替代我国《宪法》作为特区最高宪制基础的地位,《基本法》中关于全面管治权的规定实际上是将我国《宪法》中对相关权力的规定进行了具体化。因此,认为中央全面管治权仅限于《基本法》中的规定就过于狭隘了,在理解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来源和范围时必须结合我国《宪法》中的相关规定。认识到中央全面管治权源于我国《宪法》而非局限于《基本法》,对于处理“一国两制”中的实践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在围绕中央全面管治权的争议中,争议最大的当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注]参见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以《香港基本法》为例,由于《香港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香港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路径,但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否主动释法并未进行明确规定,以致在刘港榕案中,资深大律师张健利提出依据《基本法》第158条,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主动解释《基本法》,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释法不具备法律效力。在该案中,张健利大律师将《基本法》第158条作为中央行使释法权的唯一法律依据,故而推导出了错误的结论,但如果能够认识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权的最终法律依据是我国《宪法》第67条,该条不加任何限制地、概括性地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包括《基本法》在内所有法律的职权,就能够充分理解主动解释《基本法》的权力是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应有之义。
2.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是“原生-派生”关系,而非分权关系。正如上文所述,虽然《基本法》也详细规定了中央全面管治权,但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是源自我国《宪法》的规定,是一国主权的具体表现[注]王禹:《“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载《港澳研究》2016年第2期;另见“一国两制”白皮书起草者之一强世功教授的论述,强世功:《香港白皮书——被误读的”全面管治权“》,载BBC中文网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4/06/140613_qiangshigong_hk_white_paper,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4月10日。。特区高度自治权不具备主权属性,[注]蒋朝阳:《国家管治权及其在特别行政区的实现》,载《港澳研究》2017年第2期。其本质上属于中央全面管治权的一部分,只是基于“一国两制”的基本方略,通过《基本法》派生出高度自治权,并将高度自治权授予特区行使。此外,作为高度自治权法律依据的《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一部基本法律,不是宪法,通过《基本法》将全面管治权转化为高度自治权的行为,不是联邦制下通过宪法划分中央和地方权力的行为。特区高度自治权与中央全面管治权的这种关系蕴含着以下几层含义:一是高度自治权并非特区固有的权力,特区在行使高度自治权时不得违背授权的目的,特别是不得侵犯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既然高度自治权派生于全面管治权,是中央通过《基本法》授予特区行使的,那么,特区在行使高度自治权时就应当服从授权的目的,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因此,任何行使高度自治权的主体,包括特首、立法会议员、法官等都不得从事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活动。二是中央对特区高度自治权享有监督权。高度自治权派生于全面管治权,是中央通过《基本法》授予特区行使的权力,为了确保特区行使高度自治权符合授权目的,没有偏离“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中央有权对特区行使高度自治权的行为进行监督。就以往的实践来看,中央较为常用的监督方式即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释法,例如,在2017年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中,由于多名立法会议员在宣誓时存在辱华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对《香港基本法》中的宣誓条款进行了解释,为取消辱华议员的资格提供了法律依据,有效遏制了特区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损害国家主权的现象。
(二)不易于被修改的特殊授权法
虽然《基本法》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一部基本法律,不是“特区宪法”或“小宪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基本法》与其他基本法律相等同,还应当认识到《基本法》是一部不易于被修改的特殊授权法,其授予了特区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治权,还对中央在特区直接行使的管治权以及中央对高度自治权的监督权进行了规范,并为特区高度自治权的长期、稳定行使提供了保障。
1.《基本法》具有特殊的授权法属性,授予了特区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治权,还对中央在特区直接行使的管治权以及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监督进行了规范。在“一国一制” 之下,中央往往也需要赋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但没有必要采取《基本法》这种特殊的形式进行,而一般是采取普通法律进行授权。之所以说《基本法》具有特殊的授权法性质,是因为在“一国两制”之下授予特区高度自治权从本质上不同于“一国一制”下授予地方一般的自治权,这种不同主要在于,授予一般的自治权并不需要在任何地区中止我国根本制度的实施,而授予特区高度自治权,意味着作为我国根本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不适用于特区,特区将“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种对根本制度的变通甚至一度引发了《基本法》是否违宪的争论。[注]叶海波:《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合宪性推定》,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也正是由于特区与我国内地有着这种根本制度的不同,必然要求《基本法》赋予特区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治权,这种高度自治权体现在特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方面,这些高度自治权是服务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政策的特区,其中的许多内容不仅是内地地方国家机关所不能行使,甚至在许多联邦制国家之下的州也难以享受如此广泛的高度自治权。[注]郝铁川:《香港特区享有的是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高度自治权》,载《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同时,为了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效行使,《基本法》还对中央在特区直接行使的管治权以及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监督进行了约束。例如,《香港基本法》第14条第3款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香港基本法》第22条第1款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香港基本法》第158条、159条规定,中央在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和修改时应当征询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2.《基本法》具有不易于被修改的属性,为特区高度自治权的长期、稳定行使提供了保障。《基本法》是中央授予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核心法律依据,《基本法》的稳定性决定了高度自治权的稳定性。尽管“一国两制”已经被作为我国的基本方略,但如果《基本法》可以被频繁地修改,那么高度自治权可能会处于不稳定、不可预期的状态之中,这会引发人们对“一国两制”这一基本方略的担忧。从过往的实践来看,中央一向十分慎重地对待《基本法》,面对若干次围绕《基本法》的争议,中央从未修改过《基本法》,而是通过解释《基本法》的方式解决围绕《基本法》的争议,并且中央在行使解释权时也十分克制。[注]其中最典型的事件是,在2000年庄丰源案中,香港法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释法的内容进行了限缩,曲解了释法的含义,但是许多人士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庄丰源案再次释法,但中央对该问题保持了克制并未再次针对居港权问题进行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实践的情况,参见王磊、谢宇:《论〈香港基本法〉解释实践队人大释宪的启示》,载《行政法论丛》第19卷。不仅如此,《基本法》不易于被修改的属性也有着充分的制度保障,由于两部《基本法》有着相同的制度保障,为了论述方便,下文仅以《香港基本法》为例阐明《基本法》不易于被修改的属性:一是《基本法》的修改主体有着特殊的限制。根据《立法法》第7条,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但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基本法》第159条明确规定“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未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基本法》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的权力,在修改主体上更为严格。二是《基本法》的修改程序有着特殊限制。《基本法》第159条规定,《基本法》修改的提案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香港特区。特区的修改议案,须经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多数、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和行政长官同意后,交由特区出席全国人大的代表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除此之外,该条还规定《基本法》的修改议案在列入全国人人大的议程前,先由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意见。三是《基本法》的修改在内容上有着特殊限制。《基本法》第159条规定,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上述对《基本法》修改限制使《基本法》处于不易于被修改的地位,为高度自治权的稳定和可预期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可以预期,特区高度自治权将贯穿整个“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历程之中。
四、结语
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统一关系到“一国两制”实践能否“不走样、不变形”,《基本法》是“一国两制”集中体现,充分体现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平衡。近年来,“一国两制”的实践取得了诸多成就,这也充分证明了《基本法》的高度政治智慧。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不断推进和《基本法》的不断实施,社会各界对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认识总体上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但是“两制”的磨合同样需要时间,在磨合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矛盾。[注]田飞龙:《香港基本法与国家建构——回归二十年的实践回顾与理论反思》,载《学海》2017年第4期。如果仅仅因为出现一些矛盾就试图扭曲《基本法》的双重属性,片面强调其中的一种属性而忽视另一种属性,会打破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平衡关系,最终会损害“一国两制”伟大实践。要保持“一国两制实践不变样、不走形”,必须正确认识《基本法》的双重属性,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