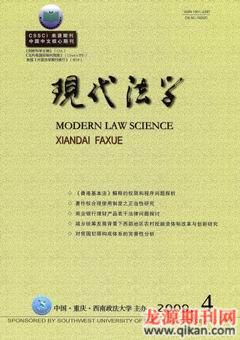《香港基本法》解释的权限和程序问题探析
季金华
摘 要:《香港基本法》是全国的宪法性法律,是香港特区的根本法。为了落实“一国两制”的精神,《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其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香港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授予香港各级法院附条件的《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由于二者的立场、视角、法律传统和利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因而在立法解释模式和司法解释模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碰撞。《香港基本法》在解释主体、权限和程序设定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在实践中也引发了宪法危机,因此,应该针对存在的问题,逐步加以完善。
关键词: 香港基本法;解释;权限;程序
中图分类号:DF29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4.01
一、《香港基本法》解释的权限和程序架构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香港基本法》或《基本法》)解释权限和程序的设计与运行问题是和它的性质和地位密切关联的。学界对香港基本法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注:许崇德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其地位仅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其他的规范性文件。”(见许崇德港澳基本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6)王磊认为,“法律包括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属于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是比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更为重要的法律。”(见王磊论人大释法与香港司法释法的关系——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J]法学,2007,(3):17)因而把《香港基本法》理解成基本法律,而不管基本法的内容是宪法性的内容这一事实,因此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李琦认为现代宪法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有关个人在政治国家中的法律地位、公民权利和义务是其直接和具体的表现,这种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人在政治国家的主体地位;二是关于国家权力的制度设计,包括关于国家权力产生方式的制度安排、对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权力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定等,以期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法律规制;三是关于宪法自身的制度设计,包括宪法的修改、宪法的解释和违宪审查等,旨在保障宪法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实效性,进而对前两方面的制度安排提供保障机制。《香港基本法》对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特区政权的结构形式、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产生办法、基本法的解释和修改权限与程序进行了制度安排,并且同现行宪法一样,规定了基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大,排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修改权,从而在内容方面与现代宪法的内容呈现出对应关系,因而不是宪法的下位法。此外,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不可存在两部宪法,宪法是主权行政的产物,不应该以其他法律为依据,而《香港基本法》是以宪法为依据的,因此,《基本法》也不是宪法,而是《宪法》的特别法。(见李琦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性质:宪法的特别法[J]厦门大学学报,2002,(5):15-23)这种看法忽视了宪法关于国家权力产生和运作基本原则和基本构架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的事实,而这些规定并不符合法理学上关于对特定的人、事项、空间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是特别法的定义,因此这样观点同样值得推敲。在我看来,还是遵从约定俗成的原则,将其称为全国的宪法性法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根本法。)
但我们认为要准确界定《香港基本法》的属性,必须从《香港基本法》的内容、功能、制定和修改权限与程序等问题入手。“从性质上,《基本法》规定的是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等宪法性内容,其立法程序也不同于其他全国性法律的制定程序,而是以类似于制宪的特别方式制定的。因此,《基本法》不是普通的基本法律,而是宪法性法律;也不是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普通的全国性法律,而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根本法典地位的全国性法律。《基本法》的这一性质,决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依据《基本法》进行的司法审查具有违宪审查的性质。”[1]简言之,《香港基本法》是全中国的宪法性法律,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根本法。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和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属于宪法解释的范畴,香港法院在审理普通案件时,对涉及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和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判断,在广义上具有违宪审查的性质。
当然就《基本法》的渊源而言,《基本法》在形式上是依据宪法制定的,其效力源自中国现行《宪法》,而实质上是落实《中英联合声明》的产物,其实质渊源是《中英联合声明》。这一点说明在设计《基本法》的解释权限和程序时,必须适当地考虑到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必须照顾到香港的民众依据司法权威保护基本权利的普通法传统。在中央和香港相互关系的制度安排上,必须坚持“一国”这一根本原则,同时也要在落实香港特区自治权力的时候,尊重香港原来的制度。从“一国”原则出发,中央对香港拥有主权性权威,香港特区的自治权力不是固有的,而必须通过中央的授权来进行,因此,与司法权、终审权密切相关的基本法解释权,也主要来自于中央的授权。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来自于中国现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注:《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的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香港基本法》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所以,《基本法》的制定者在设计《基本法》的解释制度时,充分考虑到宪法已有的解释架构、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力以及香港特区的普通法传统,设计了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相结合的解释机制,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香港特区法院拥有一定限度的《基本法》解释权。
全国人大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限来自于《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根据《宪法》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香港基本法》第158条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是最终的权威解释。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1)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2)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第4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立法法》也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通过宪法性法律、基本法律、决议的形式授予其他国家机关行使一定权限的法律解释权。1981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作出解释,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作出解释,授权国务院主管部门负责对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法律应用问题进行解释。这种解释不得违背法律、法规的原意。当三者的解释出现分歧时,以全国人大的解释为准。也就说法律解释可以推翻司法解释。在中国内地法律体制下,法律解释权和终审权是分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最高的法律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终审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法律解释是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并不是代替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对于每一诉讼案件而言,最终的事实认定、法律定性和法律适用权均在法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香港基本法》授权香港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进行解释。理论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对《基本法》享有全部范围的解释权,但是一旦作出授权就应该受其授权范围的限制,在没有收回授权之前,不应该主动解释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是通过立法程序来解释宪法和法律的,其解释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因此,一般都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称之为立法解释,其解释法律行为应该属于立法行为的范畴。(注:诚然,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行为,既不是司法行为,也不是立法行为,而是介于立法和司法之间的“半立法、半司法”的行为,也可以说是独立于一般司法和立法的专门性法律解释行为。(参见王振民论回归后香港法律解释制度的变化[J]政治与法律,2007,(3):5)在我看来,尽管全国人大解释基本法启动程序会应提请主体不同而异,但全国人大对基本法的解释是通过议案进行的,总的来说还是立法行为。)
《宪法》第67条还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宪法和法律、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权、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和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也就说,在中国内地,法律是否违宪的审查权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是否违宪、违法的审查权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依据立法程序行使《基本法》解释权。一是关于《基本法》解释的提案程序。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因此从法理意义上讲,这些主体均可以拥有解释《基本法》的提案权,不过由于各自职权范畴和性质的差异,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有关专门委员会更有可能提出解释《基本法》的议案。(注: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在王世瑚看来,解释《基本法》的议案是一种特殊的议案,考虑到基本法的精神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实际情况,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列举的提案主体都可以提出该种议案,应当由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议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基本法的议案。(参见王世瑚香港基本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C]//论香港基本法的三年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3-75)由于香港终审法院无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香港基本法》的议案,基本法从衔接香港法院的司法解释和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的需要出发,设计了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启动程序。《香港基本法》第158条规定,香港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二是征询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意见的程序。依据《基本法》的规定,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属的一个咨询性机构,由精通香港事务的资深人士组成,香港和内地各产生6名委员,它有权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发回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对列于《基本法》附件三的法律进行增减、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和修改等职权时提供咨询性意见。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仅供全国人大常委会参考,并不能产生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的效力。
三是拟定、修改《基本法》解释草案的程序。根据《立法法》第44条的规定,法律解释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研究拟定,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法律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因此,《基本法》解释草案一般也应该由专门的委员会起草,并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务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审议,最后由法律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并修改形成一个供表决的《基本法》解释草案表决稿。
最后是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基本法解释草案进行表决的程序。《立法法》第46条规定:“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因此,《基本法》解释草案只有获得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的赞成票时方能生效。
香港虽然实行判例法制度,但制定法也是其重要的法律渊源。不过在法律解释架构方面,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均无权对法律作出权威的解释,只有法院有解释法律的权威。《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区继续沿用普通法,实际承认了香港特区法院拥有解释在香港实施之法律的解释权威。如果香港特区立法机关认为香港特区法官的解释不正确,它可以修改法律或重新制定法律,形成与法院之间的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就香港特区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限而言,依据《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员授权香港特区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解释《基本法》,但依据被解释条款的性质不同,其司法解释的效力也不相同。香港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可以自行解释。(注: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主要是指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对外事务等《基本法》规定的内容。)香港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也可以解释,但当这些条款的解释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性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没有溯及力。(注: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中央管理的事务或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其解释又关系到案件终审判决的效力时,就应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立法解释程序,这对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来说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如果符合这个条件,而终审法院不主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有关基本法条款,这种不作为本身就是违反《基本法》的行为。)由于香港特区法院是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解释《基本法》,因而其解释《基本法》的行为是一种司法行为。既然香港特区法院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范围和普通法传统拥有一定限度的《基本法》解释权,那么香港特区法院就有权对香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违宪行使司法审查权。诚然,香港特区法院的审查权威要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威,它也不宜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
二、香港基本法解释存在的问题
《基本法》的解释涉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利益关系的冲突与协调问题,因此,必然会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关系体现出来。两种解释主体的权威、解释范围、解释程序、解释立场和法治理念的差异容易形成两种解释模式之间的碰撞,引发宪政危机。
基本法的两种解释模式分别是两种法治理念的产物。内地和香港在法治理念方面存在冲突。依照在内地的法治理念,当宪法和法律条文的含义不清楚时,应当有一个权威的机关出面进一步说明立法的原意,而最了解立法原意的机构当然是制定法律的机关,因此应该把把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授予立法机关。与此相反,依据普通法的法治理念,同一机关解释和审查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是不可靠的,不符合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原则。这种观念上的冲突在“吴嘉玲案”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在“吴嘉玲案”的判决书中称:“一直引起争议的问题是,特区法院是否具有司法管辖权去审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以及倘若发现其抵触《基本法》时,特区法院是否具有司法管辖权去宣布此等行为无效。依我等之见,特区法院确实有此司法管辖权,而且有责任在发现有抵触时,宣布此等行为无效。关于这点,我等应藉此机会毫不含糊地予以阐明。”[2]香港特区终审法院的逻辑是,基本法是全国的宪法性法律,是特区的宪法,具有高于一般法律的地位,即便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能与之相抵触,香港特区法院依据《基本法》拥有终审权,并且有权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作出解释。一些香港学者也赞成终审法院的立法,在他们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终审法院是否凌驾于人大常委会之上,而是人大常委会是否受制于基本法。”[3]如果人大常委会的行为和《基本法》相抵触,依据普通法原则,终审法院有权作出这种判决。而在祖国大陆法律专家看来,香港特区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的,是有条件和范围限制的,法院的审判权不能凌驾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上;作为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威是任何机构都不能否定和挑战的。[4]在我看来,谁拥有宪法解释权和违宪审查权,并不仅仅取决于行使这种权力的国家机关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是以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的效力、人民意志高于代表意志、司法程序高于一般程序为合理性基础的。因为两种法治理念的内在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在《基本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无法回避这两种文化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基本法》的制定者在设计《基本法》解释制度时,过分乐观地相信依靠祖国大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能够在《基本法》的解释架构上实现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权威和香港特区法院司法解释传统的整合。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基本法》的制定者在处理国家的司法主权时,将原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终审权完全给予香港特区法院,试图通过现行体制下的人大释法模式来控制香港特区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并力图借助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来协调立法主权和香港特区法院司法终审权之间的关系。在当今世界,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地区联盟和成员国的关系虽然都首先通过某种政治机制来加以整合,但是最为权威、持续、有效的是法律整合机制。欧洲联盟是法律整合的最佳典型。中央在协调和香港特区的关系模式上,选择了政治协商的协调模式,不考虑中央司法主权,放弃了司法监督的协调模式,给香港回归以后的深度整合造成了根本性的障碍。当然,《基本法》的这种制度安排有其深厚的政治文化底蕴。在祖国大陆的政治文化传统中,立法机关具有法理上的至上权威,行政机关具有事实上的主导地位,而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一直没有在实践中加以落实,司法独立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司法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发挥宪法所设定的功能。在对香港特区自治权的控制机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是重要的主体角色,而最高人民法院是辅助性的角色,仅仅起着两地司法协助的作用。
从性质上讲,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是一个正式的咨询机构而非职能机构,它没有任何职权,其意见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强制约束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自行决定采纳或不采纳这些意见。《基本法》也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采纳基本法委员会对有关《基本法》解释的共识性意见,还是采纳多数人的意见。基本法也没有对基本法委员会作出正式意见所必须遵从的程序给予明确的规定。由于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来自于内地和香港,在许多问题上因委员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立法不同,未必都能达成共识,甚至有时无法形成多数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综合各位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意见,独立地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因此,应该很有必要通过《基本法》解释或以宪政惯例的形式对全国人大征询基本法委员会意见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
由于《基本法》将终审权授予了香港特区法院,完全放弃了中央的司法主权,中央为了保证《基本法》立法宗旨的实现,人大常委会必然经常和主动地行使《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香港特区法院认为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是被动的,必须由特区法院提请人大常委会才能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并且是否符合提请释法的标准由香港特区法院自主认定。这实际上架空了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和《基本法》享有的解释权。另一方面,在中央司法主权缺失的情况下,香港特区终审法院能够借助普通法司法传统尝试地挑战中央立法机关的主权权威,虽然中央能够通过人大常委会的法律终极解释权和基本法委员会的政治协调作用,凭借强大的中央政治能量和协商政治传统解决《基本法》的解释引发的危机,但那只是《基本法》模式的个案性胜利,很难说明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基本法》解释危机。
欧盟成员国都是主权国家,能够依据其签署的基础条约自愿接受欧洲法院对法律解释问题的先行裁决权,能够自动接受欧洲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和司法判例发展欧盟法、实施欧盟法的制度。在这些成功的实践中,欧盟成员国这些主权国家并不认为这样的做法会妨碍本国的司法独立,那么作为一个仅仅是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区的香港,为何会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解释会僭越其司法独立的权力?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的原因有:
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担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动辄行使《基本法》解释权而使香港特区法院实质上丧失《基本法》的解释权。根据《宪法》、《立法法》和《香港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当出现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情况,以及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情形,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有权主动解释《基本法》,并且不以任何机构或个人建议它解释为前提,也不以法院是否存在相关诉讼为基础。此外,尽管《香港基本法》已经为中央和特区的权限作出了界定,但基于成文法的局限性、法律语言表意的有限性和立法技术的时代限制,《基本法》不可能在中央与香港特区自治事务之间划出绝对清晰的界限,总有一些事项处于边缘性的模糊地带,不那么容易进行界定;因此,当香港法院不主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相关条款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履行宪法赋予的职权,主动对《基本法》的相关问题进行解释。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并不能直接推翻香港特区终审法院生效判决的效力,但在事实上将终止既存判决对后续司法实践的约束力,故仍然会影响香港特区法院的声望,进而影响到香港民众及国际舆论对香港特区司法甚至“一国两制”的信心。可以说,全国人大的这种立法解释机制必然会引起香港法院和香港有关人士的担心。
二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专业性的质疑。相比之下,欧洲法院对欧盟基础条约解释的先行裁决是由各成员国有名望的法官和法律专家按照司法程序作出的,这种解释具有极大的公信力,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不一定具有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丰富的法律适用经验和长期积累的法律理性,其解释也不是按照司法程序进行的,没有司法程序权威的支撑,其解释权威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同司法解释权威相提并论。《基本法》的解释属于广义上的法律解释,但《基本法》是宪法性法律,其解释属于宪法解释。《全国人大组织法》、《立法法》规定了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程序,但没有规定解释《宪法》的程序,也没有明确规定基本法解释议案的提案权主体。《香港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特区终审法院具有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涉及中央管辖事务或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的提请权,但没有明确这种提请权的性质。在内地最高人民法院还从来没有正式公开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过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下,要求一个新成立的特区终审法院主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确实有点强人所难[5]。香港特区终审法院作为一个普通法传统下的司法机关,享有《基本法》规定的司法权力,是特区权力架构中独立程度最高的权力,它承载着香港社会对其维护法治、控制权力、保障人权的期望,这决定了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很难屈从于中央的立法解释权威。实际上香港特区终审法院至今尚未开创提请全国人大解释基本法条款的先例。很显然,这种提请权不属于司法系统内部的制度安排,很难获得香港特区终审法院的认同。在实践中,全国人大要么自行启动解释《基本法》的程序,要么在特区政府寻求国务院协助提请下启动解释基本法的程序。因为《基本法》没有明文规定特区政府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所以,一些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当然,特区政府并非依据《基本法》第158条而是依据《基本法》第43条和48条的规定,向中央政府报告。根据这些条款,特区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对外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其法定的职责之一就是执行《基本法》,当《基本法》的实施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有权力和责任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中央政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基本法》的议案。但这种启动机制并不是《基本法》制定者原来的设计意图。
三是害怕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终局性权威会阻碍香港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制度延续普通法传统和建立连续的判例制度。香港虽然也有大量的制定法,但是判例法一直在香港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判例法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司法解释在法律解释体系中具有至上性权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司法判例原则和规则具有约束后续类似案件的拘束力。全国人大对《基本法》的立法解释一旦进入香港普通法传统下的司法解释领域,必然会影响乃至冲击司法解释的权威,影响司法的公信力,进而对判例法的存续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解决香港基本法解释问题的构想
既然特区法院的终审权是全国人大通过《宪法》和《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区法院的,在法理上中央可以依据主权原则收回终审权,恢复对香港特区的司法主权。《基本法》实施50年后,《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可以考虑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剥离。但在此之前的过渡时期,在中央司法主权缺失的情况下,《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掌握,并且通过完善征询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之程序来加以强化。因此,可以有3种方案来解决基本法解释制度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目前《基本法》设定的解释模式上,通过宪政惯例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征询基本法委员会意见的程序,明确基本法委员会意见的效力,使意见咨询成为过渡时期协调基本法解释权的有效机制。(注:也有学者认为,《基本法》解释权的协调机制应当建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特区终审法院之间。“理由是:这两个机构分别是现行《基本法》框架下内地与香港的基本法监护机关,其他机构无法取代。不过,基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至上性,不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出面,可以考虑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其所属的法制工作委员会与终审法院进行协调。”(见王玄玮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冲突与协调[J]云南大学学报,2007,(3):7))在基本法委员会形成一致意见或多数意见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充分尊重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即使这种意见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看法不同,也应当首先充分听取基本法委员会的建议。基本法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深孚众望或具有深厚法学功底的人士,尤其基本法委员会的香港成员都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立法会主席和终审法院法官联合提名产生的,在《基本法》制定和实施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意见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相比之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往往不一定是香港问题的专家,也许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复杂的法律和政治问题缺乏深刻的理解和细致的钻研,加之观念和视角的差异,不一定能够准确地把握问题的关键;因此,为了确保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解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应只把基本法委员会视为普通意义上的咨询机构,而应该尊重他们形成的多数意见,建立依照基本法委员会一致意见或多数意见作出决定的惯例[6]。如果出现基本法委员会中的香港委员与内分歧地委员意见严重分歧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召开听证会,全面了解不同见解,谨慎地作出解释决定,并向持不同意见的委员和各界人士详细说明解释决定的法律依据和理由。
第二,借鉴英国的经验,通过宪政惯例逐步实现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之程序的准司法化。《基本法》承认香港普通法存续的合法性,而判例法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确保司法解释的至上性和权威性,为此必须将全国人大解释《基本法》的程序纳入准司法程序的轨道,借以消除内地立法解释主导型与香港法院司法解释主导型法律解释模式的碰撞。在议会解释程序的司法化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法律最终解释权由上议院中的司法委员会行使,立法则由下议院负责的经验,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职能和法律解释职能分开并通过不同的程序来履行这两个职能。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通过司法程序来解释《基本法》,只有当法院审理案件时涉及到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或关于国家政治行为、外交行为的界定等问题时,在当事人或法院的提请下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程序。(注:香港回归前,香港最高的法律解释机关是英国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香港最高法院并没有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和司法终审权。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不仅有权解释当时香港的《英皇制诰》和《皇上训令》这些宪制性法律,而且可以通过对案件的审理解释香港本地立法。枢密院通过司法程序结合具体案件进行法律解释,当事人因对香港最高法院的解释持不意见而不服判决时,有权上诉到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请求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解释相关法律,双方当事人有机会在司法委员会委员面前就如何理解法律条款的含义发表自己的意见。)
第三,建立宪法法院专门行使对《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权。随着我国民主不断推进,人们会深刻地认识到司法解释是弥补法律漏洞,进行权利推定,扩大利益保护,维护法律稳定性,树立法律权威的最佳机制,我国的政治体制也会顺应民主发展趋势,把宪法司法化当作我国重要的宪政机制。法律解释模式可以参考德国宪法法院和美国普通法院模式,凡是有关宪法的解释问题可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附带进行,通过宪法解释来对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由普通法院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可以强化司法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有效地制约立法权和行政权,保证国家权力处于分立与制衡的状态。而由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可以减轻普通法院的负担,保证违宪审查的有效进行。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就能更有效地进行宪法解释,实施宪法的司法化,更好地履行违宪审查的职能。实际上,现代宪政制度设计和运行理念不仅强调代议制的民主特质,而且还注重在权力与权利平衡配置的宪政架构实现群体决策与个人自由决策之间的适度平衡。而宪法程序则通过对司法程序的设定为个人选择提供了程序性平台,以期通过司法审查程序让具体的利害关系人和法官依据宪法对法律和法规进行商谈性评价并进行理性反思。法律解释的司法化和违宪审查的司法化乃是民主宪政制度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就司法解释和司法审查的主体要素和对象要素而言,司法解释和司法审查主体的选择应结合我国的国情,利用已有制度资源,建立独立于现行司法和立法体系的宪法法院,专门负责对《宪法》、宪法性法律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解释,并对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宪的案件进行审查和审理。而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则作为一般司法解释主体行使有限的宪法解释权,负责审查法规是否违宪。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可以对地方法规、规章的违宪问题行使司法审查权,而国务院行政法规、规章的违宪问题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审查,同时可以考虑由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解释《宪法》、宪法性法律和一般法律的请求,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考虑到具体行政行为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仍然由各级法院中的行政法庭进行。宪法法院的法官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就司法审查的依据而言,《宪法》、宪法性法律和宪法判例应该是司法审查的最权威依据;就司法审查的程序要素而言,坚持审查程序的司法化原则,通过对宪法和法律的司法解释来审查立法行为或其他违宪行为。就宪法解释和司法审查的启动程序而言,对有关国家机关权限争议的宪法诉讼的请求人应该是权限纠纷的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有关法律和法规是否违宪的审查请求可以由各级法律实施机关和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提出或者由认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提起;违宪审查程序的启动要坚持前置程序先行和穷尽一般救济程序的原则。就司法审查的效力而言,宪法法院作出的宪法性判决是终审判决,具有既判力,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澳门特区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法院对法规是否违宪的判决属一审判决,上诉至宪法法院后作出的判决具有终局性效力。
在这里,宪法法院和特区终审法院的关系类似于欧洲法院和欧盟成员国法院之间的关系。欧洲是通过法律统一来建立区域性一体化组织来实现区域统一的,欧盟法院也是由欧洲法院和成员国法院共同组成的,它们拥有不同的职责和管辖权。从既要保障共同体法律得到统一实施,又要保证不损害成员国的主权和司法独立出发,欧盟设计了先行裁决制度、咨询管辖制度,有效地解决了欧洲法院和成员方国内法院的关系问题,进而成功地理顺了欧盟和成员国的关系问题。(注:宪法法院具有先予裁判权、终极的司法解释权、司法审查权和咨询管辖权。欧洲法院利用先予裁决权威、司法解释权威、司法审查权威和咨询管辖权威维护了欧盟法的统一,保障了欧盟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在各成员国的统一实施。欧洲法院通过司法审判为欧盟发展了新的法律原则、并利用司法判例有效了调整了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明确和提升了欧盟组织的法律地位,事实上成为欧盟法的又一个创制中心;欧洲法院还通过判例式的司法解释,使框架式的欧盟法律得以具体化,从而在整个欧盟层次和各成员国得到有效的实施,由此创立了法律实施的新模式。)欧共体基础条约赋予欧洲法院先行裁决管辖权,并规定先行裁决程序是成员国法院诉讼程序中的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成员国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遇到了对共同体法释义的问题时,应该将这一问题提交给欧洲法院。欧洲法院不得以所提问题无助于争讼案件的审结为由拒绝作出解释。欧洲法院通过先行裁决程序作出的裁决不仅对主案具有约束力——成员国法院必须适用该裁决的结果对主案作出裁决,而且还在欧盟法律制度中具有先例判决的效力。显然,先行裁决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成员国法院成了欧盟法的司法机关,与欧洲法院一道承担实施欧盟法的司法职能,从而保证了欧盟法适用上的统一。为了保证条约执行的正确性,欧洲联盟在有关基础条约中还规定欧洲法院拥有咨询管辖权,可以应欧盟委员会的请求,对理事会、委员会或一成员国拟议中的协定是否符合基本条约的规定,发表咨询意见,该咨询意见具有法律拘束力。实际上欧洲法院通过对条约的解释与适用,对欧盟法的实施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本法》解释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欧盟先行裁决制度和咨询管辖权制度,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1988年10月出台的《欧洲共同体法律解释程序与基本法解释程序的比较》咨询报告中明确指出《基本法征求意见稿》中有关《基本法》解释程序的规定参考了欧洲共同体的“先行裁决”制度。[7]但是在基本解释的主体模式上,《基本法》制定者鉴于中国没有一个地位在最高人民法院和特区法院之上的宪法法院,故只好利用原有的大陆法律解释模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和法律的终极解释权,授权特区法院有限的《基本法》解释权。我国设立宪法法院后,全国人大可以收回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终审权,同时规定由宪法法院行使宪法和宪法性法律的终极解释权、特区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有限的宪法、宪法性法律的解释权,特区法院在《宪法》、特区《基本法》和其他在特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的解释方面不再拥有终局性解释权,尤其在《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之解释上没有最终的解释权。ML
参考文献:
[1]徐静琳,张华关于香港特区违宪审查权的思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24
[2]NgKa睱ing Other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1999]1HKLRD315
[3]陈文敏司法独立是香港重要基石[C]居港权引发的宪法争论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63
[4]凌兵解决基本法与人大其他立法行为之间的冲突的应适用法律[C]居港权引发的宪法争论,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156
[5]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63-369
[6]史深良香港政制纵横谈[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6
[7]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R]1988,(2):33
The Authority and Procedure to Interpret Hong Kong Basic Law
JI Jin瞙ua
(Law schoo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
Hong Kong Basic Law, a national constitutional law, is the basic law for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execute th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Basic Law specifies that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uthorized to construe the Law, while the Committee may delegate its interpretation power to the courts of different levels in Hong Kong with certain conditions.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are thus inevitable between the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ince the courts and the Committees positions, perspectives, legal traditions and interests differ a lot. The defective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in respective of the interpreting agencies, power and procedures will surely lead to unconstitutional crises in practice and should be improved accordingly.
Key Words:Hong Kong basic law; interpretation; power; procedure
本文责任编辑:张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