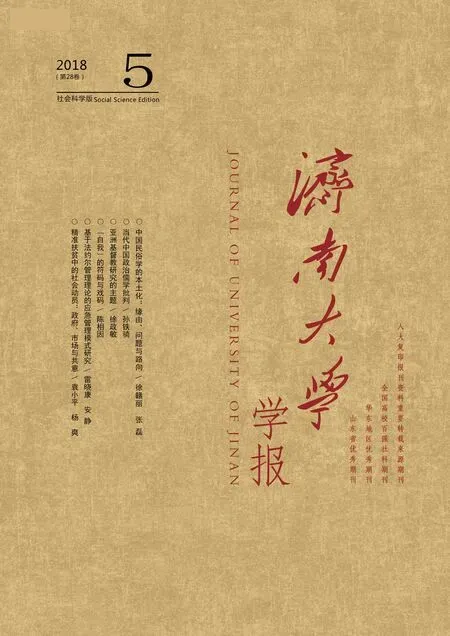“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
——大陆新儒家反思
鞠 曦
(长白山书院,吉林 抚松 134500)
在人类之历史长河中,曾存在多种文明,如中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等等,而历史表明,其它文明类型早已消失,能够存续至今的只有中国文化,从而保留了丰富的文化传统与浩如烟海的典籍,其表明,中国文化有一个其它文化没有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使中国文化有极为坚强的生命力,以至于在人类文明的浩瀚历史中没有中断自己的传统,这个特点就是:无论中国文化遭遇外来文化之何等冲击,只要坚守道统,中国文化就会以自身的文化理路,同化外来文化。中国近现代史表明,中国文化尤其儒学遭遇了空前危机,甚至走到了生死存亡之边缘。表面看来,这次危机起源于以民主、自由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实际上则产生于“新文化精英”对道统的历史性误判——始于儒分为八、汉儒篡经所导致的道统异化从而最终发生以“罪丘”为问题形式的文化危机。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孔子对必然发生“罪丘”问题的正确预见,并给出了“以易知丘”的逻辑进路,从而可以解决儒学所积淀的各种问题、重新以正本清源后的孔子儒学解决中国及人类所面临的疑难问题,引领人类文明的历史方向。显然,这些应是中国当代儒家及其儒学界的自觉与担当。然而,奉行“新康有为主义”的号称“康党”的“大陆新儒家”们,却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康党”近年来的频繁出场与强势主导“大陆新儒家”的吊诡行为,乃经过长达十数年的“层累”,蒋庆、陈明所表达的“大陆新儒家的理论成熟”,说明了“康党”之为“康党”的条件已然具备,从而使其能够以“清一色的康党”独领风骚而“草堂论剑”,并企图以强势“康党”代表“大陆新儒家”以引导儒学的复兴方向。然而,由于“康党”逆儒学的历史与逻辑而动,给当代的儒学复兴带来了极坏影响,在腐败的学术体制下,“装睡着了”或“真睡着了”成了普遍现象,由此表明当代的儒学前途已经充满危机。问题表明,与时而来的“儒学热”,使各路人马粉墨登场,以“儒家”的角色出场,用孔子装扮门面,沽名钓誉,忽悠社会,亦不过是为了索取、维护各种利益而已,与孔子儒学的真谛毫无关联,与真正的儒学复兴更了无干系。
显然,基于现代中国教育体制与社会制度长期以来对儒学的批判、排斥,使儒学复兴的基础——儒家人才的生长缺少体制性土壤,正如没有工程师就不可能成就一项合格的工程一样,没有儒家人才何以复兴儒学!所以,儒学的复兴面临被存在与去被存在的二难困境,一方面需要对经典的误读进行正本清源,另一方面需要以正本清源后的经典培养儒家人才,以为复兴儒学之基础。
所以,儒学的二难困境决定了儒学复兴之艰难。“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表明的严峻问题在于,“康党”们声称所代表的“大陆新儒家”,是师承孔子还是别出之贼?即称“康党”,又何言儒家?“君子群而不党”,可见“康党”已不是儒家。“康党”即非儒家,非师承孔子,其又何以自谓“儒学”并代表“大陆新儒家”?“康党”是复兴儒学还是另有企图?这些问题,关乎儒学复兴的大是大非,关乎孔子儒学的真谛与实践,关乎儒学之未来,更关乎“康党”以其贼而毁孔子,误国害民,罪莫大焉,故不得不辩。
问题表明,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从而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一、为今托古:“康党”的儒学投机
“康党”的思想理路表明,所谓“新康有为主义”,不过是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以使儒学成为政治的儒学和宗教的儒学,由于与康有为以“托古改制”对儒学进行的政治化与宗教化不谋而合,故以“回到康有为”为思想进路以获得历史的合法性,就成为康党之逻辑必然,从而使“回到康有为”成为“新康有为主义”的标志性符号。所谓“回到康有为”,不过是托康有为之古,改儒学之制。“新康有为主义”认为,传统儒学只是“心性儒学”,而“康党”则开创出了“政治儒学”与“宗教儒学”的当代传统,从而声称儒学在当代的发展方向就是“政治儒学”和“宗教儒学”。
“康党”之所以谓“康党”,乃以康有为为思想核心。首先明确提出以康有为为当代儒学复兴的理论根据者是康晓光。早在2002年,他就发表了《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一文,极其推崇康有为之为了“政治需要”与“实现政治抱负”所进行的“学术”及其为此提出的“儒教复兴纲领”。他说:
早在一百多年前,康有为就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儒教复兴纲领。康有为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对于他来说,学术是实现政治抱负的手段。他对儒家学说的处理,与其说是为了发展理论,不如说是为了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一百多年后,重温他的那些文章,我们不但能够感到一种高瞻远瞩的伟大智慧,还能够体验一种不可战胜的自信、博大恢宏的气度、死而后已的责任感、对理想的无限忠诚、挑战社会潮流的无畏勇气和对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注]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战略与管理》, 2003第2期。
正是对康有为的推崇,康晓光进而十分“坦率地说,我们今天所要作的一切,不过是继承康有为的事业,完成他未竟的理想。”[注]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战略与管理》, 2003第2期。他所继承的康之“事业”与“理想”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即“为了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故其“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显然,他所谓对儒学的“重塑”,不过是为了社会政治需要而对儒学进行的宗教化。
唐文明则把康有为推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他说:
康有为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既不是孙中山,不是毛泽东,也不是章太炎,康有为才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立法者的意义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以后才能被真正认识到,且在当时还可能是个失败者,因为立法者不一定有武装,可以是个没有武装的先知。而如果我们以此来看现代中国的话,就会发现,章太炎也好,孙中山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的思路都在康有为思想的笼罩之下。因此在我看来,目前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把康有为作为现代中国立法者的地位给确立下来,其他问题才可以高水平地展开讨论。[注]唐文明等:《康有为与制度儒学》, 2014年6月26日~27日在广东南海“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研讨会,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63144232/。
在唐文明看来,因为康有为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所以,只有在“新康有为主义”的旗帜下而循康有为之法,才是高水平的真正的“大陆新儒家”,其它“儒家”则因水平太低,均应排除在儒门之外。关于康党对儒学的政治化与宗教化,基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干春松则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上对“新康有为主义”的思想理路进行了陈述:
曾亦和唐文明对康有为晚期思想的重视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可以窥见端倪,因为蒋庆的政治儒学设想和康晓光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主张都从康有为的孔教思想中发现了儒家思想与当下中国政治、价值重建之间的意义。因此,从儒家群体而言,对康有为的重视也意味着大陆的儒学研究者和实践者慢慢摆脱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港台新儒家”的学习和依赖。……重视康有为给儒学研究带来的最大变化首先是对政治儒学的重视。……回到康有为是大陆儒学以区别于港台新儒学的独特性的一种标志”……基于对康有为的孔教会的研究,将深化对于儒家宗教性和儒教作为建制性宗教建立的可能性的思考。……我曾经提出过一种想法,康有为是中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源头,因为他在戊戌变法时期对于民权和议会制度的推崇,构成了中国后世自由主义的基本命题;而他的儒教立国的思想则可以看做是新儒家思想的奠基。他在《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观念的引入和接受的重要一环。[注]干春松:《回到康有为:问题意识与现实策略》,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5415/。
为了在“康有为的孔教思想”中发现“儒家思想与当下中国政治、价值重建之间的意义”,干春松直至不遗余力的向学界鼓吹:
如果存在一个儒家的新发展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就只能是康有为。如果你要为儒学的现代发展贡献力量,那么,请追随康有为。[注]干春松:《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6页。
为了推定“儒家的新发展的起点”——此即康党“创教干政”的逻辑起点亦即为什么要追随康有为之所在,因此“需要对康有为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一个说明。”[注]干春松:《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0页,第10-12页。干春松说:
通常的看法是将儒学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至汉的儒学、宋明儒学和现代新儒学。……如果我们将中西问题理解为古典与现代的话,那么,儒家甚至可以分为两期,即康有为之前的儒家和康有为之后的儒家。[注]干春松:《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0页,第10-12页。
至此,由“儒家两期说”,康有为成为“儒家的新发展的起点”。显然,干春松的“儒家两期说”呈现出一个吊诡的逻辑,把“通常的看法”的儒学史以“中西问题理解为古典与现代”,难道“现代新儒学”不是因为“中西问题”而产生于“现代”?!难道以“古典与现代”则可以对“中西问题”有不同理解?!更为吊诡之处在于:无论以中西还是以古典或现代为视域,难道儒家就有了不同的被存在形式因此就有了与孔子不同的理论推定?!果如是,这样的儒家还能称其为儒家么!显然,与孔子背道而驰则不能称为儒家,因此其只能以贼儒的价值取向对孔子儒学进行篡改,貌合而神离,掩人耳目,故必然以“托古改制”而假康有为,挟儒学而私己。所以,康有为托孔子而改制,康党托康有为而改制,因为托尔不实,则必然背离孔子儒学,故无论康有为还是奉行“新康有为主义”的“康党”,只不过是借用儒学的“古典”价值而遮蔽“现代”的“中西问题”之本质性,力图使“托古”具有合法性,从而用改制的儒学掩盖所面对的实质问题。是故,“儒家两期说”只是为了托古而抬出康有为,以“新康有为主义”为标准而不是以孔子为标准从而把儒学分野为“康有为之前的儒家和康有为之后的儒家”,乃背叛了儒学道统而走向了贼儒。
由此可知,排斥“心性儒学”从而提出“政治儒学”——实质上是对儒学进行的政治化——的蒋庆之所以与主张对儒学进行宗教化的陈明、康晓光及其与明确提出“回到康有为”的干春松、曾亦、唐文明等人最终以“新康有为主义”“结盟康党”,则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当代政治之考量,对儒学进行政治化是为了投机政治,而对儒学进行宗教化则是为了“创教干政”。由此出发,“政治的儒学”与“宗教的儒学”一拍即合,从而使政治与宗教合流,是“康党结盟”的重要特点。以政治与宗教合流为基点,以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为基础,康党认为儒家本身就是一个宗教,它的整个教会组织就是国家,因此必然为此而改变儒学的本质与制式而“托古”,从而托康有为曾进行的“托古改制”,则成为康党思想中的历史与逻辑之必然。
“康党”以今托古,难能正确面对当代社会存在的所有问题,故“回到康有为”,绝不是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试问:既然找到了康有为,所进行的宗教化、政治化是理性的进步还是倒退?正确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寻求造成问题的本质性原因。按照“康党”的逻辑,即当代中国的问题不是因为近代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不是因为对“传统”的决裂与彻底否定,而是因为没有执行康有为的路线。可见,康党的这一逻辑如果成立,那么,原因只有一个,即为了“创教干政”而为之以儒学投机,不过如此而已。
二、托古改制:贼儒之康有为
为了给“托古改制”进行理论奠基,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书。《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的主要内容是力图否定汉后儒家刘歆篡修的五经,“恢复”孔子为“改制”而“托古”所作之六经,即“证明”孔子因“改制”之需而作六经,从而为康有为的政治需要制造儒学依据。康有为认为,“六经”非古之遗言,而是孔子“托古改制”所自创,既然如此,效法孔子的“托古改制”从而进行康有为自己的“托古改制”就有了理由,这即是说,托孔子、托儒学使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有了历史与逻辑的支持。而“回到康有为”,显然是康党托康有为之“改制”而为当下之“改制”提供逻辑依据,由于上托孔子,则可以使康党通过“改”儒学之“制”以为当下政治需要提供儒学依据,从而使康党成为唯一的具有合法性特征的儒家“学派”。所以,干春松的“儒家两期说”为“回到康有为”提供了思想的历史逻辑,使康有为成为现当代儒学的逻辑起点,从而使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与其所言之孔子“托古改制”及其康党的“托古改制”顺理成章。然而,儒学的历史与逻辑表明,“儒家两期说”的要害在于,其完全否定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割裂了儒学内在的历史进路,遮蔽了二千余年儒学的实质问题,使儒学的当代复兴,走上错误的路向。所谓“儒家两期说”,不过是为康党的“托古改制”制造的历史逻辑,其表明,这一逻辑否定了传统的儒学义理,割裂了儒学思想史,使孔子的儒学思想被“新康有为主义”所异化,由此以来,“托古改制”的康党逻辑可为当下的社会政治提供依据,通过以政治为目的而改制的儒学——政治的儒学——以为当今社会提供政治需要,此即政治与宗教——政治儒学与宗教儒学所以合流之根本原因。是故,蒋庆们所谓以《公羊学》为本的三重合法性,不过是“托古改制”的政治的儒学,完全是落后的封建专制之再版,他们的企图是使儒学成为妄议政治、干涉政治的工具,“罪我者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其不但使孔子再度罪天下,并且扼杀了当代方兴未艾的儒学复兴,此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也。所以,所谓“无论‘国教论’还是‘公民宗教说’都与康有为存在学脉上的勾连”,实为“新康有为主义”以政治与宗教改制儒学的主张寻找依据,从而成为“康党结盟”之价值认同与逻辑必然。
所以,“回到康有为”是康党的“政治儒学”与“宗教儒学”一统儒林的“改制”性战略,将迷惑那些涉世未深、涉学末然的年轻学者,以扩充学派势力,打通在体制内的上升通道——这是陈明所谓“学派特征”的康党之实质性所在。可见,康党为排除历史性障碍,必托孔子之古,改儒学之张,故“回到康有为”是蒋庆、陈明、康晓光、干春松、曾亦、唐文明等以贼行儒的题中之义。是故,于学术上以“儒家两期说”分判儒学,是对道统之背叛,把康有为确证为现当代儒学的逻辑起点,从而否定现代新儒学使康党独大,势必以学术上的倒退而终成儒贼。康党不究《易》道,否定儒学经典的哲学基本意义,投机儒学而为之以政治化、宗教化,以思想的倒退而终成伪儒。
对于康有为“托古改制”的逻辑理路,为学界所诟病久矣!侯外庐认为康有为之治学乃“野狐狸式的说经风气”[注]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之名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以作为“托古改制”的学术根据,从而使这一“野狐狸式的说经风气”一反此前的儒学而游离出道统,使其与先秦两汉及宋明儒学具有巨大不同。康有为实质上反叛了孔子儒学,背离了儒学道统,其“托古”为“托”,“改制”为质,“改制”的着力之处,是要把儒学“改制”成政治的儒学与宗教的儒学,以宗教教规与组织的政权化,进而达到“干政”之目的。所以,康党托康有为改变儒学制式而为其政治化与宗教化所用,不过托儒挟私、贼儒妄行而已。
历史与逻辑表明,“《孔子改制考》基本上象征性地颠覆和终结了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传统,破坏性非常大。”[注]甘阳:《以稳健的态度来建立健康的保守主义》,《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而今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为旗号“托古改制”,是在康有为“颠覆和终结了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传统”基础上之变本加厉,对当代之儒学复兴造成了极大危害。
对于康有为之“托古改制”,时人即认为“自信过深,偏见遂执,有不合己意者,则妄加窜改。有不便窜改者,反诬为古人窜入。深文剖击,不遗余力,岂足为定论乎?其立论虽主底汉儒,其大旨犹为尊孔子。若律以离经叛道,则全书并无实证。”[注]马洪林:《康有为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0页。做为康有为弟子的梁启超,于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无论对康有为其学还是其人,都作了否定。梁启超说:
(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8年版,第78页,第79页。
(康)有为谓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为教主;误认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于是有为心目中之孔子,又带有“神秘性”矣。《孔子改制考》之内容,大略如此。[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8年版,第78页,第79页。
由此可见,如果以价值论承诺与范畴推定的统一论之,康党之所以要以“儒家两期说”推出康有为进而“康党结盟”,也只能因为两者在“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及其“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的问题上具有一致性。简而言之,康党与康有为均为了“创教干政”而假以学术,“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诚哉斯言是也。
《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表明,因康有为不是从学术上治经,其治学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所以治学必伪。然而,康党为政治而治学则比康有为更加露骨——无论如何,康有为还能以治经遮掩其政治目的,而康党则直接以政治的儒学与宗教的儒学而托古康有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政治的儒学及其问题,赵法生进行了深刻揭示:
蒋庆政治儒学的理路:他割裂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断言前者为儒家正宗而后者不是;继而宣称政治儒学的代表只有汉代公羊学,于是,公羊学就成了唯一纯正的儒学,孔子思想之唯一代表。于是,丰富、博大而精深的儒学,就被蒋庆简单、片面地与作为一家之言的公羊学画上了等号。不但如此,他就像南辕北辙故事中所说那位行者一样,在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继续曲解孔子思想,将孔子的人性论说成是性恶论,将孔子的思想重心说成是礼而不是仁,并将礼看作是批判人性的。可见,蒋庆的“政治儒学”,是建立在对于孔子思想的多重误读之上的,可谓失其根本一错再错。[注]赵法生:《政治儒学的歧途——以蒋庆为例》,《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因为康党的学术目的是为了“托古改制”,因此必然回避与否定哲学基于学术的本体论地位,从而对儒学具有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充耳不闻,亦必然诉诸于实用主义、投机主义的立场,依托康之的“托古改制”对儒学进行政治化、宗教化,这是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学术立场,而不是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新康有为主义”之所以不能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是儒家,故其根本就不可能坚守道统,不可能也不屑于从根本上把握孔子儒学的思想精髓。康党出于政治需要,只能以儒贼肢解儒学思想,以掩盖其跻身儒家的功利化目的。为了抬出康有为,康党通过篡改儒学史,以所谓的“改制”说推出了“新康有为主义”,从而使康党成为“大陆新儒家”的合法代表与理论核心,以“政治的儒学”与“宗教的儒学”实现其投机儒学的功利化目的。所以,并不是康有为具备了儒家特色,而是因为其异化歧出的思想特征可以为康党所利用。
三、理性倒退:去哲学的康党
“回到康有为”而假以“古典与现代”及“中西问题”,故分殊出“儒家两期说”,必然置道统而不顾从而以去哲学为手段,以此才能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所以,去哲学是“新康有为主义”的康党之理论特点。由于去哲学,使“新康有为主义”必然违背历史与逻辑,自说自话,纯粹服务于自我之价值取向,与孔子儒学毫无关联,从而使其理论与时代格格不入,成为一反人类文明进路的理论形式,以对理性之反动而沦为当代的思想垃圾。
显然,按照哲学的理路,无论“古典与现代”以及“中西问题”,在儒学中不过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经·说卦传》)。在哲学的理路中,《易》之“穷理”、“尽性”、“至命”,此三者概称为“终极关怀”问题。西方哲学表明,为了于理性中究及所有“存在”之理,其使用了主客两分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从而使本体与主体处于对立的地位,故始终无法确证本体从而不能对“理”进行主客统一的理论推定,本体的缺失使所有的“理”处于空中楼阁,最终导致失缺本体论即没有“存在之为存在”依据的西方哲学走向终结。
康党的理论表明,其没有在所建构的“新康有为主义”中以“哲学的终结”为逻辑起点,而是排斥哲学,即回避“哲学的终结”问题而去哲学,由此呈现康党的哲学吊诡——“新康有为主义”无力解决经久不决的哲学问题反而声称拒斥哲学的合理性——这是“新康有为主义”的要害,由此决定了其所有“主义”不可能应对其所谓的“中西问题”,必然走向理论的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正是对于哲学的拒斥,康党无视《易》之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路,故对一以贯之的儒学思想体系、对群经之首的《易》学之道浑然不知。
作为哲学、理性及其文化的核心,是《易》所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因此形成了恒以一德的思想体系。然而,到目前为止的人类所建构的除《易》而外的其它所有理论——无论哲学、科学或宗教,都没有解决“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核心问题,因此形成了多元化的自以为是的人文现象。然而,《易》“穷理”、“尽性”、“至命”三极中和,理穷而性,尽性知命,知命而命,对此,孔子有精深之推定,并以《易》之损益之道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所谓终极关怀的理路,于《易》中,是以“何思何虑”而“以至于命”的推定形式: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易经·系辞传》)
因为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易》因此表明了儒学理论体系之博大精深: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是故易有大恒,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六业。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易经·系辞传》)
孔子推定的《易》理是一个严谨的体系,举凡性与天道、人文伦理、思想学术,其无所不包,故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抟,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易经·系辞传》)由此可知,儒学必然有其自己的哲学,虽然不能认为儒学仅仅是哲学,但是康党认为儒学中没有哲学,由此表明其如果不是故意回避难能解决的哲学问题,则必然出于其儒学知识之浅薄,从而以政治与宗教的儒学冒充儒家,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问题了——此乃贼儒之必然也。蒋庆说:
中国文明的学术传统中没有哲学,因而中国儒学的学问体系中也没有哲学,哲学是希腊文明学术传统中的产物,是所谓纯粹追求智力的“爱智之学”,而非如儒学是“价值之学”。……儒学与哲学是不相应的,通过哲学是不能了解儒学的。[注]《专访蒋庆:回归经学是文明自信与儒学成熟的体现》,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11365/。
蒋庆非常武断的否定了儒学直至中国文明的学术传统中没有哲学,显然也否定了群经之首的《易》哲学思想。但是,《易·乾》之“元亨利贞”,却表明了哲学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易经·乾卦·彖传》)。此为孔子对天道的哲学本体论推定,进而给出了人道的哲学主体论推定:“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易经·乾卦·文言》)可见,“体仁、合礼、合义、干事”乃“君子四德”,仁者,人也;礼者,理也;义者,和也;事者,行也;德者,得也;故《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经·说卦传》)所以,儒学不但有哲学,而且其哲学义理已达“穷理尽性”,从而使人之所行“以至于命”。可见,蒋庆所谓儒学是“价值之学”,乃纯粹主观意志,其根本不知儒学之价值所在,因为否定儒学的“穷理尽性”之理路与进路,又怎么可能知道“价值”之正确与否及实现之途径?!由此可见,康党所谓的政治的儒学和宗教的儒学与孔子的《易》理毫无关联,其不过托古儒学而改儒学之制,以实现功利主义的个人野心,如此而已。
哲学的功能即“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无论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哲学的理性任务,是哲学应当解决的核心问题。哲学以其理性推定所有存在包括人的存在之所以然,给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探索与推定。但是,由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与主体论之二元分离,使本体与主体都陷入存在论——本体论的困境而终结,故西方哲学在“穷理”之阶段即走上终结而远未“尽性”,更弗论“以至于命”了,此乃西方哲学之所以终结的问题所在。蒋庆把哲学归结为“爱智之学”,显然抹杀了哲学的核心问题,难道哲学之“爱智”不是为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由此可见其对哲学之“爱智”断言,实在过于武断。
显然,正是出于对哲学的无知,蒋庆认为:“西方近代以来,哲学大多理性化,具有了纯粹理性的色彩,演变成了所谓‘理性哲学’。”[注]《专访蒋庆:回归经学是文明自信与儒学成熟的体现》,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11365/。历史表明,西方哲学不是从“近代以来”而是从“古希腊”诞生以来,哲学就是理性的表达方式,即所有的理性陈述只能用哲学的方式进行,以此区别宗教或其他学科。所谓“理性哲学”,正是哲学的本质,因为只有哲学性的思考,才能保证理性的纯粹性,而理性的纯粹性能够尽可能的避免个人的主观臆断,从而对“是”其所“是”进行正确推定,使主体走出自以为是,因此,哲学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这才是理性的“爱智之学”之本然。于此表明,正因为康党去哲学,否定哲学的理性功能,必然异化儒学并倡导“新康有为主义”,由于其非理性色彩,其所有理论必然充满难以自圆其说的理性吊诡。
虽然声称儒家,然而正是出于对《易》所代表的儒学哲学之浑然不解,蒋庆一而再的对儒学作出非理性的推定:“儒学在本质上是天道性命之学与生命体认之学,理性在理解儒学上存在着根本性的限制,不能进入到儒学的义理之中如实地理解儒学。”[注]《专访蒋庆:回归经学是文明自信与儒学成熟的体现》,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11365/。可见,蒋庆既然把儒学视为“天道性命之学与生命体认之学”,难道“天道性命”与“生命体认”的正确与否不是源自“穷理尽性”?!显然,在蒋庆看来,儒学不是“穷理尽性”的理性体系,因此“在如实理解经学及儒学的问题上,应该以信仰统摄理性,以价值指导认知,而不是信仰与理性平列,也不是价值与认知统一,因为儒学不是理性之学与知识之学,而是天道性命之学与生命体认之学,而天道性命之学与生命体认之学必须以信仰与价值为首出才能获得如实的理解,即必须价值立场与情感认同优先才能获得如实的理解。这正是如实理解经学及儒学的不二法门。”[注]《专访蒋庆:回归经学是文明自信与儒学成熟的体现》,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11365/。如蒋庆所言,既然“儒学不是理性之学与知识之学”,那么“穷理尽性”当作何解?所谓“天道性命之学与生命体认之学必须以信仰与价值为首出”,其“天道性命”与“生命体认”仅仅是“信仰与价值”,即儒学“不是信仰与理性平列,也不是价值与认知统一”,可见,这样的儒学根本就无法进入现当代人类文明与文化的视野,没有理性追索必然使所有认知失缺坚实的本体论,这样的学问必然出于自以为是,从而以非为是进而自欺欺人。反思表明,在孔子所建构的儒学思想体系中,无论是“天道性命”还是“生命体认”,均出于“进德修业”,所有推定乃“信近於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而不是出于“信仰与价值”。“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易·乾·文言》)儒学之义理,成于“进德修业”之“忠信”,此“忠信”乃以“辞诚居业、知至至之、知终终之”为本,故“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儒学义理,言行一也,所言必可行,与行方可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亦即哲学与科学之中和统一是也,故“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如今蒋庆却视儒学为“信仰与价值”而不是“进德修业,言必有中”之理性,如果不是出于对儒学之无知,则只能是出于自己的价值取向而“优先”选择的“立场与情感”,由于“优先”的“立场与情感”,必言过其行,故此乃不知耻也。所以,蒋庆所谓“理性在理解儒学上存在着根本性的限制”,不过是为儒学的政治化与宗教化进行的铺垫,其由“信仰与价值”出发而言的所谓“儒学的义理”,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问题表明,康党所谓“古典与现代”以及“中西问题”,没有超越也不可能超越“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的问题形式。难道康党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天下”问题?不是“同归而殊涂”?显然,康党之谓康党,乃因其有意回避了《易》“终极关怀”之追问。实际上,任何一种思想包括康党的思想,也只能是“殊途”、“百虑”之一,只不过康党的所有思考不是对“一致”与“同归”的追索,即康党不想把其“殊途”、“百虑”“同归”为“一致”,因“同归”与“一致”的思索只能为哲学所属,故去哲学就成为康党之必然。显然,不能进行这一追索,就不可能“安身崇德”与“盛德知化”。
所以,康党不但一反《易》道,而且一反人类理性之进路,以逃避“一致”与“同归”的“终极关怀”问题。故对于儒学的性质,蒋庆断言:
儒学是中国传统的习俗礼法之学与道德宗教之学,具有超越性、神圣性、神秘性与永恒性,即是宇宙人生与历史文化的“常道”。对这一“常道”,哲学的理性反思与批判精神无疑对其所具有的超越性、神圣性、神秘性与永恒性存在着巨大的威胁,因为哲学不断的追问与怀疑必然会对儒学的义理系统造成解构性的破坏,最终会消解儒学所具有的超越、神圣、神秘与永恒的特性。[注]《专访蒋庆:回归经学是文明自信与儒学成熟的体现》,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11365/。
蒋庆在这里又一次否定儒学之“辞诚居业、知至至之、知终终之”,而以“习俗礼法与道德宗教”冠名儒学,以宗教的“超越性、神圣性、神秘性与永恒性”为儒学之本质,因此不能以“哲学的理性反思与批判精神”去“追问与怀疑”儒学,由此可见,对于儒学之“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的理性精华,其的确一无所知。然而,蒋庆一方面反对理性,另一方面又说:“儒学内部也存在着自我批判与理性反思的能力,也在不断地通过儒学内部的自我批判与理性反思来纠正自身的错误,从而完善儒学自身的义理系统。”[注]《专访蒋庆:回归经学是文明自信与儒学成熟的体现》,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11365/。对此不禁要问:蒋庆所谓的“儒学内部”,难道能够超越“天下同归、一致百虑”?“儒学内部的自我批判与理性反思”是否还是也只能是“超越性、神圣性、神秘性”的宗教性质?如果“自我批判与理性反思”不为哲学性质而是宗教性质,那么,“自我批判与理性反思的能力”从何而来?“反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由此可见蒋庆去哲学的吊诡——只要思维则根本离不开理性。由此表明其思维方式的混乱,反理性而又不得不诉诸于理性,这是康党的思想特点。
为了其价值取向,蒋庆道破了去哲学之本然:“所谓理性反思,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理性的批判考量,即进行理性的追问怀疑,然后通过个体的自主理性作出自由的选择。因此,理性反思对现存的传统、习俗、道德、宗教都具有强烈的颠覆性与解构性。”[注]《专访蒋庆:回归经学是文明自信与儒学成熟的体现》,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11365/。这就是说,康党坚决拒斥哲学的原因,乃因为哲学的批判能力足以否定康党提倡的“习俗礼法与道德宗教”之“超越性、神圣性、神秘性与永恒性”,此乃康党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而必然去哲学从而形成“新康有为主义”之荒谬。
康党把儒学应对的问题分为中西古今,本身就是对儒学的误解。儒学之道,恒以一德、一以贯之,恒久不变是也。所以,康党应对时代需要而对儒学进行政治和宗教的异化,说明康党所受的教育是以变化、发展、进步为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本身就是一种西方的观念,康党反而拒斥西学,强调中学,不过是为政治化与宗教化所作的辩护而已。显然,拒斥哲学的理性进路从而通过“回到康有为”开出政治的儒学与宗教的儒学进路,这样做的理由只能是“创教干政”的价值取向。按理性的人文学术研究之承诺与推定,所有的理论根据必须是哲学的,而所有的形式必须是科学的。显然,“康党”们并没有于哲学上给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之论证,没有在哲学上证明政治的儒学与宗教的儒学在历史与逻辑上的合理性,这显然不但是学术理性的倒退,而且无论对自身、对学术、对儒学都是极端的不负责任,在人类理性已经达到哲学与科学高度的现代文明进路中,康党们却刻意回避之,本质上是对儒学的毁败,为贼儒之举,其贼所败者,儒学及其人文化成是也。康党对儒学的政治化与宗教化,是对儒学之否定,是理性之倒退,是文明之反动。故康党之害儒败道,乃世人皆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