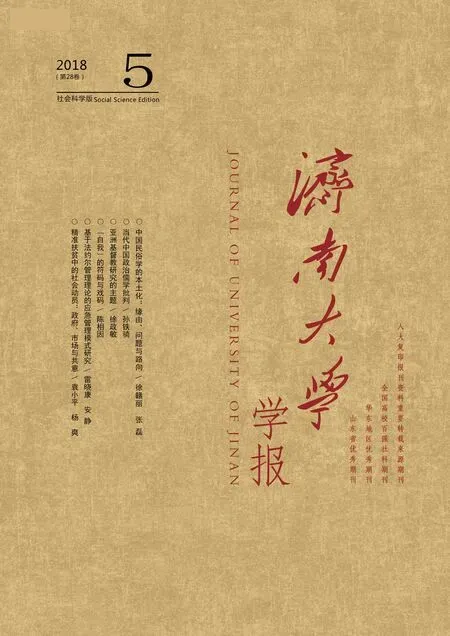亚洲基督教研究的主题
——日中韩基督教的历史及其展开过程的诸前提
[韩]徐政敏著,朱海燕译
(明治学院大学 教养教育中心,日本 东京 108-8636)
一、绪论:日中韩与对亚洲的认同感
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是“东亚的近现代史与基督教”。迄今为止,日本、中国、韩国各地有关基督教的研究,因研究目的和方法论各不相同,有着以个别研究为主的倾向。各国与基督教的接触过程和其后的发展、历史的特殊性各不相同,从这一角度来说这种研究倾向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最近开始出现互相比较各地区接受基督教的历史及现状,或在大的框架和视野下一同讨论基督教在现代化过程中所作出的积极贡献等事例。本研讨会的重要宗旨也在此,即通过比较和考察与日中韩的近现代史相关联的基督教的传播,对研究主题和方法论的相互启发和交流作出贡献。
在这里,笔者代表本研讨会的所有企划人员,想提出几个对东亚的基督教史及其展开过程的研究可成为共同前提的话题,拓展今后东亚基督教研究的视野。重点考察作为亚洲中心成员的日中韩三国在其过去的历史和现在对亚洲的认同感,以及在亚洲的近现代史上有力地开展过的重要的政治命题和基督教的关联性等。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中国都缺乏对“亚洲的认同感”,其原因在于中国一直为中华思想(sinocentrism)即世界中心意识所主导。从历史上看,对中国来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亚洲是周边,是自己直接或间接行使影响力的对象。而韩国,则不断重复了对于中国的独自性的确保和依赖性安定的追求。特别是近代以后,日本即“亚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被殖民化的经验,扩大了韩国对亚洲的否定认识。而且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欧取向在经历民族分裂和纠纷、6.25韩战(朝鲜战争)、参加越南战争等过程之后,逐渐表现为对亚洲的厌恶。所以韩国的“亚洲的认同感”是有极大局限性的。再看日本,它的近代化过程本身就是脱离亚洲脱胎换骨。“脱亚入欧”是日本的主要目标。在达成西欧式的近代化后,它虽然提倡了“大东亚共荣圈”,但是其所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并不是与亚洲的对等的联合和合作,而成为侵略、奴役东亚、东南亚诸国的代名词。日本依然没有完全回归亚洲。
总而言之,从结果来看,日中韩的亚洲认同感是极为不充分的。但是,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就是在基督教方面,日中韩也都是具有绝对分量的亚洲的中心力量,如何提高对亚洲的“认同”,日中韩三国自应努力,以承担各自应尽的责任。
二、日本、中国、韩国的基督教前史
耶稣基督的使徒多马远到印度宏传福音的事情已大体确定为正说。据三世纪初成书的外典《多马福音》(The Acts of Thomas),当保罗在小亚细亚地区传教时,多马到达印度并在那里传教。据16世纪开始在印度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们的报告,在印度西南部海岸马拉巴尔地区,有从使徒多马那里听到基督教信仰后将信仰告白延续下来的共同体。不仅如此,在印度东南部麦拉坡地区还发现了与多马殉教有关的遗迹。虽然不能将此证明为确切的历史记录,但是存在有关多马的印度传教和殉教形迹的告白传承却是不能动摇的事实。另外,也有一部分说法主张多马经由印度到达中国传播了基督教信仰。东汉时代连接印度和中国的交易之路来往频繁,如果考虑这一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历史,就不能完全排除以多马为领袖的信仰共同体接触到中国的可能性,不过多马直接去中国传教的说法本身应该说是难以证明的推测[注]参见A.F.J. Kljin, The Acts of Thomas: Introduction, Text, and Commentary,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3;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Bangalore: Church History Association of India, 2001; S.J. Anthonysamy, A Saga of Faith: St. Thomas the Apostle of India, Mylapore: National Shrine of St. Thomas Basilica, 2009; H.D. Souza, In the Steps of St. Thomas, Mylapore: Disciples of St. Thomas, 2009;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文芸出版社,1979版;韩国基督教历史学会编:《韩国基督教的历史1》改订版,首尔: 基督教文社,2011版等。。
在东亚,基督教历史的具体开端是7世纪唐朝时传到中国的“叙利亚的基督教”——景教。从记录上我们可以看到,公元635年以阿罗本为团长来华的传教团在中国大为流行,一直隆盛到9世纪唐朝末期。相传这时期景教还传播到与唐王朝往来频繁的韩国(统一新罗时代)以及日本,但是,以韩国为例,对于景教的传播,虽有可旁证的痕迹,可是因为没有可以验证的记录留存下来,所以至今未被认定为正史。随后,13世纪元朝时期复兴的景教即也里可温教,也让人窥见传到当时的高丽和日本的可能性。
1246年抵达元朝和林的罗马教皇的全权大使若望·柏郎嘉宾和1253年访问元朝的方济格会修士纪尧姆·德·卢布鲁克、克雷莫纳以及1294年同属方济格会的科尔维诺的北京宣教和1307年中国教区的建立是东亚与天主教交流的开始。可是,天主教在东亚的正式传教应是宗教改革之后,而且其第一个到达地是日本。最早开始在印度开展传教活动的耶稣会士沙勿略于1549年8月15日抵达了日本的鹿儿岛。从那以后至1580年代末开始受迫害为止,改宗的吉利支丹人数一度超过了20万人。可惜因受政治和外交的影响,日本的早期天主教受到巨大的镇压后急速地衰落了。而在中国,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和中国的第一次接触是1552年8月开拓日本宣教的沙勿略到达广东附近的上川岛一事。之后,罗马教廷任命Carmeiro为中国主教(1568年),开始了正式的传教。再后来,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成为了草创期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和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人物。最后看韩国。比起日本和中国,韩国接触天主教为时较晚。1592年壬辰倭乱(日本称此为文禄之役)时当时担任日本军队从军神父的Cespedes,作为神父第一次踏上了韩国的土地。当然他的目的并不在于向韩国人传教。在韩国天主教正式被接受是在18 世纪后期左右,当时韩国的学者们先从学问上开始研究起了在华耶稣会传教士所著的天主教书籍,后来在他们中间逐渐形成了自发性信仰共同体。虽然韩国接受天主教为时最晚,可是就其结果来看韩国的天主教发展得最为活泼。对蓬勃发展的天主教,朝鲜王朝开展了强有力的禁教以及镇压政策,造成了东亚最为剧烈的“血的历史”,即殉教、受难的历史。
关于新教,传教活动最早开始的还是中国。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受伦敦宣教会的派遣首次到达中国。他是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也是圣经翻译者,为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在日本,1873年政府废除了基督教禁令,由此西欧新教传教士获得了传教的自由,除了直接的传道活动以外,还通过教育机关开展了充满活力的布教活动。而在韩国,和天主教的传播相同,在接受新教方面韩国晚于中国和日本。1880年代初期,通过经由中国接受新教的韩国的改宗者和韩语圣经翻译者、以及为学习日本的先进文化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李树廷所进行的圣经翻译等活动,韩国开始了接受新教的历程,并开启了与新教的交流。后由1884年美国医疗传教士安连(H. N. Allen)的来韩和1885年教育传教士元杜尤(H. G. Underwood)、亚扁薛罗(H. G. Appenzeller)等的来韩,正式开始了新教在韩国的传教活动。
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基督教
关于近代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如果把它的概念和历史限定在宗教改革和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的时代,那么,其与基督教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性。先进的近代国家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扩大本国的影响力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并在各个地方竞相角逐扩张了殖民统治的领域。这种动向可以统称为近代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
近代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始于15世纪后半叶,16世纪时它的范围逐渐被扩大,虽然也曾有过一段平缓的时期,可是从17世纪至19世纪,甚或到20世纪中叶为止,全世界各大地域几乎都被卷进去了。因帝国主义的中心国家大都为西欧基督教国家,所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的世界宣教战略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动。基于这些,我们可以把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分为以下几种。
①天主教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其中心国家是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其扩张对象是非洲和亚洲的一部分以及中南美洲(拉丁美洲)的大部分。从时期上看为时最早,自15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殖民地的开拓,特别是从中南美洲的例子可以看到,其推行了史上最为残酷的殖民主义。
②新教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其中心国家是英国、荷兰、德国以及后进国家美国等。其扩张对象是北美大部分地区、非洲诸地区、印度和印度支那(中南半岛地区)、马来、印度尼西亚等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大洋洲地区等。在15、16世纪的新教国家中,荷兰、英国等强力推行海洋贸易的国家是它的中心。有一段时期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世界,所以英国还有“日不落帝国”的别称。
③非基督教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其中心国家是日本,其扩张地区是朝鲜半岛、中国以及亚洲的一部分地区。虽然是最后崛起且为时甚短的帝国主义,却是强大的殖民主义的典型。
从以上的区分可以看到,基督教的传教路线和近代帝国主义即殖民主义的侵略路线是相互重叠的。与此相反,日本帝国主义却表现出了颇为鲜明的“基督教恐惧症”,同样对外侵略、扩张,但对西方基督教帝国主义的极端警戒。
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走向终结。可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很多地方还残留着它们的痕迹。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与从前不同形态的帝国主义,这些地方仍然受着(霸权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这种观点上看,无须赘言,作为近代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受害者的韩国、中国与加害者的日本,日本在从与帝国主义关系视角看亚洲基督教史的方方面面,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四、“民族主义”与基督教
这里所指的“民族主义”,大体上是一个近代的概念。但有必要和古代犹太教式的民族主义做区别。并且也不是19世纪以后兴起的“锡安主义”(zionism)的近代的概念。还有,基督教有着从犹太民族中心的犹太教自我认识出发,追求成为世界万民主义的一种完全相反的思想路径。从这层意思来说,基督教天生拥有着与任何形态的民族主义都不能联手(融合)的特性。
而欧洲近代革命时期以后形成的民族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被转移到亚非地区的同时,转变成了“殖民民族主义”。为了更为合理地理解这些近代民族主义,笔者思考时习惯将其分为“攻击性民族主义”(offensive nationalism)和“防御性民族主义”(defensive nationalism)。若从大的框架上议论,可以说以近代亚非地区为中心的“殖民民族主义”和“防御性民族主义”是一脉相通的。因此,在亚洲,基督教和民族主义只能是敌对关系。因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即殖民主义者的专有物,而亚洲的民族主义必须和它对抗。但是,唯一例外的是,与不是基督教帝国主义的日本帝国主义相对抗的韩国的民族主义,它与基督教联合形成了“韩国民族教会”。这一点与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不同,它不止于韩国所受到的是“非基督教帝国主义”侵略的这种结构上的例外性问题,可以说它是显示“防御性民族主义”所拥有的“苦难的实际存在”和作为“十字架的宗教”的基督教有联合的可能性的事例。而在中国,民族主义则扮演了排击基督教的抵抗性力量。在日本,接受了基督教的信徒之间,则出现了基督教追随基督教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的现象,甚至还创造出了率先垂范实现国家目标的“欧洲型国家主义基督教”的形态。这种与民族主义相关的问题,也是研究日中韩的基督教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题目。
五、“社会主义”与基督教
社会主义在思想基础的特性上,只能和基督教处于对立的关系。尤其是亚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与帝国主义强烈对抗的特征,所以对被认为具有西方帝国主义背景的基督教只能愈加受到排斥。可以说,1945年以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和战争以及朝鲜政权和基督教相纠葛的过程,是细致地显示东亚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关系的一个事例。比起南部地区,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原来是基督教更为发展的地区。甚至有一段时期平壤还被称作“亚洲的耶路撒冷”。分裂以前朝鲜半岛基督教的多数,至少70%以上的信徒分布在北部地区。可是,南北分裂以后朝鲜的社会主义政权和基督教之间出现了源于政治理由的深刻矛盾。很多基督教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为数众多的基督徒为了避难而选择了南迁。可以想见,朝鲜战争时期朝鲜半岛的几乎所有地区都出现了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尖锐对立。结果,朝鲜的基督教衰退,变得有名无实;韩国的基督教则达到了确立强有力的“反共基督教”的自我认识及其传统的地步。
另外,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关系,也是理解有关亚洲基督教情况的关键之一。特别是,1966年以后的大约10年,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也是一个作为不同的历史事例值得研究的课题。总之,与世界史脉络的一般论不同,根据亚洲的特殊情况,特别是东亚这一地区形成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基督教的关系需要作具体而绵密的考察。
六、“资本主义”与基督教
资本主义的源流始于宗教改革以后的欧洲的变化。尤其是产业革命和西欧帝国主义的扩散牵引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今资本主义已经超越了对它的肯定及否定的一面,成了世界性价值取向的基调。换言之,也可以说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是一丝不苟地实践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对利润的追求是它的绝对命题,同时它还具有正当的财富分配和正义的实现等价值动机被保留的特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具有上述性质的资本主义,曾面临过作为对于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主义的抵抗而兴起的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及1930年代世界经济的大恐慌等危机。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一部分国家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成功,资本主义又开始力挽狂澜。之后,终于如中国的实用主义经济政策所代表的那样,不管其政治体制为何,采用一部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式的模式扩散到了诸多地区和国家。总之,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虽然也曾有过改革或改良的局面,但其影响力是持续性的。当然,无须赘言,现在也有极端的资本主义及拜金主义的弊害,还有只关心追求片段且无关紧要的利益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之泛滥等诸多需要警惕的要素。
总之,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思想置之不理,搭西欧帝国主义的便车来到亚洲的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紧密地拥有共同背景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由此派生出来的目前的问题,还有现在韩国的一部分新教大型教会和属于特定基督教系统的新兴教会团体,与这种极端的资本主义勾结在一起的事实。被称为“宗教产业”的这些集团的内部特性在于运用企业经营的方式,即根据确保投资和利润的逻辑,开展基督教的布道以及教会成长的计划。而且,这种“宗教产业”并不限于韩国,呈现出向一部分亚洲地区扩散的趋势。我将它称之为“新的帝国主义宣教模式”,这种说法或许有点极端,但是这种宣教模式正在被局部性地重演着。这是在日中韩之间也起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一种现象,也是人们关注亚洲基督教的现在和未来方面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
七、结论:新的“亚洲神学”的可能性
“亚洲神学”被理解为:把基督教和亚洲的宗教、思想、文化、价值等联系在一起,通过比较,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加上亚洲式特征的、从而形成具有亚洲特征的神学的一种努力。即,一直以来,在“亚洲神学”的研究方面,把通过“组织神学的思维移入”使亚洲传统的宗教基调和基督教神学的一部分表述一致起来,然后再宣布两者具有相同的内在思想等的工作成了它的重要课题。所以,比较佛教和基督教,或比较儒教和基督教,或发现与其他亚洲的宗教观念及文化类型相类似的基督教传承的工作显得格外重要。我们知道,通过这种研究,不止一次地连接上了儒教和东洋哲学中上帝的概念以及基督教的“哈努尼姆(上帝的韩译——译者注)”,佛教的“弥勒信仰”和基督教的救世主思想,韩国的民间信仰“郑鉴录”信仰和基督教的救世主信仰等等。总的来说,这些都是“本地化神学”的一个环节,其核心特征就是“适应主义宣教神学”。
基于这种批判性认识,欲重新设定“亚洲神学”的方案就是2017年明治学院大学基督教研究所开讲的“亚洲神学研究班”课程的开办旨趣。以下引用其中一部分内容来作本报告的结论:
在当前的起步阶段,本研究班将把东亚基督教史作为探讨的主要范畴,这种研究是以我们对历史认识的问题和超越它的实践性问题的关注为基础。这里所指的历史认识问题就是,作为少数宗教的基督教在过去是如何与如同佛教在真正的亚洲宗教的根基里广泛存在的“崇拜泛灵论的感性”以及“亚洲式的灵性”相处过来的,现在是怎样相处的,未来应该怎样相处下去等问题。
对于亚洲宗教的主流即已经习俗化了的宗教综合(syncretism),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在宣教上经历了很多挫折才到了今天。对于重新审视这些经验所提出的“欧美文明化” 型基督教宣教和一路支撑它走过来的神学及基督教伦理的问题,在亚洲的文脉中阅读圣经的问题等等有关基督教根本的问题群也是本研究班将要依次讨论的。这些问题是以前的亚洲宗教(比如禅宗的佛教徒)和基督教(神学家)之间所进行的“宗教间的对话”中是难得一见的主题,如要探讨这些问题,挖掘包括日本人在内溶化在亚洲人日常生活中的多样的宗教感性(包括政治和社会的感性)与基督教之间的接触面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这些是通过在教会的牧会现场、基督教学校的教育现场、工作单位等地方得到的具体经验、见识,和大家一起讨论才能看清楚考察对象本身性质的东西。对此本研究班试用广义的“亚洲文脉(Asian context)中的基督教”一词来把握,将其原有的问题点和基督教神学的诸概念相比较的同时,检讨过去的神学概念的有效性及无效性。为此,本研究班将重视参加者来自真实的生活感觉和诸般经验的报告以及围绕这些报告进行讨论的同时,也将重视目前面临的课题本身的发现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实践性检讨。本研究班的主要目标是,不急着在传统的组织神学的框架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换个角度,即把它看作“亚洲文脉”上的问题,然后当场通过“做神学”来找出解决问题的神学上的道理。本研究班的最终目标是积累从这些过程中所得到的神学思考的道理,探索“亚洲文脉的神学的可能性”,再把它告知世界(摘自“亚洲神学研究班的趣旨书”,2017年4月)。
——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