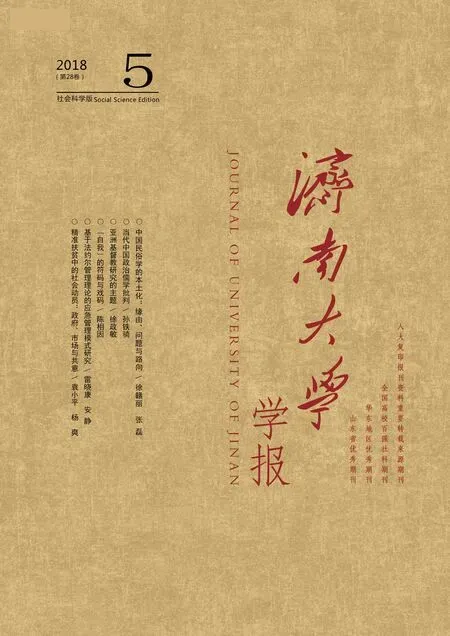日本近现代史与基督教*
山口阳一著,李剑锋译
(东京基督教大学,日本 东京 270-1347)
序
耶稣会以葡萄牙侵略亚洲为背景,于1549年以澳门作为基地开始了向日本宣教。1597年以后,弗兰西斯会以西班牙的马尼拉为立脚点对日本宣教。天主教会从1549年开始到1614年这一期间获得信徒37万人。这占当时推测的日本人口1200万的3.7%。在此期间,豊後、肥前、高槻等地也同时出现了切之丹(基督徒)大名,南蛮文化[注]南蛮指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南蛮文化主要指日本从战国时代到安土桃山时代的日本文化。这一时期由于与南蛮的贸易并加之天主教的宣教,西洋文化开始逐步进入日本。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日本文化与西洋文化的接触。(译者注)开花于日本各地。织田政权为要驱除旧的势力、控制战国时代的日本,也曾利用切之丹。但是统一了日本的丰臣政权以“神国日本”为由开始限制切之丹,其后的德川政权又将切之丹作为国害并宣布了锁国体制,从而彻底地镇压切之丹,利用镇压来达到其统治人民的目的。1650年除去潜伏于西九洲的切之丹之外,日本各地基本上根绝了切之丹的存在。德川幕府以镇压切之丹为名目,开创了寺请制度,改宗以及五人一组的制度,并且根据这些制度将佛教定位成为有助于统治的宗教。在1549年到1643年这一期间,共有宣教士301人,天主教会所掌握的殉道者人数为5500人[注]五野井隆史:《日本切之丹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2002年版。。
近代日本的基督教传教,是一场对抗拥有250年镇压基督教以及基督教邪教观念之历史的争战。鸦片战争后的1846年,西方开始了对中国的宣教,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对于琉球(冲绳)宣教的开始。之后,欧美列强正式展开向日本宣教是在日本国门被打开的1859年。1873年禁止切之丹的告示(高札)正式被撤,同时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地规定了“信教的自由”。基督教新教以克服基督教害国论为目标,自负地认为自己可以对近代日本作出贡献,成为 “报国的基督教”。
一、基督教的再次传入
天主教会的Girard神父根据日法修好通商条约在1858年来到日本,同时1861年于横滨、1865年于长崎建立了天主教堂。Petitjean神父在1865年3月17日“遇见”了浦上的隐藏下来的切之丹。根据Girard神父的说法,之后共出现了5万余隐藏的切之丹[注]F.Marnas:《日本基督教复活史》(Nihon Kirisutokyo fukkatsushi),东京:みすず书房,1985年版。 高木一雄:《日本天主教会复活史》,东京:教文馆,2008年版。。1867年,以基督教葬仪为契机发生了“浦上四番崩”(Urakami Yoban Kuzure 译者注)事件。1868年浦上的114位中心信徒被带到津和野、萩福山。第二年又有3300名村民遭到逮捕并关押在全国的21个藩。其中有1022人因为拷问而弃教,殉教者有664人,1883名信徒坚守了自己的信仰,最终回到浦上复兴了基督教[注]浦上小教区编:《上帝家族的400年》,1983年版。。之后在日本有很多村落的天主教会是以潜伏下来的切之丹的回归而复兴的。这一特征是基督教新教所没有的。1876年(明治9年),在琵琶湖以北有信徒1235人,以西有17200名天主教信徒。根据1941年的宗教团体法,成立了日本天主公教团。教团统理是土井辰雄,共有信徒12万人[注]高木一雄:《大正 昭和天主教会史》1~4册,东京:圣母骑士社,1985年版。。1878年(明治11年)的基督教新教信徒有1617人。1933年有249间教会,司祭276人(其中宣教士182人),信徒96736人。
东正教于1859年在函馆建立了圣堂,1861年尼古拉斯赴任。尼古拉斯在当时体制化的母国俄罗斯正教会里立下宣教的志向,这是十分罕见的例子。尼古拉斯不单单学习日本語,还努力学习日本历史、儒教、神道教、佛教以及日本的风俗习惯。同时,尼古拉斯也能阅读汉文书籍。这一点也是那些以英文为主并且教导英美学术的新教宣教士所不具备的特征[注][俄]尼古拉斯:《尼古拉斯所看见的幕末日本》(中村健之介译,东京:讲谈社学术文库,1979年版),《明治日本正教会》(中村健之介译,东京:教文馆,1993年版),以及《宣教士尼古拉斯日记》全9卷(中村健之介监译,东京:教文馆,2007年版)。。1872年尼古拉斯进入东京,并向全国各地派遣男性信徒传道者,1880年拥有信徒6099人,教会96间,讲义所236间,1898年增长到170间教会,信徒25231人。同年长老会、会众派、监理会(Methodist)一共拥有215间教会,信徒31245人。日本正教会同时以仙台为中心向东北以及关东和东海的农村地区渗透。但是,由于受到日俄战争以及俄国革命的影响,日本正教会的宣教在以近代化为目标的日本,由于因着前近代性而进入低迷期。1930年左右的信徒数是13000人,战争期间由于内部分裂从而没有办法根据宗教团体法设立教团[注]牛丸康夫:《日本正教会史》,东京:日本正教会教团,1978年版。。
基督教新教由于是从美国与英国传入日本,这比法国的天主教以及俄国的东正教在宣教上拥有优越性。为日本的近代化作出贡献的是新教,同时与日本的传统发生冲突的也是新教。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保障了外国人居留地的信教自由。翌年宣教士来到了长崎与横滨(神奈川)。其背景是1846年在伦敦结成的福音同盟会(The Evangelical Alliance)运动。先驱是美国的英国国教会的威廉,长老会的赫本(James Curtis Hepburn),改革派教会的S.R.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与Verbeck(Guido Herman Fridolin Verbeck)。赫本与布朗因为具有中国宣教的经验,所以可以理解教派教义中所存在的弊端。根据J.H.Ballagh记载,1872年日本人在横滨设立的最早的新教教会援用福音同盟的信仰9条作为教会信条。在长崎、横滨、东京(筑地)、神户、大阪(川口)、函馆等地的居留地开始了传道。很多武士阶级的青年人以学习英语为契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出身于曾与新政府军战斗过的旧幕府军番阀,是戊辰战争的战败者。在政治上失去了优越地位的他们,以精神层面上的贡献为目标,在传道与教育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今天日本的基督徒人口比例不到日本总人口的1%,然而在基督教教育机构学习的人数却是日本基督徒数量的10倍。铃木范久注意到基督教在近代日本社会、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2017年在《日本基督教史》(教文馆 2017年)上发表题为“日本圣经思想的广义文化史展开”中,铃木提到“日本基督教史的事件,是与这样的共同体(国家共同体与村落共同体)的交涉史。在这样的交涉中,基督教的历史就是被吞并,被怀柔,不得不屈服,也有一些微小抵抗的历史”(第372页)。 以下,在论及日本新教的同时,也涉及中国与韩国的历史。
二、近代日本的“国体”思想
平田篤胤(1776~1843)曾经读过利玛窦的《畸人十篇》,在抄译此书之后写作了《本教外篇》。在平田神学里,主宰神(大国主命)与来世信仰(灵界)十分明显[注]村冈典嗣:《耶稣教影响下的平田篤胤的神学》,见《增订 日本思想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40年版。。平田神学影响了草野的国学者,与水户学一同形成了尊王思想。明治政府根据尊王思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在参考欧洲基督教的基础上,根据以天皇为“轴心”的祭政一致的神道国家为导向设置了神袛官,在1871年设置了官幣社国幣社(国营神社)。在此之际,政府继续禁止基督教,促进废佛毁释,但此举受到了佛教界以及欧美国家的批判。1872年转换为教部省主导的国民教化运动。这里所教导的“三条原则”,即“体敬神爱国”,“明天理人道”,“戴皇尊旨”。之后,明治政府将皇室祭祀与神社的礼仪规定为非宗教,并定位于教派神道、儒教、佛教与基督教之上,这样便确立了国家宗教体制。
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是君主立宪制的钦定宪法,其核心内容是被神格化的天皇。“第1条,大日本帝国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统治”,“第3条,天皇神圣不可侵”。进而,规定了教育目标的“教育敕语”(1890年)赋予了日本臣民为国家与天皇而存在的义务,即“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政府在1900年将内务省社寺局分为神社局与宗教局,1913年宗教归文部省管辖,神社归为内务省管辖。这样一来就可以巧妙地将神社规定为非宗教,1940年神社局升格为神袛院。把为了天皇而战死的臣民也作为神灵(英灵)来祭祀的靖国神社同时也升格为官幣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根据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日本的“国体”之中没有了作为统合国民之象征的天皇。但是,回归于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教育敕语的愿望仍然残留在日本社会之中,在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没有实现的情况下首相与阁僚的公式参拜,元号(天皇历)法制化(1979年),日丸、君之代的国旗、国歌化(1999年),教育基本法的改正(2006年)等都在不断地进行,国家主义在缺少对于历史反省的历史修正主义的氛围中不断地增长。
三、从与“国体”的冲突到融合
大日本帝国宪法28条(1889年)规定了“信教的自由”,对此教会十分高兴。这件事意味着结束了自从伴天连追放令[注]1857年7月24日丰臣秀吉发布的禁止基督教宣教以及南蛮贸易的禁令。(译者注)颁布以来长达302年的对于基督教的法制上的禁止。但是,这种“信教的自由”是有附加条件的,即“只限于日本臣民不违背妨碍安宁之秩序以及臣民之义务”前提下的自由。半个世纪后,到神社去参拜作为现人神(あらひとがみ)[注]以人的形象显现出来的神。在日本主要指侵华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天皇。(译者注)的天皇这样的“臣民之义务”,没有一个日本人对此拥有任何悬念与质疑。圣公会的宣教士曾经警告过,这对日本将来的基督教是具有危险性的[注]塚田理:《日本圣公会的形成与课题》,东京:圣公会出版,1978年版。。翌年,“教育敕语”被颁布,1891年发生了内村鑑三的不敬事件。内村面对天皇署名的教育敕语发出了叹息,并没有按惯例深深地鞠躬而只是略微低了一下头。这样的不敬受到了井上哲次郎的批判,这也成为了“教育与宗教之冲突”论争的开端。这也是教育敕语所显示的天皇制国体与基督教发生的冲突。教会的反应也是各种各样。日本组合基督教会的金森通伦认为,对于皇室与祖先坟墓的礼拜并非宗教问题。另一方面,日本基督教会的植村正久直接地指出,根据基督教信教的理念即使是基督的肖像或是圣经都不是礼拜的对象,因此教育敕语也不可以成为礼拜的对象。井上哲次郎批判道,基督教重视的并非国家而是来世,宣讲博爱,不教导忠孝,并且建议基督教要成为爱国的日本式宗教。对此植村正久等人主张,天皇应该只停留在政治性权威,不应该拥有宗教性权威。但是到1899年,根据“文部省12号训令”,规定学校不可以实施基督教教育,这样“教育敕语体制”受到强化,基督教学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柏木义円认为,对于教育敕语以及天皇御真影(天皇的照片—译者)的礼拜只是有损于人的尊严的形式上的臣民教育,柏木用其一生持续地反抗教育敕语[注]有关内村鑑三的不敬事件,参见铃木范久:《内村鑑三日錄·一高不敬事件》,东京:教文馆,1993年版。有关“教育与宗教的冲突”论争,参见铃木范久:《教育宗教冲突论资料》,东京:饭塚书房,1982年版。。
接下来是对于战争的态度。近代日本自1874年出兵台湾以后,经常运用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并在1894年发动了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下同)。井深梶之助等人作为发起人,本多庸一作为会长组织成立了“清韩事件日本基督教徒同志会”。该会四处呼吁义捐,并向日本各地派遣教师支持战争。主张和平主义的贵格会也发生了分裂,无论是内村还是植村亦或是柏木,都主张日清战争的正义性。
然而,在日俄战争期间却出现了非战论。以国家独立为战争目标的朝鲜,换来的却是日本成为了朝鲜的主人,并且日本将赔偿金完全用在增强军备方面。内村对于自己曾经在日清战争期间主张的正义论进行了深刻而猛烈的反省,从而到了日俄战争期间才能够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并以圣经作为依据最终到达了绝对非战论的境地,柏木义円也一直坚持这一立场。但是,植村正久却支持日俄战争,认为战争也可以“保障世界的进步并带来和平”。当时主张非战论者只是少数,大多数人仍然支持战争。明治学院的Imbrie回顾两次战争说: “(非战论—译者)可以证明那些对于基督教的中伤,非但不能阻止战争,反而却可以有助于战争”。日本的基督教被认为是支持战争的宗教[注]山口阳一:《圣经与日本的非战论》,见《圣经与日本人》,东京:大明堂,2000年版。。另外,基督教在社会事业方面也被认为是日本的“良民”,被指望可以完善日本并不完整的福祉行政。
1912年(明治45年),内务省为了抑制国内高涨的社会主义趋势,意图利用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计划与教派神道以及佛教诸派一同协助国家政策的基督教界代表会见了内务大臣原敬。这被称为三教合同。与神道佛教一同受到邀请,这一点在整个基督教界被认为是受到了政府认同,因此得到了整个基督教界的欢迎。被认定为非宗教的神社神道不包括在内,文部省因为站在国民道德基础的教育敕语的立场上也不参加,但是净土真宗大谷派以政教分离为名目,对于邀请基督教加入三教合同一事十分不满,作为对于这种不满的表现选择了不参加三教合同。基督教界代表与佛教、教派神道的代表者们发表了共同声明:
我等发挥各自的教义,以期待扶持皇运振兴国民道德。我等期望当局者尊重宗教,融合政治、宗教以及教育问题,以此伸张国运。[注]元田作之进:《三教者合同与基督教》,桑名町:トラクト刊行会,1912年版。
这样,基督教所面对的与“国体”的冲突问题得到缓和,开始了以大正民主运动为背景的教新时代。代表人物有宗教哲学家波多野精一、惠泉女学园的河井道、领导大正民主运动的政治学者小野村林藏和富田满、圣洁教会的米田丰、基督教历史学家石原谦、植村正久的后继者高仓德太郎、无教会的塚本虎二、自由监理会的土山铁次、监理会的阿部义宗、神学家大塚节治、村田四郎、路德派神学家佐藤繁彦、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社会活动家贺川丰彦、小崎弘道的后继者小崎道雄、法理学者中岛重、社会党委员长河上丈太郎、政治学者南原繁等人。
大内三郎对于从明治到大正的时代变化,如此评论道:“明治时代的基督徒不可能离开 ‘国家’而单独地思考基督教信仰。或者说这些基督徒们也不能忘记在儒教式的训练与教养的氛围中孕育出来的武士道。这样一来,进入到大正时代的他们,即使是很少,但也吸收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空气,他们将自己归属于为要解决作为个人而寻求基督教的这样一种人生追求派。而且,受到教义主义的影响,将广义的神学研究提高到严密的神学(学术学问)。这些人持有这样一种神学态度”[注]大内三郎:《日本基督教史》,东京:日本基督教团出版局,1970年版,第443~444页。。
在大正民主运动时期开花的基督教社会事业的理想,在1928年的日本基督教联盟的“社会信条”中有鲜明的表现。“我等将上帝尊崇为父亲,将人类作为自己的兄弟而相亲相爱。将基督教的社会生活作为理想,祈祷实现基督所显示的爱与正义与和平”。而且,揭示着如下的主张(摘录):
人权与机会的平等,人种与民族的无差别待遇,婚姻的神圣,女子教育,对于儿童人格的尊重,制定星期日为休假日,废除公娼制度,促进国民的禁酒运动,完备最低薪金法,手工业法,社会保障法,国民保险等立法,鼓励有关设立生产以及消费者的协同组合,设置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协调机构,制定合理的劳动时间,制定所得税与遗产税的高率累进法,确立缩小军备,仲裁裁判,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
然而这些理想,却被带进到迅速展开的战争的洪流之中[注]土肥昭夫:《生存在天皇制狂奔时期的基督教》,富坂基督教中心编:《十五年战争时期的天皇制与基督教》,东京:新教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战争与福祉、理念与现实是极端的两个方面。大正民主运动时代的社会事业的萌芽,被“大东亚战争”所践踏。
四、与中国及韩国关系之中的基督教
马礼逊的《神圣天书》(1823年)成了对于同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宣教的准备。郭士立在漂流民[注]一般指遭受海难而漂流到其他地方的海难受难者。但是在江户锁国时代的日本,不仅指这些漂流到其他国家的渔民,同时也指这些被同化、将外国的知识带回日本的人。(译者注)的协助下翻译了《约翰福音之传》《约翰上中下书》(1837年),这也是基督教信教最早的日本语圣经。之后的日语圣经也是借用汉语圣经的词语。初期的基督教也同样是通过中文文献被带到日本的。小泽三郎介绍了谍者伊泽道一在1872年3月的报告“藏书目录”中记载的汉语基督教书籍135种[注]小泽三郎:《幕末明治耶稣教史研究》,东京:日本基督教团出版局,1973年版,第156~158页。,1875年设置在千叶县的法典长老教会的汉语教科书88种113册,圣经18种26册[注]山口阳一:《法典长老教会与〈威斯特敏斯特小教理问答〉最早的日语翻译》,载《基督教神学》23,东京:东京基督教神学校,2011年版。。
但是,之后的基督教基本都是通过欧美传入日本的,日本的基督教也开始脱离亚洲进入“脱亚入欧”之路。日本开始了同化并非大和民族的琉球人与爱努人,不久就企图将台湾与朝鲜作为殖民地开始同化。在进入台湾开始殖民的2年之内就有超过2万人(日本人来到台湾者—译者),日本基督教会等各教派开始了面向在台湾的日本人传道。
1883年,李树廷[注]原文没有注明,但是应该是朝鲜人。在东京接受了安川亭的洗礼,同时记载到第三回全国基督教信徒亲睦会中有人用朝鲜语进行信仰告白的祈祷。1885年马可福音以韩文出版,监理会的Appenzeller(Henry Gerhard Appenzeller)与长老会的Underwood(Horace Grant Underwood)开始学习朝鲜语,在东京开拓了新教的朝鲜传道之路。不久,在朝鲜被强制合并的时期,日本的基督教会也迎来了“成长期”。另一方面,朝鲜的基督教会在日本侵略之中迎来了1907年开始的“平壤大复兴”。在强制合并的1910年,朝鲜有信徒198974人,是日本同时期基督徒的2.5倍。日本政府为要统治朝鲜,试图对以独立运动为中心的朝鲜基督教采取怀柔政策,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接受了这项任务。推动这项任务的是海老名弹正的弟子、京城学堂长的度濑常吉。他在《关于朝鲜传道的宣言》中如此描述:
此时朝鲜并入我国,八道一千两百万同胞亦开始与我等一同沐浴皇恩。……向我等新同胞传扬福音,同时也可以结出精神同化之果实,在此我等决定朝鲜传道之大事,向朝鲜派遣精通朝鲜事情之代表,以此期望此天人共期之大业。如若有志之赞同,必尽吾人之微力。[注]《日韩基督教史资料1876~1922》, 东京:新教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
实际上这样的传道,得到了朝鲜总督府与大隈重信、涉泽荣一等政治家,以及岩崎、三井、住友、古河等财阀的援助,以对朝鲜人的同化为目标的。
无论是日本亦或是朝鲜的教会,都是在与民族心的融合中成长的教会,然而日本是在顺境之中,朝鲜却是在逆境中成长。对于与民族心的协调,日本是以国策协力,朝鲜则是以独立运动的形式运作的。1925年,在京城(汉城—译者)创建了祭祀天照大神与明治天皇的朝鲜神宫,神祠的数量达到1930年231间,1935年324间,1940年702间,1945年1141间。强制神社参拜在1935年也导致矛盾激化,1938年日本基督教会大会长的富田满说服朱基撤等牧师进行参拜。“诸君的殉道精神是伟大的,然而什么时候日本政府放弃基督教强制对于神道的改宗,还请您提示具体的证据。这只不过是国家向作为国民的诸君要求进行国家祭祀而已”[注]《福音新报》,1938年7月21日。。但是朱基撤等牧师以违反第一戒为由拒绝参拜神社的主张没有任何让步。因为拒绝参拜神社,有200间教会被关闭,2000人被捕入狱。是年的第27次朝鲜耶稣教长老会总会促使决意参拜神社的议员们参拜平壤神社。
日本基督教会的植村正久在1902年到1920年对台湾进行10次传道旅行,从1909年到1923年9次访问朝鲜和满洲,1921~22年进行3次中国内地传道。
满洲传道会的创建是1933年左右。不久传道会被改名为东亚传道会,传道的范围扩大到中国全部地区。根据1941年9月的报告书,有教会、传道所79间、传道者109人(其中日本人30人),开教以来的受洗者2349人。山口高商的助教授福井二郎,接受呼召辞掉了工作,从1935年开始赴满洲、热河和承德等地。他在称为“我的山”的山上每天晨祷,与中国的弟兄姐妹每天一起学习圣经,一同祷告。在中国考察期间看到福井每日生活的泽崎坚造,辞去京都大学助手的工作,投身于热河传道。但是,热河是日本军展开三光政策与无人区政策的最前线,有5万5千人在此遭受屠杀。国民教化机关的协和会与传道者们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在考虑最初的中国人归信者王玉新与战后被(国民政府)[原文没有提及]枪杀的医生刘艺田等对日协助者的时候也不应该简单地归为美谈[注]渡边祐子,张宏波,荒井英子:《日本的殖民地支配与“热河传道”》,东京:いのちのことば社,2011年版。。
1937年侵华战争开始之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的矢内原忠雄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国家之理想”,论及到对于中国大陆的侵略是反和平与反正义的,最终势必会将日本带上灭亡之路。同时在藤井武的纪念大会上发言,讲到“为了发挥日本之理想,势必要先将此国埋葬”。由于矢内原的反战言论,他被赶出了大学。
五、日本基督教团的战争协力与神社参拜
1938年,大阪宪兵队向大阪府的教会与基督教主义学校送去13条询问状,询问到底是跟随天皇还是跟随上帝。1940年救世军司令被怀疑为特务而被逮捕。救世军也被更名为救世团。同年贺川丰彦也被涉谷宪兵队检举。1941年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耶稣基督之新约教会的43人和普利茅斯兄弟会的6人也受到检举。1942年日本基督教团的旧圣洁教会的牧师们一并在全国受到检举,加上追加检举共有131人遭到逮捕,其中71人被起诉,14人受刑,7人死在狱中。其理由是基督再临信仰有违治安维持法[注]《日本基督教历史大事典》,东京:教文馆,1988年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中,日本的新教作为日本基督教被联合在一起。1941年的日本基督教团的成立是日本新教史上最大的一个事件,在战争协力与偶像崇拜方面也拥有最为恶劣的过去。“日本基督教团规则”的第7条“生活纲领”中记载到,“跟随皇国之道,贯彻信仰,各尽其责,扶翼皇运”。这并非是“遵从圣经”,而是“跟随皇国之道”,是致命性的。教团统理富田满在翌年期待,新的教团可以“贯彻信仰,跟随皇国之道”,在敬畏主的同时也可以参拜伊势神宫。
1942年10月的“日本基督教团战时布道指针”中将大东亚战争定位为“圣战”。“尤为本教团在此大战爆发之际成立,此正为颂赞天翼,克服国家非常之时局,不愧蒙天父之恩召”。也就是说日本基督教团是为了大东亚战争得到胜利,接受上帝呼召的结果。布道指针纲领的第一项中规定,“贯彻国体本意,向大东亚战争的完全胜利迈进”。1943年秋以后,日本基督教团通过全国教会募款72万日元,向海军和陆军各献纳2架战斗机。
日本基督教团也向各教会指示,实施宫城遥拜与国歌齐唱等国民性礼仪。这已经不再是“神学”,而是努力地确立“日本教学”了,创作了与战时相迎合的《兴亚赞美诗》,产生出“殉国即殉教”这样一种日本式的基督教。何谓宫城遥拜,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朝鲜半岛或是中国的日本人,也要面向皇宫进行礼拜。“殉国即殉教”是将在“圣战”的大东亚战争时在战场上战死定位为殉教的理论。赞美诗委员会编辑的《兴亚赞美诗》(1943年)中有这样的一节。
出生在荣光之神国,尊崇敬拜天皇,日日精进,认识天神(第4首第1节)
1944年的复活节发表的《日本基督教团致大东亚共荣圈之基督徒的书简》,向亚洲国家的教会这样写道,“能够真正指导世界拯救世界的,是冠居于世界之首、万邦无比的我日本之国体,这一事实希望在信仰中不断地被确认,被信赖等”。在战局不断恶化之中,1944年8月18日发表了《日本基督教团决战态势宣言》,其云:“值此之际,身负皇国使命,本教团为皇国之必胜而崛起,坚决灭敌,以安吾辰襟”。辰襟指的就是天皇之心的意思。教会宣誓忠诚于天皇,称大东亚战争为圣战,胡乱地将殉国视为殉教,这些都是日本基督教会的重大错误。
六、战后的教会
在战争中,广岛流川教会变成了被美国原子弹烧毁的钢筋水泥的残骸,冲绳首里教会的教堂(旧监理会)也在美军登陆战之中成为遗迹。在全国有482间教会经历了空袭,以不同的形式经历了这场灾难[注]戒能信生:《从教势看到的日本基督教团的50年》,见《日本基督教团50年史的诸问题》,东京:新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惨败的战争结局,无论对日本亦或对日本的基督教会都是一场毁灭。
战后最初的统理指令《教团与终战》中记载了深刻的忏悔:“我等在此深刻忏悔,毕竟我等缺乏精忠报国之力,今后身负荆棘为新日本之建设贡献我之力,在此宣誓”[注]《日本基督教团资料集》2,东京:日本基督教团出版局,1998年版,第276~278页。。然而这并不是在上帝与人的面前,对基督教的偶像崇拜与协助战争的悔改,而是忏悔自己没有更好地侍奉天皇以至于战争失败,从此宣誓尽力建设新日本来报效皇国。
在战争期间支持战争,在战后建设新日本,目标虽然改变,然而“报国”的基督教没有任何改变。虽然这一开端在战后并不轻松,然而也还是宣告了一个疯狂时代的结束。以联合军最高司令部(GHQ)的占领为契机,民主主义之风又一次吹回日本,时局变换也迎来了日本基督教的时代。根据以战后民主主义为基础的日本国宪法与教育基本法,基督教宣教与教会形成也得到了从没有过的优越条件。贺川丰彦参与战后日本内阁的重组,开始了推动总忏悔运动。宗教团体法在1945年12月被废止。实施宗教法人令,日本基督教团也开始了新日本建设基督教运动(1946~1949年)。
旧的教派也开始从日本基督教团中纷纷脱离出来。而且还有更多的欧美宣教士来到日本,其数目是1947年36个团体。在战争时期因为出征,征用或是疏散而闲散下来的教会也有很多人重新利用起来。在1947年4月根据新的宪法展开的最初的众议院与参议院的选举之中,参议院有10人、众议院有21人的基督徒议员当选。5月富士见町教会的长老、社会党的片山哲开始组阁,文部大臣森户辰男等6人与众议院议长松冈驹吉也是基督徒。新制东京大学总长矢内原忠雄也对于青年人有很大的影响。
作为日本人320万人死亡、亚洲有2千万人牺牲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教训,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国宪法,在第9条中规定“放弃战争”。这是一份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遗产,也是日本对于亚洲的承诺。
1945年12月,根据联合军最高司令部(GHQ)的“国家与神道的分离指令”,国家神道体制被解体。安放御真影的奉安殿也被破坏,海外的神社也被破坏,同时以靖国神社为首的神社也成为了宗教法人。根据宪法第20条,日本否定国家神道体制,实行政教分离。因此,日本的基督教会,第一次获得了作为基本人权的信教的自由。
东京大学总长南原在1946年2月11日,立足于天皇的人间宣言发表了“新日本的文化创造,建设道义国家日本”的热情洋溢的讲演。南原承认天皇制的维持,但是因为战争责任问题而要求天皇退位。另外,赞同放弃战争,但是考虑到自卫军(自卫队—译者)的维持与将来的国际贡献,并不能只是围绕着日美安保条约的讲和,而应该主张永世中立与全面讲和。只是围绕着日美安保条约的讲和并非是全面讲和,这是残留至今的课题。教育基本法应该修改国家支配教育从而培养天皇之臣民,“教育不可服从不当的支配,必须对国民全体直接负责”(第10条第1项)。但是,在2006年修改的教育基本法却加强了行政对于教育的支配。
战后的新教发展成为两极化,即以日本基督教团为中心加盟到日本基督教协进会(NCC)的战前的各教派,与日本福音同盟(JEA)内结集在一起的“福音派”的集团。基督教新教的信徒数,从1948年的20万人增加到1968年的40万。70年代日本基督教团的教势开始停滞,但是福音派却在增加。福音派在1960年成立日本基督教新教圣经信仰同盟(JPC),1965年福音派的圣经学者结集在一起,发行了新改译圣经,1968年创建日本福音同盟(JEA)。日本基督教团在1967年发表对于战争协力这一罪责的战争责任告白,包括福音派在内的还参加1970年代的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法案运动。1990年的天皇参加的大尝祭[注]天皇即位后参与的第一次神道教祭奠。(译者注),标志着战后的国体维持的回归点。这也可以理解成为是日本民族主义对于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回应。1990年日本基督教会对于曾经劝说朝鲜长老教会参拜神社进行罪责告白。新教的信徒数在1990年代是60万人,天主教会至今超过40万。
在迎来战后50年的1995年前后,福音派诸教派相继发表在战时下的罪责告白。但是,这一时期也是以自己国家为中心的历史修正主义等保守化开始胎动的时期。
结语
关于日本的近代史与基督教,我们考察了被日本“吞并,怀柔,屈服,也伴随着微小的抵抗运动的足迹的历史”(铃木)。战后史,也可以说是这种自觉与改革的历史。战后的日本根据与美国的讲和,并没有与中国、韩国、北朝鲜(朝鲜)进行全面的讲和,换句话说到现代为止仍然没有改变“脱亚入欧”,现在却出现了以历史修正主义为根基的攻击性言论。虽然这么说,但是自从“韩流”以后,从韩国来日的宣教士达到1480人,在日本的中国人有70万,韩国人45万,在日本用韩国语进行礼拜的教会有212间,中国语教会63间[注]《第6回日本传道会议日本宣教170》,200项目编辑:《数据日本宣教的今后-基督教的30年以后》,东京:いのちのことば社,2016年版。。日中韩的基督教立足于东北亚汉字文化圈的200年以来的交流史,期待可以开创新的关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