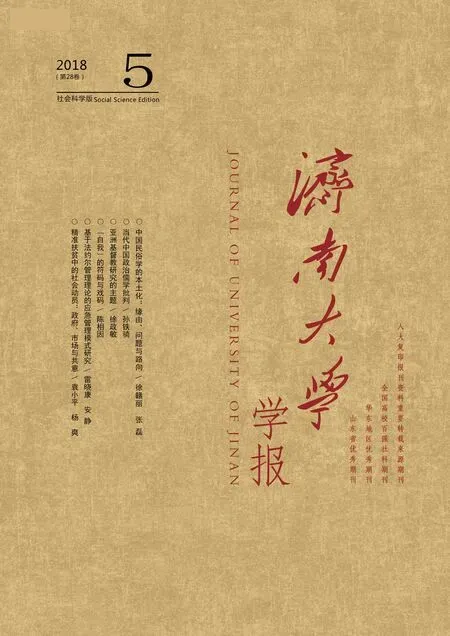中国近现代史与基督教*
陶飞亚
(上海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4)
引言
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与基督教的关系中,基督教与中国的相遇算得上源远流长。第一次是景教在唐贞观九年(635),波斯人阿罗本(Alopen)沿着丝绸之路跋涉5000多千米到达长安传教,一度得到唐代皇帝的支持,曾经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但在唐会昌五年(845),因唐武宗下令查禁佛教及其他宗教,景教跟着销声匿迹。第二次是在元代,马可·波罗1275年来中国以后曾发现一些蒙古部族有景教团体存在。1289年罗马教廷派遣的方济各会神父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来中国,1294年到达北京,逐渐建立起3万多人的天主教教团。1368年明朝建立,天主教随蒙古人退出明帝国。到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第三次来华时,已经是借着大航海时代的技术从海路络绎不绝地进入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3年到广东,1599年进入北京,获得朝廷永驻北京传教的许可。在利玛窦于1610年去世时,中国大约有2500名天主教徒。1644年清廷进入北京取代明朝之际,全国天主教徒大约有10万人。这一次天主教并没有随着明朝一起灭亡。聪明的耶稣会士因为历法、医学、火炮和其他科学知识获得清朝皇帝的欣赏,使得天主教继续发展。但最终因“礼仪之争”(17—18世纪),导致从康熙帝晚年起长达100多年的禁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再次中断。直到西方帝国主义向远东殖民扩张的时代,在宗教运动与基督教背景和非基督教背景的帝国主义侵略的交织和断裂中,基督教开始在中国以与日本、韩国不同的道路逐渐生长起来。
一、晚清基督教之传入与立足
传教士再度“合法”进入中国是和宗教上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纠结在一起的。美国学者赖德烈认为1840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虽然没有明确把在华外国人和中国人信教问题列入条款之中,但实际上已间接包含这些内容[注][美]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陈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5页。。此后,1844年7月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正式出现美国人可以在中国五口买地建立教堂的条款[注]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4页。。1844年10月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准许法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自由传教[注]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2页。。道光帝在1846 年2月颁布弛禁上谕,承认天主教“劝人为善”的性质,对民人信仰天主教“准免查禁”[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页。,新教由此得到“一体保护”。1851年9月两江总督陆建瀛拟定的《内地民人习教章程》规定:“内地民人习教为善,其设立天主,供奉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免其查禁。”但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仍是非法的[注][美]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雷立柏等译,香港:道风书社,2009年版,第197页。。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条约体系中,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获得三个有利条件:一是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地建堂传教,二是中国民人可以公开信仰基督教,三是往日被清政府没收的“教产”得以发还[注]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年版,第276页,第276页。。参与谈判的法国传教士还通过不诚实的手段,在条约的中文版本中加入了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买地建堂的文字,为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取得了拥有产权的立足点[注]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年版,第276页,第276页。。著名的西方中国基督教史学者狄德满说:“条约规定向外国人开放更多的港口,其中包括中国腹地长江沿岸的几个港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条约,尤其是法国条约,既规定外国势力可以保护传教士和教徒,也给宗教带来了更大的自由。换句话说,传教士更紧密地、更具侵略性地与帝国主义融为一体,渗透进中华帝国。”[注][德]狄德满:《基督教与现代中国社会历史——东西方学术理路的态度变迁》,载吴梓明、吴小新主编:《基督与中国社会》,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6年版,第32—33页。近代中国外交家顾维钧认为,这些条约表明了“中国始完全承认耶稣教士有传道及劝人信教之自由矣”[注]顾维钧:《外人在华之地位》,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74页。。民国时期的研究者伍朝光曾评论说:“不能否认宽容条款在改变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身份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自此中国就被剥夺了不实行宗教宽容的主权。”[注]Chao-Kwang Wu, The International Aspect of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30, pp.24-25.因此,最初“自由”传信基督教的权利是列强通过武力强加给中国政府的。这最初受到传教士们欢呼的“条约权利”后来成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原罪”,也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反教的永远的理由。
这个时代的传教运动时多时少地伴随各类教案冲突的发生。翻检清政府总理衙门的档案可以发现,其中民教相争的民事案件占据了大多数,它们一般都在列强施压和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干预下,经由外交与司法因素的综合考量得到解决,影响较小。但也有起源于民事争端变为刑事冲突的教案,如1898年原本因双方争夺庙产的河北冠县梨园屯教案则为义和拳组织兴起的源头。刑事案件视其发生的地点与时机有时有巨大的影响,如1870年6月21日因谣言失控导致19名外国人和数十名中国人丧命的天津教案演变为中外冲突的严重危机,1897年11月1日的山东巨野张庄教堂杀毙两名德国传教士一案更被德国作为强占青岛的借口。在民族危机、经济危机和清廷内部政治危机叠加情况下,原本星星点点的山东内地民教争端也演变为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这些冲突对清政府和基督教会都是不利的。从清政府的立场看,国家治理基督教应该以控制冲突、维护自身统治为目标;从基督教会的利益出发,是要使得在中国传教和民人信教能得到官府的保护。晚清官方经历许多挫折才摆脱此前禁教传统的惯性,认识到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传播所产生的多种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也看到了基督教及其现代性事业对中国的助益。而基督教也为了自身利益逐步适应中国“政主教辅”的传统,约束传教士和教徒行为,向官方喊话并与官员保持接触,使其对西教从怀疑不安转向习以为常。官方最终以务实的态度,把教会作为治理议程中的一个参与者而尽量减少列强插手,在保护正常信仰的同时建立规范民教关系的治理制度方面,达成某种妥协与合作,基本上缓解了长期困扰晚清政治的基督教问题。晚清最后10年,基督教引起的教案,已不再是清廷政治议程中的重要问题。
这个时期的天主教由于有明末清初以来的传教基础,发展相对迅速。到1865年中国境内已有22个教区[注]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81页,第281、283页。。教宗良十三世(Pope Leo XIII)于1879年又将中国全境划分为五大传教区。上海及北京成为天主教主要的教务中心。此前已经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多明我会、奥斯定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继续派遣神职人员来华。法国“保教权”也吸引了更多新兴修会如米兰外方传教会、圣母玛利亚圣心会、圣言会等的传教士相继抵达中国传教区[注]Columba Cary-Elwes, China and the Cross: A Survey of Missionary History, New York: P. J. Kenedy & Sons, 1957, p. 203.。20世纪初,美国等欧洲以外国家的天主教传教士也逐步来华,但数量较少,美国天主教会大量输入传教士至中国,要在一战结束之后[注]Thomas A. Breslin, China, American Catholicism and the Missionar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0。1903至1904年间,来华外籍传教士达到1 110人[注]金鲁贤:《金鲁贤回忆录:绝处逢生1916—1982》,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中国神职人员的数量为534人,1907年时天主教徒人数增长至103万8千余人[注]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81页,第281、283页。。与新教差会和人员在中国的分布相比,有更多的天主教传教士散布在远离中国沿海沿江城市的偏远地区。1933年,中国天主教徒约有245万。到1949年时,天主教信徒大概有300万人。
基督新教直到1807年才由英国伦敦会派出的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马礼逊在广州等地的活动始终处于非法状态。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获得条约保护,新教在中国才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相比天主教来说,新教传教士快速增长。1860年10月《天津条约》签订后,另一个新教传教士活动扩展的时期开始了。首先是老的差会在发展。此前已经进入中国的英国伦敦会、英国长老会、英国圣公会、英国的卫斯理宗监理会(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英国循道会)、美国长老会、美国浸信会、美国圣公会、美国北部的美以美会与南部的循道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of the Southern States)等差会从中国沿海沿江向北方和内地拓展传教活动。其次是新的差会也陆续进入中国,最著名的是由戴德生(Hudson Taylor)于1865年创立的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注]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Chichester,West Sussex;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2012, pp. 68-69.。到1893年时来华新教男女传教士已经达到1324人[注]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p.52; China Mission Handbook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p.325; [美]莫菲特(Samule Hugh Moffett):《亚洲基督教史》(第2卷),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83页。。基督徒在人数增长方面则比较缓慢,到1907年新教来华整整一个世纪时,新教信徒虽达到178000人,却仍不及95万天主教信徒的五分之一。至1912年,据《教育杂志》统计:在华外国新教男传教士有1836人,加上未婚女教士和教士夫人,共计4628人。此外,还有中国人担任教士和教会学堂教员的男女教会工作人员,共计13679人[注]《调查:在我国之基督教士数》,《教育杂志》,1912年第3卷第12期,第127—128页。。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马礼逊认为的到19世纪末中国会有1000名新教教徒的预期。
尽管基督教信徒在中国总人口占比中仍然微不足道,但它在晚清社会的现代事业中却拥有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影响力。相比新教传教士对社会改良活动的热情,天主教传教士比较消极。新教传教士入华是要来改造社会的[注]Rev. Bertram Wolferstan, S.j.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From 1860 to 1907, London and Edinburgh: Sands & Company, 1909, p.272,273,274.。他们在中国创办的西式学堂,为在中国延续千年的科举考试体制外的知识输入和传授打开了大门。新教出版机构大量印刷、发行的各类人文科学知识书刊,也成为传播西学的有力渠道。19世纪90年代,同文书会(广学会)的一些出版物的发行量达到数万册。1898年,广学会在一份报告中说:“全国各地的中国学生纷纷请求传教士教他们英语、法语、德语或一些西学。因此,传教士与各地知识阶层之间的友谊代替了憎恨与敌对。……”[注]同文书会:《第十一次年度报告,1898年》,第11页。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于1869年被清政府聘任为北京同文馆教习,1898年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于1864年翻译的《万国公法》是近代国际法学体系第一次输入中国[注]关于丁韪良在华生平参见氏著:《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A Cycle of Cathay),沈弘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从1868年起被聘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从事教育与介绍西学的活动,在28年的任期内口译各种科学著作达113 种,以至被传教士们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另一位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74年开始创办《万国公报》,刊译了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在近代维新派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深远[注]参见李天纲编:《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1895年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林乐知和中国人蔡尔康合著《中东战纪本末》,期望中国吸取教训,以求变化而自强[注](清)沈毓桂:《中东战纪本末序》,《万国公报》,1896年第90期,第21—22页。。最为活跃的应该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除了鼓吹改革,与清廷高官多有来往和建议外,维新运动之前李提摩太应李鸿章邀请赴天津出任《时报》主笔,撰写大量鼓吹变法的文章[注][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196页。。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李提摩太与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李提摩太曾聘用梁启超担任他的私人中文秘书,梁启超则撰写了大量影响很大的时论文章。梁氏《饮冰室文集》中许多热情宣传泰西政治经济制度的文章,都有李提摩太影响的痕迹[注]Z. K. Zia, “Timothy Richard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Chinese Recorder,Vol.,no. (Aug. 1935), p. 505.。在一定意义上,传教士的教育、文字活动激发了部分知识分子、官员向西方学习和改革中国制度的积极性。作为传教士,他们的落脚点还是希望为基督教传播营造有利的社会氛围。当然,维新运动失败之后,基督教影响力下降。但在晚清新政时期,基督教又重新活跃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清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基督徒而不再是传教士走在了前列。当时梁启超从日本传回中国的关于国家和宗教问题的理论,以及政教分离、信教自由的基本原则[注][法]巴斯蒂:《梁启超与宗教问题》,载[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1910年冬,清政府准备实行宪政,中国信徒许子玉、诚静怡、俞国桢及刘芳等人在北京发起宗教自由请愿会。这一请愿活动虽因清廷垮台未见成果,但却影响了民国立法。
对晚清最后10年的反清革命,传教士内部有分歧,传教士与中国基督教徒也有分歧。在中国生活的数以千计的传教士对这场革命是有感觉的。1901年耶士谟(William Ashmore) 谈到基督教的宣道与发行报刊杂志的功能,使得学生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注]Rev. William. Ashmore: “Permeation of the Asiatic Mind with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以下简称CR),(November 1901)pp. 534-535.。多数传教士希望与革命保持距离。季理斐给《教务杂志》的编辑写信“警告”说传教士不要成为“中国熟人的工具”,并因此损害与当局的关系[注]D. MacGillivray: “To the Editor of ‘The Chinese Recorder’”, in CR,(December,1902),p. 624.。但乐灵生(Frank Rawlinson)却在文章中赞同和期待中国“革命”的到来[注]Rev. Frank Rawlinson, “A Study of the Rebellions of China”, in CR,(March 1905),p. 107.。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昌首义之前,孙中山的名字已经在新教《教务杂志》上出现了三次[注]“Our Book Table”, in CR,(December 1894),p. 601;“The Month”, in CR,(June 1908),p. 355;“The Month”, in CR,(July 1908),p. 411.。还有三次报道涉及到革命党人的活动[注]“Diary of Events in the far East”, in CR,(August 1903),p. 421;“Diary of Events in the far East”, in CR,(September 1903),p. 475; “Diary of Events in the far East”, in CR,(December 1905),p. 652.。在革命爆发并取得成功后,《教务杂志》1911年11月的社论中写道:“革命情绪能够瞬间爆发而且遍及全国,这让我们感到惊叹;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人们长久以来所积累的不满。……”[注]“The National Assembly”,in CR,(November 1911),p. 613.他们认为,革命的到来和清廷的倾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种族的对抗,但更多的则是“西方思想和现代政府的理论经过长期作用后爆发的体现”[注]“The Abdication”,in CR,(March 1912),p. 125.。有意思的是,传教士们某种程度上把革命看成是自己工作的成果[注]“Retrospective”,in CR,(January 1912),pp. 1-2.。当时中国的政治家们从孙中山、袁世凯到黎元洪等无不认为这场革命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关[注]王静:《“觉醒的中国”: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第24页。。
尽管传教士充其量是 “口头革命派”,但中国基督徒在这场革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费正清指出早期革命的鼓动者是基督徒[注]John K.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Harper & Row, 1987, P.138.。柯文说:“几乎和被忽视了的基督教对中国早期改革的影响一样,基督教在初期革命运动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孙中山1884年在香港接受洗礼是人所共知的。香港兴中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即世纪之交广州香港地区的早期革命者的核心人物,也多是基督徒。”[注][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陆皓东、黄吉亭、曹亚伯、刘静庵、殷子衡等人宣传了革命思想,积极组织和参加革命活动,有些人献出了生命。如黄花岗72位烈士中就有24位是基督徒[注]王利耀,余秉颐主编:《宗教平等思想及其社会功能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孙中山把自己一生的斗争始终与上帝的呼召和耶稣的精神联系在一起[注]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推翻清朝当然不是基督教会的任务,而是民族革命的任务。但中国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要来得重要。唐日安(Ryan Dunch)指出福州地区基督徒深入和广泛地卷入了当地的社会和政治变动,在晚清新政成立的咨议局中和1911年的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基督教仪式也影响了辛亥革命后当地一系列如旗帜、歌曲等象征中国国家身份的仪式建构[注]Ray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总之,晚清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和行动,与在日本、韩国的类似之处是他们各自参与社会转型中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不同之处是中国基督教在晚清改良运动中一度影响较大。清政府与教会的关系也与日本政府一直试图迫使教会顺服天皇体制有一致性。只是半殖民的国家地位已经使清政府力不从心。另外的不同之处是,在日本、韩国教会中,外国传教士对日、韩基督徒的影响要远低于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基督教的影响。反过来则是,日本与韩国的本国基督徒在本国教会中基本上居于支配性的地位。这一点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二、民国基督教的发展与转折
民国初年基督教曾面临非常有利的社会氛围。民国政府第一次以立法形式,引入了现代国家在宗教上关于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两大基本原则[注]张训谋:《欧美政教关系研究·绪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1912年3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六条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107页。孙中山强调宗教不得干预政治,但他认为宗教可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注]《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5日),同上书,第447页。。他在对基督徒的演讲中说:“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注]《在广州耶稣教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5月9日),同上书,第361页;《在北京回教俱乐部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中旬),同上书,第477页。“更愿诸君同发爱国心,对于民国各尽应尽之责任。”[注]《在法教堂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68—569页。《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启了宗教活动的新阶段。1920年一个全国性的调查表明各省宗教纷纷建立组织开展活动,除了制度化的儒佛道外,民间信仰也相当活跃[注]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上卷,蔡咏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18页。。自然,从民初的信仰自由中得益最多的还是基督教。
从民初到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之前,中国有过一段基督教自称的“黄金时期”。义和团运动中传教士的死亡并未阻吓西方人的传教热情,例如在保定的传教士、耶鲁大学毕业生毕德金(Horace Pitkin)被杀之后,居然刺激了美国东海岸一些大学生报名来华传教。1905年来华传教士3500人,1915年达到5500人,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最高潮时超过8000人。中国新教徒也从1900年的10万人,至1922年时增长到了50万人。信徒也不仅仅是来自乡村的穷苦农民,教会学校为一部分年轻人提供了在社会中上升的通道,在几个沿海城市形成了一些富裕信徒群体[注]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p.94.。民国时代的中国信徒也更有自信了,他们可以注册和拥有自己的教产和教会。上海的俞国桢成立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天津和北京的基督徒组建了“中国基督教会”。山东济南也建立了“山东基督教自立会”。与这些分散、规模较小的自立会不同,由差会教会体系发展而来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1922年5月2日成立,代表着全中国366 525位信徒[注]《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宣言书》,封面,档号:U123—0—36—142,上海档案馆藏;《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概况》,档号:U123—0—6—18,上海档案馆藏,第1页。。
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界的强势地位,终于引起了五四运动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进步人士的警惕。1922年初处于发展全盛期的在华基督教,大肆张扬地在清华学校召开了世界基督教青年学生同盟大会,正好成为一个适当的斗争靶子。1922年3月9日,标志“非基运动”开端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把矛头对准了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联系,它指出基督教不仅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还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工具,麻醉人民的鸦片[注]恽代英:《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载《恽代英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3—826页。。这些论断成为自此以后反对基督教的利器。从基督教一方来讲,“非基运动”激活了中国信徒的民族主义思想。教会中人罗运炎曾说:“从此国人对于国家之观念大非昔比。”[注]罗运炎:《罗运炎论道文选》,上海:上海广学会,1931年版,第24—25页。另一教会人士翟从圣认为英美人士中也有“文化侵略”者,因此就“文化侵略”言,不能不收回教育权[注]翟从圣:《收回教育权的我见和今后外国信徒办学应取的态度》,《真光》杂志第25卷第2号,1926年3月,第36页。。不仅如此,“非基运动”对西方在华教会事业形成了民族主义的压力,成为迫使这些事业中的中西人士发动内部改革的动力,以求教会事业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注]《中华基督教会废除不平等条约大运动宣言》,《真光》杂志第25卷第456号,1926年7月,第179页。。
在1926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中,其所到之处,教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进入南京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在该事件中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等传教士被杀。在这一事件后,大批传教士返回西方,许多人再也没有返回中国[注]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69页。《申报》,1927年4月7日。。从此,在华传教士人数再也没有达到此前的峰值,这成为在华传教运动逐渐由盛转衰的标志。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中国耶稣教自立会领袖俞国桢、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余日章等向国民政府呈请通饬各省保护宗教团体,国民政府颁布告示称反帝并非反教和排外,下令保护教会[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6、1097页。。不过,当时国民党内反对英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依然高涨,一部分国民党人仍坚持打击教会、反对教会在华兴办和控制文化教育的立场。所有这些都使国民党一方面力图压制体制外的学生反基督教运动,另一方面则通过政府法令来实施反对“文化侵略”运动中提出的要求[注]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刘寅生等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34页,第435页。。国民党当局于1929年4月颁布“教部颁布宗教团体兴办教育事业办法”,1930年禁止金陵大学办理宗教系,1930年6月严令燕京大学撤消宗教科目[注]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刘寅生等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34页,第435页。。1931年2月,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拟定了《指导基督教团体办法》;6月,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审议,改名为《指导外人传教团办法》。按规定,各地外人传教团体应受党部指导、政府监督,各团体如违反该法规定,由政府依法取缔。
不过,在国民党从在野到在朝的地位转化过程中,随着与英美关系日益密切,形势向有利于基督教一方倾斜。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上海受洗入教,对基督教产生有利影响[注]郭中一:《蒋主席加入教会以后》,《鲁铎》(半年刊)第2号第1卷,第13—14页。。其他党国高层信仰基督教者不胜枚举,如四大家族中的三家(蒋、宋、孔)及冯玉祥、张群、何应钦等。此后,国民党高层中的基督教徒积极推进“党教合作”[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二,第1117页、第1125—1126页,第1141页,第1121-1123、1133页。。天主教方面也与国民政府互相联络[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二,第1117页、第1125—1126页,第1141页,第1121-1123、1133页。。大致可以说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反对文化侵略和反对基督教逐渐淡出国民党的舆论宣传。九一八事变后,这种针对英美在华教会事业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被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取代了。基督教在“乡村建设运动”及“新生活运动”中积极与国民党合作,部分实现了所谓的“党教合作”。但这不等于说国民党对基督教及其在华事业完全放任。对地方上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一些违法行为,国民党政府也予以关注和限制[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二,第1117页、第1125—1126页,第1141页,第1121-1123、1133页。。民国政府未能完全废除在宗教方面的不平等条约,但它对基督教及其事业的管治较之前清和北洋政府时期是大大加强了。
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走上武装夺取政权道路,面临着在根据地如何在实际层面上与宗教打交道的问题。1931年11月5日,中共中央给中央苏区指示的“宪法原则要点”中第十三条规定:“保证劳苦民众有真正信教自由的实际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62页,第467页。在随后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进一步对上述原则作了阐述:一是中国苏维埃政权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二是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三是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政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费用;四是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的自由;五是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允许其存在[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62页,第467页。。这个宪法大纲肯定了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教关系基本原则,但它将信教自由的权利只限于工农劳苦群众,信仰自由就有了阶级身份的限制,明确声明政府不保护宗教的条文也与保障信教自由自相矛盾。另外,强调反宗教宣传的自由多少会被理解为政府对宗教的倾向性。显然,这一政策表现了年轻的革命政权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年代处理宗教问题方面的激进性和某种不成熟性。这里可能也有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对中国革命的某种影响。不过,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的宗教政策开始转变。促成变化的原因既有实际斗争的推动,也有理论上的思考。首先,建立国际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在日军侵华的局面下,必须团结和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民族战争,与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有广泛联系的各教各派宗教团体应当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力量。其次,有的红军将领在实际斗争中在与宗教界的接触中,对宗教问题有了新的实际经验,例如萧克将军在与传教士薄复礼(Rudolf Alfred Bosshardt)的接触中,逐渐认识到寻找各国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共同点的重要性[注][瑞士]薄复礼:《一个被拘传教士的自述》,张国琦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最后,这一时期中共在理论上对宗教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37年李达发表《社会学大纲》,对原始宗教的世界观、观念论与宗教的关系、宗教的起源及其形态、古代宗教的特征及基督教的起源、宗教在现代社会上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与宗教的斗争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1938年毛泽东在读李著中关于宗教问题部分时,对宗教产生的根源及宗教在阶级社会存在的必然性作了深刻的论述。
这一时期,基督教在文化、医疗事业方面依然有很大的投入,但此前的独占性地位大幅下降了。进入20世纪后,随着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自身的新式教育迅速拓展,教会教育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以往的垄断地位。基督教教会企图主导中国教育航向的雄心壮志慢慢消退[注]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页。。他们开始强调如何提高教会学校办学质量和寻求中国政府对教会学校毕业生的承认[注]在这种努力下,教育传教士的人数稳步增加,到1914年,教会学校达4 100余所,学生1906年57 683人,1912年138 937人,到1916年达184 646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5页。。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各国在华基督教团体联合办学成为一股潮流,逐渐形成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普通教育体制,外加幼稚园、神学教育、职业教育、盲童聋哑教育等特殊教育在内的完备的教育系统。这个系统的顶尖学校是东吴、齐鲁、沪江、华西协和、金陵、之江、金陵女子、福建协和、燕京、华中、岭南、圣约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一系列教会大学。其中燕京大学等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注]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P.531-533.。这个在基督教差会管控之下的教育体系,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除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外,都按照要求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门注册登记,至少在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的监管,成为中国国家教育资源的组成部分。这些学校不仅培养教会人才和吸纳基督徒,也面向非基督徒。其所培养的新式人才在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以教会或教会学校为桥梁得以留学欧美的庞大的留学生群体归国后往往成为中国各界的精英,在社会和政治改革活动中相当活跃[注]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123页。。
随着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有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增长,在华基督新教运动的权力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成静怡1910年在爱丁堡国际基督教大会上要求西方人从中国人立场看中国教会的发言引起关注,中国基督徒精英被吸收进在华传教运动中逐渐形成的由有影响力传教士主导的中外合作的新教领导机制,其中有成静怡、余日章、王正廷、刘廷芳、赵紫宸、洪业、吴雷川等人。这些人除了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外,基本上都是燕京大学的教师。这个机制的意见和议程对倾向于社会福音派的新教运动的走向发挥重要的影响[注]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p.101-103.。
民国时期的基督教还有一个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外国传教运动在中国“走向成熟、蓬勃发展,接着是衰老和死亡”的阶段。传教运动在晚清尽管有宗派差异但还能保持传教运动“意见一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保守的基要派传教士和主张适应时代的自由派或者现代派传教士的关系日趋紧张。1932年刚刚获得普利策奖的赛珍珠(Pearl S. Buck)因为在纽约的演讲中批评了传教士的无知与傲慢,被保守派要求辞去在美国南浸信会董事会的职务。差不多同时由哈佛大学教授霍金(William E. Hocking)主持的对传教运动的评估报告,以自由主义神学思想表达了对基督教的排他性和传教运动的合法性的质疑,这也引起了以中国圣经公会成员为主的保守派与中外新教合作机制聚拢的自由派之间的分歧和对立。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整个中国的新教教会大致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是与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相关的教会组织,中外合作新教建制中人在其中依然活跃,他们支配着主流教会的议程和做出相关的决定,其社会特点是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和积极参与社会改良运动。第二类是一些比较明显的保守的差会群体和教会,他们脱离或者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中华基督教会,因为不赞成后者的自由主义神学和追求社会改革。它们可能是中国圣经公会的成员,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内地会,但也包括了基督徒和传教士联盟,美国南长老会和圣公会,几个路德会,美国自由卫理公会,拿撒勒会,神召会,几个较小的五旬节会,还有就是十多个很小的、有时只有一个人的信心差会。这些派别更强调个人而不是社会的皈依和重生。他们并非没有爱国主义,但他们没有把国家建设和改造社会放到优先地位。第三类是民国以后出现的新教会与运动,尽管这些教会与运动的领导人在其个人成长的早期都受到过外国基督徒的影响,但他们组织的教会则完全独立于外国差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以及在福州、上海围绕着倪柝声的运动,它们有几个不同的叫法,如聚会处、小群,或者干脆叫地方教会。
义和团运动时在华天主教受到重创,运动之后它修改过去咄咄逼人的政策,换来与中国官民关系的缓和;同时一次大战后罗马教廷为削弱在华法国天主教势力在保教权问题上的坚持,派遣美国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美国天主教支持在华传教给天主教带来了新的动力,结果是天主教在华事业获得较大进展[注]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0页,第246-279页。。与新教主要在城市发展和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相比,天主教主要在农村活动,对高等教育等世俗事业关注较少。但天主教和新教一样同样面临如何改变洋教形象的问题。由于天主教教阶制度更多体现为自上而下的体制变动,同时由于天主教传统势力的保守性,其改革的过程漫长而且成效甚微。1922年11月教廷第一任宗座代表刚恒毅秘密抵达香港,并巡视中国各地教区[注]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0页,第246-279页。。与此同时,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巨大压力,迫使刚恒毅为应对中国民族主义挑战,推行以本土神职人员为基础,成立本地教会,重视适应化策略和学术文化传教,并借平信徒协助传教,共同促进教会的复兴和本土化的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的传教模式。1926年教廷特意针对非基运动发布了《自吾登基以来》牧函,重申以本土神职代替传教士的宗旨,并嘱传教士应专注传道而不得涉足政治。这双重因素使本土化再次向前迈进,刚恒毅又先后成立4个本籍代牧区。同年10月罗马教宗亲自为随同刚恒毅而来的6位中国主教祝圣,这是自清初罗文藻担任主教200多年以后再次由中国信徒担任主教,在教内外产生巨大影响[注]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309页。。在刚恒毅积极本土化策略的推动下,到1935年中国本籍主教区从无到有共达23个,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弱。中国籍神父到1933年达1600人,而修女则相应增加到3600人,本土神职的培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注]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152页。。在其主持下,许多培养平信徒的组织如全国公教进行会、公教教育联合会、中国公教青年总会等先后成立,为发动平信徒的潜力和提高天主教在公众层面的影响提供了组织路径,天主教教育机构的进一步拓展如辅仁大学的创设等也是其注重学术文化传教的体现。1933年刚恒毅离华后,其积极本土化进程放缓。全面抗战爆发对本土化形成新的障碍,使之陷入日本侵华和伪满问题的纠葛中。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分成敌(日)占区、国统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华基督教会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大后方,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继续活动。大部分基督教大学也像国立大学一样西迁,在困难的局面下继续发挥培养知识精英的作用。在整个全面抗战期间,这个系统的教会领导架构在人员和财力都大受影响的情况下,继续发挥有限的作用,加入中华基督教会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教会组织也没有增加,其信徒总数一直没有达到整个中国新教徒数目的一半。它们发起的西藏、云南、贵州等边疆地区的传教运动到抗战结束时并没有多大的进展。相反那些鼓吹末世论和前千禧年的教派如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和小群却在战争灾难的局面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共的抗日根据地一般都是基督教发展比较薄弱的地区,由于战争影响,教会都受到一定的削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成为日本的交战国,相当数量来不及撤离中国的传教士被日本人关进了在山东潍坊和上海近郊的集中营,受尽磨难。1941年日本军方为了控制华北地区的基督教会,成立了所谓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除了王明道的北京基督徒会堂外,所有华北的基督教团体都被迫参与其中。但对耶稣家庭,以及在乡间活动的基督教组织,日本人的控制仍是鞭长莫及。
日本在扩大对华战争时,除使用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外,还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宗教力量,采取各种手段,破坏中国的国际和国内抗日统一战线。比如,在佛教广泛流传的东南亚各国,日本人大肆宣扬 “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把自己的侵略战争美化为 “弘扬佛教的圣战”,甚至欺骗东亚的佛教界,鼓吹通过战争在中国建立佛教的 “新摩揭陀帝国”,以此来破坏东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也利用宗教反共。如1943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制定的反共计划书就指出:“运用基督教民,向在当地之外国教士宣传中共之一切暴行,取得国际间之明了与同情。”[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印,1979年,第303页。
抗战期间中共的宗教政策有过明显的变化。1936年中共中央在创立全国各党各派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表示“不分主张与信仰……共赴国难。”[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1936年7月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提出了“苏维埃对外国传教士的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将承认他们财产权?他们是否将继续享有传教、教书、拥有土地、办学校和其他事业的权利?”毛泽东除了将日本传教士排除在外,对此都作了肯定的回答[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页。。在基督教受到质疑时,《新华日报》以《抗战与基督教徒》为题,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徒,都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者”,还特别提出“基督教青年会团结了许多青年,成为中国青年中一种很重要的组织。”[注]《抗战与基督教徒》,《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1942年2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在信教自由的旗帜下》,对抗战以来各宗教团体在战争中的贡献,特别对基督教会的活动作了充分肯定。社论还认为不仅在抗战中,而且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基督教会也将发挥作用。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它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予保护”[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抗战期间中共与西方传教士也有接触和交往。周恩来在抗战中到武汉开展工作,汉口公会大主教美国人吴德施(Logan Herbert Roots)积极参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活动,周恩来通过他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注]《人民日报》,1993年9月12日。。在抗战中到过延安的西方传教士为数不少。1941年到延安的加拿大传教士罗天乐(Stanton Lautenschlager)后来写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一起》,向世界介绍了中共领导对宗教问题的新看法。中共还同一些宗教界知名人士建立联系。1939年5月,周恩来在汉口专程拜访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向他表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文汇报》,1979年3月5日。1941年12月和1943年5月,周恩来又两次会见吴耀宗,详细阐述了党的宗教政策,对宗教界人士为抗战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939年4月6日,天主教爱国老人马相伯百岁诞辰时,中共中央致电祝贺,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1940年9月,彭德怀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就指出与教会“建立了一些友谊关系”[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0页。。
抗战胜利后,中华基督教会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迁回上海,大批传教士也返回中国。由于离开传教现场8年之久,一些差会的传教士小心翼翼地与中国同事重新相处,而另一些特别是新近来华的传教士则忘掉了过去模式的不平等,认为理所当然应该由自己负责,因此重新引起差会与教会关系的紧张。特别是当以美国为基础的教会大学董事会要合并或者缩小教会大学规模时遭到这些大学中方领导的顽强抵制[注]Liu Jiafeng,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The American Postwar Plan for China’s Christian Collegs, 1943-1946”, in Daniel H. Bays and Ellen Widmer(ed.)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 1900-1950,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p.281-240.。基督宗教同样经历革命运动的震荡和日本侵华战争打击,但由于有西方差会此前打下的基础及抗战后西方差会的支持,以及蒋介石夫妇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事业上是其他任何宗教望尘莫及的。以1950年的基督教新教的全国性统计资料来看,新教在全国各地有大学13所,中学240所,医院、诊所312所。各种刊物89种,全国性社会福利救济机构8个。连中国国际工业合作协会、中国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难民组织、国际儿童紧急基金等组织都是基督教的附属机构。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社会化程度也是最高的,除了全国性的基督教协会外,还有各种地区性的协会[注]刘家峰:《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两种》,未刊稿,第252—362页。。在有基督教社团的乡村地区,它们也成为传统宗教的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民国时期有一些传统宗教的精英流向了基督教会,一些民间宗教社团的信徒,如金丹道、离卦教的信徒转变为基督教徒,其庙宇被改建为教堂[注]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33页。。
抗战胜利后,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给中国天主教的指示是“更加中国化”,开始酝酿祝圣中国枢机主教,1945年青岛教区主教田耕莘被教宗任命为远东第一位枢机主教,并赴梵蒂冈行加冠礼,向教宗建言早日在华设置圣统制。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布谕旨,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将全国分为20个教省,每省设立一个总主教座,另分79个主教区和38个教区,共137教区[注]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513页。。中国圣统制的建立使教内统序由代牧制转化为通常的主教制,使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这并不足以完全改变中国天主教受传教士主导的附属地位,在20名总主教中华人只有3位,其中田耕莘枢机出任北京总主教,于斌出任南京总主教,周济世出任南昌总主教。而在全国137名主教中,传教士占了110名[注]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第180页。。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之路仍然有待来日。
不过,经历了中国一个来世纪的风风雨雨,教会中人对用基督教改造社会的效果充满失望。教会领袖曾经综合各方面的批评,指出存在的8个问题:“1.对于现实社会罪恶太屈服,不能左右人心,不能左右政局,不能挽回社会风气。2.不能领导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不能帮助国家建立新道德文化基础。3.多数教友‘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不问国事,不知民间疾苦,不能实行耶稣基督的教训,‘能说不能行’。4.教会中人或信仰不坚,常有投机,变节,腐化事实,致有人乘隙利用基督教,出卖基督教。5.对于青年失去号召作用,对于时代失去挑战作用,尤其对于热心国事的青年不能发挥积极有力的指导。6.多数教友宗教生活松懈,灵性生活空虚,甚或不礼拜,不读经,不祈祷,不灵修等。7.大部分牧师(尤以乡间为然)墨守成规,不读书,不进步,无胆识,无灵力。8.有一部分教友只知个人得救,不管民生疾苦,不顾社会沦亡。总之,今日中国教会是患了‘贫血症’,往者已矣,目前又无杰出的人才和领袖,又乏新进的有学识的热心青年教友,无怪基督教阵容散漫,难有活泼魄力和生气。”[注]方贶予:《基督教的复习和前进运动》,《恩友》复刊第2期,1947年4月,第3页,转引自段琦:《奋进的历史━━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第501—502页。
这份报告发表时,内战已经爆发,中国教会又面临一次历史选择。尽管蒋介石本人是基督徒,但还是有一批教会人士极其厌恶国民党政府的贪腐与无能,他们宁愿生活在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之下。中华基督教会的《协进》和独立的《天风》杂志表达了基督教中自由主义甚至是激进主义的观点。《天风》后来成为20世纪50年代基督教“三自运动”的官方刊物。常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吴耀宗和青年会的江文汉不仅是同情而且是盼望共产党取得胜利。1949年初,共产党在内战中胜出的大局已定,传教士和中国教会领袖面临着离开还是留在中国大陆的选择时,尽管许多新教徒、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对教会的未来感到忧虑,但还是有许多人对中外合作的新教事业能够在共产党政权下存在下去,并为“新中国”做出基督教的贡献抱有希望。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宗教界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8人,其中基督新教代表占5人,成为最接近中共的宗教。
三、余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对苏联“一边倒”对外政策的实施,执政党对社会组织和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西方在华传教事业随着传教士的撤离中国大陆而走到了历史的尽头。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争的大背景下,基督教开展了革新运动。1950年7月底吴耀宗等40名新教教会领袖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发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注]段琦:《奋进的历史——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第542—545页。。在1950年的年底形势突变以后,中共开始全面肃清基督教内的美国影响力,各项教会附属事业被处理、接收和改造,教会内部发起控诉运动,美国差会及传教士最终被迫退出中国大陆。中国教会内部也完成一次大的权力转移,中国基督教走上反帝爱国的道路[注]陈铃:《落幕:美国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结束(1945—1952)》,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3年,纸本第1页。。天主教晚一点也建立起天主教爱国会。值得一提的是,经过这次基督教的改革之后,积累了一个多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教育、医疗等现代事业,都被并入到国家体制中继续发挥作用。基督教和中国传统的佛、道宗教处于一种同样的没有任何世俗事业的纯粹宗教状态。这种情况要到新世纪以后才逐步改变。
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共宗教政策的偏差,对宗教的存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例如,上海从1963年到1965年受洗信徒只有10人[注]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744—747页,第750-759页。。“文化大革命”中排斥宗教达到最高点,基督教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自发基督教活动在城市和农村有了新的发展[注]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744—747页,第750-759页。。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统一战线框架下的宗教政策,基督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中国一度出现过“基督教热”的现象。经过将近40年的发展,按照不完全的统计数据,1949年中国约有70万~80万基督徒,1982年增加到300万,1988年为450万,1997年为1200万,2009年为2300万[注]卢云峰:《走向宗教的多元治理模式》,《文化纵横》,2013年第3期。。2012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对中国当代宗教状况进行了描述。调查发现,中国只有10%的人自认为有宗教信仰。在这些人中,女性、中老年人、受教育水平低的被访者比例偏高;宗教信仰与收入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但当人们的客观收入相当时,有宗教信仰的人对自身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更高,这意味着宗教信仰有助于增加人们对现状的满足感。佛教仍然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6.75%的被访者自认为信仰佛教,几乎是其他所有宗教信徒总和的两倍;另外,相较于基督徒,佛教信仰者中的年轻人和高学历者比例更高,而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更低。数据显示,1.9%的人信仰基督教,据此推算,中国大概有2600万的基督徒,从信徒规模来看,基督教已成为汉族人口地区的第二大宗教;在局部地区基督徒的绝对数量已经超过佛教徒,所以据此可判断基督教在中国已形成“全国存在、局部聚居”的格局。另外,从信徒的组织化程度、信徒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以及信徒对宗教信仰重要性的主观评价这三个指标来看,基督教甚至已经超过佛教[注]卢云峰:《当代中国宗教状况报告——基于CFPS(2012)调查数据》,2014年3月25日,http://www.zhexue.org/f/religion/17563.html,2018年6月3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2010年时中国信教人数的报告与上述数据有点不同。认为中国大陆有:基督徒6841万人,穆斯林2469万人,印度教徒2万人,佛教徒2.44亿人,民间宗教信徒2.94亿人,犹太教徒1万人,其他宗教信徒908万人(包括道教徒800万人);共有宗教信仰者6.4亿人;无宗教隶属7亿多人。而中国官方权威观点:中国有近2亿宗教信徒,占全国人口的15%。见《宗教学家卓新平:如何正视中国文化核心与中国人信仰?》,http://guoxue.ifeng.com/special/zxpjdzgwhhxyxyjzj/,2018年6月3日。。
无论如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基督宗教的传播终究带来与传统宗教有明显区别的新宗教。实际上,晚清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之际,中国自唐宋以来已经形成了儒释道三家支配中国人精神领域的格局。基督教的传入给中国的宗教文化带来了新的内容。从信仰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宗教与传统的儒家学说和佛教、道教有许多不同。第一,也许相比佛教、道教那些复杂的神祇世界和卷帙浩繁与难懂的佛教、道教经卷来看,基督教是一个简单朴素明了的宗教。基督教只有一个三位一体的神,讲述这个至高无上的神的故事性很强、浅白易懂的《圣经》,以及其中人神沟通时无所不在的“圣灵”是中国其他传统宗教所没有的普设性存在。这在中国信徒那里使他们感到基督教的“神”的临在是及时的、可亲近的。第二,基督教和佛教、道教的差别还在于它把平信徒带进了一个组织性、社区性和参与日常生活频度一般来说高于其他传统宗教的团体。这个团体比较小,也比较平等和民主,使得中国信徒有更多的群体感和参与感,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从团体得到各种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变中国基层社会的疏离状态。第三,基督教制度化的经常性集体礼拜也有助于强固信徒群体的宗教归属感,使得教会与信徒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基督教布道、读经、唱诗等活动反复强化信徒的宗教意识,从而也对信徒的社会生活发挥经常性的影响。如果说除了佛道神职人员外,人们很难在世俗社会的基层发现明确的佛道教徒团体,那么那里的天主教和新教的社团是一目了然的。总之,基督宗教带来的信徒的群体性、凝聚性和社会性在中国宗教史上是新的现象,是一种中国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合法的社团组织。从神学上来说,基督教徒对神的委身,对人性的否定,对自我反思的要求,在宗教活动中获得的激情与释放在中国文化中都显得非常独特,显然是对比较自敛的中国宗教是一种补充,这也是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
回望历史,如果和1949年以前相比,当下中国基督教有几个新的特征:第一,外国传教士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全部退出中国大陆,经过在基督徒中广泛开展的三自爱国运动,基督教已经成为完全的中国人的基督教。人们只是在追溯中国基督教的源头时还会想起早年传教士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阴影下筚路蓝缕的贡献。第二,以前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主张基督教合一的愿望也变成了现实。对基督新教来说,全国只有一个教会系统,在地方上也没有以前各个宗派林立的现象。这个教会是自治、自传和自养的教会。虽然各个地区教会治理、传教和自养的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别。但笔者到过一些神学院,看到的神学生们和过去相比更加阳光、更加自信。第三,由于1949年以后教会的教育文化机构的消失,基督教没有了原先与社会精英联系的纽带,今日的基督教徒群体或许更加草根化。在过去的基督教的现代性逐渐消失以后,基督教在许多方面正变得更亲近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亨廷顿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过:“虽然中国于1602年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但以后又在1722年把他们驱逐出境。与日本不同,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注]②[美]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第68页。还是亨廷顿所总结的:“学者们认为,中国从印度吸收的佛教并没有导致中国的‘印度化’,中国吸收佛教是为了中国的目的和需要,中国的文化仍然是中国的。中国人至今仍在不断挫败西方使他们基督教化的强大努力。假如在未来某一天,中国确实引入了基督教,那么也只能期望它在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要素相容的前提下被吸收和改造。”②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下“宗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包括宗教界的共识和努力方向。从历史来看,中国文化确实比较能够包容和影响不同的宗教,中国基督教也正走在这条历史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