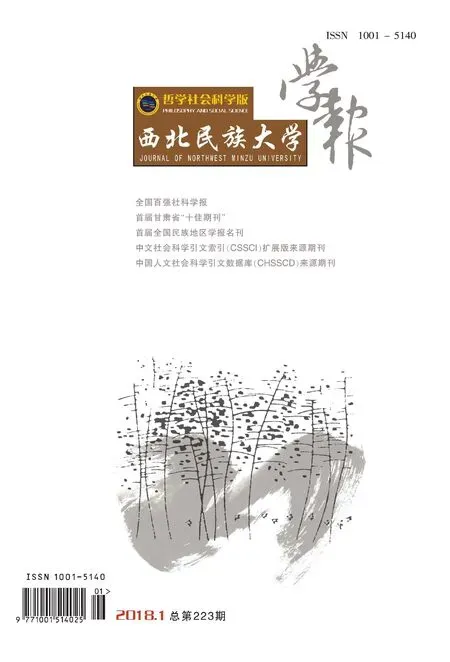元代桑哥的历史形象探析
——基于《元史》和《汉藏史集》相关记载的比较研究
李红阳
(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
桑哥在元世祖至元(1264年~1294年)中后期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政治家,对于元代初年的政治、经济和民族政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史》和《汉藏史集》对于桑哥的记载都比较详尽,但是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元史》侧重于桑哥在担任丞相期间的相关历史活动,而《汉藏史集》则侧重于对桑哥在西藏地方的事迹;同时《元史》和《汉藏史集》对于桑哥之死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但是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评价。史学界对于桑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学术成果:仁庆扎西的《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中对桑哥的族属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究,作者根据《汉藏史集》中“有大臣名桑哥者,系出身于噶玛洛部落的青年”[1]的记载经过考证认为他是畏兀化的藏族人,同时对桑哥在担任丞相期间的历史活动进行了论述,其研究比较深入;而尹伟先的论文《桑哥族属问题探讨》[2]通过对吐蕃时期西藏家族传承的详细考究,赞同仁庆扎西关于桑哥族属的观点,之后史学界基本沿用这一说法;杨德华在《元代藏族宰相桑哥理财的政绩》[3]中对桑哥的财政政策进行了梳理,并基本肯定了桑哥的历史地位;伯戴克(著)、张云(译)的《中部西藏与蒙古人——元代西藏历史》[4]对于桑哥的论述比较全面,但是篇幅较小,相关探讨只是浅尝辄止,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实际上,学术界对于桑哥之研究关注的问题主要是桑哥的族属问题、桑哥担任丞相期间的施政问题和桑哥之死问题,但是相关研究都没有在对《元史》和《汉藏史集》进行详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还原桑哥的历史形象,这也是本文试图论述和探讨的主要方面。
一、《元史》中的桑哥形象
《元史》是成书于明代初年的一部官修元代正史,明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明太祖朱元璋“召儒臣,发其所藏,撰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5]4677,两年之后的洪武三年(1370年)十月这部官修纪传体断代史定稿,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二十四史”之一。由于明太祖的急功近利,《元史》在短短的两年内便编修完成,因此也导致这一部史书的质量差强人意,相关历史的记载也不够全面和客观。但是,《元史》详细地记载了那个时代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由于元代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因此《元史》对于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记载也十分详尽,而有关桑哥的记载就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例子。在《元史·桑哥传》[5]4570-4576中,详细地记载了桑哥的生平事迹,包括桑哥的早期历史活动、桑哥在担任丞相期间的主要政绩和桑哥之死三个主要的人生阶段,这对了解桑哥的历史形象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元史·桑哥传》的开篇便交代了桑哥的早期历史活动,他“通诸国语言”,因此成为“西蕃译使”[5]4570,他通过充任官方译吏沟通了各民族上层人士之间的交流,因而在元初中央政府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至元中期,桑哥升任为总制院使,总制院就是管理天下佛教和治理西藏地方的一个机构,桑哥在此时便显露出了杰出的管理才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桑哥升任尚书省的平章政事,成为元代中央政府的高官之一,在这一期间他奉旨检验中书省,对于中书省的渎职的官员进行了参奏,其中中书参政郭佑遭到桑哥的严惩。时人都感觉到桑哥极其残暴,桑哥于是对于私底下议论他的人进行严厉报复打击,如御史王良弼和江宁县达鲁花赤*达鲁花赤,由成吉思汗设立,广泛通行于蒙古帝国和元朝。“达鲁花赤”是蒙古语,原意为“掌印者”,是蒙古帝国历史上一种职官称谓,其实相当于督官。达鲁花赤是代表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行使军政、民政和司法的官员,以《大札撒》为根本,结合当地的惯例行使统治权。达鲁花赤后来成为长官或首长的通称,在元朝的各级地方政府里面,均设有达鲁花赤一职,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各级的最高长官。在元朝中央政府里面,也有某些部门设置达鲁花赤官职。达鲁花赤一般必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这种做法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民族不平等色彩。明朝以后,达鲁花赤这一官职被废除。吴德被其定罪并处以极刑,其家产也被没收。这一时期桑哥还向元世祖提出了一些执政的理念和官员任命名单,元世祖都采纳了他的意见,由此可见元世祖此时是十分欣赏和信任桑哥的,这也是桑哥能够在其政途上再进一步的关键性因素。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月,在满朝大臣的推荐下桑哥被授予“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5]4572,桑哥的官位达到了极盛,成为辅佐元世祖忽必烈的左膀右臂。在桑哥担任丞相期间,他的主要历史活动有:一是对于那些不能胜任的官员进行了弹劾,并在元世祖的支持下将这些人的官职罢免,主要包括诸道宣慰使司中的渎职者、兵部尚书忽都达尔等;二是清理财政,进行钩考,这是一次从中央到地方的理财方案,桑哥及其属下官员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月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十月间,对全国各省的财务进行了监督和检查,发现了许多贪官污吏并将他们绳之以法;三是增加税收,桑哥提议“盐课每引中统钞三十贯,宜增为一锭;插每引为五贯,宜增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宜增额十万锭,内地五万锭”[5]4575,桑哥所拟定的这一政策大大提高了税收的标准,虽然能提高元初政府的收入,但是却损害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桑哥担任丞相期间,其所实行的政策实际上已经使得人们十分惧怕,以至于桑哥进行财政整顿时人们“皆弃家而避之”[5]4573;同时那些奸佞的小人为讨好桑哥为其立碑颂德,这块被称为“王公辅政之碑”[5]4575的功德碑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十月被立于尚书省的门前,可见当时的桑哥处于一种十分显耀的官位之上。桑哥的权势越来越大,同时使得他易遭到同僚的嫉恨,并最终被诛杀。其被诛杀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的专政。当时所有内外官员均出自他的门下,并且他善于敛财,进行了一系列的权钱交易,因此使得“纲纪大坏,人心骇然”[5]4575。桑哥的专权使得蒙古贵族十分恼怒,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他们上奏皇帝说:“桑哥壅弊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复。”[5]4575起初元世祖并不信以为真,后来很多官员都弹劾桑哥的这种不良言行,因此元世祖决心将其诛杀。诛杀桑哥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丞相,元世祖还是费了一番功夫,他将御史、中书省、尚书省的官员召集起来并命令他们就桑哥“专权”且鱼肉百姓的恶行进行讨论,其后一致认为桑哥危害到大元江山社稷,因此“仆桑哥辅政碑,下狱纠问”[5]4576,元世祖二十八年(1291年)七月桑哥被诛,其妻在湖广也被杀戮,至此桑哥的历史形象被定格在了奸臣之上。
实际上,明初撰修的这部《元史》对桑哥的评价是很低的,关于桑哥的列传被编排在了《元史·奸臣传》之中,因此可见在明代士大夫眼里桑哥就是一个任人唯亲、无恶不作的奸臣,这也代表了元朝政府观点;同时,在《元史·桑哥传》文字中极力渲染桑哥的奸臣形象,从他“狡黠豪横,好言财利事”[5]4570的记载到“天下骚然”[5]4574的描述,无不显示了明代史学家对于桑哥的总体印象,这其实就是《元史》中桑哥的历史形象。
二、《汉藏史集》中的桑哥形象
《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以下简称《汉藏史集》)是藏族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作者是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大约成书于1434年[6]1-2。在内容的编排上,该书分为上、下两篇,其所包含的内容繁多,包括了释迦牟尼及佛教的传播,赡部洲的王统世系,吐蕃的经济社会情况,元代萨迦的历史,元朝在西藏的军事、赋税、设立驿站等方面,对于研究吐蕃史、元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具有不可多得的情报价值。在《汉藏史集》最后一部分《跋语及祝词》中谈道,这本书的完成由“各种王统、史籍中摘要汇集而成,其简明流畅之文字,在此幸福美妙之人世,犹如饥渴之中送来的佳肴美食”,同时留有余地谈道:“写书时所依据之底本多为无头之旧字,错漏之处甚多。”[6]314-315由此可知,《汉藏史集》所参考的资料大多是已经失传的文献记载,因此其文献价值不容质疑,其保留了珍贵的藏文史籍,研究吐蕃史、蒙元时期西藏史的学者不可不读[7]。在《汉藏史集》中对桑哥的记载比较突出,而关于他的历史事迹则主要集中在桑哥的族属及其与八思巴的师徒情谊、桑哥进军吐蕃及善后政策、桑哥之死三个方面,而对于桑哥担任丞相期间的历史活动的记载则十分简略。
《汉藏史集·桑哥丞相的故事》开篇即说:“有大臣名桑哥者,系出身于噶玛洛部落的青年。”[6]158,这条记载将桑哥的出身问题介绍得十分明确,正是由于这条记载才使得后人通过考证、分析得出了桑哥是畏兀化的藏族人的结论[2]82,同时这一结论与意大利著名藏学家伯戴克的研究成果亦十分吻合[4]32。《汉藏史集·桑哥丞相的故事》的开篇还讲述了“桑哥通晓蒙古、汉、畏兀尔、吐蕃等多种语言”[6]158,因此成为译吏。桑哥拜见了八思巴,并成为八思巴的译吏,后因为八思巴的缘故桑哥成为皇帝身边的官吏,并且他对于各级官职都能够胜任。八思巴和桑哥之间的情谊是十分深厚的,在桑哥担任宣政院官员时,他为八思巴修建了一座佛堂,而御史台因此将其治罪并投入监狱,这时八思巴为其向皇帝求情说:“在我们吐蕃地方,儿子关在狱中,其父在街上行走都感到羞愧。”[6]158因此皇帝宽恕了桑哥。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八思巴对桑哥的喜爱之情,表明桑哥的升迁与八思巴有密切的联系。
《汉藏史集·桑哥丞相的故事》中关于桑哥进军吐蕃的记载是十分详尽的,由于当时的本钦贡嘎桑布做出了背信弃义的事情,故皇帝令桑哥率十万大军前往讨伐,桑哥不仅成功使贡嘎桑布伏法,而且仿造汉式风格修建了供奉佛教的“东甲穷章康”[6]159。与此同时桑哥还对当时的管理制度进行了调整:一是命令蒙古军队对西藏的军事要地、佛教上师、寺庙进行驻守以保证其安全;二是对西藏的驿站制度进行了调整,驿站的驻军改为蒙古人,而西藏人仅仅提供乌拉差役,不再在藏北驻站。另外,《汉藏史集·桑哥丞相的故事》还简要记载了桑哥丞相整顿财政吏治的措施,一是将“使用铜钱改为用钞”,这一举措使得国库和社稷日臻稳定;二是各级官员及家室由国库供给俸钱和粮食肉食,严厉惩治贪污;三是免除了吐蕃人驻站服役和贡赋,使得西藏地方减轻了负担。
由于桑哥“具有智慧、财用充足,使许多蒙古人忌惮难忍”[6]160,又因为他为巩固国家财政而侵犯了蒙古权贵的利益,故而他们向皇帝控告桑哥贪污了钱财,但是他们几次三番的控告都没有得逞,皇帝仍然十分信任桑哥。但是皇帝最后还是将桑哥的罪状揭露出来:“你在斡耳朵迁移的路上,一棵大树底下,在我乘凉时坐的座位,你坐了,从大都给我送来的果子箱,你把封蜡开了,吃了送给我尝新的果子,你没有罪吗?另外,我身体易出汗,衣服容易脏,洗后再穿就窄小了,所以汉人织匠为我织了无缝的衣服,献给我两件,你手中却有三件,甚至超过了我,这不是你的罪过吗?”[6]160从皇帝为桑哥所定的罪行来看,当时的桑哥确实十分张扬,其吃穿用度甚至超过帝王,因此最后被处死。
《汉藏史集·桑哥丞相的故事》最后谈道,“由于他是一位有功绩的贤能大臣,故记下其事迹”[6]160-161。因此在《汉藏史集》的作者看来,桑哥是一位十分贤能的大臣,其进军吐蕃为西藏地方的安全和稳定做出了贡献,而他对财政吏治的整顿则使得元朝的吏治和财政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总之,《汉藏史集》中桑哥的历史形象是高大而贤能的,桑哥对于元初的稳定和西藏地方的安定是有其独特贡献的。
三、《元史》与《汉藏史集》所记载的桑哥历史形象之比较
如前文所述,《元史》成书于1370年,而《汉藏史集》大约成书于1434年,因此这两部史学专著的成书年代十分相近。但是这两部史书的著述方法、著述精确度、著述之目的都存在明显的不同:从著述方法上来看,《元史》继承了中国官修史书的体例和体裁,而《汉藏史集》则没有一个标准化的体例和体裁,其著述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展开;从著述的精确度来看,《元史》的时间交代十分清晰,甚至精确到了某年某月,而《汉藏史集》的时间交代则十分模糊,大多数的记载需要靠其他文献的校对才能得出准确的时间界定;从著述的目的来看,《元史》无疑是在文献的整理和文化的积累下为巩固明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而编著,《汉藏史集》则是“为利益教法众生而以虔诚之热情写成、又仰仗无欺之三宝真谛之法力”,“向释迦牟尼、如来诸佛、阿罗汉、证得菩提之众佛、满足一切善缘之王敬礼”[6]313-314,因此是为佛法的传播、众生的利乐而整理的。通过对《元史》和《汉藏史集》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史书著述方面的多元化色彩,同时也造成了其所记载的历史形象存在差异。
结合《元史》和《汉藏史集》对于桑哥的记载,可以梳理出桑哥历史活动的轨迹:至元(1264年~1294年)中期,桑哥因通晓各种语言并且能力出众,先后充任八思巴和元代中央政府的译吏,在此期间他与八思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之后成为总制院使;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他担任尚书省平章政事,同年十月升任丞相,在此期间他施政西藏地方并稳定了西藏的形势,同时他还打击贪腐、整顿财政、提高税收,加强了元代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七月桑哥被诛,一代丞相至此殒命。对于桑哥的历史形象,透过《元史》和《汉藏史集》的相关记载,可以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元史》通过对桑哥担任丞相期间违法乱纪、任人唯亲、权钱交易等“专权”和劣迹的交待,认为桑哥就是一个“奸臣”;而《汉藏史集》通过对桑哥施政西藏和整顿财政吏治的历史事迹,认为桑哥是一个十分贤能的丞相,而其最后被诛杀也是由于他的历史活动触犯了蒙古贵族的利益而被“诬告”致死。实际上,对于桑哥的历史形象如何认识,需要分析的历史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桑哥与八思巴的关系问题,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尹伟先教授认为“桑哥初为膽巴国师的弟子,后来成了八思巴的弟子而飞黄腾达”[2]81,尹伟先教授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根据便是《元史》中“讳言师事膽巴而背之”[5]4570的记载,而这一记载只能表明桑哥忌讳自己是膽巴国师的弟子并且背叛了师门,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桑哥的背叛师门是因为他拜八思巴为师,因此桑哥是八思巴弟子的说法缺乏足够的史料依据。而根据《汉藏史集》的记载,桑哥被八思巴从监狱救出来之后,“施主与福田二人亦得会面”[6]158,从这里可以得出桑哥与八思巴是施主与福田的关系,这一结论基本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当时的桑哥的官职虽然并不高,但是为藏传佛教施舍一些财务的能力还是应该有的;同时,桑哥曾经做过八思巴的译吏,此时已经高升的他也必然向藏传佛教施舍财务以报答八思巴的知遇之恩。
二是关于桑哥的执政政策,如前文所述,桑哥的执政政策主要是在西藏地方驻军、财政改革和提高税收。桑哥进军西藏并在西藏地方驻军,将西藏地方的驿站管理收归中央政府,实际上加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一步确立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因此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方针;桑哥的财政改革实际上将那些在财政上进行贪污渎职的官员进行了清理,虽然导致了官场人人自危,但是维护了元代初期的财政稳定,是符合历史发展需求的;桑哥提高税收,有些商品的税收甚至提高了两倍之多,这实际上损害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元初经济的恢复,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提高政府的收入,但是对元代社会的长期发展不利,而桑哥减免西藏地方的税收,则对西藏地方经济的恢复是有利的。
三是桑哥被诛杀的原因,如上文所述,桑哥之死是他“专权”的必然结果,也与他所进行的历史活动侵犯了蒙古贵族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汉藏史集》和《元史》的相关记载都有其合理化的理由,因此桑哥之死与其说是利益集团的争执,不如说是功高震主,“王公辅政之碑”的修建可以从侧面印证。因此,桑哥之死从元世祖为其修建“王公辅政之碑”就可以看出端倪,但是这些都不能否定桑哥在元代政治史和西藏地方发展史中所占有的地位和做出的突出历史贡献。同时,桑哥的吃穿用度超过了皇帝,这实际上也表明桑哥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贪污腐败的问题,他优厚的生活方式甚至引起了皇帝的嫉妒,这也是他被诛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桑哥在元代初期的历史上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进军西藏地方并驻军,巩固了元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同时他整顿财政,对元初中央政府的财政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桑哥提高税收,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元初经济的发展;同时他生活奢靡、贪污腐化,以至于最终在政敌的打压和皇帝的钦定下被诛杀。因此,桑哥的历史形象其实具有两面性,是一个毁誉参半的政治家。
四、结论
通过对《元史》和《汉藏史集》的比较研究,桑哥的历史形象逐渐明晰化:一方面他通过进军西藏并在西藏地方驻军,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同时他对元初财政进行钩考,保障了元初财政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他提高税收,置黎民的生计于不顾,不利于元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其生活奢靡腐化,严重影响了当时政治的清明。我们对于桑哥历史形象的塑造和还原,与《元史》中的“奸臣”形象和《汉藏史集》中“高大贤能”的形象都不吻合,这其实是在史实基础上的一种客观解读,符合历史的事实。
实际上,一个历史人物在参与历史实践时,必然会受到客观政治形势和文化形态的制约,桑哥的人生历程也是如此。桑哥作为一个畏兀尔化的藏族人,能够在元初中央政府担任高级官员,自然是由于元代实行的“四等人制”的民族政策,这使得边疆各民族人们(色目人)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因此桑哥才有机会进入元代中枢系统并充任丞相。同时,桑哥本身十分出色,他不仅通晓各种语言,而且性情机敏,先后得到了八思巴的协助和元世祖的信任。而这一切都受到了元代文化形态的制约,由于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存在,因此桑哥的才能在这个多元的文化形态里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诚然,桑哥在历史上留下了毁誉参半的历史形象,这也是当时政治形态的一种客观表现:当时的元朝刚刚建立,没有足够的财政保证政府的运作和蒙古贵族的享乐,因此桑哥提高税收的政策似乎是一种必然之举;而有元一代,政治十分黑暗,贪污腐化亦是一种常态,因此桑哥走向贪腐也是社会现实使然。
总之,通过对《元史》和《汉藏史集》的比较研究,桑哥的历史形象逐渐明晰化,桑哥既为元初政治的巩固、财政的好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他提高税率的政策也损害了人民利益,而他本人奢靡腐化、专横跋扈最终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桑哥毁誉参半的历史形象受到了当时政治形势和文化形态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性不仅塑造了历史本身,而且丰富了历史的内涵。
[1]仁庆扎西.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J].西藏研究,1984(2):64-68.
[2]尹伟先.桑哥族属问题探讨[J].民族研究,1998(1).
[3]杨德华.元代藏族宰相桑哥理财的政绩[J].中国藏学,1995(4):64-69.
[4]伯戴克.中部西藏与蒙古人——元代西藏历史[M].张云,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
[5]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7]陈庆英,沈卫荣.简论“汉藏史集”[J].青海社会科学,1988(4):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