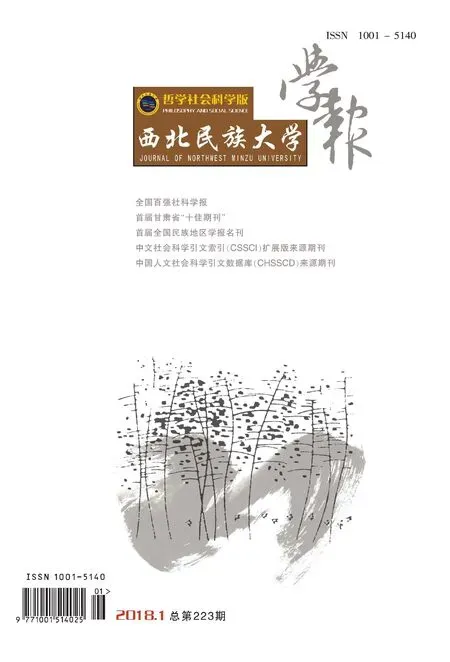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发展中国民族关系
——乌·额·宝力格《通向“外亚”的“内亚”之路》述评
多杰昂秀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一带一路”倡议象征着一种全新的亚洲秩序,甚至世界秩序的建立,这促使我们重新考虑中国和周边区域的关系。在“亚洲的中国”议题之下,我们必须思考,要成为整个亚洲的领导者,中国与亚洲各个板块间的连接点在哪里?什么才是推进并领导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动力和价值基础?就此问题,剑桥大学著名人类学家乌·额·宝力格教授(以下简称宝力格教授)在中文学术刊物《文化纵横》2017年第2期上发表了《通向“外亚”的“内亚”之路:“一带一路”与中国亚洲新秩序的构建》一文,引起学术界的一定反响。宝力格教授于同年4月3日—7日,受邀访问了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就中国民族关系、中蒙关系与“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等相关议题进行了多场学术讲座。笔者有幸聆听到宝力格教授的系列讲座,关注到宝力格教授关于中国民族关系的研究中不乏建设性的意见。受其启发,本文在宝力格教授的学术思想脉络之下,对其论文展开述评,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作为发展中国民族关系的新契机的认识,探讨中国民族治理及其相关话题。
一、亚洲与“亚洲中的中国”
亚洲在哪里?这常常不是一个由亚洲人自己发起的问题。相反,它作为欧洲的衍生物,在以欧洲为参照之下才成为了一个被认真对待的话题。实际上,亚洲从来不是一个在政治抑或地理空间认知上的统一实体。众所周知,它被分割成了几个板块:内亚、中亚、东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等等。正因为如此,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亚洲的认识多是基于各自碎片化的想象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对于“亚洲的本土”或“中心在哪里”这个问题上,亚洲内部并未达成共识。这与现如今欧盟等区域致力于打造“一体化”的进程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景象。然而,亚洲打造共同体的实践却并非始于今天。近代历史上,孙中山受到日本“亚细亚主义”的影响,曾于1924年提出过“大亚洲主义”,其“三民主义”思想中构思的大同世界理想就体现出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想象。到后来的冷战期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并列为第三世界,并试图成为这个共同体的领导者,然而这种尝试也是失败了[1]。
今天,伴随美国领导力的日渐式微和中国的强力崛起,“一带一路”倡议成为重新连接亚洲各区域的新的尝试,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与其周边区域的关系。因为从地理区域上看,亚洲内部的差异是如此显著。它的西部、中部与东南部是伊斯兰文明为主导的区域,南部印度构成一个独立的多元文明区域,而在东部,中国与日本、朝鲜与俄罗斯之间也没有形成了一个亲密的共同体关系。就中国自身而言,其自我想象也是长期游离于亚洲之外。在中国的“天下”体系之中,亚洲过去偏居“中朝”一隅,属于化外之地。按照朝贡体系和“五服”观念,内亚边疆以及更为遥远的区域都曾是“四裔”,而中国自然不在其列[2]。然而,如今面对诸多独立的国家实体来重新想象“亚洲的中国”,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领导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愿景,除了同其外围地区建立经济与贸易合作关系以外,是否需要更为重要的动力来源和价值基础呢?有意思的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沙漠骆驼商队作为“一带一路”的形象化标志,并非是一个来自中国本土的符号想象,其具有典型的中亚、内亚风光,也即拉铁摩尔称之为“内亚边疆”的风光[3]。换言之,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内亚作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已经成为中国将自己想象为“内亚国家”,进而对外展现自我的“符号表达”。这迫使我们在想象“亚洲的中国”这一新的议题时,从族裔、文化以及地缘等方面都将中国重新定义为中国和内亚的结合体,而非单纯的等同于汉族的中国[1]。
二、“外亚”元地理:宝力格教授的原创概念
既然“内亚”是中国的有机构成部分,那么谁是与之对应的“外亚”呢?在“内亚”与“外亚”之间我们又该做出怎样的认知调整?面对亚洲大陆缺失“元地理”认知的困惑,宝力格教授借助美籍泰裔学者ThongchaiWinichakul之“地理身体”(geobody)[4]概念,提出了与中国内部的“内亚”相对应的新的政治地理概念——“外亚”。如其所言,“这样既维持了中国之差异性和中心性的特有观念,以及中国与内亚间的有机连接,还能够体现中国在其要建立的新世界秩序格局中与亚洲其他区域紧密合作的愿望和努力。”[1]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宝力格教授并非暗示要恢复过去中国天下体系关于“内”与“外”的世界秩序构造,即从“中央”来衡量其他文明程度的等级秩序,而是对此有所设限。那么,又该如何进一步来理解“内亚”与“外亚”之间的关系?因为若以民族主义视角去看待,内亚作为中国的边疆,往往被视作负面的异质性存在。但是从“地理身体”的角度来看待内亚,中国的内亚边疆民族同其外围地区形成的是一种无中心的自然联系,无论从血亲上、文化上、心理上还是从宗教上都无可争辩。例如,从中国东边开始,东北的朝鲜族与其外面的朝鲜和韩国是同一个民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边境有同民族亲属;内蒙古和蒙古国之间同样如此;在往西北方向来看,哈萨克族在蒙古国西部和哈萨克斯坦有民族亲缘关系;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有同族的关联。尽管维吾尔族在新疆以外没有和哪个国家有同族,但是穆斯林与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所有伊斯兰国家都有宗教上的关联。在西南方向,西藏也与印度的拉达克、尼泊尔、不丹有宗教和民族上的关系。贵州、云南的许多民族在泰国和缅甸也都有同族[1]。
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否认各民族有其国家归属和存在国家间领土界线的事实,内亚同外亚的文化—社会边界不必与其国家边界相互一致。*有关此话题的法律人类学讨论,可参见谢晖.族群—地方性知识、区域自治与国家统一——从法律的“普世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说起[J].思想战线,2016(6);另可参见[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M].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面对这一事实,需要我们从地理政治的角度,对以内亚为代表的跨境民族做出新的认知调整,而不再是依靠传统的“怀柔远人”“羁縻”的手段和策略来笼络边疆。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有所作为、充满自信并向外发展的国家。这就要求中国重新调整其国内的边疆政策,使之匹配于新的大国身份,即在定位中国及其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上,承认内亚公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缔造者的同时,承认他们与外亚之间存在相同的一面,而不是选择对其刻意回避的态度。也正是基于中国自我定位的悄然变化,边疆地区对此应当有敏锐的洞察,并积极承担起“一带一路”沿线中的基础研究,适时调整已经不切实际的民族观,以中国自信去回应各类现实的挑战。现如今,广阔的内亚边疆地区不仅不是“悲情之地”,而且已经成为中国通向外亚,连接欧洲和东亚的核心地区,这一没有固定边界和游离的内亚资产,应当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重要动力和关键纽带。毫无疑义,“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不仅需要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支持,还要获得各内亚人民的支持,因此就需要从正面的向度重新调整对内亚的定位,承认并接纳其异质性。对此,宝力格教授多次提到将“悲剧”化为“希望”。
三、被遮蔽的“内亚”主体性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史学想象了一个以长城为界线的中国,以及一个富有英雄气概的中华民族,歌颂着他们在历史上赶走了内亚入侵的蛮族,文天祥、岳飞等都是这一历史叙述的典型人物。不难发现,在这样的民族主义史学观看来,对待“内亚”的态度要么是通过坚固的防御体系来“堵截”,要么就是将其“驱逐”。宝力格教授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假想了自我与他者对立的类似于免疫学的语境,即一个纯净的、脆弱的自我,对应着一个能够对我产生致命危害的非自我,而只有通过杀死异物其才能存活下来。然而,这一历史叙述既受到以“新清史”为代表的国际学界的挑战,也受到来自国内政权和学界重新反思中国历史的质疑。例如,从清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近代中华民国提倡“五族共和”之间,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现代中国的形成是以“清帝逊位诏书”这一具有宪政契约性质的文书,从而实现将包括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内亚资产转让给了中华民国,使其成为清朝帝国的法定“继承国”。*中国宪政学者对1911年辛亥革命意义的讨论与解读说明了这一点。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常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显然,这重构了不同于以往的将中原与内亚对立起来的中国,代以“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承认了“内亚”的主体性存在[1]。
而由自我与他者从假想对立到承认彼此共生关系的转变,却引发了中国认同的激烈讨论。1939年到1940年之间,顾颉刚、傅斯年与费孝通、翦伯赞等学者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问题展开了多次辩论。这场争论产生于抗战全面爆发的背景,顾颉刚与费孝通之间的讨论基于二人不同的民族观。顾颉刚从传统民族史观出发,认为内亚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主张在国难面前通过彻底同化来消除内亚异质性。而从英国留学回来的费孝通则以人类学视角对顾颉刚的观点提出质疑。后来蒋介石介入争论,试图以“宗族论”的提法改写内亚人的族谱。这与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承认少数民族的合法身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华民族”前前后后的争论折射出这个国家急切想寻找一个“民族”的愿望。但这首先需要消解内亚各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冲突。宝力格教授指出,重构一个内亚与中原不可分割之中国的努力,却意外地转变了自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界的发现。如苏秉琦提出的“满天星斗”概念,呈现了中国不同文化和族群无中心的各自分布的事实,从而使青铜时代和当下中国的多民族形态被连接起来[1]。由此,费孝通受到启发,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5]。但是受制于费孝通理论的某些缺憾,以至于后来学者自觉地将之阐述为汉族的“多元一体”学说。如赵汀阳在“天下”的新解中,尽管承认内亚民族有其正当性,却又在“逐鹿中原”的理论漩涡中再一次遮蔽了内亚的主体性,因而难免沦为“一厢情愿”[6]。对此,葛兆光等学者也提出质疑和批判[7],这再一次暴露出“中国”定义的歧义。中国重回亚洲,成为亚洲之一部分,需要告别边疆的“他者形象”[8],走出“边疆中国”[9],凸显被遮蔽的“内亚主体性”[10]。如此,“中国”或许能够得到丰满的定义。
四、中国如何通过“内亚”之路通向“外亚”——兼议中华民族建设
尽管不乏有人假想出一个绝缘体的中国,但中国是“亚洲的中国”这一点无法从现实中予以否认。正是因为中国过早地意识到其与周边世界的紧密联系,从而造就了一个极具包容和海纳百川的中国。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目标,表明了中国自我意识的变化,它不再是过去那个收敛的内向型国家——对内亚人的闯入抱持躲避、抵抗的心态。近些年中国官方话语中频频出现的“自信”这一词汇也表征了中国实现自我转型的方向性变化。对此,很多人俨然不足为奇,觉察不足,进而又出现中国地理认识上的尴尬与迷茫。由此,我们看到在一些表述当中,内亚重新变成了是非之地,成为“一带一路”交往中被提防和遏制的对象。然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引起内亚公民的“焦虑”以及由不被信任所引发的“痛苦”。如果说中国适应“亚洲”的焦虑和不自信源自近代试图闭关锁国的内向性情,那么今天,当中国变得视野开阔,以“一带一路”建设沉着地带领亚洲邻里建立一个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时候,这种针对内亚人的负面情绪就失去了法理和道德上的基础。坦率地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以及它所期盼的结果,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内亚公民,即它是否有勇气和真正的信心,信任自己的内亚公民,让他们去建立一座连接外亚的桥梁,而不是以相反的做法去隔离他们[1]。
中国适应亚洲的焦虑从某一层面反映了内部共同体建设的复杂性,但这并不构成中国实现“走出去”倡议的内部“困扰”。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内部共同体恰恰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前提。在此方面,美国的多元文化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其较为成功的国家民族建设的经验,对中国不无启示意义。在很长的时间里,美国一直将非英语的外来移民视作对美国文化的威胁,因而采取“大熔炉”的政策将其同化到主流文化当中。但是经历1960年的民权运动之后,族群多样性在美国开始得到承认,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借此也重新得以定义。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人群被看作是美利坚民族的财富,构成“美国梦”的重要精神内涵。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成效来看,今天中国的内亚民族以及国境线以外的跨境民族,比谁都更加希望中国在民族国家建设方面有所作为。如此,中华民族不仅将实现一个对内凝聚、关系和睦的共同体的建构;在对外方面也会呈现出包容、开放的大国仪态,从而真正赢得外亚人民的尊重。毫无疑问,这样的“中国梦”也将同中国内亚各族人民的“中国梦”连接起来,并在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伟大“中国梦”当中变得利益一致起来。就此而言,中国各边疆民族地区,如同其构成“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前线,对于发展中国民族关系责无旁贷。总之,有如内亚视角是定义中国的主要参照一样,内亚边疆同样构成新时代背景下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内涵的重要生长点。
五、天下想象:中国道德主体的树立
重构一个以“内亚”为核心的中国,并不是回到“内亚”大陆作为“心脏地带”[11]的另一种中心主义,而是如宝力格教授所言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提升中国民族关系,并将内亚人民纳入到新天下的想象中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宝力格教授并不是要重新恢复一个有内外之分和尊卑之别的天下体系,而是尽其所能在理论上实现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与韦斯特法利亚体系之间的对接。很显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展开的天下想象并非仅仅表现为经济与物质的交换,正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自我标榜的和平道路一样,它同时也是一个道德体系,如同一个像东南亚“星系政权”(galacticpolity)一样的向心制度[12]。“一个‘星系政体’由一个中心和围绕旋转的卫星国或属国组成,而后者可能对其他中心也有附属关系。星系政体中的政治权力不是通过霸道地对边缘领土的控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道德权威和声誉的累积来获得边缘的钦慕和尊重。”[1]这与过去中国仁人志士所努力追求的“内圣外王”的崇高境界有一定的相似性。正因如此,“同气相求、民胞物与”的天下想象成为中国的贤圣向来孜孜以求的道德境界。然而,近代以来深受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国家建构模式的影响,内亚民族认同与其国家认同被推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致使中国“族性”的追求难免引发离心离德的倾向。显而易见,中国认同具有复杂性,只有跳出西方民族国家模式的窠臼,从中国自己的国情来反思民族关系,才能对之做出理想的调适。
中国《宪法》序言开宗明义写到,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适度松绑“关系主义”的民族治理模式,即在保持民族友谊和交往关系的同时,又能确保彼此间有适度的距离和必要的信任[13]。如此,内亚人民也将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而更多地承认并肯定中心的“主体性”;换言之,中心的自我道德树立是实现民族和解,赢得内亚少数民族以及更远的外亚对其“心向往之”的决定力量。而这种道德主体的树立,在各内亚人民可感知的范围内,需要以制度建设的行动能力予以表现。在新中国历史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仅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族之间的政治友谊,同时也为世界范围内建立统一多民族的国家结构形式树立了中国特色的标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50年,这一制度经受住了世界格局变化对中国国家建构的考验,表现出了制度上的优越性。中国领导人在最近的中央民族会议上也指出,“这一制度是对苏联模式、任何形式民族自决的摒弃,是对‘大一统’而又‘因俗而治’政治传统的超越,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创新和沉思熟虑的伟大创举。”[14]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自身而言,这需要弥合内地与内亚的经济发展差异,释放出边疆民族地区作为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管理体制改革和“一带一路”对外交流方面的巨大潜力。而这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自我创新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尽早提上议事行程已经显得非常迫切。
六、结语: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发展中国民族关系
宝力格教授以其宏观视野,为我们审视中国民族关系提供了新的认知点。首先,要摒弃过去“中国与内亚”的二元对立思维,即一种建立在非此即彼观念基础之上的非生态的民族观。实际上,国内学者对此早已有所呼吁。北京大学社会学家马戎教授提出,“汉族—少数民族”的二元认知模式如同“城—乡”二元结构一样是不可取的,它阻碍了各民族公民享有宪法规定之平等权利的实现,成为制造民族隔阂的思想藩篱[15]。马戎教授提倡的无差别之公民待遇的说法与宝力格教授的观点有相通之处。但是,其主张“去政治化”[16]的思路也许并不可取;相反,以宝力格教授提供的认知来看,通过凸显内亚主体性,将“中国与少数民族”的二元结构转变为“三元结构”,既符合真实世界的想象,也是重构中国民族关系的一种新思路。这一思路的优势自不待言,它将中国放置于世界之中,从而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起联系的同时,兼顾到国内民族生态有其可持续性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视为发展中国民族关系的新契机具有重要意义。
内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其不仅连接中国与外亚,构成中国走向外亚世界的必要通道,同时也是中国展现对外形象的重要窗口。当然,将视角转向国内,这就要求承认内亚人民无论在文化、领土,还是在基因上都对中国作出的贡献,并与中心共同组成中国国内的天下体系。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全球化发展业已凸显出西方国家在民族治理与国家建构方面的局限性,这反衬出中国在民族国家建构及其治理方面的某些优势。“新天下主义”思潮的兴起,就是肇事于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法体系的基本单位从而暴露出其弊端的背景。当前欧盟加紧一体化的进程,也是在试图超越碎片化存在的民族国家对跨区域交流的种种限制。而联合国在解决民族争端和国家冲突方面同样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在此背景之下,“天下”被中国学者看好为重构世界新秩序的政治哲学。对此,西方亦表现出一定的“恐华”心态。以“外亚”元地理的新认知实现中国走向世界,既是发挥“天下”体系对世界做出中国贡献的重要保障,又使之与国际法体系得以兼容。然而,这完全取决于中国自我道德主体的树立及其对自我意识的超越。中国民族关系如何发展?将直接考验着中国在领导亚洲命运共同体及其世界新秩序构建中的担当与能力。
[1]乌·额·宝力格.通向“外亚”的“内亚”之路:“一带一路”与中国亚洲新秩序的构建[J].田甜,石含,译.文化纵横,2017(2).
[2]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中华书局,2011.
[3]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SeeThongchaiWinichakul,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M].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5]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版)[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6]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J].思想,2015(29).
[8]范可.边疆——告别他者形象[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12.
[9]邹思聪.靠不住的“自古以来”与走不出的“边疆中国”[N].经济观察报·书评,2017-05-17.
[10]黄达远.从海洋视角到内陆视角:不能把西北“边疆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11]See H.J.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J].The Geographical Journal,No.4,1904.
[12]See Stanley J.Tambiah,“The galactic polity in Southeast Asia”[J].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2013(3).
[13]See Uradyn E.Bulag,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on China’s Mongolian Frontier[M].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0.
[14]国家民族事物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71-74.
[15]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16]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