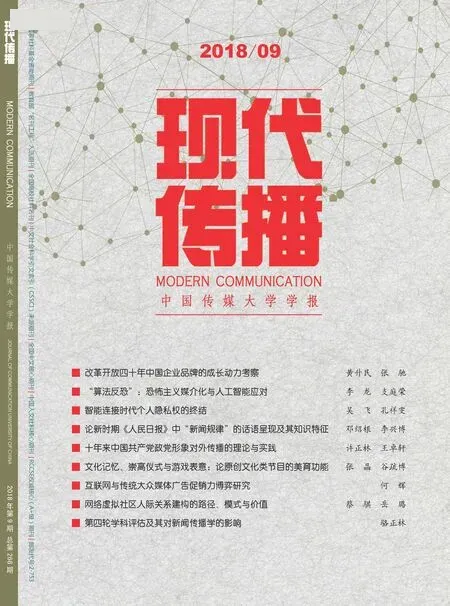政治媒介化与党管媒体的地方实践逻辑*
——基于“海口强拆”事件的个案研究
■ 王 庆
一、前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纵深发展,新旧媒体构成的复杂媒介生态逐渐深入地方社会,地方治理开始面临“媒介化”挑战。就地方公共危机事件而言,“媒介化”一方面是“危机媒介化”,即危机事件不仅发生在实在空间,还延伸和映射到由媒介所编织的虚拟空间。组织和个人越来越依赖于媒介见证、感知和参与解决本地危机;另一方面是“治理媒介化”,即媒介信息及其传播作为一种过程要素,已经渗透到危机预警、研判、决策、执行和反馈等各个环节。地方治理主体和媒介的互动甚至重塑了社会关系,影响危机治理的过程和结果。
“媒介化”极大地突显了危机进程和地方治理中媒介角色的重要性,同时也增大了地方治理决策者应对媒介和公共舆论的压力。如Frank Esser所说,“政治依赖大众媒介调节舆论(媒介报道被视为公众情绪的代理)、引发公众对其政治行动的关注和接纳,以及建立起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将媒介渠道用于政治的公共表征)”,①由此媒介管理成为地方危机治理工作的重心。
党管媒体是我国新闻媒体管理的最高原则。由于国家对媒体实施行政分级制管理,因而各地党委是贯彻和实施这一原则的现实主体。面对互联网技术的纵深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媒介生态变化的新形势,地方党委如何进行“党管媒体”的政治实践,这一政治过程及其策略体系在与媒介实践的互动中呈现出怎样的“地方”逻辑?我们又应该如何通过党管媒体的实践逻辑去评估地方政治“媒介化”的发展现状,这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二、文献综述
(一)“政治媒介化”
“政治媒介化”(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描述的是在政治实践领域中“暗含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趋势”,即“当政治家谋划政治战略和和制定决策时,会越来越把媒体纳入考量之中”。②相比于强调媒介“内容”对政治实践的微观效果的传统媒介研究视角,“媒介化”理论范式更关注“媒介形式”(Media form)③对政治领域的全面“介入”以及传媒与政治的互动如何持续地形塑政治实践。
“媒介化”本质上是一个“过程导向”的概念——“是一个开放且未完成的、发展式的进程”。④Schulz指出媒介化形式有强弱之分,其过程由“延伸”(Extension)“替代”(Substitution)“融合”(Amalgamation)和“适应”(Accommodation)依次组成。⑤Asp和 Esaiasson也认为政治媒介化是一个随着媒介影响力(Media influence)增强而不断发展的过程。⑥
上述“过程”视角突显了“情境”因素之于媒介化研究的重要性。Jesper Strömbäck在将政治媒介化、概念化为四个阶段时强调:“一个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不同政体、政策、事件的影响,都可能在四个阶段的两级之间摇摆游移。”⑦旨在说明媒介影响力在程度和方向上都并非恒定不变,媒介化不能被视为社会机制向媒介逻辑“臣服”的单向度过程,而应该将其看作是一种媒介扩展社会实践者实践可能性的“非决定”过程。⑧换句话说,政治媒介化并不预设媒介影响力大过政治的武断立场。尽管传媒试图藉由报道向机构外部扩张自己的系统性规则,但同时“各种社会组织,亦思考如何回应这套潜规则的运作,并进而试图操纵……”⑨因此,政治本身的能动性和反向形塑力同样是媒介化进程不可低估的动因。这为我们跳脱以媒介为基点的刻板研究视野转而从政治自身出发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将研究旨趣转移到——在媒介表征驱动下“政治机构内部在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以及政治自身效能上的转变”。⑩
(二)“实践逻辑”
“逻辑”堪称媒介化研究的核心命题。按照Stig Hjarvard的说法,逻辑就是“操控一个特定范畴的特定的规则和资源”。如“媒介逻辑”就被视为“所有媒体组织共有的操作模式”,是“媒介选择、解释和结构政治信息的特定规则”。但“逻辑”并不仅限于媒介,政治和其他社会专业领域也都有其自身逻辑。政治逻辑的核心在于“政治最终是关于集体性和权威性的政策制定及其执行”,即由政治来界定社会问题、给出解决方案并付诸行动。
“逻辑”在成为实践之前,隐含着一种“应该怎样”的价值规范,然而一旦被付诸实践,比如新闻工作者运用媒介逻辑从事新闻生产或政治行动者运用政治逻辑进行政策生产,就既不是“逻辑学的逻辑”(即纯粹理性的逻辑)也不是“价值的逻辑”了,而是由实践者与环境互动所生成的新的“实践逻辑”。
布迪厄用“惯习”(Habitus)指称实践逻辑。他特别强调,惯习所产生的行为方式并不像根据某种规范原则或固定格式推演出来的行为那样具有严格的规律性。作为一种生成性的自发性,惯习是在与不断变动的、各种情境的即时遭遇中得以确定自身。实践逻辑是历史性的,并且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惯习又会内化为行动者的意识,去指挥和调动行动者的行为,成为行动者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模式、行为策略等行动和精神的强有力的生成机制。实践逻辑的这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特点,使得它与具体的“社会空间结构”也就是“情境”或“场域”紧密地联系起来。可以说,实践逻辑就是在“关系”与“行为”的面向上得以确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党管媒体的实践逻辑可以被理解为由政治和媒介两种逻辑在具体场域的互赖互动所塑造出的现实行动逻辑。由此可见,“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对决”(Media logic versus political logic)不仅是政治媒介化的现实表征,也是党管媒体实践逻辑的生成机制。
(三)个案研究及案例选择
个案研究以典型事例为观察起点,但它却是以“中观研究”为指归。本研究选择海口强拆事件作为分析对象具有典型性:首先在我国中央-地方的二元行政权力体系中,省会城市可以较好地代表“地方”这个概念;其次在省会城市,国家权力结构和媒介生态既多元又分化,便于观察媒体和政治之间互动的复杂性。媒体系统内依地域划分,自外向内依次有中央媒体、外省媒体和本地省级、市级媒体,他们各自又牵扯到自上而下由中央到省、市甚至区的各级行政机构;而依属性划分,又有主流媒体和社会化媒体;最后,拆迁事件是近年来我国最为突出的地方官民冲突,地方党政在此类社会事件有关的媒体和传播管理方面已经逐渐形成了某些通行的“套路”。本研究以过程和关系构成的行动场域为重要维度展开,因为“过程”使“实践以具体、动态的形式展现”,而关系则嵌入了中观层面上“行动者关系的潜在性”,即“地方”——这样一个特定的行动者活动的环境结构,力求由此达到“对实践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真实把握。”
三、分析和讨论
(一)“强拆”事件过程
2016年4月30日下午,新浪微博爆出一段长达一分多钟的“强拆”暴力视频。视频显示在海口市秀英区当天组织的拆违行动现场,多名全副武装的联防队员挥舞棍棒殴打本地妇孺村民。视频画面十分触目惊心,被打村民大都抱头蜷缩在墙角,哀嚎哭喊声响彻一片。随后该视频又流向天涯社区和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
当地党委宣传部门监测到这一网络视频和相关言论后,迅速采取了删帖、屏蔽、封号等舆情处置措施,同时还通过市属党媒“海口网”等进行了新闻发布,将事件定性为村民“暴力抗法”。这些举措不仅未能遏止住舆情反而加剧了其反弹,迫使当地党委政府不得不决定连夜组织召开媒体通气会,研究舆情处置对策,并通过本地主流媒体发布了“对这次行动的联防中队长王某予以撤职处理”的问责决定。
5月1日起,网民议程转向全国媒体议程。岛外各种媒体特别是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网、法制网、光明网等国家级主流媒体都集中报道了此事。并且,岛外媒体都一致采取了质疑批评当地政府的报道立场,与岛内媒体“力挺”政府的基调形成鲜明对比。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海口市委组织部于5月1日下午牵头召开了第二次媒体通气会,向岛外媒体进行公关游说。同一天,海口市委主要领导还登门看望被殴打群众并现场致歉。随后,媒体又公布了第二轮行政问责决定——事发地秀英区区长引咎辞职以及琼华村拆迁暂停的官方通告。此后几天,其他相关处理结果和表态也陆续见诸媒体,舆论逐渐回落。
(二)政治逻辑-媒介逻辑的互动
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对决是政治媒介化最本质的部分。Jesper Strömbäck在提出政治媒介化的“四阶段”论时,就是以政治逻辑对媒介逻辑的接受度和内化程度来衡量政治媒介化的发展阶段。但同时他也指出,政治媒介化的程度差异可能同时取决于当下所处的历史时期和政治现状,也镶嵌于“具体的实际活动场所”。在地方尤其是省会城市危机治理的特定场域,其行政系统和媒介系统都体现出特殊性和复杂性。一方面,行政系统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层级之差以及地方内部省、市之间的层级交叠;另一方面,媒介系统也因技术差异而引起媒介逻辑走向分化,表现为不同类型的媒介具有各自独特的格式、节奏、语法等,因而也提供了不同的传播实践。
就“海口强拆”事件而言,涉入其中的媒体依技术和权力属性可分为主流媒体和自媒体;但在主流媒体内部,媒体管理的权力来源又有中央、外地、本地之分。鉴于上述现实背景,我们认为,地方党管媒体实践场域是由地方党委-本地主流媒体、地方党委-省外主流媒体、地方党委-自媒体互动的三个“子场域”共同组成,政治逻辑与不同的媒介逻辑在各自场域内以及场域之间交叉互动的过程和关系,共同塑造了地方党管媒体的实践逻辑。
1.地方党委-本地主流媒体:政治逻辑“规训”媒介逻辑
海口市是海南省省会,其辖区内“本地主流媒体”包含省、市两级。其中,海南日报、南海网和海口网被称为当地“三大主流媒体”,代表着一个整合了报、台、网、微平台等各种技术形态的地方党媒体系。在强拆危机治理过程中,当地政府始终最为倚重本地党媒网络,将其作为信息发布第一窗口和舆论战的前锋。例如在4月30日事发当日社交媒体上出现有关强拆现场的打人视频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就通过海口网进行了新闻发布,并由岛内其他党媒进行转载。不仅如此,当地党委政府在危机过程中所采取的各个关键应对决策、表态等都是首选由本地党媒向社会公布。
然而,这些经由本地主流媒体面世的新闻稿件其生产过程并非按照媒体专业逻辑进行,而主要是听命于地方政治机构甚至是政治从业者个人,依照政治逻辑行事。地方党委运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行政手段,如通过下达文件、内部审查、新闻通气会、电话通知、打招呼等插手媒体具体的新闻生产,“由谁报道”和“报不报道、怎么报道都由政府决定”。例如首篇由海口网发布的宣传通稿,就是由危机事发地秀英区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撰写后交由市属党媒海口网首发,但实际上该媒体并未承担采写任务,就更不用说对文中所涉及的事实进行核查了。事后当地相关媒体工作者坦承,实际上他们当时在接到刊登这篇宣传稿的要求时,内心也多少有所抗拒和担忧。因为依据职业经验,他们预感到该文中充斥的大量宣导、训诫式的官方话语很可能会进一步激怒公众,恶化事态。但最终这篇稿件还是被原封不动地刊载了出去,就连作为省级第一党媒的海南日报也保留了其大部分原文,仅对几处敏感措辞进行了“技术性处理”。
本地主流媒体系统在地方危机中,其媒介逻辑明显“规训”在政治逻辑之下,其中根源还是在于区域性党媒所处的制度环境。我国历来有“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纪律规定,再加上“属地化管理”的媒体管理体系,为地方政府控制本地媒体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地方政府是”通过管理人事以管理编辑权”,尤其是媒体的高层领导一般都由省委(市委)任免,甚至是省委市委宣传部门领导直接兼任。因此,在敏感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发生后,党委宣传部门能够第一时间直接介入到媒体运作中,使媒体按照“宣传模式”行事。此时媒体逻辑实际上与政治逻辑是同构的,或者说媒体根本没有自身逻辑。
2.地方党委-省外主流媒体: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合作博弈”
然而对于外地媒体尤其是国家级主流媒体来说,“属地管辖”却为它们参与地方事务时留出了一定的“制度缝隙”。本地政府无权直接指挥上一级国家媒体和平级的外省主流媒体,因而这些媒体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为媒体逻辑与地方政治的“博弈”提供了可能。在强拆危机初期,由于自媒体抢先爆料,并在随后与政府的“扩散-堵截”的信息竞争中获得明显优势,抢占了话语权,从而成功地将自身议程“溢散”到省外主流媒体。外地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的相互激荡,使得一时间针对当地政府的批评性报道呈排山倒海之势。
此时当地党委政府开始意识到省外主流媒体的重要性,他们旋即决定将媒体管理重心从本地转向省外。一方面对省外主流媒体进行直接公关,另一方面在政治体系内部寻求资源以实施间接的行政干预。例如通过本地媒体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公开向岛外发出“欢迎媒体介入”的橄榄枝,以“示诚”姿态力图改善外地媒体印象;召开非公开性质的媒体通气会向媒体人士说明情况和困难,并恳请他们为解决危机出谋划策,以“示弱”策略寻求省外媒体理解和协助。另外,中央媒体的驻琼机构也是地方党政的公关重点。这些央媒分支机构虽然在行政上不隶属于当地政府,但在工作中它们长期与当地党政有密切互动和合作,在地方党政与其中央级母媒体之间可以发挥中介和润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对母媒体的报道产生影响。当对某些省外媒体公关不奏效时,地方党委则转而求助这些媒体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如中宣部和其他省委宣传部,促成他们对各自所辖范围内媒体施以行政协调和干预,从而使媒体有所收敛。
就省外主流媒体而言,地方政治逻辑在危机中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失守”到主动“收复”的过程。“失守”的原因出自制度内部,即央-地分级管理导致的权力分化给媒体逻辑的运作提供了“缝隙“,使媒体有条件按照自己的专业标准和价值取向建构危机事件;但“收复”也同样要归功于制度自身,最终地方党委正是利用各种制度资源、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巧妙地弥合了这些“缝隙”,才使得处于自身管辖权力之外的主流媒体回归到“合作”轨道。
3.地方党委-自媒体: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非合作博弈”
自媒体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媒介。这种媒介之新表现为,过去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传播元素和过程被重新配置,引起新的传播实践。互联网的“开放”“去中心化”和“脱域”机制使得自媒体从技术、内容到制度各个维度都可以独立于政治逻辑,使“赋权”底层民众成为可能。由于在拆迁议题上的政府和民众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对立且互不信任,因此二者关系以“非合作博弈”为主,而省外主流媒体则成为博弈中双方都竭力争取的斗争工具和资源。
在强拆事件现场直接抗争失败后,当地民众利用社交媒体抢先曝光了暴力视频。地方政府得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围追堵截”——通过删帖、屏蔽等方式封锁相关舆论。而民众则是“你越堵,我越发”,跟官方展开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一些具有较高新媒体素养的当地网民还通过自媒体积极寻找外部政治机会,如当地居民“怪大叔V”在微博上发图并直接@了20名知名媒体和意见领袖以获取关注和援助,“laozishiyueliang”则直接用手机拍摄了联防队员现场殴打村民的视频并发布到微博等社交媒体,“天涯社区”也成为网民奔走相告的一个主要场所……这些举动都从外围形成了倒逼本地政府的强大舆论压力。
当地政府在与自媒体的正面交锋失利后在内部及时总结经验,并迅速调整了思路,开始利用主流媒体和自身政治资本纵横捭阖,迂回地收缩自媒体话语空间。首先是采用公关手段削弱了危机初期自媒体与省外媒体建立的舆论同盟;其次是利用本地主流媒体主动向外地媒体输送议程,逐步用“问题解决”框架覆盖“事件归因”框架,以“对冲”“自媒体舆论的影响力。除此之外,还对自媒体采取“从内部攻破”的策略,即利用“网评员”在社交媒体平台以普通网民身份发表有利于政府的言辞。这些网络评论通过运用大量”事实性“论据,包括数据、卫星地图、新闻链接甚至政府机构内部文件资料,巧妙地建立了一个”“村民违建在先、暴力执法在后”“的因果关系,力图重建地方政府“拆迁”政策的合法性。上述一系列政治运作,使这场发端于自媒体的舆论风暴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由盛转衰,化解于无形。虽然最后村民一方争取到了政府“暂停拆迁”的许诺,但其利益补偿以及后续政策等却悬而未决,更重要的是,“拆迁”作为地方社会一个重要议题依然徘徊在政治议程外围。
四、结论与反思
(一)地方党管媒体实践逻辑——策略性严控
实践逻辑具有双重结构,一方面是表现在行动者的内心情感结构中的主观精神状态,另一方面是表现在行动者的现实生活和实际活动中的客观实践。这体现了实践生成机制两个最为关键的特性:一是在宏观上实践观念和心态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二是在微观上实践策略的灵活性和变通性。
透过海口强拆危机中地方党管媒体的运作轨迹和结果,我们也能发现其实践逻辑的一体两面:一方面是“不变”。即地方党委对媒介的“严控”思维和“亲”本地媒体、”敬“外地媒体”和“惧”自媒体的”标准化”心态没变。这些思维和心态是历史性的,既脱胎于长期的实践经验,又对后续的交往实践发挥“框架”作用,决定了政治与媒体交往关系的本质和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是“变”。即地方党委在对媒介管理的具体操作方式和策略上发生了变化,对“未曾遇见的境遇”作出各种“即兴创作”。这些策略不仅因“人”而异,还因“时”而变。因“人”而异是指,对本地媒体、外地媒体和自媒体分门别类地采取“规训”“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的关系策略;因“时”而变指的是,能够适时调整在危机不同阶段的管理重心,并将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行政资源转化为自身与媒介竞争的资本,展现其在强硬管控之外权宜性调适的另一面。
(二)地方政治媒介化——低水平发展状态
按照Schulz所言,“媒介化”关涉的是那些与媒介传播及其发展有关的变化。进一步来说,政治媒介化是政治机构/组织的专业实践在与媒介互动中因受媒介影响而发生的种种“质变”。因此,政治媒介化研究重点应当是关注政治过程因媒介而发生的那些变化的本质是什么?是否改变了既有的政治组织结构、过程和政策产出?透过上述海口强拆危机中党管媒体实践逻辑特征,我们不难发现,地方政治实践虽然全面采纳了媒介新技术形式,并在管理媒介的具体方式和策略上体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但这些都属于“细节性”变化和“权宜性”调适,而非政治对媒介逻辑的主动“适应”或者将媒介逻辑“内化”于治理过程。恰恰相反,地方政治通过对媒介新技术的主动采用以及对政治系统内部资源的巧妙调配,使得自身的控制力和反塑力不断强化,从而能够化解和抵挡外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对其推行自身过程和决策所造成的阻力。
这一现状揭示出,与西方很多研究者所描述的媒介已经“入侵”甚而开始“支配”政治领域的趋势相比,我国目前地方政治领域的媒介化程度仍然较低。尽管地方治理者已经充分认识到大众媒介的重要性,尤其移动社交媒介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合二为一,使得普通民众越来越习惯于随时随地通过社交媒体感知和传播社会危机事件,甚至进行社会动员和集结行动,“迫使政治传播者在试图塑造民意或应对民意的时候必须要将媒介考虑在内”。但传统政治对媒介的重视只是出自一种工具理性,而非自愿归顺于媒介逻辑的支配。说到底,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的对决本质是权力之争,正如Mazzoleni和Schulz所指出的那样,特定的政治文化具有那种遏制媒介压力、保持政治始终处于传统国家生活中心地位的能力。
(三)“体制性”调适——地方政治媒介化的应对之道
对于政党政治而言,政治媒介化程度高低不应当是一个“好”与“坏”的价值判断。不管各国政治在制度和组织形式上存在多大差异,媒介从来都被视为是“国家”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谋求对媒介的有效掌控是政治的本性和基本逻辑。因此,即便Jesper Strömbäck等学者已经在理论世界为我们描绘了媒介化最高发展阶段的社会蓝图——“政治行动者开始有意识地‘内化’(Internalize)媒介逻辑,使得新闻价值标准“内置”于治理过程,媒介逻辑‘殖民’(Colonize)政治逻辑”。但至少目前看来,政治屈从于媒介逻辑甚至甘愿放弃自身逻辑的状况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在确保政权稳定和制度稳固的前提下实施“体制性调适”,与媒体及其承载的舆论进行良性互动,对新媒介逻辑采取深层次的体制“吸纳”而不是绕开,是我国地方党委政府应对媒介化浪潮的现实选择。
当前我国地方危机治理实践应从“权宜性”调适转向更深层次的“体制性”调适。毕竟“权宜性”调适的效力范围仍然局限在体制内部,也就是与政治逻辑同构的主流媒体上,对于体制外媒体的调适方面却乏善可陈。每当社交媒体舆情爆发,地方政府通常只从技术上采取“隔离”“阻断”的硬性手段,或借助主流媒体对它进行“合围包抄”等公关操作,这种应急做法并无益于从根本上改善地方媒介舆论生态。党管主流媒体之所以较为行之有效,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主流媒体与政治逻辑的一体性,使得这个场域更具可控性和可预见性,而社交媒体逻辑却迥异于政治逻辑,带有更多不确定性。鉴于运用传统行政控制手段钳制和打压社交媒体的做法奏效甚微,不如主动学习并掌握其传播习性和规律,使新媒介特有的“沟通”“亲民”等优势为“我”所用。地方政府不妨通过业已建立的政务新媒体和微平台终端将体制内、外相互分化的表达渠道衔接起来,将那些过去被迫寄居于各种社交平台的民间声音吸收、容纳到体制空间内来,赋予其“合法化”和“正当化”身份,使社交媒体的底层话语实践转变为一种制度化沟通实践。
注释:
① Esser,Frank,MediatizationasaChallenge:MediaLogicversusPoliticalLogic,in Kriesi,H; Lavanex,Sandra; Esser,Frank; Matthes,J; Bühlmann,Marc; Bochsler,D (ed.),DemocracyintheAgeofGlobalizationandMediatization,Basingstoke:Palgrave,2013,pp.155-176.
② Peter Maurer & Barbara Pfetsch.,NewsCoverageofPoliticsandConflictLevels:ACross-nationalStudyofJournalistsandPoliticiansPerceptionsofTwoElementsofMediatization,Journalism Studies,Vol.15,No.3,2014,pp.339-355.
③ Hjarvard,Stig.,FromBrickstoBytes:TheMediatizationofaGlobalToyIndustry.In 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Media,ed.Ib Bondebjerg and Peter Golding.Bristol:Intellect Books,2004,p.48.
④ Krotz,F.,TheMeta-processof“Mediatization”asaConceptualFrame,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2007,3(3),pp.256-260.
⑧ 戴宇辰:《媒介化研究: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⑨ 唐士哲:《重构媒介?“中介”与“媒介化”概念爬梳》,《新闻学研究》,2014年10月第1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