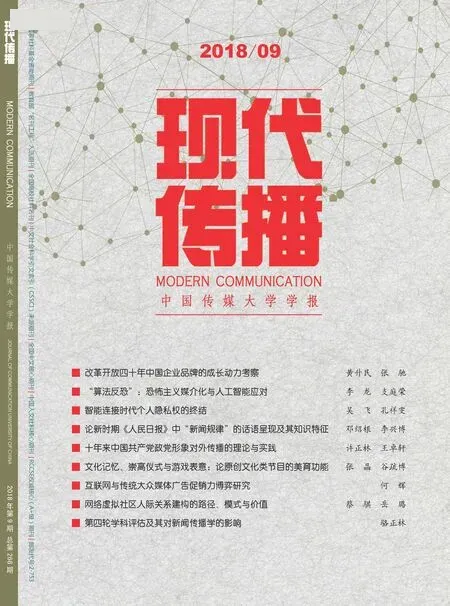多元传播视角下的城市沟通:上海人民广场“可沟通性”研究
■ 钟 怡
本世纪初,随着传播技术革命的兴起,我国开始推进信息化发展。“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5.8%,超过亚洲和全球的平均水平①”。与此同时,“互联网+”“智慧城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与新媒体技术相关的词汇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足见政府在推进信息化过程中的大力和决心。城镇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与人之间更为简单易达的“连接”,为城市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捷,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体验。
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游移在“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城市文脉该如何发展与传承?城市外来人口如何才能真正地融入到城市之中?以及在全球城市的构建中,如何平衡城市的“地方性”与“全球性”?上述这些问题都与传承、交往、交流等传播学议题密切相关。然而,事实证明,这些问题无法经由简单的技术逻辑来解决,要更好地“沟通城市”必然需要引入一种新的、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新理念。
本文从“可沟通性”的概念切入,通过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并以上海人民广场为个案进行剖析,试图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展开回应,推动“可沟通城市”的建设,并对传播的意义进行反思。
一、城市:“可沟通性”研究的入口
“可沟通性(Communicativity)”这一概念来源于“可沟通城市(Communicative city)”的提出。在现有的文献搜索中,较早对“可沟通城市”进行描述的是德国学者昆茨曼(Kunzmann K.R.),他在一篇写作于1997年的论文中指出,新的信息技术应该且能够更好地满足城市的信息需求,并且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信息,从而使得他们在不断变动的城市中生活得更为舒适。信息技术应该从信息提供和参与机会两个方面来保障市民发起和进行围绕城市未来的重要讨论,创造地方认同感和市民自豪感以及提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参与感与获得感。②在数十年后,美国一批传播学者也开始讨论“可沟通城市”。其中,汉姆林克(Cees J.Hamelink)认为,“可沟通城市”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权的体现,即城市应该具备建筑规划、空间、心理、拓扑结构和历史性等各个方面的条件和自主、安全和自由的城市氛围,从而积极促进人们在城市中传播、寻求、接收、交换信息和观点,互相聆听,互相学习。他认为,相较于列斐伏尔提出的城市权利,“可沟通城市”的创新在于提出了沟通、对话这一议题在城市中的重要意义。③加里·加蓬特(Gary Gumpert)和苏珊·J·德鲁克(Susan J.Druker)基于传播学者、建筑师、环保人士、律师、记者等各行业的参会者对“可沟通城市”的描述而总结归纳出“可沟通城市”涉及的三个基本面向: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和社交机会、城市基础设施相关因素和公民政治参与相关因素。④
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传统,西方城市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的成熟相生相伴。而中国长期以来都秉承着乡土社会的传统,中国古代的都城以经济职能为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则是中国“现代性”的产物。再加上东方文化中并不具备西方公共生活的传统,因此,中国城市无论在历史还是在文化传统上,都与西方截然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中,源自于西方的“可沟通性”概念融入到中国语境下,其意义必然会发生转变。孙玮结合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状况,提出“可沟通城市”必须特别关注的四大问题:城市如何既尊重多样性,又打破区隔;城市如何达成时空感的平衡;城市如何实现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城市如何处理城市与社区、乡村、国家以及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⑤吴予敏认为,“可沟通城市”的本质是一个公共性的议题,即“着眼于都市的信息沟通、人际交流和社会文化认同状态,及如何解决日益严峻的‘社会鸿沟’问题”。⑥
上述对“可沟通城市”“可沟通性”概念的已有研究,都关注到了传播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并对之进行探讨,这实际上击中了“可沟通性”这一概念的源头,即“可沟通性”衍生自城市,并且其内涵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演变。而从学术史的角度切入,一直以来,传播与城市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互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城市作为一种建构传播的机制,或者说城市本身便是一种传播媒介。在古希腊,作为社会本质特征的城邦,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交流结构⑦。作为最早的一种城市形态,在古希腊的城邦中,用以公共辩论、商品交换和闲谈的广场,用以祭祀众神、获取神谕(与神交流)、宣传和纪念城邦荣耀的圣殿,用以传道授业的体育学校等建筑物共同形塑了古希腊的交流,城邦空间成为了古希腊交流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古希腊的交流不可能脱离城邦而存在。
二是传播建构城市、形塑城市。齐美尔认为,社会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形成的,由此他将社会学的关注点引向了交往领域,也就是对于传播现象的研究之上。这种思想贯穿他对于城市的认识,即城市是在互动中形成的,而在这其中,媒介起到了建构性的作用。例如,齐美尔提到,正是因为怀表的使用,导致了约会和商定时间的明确性。怀表作为互动的媒介,型构了城市里的时间观念和秩序⑧。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认为,新闻具有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功能,这与他恰好生活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城市化迅速推进、城市社会瞬息万变因而急需传播进行社会调适的生活背景密切相关。而在帕克对于移民报刊的论述中,他同样将移民报刊与城市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勾勒,在这里,“媒介不是被孤立看待的,而是与整个都市发展、移民过程和社会秩序有相伴相生的关系⑨”。
及至哥伦比亚学派出现,芝加哥学派被认为是孕育了哥伦比亚学派,然而实际上,哥伦比亚学派却将芝加哥学派论述的基点——城市,从传播学研究中剥离了出来,将研究的重点落到了具体的传播效果、传播受众等维度,从而导致了城市在传播学研究中的退场。哥伦比亚学派奠基的主流传播学研究范式对于传播学的贡献不言而喻,其与政界、商界的联合为传播学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聚焦于经验研究越来越窄化、越来越精致的研究技术下回应的研究问题却越来越脱离具体的社会情境,存在走入“内卷化”的危险;另一方面,研究得出的结论使得传播效果从“魔弹论”走向“有限效果论”,使得传播学者对于传播的价值陷入了一种越来越悲观的境地⑩。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学者提出,传播研究要回到芝加哥学派,实际上就是要将传播研究与现实的社会情境、社会问题重新关联起来。“可沟通性”作为一个与城市情境密切相关的研究概念,或许能成为传播学“重归情境”的一种有益尝试。此外,以城市为切入口的传播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城市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情境,截至2016年,全球城市人口有40.27亿,而农村人口为34.15亿,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城市正在成为全球网络最重要的节点”。
二、传播:“可沟通性”研究的内核
“可沟通性”概念的演变,同样还揭示了在城市化、全球化和传播技术革命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传播”意义的转变。
1997年,昆茨曼提出的“可沟通性”,将传播的关注点锁定在信息技术用以传递信息的层面。而当时也正好是全球大众媒介发展的鼎盛时期,信息传递恰恰是大众媒介最为重要的功能。在昆茨曼提出“可沟通性”大约10年后,美国学者们将“可沟通性”拓展到了城市中的人际交往、空间实践等更为广泛的维度。这些学者开始意识到,城市中的传播活动并不仅仅发生在大众媒介与城市的互动中,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个体的空间实践同样也是城市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10年后,中国学者再一次拓展了“可沟通性”的内涵,认为“可沟通城市”还应该涉及到文化方面的融合、技术带来的虚实空间的互动以及城市历史的传承等各个面向。而这与当代中国城市正处在传播技术革命之下,以及在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中多元文化在中国城市碰撞与互动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结合上述理解,本文认为,“可沟通性”概念的演变,从以下两个维度,揭示了“传播”意义的转变:
一是传播内涵的拓展,即从单一地关注“信息传递”拓展到了更为丰富的相面。事实上,已有的学术史对于传播内涵的探讨,也并不仅限于主流范式聚焦的信息传递。例如,凯瑞将传播分为“传递观”和“仪式观”,其中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与宗教仪式同源,认为传播“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其最高境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无独有偶,彼得斯对“交流(Communication)”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后,认为交流的意义在于撒播,而不是共享。在他看来,传播的意义并不是拉斯韦尔所言的社会控制,而是要在分歧中获得快乐。
而随着传播革命的进一步深入,新媒体技术内嵌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从根本上改变了媒介、人和社会的互动方式。在这样的情境下,单一相面的信息传递已经无法解释新媒体对于社会形态、社会关系等的建构,因而从多个相面理解传播似乎已经成为新媒体情境下传播学研究的必然。
二是传播意义载体的拓展,即从单一地关注大众媒介向更为丰富的意义载体拓展。在德布雷看来,传播的意义载体极为丰富,包括“行为、场所、文字、图像、文本、意识、有形的、建筑物的、精神的、智力的等”,他举例:“一个国家的资料可以通过国旗、亡灵的钟声、英雄的大理石棺木、村落的碑刻、市政府的三角楣”。
无独有偶,日本学者伊藤卓己直指,“城市即是媒介”,他在《现代传媒史》一书中指出,“如果媒介具有沟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功能的话,那么城市就是媒介。城市里的建筑物向人们发出信息,繁华的街道、公园,或者说办公室与工厂是为了交流而创造出来的”。在这里,城市也被视为是与大众媒介、新媒介等一样的传播媒介。而随着新媒介嵌入城市空间,与城市形成“城市-媒介复合体”,就更加无法在传播学研究中把媒介与城市空间剥离开来,必须将传播研究从单一的大众媒介转向聚焦城市空间、空间实践、城市声音等多元的意义载体之上。
结合上述对传播意义的阐释,本研究认为,从“可沟通性”概念切入,研究当代中国城市的传播现象,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传播的物质性。这一层面主要关注物质层面的传播意义,即物质本身的象征意义,以及物理空间中的空间实践所产生的信息传递、社会交往、意义建构等多个层面的传播意义。
传播的表征性。这一层面延续了以往大众媒介的传统,关注媒介的表征和再现,以及其背后的意义。新媒体技术重构了传播环境,但作为表征和再现的媒介意涵依然十分显著,并且,新媒体技术在传播中同样也具有表征和再现的意义。
传播的融合性。这一层面主要关注新媒体与空间之间的融合,从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传播样态。新媒体的一大特征,就是它嵌入日常生活和空间之中,并且通过这种嵌入,重构了原有的传播方式,并在信息传递、社会交往、意义建构等多个层面产生意义。
三、沟通“异质性”:上海人民广场与城市传播
本研究的研究者在2015年5月至11月之间,以每月5-10次的频率,每次3-4小时的时间长度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对广场空间中的传播元素、社会交往、媒介使用等传播现象进行实地观察。在这期间,研究者实地访谈21人(在下文标记为A组),一对一深度访谈9人(在下文标记为B组),组织4组焦点访谈,每组5人(在下文标记为C组),共计访谈50人。此外,为了更为全面地对上海人民广场的“可沟通性”状况进行呈现,研究还选取了与人民广场相关的报纸文本、城市形象片、流行歌曲、UCG(用户原创内容)、手机App和网络视频等作为经验材料,力图展现新媒体时代参与构建城市空间“可沟通性”的丰富相面。
上海人民广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是地理意义上的上海“零点”之所在地,因此被不少人认为是上海的“地理中心”。今天上海人民广场所占据的土地,最早是英国人在上海建造的跑马场。建国后,跑马场被收回,改建成了用于政治集会的人民广场和供居民休闲娱乐的人民公园。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城市化的浪潮中,人民广场经历了又一次改造,在这一次改造中,原本空旷的广场被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等建筑填充,同时,原先作为人防工程的人民广场地下空间,也建成了商业街和地铁。这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
上海人民广场所处的城市——上海,一直以来就是一座以“沟通”为主要特质的城市。一是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是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都居世界第一,同时又设有中国大陆首个自贸区,还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承载着货物流动、商品交换、资本流动等多个维度的意义,而这些无不跟“传播”密切相关;二是在文化传统上,自上海开埠以来,大量的西方事物首先传入上海,而后再由上海传入全国,上海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经历了短暂的碰撞和冲突之后,也逐渐走向了“沟通”和“融合”,成就了“海派文化”。叶文心称上海为一座“中西交通”的城市,“本质上相异的东西在上海不得不做某种沟通”。而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又作为改革开放的前站,在现代化建设中成为了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中西交通”的上海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上海开放中再次得到延续;三是在城市发展目标上,在上海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了建设“全球城市”的目标,而“全球城市”的核心意义,就是作为全球网络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沟通全球”,促使资本、信息、技术、组织等各种要素的充分流动。
由此可以发现,上海人民广场作为上海这样一座具有“沟通”特质的城市的重要城市空间,在与城市的互动中,这一空间的核心要旨也应当与“沟通”“传播”密切相关。结合上文对于传播的内涵的阐释,即物质性、表征性和融合性,并且围绕上海人民广场这一个案的特征,研究从空间建筑、空间意象和空间实践这三个方面展开,对上海人民广场的“可沟通性”状况进行描述,进而呈现上海人民广场是如何在传播中对上海这座城市进行书写和解读的。
1.空间建筑:历史空间与现实场景的拼贴
历史传承是“可沟通性”的重要相面,同时也是城市空间之于一座城市的重要意义。然而,在现代化改造的过程中,拆旧和建新是城市空间永恒的主题,拆旧意味着将历史遗留的建筑去除,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建新的产物总是带有现代化的特质,最终导致城市空间在城市历史表征方面的断层。
今天的上海人民广场,经历了解放后的两次改造,因此也是拆旧建新的产物。在访谈中,研究者发现,当老一辈沉醉在对自己曾经亲历的那个解放后的人民广场的怀念中时,年轻一代却并不知道人民广场的过去,而究其原因,实际上就是现代化改造带来的一种历史的断层。
这里原来都是空地,很空很大的,从这里(上海博物馆)一直到人民公园,都是空地,现在这边建筑和绿化都多起来了,原来这些都没有的。(A-11,男,71岁,上海人)
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来人民广场,原来市政府的大楼都是人民公园里面的,原来这个里面有划船的,现在没有了。最大的变化是人民公园变小了,原来人民公园大多了,还有划船了。原来的人民公园面积大多了。(A-09,男,68岁,上海人)
以前的不知道,就是听别人讲这里是上海的市中心吧。(A-14,女,26岁,湖北人)
但是,相较于别的城市来说,上海的现代化改造更多了一层意义。这一层意义,是对20世纪30年代鼎盛时期的上海摩登的延续,是“上海的第二次现代化运动”,是新一轮的“在全球化”。循着这样的逻辑来观察今天的上海人民广场,便瞥见了以“现代性”为关键词的“历史的传承”。
一是对历史场景的再现。仿古式、仿制式的建筑是当前城市规划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手段,其意义在于对历史情景的再现。上海人民广场地下空间中的“上海1930风情街”,也采用仿制场景的方式,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街道场景。在这条地下街道中,通过一个老上海有轨电车模型模拟了人们排队乘坐电车的场景,另外还有一个擦鞋童和馄饨摊小贩的雕像,树立在一个电话亭模型的两边。街道两侧是仿照老上海店面设计的店铺和张贴着老上海特色建筑照片的灯箱,用手机扫一扫照片上的二维码,就会在手机上显示出非常详细的关于图片中历史建筑的介绍。这条街道见微知著地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繁华”,而新媒介技术对于这一历史场景的嵌入,更是拉伸了其传播内容的广度,将历史感延伸到了物理空间以外。
很有老上海的感觉,符合我对于上海的想象,而在人民广场建筑这样的一条风情街,我觉得影响蛮大的。现在其实所有的城市都是大同小异的,现代化、高楼林立是比较正常的,所以高楼大厦意义并不大,反而特色街道给人的感觉不错。(C-13,女,19岁,甘肃人)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地板模仿得很好,就像在国外的老的城市,最明显的特征也就是地面,他们的地面都是原来古代保留下来的。而现在的城市都是大的柏油马路,但是这个风情街的地很像是当时那个时代城市的地面,这种地面会传递给我当时的上海的感觉,包括两边的西式的装饰、古旧的灯,这些细节会传递出一种更真实的感觉,让我觉得有点像置身在当时的上海。(C-19,男,26岁,安徽省)
二是与历史空间的拼贴。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改造后,上海人民广场已然成为了一个现代性的产物。然而,当人们来到人民广场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人民广场建筑群,而是其与周边建筑的一个群像。有意思的是,在人民广场周边,既有现代性意味强烈的摩天大楼,同时也有建于1850年的跑马总会大楼和建于20世纪30年代被称为“远东第一影院”的大光明电影院等。这些建筑与人民广场建筑群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着细微的碰撞、注入和融合,城市历史的纵深感由此展现。
在我印象里,上海的历史本身就是从上个世纪开始的,历史比较久,那个时候的上海非常繁华,而历史的建筑物与现在的建筑放在一起,体现出了上海的历史。(C-09,女,21岁,四川人)
这种建筑方式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城市的发展本来就不应该是与过去切断的,而应该是一个整体的过程,有非常多的文化底蕴在里面。(C-16,女,24岁,江西人)
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在今天的人民广场,俨然形成了一种通过地理空间而表征的、历史的对话,作为上海重要城市特质的“现代性”,是这场对话的关键词。在人民广场,浓缩了现代性的流入(跑马总会大楼)、第一次现代性的鼎盛(大光明电影院、1930风情街)和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改造(当前的人民广场建筑群)这一时间线索,展现了上海城市发展的缩影。从这一角度来探讨现代化改造,就可以发现,现代化改造实际上创造了一种现代场景与历史空间的共生,而现代场景在未来,也将会是历史空间,因此,现代化改造下形成的人民广场,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海最鲜明的写照。
2.空间意象:“一千个人眼里的一千个人民广场”
空间意象是个体与所处环境双向作用的结果,因此,空间意象的建构实际上就意味着城市空间与个体之间的互动与沟通的状况。追溯历史,跑马厅时期,这一空间的空间意象主要是彰显帝国主义的殖民;而在建国后的人民广场,这一空间最为集中的意象则与政治集会等集体活动密切相关;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改造,人民广场的空间被重塑,其空间意象也随之被重构。
在空间意象的建构中,意象虽然通过个体与空间的互动而产生,但媒介的传播与再建构,对于意象的传播和稳固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在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以“上海人民广场”为全文关键词,对该数据库收录的2013年1月1日-2018年1月1日之间的报纸进行搜索,获得相关报道118篇。
对这些报道进行分析后,研究发现“文化”“商业”“轨交”是这些报道聚焦人民广场的三大关键词,其中,“文化”议题尤为突出。而在对《上海协奏曲》《上海》和《上海:灵感之城》这三部上海城市形象宣传片进行分析后,研究发现,仅在《上海:灵感之城》中,出现了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大剧院这两个文化设施的镜头,而对人民广场的全景,三部影片则均未涉及。在上海“十三五”城市规划中,人民广场与花木地区共同成为了“一轴双心”中的两个文化核心区域。由此可以发现,大众媒介建构的以“文化”为重点的人民广场空间意象与城市未来对人民广场的规划之间形成了极为鲜明的连接与互动。
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媒介的出现,使得城市中的每个人都能够直接参与到空间意象的建构和传播之中。在大众点评网上,人民广场被设置为一个景点词条,有2000多条网友点评,每一个点评都独一无二:有家人讲述的关于人民广场的故事,也有源自于自身空间实践后引发的感想;有对人民广场中的政府、博物馆等建筑场馆的描绘,也有对广场中一草一木的刻画;有对在人民广场参加的某个活动的记录,也可能只是匆匆路过的一点感想。大众点评网上的2000多条点评,建构了一个又一个独特的关于人民广场的空间意象,生动地印证了“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人民广场”。
除大众媒介和新媒介之外,流行文化也参与到了对人民广场这一空间的意象建构当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歌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首围绕“等待”的歌曲通过一种后现代的、碎片化的表达方式,将“人民广场”与“炸鸡”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象勾连在一起,用“人流如织”的人民广场反衬“等待”的孤独,用“市井气”的人民广场匹配“吃炸鸡”的日常活动,从而一个“人来人往”“日常生活化”的广场意象在轻松的曲调中浮现在听众的脑海之中。更进一步,研究者通过访谈发现,这首颇具创意的歌曲,通过对于人民广场的刻画,无心插柳地为上海人民广场的空间意象注入了新的活力,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空间的想象,并且吸引人们回到人民广场,展开空间实践。
这首歌说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我一开始会有意外,但是后来想想其实还是蛮能贴合实际的。因为陆家嘴给我印象是高端金融区,那边的人群应该高端一点,人民广场虽然说也是市中心,也有各种餐厅,但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亲民的。(B-08,男,30岁,河南人)
我在人民广场从来没有吃到过炸鸡,听到这首歌以后,我立刻就浮现出人民广场很多人,人流很多的样子,我在这里,你们在那里,有一种茫茫人海当中渺小的感觉。(C-20,女,22岁,贵州人)
我很喜欢在KTV里唱这首歌,因为我们都在上海,人民广场我们都很熟悉,唱这首歌我觉得能够更加引发大家的共鸣。我每次唱这首歌,无论跟什么人,他们都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也觉得很开心。(C-11,女,20岁,福建人)
(听了这首歌之后)当时我和妈妈只有半天的时间,但是我就想去看看人民广场,所以我们放弃了去陆家嘴。(C-17,女,22岁,安徽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主体与人民广场产生不同的互动,由此建构了不同的空间意象。当前,在大众媒介、新媒介等技术的作用下,人民广场的空间意象呈现一种高度的多元和丰富。并且在个体、媒介与空间的互动当中,不仅仅生产了空间意象,同时也创造了个体与空间之间的连接。与此同时,富有创造力的大众文化不仅仅构建了独特的空间意象,同时还通过这一意象,连接了空间实践,创造了更为具象化的“沟通”。
3.空间实践:以“相亲角”为关键词的创造、对抗与理解
从狭义的角度来讲,“相亲角”实际上位于人民广场旁的人民公园里,但是,在访谈中,当研究者要求受访者对人民广场进行描述时,大量的受访者都会提及到“相亲角”,由此可以发现,“相亲角”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人民广场的一个重要的标签。
每逢双休日,位于人民公园一隅的“相亲角”总是充满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在这里,来自上海四面八方的父母替他们的孩子相亲,学者孙沛东将这一场景称为“白发相亲”。“相亲角”的符号化,就是在这些“白发相亲者”年复一年的空间实践中建构的。在这个过程中,“相亲角”从一个地点,变成了由空间实践生产出来的符号,承载了丰富的传播意义。“白发相亲者”在“相亲角”长期的空间实践中,生产出了一整套涵盖户籍、财产、情感等在内的上海特色的相亲观念体系,而这种老一代上海人特有的婚姻观念,是上海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相亲角”在此则成为了重要的文化传播空间。
相亲主要还是要实地见面的,我跟其他家长见面的过程中,交流了就可以看看对方父母跟我们是不是合拍,有些时候孩子很不错的,学历啊工作啊相貌啊,但是对方家长的谈吐啊什么的,如果跟我们不是很匹配,那也不是很合适。(A-17男,51岁,上海人)
“微信上聊没有用的,一定要出来见面,否则微信聊得再好,出来见一面,就不行了。”(A-18,女,62岁,上海市)
“我跟朋友去人民广场,特地去了相亲角,因为她觉得这个是上海特有的,想见识一下。”(B-06,男,22岁,上海市)
“相亲角给我感觉就是上海的那种父母的要求,对自己的婚姻要求很高的、父母很急的。”(B-04,男,22岁,陕西省)
与此同时,随着“相亲角”知名度的提升,媒介也参与到了对“相亲角”这一符号的再生产之中。2015年3月,一款名为“人民广场相亲角——给父母家长们用的免费相亲网络”的App突然之间火了起来,引发了众多媒体的报道,并且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中刷屏。事实上,世纪佳缘、百合网等网络婚姻平台早已开发手机端的App,因此手机相亲App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这款以“人民广场”命名的手机App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人民广场相亲角这一符号化的相亲代名词的强烈关注,研究者打开这款App发现,其中的一些标题也颇有上海特色,如“浦东股神的女儿”“上海好丈母娘的女儿”“老夫急萨特了的女儿”等,这与上述提及的“相亲角”这一符号承载的上海特色的婚姻观念和“中国式焦虑”实则一脉相承。
而在另一方面,媒介对于“相亲角”这一符号也进行了再建构。2016年4月,一部名为《她最后去了相亲角》的广告片在网络上刷屏,在这部影片开头,父母一代表达了他们“对于未婚女儿的焦虑”,而“相亲角”则成为了父母对婚姻观念的符号。有一位单身女性直截了当地指出“不喜欢相亲角”,因为“相亲角”意味着一种“为物质结婚”“为合适结婚”的婚姻观念。因而在此,相亲角成为了一个对抗的对象。而在影片的后半段,设置了一个以“为了把真实的想法告诉父母”的实体展览活动,在“相亲角”展出了单身女性们的照片和他们对婚姻的真实看法,并且让父母和他们的女儿一起参观,在两代人坦率地沟通了自己不同的观念后,在拥抱和泪水中达成了理解,在此,“相亲角”又变成了一个观念“沟通”的场域,两代人不同的婚姻观念,在此得到了一种“沟通”。
在路易·沃斯看来,异质性是都市生活相较于农村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事实上,当前城市发展中遇到的“沟通”问题,绝大多数都与城市的“异质性”特征有关,例如“全球性”与“地方性”如何融通,流动人口与城市原住民之间如何“沟通”,传统与现代如何实现文化互动等。但事实上,这种可能带来碰撞甚至冲突等“沟通”问题的城市“异质性”,恰恰是城市最为宝贵的特征,因为“异质”意味着丰富、多元和鲜活。因此,探讨“可沟通性”,绝不是要消除“异质性”,而是要“沟通异质性”,这正如传播的意义并不在于达成一致,而在于意义的共存和流动一样。在上海人民广场的案例中,历史的异质性、意象的异质性与观念的异质性在这一城市空间交汇、生发、创造以及被再创造,这实际上便是人民广场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沟通”的意义之所在。
在以往的传播学研究中,新媒体技术被寄予厚望,力图通过技术范式来解决城市中的“沟通”问题。事实上,在上海人民广场的案例中,新媒体确实在“沟通”层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1930风情街里,灯箱上的二维码使得个体能通过扫一扫的方式了解更多的关于上海老建筑的知识,并且构建了个体与建筑本身的连接与互动;在空间意象方面,新媒体技术赋予了个体参与到多元意象的建构之中,从而展示了城市空间意象更为丰富的可能性;而在相亲角,新媒介技术则不断为这一经由空间实践而生产出来的符号增发新的“性情”。由此可以发现,在上海人民广场,新媒体技术确实提供了更多的连接,更多的互动,从而实现了更多的“沟通”。
但与此同时,在上海人民广场的案例中,除了新媒体技术之外,也展示了城市空间在“沟通”过程中更多丰富的维度。其一,是空间本身呈现出来的对于历史的书写和融通。在人民广场,现代场景与历史空间的拼贴,使得现代化建设中可能断层的历史表达得以弥合,上海丰富的“现代性”历史在空间拼贴中流动;其二,是空间实践呈现出来的观念的表达与沟通。“白发相亲者”通过长期的相亲实践将“相亲角”从一个单纯的物质空间,建构成了一个用以表征“父辈婚姻观念”的符号,而子辈又通过媒介对相亲角展开对抗,借此表达自己的对抗。而在这种现象背后,实际上呈现出了一种观念“沟通”和“共享”的可能性;其三,是创造性的大众文化对于空间意象的锻造和空间活力的激活。通过《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首歌曲,人民广场被赋予了一种后现代意味的空间意象,并且通过这种意象激发了空间实践,赋予了空间以新的活力;其四,是大众媒介对于城市意象的表达与呈现。在上海人民广场的案例中,大众媒介建构的空间意象与城市未来的规划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因而也在一定程度成为了政策层面与大众层面沟通的桥梁。
由此,从上海人民广场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围绕城市空间的“可沟通性”的探讨,实际上涵盖在了主体、空间与媒介多重的互动之中。单一的技术范式,并不能根本性地回应当前城市中多元的“沟通”问题,在当前城市中,城市空间的“沟通”价值,与空间规划、主体的空间实践和创造力以及媒介技术都具有密切的关联,“可沟通性”是在上述多个维度的互嵌中型构的。
当然,上海人民广场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可沟通城市”的城市空间案例,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可能存在一个面面俱到的、完美的“可沟通案例”。本文只是将其在“可沟通性”众多维度中表现出来的“沟通”的偏向进行了阐释,以求能够管中窥豹,对当前城市中存在的部分“沟通”问题进行回应,并且提供一种新的理解城市问题的思路。
四、“共存”创造城市活力:城市传播中的“媒介融合”
在上海人民广场的个案中,城市空间、传播媒体、个体实践等多元主体在信息传递、意义建构、观念交流等多个维度,共同构建了上海人民广场的“可沟通性”状况,由此可以看到,在上海人民广场,传播的意义也涵盖了物质性、表征性和融合性等多个维度。
在这个层面上再次探讨在城市传播中的城市媒介,如果媒介的意义在于沟通信息、实现互动和意义建构,那么,城市媒介就不仅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和新媒介,还应该包括城市空间和在城市空间中创造各种空间实践的个体。在此,本文借用“媒介融合”一词来形容这种现象,认为当前的城市传播也进入了“媒介融合时代”。“媒介融合”最初来源于对整合多种技术的媒介业态的形容。而延伸对媒介融合的探讨就涵盖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三大维度,在此,媒介的意义已经不限于媒介业态层面。那么,循着这样的逻辑,城市传播中的“媒介融合”,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在城市传播中,城市空间、媒体、个体等多元主体都承载了媒介的意义;二是城市空间的“可沟通性”是在上述多元媒介的融合中构建起来的,不是单纯的传播主体的叠加,更重要的是多元主体的融合互动。
此外,上海人民广场的个案启示我们,“可沟通性”的意义和城市传播的价值,并不在于通过信息传播来消除分歧,正如人民广场在上海这座城市中起到的“沟通异质性”的意义一样,传播的意义在于给差异性的观点多一些表达的空间和平台,从而使得差异能够更好地共存,城市与社会的活力,将在差异的共存中得到进一步的激活。这种观点也回应了文章开头提及的城市文脉的问题、城市外来人口的问题和全球化与本土化如何共存的问题,同时,也恰恰与互联网时代多元平等的核心精神不谋而合。
注释:
① 《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新华网,www.xinhuanet.com/info/2018-02/02/c_136943383.htm。
② Nico Carpentier.TheBellyoftheCity:AlternativeCommunicativeCityNetworks.In: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70 No 3-4.SAGE,2008:237-255.
③ Cees J.Hamelink.UrbanConflictand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70 No 3-4[C].SAGE,2008:291-301.
④ Gary Gumpert & Susan J.Drucker.CommunicativeCities.In: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70 No 3-4[C].SAGE,2008:195-208.
⑤ 孙玮:《城市传播: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
⑥ 吴予敏:《从“媒介化都市生存”到“可沟通的城市”——关于城市传播研究及其公共性问题的思考》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3期。
⑦ [法]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邓丽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⑧ [德]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⑨⑩ 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书城》,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