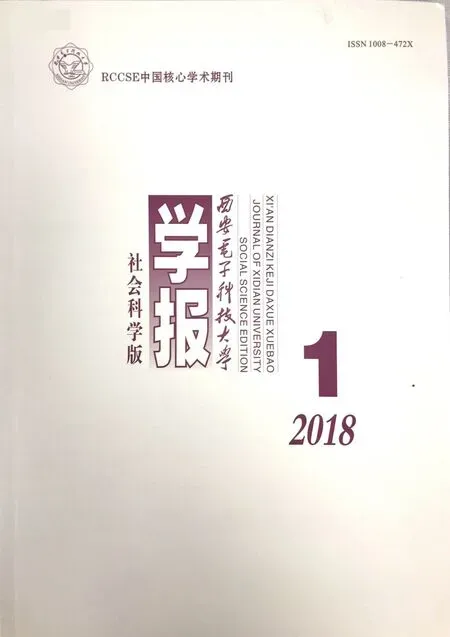电视问政节目的有效性反思及改进
赵景辉
电视问政节目的有效性反思及改进
赵景辉
(陕西电视台,陕西 西安 710062)
电视问政是媒体代表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重要方式。电视问政中公众对节目问责功能的强化遮蔽了问政节目的改进功能,从而降低了问政节目在实现社会善治中的有效性。因此,建议政府强化问政节目的改进功能,媒体加强对问责改进效果的持续报道,社会建立改进导向的节目质量评价体系。通过监督类节目问责功能的实现提高其有效性。
电视问责;有效性;舆论监督;善治
电视问政这一源于西方的监督类节目在我国已走过了十三年的发展历程。从2005年兰州市电视台的“‘一把手’上电视”到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杭州电视台的“我们圆桌会”,西安电视台的“问政时刻”,近十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开设了几十档电视问政类栏目。目前问政类节目影响力最大的是西安电视台的“问政时刻”和“每日聚焦”。“问政时刻”每月一期直播,每期90分钟;“每日聚焦”每天一期,每期5分钟。西安电视台以融媒体全方位的方式,进行网上征集话题。市委主要领导圈定选题,通过暗访制作小片,在演播厅进行现场问政领导并将过程进行直播。同时以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助力,让老百姓零门槛参与现场办公,督促热点难点问题解决。尽管问责类项目相对受到公众欢迎,但是其含义和效果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电视问政是“执政者、社会公众借助于电视媒体对公共事务展开咨询、讨论和协商,并以监督、问责为取向的政治传播活动”[1]。也有学者认为电视问政是一场政府指导、媒体搭台、多方参与的公共新闻运动[2]。有公众认为电视问政是一种真人秀,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尽管公众对电视问政褒贬不一,但是电视问政节目的收视率却一直居高不下,而且揭露并有效解决了许多问题,因而成为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这一节目将作为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直接方式而长期存在,但是这一节目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其有效性是否还有提升的空间呢?如何提高问政类节目的效力?这些是当前新闻媒体工作者和研究者应该关注的话题。
一、电视问政类节目的有效性反思
电视问政是官员、媒体人、民众、学者嘉宾组成的多元参与社会治理的形式,目的在于推动政府的“善治”与公共利益的更好实现,由于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而经久不衰。政府将电视问政看作是治庸问责、沟通民意的新渠道,不仅希望密切与民众的联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而且希望在文化、社会管理领域获得更多经验与建议,增加自身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使公众的权力意识与民主观念不断提高。民众迫切希望通过更加直接的渠道与平台表达诉求、实现政治参与,以获得在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等领域更大的发言权与影响力。总之,电视问政节目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直播方式聚焦社会热点问题,吸引公众参与,揭示问题,提出改进性意见,实现对公共管理事件的问责和改进,从而实现善治。因此,判断电视问政类节目的有效性,主要看问政类节目对社会善治产生的影响。有效性指目标的实现程度及其产生的影响力。电视问政节目的有效性取决于节目的目标实现程度及其产生的影响力,目标实现与目标实现的过程密切相关。主要指问政节目的选题,问责的形式和问责主体的专业化程度。问政类节目播出十几年来是否实现了社会善治的目标?彻底解决了社会现实问题呢?相对其它节目,问政类节目的确因其直观性和真实性,在短时期间内高效地缓解了社会问题。比如,2018年4月8日西安电视台播出了观众期待已久的“教育问政”节目,邀请了西安教育局及区县教育局局长、中小学校长、专家、公众代表聚焦西安义务教育的问题。深刻揭露了西安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引起的“天价择校费”、“管理不规范”、“辅导机构丛生”等教育乱象,公众现场给出了对西安教育21.89%满意度的评分。节目播出后,西安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教育乱象引起教育部的高度重视,在4月12日派出教育部督导办专家专程调查西安教育。西安所有辅导机构在问政期间全部停课,中学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周六补课也全部停止,中学教师和学生终于有了双休日,持续了十年的小升初奥数择校考试也在今年停止,变成了摇号政策。西安基础教育的问题终于在问政中浮出水面,并得到了相关负责人“连夜整改”、“彻底排除”的承诺。教育问政对西安基础教育的改革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电视作为一种视听的结合体,声音与画面的完美结合不仅带给受众极大的视觉冲击,也因为它能完美的再现外部世界而带给观众“眼见为实”的心里体验,现场的证实性也就成为电视传播媒介最为重要的本体特性。电视新闻报道将电视新闻本质的真实和新闻报道表现手法的真实统一起来,即真实性与真实感统一起来。特别是在暗访式的电视新闻报道中,对违规补课、择校高收费问题的报道,使辖区负责人在直播现场看到为之汗颜。原生态的声画形象更好地印证了新闻的“真”,使信息的传播有力量、有信度[3]。因此,许多公众认为电视问政是最有效的问责形式。但是,电视问政是否彻底解决了棘手的社会问题,如果是,为什么许多地方已经被电视问政过的领域,依旧问题丛生?由此看来,电视问政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只是有限的进步,其效力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哪些因素制约了电视问政节目有效性的发挥呢?
二、电视问政有效改进的制约因素分析
电视问政的目的在于改进。制约电视问政有效改进的原因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问政的高风险影响参与者的积极性;二是节目缺乏持续问责改进机制导致对效果的忽视;三是缺乏节目问责效果的评价机制。
(一)电视问政的高风险影响参与者的积极性
虽然电视问政节目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启动的,但是以问题为切入点的问政类节目直接让负责人面对镜头接受公众的问责,甚至让公众当面指出问题,让相关领导直接做出正面答复,答复的结果有可能决定相关负责人的职场命运。电视问政是一种视觉监督,是一种面对面监督,这种舆论监督形式就是将被监督的政府官员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媒体和公众的询问、质问甚至责问,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展现在公众面前,这种视觉监督能产生很强的紧张感和冲突感。因此,组织这类节目,首先让节目负责人面临道德两难的冲突,揭示问题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促进社会善治,但却会使相关负责人感到尴尬,甚至影响他们的前程。参加这种问政节目,对相关部门负责人而言,上问政类节目是一次严峻的挑战,问政的结果与自己的前途命运高度相关,但是又不得不参加,有几个地方的负责人就是在问政节目众当场被撤职。对公众而言,也有说出事实真相会对自己带来负面影响的担忧。总之,问政类节目如果处理不当,必然会对参与者带来高风险。对风险的担忧影响了问政选题的范围和对问题分析的深度,过多的心理焦虑也影响了参与者参与问政的效果。
(二)问政节目缺乏对改进效果的追踪报道
问政节目虽然对某一问题从选题到录制、播出会经历很长时间,但是却很少有节目在问政结束之后进行周期性的回访和再问。电视问政毕竟属于舆论监督,没有行政效力,节目播出之后没有对问政的效果和改进措施进行追踪报道,导致有的官员在节目中承诺之后由于在执行中面临各种阻力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此主管部门也没有监督,导致许多问政中的承诺成为空谈,被公众给予高期望的问政类节目因为没有达到人们理想的目标而被人称为“真人秀”。电视问政的目的在于促进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善治。电视问政的效力指电视问政对社会公共治理产生的影响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效果。问政节目一旦丧失了其改进社会的价值,必将失去其原有的受众群体及其信任。
(三)缺乏节目问责效果的评价机制
目前对电视节目质量评价的主要指标是节目收视率及其产生的社会效益。节目收视率虽然是节目质量的主要指标,但是收视情况只反映了节目播出的时间段观众的参与度,问政类节目的主要目的在于公众参与问责之后相关部门是否采取了合适的改进措施及其产生的社会效益。社会效益虽然也是节目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但是由于收视率简单易测而收视率监测难度太大而经常用收视率代替节目质量,对结果和社会效益评价的忽视导致许多节目不关注节目产生的长期效益。由于对问政类节目评价中缺乏对其改进效果的评价,许多问政类节目关于一个主题只做一期,对后续的改进没有追踪报导。使问责类节目丧失了其应有的改进功能。还有的评价将对问责的结果作为评价节目质量的标志,比如,西安电视台“问政时刻”从2016年4月18日推出,到目前已被追责的官员达到300人,大大转变了西安市干部的工作作风。对官员的追责是节目影响力的标志吗?过于强调问责而忽视改进功能有助于社会问题的彻底解决吗?
三、电视问政节目效力提升的路径探索
电视问政的目的在于通过公众问责改进社会。问责的目的在于改进,而不在于追究责任。对问题和责任的纠结和对改进效果的忽视影响了问政类节目的有效性。因此,提高问政类节目的效力首先要强化问政的改进功能,其次是追踪报道改进措施及其产生的影响,第三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引导问政节目改进功能的充分发挥。
(一)强化问政类节目的改进功能
问政的目的在于改进,而不在追究责任。追究责任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但是被追究责任却是许多官员参加问政节目的最大顾虑。想法设法遮盖问题也成为参与者的行为习惯,对问题的遮蔽会影响节目的信度。如果政府部门负责人,节目制作人,参与者能充分认识到问政节目的改进功能,使公众以多元参与的形式问政、听政、议政,从不同时间反映存在的客观问题,帮助执政者协助解决问题,学者专家和媒体成为官员观点与民间观点的中间平衡者,努力寻找官方舆论场与民众舆论场的最大共识和利益交汇点,促进官员和民众在电视问政场域中既问责也协商,既批评也对话,使电视问政的场域始终保持活力。[4]无论被问政的行政部门存在任何问题,都不因为节目的播出和发现而追究其责任,只关注其采取的改进措施和效果,以问题的改进作为对其执政能力的判断标准,这样参加者就会放下思想包袱,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采取积极的改进措施。
(二)加强对问政内容改进效果的追踪报道
问政节目的播出只是发现并分析了问题,问政节目对社会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改进的过程中。因此,持续进行的问政节目才是监督社会问题有效解决的关键。建议西安电视台在“教育问政”之后继续关注基础教育的改革,在2018年9月开学之初,对教育局负责人及相关领导再次问政。问询对择校问题,违规补课,采取的具体改进措施以及改革的效果,针对改革的效果让公众再次评判,如果公众对西安教育经过半年的改革结果满意度有明显提高,教育负责部门的领导应该得到鼓励,“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社会只有包容错误,给犯错误者改进错误的机会,当事人才有直面问题的勇气,改进问题的动力。否则,问政带来的只有尴尬和恐惧,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持续对改进效果进行追踪报道,既是问政类节目强化问责改进功能的主要手段,也是通过舆论监督促进社会善治的必要条件。
(三)建立以改进为导向的节目质量评价体系
有效的评价是电视节目规范发展和质量提升的内在诉求。评价指标与质量的相关性是评价有效性的重要决定因素。评价指标既是测量节目质量的判断标准,也是引导节目发展方向的指挥棒。因为评价指标具有同时具有鉴定功能和引导改进功能,引导节目向理想的目标迈进是评价的重要功能。因此,如果电视节目质量评价中如果能增设节目帮助改进效果的相关指标,将能有效引导节目制作者通过对改进措施的关注和追踪报道,促进相关负责部门积极采取改进措施,并通过对改进措施的公开,增加公众对该领域的信心,为负责人提供改进的机会和空间。通过电视问政这种舆论监督形式,政府、媒体、公众的沟通形成立体的信息场,每个人在其中都感受到强烈的时间的同步感和空间的存在感,这会形成一种凝聚性力量,人们不再像在网络传播时那样注重自我和情绪化,而是把自己看成是统一中的个体,为了共同的愿景发挥自己的力量,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舆论监督的建设性作用。
结语
电视问政类节目的出现是社会走向民主和善治的标志,使公众有合理的参政议政权利。但是在实践中对问政节目“问责功能”的放大和对其“改进功能”的弱化导致参与者的尴尬,影响了问政节目的效力。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强化问政节目的改进功能,媒体对问政节目播出后的改进效果加强追踪报道,社会建立致力于改进的节目质量评价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问政类节目促进社会改良,实现善治的目标。
[1] 葛明驷,何志武.电视问政十年:文化效应与反思[J].中州学刊,2015(3):168-171.
[2] 顾亚奇.电视问政:中国式公共新闻的新探索[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2):152-157.
[3] 汪明香.从“电视问政”看电视媒体的舆论监督模式与功能[J].现代视听,2013(11):36-39.
[4] 方晨,何志武.场域视角下的电视问政:资本转化与权力生产[J].新闻与传播,2015(12):181-183.
本文推荐专家:
张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学。
段建军,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文学批评、中国审美文化史。
The Reflection and Enhancemen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ccountability TV Programs
ZHAO JINGHUI
TV Accountability has become a very popular public involvement on Pubic governance. However, the stakeholders care too much about accountability instead of improvement. This has limi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ccountability programs on fulfilling its improvement on social good governess. Therefore, it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Fir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mphasize the improvement function of accountability programs; second, the media should focus on the continuous tracing of th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and its effect; at las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improvement-based evaluation system.
TV accountability; effectiveness; social monitor; good governance.
D630.1
A
1008-472X(2018)01-0108-04
2017-12-26
赵景辉(1971-),男,陕西乾县人,陕西广播电视台,研究方向:电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