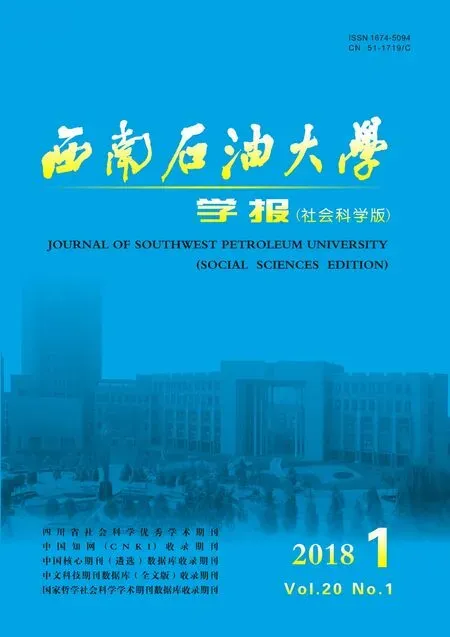《岛》中的麻风病与社会乌托邦
蒋天平,夏双姗
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引言
《岛》是英国女性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希腊克里特岛及其北面的斯皮纳龙格岛上以佩特基斯家族为代表的人们和麻风病抗争的故事。小说一经出版便受到读者的热捧,荣登英国各大畅销书的榜首。国内对《岛》的研究多集中于生态主义,针对“岛”的象征意义和书中主要人物进行分析。余欣认为,岛上的麻风病是要提醒人们保护社会生态和自然环境,是一种警示,而小说中的人物所要表现的,是对生命的敬畏,最后所有病人离岛则代表着重返自然生态[1]。谢文琴认为《岛》中融合爱恨纠葛的凄婉故事贴近现实,“麻风病人”这一特殊群体面对生存困境和压迫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反应具有力与美的震撼性,从而强烈地唤起了人们对生命的思索[2]。张春燕对小说中“岛”之意象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和解读,认为“岛”就是悲凉生活中的希望,是污秽之地的鲜花,而浇灌、滋养这鲜花的,是温暖、博大的人性之爱,“岛”之意象代表了希望和重生[3]。余雅璐通过对《岛》的解读与分析,利用西方存在主义与女性主义等理论,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重点探讨了希斯洛普小说中的存在意识[4]。聂欢认为麻风病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常被污名化为“不洁的、罪恶的”,被社会所歧视和排斥[5],因为感染了麻风病,佩特基斯家族祖孙三代备受污名的影响,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在应对污名后最终各自找到了归属。笔者拟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对小说中的他者形象进行分析研究,探讨麻风病的文化内涵及作者的创作目的。
1 麻风病与“他者”
作为一种文化,现代西方医学代表西方文化和社会体制,是帝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共卫生观念的建立、传染病的研究与防治、热带医学研究的建制、医疗体系的制度化发展等西方现代医学成为帝国内部权力统治的范式。西方对其的传播和推广加强了对异域文化、医学制度的殖民统治。20世纪西方医学的发展与帝国的发展相互支持,促进了帝国扩张和殖民统治。诚如殖民医学史家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所言,“西方医学话语对普世主义与现代性的宣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涵盖了帝国的欲图”[6]。因此西方医学成为帝国医学为帝国服务的工具。同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认为,宗主国文化中的每一种文学和艺术的目标是维护帝国[7]。因此西方人道主义者无法拒绝帝国的诱惑,在20世纪的文学想象中暴露出他们无意识的帝国野心。人是一种政治动物,而医学是一门关注人体的科学,必然受到政治的影响和控制,与身体政治息息相关。
“他者”,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中很常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术语。在后殖民理论中,西方人往往自称为主体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则被称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称为“他者”。“他者”和“自我”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都视为“他者”,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所以,“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医学制度不断进步,体现了西方文化和社会体制的不断进步。在帝国的殖民统治中,医学作为一门工具,起到了维护作用。医学技术的发展能帮助帝国清除异己,稳固权力,西方医学成了帝国医学。“他者”往往不被看作正常人类社会的一员,而属于另外一个低级混乱的世界,常常和一些贬义词联系在一起,如无知、低下、落后、粗俗、愚昧等。他者的存在就是为了确立主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威。在《岛》这一小说中,一旦某人身上出现了麻风病的病症— 奇怪的斑点,就会被送到斯皮纳龙格岛隔离。麻风病人便是生活在主流社会之外、社会的最底层的“他者”。此时,医学成了鉴定“他者”的一种手段,医学术语不单纯的是一门科学术语,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具有明确的形象性和鲜明的感情色彩[8],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另外,小说中的“他者”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健全人中的思想堕落者,安娜便是典型的代表。
2 身体与“他者”
福柯在《不正常的人》一书中就权力的控制提出了“麻风病模式”,即排斥模式,这是与“鼠疫模式”,也就是容纳模式相对立的[9]。对于麻风病这样一种慢性疾病,麻风病人很容易被边缘化,中世纪时人们采取的措施往往就是把麻风病人驱逐出生活的共同体。而在17世纪以前,人们对待乞丐、流浪汉、游手好闲之人,同样也是采取了驱逐和排斥的措施。以此来确保将社会的污染源控制在“一个神圣的距离之外”,通过这种身体的隔离和精神的拒斥,实现社会的自我净化。麻风病人由于其传染性及患病之后肢体外貌的恐怖扭曲,难以逃脱被遗弃的命运,人们把他们拒之于一种神圣的距离之外,等待他们的只有毁灭。小说《岛》中的麻风病人,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也由于麻风病的传染性及其病变带来的外貌扭曲,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的主体性被压制,而他们居住的地方更是人们陌生的、存在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令人恐惧的斯皮纳龙格岛。麻风病被固定在了一种反面宣传之中,他们的形象往往是触目惊心、令人恐惧的,这种可怕的形象具有反面的社会意义。研究者柯罗杰(A Krojer)指出,“在健康‘现金’这种理念下,患有自体免疫性疾病或免疫缺陷疾病,如红斑狼疮、HIV、AIDS等的病人经常会被认为存在道德缺陷,被污名化为新的下层阶级,成为‘政治话语被还原为体液纯洁度’的‘身体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10]。麻风病人身体的腐烂,正暗示着社会的腐败、堕落,只有把他们清除出去,社会才能被净化,重新恢复正常。一个人无论之前是多么的高贵、富有,一旦被认定为麻风病患者,这个人就被划分到乞丐、流浪者之流。而小说中的麻风病人,地位可能更低。“雅典麻风病院......病人吃的都是来自监狱的残羹剩饭,他们的病服是从市里大医院死人身上剥下来不要了的衣服”[11]84。病人待遇之低下令人瞠目结舌,“他们觉得自己还不如寄生虫有价值”[11]85。麻风病人的地位,甚至还在囚犯、死人之下,麻风病人已经完全丧失了话语权。无人看管照顾,他们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只能自生自灭,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这里所反映的,是作者对麻风病人生活状况的担忧,对他们遭遇的同情。
关于斯皮纳龙格岛,小说《岛》中篇首一开始就写道:“1903年至1957年间,克里特岛海岸以北的斯皮纳龙格岛是希腊主要的麻风病隔离区。”[11]扉页麻风病是半个世纪前全球都恐惧的一种传染病,甚至被称之为瘟疫,人们对其恐惧的程度可见一斑。由于麻风病总会导致病人外貌上出现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扭曲,这些异变往往使人感到恐惧。小说中对此也有描述,“一只弯曲的犹如牧羊人曲柄手杖般的手”[11]54,“满脸胡桃大小的肿块,整张脸已变形”[11]55。尽管麻风病患者很少会因此而丧命,而且麻风病难以传染,但是它也许成了所有的疾病中“最声名狼藉的疾病”[12]112。身体的异变,往往会受到他人的歧视,常常成了别人反感和攻击的目标,麻风病人因此成了不受待见的“他者”。麻风病在中世纪时就被看做一种社会学文本,暗示着社会的腐败。麻风病人作为腐败分子,是必须要驱除干净的[8]。在圣经里,麻风病人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人,是丑怪、邪恶、肮脏的,因此欧洲普遍对麻风病人采取歧视、排斥,甚至是驱逐的态度[13]。斯皮纳龙格岛正是作为被驱逐之地,岛上生活着被逐的麻风病人,由于这一病症在当时的医学界还是一种不治之症,所以斯皮纳龙格岛被赋予了禁忌和绝望的含义。麻风病人是受审视的“他者”,绝不允许出岛半步。每个发现自己有麻风病病症的人都竭力地隐藏这一点,生怕被人发现后就要被送往“死亡之岛”,当时人们称之为“活死人之地”[11]40。即使是年仅9岁的小男孩迪米特里抑或是受人尊敬爱戴的老师伊莲妮,都无法逃脱这一命运。主流社会的人们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绝不会心慈手软,所有可能的“威胁”都必须彻底清除。“麻风病人,无论是男人、女人,甚至小孩,都应该与社会隔离”[11]50。主体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他者”只能沉默地接受。
麻风病是让人闻风丧胆的瘟疫,它的降临往往预示着对社会的审判。圣经里经常用麻风病来代表罪,因为罪也会传染、也会伤害人,麻风病成了“罪”的代名词。圣经中常把得了麻风病的人称之为“基督的穷人”,麻风病人溃烂的外表成了他们腐化了的灵魂的反映[14],麻风病被刻上了特殊的文化烙印,成了道德堕落的标志。彼得·理查德兹(Peter Richards)在其《中世纪的麻风病人和他的北方后裔》(The Medieval Leper and his Northern Heirs)一书中曾写道:“麻风病与道德有着深刻的联系,文学作品中对它的描述总是充满了厌恶与歧视。[15]”
“疾病尽管是一种生理现象,但在生理的痛苦、心理的重压中却分明有着人类社会与文化的遮光,负载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批评。”[16]在麻风病人被驱逐前,人们会为他们举办“死亡仪式”,就使麻风病人在肉体还活着时这已经被宣判了其社会上的死亡,预示着和家庭以及社群关系的分崩离析。当伊莲妮要被送往斯皮纳龙格时,人们聚在一起,“相看、流泪、挥手作最后的道别”[11]47,“在这样异常的环境里,都会以为这群人是在参加葬礼”[11]48。这样的场景,何尝不是一种葬礼。伊莲妮即将告别过去的生活,过去的身份,过去熟知的一切人和事,奔赴“墓地”— “死亡之岛”。以往的一切都和她毫无瓜葛,她只不过是个活死人。这与人们根深蒂固的对麻风病人的看法是一致的,麻风病人理当受到驱逐与隔离,来保证社会主体的安全。
3 麻风病人“他者”道德的反写
把斯皮纳龙格岛看作“死亡之岛”,其实只是岛屿之外的人对它的看法,住在岛上的人们,却从来没有从此自暴自弃。初上岛时,被家人、朋友、社会抛弃,麻风病人自然都是满心戚戚,想到的只有苟延残喘。小说中,伊莲妮把往返岛屿与村庄之间运送病人和物资的自己的丈夫吉奥吉斯看作是将亡魂渡到阴界去的冥府渡神卡戎,把带领她参观岛屿的岛主夫人娥必达看作是领着她在冥府参观的喀迈拉,而她能做的,只有“留在这里等死”。当她难过哭泣时,岛主夫人娥必达告诉她:“眼泪在斯皮纳龙格可以自由洒落。”[11]63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牢笼,而这座岛,看似把他们困住了,其实反倒获得了自由,麻风病这一标签使这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有在这里,他们逐渐认清了自身的现实处境,不再自怨自艾,开始觉醒。在这里,麻风病人不再是道德堕落者,麻风病的文学隐喻开始彰显出了其悖论性的一面。
每个被送来岛上的病人都会受到接待,“每当新成员到来,必会受到相当礼节的接待”[11]54。这里的人们甚至还保留着礼节,相反地,在岛屿之外健康的人们却未必。安娜在圣康斯坦丁诺斯节上邂逅了当地富有大地主的儿子安德烈斯,两人一见钟情,然而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安德烈斯说话时总是“惯于发布命令,等着命令被执行”[11]159。明明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写给安娜的信却像“古希腊语法书一样,毫无情义可言”[11]163。安娜和父亲去安德烈斯家拜访时,尽管他们一家尽力表现得礼貌,但谈话间还是明显地趾高气扬,父女俩感受到的只有痛苦和接受审查的感觉。这里所表现的,是麻风病人并没有像传统所认为的那样道德堕落,相反地,他们甚至比那些所谓的“正常人”道德更高尚。诚如在帝国主义者眼中,共产主义者是帝国政治的病毒,必须被清除干净。作为“他者”的共产主义者也并非如帝国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形象。
岛上的人们激情洋溢地把斯皮纳龙格岛变成了没有硝烟、没有邪恶、充满了大爱的世外桃源。小说中,克里特岛曾在二战期间遭到德国纳粹的入侵,而斯皮纳龙格岛却免遭蹂躏。这是因为“德国人害怕仅一水之隔的斯皮纳龙格”[11]133,害怕岛上的麻风病人会把疾病传染给他们。当克里特岛因战乱闹饥荒的时候,隔离区的雅典人却还买得起“巧克力和上等烟草”[11]132,人们甚至开始羡慕隔离区的病人,当他们饱受战乱之苦时,那些病人才是享受着真正的自由,麻风病成了他们的“护身符”。有人甚至划船到岛上去乞求食物。在西方中世纪人们的印象中,麻风病人便是身着奇异服饰,身上带着铃铛到处乞讨的人。人们听到铃声之后会把布施置于路旁,然后迅速躲避。而小说中,手持讨饭碗的成了没有患病的正常人,麻风病人成了布施者,这是他们身份转变的一个巨大转折。战争是比臭名昭著的麻风病更令人恐惧的存在,“占领”是“最可怕的疾病”,作者所表现出的,是对战争的批判与深恶痛绝。而在作者的另一部小说《回归》中,通过对西班牙内战的描写,更是表现了战争的残忍以及对战争的厌恶之情。战争是帝国主义赤裸裸的暴力、压迫、掠夺的体现,二战所带来的创伤,是许多国家抹不去的痛。
“死亡之岛”在岛上居民的努力下,变成了所有人的“生命之岛”“重生之岛”。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员,也有生存的权利、接受治疗的权利。他们知道要做的就是“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11]62,不再做“沉默的他者”,要想摆脱他者的困境,摆脱自己被“自我”视为“他者”的束缚,就必须使自己变得坚强,争取话语权,才能使他者获得完整的自我。在他们的努力下,政府每月会发一定的生活费,给他们建公寓楼来保证每个人都有私密的住所;“开设像样的药店和诊所”[11]61,甚至派医生定期探访,为他们提供治疗。政府之所以会尽量满足岛民们的要求,是为了安抚他们,让他们安分地待在岛上,不至于逃出岛去威胁岛外的其他人。而岛上的居民也意识到这一点,这成了他们争取权利的有力后盾。麻风病人不再是“道德堕落”的代名词,而是开始觉醒、积极争取人权的代表。
身体的疾病和心灵的扭曲,到底哪一种疾病更为严重?安娜是一个健全的人,却是小说中心灵扭曲的代表;而她的妹妹玛丽娅,虽然患了麻风病,却一直是道德高尚的代表,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二战袭来,其他人都是惶惶不安,而安娜却是异常兴奋,在她看来,只要能给她的生活带来变化,她都欢迎。面对德国的士兵,她不是害怕地躲避,而是故意从他们面前走过,想展现自己的魅力。这种对待战争和敌人的态度,显示了她的极端个人主义,让人讶异。当村子被德国占领之后,有英国士兵来支援,为了躲避德军,他们一直风餐露宿。安娜为了自身安全,认为村民不应该维护他们,因为如果被德军发现,性命就不保了,正如有些村民忍受不了饥饿跑去告密。安娜不仅是极端地自私,还有满足不了的情欲、爱慕虚荣、任性、嫉妒心强。嫁入豪门却又与丈夫的堂弟偷情,最终死在了丈夫的枪下。玛丽娅虽然患有麻风病,却被治愈,还在岛上邂逅了爱情。心灵的扭曲远比身体的疾病更为严重,俩姐妹最终不同的结局便是最好的印证。
总之,岛上被放逐的是一群没有“病”的麻风病人,岛屿之外生活着的正常人却过着失序的生活,作者颠覆了麻风病的传统文学隐喻。
4 岛上“他者”乌托邦
乌托邦本意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来的,后由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英国人)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中虚构出了理想之国“乌托邦”。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现在乌托邦一般用来描写想象的、理想的社会。乌托邦作品一般是以作者设定的价值观和社会状况来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并以此来对现实的丑恶社会状况进行批判,设计未来社会的发展方案。这类小说的目的不是再现社会现状和人民的生活,而是以独特的观察视角阐述自己的理性和主张[17]。《岛》是乌托邦小说,表现了作者的乌托邦理想。
同是麻风病人的特殊身份正是岛上居民平等的开始,而平等是乌托邦社会存在的第一要素。正是他们的特殊身份,使他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明白了什么是最重要的,该怎样去生活,怎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岛上有建筑、街道、社区规划,有领导,有日常的管理,有着异常“正常”的生活,甚至还有学校,雅典病人来后,甚至兴建了各种娱乐设施。岛主把土地分给岛上的居民,病人在岛上的住宅院子中,可以种花种菜、做女红,继续自己许多美丽又平凡的小梦想。许多麻风病人在到岛上来之前,也许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在社会之外”[11]54,只能“靠小偷小摸生活”,岛成了他们的“救济所”,不再生活在卑贱苦难之中,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总之,岛上的生活与岛外正常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区别,岛民们彼此平等,相互友爱,共同和病魔作斗争。在这里,麻风病人不用忍受他人的歧视,他们逐渐意识到了自我的价值,不再作为社会之外的“他者”而存在,而是有尊严地活着,甚至比之前活得更加精彩。麻风病患者往往会有抑郁、怀疑、恐惧、自卑、孤独感等心理障碍,对他们的心理治疗尤为重要,而好的社会环境对他们的治疗相当重要。岛给了所有麻风病人归属感,因为每个人的特殊身份,生活反而没有了负担,每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积极向上地生活。作者想批判的,是社会对麻风病人的歧视、冷漠,想要让人们看到他们与常人无异,想人们能够放下偏见,平等地对待他们。麻风病人也有权利过正常的生活,他们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小说最后陈述的情节是:在医生的努力下,很多病人痊愈了,而还未痊愈的病人也被转到更好的医院接受治疗,所有的麻风病人最终都离开了斯皮纳龙格,麻风病隔离区不复存在。这似乎暗示着社会对麻风病人的接受。而麻风病人出岛时的恐惧,害怕疾病留下的、明显的无法消除的残迹会让他们很难重新融入社会,暗示着社会对他们的接纳也许没有那么容易,人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改变起来很困难,思想上的顽疾往往比身体上的疾病难治愈得多。
《岛》是阿丽克西斯寻找家族历史的一部小说。在了解了家族史之后,作者发现寻找遥远的过去是解决危机唯一的出路,因此选了希腊的一个岛来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希腊的民主理论与实践,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希腊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其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全体公民是统治者,参与政治,集体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公民集体内部相对平等;法律至上。小说中,斯皮纳龙格岛上就有着岛外其他任何地方无法相媲美的民主政治制度,岛上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拥有选举权,会定期进行选举,以此来保证人们的不满都能得到重视,不至被忽视,这正是作者心里所向往的那个自由、民主的国度。在这里,麻风病人成了品德高尚、思想自由、平等的代名词。英国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王位是世袭的。英国是个封建等级森严的国家,是个王权和王室特权高于一切的国家。同时,英国又是民主国家,但只是表面上民主,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因为在一个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保证所有人的利益的,实际上都是要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岛上的民主政治,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想象,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出自己的心声,为自己想要的生活发言,但这是不可能在现实世界得以实现的一种乌托邦的想象。1957年,这个小岛被废弃,成了无人居住的一座荒岛,作者选这一岛屿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其命运也许正是她所向往的世界的命运。正如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因其局限性,最终也消亡殆尽。到底该怎样构建民主才能持续永恒,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5 结语
苏珊·桑塔格认为,“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12]88。像麻风病人这样的传染病患者,往往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需要被关注。小说中的麻风病人从沉默的“他者”,到觉醒的“他者”,再到歌唱的“他者”,反映了他们一步步的进步,其形象逐渐由道德堕落者上升到道德高尚、积极向上者,甚至是乌托邦社会的代言人。作者心系麻风病人,对他们积极生活的一面做了大量描述。通过反写麻风病人这一群体形象,批判了主流社会的种种罪恶,期望重建乌托邦社会,岛上乌托邦式的社会是作者的美好想象,反映了作者的社会主义改良思想及乌托邦。作者向往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希望颠覆现实社会的不满,连曾处于边缘、社会底层的“他者”都能够建立出岛上“乌托邦”式的美好社会,这一描述足以引发健全的“我者”的深思。
[1]余欣.《岛》的生态批评解读[J].闽江学院学报,2010(1):89-92.
[2]谢文琴.死亡之岛绽放生命之花—英国当代小说《岛》对生命的诠释[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25):32-35.
[3]张春燕.“岛”之意象的内涵分析—对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小说《岛》的解读[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39-41.
[4]余雅璐.希斯洛普《岛》中的生存意识[J].中华少年,2017(3):291.
[5]聂欢.《岛》的污名研究[J].青年文学家,2016(33):116-117.
[6]Anderson Warwick.Where is the postcolonial history of medicine?[J].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1998:529.
[7][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71.
[8]郑民,王亭.文学与医学文化[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158.
[9]胡位钧.权力的谱系—从“麻风病模式”到“鼠疫模式”[J].读书,2009(10):84.
[10]A Krojer.Fluid exchanges:artists and critics in the aids critics[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2:325.
[11]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岛[M].陈新宇,译.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09.
[12]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陈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3]谷操.驱逐与救助:中世纪西欧的麻风病[D].南京:南京大学,2016.
[14]Brody NSaul.Thediseaseof theSoul:leprosy inmedieval literature[J].Ithaca: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74:21.
[15]Richards Peter.The medieval leper and his northern heirs[D].D S Brewer,Rowman and Littlefield,1977.
[16]韩冷.京派小说的疾病隐喻[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4):81-83.
[17]徐文培.开放、指涉的文本世界:冯内古特小说的互文性解读[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