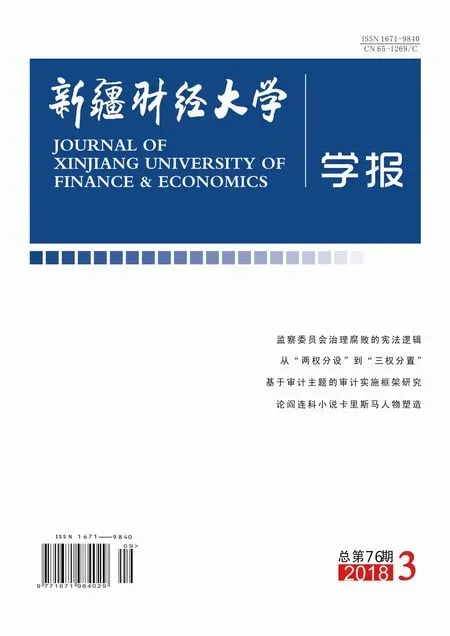妥协与坚持
——西方文化语境下《金锁记》的改写与自译
张诗琦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回顾文学史,我们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交汇和融合。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域外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还包括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二者间的交流不是单向输入或输出,而是双向互动的英语对话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张爱玲是少有的进行双语创作与海外传播的作家之一。本文通过还原并分析《金锁记》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过程及遇到的问题,尝试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切实的案例支撑。下文将重点关注张爱玲的《金锁记》这一文本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多次改写与自译,通过翻译对勘,总结其在自译过程中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试图还原张爱玲为了让中国现代文学进入英语世界而付出的半生努力,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有意无意的妥协与坚持。
一、改写自译过程
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位作家,但初到美国之时,张爱玲在写作和创作上却遭到了沉重打击。她写了大量剧本,却仅仅只能糊口,写了5篇长篇小说都不断遭遇退稿,找不到出版商。在张爱玲的丈夫赖雅的一则日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件小事,“一天夜里,她梦见一位杰出的中国作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相比之下,她觉得很丢人”*详见司马新著、徐斯和司马新译的《张爱玲与赖雅》,台湾大地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赖雅知道,这是张爱玲对贫困和籍籍无名的一种潜意识的抗议。人生际遇的巨大落差激发着张爱玲想要成功的欲望,她内心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注]详见殷允芃著《访张爱玲女士》,原载于金宏达主编的《回望张爱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
对于初入美国文化语境的张爱玲来说,想要快速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获得关注,最好选取她最成功的作品作为进入美国文学界的敲门砖。而《金锁记》这一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被认同和喜爱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她的首选。《金锁记》这一文本经历了以下几次重要的出版和发行。《金锁记》首先于1943年11月至12月在上海《杂志》第12卷第2期和第3期上连载,第一次收录该文的短篇小说集《传奇》于1944年8月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很快便销售一空,风靡上海。张爱玲最初将《金锁记》自译为长篇小说PinkTears(《粉泪》)并于1957年初完稿,而出版她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的Scribner公司却拒绝出版PinkTears[注]④详见夏志清编《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5、10~14页。。虽然在此之后张爱玲对稿件进行精心修改,但仍于1959年12月再次被拒稿。
这对张爱玲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以至于她将PinkTears抛在一旁多年。转折出现在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一年出版,在这本书中,夏志清对张爱玲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注]详见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页。。在其鼓励和推动下,张爱玲再次改译《金锁记》,并取名为TheRougeofTheNorth。根据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件内容大致可以推测TheRougeofTheNorth的成稿时间为1964年上半年,而接下来的时间,张爱玲开始四处寻求出版商,但这一过程却并不顺利④。
随着华语世界读者对张爱玲的愈发喜爱,TheRougeofTheNorth的中文译本《怨女》首先于1966年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发行。而TheRougeofTheNorth也在1967年最终得以由英国凯赛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虽然TheRougeofTheNorth后来受到加州大学英文系主任的大力推崇,但其在出版后引发的评论却很少, 市场反响十分冷淡。直到《金锁记》的忠实自译版本TheGoldenCangue于1981年入选ModernChineseStoriesandNovellas(1919—1949)后,这本小说才渐渐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接受和认可。在这一曲折过程中,《金锁记》经历了张爱玲多次改写与自译,也体现了作家复杂的心路历程。
二、从《金锁记》到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调整与妥协
由于在《金锁记》基础上改写的英文本PinkTears未能面世并被多次退稿,张爱玲不得不将其再次改写为TheRougeofTheNorth并最终出版。虽然《金锁记》与TheRougeofTheNorth在故事架构和主要人物设置上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悲剧的浓烈程度和人物性格上却有较大不同。首先,TheRougeofTheNorth中对原型为曹七巧的女主人公银娣的个性描写大幅平淡化,不但削减了她的疯言疯语和恶言恶语,在故事架构上也更偏向于讲述一个传统中国妇女的悲剧人生,而曹七巧身上原本的疯狂和魔性荡然无存,其所负载的批判性和现实性也有所弱化。在《金锁记》中,曹七巧一出场就难以讨喜,先过足鸦片瘾,再姗姗来迟地拜见婆婆,还强词夺理、诅咒丈夫,无论是对婆家人还是娘家人,曹七巧都刻薄恶毒得罪了个遍。尤其是儿媳因她而死,儿子成了烟鬼、嫖客,女儿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更让读者觉得她死有余辜,不值得同情。但在TheRougeofTheNorth中银娣是一个守规矩的女子,婚后依然清白,短暂的调情让她追悔莫及,即便分家后她引诱儿子吸食鸦片又气死儿媳,但程度分明弱了许多,最后还有了儿孙满堂的结局。张爱玲曾坦言,“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详见张爱玲著《自己的文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曹七巧集中体现了人性之恶,而银娣则是 “眼睛瞄法描法,‘小奸小坏’的人物”*详见水晶著《替张爱玲补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二者的个性差异相当明显。相比曹七巧,银娣虽然吝啬而寡情,但内心仍有温暖的东西,循规蹈矩、怨而不怒。在情节处理上,二者也有所区别,TheRougeofTheNorth不以《金锁记》那样激烈的人物冲突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来贯穿,而更偏向于描写家族内鸡毛蒜皮的琐事,用闲谈的方式穿插在银娣一家的生活里,比《金锁记》拥有更多的生活质感。
其次,相比于《金锁记》,TheRougeofTheNorth在语言描写上也归于平淡自然,具体可对比其中文译本《怨女》。《金锁记》作为张爱玲的前期作品,当中大量使用比喻和夸张等修辞格,如“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艳而凄怆”*,为体现曹七巧的处境和内心挣扎增色不少。而后期的TheRougeofTheNorth,即便是运用比喻手法也显得相对节制,如中文译本《怨女》中,对于银娣歌喉的描写,“她被自己的喉咙迷住了,蜷曲的身体渐渐伸展开来,一条大蛇,在上下四周的黑暗里游着,去远了”*详见张爱玲著《金锁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行文更加平淡节制。
三、从《金锁记》到The Golden Cangue的翻译策略
作为《金锁记》自译的最终版本,TheGoldenCangue最终收录于夏志清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选》中,与TheRougeofTheNorth相比,TheGoldenCangue更贴合《金锁记》的原文,在情节上并未出现较大的改动,张爱玲为了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采取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翻译方法和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保留了原语的陌生感。
对于一些相对容易理解的俗语,张爱玲更多采取直译的方法,将原文直接翻译成英语,然而这种语言上的直译,在异质文化语境下有时会造成意义的过滤和误读。如将“龙生龙,凤生凤”*详见张爱玲著《怨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译为“dragons breed dragons,phoenixes breed phoenixes”*详见张爱玲著《金锁记》,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27、32和30页。。在中国,龙凤是身份的象征,但在西方,龙通常象征着邪恶,凤象征着重生,张爱玲没有用西方文化中其他类似的形象代替,而是保留了原文的表达。又如,将“三媒六聘”*详见Eileen Chang,“The Golden Cangue”. C.T.Hsia.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第140、153、177、184和181页。译为“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wedding gifts”*详见Eileen Chang,“The Golden Cangue”. C.T.Hsia.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第140、153、177、184和181页。。在中国,“三媒六聘”只是结婚习俗中的一个步骤,“三”和“六”也并非实指,而是大致数量,直接将其翻译成“三位媒人与六个结婚礼物”难免造成原语文化含义的缺失,让西方读者不知所云。再如,“夫妻不和,长白渐渐又往花街柳巷里走动”*详见Eileen Chang,“The Golden Cangue”. C.T.Hsia.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第140、153、177、184和181页。,在英译中,张爱玲将“花街柳巷”译为“the streets of flowers and the lanes of willows”*详见张爱玲著《金锁记》,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27、32和30页。,虽然保留了原文形象,但其“逛妓院”的隐含意义却丢失了,在西方读者看来,长白可能只是因为家庭关系不睦去游山玩水而已。又例如,将“天地君亲”译为“heaven and earth and king and parent”,前者在中国是传统儒家道德规范的象征,而张爱玲仅仅将其翻译成互不关联的独立的词语,令西方读者理解起来相对有难度。
类似的例子还有如将“扶不起的阿斗”译为“an Ah-tou that can’t be propped”,阿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形容的是无用而虚弱的人,是刘备的儿子刘禅的小名,仅仅通过直译无法向西方读者展示其背后的文化和历史内涵。但在没有复杂文化内涵的情况下,直译的译文则可以生动形象地传达原文语义。例如将“我是个没脚蟹”*详见张爱玲著《金锁记》,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3、24、30和35页。译为“I am a crab without legs”*详见Eileen Chang,“The Golden Cangue”.C.T.Hsia.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第159、185、155、172、180和187页。,“没脚蟹”是江浙一带的方言,指人没有能力、任人摆布,在这里进行直接翻译,西方读者看字面意思也能有大致的了解。再如将“流水似的花钱”*详见张爱玲著《金锁记》,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3、24、30和35页。译为“spend money like water”*详见Eileen Chang,“The Golden Cangue”.C.T.Hsia.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第159、185、155、172、180和187页。,同样也很有画面感。
对于有翻译难度的俗语、成语,张爱玲或采用意译的方法,或创造性地用相似的英语俗语进行替代。如将“姜家是个大族,长辈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详见张爱玲著《金锁记》,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3、24、30和35页。译为“……the Chiangs are a big clan, the elders keep browbeating people with high-sounding worth……”*详见Eileen Chang,“The Golden Cangue”.C.T.Hsia.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第159、185、155、172、180和187页。。中文原文用“大帽子”来形容长辈权威,若是直接翻译,西方读者难免云里雾里,张爱玲用意译方法,将“大帽子”取其大致意思翻译为“虚夸的财富”(high-sounding worth)。再如,将“手忙脚乱”*详见张爱玲著《金锁记》,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3、24、30和35页。意译为“in great haste”*详见Eileen Chang,“The Golden Cangue”.C.T.Hsia.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第159、185、155、172、180和187页。,将“路远迢迢,打了无数的笔墨官司”*详见张爱玲著《金锁记》,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3、24、30和35页。意译为“After endless long-distance negotiation”*详见Eileen Chang,“The Golden Cangue”.C.T.Hsia.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第159、185、155、172、180和187页。,将“藕断丝连”*详见张爱玲著《金锁记》,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3、24、30和35页。意译为“persist in a friendship”*详见Eileen Chang,“The Golden Cangue”.C.T.Hsia.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第159、185、155、172、180和187页。,等等。虽然采用意译手法在某种程度上仍无法完全传达原语表达的精彩与贴切,但也收到了利于西方读者理解、减少误读的效果。
综上,在翻译中国文化特色词语和方言时,张爱玲主要采取的是直译的方法,即通过直截了当的翻译,以求保留原语言文化的特色,但在两种异质文化语境背景下进行直译,若是太过追求与原文的一致性,反而会给读者造成理解障碍,影响译文在海外的接受效果。因而,从易于读者理解的角度出发,采取意译手法不失为一个可行的策略。
四、改写与自译的原因探究
(一)创作观念的变化
张爱玲创作心态与创作观念的变化与她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她的自身生活经历在其作品当中都有或显或隐的投影。早年残缺病态的家庭生活,使她变得敏感、孤寂、自我封闭,因此对于病态的世界有着格外深切的感受,而她笔下变态而彻底的曹七巧就是这种感受的浓缩与具象。与绝望、惨烈、彻底的《金锁记》不同,TheRougeofTheNorth在意象描写、人物塑造、叙事技巧与情节安排上都显得平淡而哀怨。与《金锁记》从故事的中间开始讲述这一叙事安排不同,TheRougeofTheNorth是按照故事情节发展的顺序进行讲述,相比于《金锁记》浓缩式的描写,TheRougeofTheNorth的故事讲述更加完整从容,娓娓道来。而在情节上的一个较大的改动就是,TheRougeofTheNorth删除了《金锁记》中曹七巧一手造就的女儿的爱情悲剧,这一改动更加深刻地体现了作者创作观念的转变。银娣这一角色,正是对“变态”的曹七巧的“常态化”回归。
究其原因,与创作《金锁记》时相比,改写TheRougeoftheNorth时张爱玲已步入中年,从中国到美国后,事业和生活上遭遇的挫折让她对生存的艰辛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往昔的壮志已被岁月磨蚀,此时的张爱玲褪去了早前的锋芒,从更深的层次审视人生,因而自然获得了一份愈近成熟、趋于沉稳的心态。在1944年发表的《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就对其当下的创作思想进行了初步表述,“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详见张爱玲著《自己的文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正如王维在壮年时能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般义气豪阔的诗句,而在隐居辋川时却是“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诗歌风格日趋平淡自然,充满禅趣。张爱玲中年与晚年旅居美国,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上愈发趋于平淡安稳。她后期将大量精力倾注于《红楼梦》与《海上花》的研究,并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写道,“你这样喜欢《海上花》,我当然高兴到极点,我一直觉得这本书除了写得好,还有气质好”*详见夏志清编《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23、10和4页。。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文”与“质”是一组对应概念,可以大致理解为辞采与内容,这里张爱玲所说的“气质”便是指小说内容平淡质朴。鲁迅也认为,“光绪末至宣统初,上海此类小说之出尤多……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详见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第238页。。可见到了后期,张爱玲更加欣赏平淡自然的小说风格,那么在其改写过程中实践这一观念的转变也就自然而然了。张爱玲认为,安稳是飞扬的底子,从曹七巧的极度疯狂到银娣的四平八稳,这一转变折射出了张爱玲在自我改写的过程中趋于平淡自然的心态变化。应该说,TheRougeofTheNorth中女主人公的身份更符合张爱玲所说的“广大的负荷者”形象,这种顺应现世的安稳且有点小奸小坏的人物,更能代表一种普遍的人生态度。
(二)西方读者不同的期待视野
作为一名作家,张爱玲十分关注读者的期待视野。她在《谈写作》一文中曾说,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乎说人家要说的和说人家要听的*详见张爱玲著《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讲述那些“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详见张爱玲著《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对读者期待视野的精准把握,也是她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然而到了美国之后,全新的西方读者也就意味着全新的期待视野。在1965年12月31日写给夏志清的信中,张爱玲也表达了其已意识到自己的作品让西方读者没有代入感,她分析了韩素音的书在美国畅销的原因,“韩素音也sentimental,写与白种人恋爱,也使读者能identity自己,又引些古诗词等等,不但慕风雅的suburbanites喜欢,就连像高先生,也熟悉中国,照样喜欢而且佩服”*详见夏志清编《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23、10和4页。。此外,相比张爱玲多以上海和香港为故事背景的都市小说,20世纪3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Pearl S. Buck)则将目光投向农村,其代表作《大地》(TheGoodEarth)旨在展示混乱的时代背景下安贫乐道的中国传统乡村生活,关注普通小农家庭的精神世界。而此时,美国读者已经习惯接受赛珍珠小说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对张爱玲小说中描写的“彻底”或“不彻底”的旧中国儿女接受度并不高。张爱玲敏锐地体察到,她陈旧而遥远的东方女性的故事,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陌生而无法带入的。在写给夏志清的信件中也说明了张爱玲在有意识地分析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落实到改写过程中,就成了无意识的迎合与妥协。
1971年水晶拜访张爱玲时,谈到TheRougeofTheNorth出版后的读者反响,曾提到“有一个书评人,抱怨张女士塑造的银娣,简直令人作呕(revolting)”*详见水晶著《替张爱玲补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6页。。由于此前西方读者接触的中国小说人物,大多来源于古典小说,人物形象相对单一、扁平,很少有居于中间的像银娣这样“小奸小坏”的平常人,所以审美欣赏一时难以接受。《金锁记》的故事大多“各有其本”,以李府为创作原型,所描写的情节和人物都源于亲身经历,故而张爱玲驾驭起来得心应手,创作起来文采飞扬。然而到了美国之后,由于“《金锁记》的原文不在手边”*详见夏志清编《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23、10和4页。,故张爱玲只能根据回忆不断改写与翻译。环境的变化给张爱玲带来了很大影响,生活的窘迫使她不能潜心创作,不断遭遇退稿也让她不得不持续调整自己的写作内容。
虽然身在美国,但是张爱玲却无法真正融入美国文化和美国人的生活圈,夏志清后来回忆说,“她不与人接触,只能写她熟悉的事,她改写《怨女》、《半生缘》都是说的老上海,揭露中国人的丑陋,不合美国人的胃口,得不到出版商的青睐”*详见夏志清编《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23、10和4页。,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TheRougeoftheNorth在出版上经历坎坷的原因。所以张爱玲只有不断地回到熟悉的地方,回到她的老上海、老中国,讲述深宅大院里小儿女的爱恨悲欢,描写那些不彻底或彻底的小人物。《金锁记》中对旧式家庭制度对于人性摧残的描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和斗争,充满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对于习惯了温软懦弱的中国人形象的西方读者来说,其远离中国文化背景,缺乏对传统制度的了解,因而无法理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人物的选择;另外也使得欧美读者无法投放自己并从中体会到西方的优越感,而只能获得难以名状的朦胧的东方印象。曹七巧这一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令人理解和同情的悲剧人物,到了西方读者眼中却变得不可理喻。他们不理解中国封建大家庭制度对女人的戕害,自然更无法理解在这一环境下,曹七巧做出的种种选择和反抗。在西方文化语境下,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张爱玲选择将彻底的曹七巧改写成不彻底的银娣,以迎合西方主流文化对中国的印象。
然而一味迎合并不会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全盘肯定,有时也许连读者也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作家也不能一味迎合,也需有对自己写作态度与创作观念的坚持。到了20世纪70年代,张爱玲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翻译TheGoldenCangue的时候,可谓是字字忠实、句句对应、一字未改,说明张爱玲此时已重拾写作信心,秉持其最初的创作观念。可见文学翻译固然要顾及接受国读者的期待视野,但在传播过程中一味迁就也不利于文化立场的坚守。
(三)自我东方主义倾向
“他们想起中国时,会想到龙、玉、丝、茶、筷子、鸦片烟、梳辫子的男人、缠足的女人、狡猾的军阀、野蛮的土匪、不信教的农人,瘟疫、贫穷、危险。他们所听见过的中国人,只有孔夫子一人”[注]详见林太乙著《林语堂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林太乙的这段文字生动描绘了西方人心中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从东方主义观念出发,萨义德认为,“它(东方)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注]详见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页。。在东方主义的第三个定义中,萨义德指出,“简而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注]详见爱德华·W·萨义德著、谢少波和韩刚等译《赛义德白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萨义德认为,正是由于西方的强大,西方才能拥有霸权性地位,也才能制作出被驯化的东方,在西方主流文化眼中,“东方不是欧洲的对话者,而是它的沉默的、无能力反抗的他者”[注]详见祝朝伟著《当代西方文论与翻译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作为对应,东方就被东方主义的话语典型地制作成“沉默、淫荡、女性化、暴虐、易怒和落后的形象”[注]详见巴特·穆尔-吉尔伯特著、陈仲丹译《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5页。。
在改写与自译的过程中,也体现了张爱玲自我东方主义这一倾向。张爱玲最初将《金锁记》改写为PinkTears,虽文稿早已佚失,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篇名“Pink Tears”中窥见彼时张爱玲的英文创作心态。从题目来看,原文本篇名“金锁记”具有浓重的隐喻色彩:“金锁”二字暗示着书中人物对金钱的欲望,更暗示着金钱实为他们的枷锁。反观目标译本题目,“Pink Tears”则颇具女性暗示意味,哀怨且略带性别弱势,接近西方概念中的东方意味。从题目的处理上即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张爱玲在异域文化中寻求被接受与认同的写作心理。
这种自我东方主义倾向在TheRougeofTheNorth的改写与自译中也有多处体现。一方面,体现为增加了对独特风俗和器物的描写。在《金锁记》中,其器物与环境描写是相对克制而精炼的。例如,曹七巧的出场仅仅通过对其衣着、容貌和肢体语言的描写,寥寥数笔便将一个惹人厌烦的旧式刻薄妇女形象描画得栩栩如生。又如《金锁记》中多次出现月亮这一意象,也是为了烘托曹七巧苍凉的人生境遇,所有的描写都紧紧围绕主题展开,不多余,有力度。但在TheRougeofTheNorth当中,长度的扩张也带来描写的冗余,为了让西方读者更能理解这一中国故事,张爱玲增加了大量的描写性段落。例如,前三章讲述银娣从被聘到出嫁和婚后回娘家,张爱玲对中国的婚嫁习俗进行了重点描写,也满足了西方读者窥视中国独特风俗的心理期待,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东方的结婚风俗、发饰、服装和妆容等。第四至七章是银娣在姚家分家前的生活状况,张爱玲花了较大的篇幅描写生小孩和满月礼,对于银娣头一胎生了男孩,书中也进行了较多的描述,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东方家庭生活中独特的伦理秩序以及重男轻女的习俗。再如,为了满足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张爱玲会有意强化对“裹小脚”“三妻四妾”等内容的描写。“Carefully inspecting her hands and feet as people in shopping concubines to see if there was skin disease and if the bound feet were small and well-shaped”[注]详见Eileen Chang,“The Rouge of The Nor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第7页。,描述的就是富人娶姨太太时,会着重关注她们是否有“三寸金莲”,而有意思的是,在面向华语读者的中文译本《怨女》中,这段话被译为“买姨太太向来是要看手看脚,手上有没有皮肤病,脚样与大小”[注]详见王伟华编《张爱玲全集》(第2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弱化了“裹小脚”这一内容,更可佐证张爱玲对东方主义的有意迎合与刻意展示。
另一方面,在男性形象塑造上也更趋于弱化。《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是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阉割”了中国男性,同时也解构了男性权威。张爱玲“阉割”中国男性根源于西方人倾向于将中国男性“女性化”。在西方霸权的操纵下,中国人被认为是软弱无能、荒诞可笑的,与之相反,西方男性是无比强大、理性高贵的。在《金锁记》中未正面出场的姜二爷是个软骨病患者,一年四季躺在床上,而到了TheRougeofTheNorth中,姚二爷则患有骨痨病,他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还是个瞎子,更加弱化了其男性力量,迎合了西方人对于东方男性的孱弱想象。
(四)西方中心主义观点下的文化歧视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的个人处境与美国的文化环境下,张爱玲改写与自译的多次努力都是可以理解并值得同情的。她在出版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及在异国文化领域中的坎坷经历,也许并不全是因张爱玲个人在改写、创作和翻译上的不当造成的。20世纪中叶,美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世界大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也造成文化心态的膨胀。西方中心主义心态导致其对于其他非西方的文化大多持轻蔑态度,即便张爱玲以一种恭谦而顺从的姿态努力迎合他们的东方主义想象,但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一个窥视落后中国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他们希望看到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愚昧、落后、迷信、封建的中国。尤其在一开始,从张爱玲屡次被退稿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界甚至不屑于往这个“窗口”里看上一眼,在他们的观念里,这不过是一个来自落后国家的难民作家创作的一些“无法理解”的人物,没有关注的必要与价值。
张爱玲在1964年10月16日给夏志清的信中讲述了自己在投稿过程中遭遇的不公正对待,“我记得是这些退稿信里最激愤的一封,大意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么说’”[注]详见夏志清编《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squalid”可译为极其肮脏的、丑陋的、卑鄙的,其贬义程度不可谓不重。作为一封退稿信,西方编辑回复给张爱玲的,是充满偏见的辱骂性词语,而非文本与审美上的建议,可见问题也许并不出在作品本身,或许仅仅只是因为张爱玲的东方身份及其作品中的东方故事。张爱玲在西方文化界所受到的偏见与不公正待遇,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先声与缩影,无论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无论我们做得对与否,西方也许都会带着充满偏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阐释与误读,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难度与文化阻力。
五、结语
从《金锁记》改写与自译的多部文本等张爱玲后期在美国的作品来看,除了少有的几篇如《色戒》《五四遗事》一类的才情之作外,其他的篇章就质量而言大抵不如其20世纪40年代巅峰时期的作品。张爱玲受其早期人生经历和阅读经验的影响,使得她对熟悉备至的大家庭环境具有极强的写作冲动和创造力。在创作层面上,表现为对人性人情的深刻探索以及对人生俗世和平凡生活的由衷喜爱,既受《红楼梦》熏染,也承教于五四新文学传统,多重文学观念的影响带给其作品以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现实意义,这也是《金锁记》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
然而,之后这部作品却被张爱玲多次改写与自译,其中自有作者在主观上追求更高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体验的愿望,但细究之下,却是张爱玲在西方文化语境下无法坚守自己的创作原则和文化立场,是不断调整屈从的结果和一步步妥协退让的产物。即使经历了多次改写与自译,但由于缺乏新的创作灵感,张爱玲一直没能将自己的写作题材与美国的生活经历相结合。虽然长期在美国生活,但其隔膜程度却令人惊讶,张爱玲既没有真正走进世俗社会,也没有尝试以美国的生活作为题材来源,美国仅能成为其作品中为数不多且淡而又淡的背景。对旧中国儿女,以及对香港和上海的情结,既成就了她,也束缚了她。
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张爱玲,离开了她熟悉的“旧中国”,一方面,怀着对传统中国故事的坚持,在翻译上试图最大程度地还原中国特色,不论是直译为主的翻译手法,抑或是异化为主的翻译风格,都体现了她对旧中国儿女的眷恋;另一方面,处在异质的西方文明当中,面对来自西方文化语境的编辑与读者,张爱玲又必须迎合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迎合其从东方主义视角出发的对于中国的他者想象。妥协与坚持的复杂矛盾,充分体现在《金锁记》这一文本的改写与自译过程中。但值得肯定的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张爱玲后期在美国文学场域中的创作、改写与自译,在客观上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让西方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学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