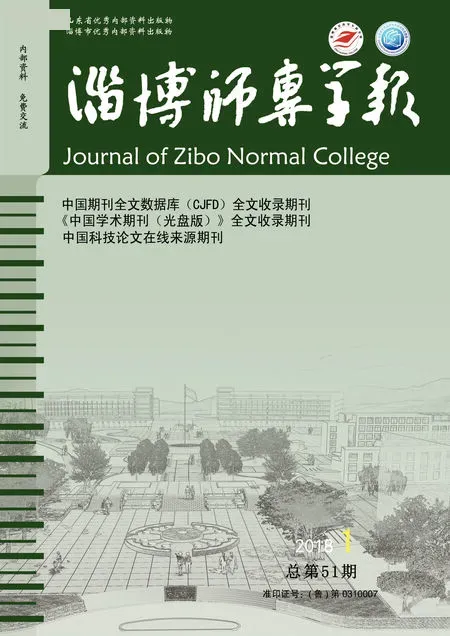法家视野下的“尧”形象探究
唐肖萌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810008)
《礼记·中庸》有言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班固评儒家思想沿用了这一说法。在儒家看来,尧是上古贤君的代表,君德的典范。关于尧的德行,《尚书·尧典》是这么记述的:“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黎民於变时雍”[1](P2-3)尧做事严肃节制、深思熟虑,举贤任能,有经天纬地之才,宽厚、大度等这些品德光耀千秋。他能把这些品德发扬光大,使九族之内关系和谐,九族之外的人各司其职,众民从化而变得和善。战国后期的法家对儒家极力推崇的这个贤君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并把他改造成了一个宣传法家法治、改革等思想的工具,利用他来推行法家的学说。
一、法家对尧的批判
法家对尧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禅让说”的批判和对贤人政治的否定上。
(一)对“禅让说”的批判
“禅让说”一直为儒家所推崇,并以此来称赞尧的贤能。法家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首先,他们认为天下没有大的吸引力。“让”天下是脱离苦海,与贤能无关。真正的高士不屑于拥有天下。《韩非子·五蠹》指出尧占领天下的时候用茅草盖房子,吃野菜等粗糙的食物,穿兽皮葛衣。“让”天下是为了避免这种苦,不足以被赞扬。“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掳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2](P1041)其次,他们认为所谓的禅让只是为君者的一种手段,被给予天下的人一定不会接受,君主最后并没有失去对天下的统治权。“人所以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必不受也,则是尧有让许由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也。”[2](P775)(《外储说右下》)另外,禅让行为本身也是虚伪的。《说林上》中有这样一则寓言:汤想要伐桀又怕落天下人口实,演了一出“让天下于务光”的戏,最终逼得务光投河自杀,让天下最终也没有实现。韩非子借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说明禅让的虚假性。《说疑》中直接把尧、舜、禹禅让的做法定义成弑君行为,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2](P925)他把儒家津津乐道的文武商汤都批成了乱臣贼子,与儒家针锋相对。
现在看来,法家的说法似乎更符合成王败寇的历史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天下变为家天下是必然的,而政权的更替必然伴随着斗争。“而且他所揭露的‘舜逼尧,禹逼舜,’这一事实,在《汲冢竹书纪年》中也得到了相应的证明”[3](P47),是有可信度的。
法家批判儒家借以宣扬尧的贤能的“禅让说”的同时进一步否定了贤人政治,重新探究了明主、贤臣在维护统治中的作用。
(二)对贤人政治的否定
明主、贤臣一直是儒家所推崇的最佳配置,他们对尧、舜、禹的贤能有大量描述,也给了极高的评价。《论语.泰伯》指出“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4](P82)这里把尧的功劳推崇到与天同齐的程度。在儒家看来,尧与舜相互成就是最理想的君臣关系。在法家看来,一方面,明主与贤臣不可兼得,过于强调臣的贤能就是君的失职,过于强调君主识人之明则对臣子不公。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难一》中。农民争田,渔夫争码头,制作陶器的人做出来的陶器质量不好等等问题都被舜解决了。而此时尧是君,舜是臣,把这么多问题丢给臣子,那国君在干什么?“方此时也,尧安在?”[2](P795)天下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尧的失察。如果国君把国家治理好了,就不会有这些问题,臣子的贤能也就无从说起。所以“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2](P796)他们认为明主和贤臣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另一方面,贤人的寿命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天下的问题是无休止的,仅仅依靠个别贤人慢慢解决,逐渐感化,收效甚微。另外,贤人的出现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不可过度依赖贤人。“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2](P888)(《难势》)要想治天下必须“赏罚使天下必行之。”[2](P796)(《难一》)即实行法治,依靠法家法、术、势等思想。他们认为强调人治是不懂统治之术的表现。这与重德行、重教化、轻刑罚的儒家形成鲜明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法家也讲德,但这个“德”与儒家道德、德行的含义不同。“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2](P111)(《二柄》)可见法家的德和奖赏联系在一起,与刑罚相对,其不靠内在修炼,且极具物质性、功利性,而是靠外在的奖赏和刑罚迫使百姓趋利避害。
总之,法家认为一再强调明主、贤臣不足以治国,治国必须靠法家的法治。所以在法家笔下,儒家的贤君就被改造成一个宣传法家法治学说的工具。
二、法家对尧的改造
这里的改造指的是法家通过尧之口宣传法家的学说。他们通过尧来宣扬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法治思想。他们还认为尧舜之道已不适合当世,借此宣扬他们的变法革新思想。
(一)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法治思想
法家认为治国必须以法为本,辅以驭臣之术和君主的权势、地位,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儒家一再推崇的贤君尧也无法治国。
1.法
在法家笔下,尧变成了一个法治的拥护者和推行者,离开法无以治国。
“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伪而不以符,此贲育之所患,尧舜之所难也。”[2](P492)(《守道》)就像制服野兽必须有笼子,阻止姦臣肆意妄为必须要有法律。《说疑》更举出尧、舜、启、伊尹、武王诛杀他们的父兄子弟的例子,指出丹朱等人之所以被杀,原因是“害国伤民败法”[2](P924)在这里尧显然成了大义灭亲、推行法治的典范的法家代言人。既然有法,那就要以法为准则,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正所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P88)(《有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否则天下就会乱套。“利所禁,禁所利,虽神不行;誉所罪,毁所赏,虽尧不治。”[2](P673)(《外储说左下》)赏罚不明必然产生混乱,任何人都无法治国。同样的思想还表现在《饰邪》中,赏罚严明,即使民众少也可富强,反之国虽大也只能是“地非其地,民非其民”,[2](P308)遑论治国。
法家重法治的思想无疑有益于规范人的行为,有其进步意义,但与今天的法治相比还是有局限的。首先法家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看似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则“是一种专制前提下的处罚上的平等”[5](P137-138)。所有的法律都是为君主统治服务的。其次,过于看重法和刑罚的作用,说到底就是统治者用严刑峻法使得人人自危来维护统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当时秦国的法律非常严苛,人民动辄得咎,结果秦二世短命而亡,物极必反。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七十四章》),班固评法家“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道出了法家重刑少恩的本质。
法家认为治理国家除了以法为本,还应辅以术和势两种手段。儒家的贤君尧在他们笔下变成了无术之人,他们认为尧治理国家离开势无从谈起。他们借尧之口论述这两种手段的重要性。
2.术
法家所谓术就是君王的驭臣之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2](P868)(《难三》)“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2](P906)(《定法》)君主掌握大臣的所长所短,使之物尽其用,掌握臣子的生杀大权,恩威并施,使臣子死心塌地为自己效力。“法家之所以讲究术是因为他们认为‘君臣之利异’(《内储说下》)。”[6](P39)这与主张君臣一心,合舟共济的儒家明显不同,所以尧在他们笔下就变成了一个驭下无术之人。《难三》指出尧自身贤德,但把重要的政事交给舜,最终失了天下是因为无术。《忠孝》也指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君臣各司其职。尧自以为明却不能以御臣之术对待舜,舜自以为贤不能像对待君主那样对待尧,这都是不对的。法家这一番改头换面无非为了突出术的重要性。
3.势
“势者,胜众之资也。”[2](P996)(《八经》)“法家之所谓势,实质上就是指政权和国家机器来说的。”[6](P40)势指君主的权势、地位,是君权得以施展的平台。在法家看来,没有势为保障,即使像尧这样的君主也根本无法获得治国的机会。“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2](P508)(《功名》)。没有权势的支撑,像尧这样的贤人也无法施展才能。法家对势的论述集中体现在《难势》中。“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2](P886)尧没有得势之前说话不起作用,南面而王后就可以令行禁止。势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要得势,其他人便无法改变局面,无论桀纣还是尧舜,无论贤或不肖。势治不可乱,势乱不可治。最终得出结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2](P888)还是回归到了法治思想上,尧在这里变成了一个衬托势的重要性的工具。
势中还包括天时和群众的作用。“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2](P507)(《功名》)“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2](P479)(《观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民众的作用不同于儒家的“民本”思想,更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统治者通过一系列阴谋手段和严刑峻法来限制百姓的行动。法家奖励耕战,于是他们想尽办法让老百姓只能参与耕战,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从长远看,这是害民。秦代焚书坑儒的愚民政策及其结果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除了法治思想,法家另一主要思想便是变法革新。
(二)变法革新思想
《商君书·更法》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7](P5-6)韩非子继承了这种思想,在《五蠹》和《显学》中有更充分的论述。“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2](P1040)(《五蠹》)他认为世间没有恒久之至道,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律,要与时俱进。尧舜之道已经过时,尧舜成了复古派的代表。尧“让”天下是因为当时的物质条件有限,天子也要不辞劳苦,“让”天下就是脱离苦海。现在则不同,一个县令都可以为后世子孙集聚无数财富。“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2](P1041)再用尧舜之道这种古老的方法去治国无异于守株待兔。这种提法在《显学》中更为激烈。当时的显学于儒墨两家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不同支派。“儒分为八,墨分为三。”[2](P1080)各派观点均有分岐却都觉得得到了孔、墨的真传。实际上真儒真墨已经被改头换面。“孔墨俱道尧舜,”[2](P1080)谁都无法确定尧舜的真面目,真正的尧舜之道已无法还原,更不能为现世所用。现在还想取法尧舜者非愚则诬。这与儒家尊崇往圣先贤,“祖述尧舜”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儒家的圣人在法家笔下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好古也好,革新也罢,在当时都是为了在乱世寻找一条出路,无可厚非。现在看来,变法革新的思想更有利于历史进步,正如《周易》所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尧这一形象在法家遭到了批判和改造。法家为什么找一个儒家的圣人下手探讨法家思想呢?一方面是由于法家和儒家的师承关系,另一方面是借助儒家的影响力为自己的学说争取一席之地。
三、改造尧舜的原因
(一)儒、法的师承关系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都师从荀子,荀子被称为先秦的最后一位大儒,其思想深受思孟学派的影响。但荀子对儒家传统的仁义思想做了改造,他主张礼法并重,王霸兼行。这已经有了外儒内法的色彩,直接促进了法家的诞生。所以韩非必然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又接触了法治、霸道的思想。所以他能找到一个儒家的圣人替自己发声,又能把他进行改造为自己服务,成为法家思想的代言人。
(二)提高法家学说影响力的需要
儒家、墨家在当时被称为显学,儒家孔子弟子三千。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在当时影响较大。而且儒家代表人物往往“知识渊博,注重个人道德修养,主张实行德政、仁政,他们的个人声望比较高”[8](P121)。所以,找他们为法家思想代言更能让人信服。不光尧舜,连孔子也被韩非改头换面用来宣传重刑思想。《内储说上》有这样一个故事:鲁国着火,救火不力,孔子出主意救火的人不必赏,不救火的人重罚,结果命令还没有传达完火就灭了。这明显与孔子的形象不合。这样做只是给其学说寻找依据。圣人孔子都觉得重罚有必要,那就必然合理。不光法家,道家也通过儒家之口宣传自己的学说。如庄子借孔子和颜回的对话阐明其“坐忘”的主张,虚构孔子向老子学道的故事以宣扬道的博大精深等等。所以法家把儒家的贤君改造得面目全非,为法家思想发声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法家通过批判尧禅让一说,进而否定了贤人政治,将尧改造成了一个宣传法家法治和革新思想的工具。这一改造一方面缘于儒法的师承关系,另一方面是为法家的学说站稳脚跟寻找依据。
参考文献:
[1]曾运乾.尚书正读[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罗祖基.先秦诸子的尧舜观[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2)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兰建军.儒法合流的根本原因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8,(2)
[6]金景芳.战国四家五子思想略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2)
[7]石磊.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赵玉洁.谈韩非对儒家学说的吸收与改造[J].河北大学学报,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