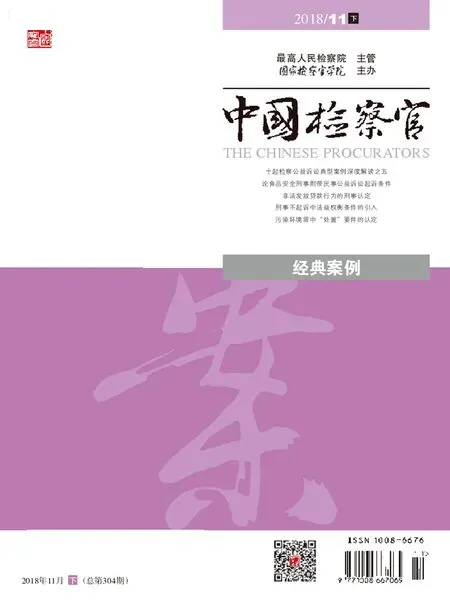存疑性侵案件质证中如何排除合理怀疑
文◎唐新宇
随着庭审中“幽灵抗辩”的多发,公诉人在质证过程中必须充分运用灵活方法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使得审判者查明真相,旁听者听得清、看得懂,做到案结事了,避免辩护人“死磕”法庭及当事人常年上访等。当辩方在提出“幽灵抗辩”,否认犯罪事实,质疑证据真实性的时候,多个相互印证的证据所产生的证明案件事实的说服力,远远大于“幽灵抗辩”对判定案件事实的干扰力。因而证据间相互印证原则是司法工作数十年传统智慧的结晶,也是目前最为行之有效的质证方法。但是,证据相互印证原则也存在一些较明显的弊端。相互印证对口供依赖较多,甚至实行“口供本位主义”,以被告人的口供为中心进行印证分析。很多“一对一”隐秘性犯罪,比如受贿、贩卖毒品、强奸等案件的被告人都不供认犯罪事实,而且其他证实犯罪的证据数量也偏少。相互印证往往要求案件拥有较多数量的证据,这种特点在性侵案件中尤为突出。如果过分强调相互印证,有可能在庭审质证中无法说服审判方,使审判方以无法相互印证为由作出认定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判断。
一、加强排除合理怀疑在庭审质证中的应用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从此,“排除合理怀疑”被正式写入我国刑事诉讼法。“‘证据确实、充分’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但司法实践中,这一标准是否达到,还是要通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主观判断,以达到主客观相统一。只有对案件已经不存在合理的怀疑,形成内心确信,才能认定案件‘证据确实、充分’。这里使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提法,并不是修改了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是从主观方面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便于办案人员把握”。[1]由此可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就是为了弥补“证据切实、充分”标准的不足,使得公诉人在庭审中面对“幽灵抗辩”时,得以在法庭质证过程中说服主审法官及人民陪审员,使其相信现有证据已经达到或者超过认定犯罪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二、把社会经验法则作为排除合理怀疑的重要准则
社会法学认为,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要改变概念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观念,将眼光更多地投向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更多的考量社会因素。一些“一对一”隐蔽型犯罪案件,较为普遍的情况是证据数量不多,符合相互印证原则所要求的证明程度的情形较少,因而社会经验法则在办理“一对一”隐秘型案件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比如性侵案件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各执一词,有时因被害人力量不足及缺乏经验等原因,现场遗留物证极少,被告人身体没有抓痕等客观证据,此时其他证据的证明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公诉人往往要从为数不多的证人证言、物证、鉴定意见等证据来提炼犯罪事实,当庭举证质证。这要求公诉人不应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必须要有众多的口供相互印证才算大功告成,而应该按照一个正常理智的人所具有的理性和良知来审视判断证据的证明力。
社会经验法则首先适合用于“一对一”证据证明力的判断。“证明力评价与认定需要遵循认识的规律,遵守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受到合理的心证制约。”[2]当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各执一词的时候,采用哪一方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认定法律事实,社会经验法则就起到重要作用。比如某成年人多次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50多岁的犯罪嫌疑人前五次供述自己不认识被害人,未和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第六次民警告知其DNA鉴定结果后开始供述被害人每次均自愿和自己发生性关系,自己抚摸被害人的时候被害人笑眯眯的,发生性关系时被害人未反抗,事后也未报警。而年仅15周岁的被害人陈述内容是首次被性侵时犯罪嫌疑人按住自己双手,结束后自己下身出血,被威胁不许说出去,否则就找自己家人。被害人妹妹证实后来被害人一直在躲避犯罪嫌疑人。该案虽然是一对一证据,但是从证明力比较上来看,犯罪嫌疑人供述明显低于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前五次不供述,面对DNA鉴定意见的时候被迫供述,逃避心理明显。考虑到双方年龄的巨大差异,事先也无感情基础及金钱基础,犯罪嫌疑人供述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被害人笑眯眯”的,明显不符合客观实际。相反,被害人作为年仅15周岁的未成年人,其陈述首次发生性关系时出血等细节属于非亲身经历不可能完整描述的内容,案发后被恐吓而不敢立即报警的陈述更加符合农村留守女孩的常理。其后为防止再次被性侵害而躲避犯罪嫌疑人的陈述与年仅13周岁妹妹的证言相印证。而犯罪嫌疑人辩解被害人自愿发生性关系无任何证据印证。
具体办案中,公诉人对案件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把握有两个重要原理:一个是“基本原理”,包括并不限于法律基本原理;另一个是“社会生活经验”,亦即平常所谓的社会“常理、常情、常识”。以性侵案为例,性侵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丰富的社会知识和多元化的心理状态,更应当结合具体案情分析其中蕴涵的社会因素,这需要办案人员本身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和社会知识,敏锐判断案件中违背社会生活常规常理的问题,从而得出有益于查清犯罪事实的结论,并结合其他证据作出总体判断。有的性侵案中,被告人当庭辩解自己在公共场所听陌生人说过被害人精神正常或者被害人年满14周岁,自己和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只是为了谈恋爱。这需要通过询问、观察被害人,向被害人邻居及案发地点附近证人了解被害人案发前的言行举止有何特殊之处等,运用社会知识在庭审质证中让审判者判断被告人在和被害人发生性行为时是否知道其为精神病患者或者年满14周岁。有的性侵案件中,被告人当庭辩解自己没有恐吓被害人,被害人系自愿和自己发生性关系,但是被害人案发时来了月经,这在庭审质证中可以说服审判者相信被告人违反被害人意志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有的被告人辩解自己某年某月曾经得罪过某个很有势力的人(只有绰号,姓名不详),被害人报案系受人指示诬陷自己。但是通过社会调查,被害人平时作风正派,和被告人素昧平生,庭审质证中可以说服法官及人民陪审员排除被害人虚假报案和诬告陷害的可能。对于判断被害人是否半推半就,被告人是否是求奸行为等影响定罪的关键事实,都需要公诉人具备一定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常识,从而在庭审质证中排除合理怀疑,让审判方形成内心确信。如笔者在2014年起诉的某强奸案,被告人当庭辩称案发时自己是经过陌生人撮合的嫖娼行为,但是物证证实的被害人衣服等损坏部位和被害人陈述的强奸情况吻合;鉴定意见证实的被害人、被害人颈部、肘部的身体损伤特征与程度和被害人陈述的情节相符,被告人朱某对此则无合理解释,在庭审质证阶段保持沉默。主审法官通过庭审质证后形成内心确信,判定强奸事实成立。
运用社会经验法则,还可以在庭审质证中解释证据间存在的合理差异。所谓合理差异,就是因为各个人的感知、表述、记忆以及其他因素有差异,导致证据间细枝末节问题并不吻合或者陈述内容稍有出入。比如证人甲证实看到作案现场实施犯罪的被告人身高1.65米,证人乙证明看到同一案件作案现场实施犯罪的被告人身高为1.70米,被告人实际身高是1.68米,那么甲乙的证言均可采信。因为根据生活经验判断,证人目测被告人身高不可能精确到厘米。
三、灵活运用社会经验法则开展举证质证
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使得一切犯罪调查必须在庭审中进行,给控辩双方在庭审质证中有了充分的自由发挥空间。对“幽灵抗辩”,公诉人在质证中可以积极进攻,主动讯问,充分披露“幽灵抗辩”的矛盾之处。具体讯问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可以和举证、质证有机结合,可穿插(使得辩方“幽灵抗辩”不能自圆其说)、可重复 (使得辩方回答同一性质的问题前后矛盾)、可埋伏(使得审判方认为辩方提出的“幽灵辩解”超出常理,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甚至可以在质证阶段对“幽灵抗辩”的辩护观点予以堵截(坚定不移地指出其撒谎)。庭审是最好的释法说理的场所,公诉人在质证阶段如果以社会经验法则为依托,举证、质证方法灵活有效,不仅有利于审判方在庭审中查明起诉书认定的事实证据,而且能够让被告人、辩护人及旁听群众听得清、看得懂,从而保证庭审结束后案结事了,避免出现辩护人“死磕”法庭及当事人上访等后遗症。
笔者在2014年起诉的朱某某强奸案,朱某某审查起诉阶段已经翻供,开庭时继续否认犯罪,并且辩解自己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所迫。公诉人出示一份侦查人员在看守所讯问被告人的配有视频光盘的有罪供述笔录时,被告人朱某某及其辩护律师辩解虽然视频光盘中被告人神情自然地自主供述犯罪事实,但是在此次讯问初期被告人遭到侦查人员的言语威胁,被告人被逼迫向侦查人员承诺作有罪供述后侦查人员才开启录像机开始录像。辩护律师要求公诉人调取此次讯问的看守所完整的监控视频以查清真相。因为2014年笔者所在市的看守所监控录像15天后存储空间已满,监控数据会自动覆盖旧数据,公诉人出示的有讯问视频的笔录中实际讯问时间距离开庭时间已经过去2个多月。控辩审三方都知道让公诉人调取看守所当时的讯问室监控视频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庭审质证时笔者依托社会经验法则,通过讯问、举证、质证的有机组合,使得合议庭当庭查清真相。首先笔者讯问被告人,要求被告人详细供述侦查人员开启录像机前如何言语威胁、诱供的过程,被告人予以详细解答。然后公诉人讯问被告人,此次侦查人员讯问一共持续多长时间?被告人回答大概两个多小时。此时笔者举证并质证,讯问录像光盘显示讯问时间持续30分钟,本次讯问笔录中反映时间跨度为35分钟(有讯问人员及被告人签字),提押证反映提押被告人及押回被告人时间跨度为42分钟(有讯问人员、看守所人员签字及侦查机关、看守所盖章)。去除讯问前开启录像机器及押解被告人来回的时间,侦查人员并无实施言语威胁、诱供的时间可能。笔者当庭堵截,指出被告人庭审中提出的“幽灵抗辩”系撒谎。此时辩护律师继续辩解讯问笔录时间、提押证时间被公诉方篡改。笔者再次出示审查起诉阶段讯问被告人笔录 (含听取被告人意见内容)及听取辩护人意见的书面材料(系辩护律师当初提供,有辩护律师本人签字及签注日期),并提出质证意见,指出当庭举证、质证的书证及被告人供述系原始证据,已经在案件提起公诉之时随案移送法院。因为在之前的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及辩护律师从未向公诉人提出此类辩解,所以公诉人不可能提前预知辩方具体的“幽灵抗辩”意见,从而提前有针对性的篡改证据。最终,合议庭的审判员及人民陪审员采纳笔者的质证意见,判决被告人朱某某强奸犯罪事实成立。
当公诉人应用社会经验法则,灵活机动地进行举证、质证时,作为辩方,当然可以予以反驳并提供证据,但是,试图仅仅通过提出“幽灵抗辩”逃避法律制裁显然不可能。如果辩方在庭审中提出“幽灵辩护”质证失败后,在法庭上“死磕”或者保持沉默,更容易使审判方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内心确信,从而作出有罪判决。
注释:
[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
[2]李明:《证据证明力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以被告人翻供为主要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