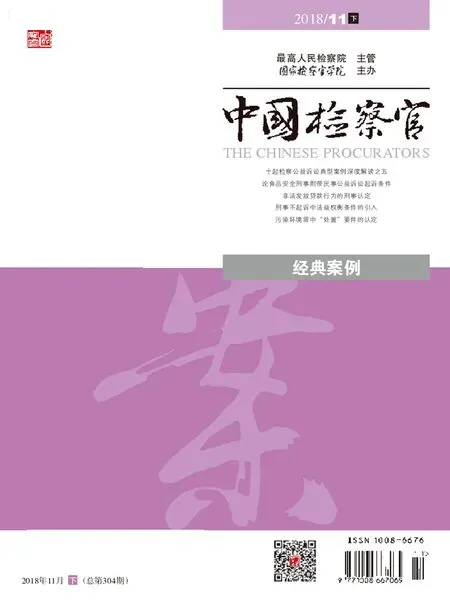浅谈防卫时间及主观条件的完善
文◎张一武*
一、问题的提出
于欢案的审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促使理论界、实务界反思正当防卫的应有内涵和作用。在于欢案热度未消之际,昆山宝马案(以下简称宝马案)再次将正当防卫推上了风口浪尖,进一步引发了对正当防卫适用问题的思考。
(一)于欢案的基本经过及其问题
2016年4月14日,吴学占等人对于欢及其母亲长时间采取拘禁、侮辱、殴打等非法方式索要债务,民警来到后警告“要债可以,不许打架”便离开办公室,最终于欢使用水果刀防卫,造成一死三伤的结果。2017年2月17日,聊城中院认为,警察在场保护则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于欢具有故意伤害的意思,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2017年3月24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于欢属于防卫过当,改判5年有期徒刑。
于欢案一审法院未能综合考虑于欢当时所处情形的特殊性而否定防卫适时,直接以伤害意思否定其防卫意图,过度重视危害结果和被害人权益保护而忽视了防卫人合法权益的保护,[1]而这也是我国正当防卫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普遍问题。
(二)宝马案的基本经过及定性争议
2018年8月27日晚,刘海龙在驾驶宝马轿车时与于海明发生争执,并从车内取出砍刀攻击。在砍击过程中,刘海龙的砍刀脱手落地,于海明抢到砍刀后对前来夺刀的刘海龙捅刺、砍击共计五刀,刘海龙受伤后跑回宝马车,于海明又追砍了两刀(未砍中),最终刘海龙跑离现场但因受重伤、抢救无效而死亡。同年9月1日,昆山市公安局认定于海明构成正当防卫,因此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并解除了于海明的刑事强制措施。
尽管社会舆论倾向于认为于海明构成正当防卫,但是学界对此仍存在一定的争议。反对者认为,从于海明夺刀成功和刘海龙逃跑来看,刘海龙已经放弃侵害,因而防卫时间结束。而且,从砍击的程度、部位及追砍行为来看,于海明的行为目的除防卫外还包含着报复、攻击的目的,故其防卫主观条件不符合。但昆山市公安局认为,丢刀后刘海龙的抢刀、殴打行为表明侵害未结束,且于海明为保护自己而实施反击符合防卫主观条件,不能强求其在当时能冷静思考分析,因此于海明构成正当防卫。[2]由此可见,关于防卫适时的判断以及防卫者主观目的的定性问题亟需进一步明确,以统一正当防卫的理解和适用。
二、防卫时间与防卫主观的认定
根据刑法的一般理论,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防卫意图、防卫起因、防卫对象、防卫时间和防卫限度。[3]基于前述两案的主要共同点,本文仅就防卫时间及主观条件的认定问题展开论述。
(一)防卫时间的认定
通说认为,防卫时间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但尚未结束的进行阶段。于欢案一审和宝马案反对观点在防卫时间结束(以下简称防卫结束)的确认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于欢案一审认为警察到场保护就不再具有侵害威胁,但实际上于欢及其母亲所处的危险状态并未解除,不法侵害行为仍有继续实施的可能性。宝马案也是如此,双方实力的变化并未消除于海明的危险状态,刘海龙仍可能使用新的凶器或者以开车撞击的方式继续侵害,因此在驱使刘海龙远离宝马车并使其彻底丧失侵害能力、确保自身不再受威胁前,于海明都应被认定为防卫适时。
正当防卫的设立初衷是保护合法权益,因此其时间条件也应符合这一根本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防卫人之所以可以在防卫时间内实施防卫,是因为合法权益一直处在不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中,换言之,合法权益因不法侵害的存在始终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但在学理上,防卫时间的起始为不法侵害的实施或紧迫威胁,而防卫时间的结束为不法侵害的停止。[4]可见,防卫起始条件的判断采取的是行为实施和法益威胁标准,而结束的判断则仅有行为停止标准。尽管不法侵害行为的终结一般就意味着被防卫法益的安全,但在不法侵害行为的结束有争议或仍有继续可能的情况下,行为停止只等于合法权益的暂时安全,但威胁仍然存在。[5]由此可见,侵害行为的停止标准难以有效保障合法权益的安全。
(二)防卫主观的认定
在于欢案中,一审法院基于于欢具有故意伤害的意思便否认其防卫意图,对其防卫意思则未做认定,这也是我国法院对正当防卫认定的限缩原因之一。[6]在宝马案中,反对者认为,于海明同时具有攻击、伤害的目的,因此不符合防卫意志的要求。但实际上,要求防卫人具有纯粹的防卫目的并不切合实际。如黎宏教授就指出,“在伴随有报复加害对方意图的正当防卫的场合,行为人在防卫之外,同时也存在攻击、伤害对方的意图”。[7]于欢案和宝马案中,要求防卫者对不断侮辱、伤害自己的人不抱有任何报复及侵害的目的是不切实际的,以此为由否定其防卫意图将不合理地限缩正当防卫的适用。
三、个案推动下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
于欢案相继入选2017年十大刑事案件、最高法指导性案例、最高检十大法律监督案例,宝马案的发生及妥善处理也获得了社会广泛关注,这两起典型案件的处理不仅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也为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契机。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完善:
(一)增设法益安全标准对防卫时间进行判断
如前所述,由于传统的行为停止标准无法准确判断防卫的结束时间,不利于保护防卫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建议参考防卫起始阶段的法益威胁标准增设法益安全标准。所谓法益安全标准,是指在具体防卫案件中,由于不法侵害人停止或相对停止实施侵害,合法权益已经脱离不法侵害威胁而重归并将持续处于安全状态时,防卫时间即结束。该标准不仅可以弥补行为停止标准的机械性和法益保护不彻底的缺点,也可以呼应防卫起始时间的法益威胁标准,并可促使正当防卫回归其制度设计初衷,切实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并消除防卫人的顾虑。此外,从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出发,笔者认为防卫时间的判断应采取“宽入严出”的模式,防卫时间的起始满足侵害实施或法益威胁之一即可,而防卫结束一般要同时满足侵害停止和法益安全两项标准,即防卫结束的认定更为严苛,以此合理延长防卫时间并彻底恢复合法权益的安全状态。需要注意的是,侵害停止标准应为先行标准,合法权益安全标准为进一步的实质判断。另外,针对第三方介入或是情势突然转变的特殊情况,法益安全标准的适用尤为重要且需要综合案情具体判断。对于第三方介入的案件,比如于欢案中警察的到场,需要评估第三方介入的影响程度是否足以彻底终止不法侵害的继续,并确保合法权益重归并将持续处于安全状态。对于情势突然转变的案件,比如宝马案中的凶器易主和侵害人受伤、逃跑的情形,此时应当评估该转变的稳定性及影响程度,即该转变会不会因为侵害人使用新的凶器、召集帮手等原因而逆转等,该转变是否使侵害者彻底停止侵害等。
总之,防卫结束的确定必须要以侵害人彻底停止侵害和合法权益已归于并持续处于安全状态为本质要件,对于侵害的停止,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判断,准确认定防卫结束的时间节点,维护防卫人的正当权益。
(二)正视防卫性攻击目的,审慎对待侵害性伤害目的
实践中,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时的主观目的往往不具有单一性和纯粹性,因此不能简单地依照某一目的定性,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服务于传统防卫目的的攻击目的应当认定为从属于防卫目的。传统理论上,防卫目的包括制止不法侵害和保护合法权益两个层次,前一层次实施防卫行为所想要达到的直接目的服务并从属于后一层次的根本目的。[8]制止不法侵害就意味着行为人要采取一定手段作用于侵害人,具体到案件中主要是采取攻击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此种服务于防卫目的的攻击目的应认定具有防卫性质,并承认防卫人的防卫意图。另一方面,对于基于报复、致伤、致死等动机而产生的伤害目的,则应区别情况确定。第一,若防卫人的主观目的仅为伤害,因其防卫的主观正当性已不存在,故应根据具体案件情况追究责任。第二,若防卫人同时具有防卫与伤害目的,则应当按照两种目的在主观中所处的地位来综合确定其主观性质。[9]若防卫目的为主要目的,则应认定防卫人符合防卫主观条件。但如果防卫人的主要目的为伤害,防卫目的仅系次要的、辅助性的目的,则应否定其综合目的的防卫性质,根据具体情况追究刑事责任。尽管法律上对防卫者的伤害目的予以一定程度的宽宥,但也是建立在防卫人主要目的仍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上,倘若综合目的本身都不具有正当性,免除其责任也不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当不能判断防卫人主观目的性质时,应当做有利于防卫人的解释,即认定符合防卫主观条件。
总之,判断防卫人是否符合防卫主观条件,必须要对其主观目的的正当性进行评判,既要兼顾主观纯粹正当之不能,也要坚持主观不法的可谴责性。
注释:
[1]参见高长见:《从于欢案看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问题》,载《理论视野》2017年第8期。
[2]参见《警方通报“昆山砍人案”: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http://www.sohu.com/a/251378474_100242732,访问日期:2018年9月7日。
[3]参见高铭暄、马克昌、赵秉志等:《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142页。
[4]同[3],第 145-146 页。
[5]参见吴骏:《论正当防卫时间条件的认定》,载《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20期。
[6]参见宋亚霖:《从于欢案论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及反思重构》,载《怀化学院学报》2017年第8期。
[7]黎宏:《论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
[8]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4-747页。
[9]参见储陈城:《正当防卫回归公众认同的路径——“混合主观”的肯认和“独立双重过当”的提倡》,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