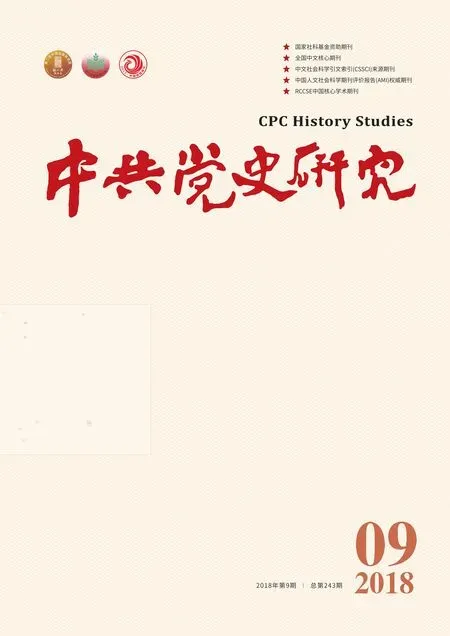近代中国的“亡国奴”身份抗争与抗日动员
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辞源续编》中,“亡国奴”被解释为“骂被异族征服之人民及不爱国者之词”*方毅、傅运森主编:《辞源续编》,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82页。。事实上,它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长期流行,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大量出现在题词、传单、标语、口号、演讲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舆论宣传中,也经常进入人们的日常对话和写作中,成为国人认知时势和定义情境的一个重要名词。抗战期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出的“抗日问答”,便以不当“亡国奴”为抗战的逻辑起点,说明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什么是“亡国奴”,以及怎样才能不当“亡国奴”*十项“抗日问答”的第二、三、四项原文如下:“二、不抗日可不可以呢?不可,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了。不仅自己当亡国奴,子子孙孙都要当亡国奴的。三、什么叫亡国奴呢?亡国奴就同高丽台湾人样,任人欺侮,任人劫夺,任人宰杀。祖宗的坟墓不能保,田园庄宅不能保,金银财宝都不能保,生活真是连猪狗都不如。四、怎样才能不当亡国奴呢?只有信仰我们中央政府,帮助我们的国家军队,拥护我们的军事领袖,大家一致起来抗日,才能不当亡国奴。”(《市党部颁发抗日问答十项》,《申报》1937年10月13日。)这十项问答可能在抗战宣传中得到了一定的普及,日本军人小原孝太郎在南京期间的日记即记载:“各户的墙壁上还贴有辰述霜政印刷的‘抗日救国问答十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647页。)小原抄录的内容与《申报》所载一致。由此衍生的叙事在抗战宣传中或被广泛采用,如四川某县城中小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即设计过极其相似的对话。(参见《蓬溪文史资料》第20辑,内部资料,1991年,第15页。)。可以说,“亡国奴”这一词汇在抗战宣传叙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针对个人和群体的政治性污名的流行,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诸如“洋鬼子”“洋奴”“汉奸”“卖国贼”等名词直接与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产生关联,“亡国奴”亦然[注]目前学界无论概念史、观念史的关键词研究,还是民族国家建构研究,对污名现象及其历史意涵都缺乏关注。桑兵近来的“汉奸”系列研究展示了民初“汉奸”概念的词义和史实,但并未将其放在污名泛滥的历史语境中去观察。参见桑兵:《辛亥前十年间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桑兵:《辛亥首义之区的汉奸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桑兵:《辛亥时期的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桑兵:《辛亥光复各省的防奸锄奸——以沪军都督府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那么,“亡国奴”这一名词的产生和流行与近代时局变迁有何关联?它所对应的观念如何为中国人接受?对中国人产生了怎样的心理影响?作为一种民族动员的手段,其历史逻辑是什么?对中国的抗战救亡乃至中国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近年学界提倡“大抗战史”,主张借助更长的历史脉络观察抗日战争[注]参见王建朗:《抗战研究的方法与视野》,《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高士华:《坚持做“大抗战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1期。。从“亡国奴”这一概念的产生和流行来看,它与1895年至1945年的中日关系息息相关,本文即尝试从概念与史实互动的角度勾勒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脉络。
一、“亡国奴”称谓与日本侵华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清王朝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急剧恶化,许多士大夫已开始相信“亡国灭种”惨祸迫在眉睫,康有为在为强学会所作的“序”中,便借助多个典故铺陈亡国景象[注]康有为称:“桀黠之辈,王谢沦为左衽;忠愤之徒,原郤夷为皂隶。伊川之发,骈阗于万方;钟仪之冠,萧条于千里。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弟妹,各衔乡关之戚。哭秦陵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虫;觅泉明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肝脑原野,衣冠涂炭。”其中罗列的典故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文文献中相当常见。参见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强学报》1895年第1期。。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将“亡国”与“奴隶”两种意象相结合。如康有为1899年提到:“中国遂真亡而无可救乎?我四万万之同胞遂永为奴隶乎?”[注]《康有为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次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有“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箠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之语[注]《梁启超散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页。,描述的便是一种亡国想象。稍后,梁启超在《新民说》中鼓吹自由时批评“身奴”和“心奴”,鼓吹民权时则批评“亡国民之根性”[注]梁启超著,黄珅评注:《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5页。。1903年《湖北学生界》第2期和第3期相继出现“甘心作亡国奴而不耻”与“使一国同胞免为亡国奴”的说法[注]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2期;《国民教育》,《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3期。,表明“亡国奴”已作为名词问世[注]此时并行多种相似称谓,如“亡国奴隶”“亡国民”,有文章且谓:“宁为亡国儿,不为亡国人。”参见《学生军缘起》,《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4期。。
20世纪上半叶,“亡国奴”成为指代亡国之人的称谓。不过在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曝光之前,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亡国奴”三字尚缺乏切肤之痛。虽出现过志士断指血书“用外货不用国货亡国奴”之事[注]《汉口救国会断指悲剧》,《申报》1912年5月31日。,但总体而言,“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将人人欢然自戴而不自知耳”[注]李彬主编:《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2页。。随后,“亡国奴”称谓传播得越来越广,这与日本侵华活动的日益加剧和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息息相关。
1915年,袁世凯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公之于世,许多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日本的“亡我之心”。此后的“亡国奴”称谓因而有了集中指向日本侵华野心的趋势。爱国社团和政界人士纷纷用该词表达对时局的愤怒与绝望,例如一份民众团体宣言针对五九国耻宣称:“列位可知我们中国,什么为瓜分,什么为亡国奴,现在日本借欧洲战争为名,说是维持东亚和平,明是欺压我们中国,割我国之土地,夺我国之国权。”宣言号召四万万同胞“宁为中华鬼,不为日本奴”。[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4—325页。又如1917年,政界暗中披露“西原借款”相关事宜,上海某同乡会遂致电北洋政府称:“报载军械借款将成,国家沦亡指日可待。凡我国民不忍为亡国奴,乞速将原议取消以挽危亡而全大局。”[注]《旅沪粤人致北京电》,《申报》1917年11月6日。再如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张謇致电徐世昌:“顷见报载日人制我专使巴黎议会发言权,又威胁我外部不宣布种种诡诈取得之秘约,令人愤悒。悬‘亡国奴隶’四字为帜,无南北无智愚、贤不肖皆耻之,行见举国腾沸也。”[注]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703页。在这一阶段,“亡国奴”一词超越知识界的范畴,成为社会团体和政界人士向政府陈情的符号,开始对国家政治产生舆论压力。
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亡国奴”一词也在这一付诸抗议行动的爱国运动中获得更多普及。“亡国奴”是五四运动中大量标语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宁做爱国鬼,不甘亡国奴”[注]《沪上商界空前之举动》,《申报》1919年6月6日。,又如“宁为救国雄魁,勿作亡国奴隶”[注]《公电》,《申报》1919年6月12日。。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亡国奴”广泛出现于他们反抗的呼声中。罢课期间,上海的学生会组织痛陈:“今中国将沦于异族政府,与吾民亦同为含羞忍垢万劫不复之亡国奴耳!”[注]《学生联合会组织之经过》,《申报》1919年5月10日。广东学生的游行大会标语也有“作亡国奴须知极惨,请看高丽便明”的内容[注]《广东学生之游行大会》,《申报》1919年6月5日。。五四运动以后,“亡国奴”已不仅是口头和纸面上的词汇,各地学生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将日货代理商乃至消费者骂为“亡国奴”,并与之发生激烈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深受刺激,参与此案中日交涉的方振武感受到极大屈辱,在汇报惨案真相时呼吁:“国未亡而吾人所受之痛苦实有甚于亡国奴!斯仇不复,何以为人?”[注]《方振武代表报告济案真相》,《申报》1928年6月2日。蒋介石也在日记和书信中不断留下类似表述。这时,国民政府已在宣传层面暗中鼓动抗日,不过为掌控局势,对学生抗日运动的态度仍很谨慎[注]相关研究参见裴京汉:《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而学生团体则以拒做“亡国奴”为由反对政府压制,上海学联的声明即称:“放弃国民天责,埋头读死书,以求个人利禄,此亡国奴之为,而非热血青年所忍为。”[注]《沪学联反对取消青运之宣言》,《申报》1928年8月3日。国民政府因济南惨案感受到“亡国奴”的羞辱并将其公之于世,助推了民间抗日情绪的高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导致东三省转瞬沦陷,亡国景象在中国空前真实起来。此后国民政府的公开言论中频繁出现“亡国奴”一词,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多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及。其中,他在成都讲“青年责任”时,甚至将“四体不勤,好逸恶劳”和“亡国奴”联系起来[注]参见《蒋委员长演讲青年之责任》,《申报》1935年7月14日。。同时,军政官员也纷纷以拒做“亡国奴”来表示抗战决心。长城抗战中,宋哲元“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题词成为影响深远的抗战口号。冯玉祥在1937年元旦之际立下遗嘱称:“我是抱定为国而死的,我是抱定为抗日而死的,不为国不为公必定都作亡国奴。”[注]《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页。傅作义说:“我们人人都有不作亡国奴的决心在心头,乃能不顾一切与敌作殊死战。”[注]《傅作义勖勉部属勿再予敌侵略机会》,《申报》1937年2月3日。
这一时期,中共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亡国奴”的论述,构成了中共抗战思想的重要一环。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提到日本帝国主义想“把全中国的民众变为亡国奴”[注]《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第58页。,这就将对做“亡国奴”的担忧与北上的战略选择联系了起来。1935年,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更从“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的危险出发[注]《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第66页。,倡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后,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中共不仅频频向全国民众乃至国民党发出统战信号,且在内部也达成共识。如一封秘密指示信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则做人,不抗日则做亡国奴。”[注]《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第72页。在此后近两年时间里,中共不断修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对民众“不愿做亡国奴”的判断一直是其中重要论证环节。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亡国奴”一词在国民政府宣传部门的抗战逻辑中开始占据关键地位,由前文所述“抗战问答”即可见一斑。蒋介石关于“亡国奴”的论述也更直截了当地指向中日关系,如在1937年“双十节”纪念中说:“中外历史决没有不牺牲而能生存之民族,也没有不奋斗而可致和平的道理。如其有之,那只有自居于束手听人支配的亡国奴,才会有此梦想。”[注]《蒋委员长广播演讲词》,《申报》1937年10月10日。
此时,中共在军事战略和战术上的指导思想也均以不做“亡国奴”为出发点展开讨论。毛泽东《论持久战》便以“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为依据,论证妥协没有前途[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5页。。后来,他列举日寇和亲日派必将失败的原因,其一便是“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页。。左权认为:“今天所进行的战争,不但是为了中国最广大的工农劳动者的自由解放,而且是为了把全民族——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亡国奴的沉重的锁链之下解放出来,只有求得全民族的自由解放,才能求得中国工农劳动者的自由和解放。”[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63页。中共还将游击战与群众不愿做“亡国奴”的心理相联系。如朱德认为,游击战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9页。。刘伯承谈到敌后抗战战术时指出:“由于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摆脱亡国奴命运的残酷斗争,所以参加斗争的成员,必须是每一个中国人,而不单是某些少数人,尤其不是几个军人。”[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9页。这些表述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共对全民抗战理念的高度重视。
从思想界的广泛宣扬到国共两党的集中倡导,“亡国奴”成为举国上下无法逃避的话题,对国人的心理冲击越来越大,对民族抗战的推动也越来越明显。而这一变化过程与中日关系的逐步恶化若合符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面抗战背后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族动员。国家抗战意志的养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亡国奴”一词几乎持续不断地完成了半个世纪的角色扮演。
二、“亡国奴”身份想象
尽管日本对华侵略越来越深入,但“亡国奴”身份更多的是一种虚拟而非真实的社会身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知识界和政界精英反复围绕“亡国奴”这一名词做文章,以便唤醒大众。那么,“亡国奴”在中国人心目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可怕形象,以至越来越多原本与政治无涉的民众谈虎色变,为避免做“亡国奴”甘愿作出牺牲?与此直接关联的是近代中国的“亡国奴”想象问题。
国人想象中的“亡国奴”形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作家徐光耀听到的“具体形象”是:“日本人到来之后,他要骑马,就先叫一个中国人跪在地上,然后登着他的脊背上马。”[注]《徐光耀文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7页。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量回忆性文献提到“亡国奴”一词时都给人心有余悸之感,对照民国“亡国奴”形象的各种描述来看,这些苦难回忆并未夸大其词。
在中日“二十一条”签订不久后的一次救国储金大会上,记者黄远庸论述“亡国奴与牛马之分别”,说:“牛马生来不应自由的,人类生来应自由的。生来自由之人类,一旦为亡国奴,夺去自由,其苦痛甚于牛马百倍。故人与其为亡国奴,不如为牛马。”[注]《北京第二次救国储金大会》,《申报》1915年5月28日。甲午战争后,人们对“亡国奴”形象有多种描摹,常常使用牛马猪狗等牲畜作类比,黄远庸清晰地道出了这一长期流行说法中的逻辑。此外,不时有人列举“亡国奴”的种种日常生活惨状,以见处境之艰难。
不过,中国毕竟未曾亡国,且在局部地区沦陷之前已经广泛流传各种“亡国奴”想象。那么这些想象的蓝本是什么?检诸史料可知,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舆论界长期流传着世界各国的亡国叙事,讲述着某国的亡国历史及“亡国奴”生活片段。这是中国人“亡国奴”身份想象的世界镜像。在“亡国奴”一词诞生之前,便已时常见到相关描述。如1903年,有作者感叹受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人民为奴隶,为牛马,俯首贴耳”[注]《菲立宾亡国惨状记略》,《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
“亡国奴”一词逐渐流行后,各种海外亡国镜像越来越多地向国人传播。正如1931年《新民》杂志提到的,朝鲜和越南(安南)便是“我们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可以望到做亡国奴的后果与前因”[注]《我们的镜子》,《新民》1931年第20期。。朝鲜被日本吞并,且日本又成为中国最大威胁,所以朝鲜的亡国史和“亡国奴”生活最为中国人关注。1918年《申报》发布广告叫卖韩国志士朴殷植所辑《韩国痛史》,颇为煽情地说:“宁作强国犬,莫为亡国奴。欲知亡国惨,须读亡国史。故《韩国痛史》实为吾国民今日不可不读之书。前车之鉴,当头之棒。”[注]《安重根:〈韩国痛史〉》,《申报》1918年4月19日。某论者有感于同胞说“这次日本出兵,有什么大不了,最多亡国做亡国奴罢了”,撰文列举了20种日本对朝鲜的残暴统治,来说服同胞不应戴“这顶亡国奴的帽子”[注]林敬璜:《你愿意做亡国奴吗》,《新民众》1931年第33期。,其中许多案例多次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的舆论宣传中,而这些案例经过一再叙述,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使“亡国奴”形象渐趋固化。
除了朝鲜,中国周边的越南、印度也经常被提及,其余如非洲的埃及和欧洲的波兰也都是重要的镜像。例如1927年,《申报》说:“波兰人一向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被认为亡国奴的。”[注]傅彦长:《波兰影剧》,《申报》1927年7月19日。清末民初,叶圣陶从报纸上看到记载“波兰故事”的《亡国奴传奇》并作抄录[注]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1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3页。。1915年,《申报》称,波兰和印度“国亡之后,家中不得集有数金,不得藏有寸铁。呼马应马,呼牛应牛”[注]《日报之所谓排东思想》,《申报》1915年7月4日。。诸如此类细节性描述,与事实难免有所出入。《申报》的广告词强调《韩国痛史》“系该国遗民手编,信而有征,毫无迻译臆造”[注]《安重根:〈韩国痛史〉》,《申报》1918年4月19日。,或许说明以往国内的朝鲜亡国叙事可能有道听途说甚至自我加工的成分。另一部《世界亡国痛史》的出版者也强调其真实性,标榜作者朱大公的“世界史专家”身份,自谓“秉笔直书”;实际上,为达到“使人触目惊心!失声动器”的效果[注]《〈世界亡国痛史〉今日出版》,《申报》1931年10月21日。,书中难免有所修饰。
艺术的夸张无疑更能吸引读者,助推此类亡国史著作成为国人的案头读物。《申报》某作者自谓“夜阑人静,一灯孤坐,读古今亡国史,不觉泪珠簌簌下”,感叹“吾非亡国奴,吾深恶泪之不知何自而来也”[注]徐位铭:《余沈》,《申报》1921年11月3日。。他在亡国史阅读中感同身受,与国家和个人未来命运产生强烈共鸣。
对“亡国奴”身份的想象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而强化。九一八事变后,出版商标榜《世界亡国痛史》一书“是唤醒国魂,同赴国难之最良好刊物!是宣传亡国奴呻吟状态警告国人之实地写真”[注]《〈世界亡国痛史〉今日出版》,《申报》1931年10月21日。。东北的沦陷使国人又增添了一个痛彻心扉的国内镜像,不久即有大量作品描述沦陷区“亡国奴”生活。出版商常以不做“亡国奴”为卖点进行宣传,如《沦亡后的东北》一书,广告称这是一本“血淋淋的报告”,“每个不愿作亡国奴的人,都应该一读”[注]《沦亡后的东北》,《申报》1937年4月3日。。
国人对“亡国奴”的想象,除了历史和报告文学等“写实”性质的叙述外,还经常通过小说、戏剧、电影等文艺形式生动地展示出来。以“亡国奴”为主角和主题的小说,首推周瘦鹃为纪念五九国耻所作的《亡国奴之日记》。据他后来说,此小说“举吾理想中亡国奴之苦痛,以日记体记之,而复参考韩、印、越、埃、波、缅亡国之史俾资印证”。他在跋中自述,创作时情绪反应极大,以至“疑吾身已为亡国奴矣”,总之是“设身为亡国之奴,而草此《亡国奴之日记》”。[注]王智毅编:《周瘦鹃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6—227页。其后,时而有“亡国奴”题材小说问世。不过,这类小说艺术价值有限,未能塑造出令读者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
在“亡国奴”形象面向大众的建构过程中,戏剧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它的受众更广,艺术形式造成的视觉冲击力更大。1914年底,上海某戏院上演新剧《亡国奴真苦》。次年,中日“二十一条”签订不久,又上演《且看看非洲的亡国奴》。从《申报》广告中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在五四运动期间,以“亡国奴”形象为主题的戏剧剧目频繁出现,且习惯使用煽情的广告词。如1919年5月14日,《亡国惨史》的广告词呼吁:“看看亡国奴的苦楚,听听亡国奴的忏悔,诸君看看此戏,且慢哭亡国奴,当留些眼泪哭哭自己。诸君当来研究研究人家的国是怎样亡的,我们须要猛醒,不要像他们一样。”[注]《十五夜准演新排警世新剧〈亡国惨史〉》,《申报》1919年5月14日。次日,戏剧《可怜亡国奴》的广告更是别具创意,利用上次演出时恰遇大雨鼓动道:“上次演《可怜亡国奴》,大雨倾盆,来宾裹足。可见亡国奴实在可怜,皇天亦为之痛哭流涕。”[注]《天哭新亡国奴》,《申报》1919年5月15日。该剧在月底的另一条广告又渲染道,“亡国奴”“就像下了十八层地狱一般,子子孙孙一辈子都不得翻身”[注]《可怜亡国奴》,《申报》1919年5月29日。。这类颇具煽动性的广告词明显具有爱国情感动员功能。
有社会团体为实现爱国动员,专门组织义演。1922年,某校校友为筹赎胶济铁路事表演新剧,剧中的乞丐陈情道:“我小花子情愿做一个中华民国的叫化子,尚能自由。绝不情愿做一个亡国奴,受人虐待。”[注]五木:《观演剧赎路感言》,《申报》1922年12月5日。在另一个团体的义演中,舞台上的俄国人一不遂意便对波兰人“连呼亡国奴不已”[注]静:《北京学界演剧记》(三),《申报》1919年6月27日。。
此时还出现了“亡国奴”的行为艺术展览。五四运动期间,某师范学校召开纪念会,学生在自习室作各种装扮。“奴隶乡一室最足令人怵目警心。室中扎有印度装束等四人。有卧地似死者,有坐而支颐者,均作亡国奴垂头丧气之状。”[注]《第二师范学校十周纪念会续纪》,《申报》1915年5月30日。1924年7月,上海某青年互助团游行演讲,“由主任高一鹏化装为亡国奴”,结果“听者三百余人,莫不动容”[注]《青年互助团游行演讲》,《申报》1924年7月4日。。1929年,某工专化装狂欢会上,“化装亡国奴者尤毕肖,行动言语上颇能暴露亡国奴者之所以亡国之特性,予人深刻之印象”[注]棒森:《中法工专“美悠远”化装狂欢会》,《申报》1929年6月24日。。此类表演中“亡国奴”形象的脸谱化特征十分明显。
近代中国始终未曾亡国,“亡国奴”身份源于国人在亡国危机中的一种预警。这一身份不难在波兰、朝鲜乃至本国历史中找到原型,但毫无疑问,国人在对“亡国奴”的描述中经常性地对原型进行夸大处理。这就形成一种“亡国奴”身份想象,这种想象通过一再的文艺展示,确立了国人对于“亡国奴”身份的刻板印象。
历史和艺术形式的“亡国奴”想象,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导致受众产生强烈的身份焦虑感,如淮河流域的花鼓灯抗战灯歌《贤良女劝夫参军》中的唱词“亡国奴哪里还有家”,难免令观众对自身处境感到忧虑;另一方面,“亡国奴”想象也会激起国人的抗日怒火,从而起到动员作用,上述灯歌中的“贤良女”便据此“苦苦劝你(指其丈夫——笔者注)把兵当”[注]于世勋主编:《淮河文化论丛》第1辑,郑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2页。。田汉和聂耳合作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插曲《苦力歌》中有“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之句[注]《聂耳全集》上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46页。,更是时代的吼声。《新华日报》的一篇通讯反映了抗战文艺对群众的感染力:“周围二三十里地以内的人都来看戏。当他们听到受难同胞的声诉,和日本鬼子蹂躏我同胞的情形,都喊出了‘鬼子来的时候,一定和他拼’。”[注]李继:《救亡工作开展中的南召》,《新华日报》(汉口)1938年6月17日。这种群情激奋的场景是抗战文艺宣传效果的生动写照。
三、“亡国奴”身份焦虑
康有为在清末曾注意到:“今好新者动以奴隶性质骂人,而以自主自立为贵”[注]《康有为全集》第8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8页。。章士钊的《箴奴隶》特意将“国民”与“奴隶”对立:“不为国民,即为奴隶”[注]《章士钊全集》第1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46页。。1915年,陈独秀亦在《新青年》撰文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注]胡明编选:《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页。“奴”在历代的身份都是卑贱的,但上述看法进一步表明,其在清末民初的新学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奴”缀于“亡国”二字之后,无疑凸显了亡国之民的卑贱身份,成为有血气之人无法忍受的骂名,对国人也更具震撼力。
“亡国奴”一词所带来的心理冲击,正如某论者所说:“在这个年头,提起了‘亡国奴’三个字,不觉身上出了一阵冷汗!”[注]萧旷士:《谈谈亡国奴》,《礼拜六》第598期,1935年6月。亦如《新生周刊》所说:“‘亡国奴’这名词也是大家听得很熟的,尤其是我们快要亡国,准备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对‘亡国奴’这三个字,一定是触目惊心,会更感到有切肤之痛吧!”[注]《亡国奴》,《新生周刊》第1卷第16期,1934年5月。这不只是舆论界的危言耸听,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在给胡适的一封私信中便哀叹:“我们老了,不期到了中年的时候做上一个亡国奴,真是可悲痛的事。”[注]《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96页。可见“亡国奴”身份给国人带来巨大的心理恐慌与耻辱感。
周瘦鹃透露,他的《亡国奴日记》“叠版数次,凡销去四五万册”,透过畅销量,他看出“吾国人心目中殆亦知亡国之可惧也”[注]王智毅编:《周瘦鹃研究资料》,第227页。。恽代英便曾在旅途中购买此书[注]《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604页。。亡国史的流行体现的是对想象中“亡国奴”的焦虑。1937年,有人撰文道:“还是我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我就听见人说:做了亡国奴是怎么怎么的苦”,“就因为听到那些宣传亡国奴的惨痛的苦楚,所以对于做亡国奴这一件‘大事’,实在是在小心里非常的恐惧的。而这种恐惧心,就是到了现在已是成人长大了,还是存在着,并且扩大着”[注]周戈:《从“活埋”到“喂狗”》,《申报》1937年1月15日。。仅是传闻便足以令人恐惧,近距离经历日军侵华的人的心理可想而知。
“亡国奴”关联的另一心理是耻辱,这是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种情感体验。清末有论者曾痛言:“白色碧眼儿,视我如无矣。腾之口而笔之书,莫不以贱种亡国奴相诮骂。”[注]徐凌霄:《古城返照记》下册,同心出版社,2002年,第651页。其中有来自外人的辱骂,也有来自国内的自我感知。1905年,宋教仁讲述近世以来汉人被统治的历史,称其为“世界上一种最丑最贱最污秽之间接亡国民”[注]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
与这一耻辱心理相关的是,国民已普遍将“亡国奴”视为骂名。五卅运动后的一份宣言中即有“贻外人之讥笑,负亡国奴之骂名”一说[注]《大革命时期的重庆》,内部资料,1984年,第228页。。有文章对少儿读者写道:“小朋友,假使有人骂你一声‘亡国奴’,那你一定会恨恨地同样地报答他一句:你自己是‘亡国奴’。大家都知道,亡国奴是一个:极不好听,极可羞的一个名词。”[注]蒋春辉:《不做亡国奴》,《中国儿童》1937年第3期。在近代上海,国人时常骂印度人为“亡国奴”,然而随着形势的恶化,“鄙弃人家是‘亡国奴’的,现在要鄙弃自己;戏弄人家是‘亡国奴’的,现在也要戏弄自己了”[注]《周立波选集》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页。。孙中山不客气地指出中国人的处境:“我们动以亡国奴三字讥诮高丽人安南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地位,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实在比不上高丽人安南人。”[注]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第20—21页。1918年,天津报界刊发戏谑文称:“中国全数亡国奴谨启:领取卖国费者,付款后即将其面部刺亡国奴三字,作为已经领款记认。”[注]《代中国全国四万万亡国奴上卖国某公要求均分卖国费书》,《益世报》(天津)1918年6月14日。希腊语中的“污名”(stigma)一词,原意正是在人的面部刺字以标记其奴隶身份[注]〔美〕欧文·戈夫曼著,宋立宏译:《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页。。
“亡国奴”骂名在中国的盛行既然与日本侵华息息相关,那么日本是否习惯以此辱骂中国人?实际上,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对中国人日益抱有强烈的歧视心理,视中国人为“亡国奴”亦是题中应有之义。1905年,一篇名为《亡国奴》的文章称,日本“人人都骂留学生是亡国奴”。例如,“有一个大成学校,里头有中国留学生三十人。一天有一个日本的学生,在黑板上大书‘支那指日瓜分,亡国奴大可奋发’十三个字”。又如,一日本女仆骂留学生道:“我虽然是一个下等的女人,程度还是比汝高过几百倍,为甚么呢?因为日本人是有国的,你们支那人都是亡国奴。”[注]崇岳:《亡国奴》,《直隶白话报》第1卷第6期,1905年4月。
上述情况若属实,意味着清末日本人已在辱骂中国人为“亡国奴”了。检索日本近代文献,尚未找到确凿证据,毕竟是辱骂之词,不便形诸文字。不过,民国以后的汉语史料中留下了大量日本人口头辱骂中国人为“亡国奴”的案例,不少案例发生在日本在华工厂里。例如,1925年《胶济铁路总工会代表泣告书》提到:“‘中国奴’、‘亡国奴’是日监工平常辱骂工人之名词”[注]柏文熙、黄长和编:《邓恩铭遗作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4页。。五卅运动掀起巨大抗议浪潮,但日本人对中国工人“打骂仍如常,‘亡国奴’、‘中国狗’之恶名,时加在我们同胞身上”[注]《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49页。。抗战时期,李公朴称,“亡国奴”三字“已成为敌寇辱骂我同胞的口头语”[注]《李公朴文集》(上),群言出版社,2012年,第502页。。统合各种史料,或可推断李氏所说之情况并非为抗战宣传而虚构。
正因为“亡国奴”交织了恐慌和耻辱,它常常与国人的泪水、噩梦相伴。周立波回忆说,班里的朝鲜同学被讥笑为“亡国奴”后,这个“三十几岁的人当着我们哭了,哭得非常的长久,但是总竭力想忍住他的声音,忍住他的扑扑的眼泪,却都忍不住”[注]《周立波选集》第4卷,第55页。。中国人也不幸有了这种体验。革命者余修回忆1919年自己八岁时发生的故事说,“校长在讲台上声泪俱下”向几百个小学生大声诉说当了“亡国奴”之后的惨状。“老师的哭声,引起我们几百个同学的嚎啕大哭,仿佛天地忽然变色,一场大祸就要降临似的,仿佛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就要立刻沦丧,不知为何,我们怨愤得不能自抑。”[注]《余修文集》,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4页。七七事变后,梁实秋“涕泣着”对大女儿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注]《梁实秋杂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第277页。胡适曾在日记中写道:“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知‘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是人情天理中事也。”[注]《胡适留学日记》(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页。1923年,有人讲述自己在梦中成了“亡国奴”后被人胁迫而“止不住大哭起来”的情形,提醒说:“恐怕真要离这一天不远了,大家快努力自救罢。”[注]《亡国梦》,《申报》1923年6月16日。随着形势日益恶化,这类极度焦虑心理下的激烈情绪反应愈益常见。
“亡国奴”身份对中国人造成的巨大心理冲击,引发了不少极端行为。1915年,一位湖南人认为“与其为亡国奴,不若早投自尽之为妙”,“是以殉身,冀诸同胞竭力救国”[注]《湘省最近之对外观》,《申报》1915年5月3日。。此后,这类惨事络绎不绝。比较著名的是1934年《申报》已故主笔秦理斋寡妻龚氏携子女集体自杀事件,其遗书提到:“忆九一八消息到沪之日,君自报馆回,惨沮不可名状,竟夕不寐。翌晨,亦不进食。旋语予,国事若斯,吾辈已无能为力,何必为亡国奴?”[注]《龚氏遗书一字一泪》,《申报》1934年5月8日。秦理斋因国事郁郁而终,其妻不久亦与子女服毒而死。这类事例固然流露出“尸谏”的决绝,但亦难掩对国家及个人前途的绝望。不做“亡国奴”成了自杀的理由,可见“亡国奴”已由屈辱和恐慌一路推演,终于成为一个与绝望甚至死亡相关联的名词。
需要指出的是,自康有为、梁启超以来,“笔锋常带情感”成为舆论界的常态,“情感”这一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共同推动着历史的进步。陈独秀在民初即撰文指出:“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而“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他痛感国人情与智皆无,竟发出“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偏激之论。[注]《陈独秀散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14页。李大钊批评此文将引起读者的“厌世之怀”,他以自杀为例指出,“社会之乐有文人,为其以先觉之明,觉醒斯世”,故不可作“哀感之文”以启人轻生之念[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6—143页。。但章士钊认为,与其“偷世”,毋宁“厌世”:“足下以提倡厌世之风,文人当负其责。愚谓提倡偷世之风,文人尤当负其责也。”[注]《章士钊全集》第3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531页。章士钊此论是对近代舆论界主流心理的一个极好的概括。甲午以来形成的“亡国奴”身份想象以及由此带来的集体焦虑,与此种心理有着密切的关联。上述三人的观点表面上是对立的,但其实都处在这一身份焦虑之下:李大钊担心陈独秀“无国”之论会导致读者“自甘居亡国奴地位”,而后者其实也处处流露着对“亡国为奴”的不甘。
四、“亡国奴”身份抗争
抗日战争最终演变为一场全民族抗战,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赖于长期的抗日民族动员。中国近代史无疑既是一部屈辱史,又是一部抗争史。屈辱与抗争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二者还会产生互相强化的效应。想象中的“亡国奴”身份便是屈辱与抗争最典型的合体,对这一身份的恐慌与耻辱心理经常被用来激励国人奋起抗争。中共中央游说杨虎城抗日,便有“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的说法[注]魏建国主编:《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编》(下),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
“亡国奴”在语言应用中有积极和消极两种表述手法。一是鼓励和倡导,表述为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应如何做。《义勇军进行曲》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即是如此。此类事例并不罕见。1936年,某书报社征求抗敌救亡歌曲,称:“际此国难严重,务望不愿做亡国奴的大文豪和大音乐家,多多赐教匡正。”[注]《征求抗敌救亡歌曲》,《申报》1936年9月24日。同年,又有售卖《国防壮歌集》的广告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急宜人手一阅。”[注]《国防壮歌集》,《申报》1936年10月1日。这一积极取向与近代以来民族英雄形象的建构有异曲同工之处。有人指出,国民在今日中国“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不是做“民族英雄”,就是做“亡国奴隶”[注]郭有文:《两条路——民族英雄与亡国奴隶》,《桂东旅衡同乡会会刊》1935年第1期。。这就是说,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便可做民族英雄。
毫无疑问,国人所谓的“亡国奴”绝不是自轻自贱,而是为了激励动员。梁启超借用西哲之言道:“凡人皆立于所欲立之地,是故欲为豪杰则豪杰矣;欲为奴隶则奴隶矣。”[注]《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30页。这种自由意志论调在“亡国奴”话语中有着深刻的烙印[注]李大钊便曾强调主体的力量,称:“国家之亡,非人亡我,我自亡之;亡国之罪,无与于人,我自尸之。”参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140页。。在西学影响下,“奴”字具有与自尊、自由、平等相抵牾的含义,如果亡国之后能有反抗的话,便不能以“奴”视之[注]作家黎烈文在从上海赴巴黎途中对朝鲜和安南人作过对比观察,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亡国奴。参见陈子善编:《黎烈文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这种看法在民国时期得到清晰的表述。例如,有人指出:“亡国的人也有分别。不战而亡国的人叫做亡国奴。屡败屡战,屡战而还不免亡国于人,便是义人,义人之国叫做义国。义气长留天地间,谁能亡他呢?谁能奴他呢?”[注]《战神前之对话》(三),《申报》1931年12月2日。汪精卫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也作过区分:“天下只有顺民,才会当亡国奴。亡国奴会以一己的生存而致国家民族于死,否则必为义民。”[注]《中央举行“九一八”纪念会》,《申报》1937年9月19日。他的慷慨陈词随着叛逃而变得极具讽刺意味,但其背后固化的观念不会随之烟消云散。将抗争者称颂为“义人”或“义民”,而不以“亡国奴”视之,显然有助于鼓动人民抗争。张学良1934年底对学生演讲称:“我绝对相信我们若不愿做亡国奴,我们便不至作亡国奴。”[注]毕万闻编著:《金凤玉露:张学良与赵一荻合集》第5部,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1937年初,傅作义也说:“我们与敌作战,虽没打胜仗的把握,但不作亡国奴这把握,却全在我。”[注]《傅作义勖勉部属勿再予敌侵略机会》,《申报》1937年2月3日。
与“义民”相对的是“顺民”。时人注意到了“顺民”与“亡国奴”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历史脉络:尽管八国联军入侵时老百姓“家家悬起了‘大英国顺民,大法国顺民,××国顺民’的降旗”,但“我们今日的民间,还居然喊出‘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这确是一桩万分可喜的事”[注]筑:《从“××国顺民”到“不作亡国奴”》,《邮声》1931年第9期。。从甘为“顺民”到不做“亡国奴”,表明民众有了进步。
二是批评和惩戒,表述为如何做便是“亡国奴”。此类事例极多,囊括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全方位规范了国人的社会行为。如购买日货、拒缴国民捐、迷信、吸食鸦片、学外语、穿西服,甚至逃课都有可能被骂作“亡国奴”。自“五四”以后,这种批评和惩戒不仅频繁出现在纸面上,而且蔓延到街头,形成民众对特定个体的暴力事件。此种现象在湖南十分突出,如1923年湖南举行的一系列抗日游行中,便有此类行为。在长沙“五七游街大会”中,“一群小学生皆呼华警为亡国奴,又有中学生大叫打此亡国奴。秩序乃乱,警察纷逃署内,闭门自匿”[注]华:《长沙通信五七游街大会中之所闻》,《申报》1923年5月13日。。此后余波不断,“长沙有许多少年聚一团体,在街游行。遇有戴日本草帽或日货长衫者,即盖以‘亡国奴’之漆印”,“有一乘钢丝车者被盖一印,行人鼓掌大笑”[注]华:《五七纪念后之湘人态度》,《申报》1923年5月20日。。对“亡国奴”耻辱身份的抗争以此种形式展现出来,对于围观群众和新闻读者都具有强烈的警示效应。
无论是奖是惩,对于群众而言,身份抗争意味着觉悟。近代盛行的亡国史书写和阅读便与之相关联。鲁迅基于对中国国民性的一贯认知,对亡国史的实际作用作过罕见的反思。他说:“我们也无须再看什么亡国史了。因为这样的书,至多只能教给你一做亡国奴,就比现在的苦还要苦;他日情随事迁,很可以自幸还胜于连表面上也已经亡国的人民,依然高高兴兴,再等着灭亡的更加逼近。”[注]《鲁迅全集(编年版)》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582页。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在强调亡国史阅读的重要性。1903年,陈独秀担心中国将要面对被瓜分的惨状,写道:“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注]胡明编选:《陈独秀选集》,第2页。在他看来,群众需要动员,方有救亡之觉悟。这种看法在思想界极为流行。1921年,谭平山愤愤地指出:“象国内‘谁做皇帝都是一样纳粮’那般头脑的候补亡国奴,那知道国民应当有救国的运动?”[注]杨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1919—1949)》,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李公朴在1933年的一次演讲中历数“五四”以来中国人的心理起伏。他说,“五四”前“大家曾感觉到一种亡国的恐慌”,但此后“又似乎对这种恐慌冷淡了许多”。即使发生九一八事变,“一般人尚认为没有民族存亡的根本关系”。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才感到非常的危险而兴奋起来,但一闻停战协定成立,一班心理则又由过度的紧张而入于异常颓废的时期了”。随后“热河失守,日军陷山海关,攻秦皇岛,逼平津”,一般国人才进一步消除“种种苟安谬误的心理”,“又立觉惶惶不可终日”。在李公朴看来,这充分暴露了“整个民族”的“无组织无民族意识”。[注]蔡元培等著:《国耻演讲集》,《申报》馆,1933年,第51—52页。随后爆发的全面抗战则为民族的组织和团结提供了空前的契机。
民族意识的普及与强化并非易事,鲁迅对亡国史阅读的反思即有“怒其不争”之意。近代有识之士为唤醒国民进行了种种尝试,清末以来流行的“亡国奴”话语即是其一。从清末到民国,伴随着西方列强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步步为营的侵略,“亡国奴”从少数爱国志士笔下逐渐传播,最终变成一个耳熟能详的污名。一则新闻称:“重庆警察厅长,不喜闻亡国奴三字。凡说亡国奴者无论老幼,必拘之而治以罪。”20世纪以来,累加附着在“亡国奴”一词上的情感相当强烈,这位警察厅长因嫌“不祥”而禁言之,其实是表达身份焦虑的一种极端方式。不过在当时情境下,禁言“亡国奴”几乎就等于反对抗战而自甘为“亡国奴”了。舆论质疑该厅长“此种恶讳,真令人大惑不解”[注]《五四运动在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54页。,足见这一概念的强大生命力。
用一种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这种意识本身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产物。甲午之前即已萌芽的议会和立宪观念,即针对中国上下的壅蔽状况,至梁启超讲“新民”,个中意味已经显而易见。此后,20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社会运动都以“国民”和“群众”立论。唯其明了这一时代大背景,才能更透彻地理解“亡国奴”身份抗争的旨趣所在。作家苏雪林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大众”只是左派“最大的幻影和由这个幻影所生出来的最后的信仰”,而且视左派为与她的“救国志愿”相悖的“恶势力”,庆幸自己受了胡适的指导,未被这“汹涌的时代潮流扫卷而去”。可是,她又不得不承认:“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向中国侵略,政府态度不明,四万万人都抱有行将为亡国奴的忧惧……左派理论,恰恰指引我们一条出路。”胡适的回信说:“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注]《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34—636、642页。考虑到苏雪林的保守和胡适的低调,可见大敌当前,民族动员的“时代潮流”对思想界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中共走上历史舞台后,对群众的重视达到了空前高度,为贯彻群众路线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抗战期间,中共曾利用群众对“亡国奴”身份的抵制进行宣传动员。如抗战伊始,八路军在宣传任务中专门设立“誓死不做亡国奴”一项,并将其与“保卫山西、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好男儿上前线去”等作为“基本的政治口号”。毛泽东在演说中也号召“一定要把亡国奴或亡国奴威胁的锁链摆脱掉”。[注]《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第198、234页。邓小平针对日伪的奴化教育,号召在宣传上“利用沦陷区的具体事实,指明亡国奴的惨痛”[注]《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周保中也特别主张教育新收的游击队员“宁做中国鬼,不做亡国奴”[注]《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874页。。《晋察冀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配合党的号召,时常出现相关宣传报道。
这种动员强化了民众的身份抗争意识。例如,陕甘宁边区印刷工人贾文龙认识到,自己的父母“在上海已做了六年亡国奴了”,为了避免做“亡国奴”,他“要永远跟着共产党一道斗到底”[注]《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陕西卷》上册,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74页。。这种抗争意识转化为抗战意志,其力量不容忽视。傅斯年就感受到“新教育”特别是“民族主义教育”所表现出的“力量”[注]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教育促进了民族觉醒,这一觉醒对于抗战具有重大意义。诚如老舍所说:“‘九一八’是我们民族莫大的耻辱,也是我们民族空前的觉醒。有了这觉悟,所以去岁‘七七’没有成为第二个‘九一八’。”[注]《老舍全集》(1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81页。中国人民对“亡国奴”屈辱身份的集体抗争,成为中华民族长期抗战的一种心理动力。
结 语
“亡国奴”这一称谓上承甲午战后清朝士人的“亡国灭种”想象,下接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及朝野各方的宣传动员,在近代民族动员中产生了极其深远、广泛的影响。在1895年至1945年这半个世纪里,“亡国奴”一词随着日本侵略的逐步加深而日益深入人心。“亡国则为奴”的观念形成和固化于各种相关文艺和历史叙事中。国人对“亡国奴”身份的焦虑成为20世纪上半叶社会集体恐慌和耻辱的重要来源。这种社会心理激发了人们对“亡国奴”身份的抗争。“屈辱—抗争”机制在抗日民族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前夕的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弱国,朝野在外交问题上存在常态性的分歧乃至对抗,而对“亡国奴”屈辱身份的共识为各方最终走向联合抗争提供了一个认知基础。
当然,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绝不仅仅是因受到“亡国奴”这一个污名的刺激而作出的反应。甲午战争以降,思想界进行的民族国家话语建构有着波澜壮阔的内容,由此唤起的现代民族情感和民族气节构成了民族抗战的心理基石。“亡国奴”身份抗争是这一宏大民族心理结构中的诸多内容之一。从“亡国奴”这一概念的产生和流行来看,它与1895年至1945年的中日关系息息相关,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历史脉络在其中清晰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