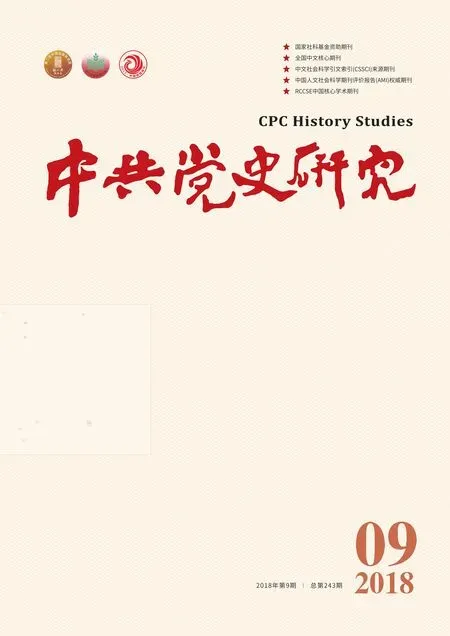纪念李新同志
金 冲 及
现有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大抵只写到晚清和民国时期。对新中国的发展即便讲到,也十分粗略。此中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再过若干年,总会有比较详备的包括新中国在内的中国史学史著作问世。拿文学界来说,不是已有不少中国当代文学史之类的著作出版了吗?以论述和剖析历史为己任的史学工作者,决不会长期对这几十年来中国史学自身的历史置之不顾,不去对它的发展历程进行严肃认真的分析研究。
到那时,我想,在这类著作中应该讲到李新同志,尤其是他主持开拓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因为它产生的影响对史学界来说是全局性的,而且过些时间后会看得更清楚。
李新同志是我尊敬的前辈学者,我知道他的名字已经将近70年了,但最初听说他,并不是因为史学,而是因为教育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复旦大学担任教务部副主任。全国的高等学校在院系调整后都在努力建设新的教学体系和制度。但是,应该怎么做,大家心里却没有数。我们许多人认真读的是苏联学者凯洛夫的《教育学》,想从这里找到依据,但总觉得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从解放区迁来扩建而成的高等学校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李新同志正在帮助吴玉章校长负责人民大学的教务工作。那时,上海和北京的交通往来还相当不便,很难有机会到人民大学看看,更不容易见到他请益。但在教育部的内部材料上,我多次读到过李新同志对怎样建立一套中国自己的新教育制度的谈话或文章,文风总是明白晓畅,独有见地,给人留下很深印象。
第一次见到李新同志,是1961年10月在武汉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现在经常忙于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中青年学者也许很难想象,那时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是极为罕见的。在上海的复旦大学不算闭塞,我在复旦给学生讲中国近代史的课程也已经八年多了,但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那次参会的前辈学者很多,如吴玉章、李达、范文澜、吕振羽、吴晗、白寿彝、邵循正、何干之等。摄影时,我和戴逸、李侃、李文海、祁龙威、王思治等站在第三排,而时年43岁的李新同志坐在第一排,可见史学界对他的尊重。在这种场合下,我不好凑上去找他,所以那次并没有同他说过话。
会后,我和胡绳武同志开始着手写《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这时,吴玉章同志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刚刚出版,我至少认真地读过五六遍。后来听说它是李新同志帮助整理的,确实使我肃然起敬。
1965年,我调到北京工作,但“文化大革命”随即开始,我被审查了五年,自然更谈不上和李新同志有见面的机会。
我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年长的同志本来很熟悉。一到北京,最早来看我的,就有丁守和等同志。王学庄、刘志琴、朱宗震、丘权政、吕景琳等是我在复旦教中国近代史课时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和近代史所同志的来往就很多了,同李新同志也有了接触的机会。那时,我在文物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1980年,近代史所曾两次来商调,都没有办成。我心里是很愿意到近代史所做研究工作的,但由于习惯于工作安排听从组织决定,所以自己完全没有过问,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后来有近代史所的朋友对我说:“调你,是‘三驾马车’都能接受的。”近代史所的“三驾马车”即刘大年、李新和黎澍。由此我才知道,这件事也包含着李新同志对我的厚爱。
1985年起,我被聘为近代史所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当时,所外的学术委员还有严中平、胡华、戴逸三位),前后共15年。李新同志当然也是学术委员。在这段时间内,我还有机会同他一起参加了不少国内的学术会议。于是,我们的接触就多起来了,谈得最多的自然是中华民国史的编写,有几点给我的印象最深:
第一,民国时期的中国,同新中国直接衔接,如果对这段历史的方方面面不进行切实的研究,那么,对新中国的国情和它的由来就难有更深入的了解。但是,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能够毅然决然地把这项任务担当起来,坚持到底,做出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成果,实在极不容易。
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前面讲到,我和胡绳武同志从1961年起开始动手写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到1963年,第一卷已经完稿,并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审读后决定出版,编辑部的具体意见也提给了我们。但当时国内的政治空气已经越来越紧张,听说夏衍同志准备拍摄关于秋瑾的电影,江青知道后就说:“怎么?现在还要宣传国民党?”我们写的《史稿》第一卷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开始时起,到兴中会成立,再到同盟会成立前夜,那不更是要被说成“宣传国民党”吗?那不是自己对准了来势凶猛的枪口冲过去?还是把这本书的出版先搁下来,看看情况再说。这一放,就放了18年,到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时才稍作补充、修改后出版。
一比,就见高下。李新同志主持编写中华民国史,虽然是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提出来的,但那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项工作一做起来,就遇到许多阻力,编写中更会碰到许许多多原来没有预料到且不易处理的问题,存在许多未知数。如果不是李新同志下这样大的决心,既有胆略,又有韧性,那么,拖一拖就可以把这件事拖黄,整个中华民国史研究都有可能停顿下来,至少还要经历不少曲折。李新同志在紧要关头表现出来的胆略和勇气,不能不令人钦佩。
第二,下决心承担这个任务后,应该编写成怎样的一部中华民国史,又面临两种选择:匆忙地草草了事,就算完成一项任务,还是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尽力写出一部在当时所能达到的高水平的著作来?
李新同志有过主持编写多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等的丰富经验,一开始就提出很高的要求,强调不能急于求成,必须首先扎扎实实地掌握丰富可靠的历史资料,进行具体分析,尽力弄清事实真相,在此基础上才能动手进行论述。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就是这样起步的。
他对编写中的中华民国史的结构,提出了一个气魄宏伟的构想,即要包括《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专题资料》等几个部分。这既体现了他先把有关史实弄清楚、弄准确,以避免出现“硬伤”或流于徒发空论的要求,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史学著作的编写传统。大家知道,中国号称正史的“二十四史”,大体上是由纪、传、志、表几部分组成的。《中华民国史》是主体,类似正史中的“纪”。《人物志》在体裁上就是“列传”。《大事记》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表”的作用。缺少的是“志”,《专题资料》原来设想在这方面起些补充作用,但没有做完。当然,民国史研究这样巨大的工程本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研究也很难说有止境,但前人筚路蓝缕的开启之功是永存的。
第三,参加中华民国史编写工作的学者人数众多,组内人员最多时达40多人,以后有些人分散到其他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去;参加协作的单位和人员更多;不少编写成果和副产品陆续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些对新时期史学界的学风所起的“润物细无声”作用是很大的。
编写中华民国史这件事,既是许多学者众志成城的成果,反过来,也培育出为数不少的人才,他们活跃在今天的史坛上,成为史学界后起之秀的骨干力量。这是一项无声的重要成果。
李新同志知人善任,能够把可以掌握的力量迅速组织起来,各尽所能,既大胆放手,又严格要求,使参加这项工作的年轻人明白自己的任务,心情愉快,比较快地投入其中并得到成长。他十分关心参加这项工作的成员在工作和生活上的甘苦,帮助不少年轻人解决了他们难以解决的重大困难。许多人都对此有过感人的描述,我就不再多说了。
这里只补充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青年学者取得研究成果是多么喜悦,并希望这些成果被更多人所了解。
在《中华民国史》有一个分卷刚出版的时候,一天,他突然到我家里来。我实在惶恐不安,对他说:“李新同志,您老人家怎么自己来了?只要打个电话,我立刻会赶到你家来的。”他就拿出这本近60万字的书来,叮嘱我写篇介绍文章,书上还有他自己的签名。这件事使我很感动。我一直把这本书放在我对面的书柜中,也是对李新同志的纪念。
今年是李新同志百年诞辰。民国史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不断走向深入。研究民国时期方方面面历史的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史学界占有很大比重,这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事实。此时此刻,曾在李新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学者写出一批怀念他的文章,汇成《踏遍荒山罕见松——李新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陈铁健同志嘱我也写几句话。这是我应该做的。虽然写得很匆忙,但多少也表达了我对这位前辈的缅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