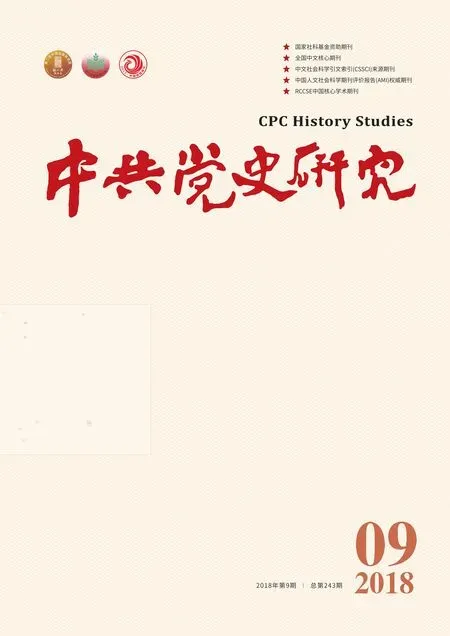我记忆中的李新先生
章 百 家
李新先生是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我是他指导的最后一名学生。那时,先生年事已高,编书的任务很繁重,因我已有十余年工作经历,他对我比较放手。尽管我与先生的接触不算很多,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却是非常独特的。
能够成为李新先生的弟子,对我而言既是运气,也是缘分。听闻先生的大名,是在北大历史系读本科时。不过,那时我并未想到日后会成为他的学生,因为我学的是世界史专业,主修美国史。毕业一年后,在报考研究生时,我决定改学中国近代史,主要是觉得应该对本国历史有更多了解,而且可以把学问做得更扎实些。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科学恢复和迅速发展的时期。1983年,社科院近代史所准备多招些研究生,民国史专业是重点,打算招个研究生班,确定了两位导师,一位是李新,另一位是李宗一——近代史所当时的所长。我因本科不是中国史,看到这个班招收的人数较多,就报考了。由于这届考生成绩不甚理想,近代史所最后只录取了三名学生,报考的都是民国史专业。结果,入学时一个分配到中外关系史专业,一个分配到近代经济史专业,只有我进了民国史班,两位导师,一个学生。
我们这届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时,院里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学生们借住在玉泉路附近的几家单位。那里离近代史所很远,但当时专业课不多,教学也不很正规……负责指导我专业课的是李宗一先生,但他很忙。他告诉我,民国史成系统的教科书只有一本,就是李剑农先生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专业学习则主要靠自学。好在近代史所有三大优势:一是藏书丰富,特别是有许多台湾版书籍,当时在别处是难以寻觅的。二是有一批老先生,知识渊博而又毫无架子。或许是政治运动经历得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恪守“君子述而不作”的原则,以读书为趣,不求著作等身,只求万事皆知。向他们求教,与他们聊天,真是长知识、开眼界、受启发。三是全所上下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严谨的学风。当时所里的一批中年研究人员多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深感被耽搁的时间太多,所以都十分努力,并乐于帮助我们这些后学。回想起来,求学路上得两位名师指教,又遇近代史所这样的环境,真可谓三生有幸。
第一次拜见李新先生,已是第二个学年的某个夏日。李宗一先生告诉我,我的毕业论文由李新先生负责指导。那时,李新先生住在紧邻颐和园的中央党校南院,院内有个大水塘,还有几座年久失修的二层小楼,先生就住在其中一个单元里。进入室内,首先看到的是拼在一起的几张书桌,上面堆满书籍。房间的一角还放着一张写字台,一个戴着眼镜、穿着白色圆领衫的小老头摇着蒲扇在那里看稿子——这是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初次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大抵是我介绍个人情况,听听他的意见。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我大约每隔一两个月会去见他一次,除讨论有关论文的问题外,谈话的内容越来越广泛。
李新先生操四川口音,待人和蔼,十分健谈。一两次接触之后,我便感到,他是那种人生难得一遇的老革命、老干部和史学大家的混合体,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又直言不讳,绝少教条气息。那种天南海北、无拘无束的谈天便是他为我授课的方式。回想起来,先生的教诲有四点令我终身受益。
其一,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历史最宝贵的品格就在于真实”。他常说,史学与文学、艺术不同,文学和艺术追求的是“善”与“美”,而历史研究追求的是“真”。求真并不容易。一方面,历史本身极其复杂,充满种种矛盾现象;另一方面,历史写作不免受到现实环境限制。他说,写信史就得说真话,有时真话不便说,那就讲几句空话,但绝不能说假话。在先生看来,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必须首先是一个正直的人。
其二,对于学生,先生的要求是严格的,最看重的一点是勤奋。他经常告诫我,做历史研究一定要坐得住冷板凳,一定要掌握第一手资料,言出有据。他总说,搞史学的人不一定要很聪明,但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只要勤奋,慢慢积累,总会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我毕业论文的选题是“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对美政策”。这个题目当时比较新鲜,很快得到先生认可。在我动笔写作时,他反复询问的是收集的史料是否已经足够,是否能做到孤证不取。先生主张“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对于那种还没研究就预设观点,然后再拼凑史料的做法,先生是很不屑的。
其三,对于文风文字,先生一贯提倡精炼、平实、准确。我以为这与先生强调史学在于求真这一点互为表里。这个要求看似平常,真正做到很不容易。从事历史研究的时间越长,对这一点的体会就越深。用寥寥数语把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概括清楚,用平实的语言勾勒出历史的波澜,这颇费斟酌,也最见功力。而“准确”所包含的不仅是对史实的把握,也包括文字表达和词汇运用。记得我在毕业论文中写道,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极为兴奋,弹冠相庆。先生即指出,“弹冠相庆”一词专用于同僚中有人升官而众人庆贺,放在这一场合属于用词不当。
其四,先生思想活跃,他总说,做研究工作一定要善于独立思考,不能拘泥于成说。然而,他在主张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强调尊重常识、保持常人见解的重要性。先生认为,事物都具有多面性,革命不能因循守旧,改革必须有所创新;过去犯“左”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偏离常识,在分析问题时把某个方面推向极端。先生以对人性的认识为例说,过去只强调人性带有阶级性的一面,而否认有超阶级的一面,比如母爱就是人类一种普遍的情感。我以为,先生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也是他反思历史的一个结晶。在他的革命生涯和学术生涯中,这类事情经历得太多。“文化大革命”中那个尽人皆知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苖”就是最极端的例子。先生的思考对我日后从事研究工作启发颇多。在梳理改革开放的历程时,我常想,我国的改革,不就是既有创新,又有向常识的回归吗?
三年时光一晃而过。快毕业时,许多同学都打算读博士。我问先生是否可以考他的博士生。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你这么大年纪了,还不赶快工作,念什么博士?我们这些人还不是啥子‘士’都没有!”毕业之后,我在近代史所工作了十年,后来又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直至退休。在这两个单位,李新先生都曾是领导。不过,我毕业那年,他也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因此我从未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与他始终是师生关系。
做学生时,我对李新先生的经历略有所闻,后来读了先生的回忆录,才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先生在中学时代即投身革命,参加救亡运动,是重庆学联的主席。全面抗战爆发后进入陕北公学,后在晋冀豫根据地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在河北永年担任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前后即投身教育事业,主要是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建工作。那时,邓小平要调先生去西南局任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这是个相当于如今副部级的职务。但是,先生仍决定留在人民大学从教,成为一名“双肩挑”干部。1962年,先生辞去一切行政职务,调至中科院近代史所任研究员,专心治史。1978年,任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1980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但并非调任,前一个职务仍旧保留着。这两个任职,一个副局级,一个副部级,今天看来算是奇葩。据我所知,先生的工作主要在社科院近代史所,主编两部大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和《中华民国史》。党研室的职务大约是为了解决他的待遇问题。1986年,先生退居二线,仍任研究员,思索不止,笔耕不辍,直至病重方休。
先生对我的影响似在有形无形之间。我对先生的敬佩是随着我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经历的延长而不断增长的。一位老革命、老干部,弃官从学,一心以治史为己任,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做学生时,先生对我的那些教诲似乎并无新鲜之处。但在从事研究工作之后,我越来越体会到,那正是历史学的灵魂和生命所系。而先生对于学生的那些要求,他是身体力行地做到了。
先生的个人著作不多,大约只有几本回忆录,后由师兄陈铁健整理汇集成《流逝的岁月》一书。这些回忆以史学家特有的敏感和反思精神,以白描式的手法,记述了先生亲历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以为,这些回忆最典型地反映出先生作为历史学家所持有的价值观。
先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两个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特长和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组织开展大型研究项目和主持编写大型史书。这两个项目涵盖了20世纪前半叶的所有重大事件。当时,这不仅需要做大量的开拓性研究,更困难的是,许多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带有政治敏感性,要形成有建树的新观点,就必须解放思想,突破禁区。读这两部书,特别是与此前的研究作比较,就会发现书中的创新很多,而这些重要的新观点、对事件和人物的新评价都是在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反复拿捏之后才形成的。能够坚持住这些新观点并写入书中,其实很不容易。先生之所以成为主持这类项目的不二人选,不仅因其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开阔的眼界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是真正的行家里手,在学术上足以服众;而且因其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在史学界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能够调动各种资源,同时还有足够的阅历和资历,可以顶住来自上下左右的种种压力。可以想见,他为这两个集体项目所付出的辛劳是巨大的。这也是他个人著作不多的主要原因。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可贵的牺牲精神。
作为史学大家,先生的身份是双重的,既参与了那段历史的创造,又主持了那段历史的编写。这种双重身份使他的认识和批判有许多独到、深刻之处。岁月流逝,那一代人已经远去。然而,先生的人格、学问永远值得后人敬重、学习与推崇,先生的思考也将永久地给后人以启迪。
——以近代史所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