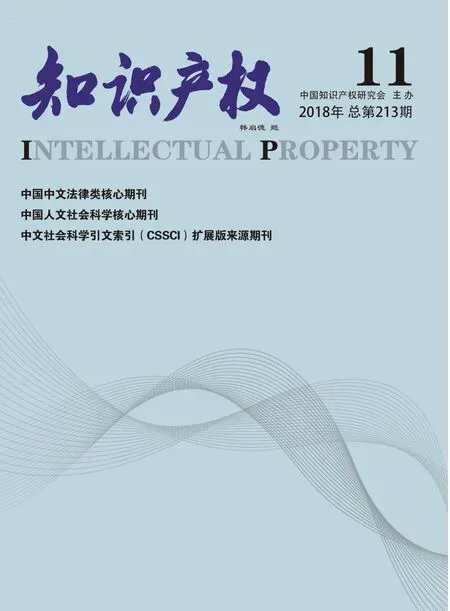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孙 山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要想获得著作权法上的保护,必须证明其独创性和智力成果属性。除此之外,“思想”“人格”是否属于作品的隐藏构成要件也存在较大争议。通过还原相关概念的规范目的不难发现,独创性判断的对象只能是已经生成的表达本身,智力成果的结论只能根据已经生成的表达结果进行推定,在具备生成一定数量不重复内容可能性的情况下推定为智力成果,“思想”“人格”不具有实质上的规范意义。因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应当采用拟制的技术将人工智能的所有人“视为”作者,从而确保完整产业链的形成。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之一,言必谈人工智能变成一些行业领域的时髦之举,毕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对诸多行业领域产生必须直面的影响。人工智能热议的同时,我们也应当保持适度的冷思考。目前的人工智能,还只是窄域人工智能(ANI,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专注于完成某种特定任务,并非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通用人工智能(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未来还远未到来,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掺杂了很多不必要的焦虑与恐慌,困境多由此而生,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法保护问题上也是如此。按照《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的规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和“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判断无需更多赘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作品属性的关键在于独创性和智力成果的证明。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以作品应当体现作者的思想、人格为由否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①参见刘影:《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法保护初探》,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9期,第44-50页。思想、人格究竟是不是作品构成要件中的隐藏要件?由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保护陷入困境:如果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构成作品,那么就要解决前述法理上的诘问;如果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构成作品,而是通过邻接权的范畴对其实现救济,那么我国著作权法上封闭的邻接权体系就会成为横亘在邻接权模式面前的“通天河”。本文则要通过还原相关概念的规范目的来证明如下判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属于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相关权利归属于人工智能的所有人;“思想”“人格”因素在作品认定中没有法技术层面的意义,不能以此否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只有将独创性的判断还原为针对表达本身的纯客观判断,排除“思想”“人格”等主观因素的干扰,我们才有可能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完成逻辑论证;只有将相关权利归属于人工智能的所有人,厘清所有人与设计者间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建构符合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要的著作权制度,寻找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法保护的出路。
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独创性的证明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法保护的焦点之一,是生成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在这一问题上,支持者认为独创性判断是只对作品的表达本身作客观评价,生成内容与既有表达不同则独创性产生;②如易继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37-147页;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第3-8页。反对者则认为独创性要求创作过程中必须拥有独创性的思维和方法,独创性判断实质上以生理意义上的人的存在为前提。③参见罗祥、张国安:《著作权法视角下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145页。争论也可以被转化为,独创性的判断是只针对已经形成的作品的具体表达,还是延及作品形成过程中的思想?换言之,独创性的判断,究竟是作品出现后的事后判断,还是创作过程中的事前判断,这是个必须解决的前提问题,判断的准确性正基于此。
独创性的判断对象是已经形成的表达本身,判断时只需要对表达作形式上的审查,独创性的判断是一个纯客观的过程,是表达形成后的事后判断。独创性强调作品是由作者本人独立完成并具有创造性,独立完成是对创作行为的要求,创造性是对创作结果——表达的要求,二者均与思想无关。独创性的实质,是新生成表达与既有表达间的差异,至于表达背后可能蕴含的思想是否相同,基于思想/表达二分法的排除作用,在所不问:“独创性指称、描述、限定的对象,是且只是表达”。④孙山:《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法规制——基于对核心概念分析的证成》,载《浙江学刊》2018年第2期,第114页。在具体的表达形成之前,无论思想多么深邃、与众不同,都与著作权法绝缘;在具体的表达形成之后,如果新生成表达与既有表达不同则符合独创性的要求而构成作品,反之则否。对于创作过程中藏之于创作者头脑中的思想,外人无从得知,也就不可能作表达形成前的事先判断。作品形成后,思想具化为表达,具有著作权法意义的范畴,是表达而非思想。总之,独创性的判断对象是已经形成的表达本身,是表达形成后的事后判断,法律保护只针对创作结果,不能扩及到创作过程,强调“独创性思维和方法”的事前判断超出了著作权法的调整范围。
基于技术层面的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符合独创性的要求。与人类相比,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在生成不同于既有表达的内容方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在没有外界刻意提示的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人类作品没有区别,人类已经很难从表达形式上分辨出人类作品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也就是说,从外在形式上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完全符合独创性的要求。当然,从内在逻辑看,部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随机性的成分,在逻辑上有悖于常理,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有待提升,但思想性和艺术性本身不是赋权时考虑的因素,逻辑上的不足也会随着算法的改进而逐步弥补。在绝大多数人无法有效区分的情况下否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独创性,事实上很难行得通。换言之,一些学者否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独创性的理由,并不是其本身不具有独创性,而是因为人工智能这一生成主体本身,是基于对人工智能的事后认知而回溯完成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具有独创性的事先判断,是在脱离表达谈独创性。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人工智能的设计者会努力开发出生成内容有差异的人工智能。一些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只是生成相同内容的技术手段,都是在执行既定流程和方法,与体现个性化的智力创作存在根本区别。⑤参见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48-151页。实际情况则有所不同,不同企业间的人工智能设备所生成的新闻报道等并不相同。如果说所谓“生成相同内容”是指同一人工智能只会生成相同内容的话,那么微软小冰对同一图片所生成的不同表达的诗就会推翻这种假定。退一步讲,即便“生成相同内容”指向的仅是需要大量数据支撑和数据分析的体育和财经等新闻报道撰写类人工智能,那么独家研发或买断的市场运营实践也会在事实上排除了相同内容生成的可能性。因此,“生成相同内容”只是部分学者对人工智能的想象,不足以否定生成内容的独创性。
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智力成果属性释明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智力成果属性,面临如下质疑:有以生成过程并不需要创作过程所需的“智能”为否定理由的;⑥参见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52页。也有以人工智能并不具备同于人类的“思想”“人格”为由否定生成内容之智力成果属性的。⑦例如曹源:《人工智能创作物获得版权保护的合理性》,载《科技与法律》2016年第3期,第488-508页。但是,如果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生成过程中不包含“智能”,那么人工智能本身都需要重新界定,至少在现阶段技术水平下人工智能便名实不副。“思想”“人格”固然为人所独有,但作品能否体现二者以及体现了何种具体内容的“思想”“人格”都是无法确证的,不体现二者的作品类型也在各国著作权法中有规定,以“思想”“人格”的欠缺为由否定智力成果属性存在很大漏洞。因此,有必要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智力成果属性予以释明,确定智力成果与哪些因素有关。
智力成果的判定只能根据已经生成的表达结果进行推定,在具备生成一定数量不重复内容可能性的情况下推定为智力成果。此处所说“智力成果”,是著作权法上的概念,属于功能性的界定,与生活语言中的“智力成果”不同,后者只需要考虑智力的投入和表达的形成,前者则要服从于特定规范目的的实现,包括“鼓励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⑧特定规范目的的表述参见我国《著作权法》第1条。“智力”与“智能”二词,貌似有别,还原为英文则均为“Intellectual”。因此,如果还要继续使用“人工智能”这样的表达,承认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至少已经达到了窄域人工智能,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人工智能的“智能”与人类的“智力”具有相同的逻辑基础。与动物不同,人工智能和人类均使用了人类创造并能为人类所理解的符号形式,人工智能和人类有相互理解的对象前提,此即为相同的逻辑基础。人类生成内容之所以能被认定为智力成果,在于人类作者有选择的空间,在自由选择的前提下生成了不重复内容,构成具有独创性的表达。也就是说,人类生成内容被认定为著作权法上的智力成果需要考量以下因素:第一,有选择的空间,只有有限选择甚或唯一选择的情况下,则基于思想和表达的合并理论(the merger doctrine)被排除在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第二,经过选择之后生成了不重复的内容,与既有的表达能够清晰区分;第三,只关注构成表达结果的智力成果,不涉及生成过程。在有选择空间的情况下生成的不重复的内容,属于智力成果,至于生成过程中的思想,只能通过已经生成的表达结果推定存在,并不能作为独立的、有规范意义的作品的构成要件。显然,在不预设智力成果只能由人类完成的语境下,目前的人工智能已经可以生成一定数量不重复内容,符合智力成果的要求。
智力成果的界定,不仅要考虑智力的存在,还要考虑生成内容的可通约性,考虑是否能为人类所理解,处于人类理解范围之外的生成内容都不可能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智力成果。智力并非由人类独占的现实并不能推导出动物的智力成果也应当受到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同等对待,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有观点认为,动物具有创作作品的智力和情感能力,动物画作属于作品。⑨参见刘媛:《动物画作的著作权研究——以实证主义为视角》,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25-29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动物是否有智力,而在于动物的智力成果能否被人类所理解,动物能否有意识地大量、长期生成一定类型的智力成果。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人类理解动物画作只能是一句不负责任的玩笑而已。动物画作的出现,都是动物主人的长期有意识训练,并非动物的自主行为,设置权利不会刺激动物的生成行为,不知所云的画作也不可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充其量只能促进个别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而这与著作权制度风马牛不相及。“动物不可能完全懂得人类的符号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并能动地选择符号有机组合在一起”。⑩张玲、王果:《动物“创作成果”的民事法律关系三要素分析》,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2期,第14页。人工智能与之不同,其使用人类表达方式,表达结果能被人类认知、理解并作出评价,增加了人类社会可供阅读的作品总量,应当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
“思想”“人格”因素被部分学者引入作品认定中的目的之一是排除非人类生成内容成为作品的可能性。通常认为,“作品是作为有血有肉的自然人对于思想观念的表达”。⑪李明德、许超著:《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一些学者否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以构成作品的理由,是传统著作权理念中只有人才能创作作品,只有人才能受到著作权制度的鼓励而产生创作的动力;⑫参见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48-155页。人工智能不可能具备思想,生成内容不可能是思想的表达,仅是一种通过算法进行分析、选择所完成的机械式输出,⑬参见曹源:《人工智能创作物获得版权保护的合理性》,载《科技与法律》2016年第3期,第494页。故而排除在作品的保护范围之外。毫无疑问,只有人才能准确感受到著作权制度的鼓励,所以自然人和拟制的法人才能成为著作权的主体,本文亦不赞同著作权应归人工智能本身。但是,只有人才能创作作品的理念则是在以下推论基础之上的:作品必然体现“思想”“人格”,而“思想”“人格”为人类所独享,所以只有人才能创作体现“思想”“人格”的作品。
然而,作品并不必然体现“思想”“人格”,作品体现“思想”“人格”的假设是为了完成著作权制度正当性的说明,这一假设本身难以确证,不具有实质上的规范意义。首先,作品是否体现了“思想”“人格”,作者以外的主体无从确定实际存在,只能推定存在。所谓“思想”,是读者对作品解读后的结果,我们根据表达而解读“思想”“人格”,而真正的“思想”“人格”只有作者本人才可能确定,作品与“思想”“人格”只有形而上意义上的关联,不能据此界定作品的构成要件。其次,作品究竟体现了何种“思想”“人格”,也只有作者本人可以确定,“思想”“人格”并不像“表达”一样具备立法与司法中必需的确定性,不能作为规范设计的基础。寻找确定的中心思想,这是我国千百年来的科举考试和近几十年的应试教育所造就的独特国民心理,已经深入骨髓,而其实质,则是一种无知导引下的狂妄。思想是仅仅存在于人脑中的智力活动结果,表达则是由此发生形成的外在形式,⑭参见金渝林:《论版权理论中的作品概念》,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99页。我们只能通过表达来倒推思想的具体内容,即便作者确实通过作品的表达想传达某种思想,作者以外的人也不可能尽知。“思想”如此,“人格”亦然。第三,即便作品没有体现“思想”“人格”,仍然可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对作品的概念界定中并没有出现“思想”“人格”,第4条对13种具体作品的定义中只有舞蹈作品明确规定“表现思想情感”,仅从条文的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来看,没有体现“思想”“人格”的表达也属于作品。13种具体作品类型中,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要发挥指示功能,受制于客观事实,根本无从体现“思想”“人格”。 进言之,“作品是个体的精神涌现物和表现物,是思想或者情感的表达”⑮李雨峰著:《中国著作权法:原理与材料》,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的界定只是理想状态下应然意义上的描述,并非现实状态下实然意义上的定义。综上,作品并不必然体现“思想”“人格”,作品界定中无需强调“思想”“人格”的存在,不能据此否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成为作品的可能性。
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权利归属的制度选择
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问题上,存在着三种分歧较大的看法:按权能类型分别赋权给人工智能的使用人和设计者,⑯参见王小夏、付强:《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问题探析》,载《中国出版》2017年第17期,第36页。赋权给人工智能的所有者,⑰如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第3-8页。赋权给人工智能本身但由人工智能的所有者代为管理。⑱参见孙那:《人工智能创作成果的可版权性问题探讨》,载《出版发行研究》2017年第12期,第61页。赋权给哪方主体固然需要论证,而其前提——通过著作权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促进人类社会的作品传播和创作,也需要作出实证分析和逻辑上的说明。
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通过著作权法进行保护,这样的制度选择对于人类社会的作品创作与传播而言,利远大于弊。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予以著作权法的保护,表面上看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人的就业,实质上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目前来看,人工智能主要用于生成以诗歌和新闻报道为代表的文字作品⑲例如微软小冰、腾讯的Dreamwriter等。、音乐作品⑳例如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音乐学教授戴维·柯普(David Cope)完成的EMI(Experiments in Musical Intelligence)。及美术作品㉑例如美图公司旗下的绘画机器人Andy。,这些作品的表达相对简单,不需要大量的、意义取决于情境的对话,不需要打造复杂的结构,也不需要融入大量的生活体验。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也很难突破上述基于生理原因而形成的限制,生成内容局限于特定的作品类型,“从人工智能在各个门类的创作活动及相关作品中,至今看不到电脑能够完全代替人脑的任何可能性”。㉒杨守森:《人工智能与文艺创作》,载《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190页。因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保护只会让从事限定类型作品创作的人失去原来的工作,不会对绝大多数类型作品的创作者产生冲击。即便是对于那失去工作的一部分人而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保护所导致的失业也并不意味着人生的终结,而是意味着解放,将那一部分人从无趣味、繁琐、低创造性类型作品的创作活动中解放出来,从事新的、更有价值的工作。新技术的出现在导致旧工种消失的同时还会带来更多新工种,这一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趋势已经在历史上被无数次证明。有一种观点认为,不保护人工智能创作成果从长远来看会挫伤人类创作的积极性,从根本上瓦解版权制度存在的根基。㉓参见孙那:《人工智能创作成果的可版权性问题探讨》,载《出版发行研究》2017年第12期,第17页。这种担忧纯属杞人忧天。如上所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仅限于特定的作品类型,根本无力挤占人类作品的市场,立法者保护与否的价值判断不会影响到靠金钱激励的创作者,更不会影响到醉心于自我表达的创作者。不但如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保护还会倒逼人类作者创作出具有更高独创性的作品,提升人类作品的整体质量。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上的著作权,应当归属于人工智能的所有者,所有者被“视为”作者。赋权给人工智能的所有者,根本理由在于确保完整产业链的形成,维系产业的发展。需要明确的是,不给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法的保护,会影响到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但不会影响到著作权制度的存在。我们必须审视此前部分国家立法将著作权主体限于人类的深层原因,反思其理由的可靠性。主体限于人类,有完成正当性说理的需要,也有有效赋权、方便追责的考虑,更有科学设计著作权制度的考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法律保护,归根到底,是要合理分配因生成内容的商业利用而产生的利益,助益人工智能产业的良性发展。著作权制度只能激励人工智能的所有者,不能激励人工智能本身,将人工智能当作主体对待没有法律意义。如果不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加以保护,那么理性市场主体的选择必然是不购买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就成为梦幻泡影。如果不能赋权给人工智能的所有者,那么理性市场主体的选择依然是不购买人工智能,无法收回成本的设计者也将选择不研发,产业的发展无从谈起。赋权给人工智能的所有者,保障其获得收益的可能性,著作权法语境下的人工智能产业才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相比之下,赋权给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而言,积极效果不如赋权给人工智能的所有者。如果设计者自身使用该人工智能,则设计者与所有者身份重合,赋权给谁没有实质差别。如果设计者自身并不使用该人工智能,而是转让给其他主体,此时设计者与所有者有别,设计者在出售人工智能的同时,还对生成内容保有著作权的话将会极大限制生成内容的利用,人工智能购买者的权益形同虚设。此种情形中,唯有将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赋权给人工智能的所有者,也就是购买者,人工智能产业才可能形成完整产业链。因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上的著作权,应当归属于人工智能的所有者。类似于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中规定的法人作品,㉔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人工智能的所有者可以被视为作者,此种选择并不会对社会公众造成任何不正当的限制。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应赋权给人工智能本身。立法应当未雨绸缪,同时也要注意前瞻性的限度,不能针对过于遥远的未来作远景规划。固然,民事主体经历了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的历史变迁,㉕参见李拥军:《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民事主体制度与理念的历史变迁——对法律“人”的一种解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2期,第45-52页。但这种历史变迁的背后,是经济交往的需要,而非泛滥的博爱情感。通过著作权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能与赋权给人工智能划等号。从科学技术层面来看,目前的人工智能尚不具备产生独立意志的可能性,功能与能耗的限制消解了人工智能之主体地位的现实基础。库兹韦尔笔下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奇点”是否真的存在及何时到来,没有人能给出确切、可靠的答案。当下的人工智能只是专注于完成某种特定任务的窄域人工智能,功能非常有限:“在科学或艺术的一些小角落里,它又可以与人类的创造力一决高下,甚至超过人类。但在一般情况下要与人类创造力匹敌就另当别论了”。㉖[英]玛格丽特·博登著:《AI:人工智能的本质与未来》,孙诗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若是寄希望于生物学意义上大脑的模拟,那么能耗将是难以逾越的山脉:人类大脑每小时大约消耗20瓦能量,而据埃罗斯加鲁菲估算,AlphaGo内含的1920块中央处理器和280块图形处理器每小时的能耗达440千瓦,如果机器达到与人类水平相当的能力则所需能耗将超过各国能耗之和(每小时15万亿瓦)。㉗参见[美]皮埃罗·斯加鲁菲著:《智能的本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64个大问题》,任莉、张建宇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从立法技术层面来看,赋权给人工智能本身没有法律意义,实质上只是掩耳盗铃式的文字游戏。人工智能不具有独立意志,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具备承担责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主体身份无从获得。相比之下,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所以能被视为作者,法人作品之所以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就在于法人作品是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㉘《著作权法》第13条第3款。承认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步子迈得过于大,远离法理、逻辑和常识。从立法的实效来看,赋权给人工智能达不到预期的激励创作的立法目的。人工智能本身没有利益需求,不存在物质方面的刺激和精神方面的满足,赋权给人工智能不会对内容生成产生任何影响。著作权制度不能对人工智能本身提供任何激励,在赋权给人工智能的模式中,人工智能都只扮演招牌幌子和敲门砖的角色,用以完成正当性的说理,但这种曲线救国式的论证恰恰是多余的。
结 语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冲击,我们应当避免无视或过度恐慌的极端情绪,理性、积极应对由此而生的新问题。在一些研究者看来,通过逻辑和解释的方法剖析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法律保护问题时会出现有独创性但不能被认定为作品、由人工智能生成但无法明确归属的法律效果悖论,主张通过法律修辞的方式将人工智能“创作物”视为作品,赋权给人工智能所有者。㉙参见王文亮、王连合:《将法律作为修辞视野下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考察》,载《科技与法律》2017年第2期,第60-66页。实际上,上述法律效果悖论是在强调将“思想”“人格”作为作品的隐藏构成要件和遗忘“视为”这一拟制的立法技术之前提下才可能出现。独创性的判断,只考虑生成内容的表达本身,与创作过程中是否包含言之不清道之不明的“思想”“人格”无关。承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独创性和智力成果属性,并不等于赋权给人工智能本身,著作权制度所能激励的,只能是人类的行为。所以,从确保完整产业链形成的立场出发,本文主张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应赋权给人工智能的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