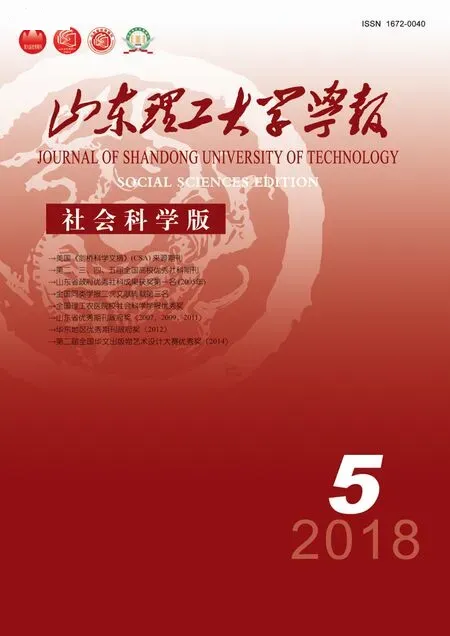民俗传播视阈下地方戏语言价值与特性探析
张晓明,李圣男
(1.山东理工大学 齐文化研究院,山东 淄博 255000;2.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民俗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广义来讲,民俗语言是记录民俗事象的语言。民俗事象范围十分广阔,大致分物质、精神、社会民俗事象三类,包括: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间信仰、民间科学技术、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语言、民间艺术、民间游戏娱乐等[1]5。狭义来讲,民俗语言是记录语言民俗的语言。语言民俗是指因语言而生成的民俗事象,主要是语言崇拜、禁忌以及谐音等约定俗成的民俗[1]16。一般认为语言民俗属于精神民俗,可归为三类:一是日常生活中的俗语:亲属称谓、社交称谓、人名、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俗成语、俗短语、方言词、流行语、招呼语、脏话、骂詈语等;二是特殊场合或仪式中的套语:咒语、吉祥语、禁忌语、委婉语、神谕、祷词、誓言、隐语(含暗语、黑话)等;还有一些具有民俗文化内涵的语音、语法、修辞等方面的语言现象[2]10。我们取广义的民俗语言说法,主要以鲁中地方小戏五音戏为例,探讨民俗学视阈下的地方戏语言价值与特性。
一、地方戏语言的民俗学价值
这体现在民俗资料价值与研究价值上。
(一)记录和保存民俗事象
地方戏语言记录和保存丰富大量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有的是戏曲情节内容中直接记录和描述的,更多的是作为故事情节开展及人物描写的次要内容被提及,或作为背景材料衍入故事情节而被间接提及,比如人名、地名、物产、服饰等。地方戏语言语料中记录民俗事象之丰富全面,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民俗资源宝库。借助戏曲戏剧这种文艺形式,这个宝库保存与传承下去,其巨大的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取鲁中地方小戏五音戏传统剧目20部20万字(马光舜主编《五音戏传统剧本精选集》,齐鲁书社2017年版),对其进行民俗事象测查与统计,发现:不计重复数,出现民俗事象近300项,涉及内容丰富繁杂。有饮食类的胡饼、糁子、小豆腐、莱州盐、乐陵枣,服饰类的马连坡草帽、蝴蝶梦鞋、江南官粉、苏州胭脂,婚俗类的喝冬瓜汤、三媒六证、送颜房、坐家女,丧葬类的顶瓦盆、送浆水、宽衣连衣,教育类的南学、黉门、上下论、戒尺、茶条,音乐类的《房四娘》《当年忙》《大四景》与迎宾乐、唱道情,游戏类的拔河、玩狗熊、变戏法、寻七、打瞎驴、放风筝、打秋千、猜谜,宗教信仰类的北极庙、奶奶庙、娘娘庙、关王庙、马王庙、女儿寺、圣人寺、二郎庙、狱神庙,还有多种节庆民俗和社交民俗。单是语言民俗,就有谚语60余条、歇后语50余条、诙谐玩笑10余条、咒骂与祈愿20余条、祭求祷告20余条、民间故事传说50余个。还有大量的重复民俗事象,比如:多部戏提到“南学”“南牢”,常见粗语“把×”“把×娘”,大量的方言方音语法现象,等等。若全部统计在内,五音戏语言语料中民俗事象出现频率之高,密度之大,令人震惊!毫无疑问,五音戏语言就是民俗语言。
(二)展现民俗语境
所谓民俗语境,是指民俗赖以生成和传承的环境以及赋予民俗以特殊意义的上下文关系,是民间文化的全面表述与集中重现。较早期的民俗研究把民俗语境限定在文本,侧重文本搜集、整理和分类,虽然也被称为田野调查,但与真正的民俗再现还存在较大距离,被称为“采花”式调查。近年来,民俗研究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3]6。民俗学经历了从传统的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事象研究向当代的语境研究、生活研究、整体(事件)研究的学术转型[4]18。地方戏植根于地域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民众用自己的方言世代传唱,艺术地表现他们自身的生活与感情,其间记录与展现的民俗资源,往往保留着自然、历史、生产生活方式的原生特征,保留着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特色与传统,承载着大量历史文化信息,是“活态”民俗语境的真实具体的再现。
五音戏流传于济南、淄博、滨州、潍坊等地,从戏词中可以看到这个地域的社会风情。比如:趣味盎然的节庆习俗(《王二姐思夫》)、风景名胜济南千佛山与大明湖(《王小赶脚》)、金陵苏州旅游玩乐(《双生赶船》《鹦哥记》)、赶赴京城科举考试(《彩楼记》《风筝记》《刘香莲》)、青楼与官场(《打面缸》)、神仙世界与人间冷暖(《劈山救母》)以及各地物资交流。既可以看到济南周边地区的地理特征、气候特征、水系特征等自然环境,也可以看到祖先崇拜、岁时节令、庆典祭祀、礼仪宗法的人文环境,甚至可以看出此区域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特点:政治文化上受京都与中原影响,经济贸易往来上则多倾向于江南地区的南京与苏杭。
(三)揭示文化特色
民俗语境能够折射出人们的思想与观念,其中生产与生活境况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帮助探讨民俗文化特色乃至整个地域文化特色。
五音戏代表作品是《王小赶脚》《拐磨子》《亲家婆顶嘴》,主要表现的是农业商镇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大背景仍是农业,但主人公多是生意人、读书人、富家子弟,物质生活比较富裕,享有受教育权,娱乐活动比较独特高级,文化交流便捷顺畅,性格自信幽默,直率达观。这种文化范型相对小众一些,并非典型的北方乡村文化,而更接近乡镇文化,与齐鲁地区其他剧种有所差别。这种文化范型反映某一特定阶层的情感与心理状况,形成特有的文化惯习与文化风格,决定地方戏的区域归属、族群识别、群体认同方面的特色,也是地方戏戏曲本质特征的表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齐鲁地方戏,尤其中部与东部各剧种,其剧目多是共有相通的,但上述三个小戏,尤其是《拐磨子》和《亲家婆顶嘴》,是五音戏代表剧目,而不是其他剧种的代表剧目。
这个特色在语言民俗中也能得到印证。五音戏谚语60余条,有广为熟知的“生米做成熟饭”“打着灯笼没处寻”“闺女是娘的连心肉”“县官不如现管”等,也有地域特色鲜明的“没有红枣照样蒸糕”“滚锅就怕凉水点,前窝小孩怕后娘”“为人自在花下死,死在阴曹也不冤”“醋调萝卜蜜调蒜,酸甜苦辣尽着闻”等。但60余条谚语只有2条与农谚沾点边:“桃树园梨树根,十里闻见九里亲”“生锈剪子难张口,抽穗的黍秸头难抬”。这与其他地方戏剧种语言中农谚内容与数量比较,也反映出五音戏乡镇文化特色。
二、地方戏民俗语言传播方式
民俗传播可以通过语言传播,也可以通过实物、实践与体验等其他方式传播,民俗形成的过程就是传播的过程,是民俗被接受和认同的过程[5]7。地方戏的上演本身就是民俗活动,语言传播既是这项民俗活动的组成内容,也是这项民俗活动的开展途径,语言传播方式亦如此。
(一)人际传承的传统性
民俗传播可以分为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传统地方戏的上演与观看属于人际传播,有共时的群体传播,也有历时的代际传播。与一般的信息传播和大众传播不同,在人际传播过程中,传播双方共同承担传播者角色,共同参与、集体接受或改变剧情和人物。常任侠曾谈到民间皮影戏是农民农隙时集资演出,演戏艺人多半就是农民自己:“观众和演员,有着共同的情感和兴趣,共同的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希求和愿望,戏的情节与观众的感情联系在一起,他们到夜间聚集在灯影前,可以连续演出数夜不倦,欣赏着戏中的故事发展。”[6]535五音戏演出情境与此基本相同,多通过民间集资方式,选取各种节庆或宗庙活动场所进行,在一些人生礼仪中也常常出现。演出或祭祀神明祈福还愿,或庆贺娱乐,增添欢乐喜庆。情节已广为熟悉和接受,观众也有足够的时间、以缓慢的步调和充分的耐心,逐渐完成传统剧目或长或短的艺术欣赏。虽然是即时的现场演出,但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因为娱乐活动相对缺乏,观众群体和数量都受到限制,反而呈现出相对集中和稳定的状态。剧目题材与内容稳定熟悉,易于得到长久与持续的关注。
五音戏表演情感真挚,爱憎分明,抒情直白。唱词采用浅显诗文形式,对白多用方言土语,雅俗兼具,清新活泼,情趣盎然,德法礼教色彩和娱乐喜庆气氛贯穿隐藏在浓郁的北方乡镇生活气息中。在共同参与中,不仅抒发排遣个体情感,而且获得群体认同与文化归属,这就是黑格尔指出的:“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中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意在艺术里感觉到一切都是亲近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生活的。”[7]348这种朴质清新、欢娱喜乐的民间艺术风格,满足观众的情感和审美需求,体现民间的诗性与智慧,反映淳朴质爽的文化观念与中庸悦乐的审美精神,是一种典型的鲁中民间文化品格。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地方戏展演方式,深受民众喜爱,是民俗与民俗语言传承特性的表现,也是传承特性的有力保障。
(二)精神观念的传承性
参与性极强的传播方式,必然带来认同感极强的精神观念与艺术风格。山东地方戏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崇尚顺应天意人道,讲究宗法和顺与等级秩序,重视礼法乡约与传承教化,赞扬勤劳善良、忠义贞烈、贤孝淑德、隐忍顺从。作为戏曲文艺,地方戏需要展现的是戏剧化的甚至非常激烈的矛盾冲突,时代背景与故事情节的开展,往往选取基本价值观念受到挑战或者它们自身发生冲突的时间节点。
地方戏对于矛盾冲突的处理是自然的,但也充满教化感。五音戏中处理方式一般是三种。一是隐忍修炼。像《松林会》庞三娘,虽然遭遇来自婆婆和丈夫的误解与不公待遇,身处困境仍委曲求全,顺从退让,贤良淑德感天动地。二是正面反抗。像《彩楼记》刘瑞莲,面对嫌贫爱富的父亲,毅然决然苦守寒窑,最终守得夫君吕蒙正高中荣归,美满团圆。这种勇敢反抗与贤良忠贞完美结合,亦为感天动地。三是勇于赴死。像《兰桥记》中兰瑞莲与魏魁元,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追求婚恋不得,双双赴死。折子戏《大卷帘》尚未到最终赴死环节,但山伯与英台之间互为试探,已表现出为婚恋自由勇于赴死的决心。赴死过程中,人们最终感受到的不是悲痛,而是解脱的愉悦与坚韧忠贞的升华。
魏魁元:(唱)咱二人好比风流鬼,
兰瑞莲:(唱)水波以上作乐玩。
……
魏魁元:(诗)魏魁元兰瑞莲,
兰瑞莲:金童玉女降临凡。
魏魁元:待要夫妻重相会,
兰瑞莲:转化双生来赶船。——《兰桥记》
山东地方戏有明显的道德教化作用,与封建社会主流思想观念完全一致。重大冲突面前,反抗是最直接选择,修炼隐忍是间接反抗,反抗不得则相信命运安排、缘分因由、前世今生,借助宗教的玄幻来摆脱与超越现实痛苦,在情、礼、理、俗的对立冲突中,寻求最终的精神平衡与升华解脱。情节发展水到渠成,入情入理,有广泛深厚的民间基础,为广大民众接受和仿效。这里既有道教的报恩、贵生,也有佛教的因果、轮回、报应,民间宗教、民间信仰与民俗体系混合穿插在一起,与日常民生紧密结合,成功消弭宗教意味的神秘感,完美融合异质文化冲击,呈现和谐稳定的、自觉顺从的文化心理。这种民间社会特有的、普世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是中国社会最基础也最真实的精神观念。作为民俗的内核,它以一种集体潜意识方式,内化到人物言行中,渗透到剧情发展中,凝结着共同的情感与追求,演变为群体共有共享的民风民俗的重要内容,广泛传播出去,代代传承下去。
美国人类学家维特·巴诺指出:“如果一种民俗的内容同当前社会盛行的价值与态度偏离太远,它将会被遗忘,而不会继续流传下来。既然某一民俗能够流传至今,则其价值观必然有与现代的价值观相通之处。”[8]124现在反观地方戏的思想观念,除去受制于封建礼教压制人性的内容,勇于追求幸福和自由,坚韧不拔,和善忠贞,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提倡和尊崇的。
三、地方戏民俗语言特性
这个问题一般在民间文学与口头文学研究领域讨论,主要针对方言特色、模式化、重复性特色进行概括性研究[9]86-92。
(一)题材内容的固定性
地方戏多取材于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与历史故事。齐鲁中部东部地方戏比较固定的传统剧目是“四大京”和“八大记”,与以英雄戏和包公戏占绝对优势的山东梆子戏等西部戏有明显不同[10]38。“四大京”为《东京》《西京》《南京》《北京》,“八大记”为《罗衫记》《玉杯记》《绣鞋记》《火龙记》《金簪记》《钥匙记》《风筝记》《丝兰记》。这些剧目应用场合也是基本固定的,比如庆寿戏、庆生戏、堂会戏、婚庆戏、节庆戏等。
这些剧目在不同剧种里唱腔唱词各异,但是题材内容与故事情节大致相同,如:嫌贫爱富,背信弃义,或撕毁婚约(《风筝记》),或抛妻弃子(《裴秀英寻夫》),或杀人越货(《刘香莲》),最终遭受严惩;亦多有大户小姐忠于爱情,或勇敢资助落魄小生进京赶考(《鹦哥记》),或坚贞守候夫君得中功名衣锦返乡(《彩楼记》),或追斥鞭笞忘恩负义之人(《排环记》);亦有因为年龄相差过大或相貌丑俊悬殊丑陋造成不般配婚姻,后来巧妙扭转(《双生赶船》《鹦哥记》);有青年男女相恋、夫妻恩爱、矢志不渝(《松林会》《兰桥记》《双下山》《大卷帘》《王婆说媒》);有官府黑暗、欺压百姓、百姓机智反抗(《打面缸》)。五音戏是地方小戏,多取“四大京”中一折或两折,如《东京》中《赵美蓉观灯》和《西京》中《裴秀英寻夫》,“八大记”中有《风筝记》和《罗衫记》,“梁祝”传说中有《双下山》和《大卷帘》。五音戏中独具特色的是《王小赶脚》《拐磨子》和《亲家婆顶嘴》等,描写日常百姓家长里短,很有代表性。
五音戏虽为地方小戏,但剧目丰富,表现手法多样,长于描述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善于塑造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小戏《王小赶脚》《拐磨子》,还是十四场的《刘香莲》,无论取材于家长里短的《亲家婆顶嘴》,还是家国纷争的《劈山救母》《刘香莲》,都会塑造出重情义讲道义、乐天勇敢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的展开有强烈的套路倾向,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脸谱化嫌疑,却极易引发民众热情,收到广泛传唱的艺术效果。民俗文学把这称为文化“意境”“符号”“象征”“隐喻”等,解释其在民俗文化中的价值。
(二)语言表达的程式化
戏曲行里“套路”这个词,不仅是指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设定的模式化,也指表演手段的模式化,表现为一整套有规律的唱腔、动作、服饰。每个剧种都有各自的套路。我们这里只说语言表述方面的“套路”,称之为语言模式的程式化。这个程式化可以指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的区域方言特色,更主要的是指表达的程式化。五音戏地方小戏,其语言程式化特征亦已鲜明突出。
比如众所周知的语言衔接方式,除去上场独白自介,还大量运用“尊声”“叫声”“骂声”“听”“言”来开腔。
二姑娘:(唱)叫声王小别翻脸,我是和你闹着玩。——《王小赶脚》
兰瑞莲:(唱)兰瑞莲好心焦,骂声丈夫你听着。——《兰桥记》
冯秀:(唱)走上前来双膝跪,过往神灵你听言。——《双生赶船》
祝英台:(唱)磕罢头来抬身起,尊声大哥你听着。——《双下山》
又如情感心理表达简单直白,多用“哭”“泪”“说声苦”“惊动”“恼”“怒”“气”,或与“听言”“骂声”等合用。
祝英台:(唱)说声苦来泪如梭,梁大哥不来你想死我。——《大卷帘》
刘瑞莲:(唱)说声苦,泪悲啼,从今天离相府永不回去。——《彩楼记》
兰瑞莲:(唱)在绣房惊动了兰瑞莲。——《兰桥记》
祝英台:(唱)忽听门外有人声,书房惊动祝九红。——《双下山》
周腊梅:(唱)惊动腊梅女娥皇。——《打面缸》
盖月英:(唱)林内惊动女婵娟。——《王婆说媒》
乡里妈妈:(唱)听一言,怒气发,亲家婆你这个母夜叉。——《亲家婆顶嘴》
卢凤英:(唱)卢凤英怒气冲,骂声狂徒你不是人。——《赵美蓉观灯》
张文秀:(唱)听一言来了毕赛金,气得学生炸了心。——《风筝记》
程式化特征是语言模式稳定并固定化表现,是民俗语言超越具体情境,成为人所共享的耳熟能详的民俗仪式的重要过程和环节,也是民俗和民俗语言被大众接受、传播和传承的形式体现和保障。程式化内容与程度是观察民俗与民俗文化的重要指标。
五音戏中相貌程式值得关注。比如女性容貌描述多用白描手法,描述简洁,侧面烘托。男性称述女性相貌多只写眉目发肤,且多见以感想与评价代替描写。只有女性自述相貌会稍微详细些。对于男性相貌,更多是直接评价俊丑,不做描写。
魏魁元:(唱)头上的青丝如墨染,红绒丝绳末根缠。江南官粉净了面,苏州胭脂点唇间。——《兰桥记》
吕蒙正:(唱)眉清目秀多好看,好似月里嫦娥出广寒。为人若得小姐配,也不愧阳世三间过几年。——《彩楼记》
吴俊琪:(唱)好比昔日莺莺女,容颜长的赛天仙。为人要得此人配,恩恩爱爱过百年。——《王婆说媒》
张文秀:(唱)黑腾腾乌云梳鬓,二目闪闪有精神。——《风筝记》
对男性相貌一般不做描写,服饰描述简单且高度程式化,常用“俊巾”“蓝衫(兰衫)”。
兰瑞莲:(唱)有顶俊巾头上戴,可体兰衫穿身间。——《兰桥记》
祝英台:(唱)头挽抓髻外戴巾,身穿兰衫不扎裙。——《大卷帘》
赵美蓉:(唱)插花俊巾双飘带,可体的兰衫穿身中。——《赵美蓉观灯》
吴俊琪:(诗)头戴俊巾脑后飘,身穿兰衫腰系绦。——《王婆说媒》
宫舜英:(唱)插花俊巾头上戴,可体兰衫穿身中。——《排环记》
我们认为这反映了民俗文化的特点:男性主体观念、男性观众群、女性品评赏鉴及其角度等,是个有趣的民俗语言现象。
(三)民俗语汇的群体性
戏曲语汇是一种专门语汇,戏曲辞典多各有侧重进行整理。不同剧种的语汇显示出不同的群体特征,从某一层面与角度揭示民俗文化时代性、地域性、阶层性。
有些民俗词语在五音戏里多次出现,属于高频词。教育类民俗高频词有“南学”“寒窗”“赶考”“功名”等。“南学”出现40次,除去《安安送米》和《劈山救母》中作为主要情节地点,其他都是背景材料。这反映出民间对于教育的重视,更反映出对于通过科举考试当官求仕改变命运的渴求。女性相貌描写高频词,如:“樱桃口”6次,“金莲”5次,“描花腕”4次,“杨柳腰”2次。因此有人说戏曲呈现的是富家小姐的生活与精神面貌,与故事男性主人公多为蓝衫书生相呼应。其实,这里不仅仅反映贫富阶层,还反映生活场景的选取,回避了劳作场景。这种回避是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观赏原因与需求所决定的,也反映了观赏人群的男性主体观念倾向。
有些民俗词不是五音戏的高频词,但是属于富有代表性的民俗现象,提供出有价值的信息。比如《房四娘》:
李妻:(唱)黄河南,十三乡,出了个贤女房四娘。十一十二学弹唱,十四五上进了机房。——《拐磨子》
这里提到一首民间歌谣,又称《房四姐》,亦记作《方四姐》,来源于同名民间故事,讲的是贤良能干的房四娘(或称四姐)受婆家虐待致死而还魂报仇的事。长歌《房四姐》主要流行于江苏,山东还是多称《房四娘》。开头唱“黄河南十三乡”,可见此歌衍生于宋代黄河决口之后。聊斋俚曲中也有《房四娘》,说明鲁中地区颇为流行[11]110-119。
又如《当年忙》:
鹦哥:(唱)说个姑娘本姓黄,一心要嫁刘二逛荡。正月里提媒二月里娶,三月里添了个小儿郎。四月小五月大,六月里小孩会叫娘。七月里南学把书念,八月里进京赶考场。九月里从把状元中,十月里封官做宰相。十一月里告了老,腊月里得病发了丧。明公要问什么段,这段就叫当年忙。——《鹦哥记》
《当年忙》在五音戏《鹦哥记》里出现,也出现在四根弦《大井台》和柳琴戏《珍珠汗衫》。《当年忙》还作为民歌先后收入《寿光民间文学集成》第一集、《临淄民间文学集成》第一册、《清河民间文学集成》《禹王亭下的传说·禹城县民间文学选编》《山东民间文学系列丛书·淄博歌谣卷》《山东民间文化艺术》《大沟民俗风情录》《琅琊采撷:胶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线索暨实物登记汇编》;作为传统小段,存目收入《中国节日志·胡集书会》;作为鲁中秧歌词谱,收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这说明《当年忙》是个有代表性的民间歌谣,山东流行甚广。
四、结语
我们从民俗学视阈分析地方戏语言价值与特性,在探究地方戏语言本质特点的同时,也希望探索民俗语言的价值意义及其传承方式、途径。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传统地方戏产生于农耕文明社会背景下,并与之血肉相连,而当下社会文明中,知识教养、传播媒介、欣赏方式、审美观念的演变,使得传统地方戏逐渐与现实民俗语境相脱离[12]381-382。表面看来,二者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一般称前者为农耕时代与乡土文化、乡村文化,称后者为后工业时代与消费休闲文化。实质上,传统民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与当下社会形态、文化心理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一方面,在深层次上,或者说潜意识中,传统形态不仅与当今形态密切相关,可能还决定未来形态;另一方面,差别越大的文化形态,越容易引起现代社会的关注,越容易赢得展示与保护的平台或空间。当然,这些愿景的实现,更多倚仗对民俗纯洁性、真实性、独特性乃至现代性特征的发掘与保护,语言民俗与民俗语言亦当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