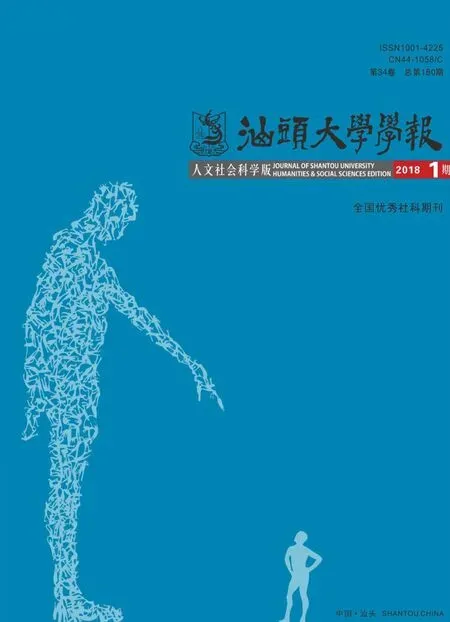着眼于文艺学生态建设的文艺学批评实践
——读郑惠生先生《文艺学批评实践》有感
易崇辉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一
郑惠生先生的《文艺学批评实践》是一本颇为特别的书,也是一项颇为特别的“批评实验”。其特别之处在于,作者批评实践的对象,与一般的文艺批评的对象明显不同,甚至可以感觉到,作者在刻意与传统的文艺批评的对象保持距离。一般的文艺批评对象,是作家、作品抑或文艺思潮等,而郑惠生先生著作的聚焦点,却是作家、作品、文艺思潮以外的方方面面——尽管也与文艺学相关。具体而言,《文艺学批评实践》的第一章“文艺批评的批评”、第二章“文艺理论的批评”、第三章“文学史的批评”,都可算作是“广义上的文艺批评”的批评,这跟贯常的文艺批评的对象隔着一层;第四章“文艺学课题、标准和期刊的批评”及第五章“文艺学学术事件的批评”当是对文艺批评的条件、环境的批评,这跟我们理解的文艺批评的对象隔着二层;而第六章“高校文艺学的批评”,则跟传统的文艺批评的对象隔得更远些。掩卷沉思,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文艺学批评实践》一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文艺学学科的“巡视”——对文艺批评的巡视,对文艺批评环境、条件的巡视,对文艺学学科从业人员素质及其培养的巡视,一言以蔽之,是对当下文艺学生态的一种巡视。
着眼于文艺学及其生态的批评,与传统的文艺批评当然是很不一样的:传统的文艺批评对象——作家、作品、思潮等,感性而单一;着眼于文艺学学科巡视或生态建设的批评——对象为整个文艺学学科的诸方面、诸问题,即文艺批评的批评、文艺批评的条件、环境、队伍素质与培养等等,则繁复得多。郑惠生先生将前者称之为“文艺批评”,后者,也是作者倡导并倾力而为的,则称之为“文艺学批评”。《文艺学批评实践》一书中践行的不是“文艺批评”,而是“文艺学批评”,怪不得全书给人一种全新而特别的感觉。
“文艺学批评”,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倡导,还是作为一种批评实践,都是全新的。然而,任何新的理论的提出和倡导,都是为了应对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至少也是为了应对和解决新问题的努力。“文艺学批评”理论的提出和批评实践,不是作者一时心血来潮,异想天开,也不是作者趋时赶潮,花样翻新;理论的提出和批评的背后,隐含着作者对文艺学生态环境的隐忧和责任。
二
在柏拉图的《斐德诺篇》中有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奥林匹斯的诸神每天驾着马车驶向苍穹的顶端,而人的灵魂尾随其后。诸天之外是存在的居所,只有到那里,人的灵魂才能观照到具有永恒秩序的存在之物。可惜,尾随诸神之后的人的灵魂对永恒存在的观照只有那么短暂的一瞬,此后他们就坠落在大地上而同真理分离,仅只保留着对这分离的真理的模糊的记忆。人的灵魂中曾与真实的存在有过照面,但只是片刻拥有这些事物的景象,时间短暂,记忆模糊;有些灵魂在落到地面上以后还沾染了尘世的罪恶,忘掉了上界的辉煌景象;更有人每逢见到上界事物在人界的摹本,就惊喜若狂而不能自制,将摹本视作天上的正本,于是,人世间大量堆陈的,自然是错误、悖谬、偏执、愚昧。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讨论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希腊的情形,倘若他们活到现在,他一定会惊异地发现,人的灵魂在从天上坠落在大地上后,在距他们二千多年后再一次发生了坠落——又从地上坠落到欲望的世界,一个了无理性烛照的黑暗领地。对于苏格拉底而言,或者说对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而言,灵魂是不朽的;而经再次坠落而堕入欲望世界的人却认为,人无须再回忆上天的永恒,永恒天庭中的“存在”并不存在,甚至人的灵魂也是虚幻的。坠入感性欲望世界的芸芸众生认为,人即人的肉身,人生的意义即是肉身的充实。在肉身枯朽之前,尽可能使它充实、满足、膨胀,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与目标。而能使人欲望不断得到满足的,是金钱。于是,欲望与金钱携手,恣意狂奔。社会拼经济,个人为赚钱。跟着感觉走,玩的就是心跳,我是流氓我怕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再是目的,一切都是获取金钱的手段——不是有一种资源称之为“人力资源”吗?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金钱是目的,其它一切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学界也未能幸免,不仅学术环境、学术条件如课题、期刊等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弄潮,学术批评在日渐浮躁的学术氛围者中也免不了在随波逐流了,文艺学界乱象丛生,到处裸露出金黄色。
文艺学的学术生态犹如同时期的自然生态一样,迅速恶化。文艺学生态失衡之深之广,甚至更甚于同时期的自然生态。一个没有灵魂的文艺学,一个视灵魂为虚幻的文艺学,或者用流行的话语说,只有眼前的苟且,不要诗和远方的文艺学,文艺学何以成为文艺学?像很多学者一样,郑惠生先生知觉到文艺学生态失衡的严重;与很多批评者不同的是,郑惠生先生积极开始了他的巡视、批评和批判,以期用他的理性反省和反思,整治、改善、建设文艺学的生态环境。正因为是以建设、整治和改善为目的,所以二十多年来作者秉持的始终是一种严肃而冷静的态度,《文艺学批评实践》始终也是一种纯学术式的批评与反省——一种自觉严谨的慎思明辨,一种冷静深沉的理性思考。至于辩驳文字极难避免的一些现象,如吹毛求疵地挑错,上纲上线地指责他人,戴帽子、打棍子——用作者自己的话说,“非学术式”的批评——“笼统式、自顾式、偏执式、臆想式、吹捧式、推销式、捏造式、上纲式、打压式、谤毁式、谩骂式”,则与《文艺学批评实践》一书无缘。
再说一点题外话:我一直认为人性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感性欲望如饮食男女自然是人性的一部分,理性也理所当然地是人性的一部分,神性也应该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不是都关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类问题吗?不是一直都在追问死后的世界吗?在人类历史上,人类先是用神性压制理性与感性,后来是用理性来排斥神性与感性,现如今,感性欲望又假人性之名而君临神性与理性了。神性、理性、感性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不论用人性的哪一部分压制人性的另外两个组成部分,不仅仅是将人性简单化、单数化,更是对人性的割裂和摧残,也都会导致学术生态或文艺学生态的失衡。在感性欲望君临天下的今天,金钱与欲望致使文艺学生态失衡。《文艺学批评实践》秉持理性的立场与态度,不随波逐流,这不仅是在维护文艺学的生态与尊严,更是在维护人性的尊严与完整。
三
《文艺学批评实践》都是辩驳、批评的文字,但就整个“文艺学批评”理论而言,其学术建构,也即是说,“立”,也是应有的题旨。
经常听闻这样的感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学界非常热闹,西方数百年的各种思潮、理论走马灯地在中国上演了一遍。然潮起潮落之后,沙滩上似乎什么也没留下。确实,仅就文艺学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尼采、弗罗伊德、萨特、海德格尔、阿多诺、弗罗姆、维特根斯担、福柯、哈贝马斯、利奥塔、德里达、德勒兹、杰姆逊、罗蒂、伊格尔顿等等都被引进到了中国,各式主义如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依次登场,各种文学流派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黑色幽默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垮掉的一代都被推崇和摹仿,各种文艺批评方法如精神分析、直觉主义、符号论、俄国形式主义、语义学和新批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都被中国文艺学界所关注。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的文艺学界显得异常繁荣、热闹。然而,在这热闹、繁荣的背后,学界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冷静的思考:西方的理论、思想、思潮是在西方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他们意欲描述、解决的是西方的社会和西方的社会问题。我们跟在西方的后面,自愿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接触和学习的也是西方的思潮和理论,思考和研究的也是西方的问题。我们缘于中国自己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现代理论在哪里?我们解决中国现当社会历史问题的思想在哪里?当代中国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方法在哪里?简言之,当代中国自己的学术建构在哪里?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社会现实,始终缺乏足够的关注,也没有足够的学术信心,更没有建立起自己有效的学术生长机制。诚然,仅就文艺学而论,近四十年来我们的文艺批评与研究有相当的实绩,也有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思想,但我们缺乏疏理,没有沉淀,因而也就没有了真正的学术积累和生长,至于一些可供学术累积和增长的思想,却几乎都淹没在了大量对西学的追逐之中。倘若在文艺学批评中,我们在分析、反省、批判的同时,也分学科进行整理,披沙炼金,找出原创性的思考和思想,疏理出学术谱系和理路,分析其出现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向,则在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的背景下,建立当代中国自己的思想与学术,建构当下中国自己的文艺学体系,则可期可盼。
当然,学术成果浩于烟海,这种基于学术建构和开拓的文艺学批评非短时间可以完成,即便在长时间里,靠一个人或一群人也难以完成。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文艺学批评”学科建立起来了,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应该有理由期待。
郑惠生先生的《文艺学批评实践》,致力于打造一个全新的学科,整治和维护文艺学领域的学术生态,我赞赏他的努力。郭德茂教授说他读过郑惠生先生的著作后的印象是:无边的荒原上,远方有一束光,一个学者从青年到中年,一直踉跄而执着地朝那束光走去……。我眼前出现的画面已然是:这位孤寂的学者踽踽独行中将洒漏在他身上的光亮采撷、聚集起来,然后回过头来,悉心撒播在他所挚爱的文艺学这片园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