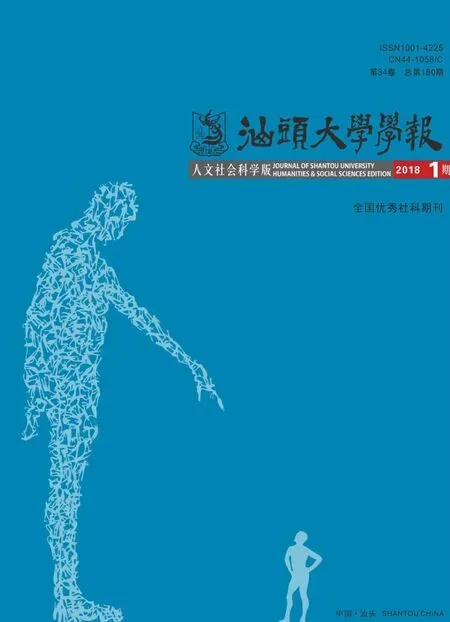文艺学批评的分寸与常道
冯 尚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惠生君《文艺学批评实践》一书的出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说的原因有二:一是这部著作展示了文艺学批评的科学态度,一是它所体现的批评著作本身品行的纯度。语文专业的学生大多知道“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难度几何,至于稍后更名“文艺学导论”,丝毫没有减少这门学问的难度,虽然乍看起来其与具体的文学、艺术的作品更为亲近,缓和了这门学问的抽象性、系统性;加之“文学理论”(或“文艺学导论”)这门课程在语文专业享有的特殊地位,它格外受到专业内外的关注。伴随教育现代化、文学自主性时期的到来,“文学理论”(或“文艺学导论”)这门曾经高严的知识受到的批评最烈、质疑度最深,有关文学本质的争讼就是其中重要话题之一。
即使到了2001年,有学者在其专业文章中重复文学本质的“某种虚幻性”的断语,文学理论界的人们大都似乎已经默认了的一个常识,惠生君却大不以为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这个批评的路径并非“以毒攻毒”,以彰显批判的豪情,而是唤起人们对认知常识的清明意识,“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学科是否能够建立起来,首先取决于研究对象是否能够确定,至于研究对象能否确定,那就要看该对象能否与其他的事物区别开来并具有被系统研究的价值。尽管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区别是多方面且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区别却是最深层次的区别——即事物之间的本质区别。由此可见,探究被研究的事物的本质,既是学科建立的基础,也是学科建立以后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着的重要问题”(见该书页116)。惠生君的“常识”是学理的常识,而非貌似常识的动人说辞,学理的常识是人们从事学术工作所应该遵循的基本道理,而非流行业界前沿的“大词”“丽句”,惠生君在此所特别提及的这样的常识,往往为急于开疆拓土的年轻学子所轻忽,由此造成他们呼号而起的新学高论,仅止于耸动的词语,对学理、专业问题几无触及。
学理常识的习得,是现代知识人问学求道的基本素养,倘没有这样的修行,在涉及专业问题的争论时,往往走向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强词夺理的歧途。惠生君在这部《文艺学批评实践》中所恪守的学理常识,再通俗点说就是科学的精神,而这一点在一向执著于虚构、激情、创新义理为能事的文艺学行当,显得十分突出,也许用“刺眼”一词更为准确。文学以激情、创新为天职,而文艺学的研究与此相呼应,求新求异乐此不疲,其间研究者所应该具有的起码的科学精神俨然成了文艺学创新的羁绊、甚至对手。因此,人们看到的所谓新锐学者只是耽于文字表达的激烈,而少见甚至不见服人道理的呈现、论证过程。这里有个例子,2003年,有学者提出“经典文学”为“后文学”消解的批评狂欢时,断言既有的文学史分期方法和成史标准统统过时。对此,惠生君客观地提出,“即便‘经论’与‘后论’的分期方法和成史标准是可用的,那也并不等于已有的其他方法和标准都不能用,因为无论是文学史还是文学理论,其‘框架’是多样也可以是多样的。进而言之,黄浩教授对以往各种‘分期方法和成史标准’的一概否定远非基于‘科学精神’,而是出于张扬‘经论’和‘后论’的‘高涨的感情’”(见该书页 205)。
文艺学,是文学学科中要求更多批判勇气、观念创新的一门学问,但这样的批判、创新更需要建立在对既有文艺现象的客观把握、对学理常识的持之以恒的坚持,更需要对基本的学术规范的遵循。惠生君的《文艺学批评实践》着意讨论的也正是这样的学术功夫的修习之法。在该书第二章“文艺理论的批评”栏目下,著者特别提示,“‘科学性’是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灵魂。我们既不能墨守成规,但又无法‘在一天之内把罗马建成’。在批判既有文艺理论成果时,应该遵循科学规律,重实证、讲逻辑”。说法朴实,是问学者的常谈,却也是行家里手的“诛心”之论,更是文艺学界能否获得长进的第一行诫。
文艺学批评,是一种专业的批评,而一种专业的批评,需要两项基本的条件,一是对该专业的基本概念系统及其运行机能的熟稔,还有一项是对其学术前沿的敏感。而后一项是批评锐利程度的指标所在,往往也是学术新军用力过猛之处,甚至于虚张声势、故作高深,罔顾基本概念、学理也在所不惜。如果读者认真浏览过惠生君的《文艺学批评实践》一书,不会不注意到,文艺学专业人士口中念念有词的现代哲学经典,诸如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福柯的巨制名篇,甚至康德、黑格尔的美学专书,不论是在这部著作具体章节的引文中,还是在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中,都付之阙如。即使那些做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在有关、多少有关、甚至毫无关系的讨论中,都会拿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及其著作来为自己的说法壮胆,来装点自己专业的前沿景观和理据深度,而这本相关、相近于现代哲学的文艺学专书,却干脆悉数省却了诸如此类的“前沿”、“深度”。这一异乎常例的情况,该会让人吃惊不小。细细想来,即使仅仅这一点,这本专书的出版就值得认真推荐给关心文学问题的读者,因为这本书不论是就提出问题的具体性,还是就讨论问题的专业性,引述文献的丰赡性,都显出著者思考的深入、说理的严谨细密。但著者始终保持着文章可读性的纯度,决不故弄玄虚,少有言不及义的痴话、不知所云的新词出现在字里行间。不妨说得远些,一定意义上,这样的论文、著述方式,连接上了民国学者常有的朴茂学风:就事论事、问题为上,而游离出名人先行、哲学指导的现行研究、著述模式的潮流。
不用新学名词壮胆、不以新军傲气示人,这是因为著者有自己的常道打底,这个常道说来寻常,也就是读书作文者常常念叨的“独立态度”,不过,我还是更愿意用“中立立场”这一术语来表达之。独立,听起来多少有些故作姿态的味道在,虽然现代汉语更常用的是独立云云。中立,就是不依左右、不靠先后,更不自以为是,而是让自己置身事中,对诸多因素细细打量之后,择其相对公正的地方,把自己用功找出的道理表而出之,真正促使当事诸方明晓事有常理、世存中道的不磨明光。这一点在有关汪、王争执事件的批评方面有惊人表现(分别见该书页 302、页 329)。
曾经或者现在依然流行的名人、名刊、名著,分别在惠生君的《文艺学批评实践》著作里受到点名批评。这与其说是研究者的一种胆气,不如说是一种读书人的平常心更为恰切。批评的对象是否名著、名刊、名人,都不应该是批评考量所在,批评仅仅在于求真、认理,非关其他。行文至此,眼前又浮现出当年在江城桂子山求学时的一片场景。仲秋某时,穆如清风,三号楼头,一位讲魏晋文学的老先生,把细腻的腻的“肉”字旁,误写成了“糸”字旁,与我们一起听课的长者石声淮老师,即时支着拐杖走向台前,去掉“糸”,换上“肉”。全堂无声,持续了老长一阵时间都没有一点动静,直到石老师的拐杖触动地板的声音消失在堂外走廊尽头。师长的如此一字之订,也该有求真认理的奥义在焉。毕竟,此时的石老师,已经不需要制造哪怕是些微的响声,再来为年迈的自己添写荣名了。也许当日惠生君有幸在座?
说的好像都是点赞的话,其实求全之责也不妨说一个,就是希望该书将来再版时,编辑体例上是否可以稍作调整。现在“参考书目”的六类分别,应该是照应于“目录”的六章所设,但眼下两者各自的六个标题却是自行其是,“目录”的六个标题依次是:文艺批评的批评,文艺理论的批评,文艺史的批评,文艺学课题、标准和期刊的批评,文艺学学术事件的批评,高校文艺学的批评;而“参考书目”的六个标题依次是:文艺批评,文艺史,文艺理论和美学,哲学和文化,科学与道德规范,高等教育与科研。这恐怕不是“参考书目”原来所拟设六个标题的目的吧。但愿这只是我的个人偏向:每一本著作后面所附的参考书目,越是具体地指向正文的每一章节,也就越是增加读者检索文献时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