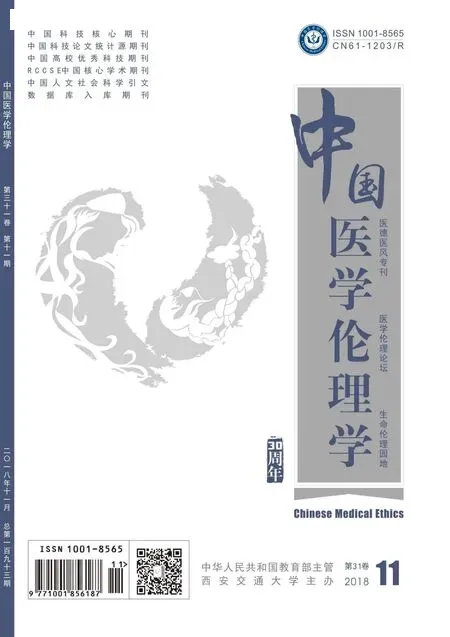儿科人群临床研究中“同意”的伦理探讨及对策*
王晓敏,虢 毅,袁秀洪,阳国平,邓 昊
(1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临床药理中心,湖南 长沙 410013,xiaominwangcsu@163.com;2中南大学信息安全与大数据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13;3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临床心理科,湖南 长沙 410013;4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医学实验中心,湖南 长沙 410013)
目前儿科用药主要是依据成人用药的酌情减量。然而,适合儿童剂型和剂量的药品短缺已成为影响我国儿童身心健康的重大问题,美国和欧盟通过儿科用药立法推动儿科临床试验和更适合儿童的药物研发[1]。我国各级政府也大力鼓励儿科用药的创新和研发。儿科人群临床研究中,“Assent”(儿童/未成年人同意)是重要的伦理和法律要求。尽管很多声明强调儿童/未成年人的自主权,但儿童/未成年人天然的脆弱性及不断成长变化的生理特点,使同意变得异常复杂,无法使其具有自主意识的同意转化为知情同意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儿科临床研究的发展。一般情况下,几乎所有文献和法规都要求,儿科临床研究除获得父母的知情同意之外,还应额外得到儿童/未成年人的同意。但是,目前有关儿童同意细节的指导方针存在很大差异[2],在儿童同意概念和操作程序上,国际上尚未形成共识。笔者拟就儿科临床研究中存在的“同意”概念的不同理解,同意能力和程序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希望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促进儿科人群临床研究的健康发展。
1 “Assent”的概念辨析及其伦理基础
虽然很多人强调“同意”的重要性,但是对“同意”的概念及其基本理由缺乏详细阐释。一般认为同意来源于知情同意,是建立在尊重自主和不伤害基础上的。《纽伦堡法典》指出,任何研究的自愿知情同意的获得是必要的[3]。这意味着未成年人、精神障碍人士和无意识的不能合法同意的人除外。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由于儿科人群无法给出同意的意见,涉及儿童的临床研究可能无法合乎伦理地实施。《赫尔辛基宣言》(1964年)规定,任何潜在受试者,如果没有能力给予知情同意,应获得其法定代表的同意[4]。目前,这是各国政府和医学协会公认的规范。同意(Assent)概念最早出现于1977年美国国家委员会(US National Commission)的一份生物医学研究和行为研究的保护人类受试者的报告中[5],而直到2000年第五版的《赫尔辛基宣言》才将其引入[6]。我国《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规定:“儿童作为受试者,必须征得其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当儿童能做出同意参加研究的决定时,还必须征得其本人同意。[7]”儿童同意降低了儿童被剥削的风险,也体现了其生长发育动态变化的生理特点。
医学伦理规范中,Assent(同意)是一个新生的术语。在临床研究中招募儿科人群受试者时,就不伤害原则而言,同意应被视为一种在伦理上恰当的方式。尽管成年人的Consent(同意)有明确的定义和操作程序,但是儿童的Assent(同意)是复杂的。全球各国有不同的标准,对于儿童同意的操作和架构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有时还与父母的同意相混淆。很多情况下,Assent和Consent都被理解为同意,然而两者实质存在很大差别。Assent是赞同的意思,对某一主张或行为表示允许,例如对参加某一临床试验表示允许,但并不代表其完全理解临床试验的风险和受益,并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思考;而Consent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年人同意,是经过了反复的思想检验和分析论证,理解了临床试验的风险和伤害。因此,Assent应理解为赞同更为合适。
2 儿科人群“同意”能力的差异
目前,儿童、成年人和知情同意法定年龄的定义因地理、文化和立法历史而异。美国联邦法案中指出,儿童参与研究需要父母/监护人的许可,“尊重人”这一生命伦理原则要求儿童同时提供自身有能力提供的同意,并且考虑儿童的年龄、成熟度和心理状态[8]。但是,现实操作层面上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要求,比如儿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可以提供同意?提供同意意味着什么?等。有些地方将19岁以下界定为儿童,而另一些地方满16岁就意味着成年。不管如何划分,源于儿童参加研究的脆弱性特点,获得儿科人群的同意都是必需的和复杂的。
伦理的考量是开展医学研究的基础,特别是涉及人类健康受试者或患者的研究[9]。临床决策是极为复杂的思想、法律和伦理等人文文化的决策,迅速发展的医学技术也难以同时解决价值选择的问题[10]。无论是家长还是研究医生,都无法替代儿童作最佳价值选择。儿童同意的能力水平与他们作复杂的、严肃决定的能力息息相关。儿童同意能力的评估和判断一般有两个标准:一是法律标准;二是认知标准[11]。研究医生有义务确保儿童知情和自主,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儿童能力的差异和独特性,例如儿童作决定时的理解能力、准确传达和沟通能力以及因研究而异的参与方式等。儿童知情同意书应当与成人的有所区分,在遵循一般伦理原则的基础上,还应充分考虑儿童的心理、思维发育尚未完全,对事物和语言文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受限等生理特点,比如以图文化、视觉化、简短化的直观和易于儿童理解的形式体现。
通常认为0~3岁儿童很难获得其真实的意愿表达,3~4岁儿童也许能了解部分风险受益;而10岁以上的儿童可能了解有利和风险[12]。有研究表明,大多数年龄小于9岁的儿童缺乏参加临床试验的同意的能力[13]。除了年龄以外,在儿童参加临床研究时,应该需要特别考虑儿童的解剖学、生理、情感和认知发展的特点[14]。文化、种族等其他因素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影响儿童对临床研究信息的理解。
3 儿科人群“同意”过程的失当
临床研究中儿科人群的“同意”非常重要,其中同意过程是一个重大挑战,在应该告知儿童/未成年人什么信息和哪些信息影响其决策等重要方面,却几乎没有共识。儿科临床研究中向父母和儿童告知有关潜在的风险和受益信息是知情同意的核心,理论上必须要求父母和儿童都同意参加。研究者必须确保以适当的可以理解的水平和形式向儿童和父母告知信息。
尽管父母同意和儿童同意在信息告知、理解和自愿这些要素是相同的,但根据儿童的认知水平不同,对这三个要素的理解和实施应该有所差异[15]。一项儿童/未成年人认为的优先事项与父母认为对子女最重要信息对比研究发现,与父母相比,儿童/未成年人更加重视隐私,较少重视研究目的和受益。与8~12岁儿童相比,13~17岁未成年人更加重视研究程序、直接受益和自愿参与[16]。
通常认为成年人判断比未成年人判断更成熟,因此固化地认为父母判断可替代孩子判断。但受试者可能是无任何直接的治疗性获益,那么,我们如何证明父母代表了儿童的最佳利益?为防止合法监护权滥用,美国健康和公共卫生事业部发布了针对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的保护性指导方针,若使孩子成为研究对象,必须取得他的父母或监护人的允许,而且儿童必须作出他们的“同意”[17]。在告知时,适当的“同意”的过程对于儿童的临床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者应该根据自主原则,尊重儿科人群的需要,提供他们需要了解的信息。
4 儿科人群临床研究的解决对策
4.1 加强儿童同意的能力评估
在西方医学中,尊重一个人的核心要素是确保其获得足够的信息后自主地作决定。年龄是儿童同意能力的重要因素,儿科人群理解信息的能力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1924年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和1959年联合国人权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父母或监护人对儿童的健康和福利负责直至18岁[14]。我国《儿科人群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对儿科人群划分为儿童(24个月~11周岁),青少年为(12~17周岁)[18]。《民法通则》第十二条规定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指出,通常10周岁以上(含10周岁)的儿科人群应参与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19]。
年龄不是绝对的判断标准,一项关于青少年乙型肝炎疫苗试验中123名12~17岁(平均年龄15岁)的青少年阅读了知情同意书并且完成了一项同意理解测试,只有56%的青少年完全理解。这可能意味着,如果要求他们作决定,那么近一半的人是基于他们并不完全理解的信息而作出的[20]。因此,可以借助于一些临床研究能力评估工具,比如麦克阿瑟临床研究能力评估工具(Modified MacArthur Competence Assessment Tool for Clinical Research)评估儿童同意研究的能力。儿童表达同意的前提是研究者提供了充分的儿科受试者可以理解的信息。因此,研究者在获取儿科人群同意时,应更注意告知的技巧,比如用心倾听,加强互动,积极回应儿科受试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决定儿科受试者本人是否参与或签署知情同意时,应提出充分的依据,并由伦理委员会审查以及确定目标受试者是否具有知情同意的资质。
4.2 构建儿童共享决策同意过程
知情内容和过程,需要根据研究目的和儿童的能力进行调整。理解力是智力、合理性、成熟性及语言的组合,应该根据研究对象的能力来决定传达信息的方式,尊重儿童参与研究的自主决策[21]。大多数儿童倾向于一种共享决策模式,在决定是否参加一项研究时,他们可积极参与并可得到父母、医生和研究者的支持[22]。研究者与儿童参与研究知情同意的交互作用具有潜在重要性,包括儿童主动参与决策过程,并在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良好的互动可能对儿童在接收信息、签署同意文本方面更有意义。
同意的内容和程序应根据儿童个体特点来设定,可通过研究者直接告知,而不是单一通过他们的父母。为了确保同意书内容的可理解性,也可采用问答和培训方式改进同意过程。某些特殊情境下的口头同意,是对不满足签署知情同意资质的儿科受试者的一种告知知情方式,有利于受试者对研究的依从性,但不能完全替代纸质版知情同意书的签署。研究者在试验方案中应提前写明儿科人群知情同意的内容,并需要得到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批准,包括是否需要获得父母双方知情同意,或是否仅需获得一方知情同意,或是否允许法定监护人知情同意,以及是否允许在未获得父母/法定监护人知情同意时,即可在紧急状况下开始的试验[19]。因此,共享决策同意模式是更符合于儿科人群特点的方式。
4.3 伦理委员会的全生命周期审查
儿科人群不同疾病类型、不同年龄以及发育变化,对药物的作用和给药剂量有极大的影响,组建涉及儿科人群临床研究的伦理委员会时,委员应包括具备儿科药学、儿科临床医学和接受过儿童心理学专业培训等不同专业背景的委员。此外,律师和社区代表(幼儿园或学校老师、育有与受试人群同年龄段子女的人员)也应包括[19]。此外,儿科人群临床研究涉及的问题远比成人临床研究复杂,从试验启动、试验实施直至试验结束,伦理委员会应加强对整体过程的全生命周期审查,审查儿童的临床研究时应至少遵循以下原则:①特殊保护原则,对儿童、孕妇、智力低下者以及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受试者,应当予以特别的保护[23];②有利原则,关注风险和受益的评估,当且仅当临床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儿童/未成年人健康的发展,且该受试人群可能合理地从研究结果中获益时才是正当的;③尊重自主原则,充分尊重儿童/未成年人的自主决定权,儿童/未成年人“同意”时应该被告知所有需要了解的项目信息,同意程序应如成人的知情同意一样满足三个基本因素:完全告知、充分理解和自主决定。
儿科人群的同意是伦理委员会批准一项研究的重要考量要素。在儿科人群临床研究中,虽然获得父母的知情同意是保护儿童的第一步程序,但同时尽可能地获得儿童的同意也极为重要,这也是一个需要根据儿童成长发育特点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同意的动态方式和过程。伦理委员会在审查时也需要考虑儿童的“年龄、成熟性和心理状态”,并确定他们是否有作同意决定的能力,不能认为没有反对就是同意。如果伦理委员会审查研究方案设计和知情同意书时,确定一项研究需要获得儿童/未成年人知情同意,那么本人意愿就十分重要,并且应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予以持续地关注。如果儿科受试者本人不同意参加试验或中途决定退出试验,那么即使法定监护人已经同意参加或愿意继续参加,也应以受试者本人的决定为准。
在临床研究中,儿科人群作为具有多重特殊性的个体,已经受到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但是,如何切实保障儿科人群受试者的同意权利,必须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的实践来实现。笔者所倡导的儿科人群同意能力评估、共享决策同意模式构建,以及伦理委员会全生命周期审查等建议,立足于不伤害和尊重自主等伦理原则,关注儿科人群认知能力动态变化的特点,将助力我国儿科人群临床研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