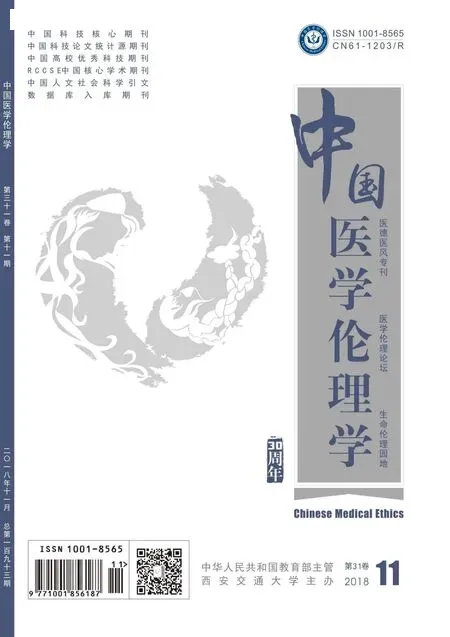社会工作介入晚期肿瘤患者的实践:家庭为本的视角
庄 洁,陈岩燕,吴晓慧*,孟 馥
(1上海市东方医院社工部,上海 200120,autumnzj@sina.com; 2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上海 200433)
1 研究背景
晚期肿瘤不仅影响患者本人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也给其整个家庭带来极大的影响。在儒家家庭主义的影响下,家庭照顾者是癌症患者的主要社会支持源[1]。患者的疾病被认为不单是患者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家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整个家庭都有照顾患者的责任,家庭需要共同协商患者的医疗与照顾方案。在医疗场域中,因患者的疾病与治疗而引起的各类问题是整个家庭面临的挑战,包括真实病情告知、医疗方案选择、身心压力、照顾压力、经济压力及家庭关系调整等。当家庭成员罹患晚期肿瘤时,考虑到患者的身心状况及对于疾病的接受度,医疗团队往往向家属做出病情告知并与其商讨医疗方案的选择。当家庭成员关于是否隐瞒真实病情与选择哪项治疗方案未达成一致时,整个家庭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满足肿瘤照顾者社会、医疗、心理方面的需求,这有助于提高其照顾能力,促进患者的康复,同时有助于肿瘤照顾者自身的健康[2]。
在国际上,医疗体系中家庭为中心的照护模式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国内现有的研究较多关注患者的家庭在医疗方面的需求,较少关注家庭在心理、社会方面的需求。本研究在分析某三甲医院社工部临床服务记录的基础上,探索医务社会工作者如何在家庭为本的视角下,协助晚期肿瘤患者与家庭处理因疾病与治疗引起的心理社会问题,为患者与家庭提供心理社会层面的支持服务。
2 家庭为本的社会工作干预
家庭为本的实践基于系统理论,后者认为家庭为系统的组成部分,家庭同时被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系统所影响,也受到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影响[3]。系统理论强调为家庭提供支持时需要关注家庭所处的环境、家庭与所处环境间的适应性及提供的支持需要促进个人、家庭与环境的资源之间的互相匹配与协调[4]。生态理论引导社会工作家庭为本的实践关注家庭内部及家庭与所处系统间的互动与影响,促进家庭内部系统、医患系统、社会支持系统及社会环境之间的有效互动。
在健康领域中,家庭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强调社会心理及发展性的支持是健康照护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实践将致力于复原家庭的自尊与控制感[5]。家庭为本的实践描述了一种患者、家庭与家庭照护团队的合作关系,尊重患者与家庭在照护计划、照护实践与服务评估中的视角。家庭为本的视角将家庭置于决定与行动的中心,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及关注家庭中的每位成员[6]。家庭为本的实践推动家庭共同参与决定制作的过程,寻求家庭层面的认同,同时关注与寻求家庭的优势与能力[7]。
在家庭为本视角的指引下,本文的第一作者在医疗场域中为患者与家庭提供临床服务。通过对以往临床服务记录的整理与分析,本文试图呈现本土社会工作家庭为本的实践经验,并反思实践的可行性及所面临的挑战。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收集的资料来自上海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社工部2014年至2016年留存的晚期肿瘤患者的个案服务记录表,共15份。这些记录表为医务社工从日常病房探访后记录所得,服务对象为呼吸科、肝胆科、肿瘤科、重症监护室及急诊病房中的晚期肿瘤患者及其家庭。服务对象的年龄从35岁到90岁,平均年龄55岁;上海户籍13人;女性7人。服务对象中,肺癌患者为9人,肝癌3人,其他肿瘤3人。服务对象由医务社工日常病房探访后接案为9人,医护团队转介6人。这15个临床服务个案的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个案的基本信息
研究者在汇总社工部临床个案记录表的基础上,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对临床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主题框架法在资料整理阶段确定分析主题、资料标记、按主题对资料进行归类、资料总结与综合,并通过描述性分析将特定主题的内容与特征呈现出来[8]。本研究运用主题框架分析法总结提炼家庭为本的医务社会工作本土临床经验。
4 研究发现
晚期肿瘤患者社会工作家庭为本实践的临床经验可概括为三个核心主题:①家庭为本的评估;②赋权家庭应对;③倡导家庭权益。
4.1 家庭为本的评估
在社会工作家庭为本的实践中,医务社工关注整个家庭的需求,提供一个开放、包容与安全的空间协助患者及家属分享感受、想法与体验。医务社工对整个家庭进行生理、心理、社会与灵性层面的评估:生理层面收集与症状及疾病有关的生理信息;心理层面评估患者及家庭因诊断、治疗及预后而产生的负面情绪;社会层面包括评估患者家庭支持系统及社会支持系统,家庭支持系统包括家庭角色、家庭结构、患者与家属面对诊断、预后与治疗的态度与信念及家庭资源;社会支持系统包括社会支持与资源;灵性层面包括患者与家庭灵性层面的需求、资源等。在为患者及家庭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医务社工持续评估与应对患者及家庭的需要。医务社工尊重患者及家庭的价值观及需求,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发掘家庭的优势与资源,这是医务社工的重要职能,也是社会工作家庭为本实践的基础。
医务社工在临床个案评估后发现晚期肿瘤患者及其家庭面临情绪困扰、医疗适应问题、家庭关系紧张、经济压力、照顾压力及医患沟通不畅等。情绪问题是所有家庭面临的共性问题,包括紧张、焦虑、无助等情绪。医疗适应问题包括无法适应疾病症状、缺乏对于疾病的认知、无法适应治疗引起的副作用及依从性弱等。家庭问题包括家庭关系疏离、病情告知意见不一致、对治疗方案意见不一致及未竟事宜等(见表2)。在家庭内部系统方面:11个家庭面临一系列因疾病与治疗引起的医疗适应问题,8个家庭面临家庭关系紧张,8个家庭面临经济压力,8个家庭面临照顾压力。在医患系统方面:11个家庭因患者医疗适应问题需要与医疗团队进行多次沟通,但医患沟通渠道的不畅使家庭在医患沟通方面面临较大挑战,进一步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效果。

表2 患者家庭的需求
例如,医生向医务社工转介了一位依从性较差的女性患者(个案1),医务社工与患者沟通后发现,原来患者的儿子也得了晚期肿瘤,正在另一个科室住院接受治疗。患者对于儿子病情的担心影响了她的情绪与治疗,同时家庭两位成员罹患肿瘤,整个家庭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通过对患者家庭全面的评估,医务社工为患者提供心理社会方面的支持,同时将患者的家庭情况及时反馈给医护团队,协助医护团队为患者提供适切的支持,患者的依从性得以改善,治疗效果得以提升。
4.2 赋权家庭应对
为协助家庭应对家庭心理、社会及医疗方面的挑战,医务社工从提升家庭内部支持系统、医患系统及社会支持系统方面为家庭提供支持。
第一,心理情绪支持。医务社工为患者及家庭提供辅导及心理情绪支持,帮助他们有能力去应对疾病、治疗与预后。医务社工在探访中为家庭提供一个表达、舒缓情绪的安全空间,协助患者与家属舒缓负面情绪,更好地应对疾病与治疗。例如,个案3的主人公为一位40岁的女性患者,她在上海组成了家庭,其他家庭成员都在新疆,为了避免家人与朋友的担心,她没有告诉他们真实的病情,每次还安慰他们自己只是接受普通的治疗,表现得很坚强。但在第三次见她的时候,她与医务社工诉说了内心真实的感受:她对于疾病感到无助、身体创痛的难以忍受、对于高中女儿的担心,她很感谢医务社工能聆听她的分享,她没有机会与其他人包括丈夫分享内心真实的情感,在这里她第一次感受被理解、被关怀。
第二,促进医患沟通。医务社工积极承担合作者与促进者的角色,医务社工每周定期参与医疗查房,推动建立医疗团队转介机制,及时发现与评估有需要的患者与家庭。医务社工在家庭评估的基础上,向医疗团队澄清家庭需求,促进医疗团队对患者与家庭心理社会层面需求的了解与接纳,提供适切的支持。同时,医务社工推动家庭与医疗团队沟通患者的治疗与照顾计划,使治疗及相关信息得到有效传递与共享,提升患者与家庭对疾病与治疗的合理认知,改善患者的医疗适应问题,提升治疗依从性,进而改善治疗效果。医务社工通过构建有效的医患沟通模式,促进患者、家庭与医护团队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推动医患系统的建立与提升。
在临床服务个案中,患者(个案9)从江西农村来上海就诊,患者的妻子有精神疾患,需要长期接受照顾。患者的女儿与父亲陪同患者来上海就诊,患者经诊断为恶性淋巴瘤,患者家人担心患者无法接受疾病而选择隐瞒真实病情。患者家属缺乏对于疾病与治疗的认知,同时担心疾病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与照顾压力。医务社工向医护团队反馈了患者的家庭情况,邀请患者的家庭成员共同参与跨学科团队会议,协助家庭成员了解并澄清疾病与治疗资讯,帮助家庭做出适切的决定,最终家庭成员决定回当地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第三,推动家庭联结。医务社工尊重患者与家属的意愿与需求,聆听患者与家属的真实想法,协助家庭成员间的沟通与理解,促进了家庭成员间情感的表达与联结,缓解整个家庭的负面情绪。医务社工推动患者与家庭共同参与决策:病情告知、治疗方案与措施的选择、预立指示的讨论及未竟事宜的达成等,促进家庭成员彼此间的关怀与照顾,提升家庭内部支持系统。在实践中,医务社工协助40%的家庭进行家庭关系协调,包括亲子关系协调、治疗方案达成一致、患者照顾问题与完成未竟事宜等。
医生将急诊科一位希望捐献遗体的63岁乳腺癌复发的女性患者(个案7)转介给医务社工。医务社工与患者家属沟通后发现因为患者的女儿在患者患病初期在国外生活,无法亲自照顾患者而产生强烈的愧疚感,因此无法接受患者遗体捐献的心愿。医务社工在了解家庭成员的想法与感受后,协助患者与女儿真实表达内心的想法与感受,缓解女儿的负面情绪,促使家庭成员彼此关怀的传递,最终协助患者达成捐献角膜的心愿。
第四,链接院内外资源。医务社工不仅仅是直接服务提供者,也是重要的资源链接者,医务社工协助家庭发现、链接及运用院内院外的资源,提升家庭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升家庭的能力感与控制感。在实践中,医务社工为其中的6个家庭(个案1、5、8、9、11、14)提供了院内外资源链接,在院内,医务社工为符合资助对象的晚期肿瘤患者提供经济援助,提供医保政策的咨询,组织患者与家属参加肿瘤患者支持小组、疼痛管理小组,组织肿瘤康复者义工探访服务等,为患者及家属构建院内支持网络。在院外,医务社工为患者链接社区资源,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宁养服务机构等,为患者提供出院后的支持服务,有效提升家庭的社会支持系统。
第五,协助家庭重整。全人关怀离不开灵性层面的关怀,医务社工同时关注与回应患者与家庭灵性层面上的需求,探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以应对疾病与死亡的挑战。医务社工为7个家庭(个案1、3、4、7、8、11、13)提供了灵性层面的支持,协助患者与家庭进行生命回顾,重整家庭生命历程,增强家庭的联结,探寻与肯定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4.3 倡导家庭权益
现有医疗体系依然专注于患者与家庭医疗方面的需求,对患者与家庭心理社会层面的需求关注与回应依然有限。在临床实践中,医务社工承担多重专业角色,倡导患者与家庭权益。
在微观层面,医务社工主动融入跨学科团队,对跨学科团队成员进行社会心理教育,倡导跨学科团队对于家庭心理社会需求的回应,提升跨学科团队对于开展家庭为本实践的认同,推动跨学科团队合作。在宏观层面,医务社工倡导现有医疗服务制度的调整,以争取患者与家庭的权益。医务社工与肿瘤科、呼吸科、重症监护室与急诊留观室建立了有效的合作关系,参与医疗查房,推动建立了有效的临床转介机制,协助推动家庭参与跨学科团队会议,使患者与家庭的需求及时得以回应。医务社工开展一系列病友支持项目,包括肿瘤病友支持小组、义工探访服务,将这些服务融入临床科室的恒常服务中,有效回应了患者与家庭的需求。同时,医务社工链接与培育社会支持系统,为患者与家庭争取经济资助、进行出院安置与获取社区资源等,医务社工成为患者、医疗系统与社区之间的桥梁。
在临床服务中,医务社工也得到了医护团队对于社会工作家庭为本实践的积极反馈。例如,在一次跨学科团队会议上,医护团队对于医务社会工作评价如下:
一位医生说:“作为床位医生我第一次了解患者的家庭、社会情况。疾病的转归与治疗有效以外,还与患者心理和情绪休戚相关,至少临床医生较少考虑和顾及。今后在我的工作中会与社工多沟通和讨论。”
护士长回应:“在平时的护理工作中,我们开始与社工更多交流患者的心理情绪状况,更多关注患者的心理状况。尝试更多聆听,更多问候,更多关心,我们能够感受到患者的微笑,患者对于我们的接纳。”主任也给予医务社工积极的反馈:“我们第一次从社会心理方面了解了患者需求及家庭系统的重要性,医生护士关注患者的身体健康,而对于患者的社会心理方面往往无法提供服务,而社工从这一角度弥补了医生护士的不足。这次分享也使我们医护人员较全面地了解了社工的工作,在未来的工作中也希望医护人员与社工更多沟通合作,全方面为患者提供服务。”

图1 社会工作家庭为本实践的流程

图2 支持系统间的互动
5 讨论
5.1 家庭为本临床实践的基本原则
医务社会工作者在以上15个个案中所开展的家庭为本实践,体现了以下原则:
原则一: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关注。社会工作家庭为本的实践回应了医学模式从生物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模式的转变,倡导并关注患者与家庭心理社会层面的需求。医务社工尊重患者及每位家庭成员的需求,并与家庭建立信任与安全的关系。医务社工将患者的健康问题置于整个家庭层面予以考虑,同时关注家庭内部系统、医患系统、社会支持系统等对于患者治疗与康复的影响,为家庭为本的介入服务提供基础。
原则二:关注家庭的优势,提升家庭的能力。医务社工关注家庭的优势与能力,而非仅仅关注疾病带给家庭的负面影响。医务社工关注患者与家庭面对疾病的信念、能力与资源,从优势视角出发,提升家庭应对挑战的能力。心理情绪支持是医务社工提供的最基础与重要的干预服务,同时关注与促进各系统间的互动,包括家庭内部支持系统、医患系统与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与提升。医务社工为患者与家庭提供个性化与适切的支持,提升患者与家庭应对疾病的权能感与控制感。
原则三:推动家庭共同决策。社会工作家庭为本的实践推动家庭内部支持系统的建立与提升,将家庭置于决定与行动的中心,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关注患者与家庭成员的意愿与需求,推动家庭共同参与决定制作的过程。如何应对晚期肿瘤患者的病情知情权、治疗选择权、身后事处理、未竟事宜等是本土家庭共同决策中面临的挑战,社会工作家庭为本的实践协助整个家庭提升对于生命的思考,促进家庭联结,协助家庭更好地面对生命与死亡。
5.2 家庭为本实践与儒家文化的契合性
社会工作家庭为本的实践有深厚的儒家家庭主义的生命伦理学基础。疾病被看作是整个家庭的问题,家庭应该在经济上、情感上与道德上有责任照顾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健康[9]。儒家家庭主义倡导整个家庭在照顾晚期肿瘤患者中的责任,推崇家庭成员共同决定模式,推崇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决策与照顾。社会工作家庭为本的实践与儒家文化相呼应,实践有效地回应了患者与家庭的需要与挑战,同时关注与发掘家庭优势与资源。家庭为本的实践关注并提升家庭能力,在家庭内部系统、医患系统及社会支持系统层面为家庭提供全面支持,协助整个家庭更好地应对疾病。
5.3 社会工作家庭为本实践面临的挑战
第一,医务社会工作专业认知度与认同度的有限。患者及家属对医务社会工作专业与服务认知有限,影响了医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医疗场域中开展的广度与深度,医务社工在临床实践中需要不断澄清自身的专业角色与职责,以提升患者与家属对专业的认知度与认同度。
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目标是协助患者与家属解决与疾病相关的心理社会问题,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及生活质量,鉴于医务社工专业的特殊性及非医学教育背景,医务社会工作在医疗体系中的专业认知度依然十分有限,同时医务社会工作本土发展实践较短,实证研究较少,医疗体系对医务社工的专业服务认可度有限。在临床实践中,医务社工与跨学科团队合作不够密切,医务社工需要不断澄清自身的专业角色与职责,主动融入跨学科团队,在跨学科团队合作方面面临较大挑战。同时,医务社工在医疗机构中的配比极为有限,进一步限制了医务社工开展社会工作家庭为本的实践。
第二,社会支持系统的限制。在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医务社工关注患者与家庭的社会支持系统,以期构建与提升社会支持系统。但现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较为有限,经济资助、照顾者支援、社区照护资源依然有限,社会资源的有限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医务社工作为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弱化了家庭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
6 总结
本研究聚焦与探索本土医疗场域中社会工作家庭为本的实践经验,讨论了社会工作家庭为本实践的优势与可行性。本土医疗场域中医务社会工作家庭为本的实践刚刚起步,在未来的实践与研究中,医务社工需要进一步定义、澄清与评估心理社会层面的专业介入如何影响家庭为本的实践,持续提升家庭为本介入的方法,丰富与总结家庭为本介入的实践经验。未来需要提升本土社会工作家庭为本实践在医疗场域中开展的广度与深度,在医疗体系中获取更多的支持与认可,进一步推动本土社会工作家庭为本的实践发展。
——医务工作者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