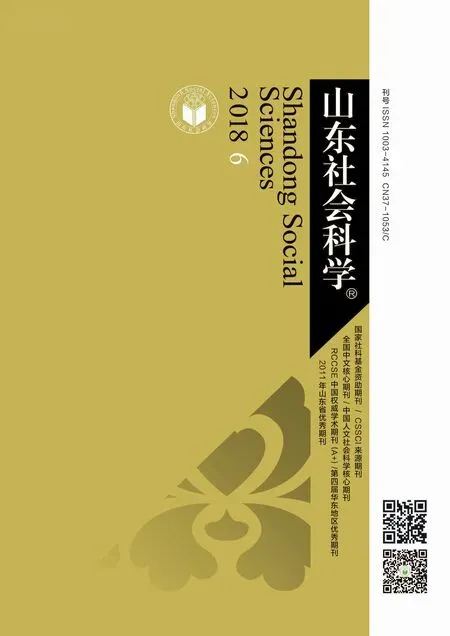马克思伦理思想立足点的转换
曾 俊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讨论“在”与“应当”的关系时指出:“在是建基于思之中,在却被应当提高了。”*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9页。哲学研究的问题是“在”与“思”的关系,也就是“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而伦理学研究的是“应当”问题。因此,哲学对“思存关系”问题的反思,为伦理学研究“应当”问题提供了基础与立足点(Standpoint)。同样,从古至今的各种伦理思想,无不以各种形式表征着其所依据的哲学立足点。马克思哲学作为实现了“哲学革命”的理论体系,从整体上表现出了对现代哲学的“意识内在性”(Immanenz)、“主体性”立足点的超越。那么,站在新的哲学立足点之上,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超越性”又何在呢?
一、现代哲学的立足点与伦理学转向
在正式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说一段古希腊时期的著名智者普罗泰戈拉和他学生的寓意深远的轶闻。相传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与他的学生欧提勒士曾约定:在欧提勒士毕业时支付给普罗泰戈拉一半的学费,待欧提勒士打赢第一场官司之后,支付另外一半学费。但欧提勒士在毕业之后一直没有打官司,因此也一直没有支付学费,为此普罗泰戈拉将其告上法庭。在法庭上普罗泰戈拉认为:若他打赢官司,按照裁决欧提勒士应该付清学费;若他输掉官司,按照约定欧提勒士也应该付清学费。因此,无论他输赢欧提勒士都应该付清学费。而欧提勒士则主张:若他打赢官司,则按照裁决他不用支付学费;若他打输官司,则按照约定他也不用支付学费。所以无论输赢,欧提勒士都不用支付学费。
这就是逻辑学史上著名的“普罗泰戈拉悖论”。从普罗泰戈拉与欧提勒士各自的推理中我们不难看出,二人只不过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决定是遵守“裁决”还是遵守“约定”,从而得出支付或不支付学费的结论,最终导致无论是“裁决”还是“约定”,都无法决定欧提勒士是否应该支付学费给普罗泰戈拉。这一悖论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对普罗泰戈拉著名的哲学命题——“人是万物尺度”的最好反讽。同时,在伦理学领域这一悖论却揭示出这样一个问题:以“自我”为立足点的伦理理论,如何寻求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规范?
对此,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中世纪的基督教伦理学家们,都试图通过设定一个外在于“自我”的“善”——“虽然善本身不是实在,而是地位和能力上都高于实在的东西”*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0页。——来解决道德规范的普遍性问题。但伴随着近代哲学研究主题从寻求世界本原的本体论,转向追问“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的认识论,导致了古代哲学所“承诺”的“终极实在”、“终极原因”与“终极价值”都要接受人类理性的“检验”。这就是说,它们要么通过理性证明自己充当知识基础具有合理性,要么退出知识领域重回信仰的世界。由此,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提出为标志,近代哲学研究的主题由“世界之上”的超验领域,转向了人“思维意识”的内在领域。
对于现代哲学而言,“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命题提出的最大意义在于确立了以“思维”(Thought)为核心的主体性原则。黑格尔将笛卡尔称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哲学家,正是因为“笛卡尔的命题却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我们必须抛开一切成见,即一切被直接认为真实的假设,而从思维开始,才能从思维出发达到确实可靠的东西,得到一个纯洁的开端”*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3页。。近现代哲学所追求的这种“纯洁的开端”恰恰成为其整个理论体系最根本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同时它也标志着整个哲学研究立足点的重大位移。这种立足点的位移不仅标志着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超越于现实世界之上的“超验世界”(Transzendent Welt)转向了人的“内心世界”,更在于将“主体性原则”作为一切近现代思想理论的潜在前提。由此,如前所述的由“普罗泰戈拉悖论”所引申出来的道德哲学中“自我”的问题,便更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并对近代以来的伦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伴随着现代哲学在思想领域统治地位的确立,主体哲学立足点的重大位移首先表现为思想家们对传统伦理学——特别是基督教伦理学进行的激烈批判。近代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费尔巴哈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作为宗教核心概念的上帝本身,认为上帝不过是“实现了的、对象化了的、被思想成或表象成实在而且最实在、成为绝对实体的那个人类想象力、思想力、表象力的实体”*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8页。。上帝的能力、智慧都来源于人的“想象”(Phantasei),那么这种“想象”自然也就无法成为制定人类道德行为准则的客观依据。而更为激进的是之后的尼采对道德本身所采取的批判态度,如其在《快乐的智慧》中所说:“一个人的美德之所以被称为‘善’,并不是因为那德行对他本身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那德行如我们所期许,并对我们及整个社会有好处”*尼采:《尼采生存哲学》,刘烨译,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从中尼采揭示出了传统道德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我们推崇“美德”,事实上并不是因为美德本身对我们有好处,而是因为“他人”的可称之为“美德”(Tugend)的行为对我们自身具有好处。故而所谓“美德”不是出自于人的“善念”,而恰恰相反是出自于人自身的“私欲”,任何“美德”与“个人利益”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传统道德哲学视之为人类天性的“美德”,本质上只是人自身追求利益的结果,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人们对道德问题的传统认知。总之,无论是费尔巴哈对传统伦理学的基础——宗教——所展开的批判,还是尼采对道德本身的批判,都基于现代哲学共同的立足点——“意识内在性”和“主体性原则”,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宗教的核心“上帝”不过是来源于人的主观想象,而传统伦理学所一直坚持的“美德”也不过是人从“自我”的利益需求出发而虚构出来的所谓“人的本性”。至此,传统伦理学“形而上”的基础遭到了严峻的挑战。
与费尔巴哈和尼采不同,基于同样的现代哲学立足点,一些伦理学家如休谟、亚当·斯密、穆勒等人,则试图建构出一种超越古代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的新伦理思想体系,形成了现代伦理学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传统。这一新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以“思维的内在性”作为理论建构的基本立足点,在此基础上,新的道德原则基础不能从外在的“超验世界”中去寻找,而要从“内在的”思维世界中探寻。因此,这些伦理学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人的内在的“情感”(sentiments)。亚当·斯密首先将道德行为的动机归于人们因“同情”(sympathy)而产生的情感:“不论当事人对任何对象所产生的是什么激情,每一个细心的旁观者一想到他的处境心中就会升起相同的情感。”*亚当·斯密:《道德情感论》,谢祖钧、孟晋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在斯密看来,人的情感具有“共通性”,情感上的“同情”(follow-feeling)是我们从事道德行为的最主要动机。与斯密同时代的休谟也持有相同的观点:“道德宁可以说是被人感觉到的,而不是被人判断出来的;不过这个感觉或情绪往往是那样柔弱和温和,以至我们容易把它和观念相混。”*大卫·休谟:《人性论》(下卷),关文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06 页。道德来自于人的情感而不是人的理性,因为理性只负责判断事物的真伪,而道德是关于事物“好坏”的评价——这种评价只能依赖于人的主观情感。功利论者穆勒则更为直接地指出:“我们内心的主观感受就是一切道德的终极约束力。”*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叶建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与传统功利论有所不同的是,现代元伦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乔治·摩尔,在其代表作《伦理学原理》中,虽然批判了以边沁、穆勒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功利主义者犯了“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将抽象的“善”的概念与“幸福”、“物质利益”等经验性要素混为一谈。但摩尔最终还是认为:“我希望在分析过程中将使人们更为明显地看出,上述那些说法是真理:对个人的热爱和美的享受包含我们所能想像的一切最大的、显然最大的善。”*乔治·摩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由此可见,摩尔所开创的现代元伦理学仍然没有超越现代哲学“意识内在性”的立足点,反而其对“自然主义谬误”的批判更进一步加深了伦理学的主观主义倾向,从而开创了现代伦理学的直觉主义理论传统。
同时,与功利论伦理学并行发展的,还有以“自然法”(Natural Law)作为道德原则根本依据的契约论(Contractarian)伦理学,其代表人物有洛克、康德以及现代道德哲学家罗尔斯等人。契约论者主张基于自然法制定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则,从而规范人的行为。以康德为例,他主张不直接论证某种“道德原则”,而是“处理意志(即欲求能力),所谓意志就是自己实现对象的能力”*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为此,康德一方面承认,传统“客体形而上学”道德论所追求的外在“终极实在”已经无法成为道德原则的基础。但同时也认为人类社会需要一种普遍性的道德法则,而功利论所追求的“现实欲求对象”、“个人幸福与自爱”都不能成为道德法则,因为“一个带有某种质料性的(因而经验性的)条件的实践规范永远不得算作实践法则”*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真正的“道德律”(das moralische Gesetz)必须是纯粹的、自由的“德性法则”(Sittengesetz)。它既能够摆脱质料性(Materie)、经验性(empirisch)的因素影响,同时又能摆脱主体(subjekt)感官的狭隘性,因此“只有那个普遍的立法形式能够用作意志的法则:那么一个这样的意志就必须被思考为完全独立于现象的自然规律,也就是独立于因果性法则,确切说是独立于相继法则。但一种这样的独立性在最严格的理解上即在先验的理解上,就叫作自由”*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2页。。“自由意志”(der freie Wille)是主体自己为自己进行“立法”(Gesetzgeben)的依据,道德法则没有任何感性质料作为“内容”而只有形式。因而只有抽去道德行为中的一切“动机”(Triebfeder)、“欲求”(Begehrung)、“感觉”(Empfindung)等具体的、经验性的内容,才能考察人类道德实践能力,同时这种能力是一种“非认识性”的能力,是一种“意志”。它的纯粹性恰恰就在于它不包括任何经验性的内容,只立足于“形式”而引导人们展开道德实践。这种基于“意志自由”的纯形式的道德法则,事实上就是“有理性的存在者对他自己发出道德命令,他所服从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8页。——人基于自己的“自由”,而进行自律行为乃是道德实践活动的保障。而早于康德的卢梭也有类似的观点:“我们从那里看到了先于理性存在的两大原则,其中一个原则让我们对自己的幸福(bien etre)和自我保存产生浓厚兴趣,而另一个原则就是在看到所有感性存在尤其是同类死亡或者痛苦时会产生天然的反感情绪。”*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邓冰艳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无论是康德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法则,还是卢梭的“先于理性存在的两大法则”,都是基于“内在性”(immanent)的前提条件,对人类社会“自然法”所进行的阐述——二者要么是人“心中的道德律”,要么是“人类灵魂最初、最简单的运作”,总之都没有超越“主观”与“思维”内在性范畴。而联系此前功利论的“同情”原则,契约论虽然与功利论在理论形态、思想主张上大相径庭甚至相互对立,但仍然与其站在同样的立足点——也就是现代主体性哲学“意识内在性”的立足点之上。
综上所述,现代伦理学在摆脱基督教伦理的影响之后,在主体性哲学框架内必然与现代哲学一样产生立足点的“位移”。在“主体性原则”、“意识内在性”的基本前提下,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外在于人的“终极实在”,而必须是主体性的“自我”(ego)。同样,决定道德原则的最终评判标准,也不是外在于世界的“神”,而是内在于人自身的“意识”。故而,近现代哲学立足点的转换同时导致了现代伦理学研究主题、理论形态的转变。而我们在开篇时所提到的“普罗泰戈拉悖论”所揭示的伦理学所面临的困境,在丧失外在约束的前提下,也将在现代社会以更为深刻的形态表现出来。
二、道德危机与现代哲学立足点
“意识内在性”作为现代哲学的立足点,在哲学领域里引发了关于如何解决“内在思维领域”与“外在现实领域”之间沟通与统一的问题。主体哲学的“意识内在性”立足点,决定了在现代人精神层面上难以克服“自在”与“他在”之间的矛盾,由此造成了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中的双重“分裂性”。
首先,“内在性”的哲学立足点所导致的“双重分裂”表现为“自我”与“世界”(Welt)的分离——“惟在人变成为主体,主体变成为自我,而自我变成为ego cogito[我思]的地方,才会有客体(Ob-jekt)意义上的对象”*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5页。现代哲学得以展开的依据是人思维的“逻辑先在性”。从近代哲学的经验论、唯理论到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无不以此为前提。这一立足点隐含的重要条件就是人的“内在世界”(Innere Welt)与“外在世界”(Externality Welt)的相互分离:“世界”对于人的思维而言不过是一种功利性的“存在”,人既无法充分“感知”这种存在,也无法全面“认识”这种存在。甚至“在内在论者看来,‘真理’是某种(理想化的)合理的可接受性——是我们的诸信念之间、我们的信念同我们的经验之间的某种理想的融贯(因为那些经验本身在我们信念系统中得到了表征)——而不是我们的信念同不依赖于心灵或不依赖于话语的‘事态’之间的符合”*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55-56页。。人与世界的“分裂”意味着人无法从外在世界为自己的知识、信念、价值规范找到客观性的基础,故而,道德规范将无法用外在、客观的真理来保障自身的“普遍性”,在此条件下人的道德行为如何找到可靠“依据”?
其次,“内在性”的哲学立足点所导致的“双重分裂”还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裂。“现代把每个人的生活分隔成多种片段,每个片段都有它自己的准则和行为模式。工作与休息相分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相分离,团体则与个人相分离,人的童年和老年都被扭曲而从人的生活的其余部分分离出去,成了两个不同的领域”*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强调“内在”的思维趋向导致了这种“分离”,在强调“意识内在性”的立足点之上,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从“自我”出发展开自身的思维与生活,强调“主体性”的优先地位与人天生作为“社会动物”的自然本性相互矛盾,造成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表现在市民社会便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页。。因此,在“意识内在性”的立足点上,现实社会所表现出的这种“分裂性”,造成了现代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中人生活“单子化”趋势。也就是说。人表面上生活在社会群体之中,本质上却如同一个个“单子”(Monad),社会中的每个个体的意识都被封闭于自身的内在性之中,这在伦理学领域导致了现代社会中人难以达成价值共识与道德共识。
现代社会中“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双重分裂性”,导致的是“个体”在“思维意识”层面上的“孤立性”与“封闭性”。这种境况在伦理学领域表现为人类社会缺乏道德共识,从而产生所谓的“道德危机”。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将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总结为三种表现形式:其一,“在当代的道德文化中,没有绝对的合理的权威,所谓的权威都是主观的、相对的,这也就是当代的道德理论纷争无法得到合理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其二,“社会大众的道德生活同样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可以依从”;其三“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到处都充斥着这种个人偏好……充满着那种因坚持个人独断而没完没了的道德争论”*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版,第3-4页。。但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现代社会道德文化缺乏合理权威、还是道德标准的“个人化”,或者是道德行为的“主观性”,都与主体性社会道德共识缺失有着密切关联,而这种缺失本质上是源于哲学立足点所具有的“分裂性”、“单子化”特征。首先现代哲学“意识内在性”立足点的“主体性”特征,决定了其不可能接受一种外在的、永恒与绝对的权威来规范“主体自我”的道德行为;其次,“自我”本身所具有的“个体性”、“封闭性”特征决定了现代社会难以建立一种“普遍性”的、为社会大众所广泛接受的“道德标准”;最后,个体思维意识的“封闭性”、“分裂性”与“孤立性”,导致了整个现代社会建立一种超越个人“主观性”、“道德偏好”的伦理原则变得不再可能。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现代人“除了另外一个信念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算作持有一个信念的理由”*Donald Davidson:Subjective,Intersubjective,objectiv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41.。
至此,当我们再次回到开篇所提到的“普罗泰戈拉悖论”时就会发现,这一悖论不仅是反映了“内在性”思维在逻辑学领域所面临的困境,更反映出“意识内在性”在伦理学上所面临的困境,也就是立足“自我”的道德意识如何在整个社会中获得“普遍性”的问题。对此,在现代形而上学框架之内的伦理学始终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唯有通过对现代伦理学“立足点”的转换与超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伦理学所面临的“内在性”困境。
自近代以来,无数思想家为了克服现代哲学所陷入的“内在性”困境,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决方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终完成者,黑格尔试图通过所谓“绝对理念”的矛盾运动来解决思维如何获得客观性问题;费尔巴哈试图通过“宗教批判”来达到这一目的;尼采则以近乎“极端”的方式批判“形而上学”,但最终结果仍然是滑向虚无主义。这些努力最终都没能真正超越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立足点”——“意识内在性”的立足点。那么,完成了“哲学革命”的马克思如何规定自身理论的立足点?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超越了“意识内在性”难题?
三、立足点的转换与马克思伦理思想的超越性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立足点”的这段经典论述,明确阐明了“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是马克思哲学的最根本的“立足点”。那么,这一立足点是如何超越了现代主体形而上学框架内的“意识内在性”问题?
马克思在其早期思想中就对近代以来哲学的立足点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指出了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哲学的“意识内在性”前提所产生的真正根源:“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30页。“意识内在性”立足点的本质在于对“意识”第一性地位的强调,但马克思明确指出思维只是一种“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这个“存在”的内容是人的“实际生活过程”。传统哲学以“自我”作为哲学研究的起点,是因为“自我”作为一种“纯粹无规定的思想”——具有无条件性、无中介性的特征——足以构成人类探索自身思维与认识过程的逻辑起点。但以这种毫无内容的空洞抽象概念作为立足点,必然导致其学说理论体系与现实生活相互分离,而思维的真正来源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的“实际生活过程”。主体哲学最大的问题在于单纯强调思维的“抽象形式”而忽视了思维的“现实内容”。也就是说,作为“逻辑起点”的“思维内在性”,在作为整个现代哲学体系“立足点”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思维”与“存在”渐行渐远的趋势。简言之,就是将“开端”问题与“第一性”问题混为一谈,从而陷入“内在性”的难题之中。
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andliche〕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页。也就是说,人不能仅从思维领域用思辨活动去寻找突破“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藩篱”,而应该从现实领域用实践的方法去寻求突破。此外,因为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也就说明,对思维客观性的理解不能从思维本身出发,而应该以实践为中介——理解人的“思维”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以人历史性的“现实生活”作为哲学与伦理学真正的“立足点”,才能正确理解思维与存在之间、“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正确关系。
当我们站在“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立足点上看待伦理学问题时就会发现:所谓的契约论与功利论的理论分歧、“自在”与“他在”的对立、现代道德危机等问题就将“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同时这也说明,我们不能站在旧的哲学立足点上,从马克思所批判的现代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的框架内去阐释、理解马克思的伦理思想。
但遗憾的是这种倾向在学界一直存在,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起以来,其理论研究者一直试图从伦理学的角度理解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但其在研究理路上一直试图将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纳入到传统伦理学、道德哲学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他们忽视了近现代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一般来说,哲学家们关注道德哲学往往将其当作一种达到行动的普遍道德箴言、法则和命令的手段”*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而经典理论家们却明确宣誓:“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03页。。这显然构成了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一个内在矛盾:马克思是反对“道德”还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当我们从传统伦理学的立足点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时,就会产生两种极端的倾向;要么选择承认经典理论家们持有“反道德论”的立场,要么尽一切可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具有内在道德诉求,只不过不是资产阶级的道德诉求。
以艾伦·伍德、R·W·米勒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伦理学家认为马克思持有“非道德论”(Immoralism)的立场。如米勒认为马克思虽然认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道德,但在政治学的视域下马克思却是“反道德”的,因为“考虑到社会冲突的实际性质,人们不能使用正义、权利或平等的标准来一贯地判断社会”*米勒:《分析马克思——道德、权力和历史》,张伟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马克思对传统道德的批判导致其在理论形态上呈现出一种“反道德”的形式,因为其对传统道德哲学所研究的重要对象:正义、平等、自由等概念几乎都采取“拒斥”与“批判”的态度。
与此相对应的是,如凯·尼尔森、史蒂文·卢克斯等人则持有不同的态度,他们倾向于采取一种“二分”(Dualism)的态度来解决问题——即将马克思所批判的道德与其所追求的道德价值区分开来。以卢克斯为例,他认为“我的建议是:一旦我们认识到它指责为意识形态和不合时宜的法权道德,而采纳为它自己的道德的是解放的道德,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态度中似是而非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史蒂文·卢克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袁聚录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也就是将马克思所反对的道德称之为“法权道德”(Recht morality);而将马克思支持、追求的道德观念称之为“解放道德”(Emancipation morality)。而尼尔森则采取一种被称之为“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理论来解决马克思道德论述中的“矛盾”——“在具备不同生产方式的不同社会里,我们拥有特定的正义原则,它独一无二地适用于那个社会及其生产方式”。也就是说,不同社会根据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正义原则(Principles of Justices),每一种正义原则对其所处的社会形态而言都是道德的,但对于拥有更高级生产方式的社会而言,低级社会的正义原则却是“非正义”,这就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道德批判的合理性基础。所以“从未来的共产主义视角看,当更高的社会形态有可能取代资本主义时,资本主义就是不正义的”*凯·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念》,李义天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8页。。
纵观这些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理论在对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阐释过程中,一直力图解决马克思对道德问题看似“矛盾”的论述,但却鲜有讨论马克思到底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上展开对道德问题的批判。如果我们基于马克思“人类社会”的哲学立足点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从根源上超越了现代伦理学所依托的哲学立足点。
首先,“人类社会”的立足点使马克思伦理思想实现了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再理解。现代伦理学围绕如何协调“自我”与“他在”的关系问题展开,但“人类社会”的哲学立足点却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提出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伦理学最早围绕“苏格拉底问题”而展开的——“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Rutledge,2006,P.63。当我们回到这一伦理学的初始问题时,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将伦理学问题又拉回到其原点:即人现实生活的原点——“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下的伦理思想,是站在新立足点的立场上,重新回答了苏格拉底所提出的伦理学基本问题:“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点在理论深度、论域的广度上超越了现代伦理学,并在此基础上彻底摆脱了“意识内在性”问题对现代伦理学研究的困扰。
其次,“人类社会”的立足点使马克思伦理思想完成了伦理学研究主题转换。传统伦理学将道德、权利、自由、正义等抽象概念作为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伦理思想将人的“社会关系”作为研究主题,这不仅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更因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道德离开社会实践、离开现实社会关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道德意识、道德原则、道德规范本质上都来源于人在社会关系实践中的抽象,而不是相反。因此对于传统伦理学所讨论的道德问题,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以社会关系为对象的实践中才能够解决——“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最后,“人类社会”的立足点使马克思伦理思想完成了伦理学研究目的的转变。传统伦理学以建立一套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伦理规范为目标,而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最终目的则是建立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对社会中全体成员联合占有生产资料的全新社会经济体制的建构,从伦理学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具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新型伦理关系的社会。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伦理思想所追寻的道德价值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统一,而不是如传统伦理学那样单纯理论层面展开对道德原则的讨论。从这一角度而言,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既是一种价值理想,也是一种对未来社会伦理原则的科学构想,具有价值追求与理论探索的双重维度。
综上所述,马克思哲学相对于现代哲学而言实现了立足点的转换,即从现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立足点转换到“人类社会”的立足点。这一转换不仅造就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同时也造就了马克思伦理思想相对于传统伦理学研究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超越了现代伦理学研究“自在”与“他在”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深化了我们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同时,也将道德研究的主题由正义、自由等抽象概念转向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并最终实现了伦理学研究的目的从道德原则研究向“共同体”(Community)建构实践的转变。因此,把握马克思哲学立足点的转换,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伦理思想内涵与“革命性”之所在。
——重读方增先《粒粒皆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