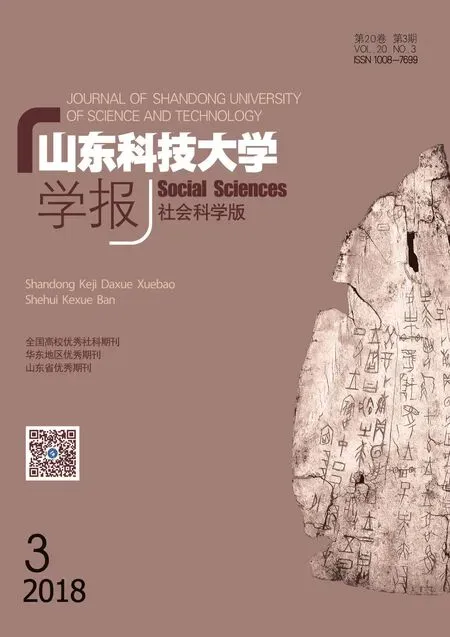乡规民约的历史嬗变及其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2)
一、乡规民约的概念与理念源流
(一)乡规民约的概念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在传统的乡土中国,“乡土社会的治理规则被称为乡规民约,乡土社会又是乡规民约的社会基础”,[2]那么,何谓乡规民约呢?笔者认为,乡规民约是指在我国基层社会的治理过程之中,在基层精英或乡绅主导之下,由尽可能多的基层乡民参与制订的一种更多的是在道德上对全体成员的日常行为进行规制的行为规范。有时也简称为“乡约”,在城市则称之为“街规民约”,它“规范着乡民的行为方式、调节着村民之间,以及村民和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化解着乡村社区的纠纷、维护着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3]由此,乡规民约也成为传统中国“最具代表性、运行时间最长、治理作用与效果最为显著的一种非正式制度规则。”[4]
(二)乡规民约的理念源流
当然,乡规民约并非凭空而来,实际上在我国古代很早的一些经典名著之中就有提倡敬老、睦邻等做法的论述,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乡规民约的源流。例如,《周礼·天官冢宰·大宰》云“以八则治都鄙”——“六曰礼俗,以驭其民”;亦云“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两种规定都隐约透露了以“礼”对民众进行治理的意识,尤其是“敬故”这一规定,更是“尊老”这一传统美德的渊源。又如,《礼记·礼运》云“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再如,《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云“死徙无出乡,乡田同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等等。
无论是《周礼》《礼记》还是《孟子》,都有一些关于“敬故”“相保相受”“守望相助”等邻里相亲、相敬、帮扶的阐述,反映了我国古代先贤希望民众之间相亲相爱,以期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世界。在传统中国,“表面上看,国家权力的终端是州县,事实上,农业时代的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农村的统治”,[5]但囿于历史的局限性,国家的统治力量很难有能力充分的深入基层,所以“地方官员对农村的控制一般是借助乡绅阶层实行间接控制。”[5]在古代中国,民众在遭遇严重的旱涝灾害之时,尽管国家也经常会有救灾或赈济之举,但若遭遇一般性的天灾人祸,除了依赖自身的能力之外,就主要依赖于宗族和乡邻的帮扶了,因此宗族和邻里之间的帮扶就显得弥足珍贵。然而,有了邻里帮扶的理念,并不代表绝大多数民众就会自发践行,这需要统治阶层的默许甚至提倡和基层士绅或社会精英的持续推动。“自秦汉以来,历代出现了一些以乡村长老和士绅贤达为代表的乡村基层组织和治理权威,以填补县级政府以下的权威真空”,[6]正因如此,才为以乡规民约为载体的乡民自治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
二、北宋时期:《吕氏乡约》的出现及其阐述
(一)《吕氏乡约》的出现
到了北宋时期,我国的乡规民约终于迎来发展的春天,代表性事件就是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在关中地区的蓝田县,被“蓝田四吕”的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制订和实施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即《吕氏乡约》。四人在北宋都曾担任要职,而且著述宏富,在经学、史学、金石学、地理学、文学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部分著作还有开创之功,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由他们制定并实施的《吕氏乡约》也随之颇受关注。北宋之后,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东移,关中在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渐衰落,但乡规民约的制定与实施却领风气之先,这应是唐朝作为我国古代法制建设的集大成者使关中这片沃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即使是从宋朝开始关中失去了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民间也能凭借深邃的法制历史在乡规民约发展的道路上迈出具有深远影响的第一步。
(二)《吕氏乡约》的特点
“北宋的《吕氏乡约》是历代乡规民约的典型代表,其内容涉及乡村社会的邻里调解、道德教化、伦理评判等各个方面,以独特的秩序意义,约束着人们的行为,维护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7]笔者认为,它具有以下六个特点:一是,乡约与官府无关,是在社会精英主导之下,且由与之居住在同一区域的乡民参与制定的产物,“《吕氏乡约》联结起来的民间组织,却并非基于血缘关系或宗族纽带,而是来自乡里交往这样的地缘关系”,[8]这是其与家规、族规最大的不同之处。二是,以成文规则的形式体现出来。虽然《周礼》《礼记》和《孟子》等古代经典著作之中有一些提倡邻里帮扶的论述,但都相当零散,并没有以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成文形式呈现出来并予以实践,而《吕氏乡约》是第一次做到了这一点。三是,以“乡”为单位而不是以“县”或更大的行政区域为单位。“乡”的区域一般不大,倘若以更大的行政区域为乡约制定与适用的单位,可能会因为难以兼顾乡俗而使施行效果遭受限制。四是,乡民自愿参与乡约的制定,“其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但由于参与之后能够与其他乡民结成事实上的帮扶共同体,有利无害,因此有远见的乡民基本上都愿意参与,一旦参与,则不能违反。尽管乡规民约在“本质上是一种‘民间法’,缺乏‘国家法’强制力的保障”,[9]但在实际的施行过程之中,以族长为代表的基层精英往往手握动用肉刑和私刑的权力,藉此保障乡规民约的施行,国家对此基本上也是默许的。五是,公开选任或推选带领乡民实施乡约的首领,选任也带有明显的“民主”色彩。“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一旦当选且愿意就职,既意味着有实施乡约的权力,也意味着有为乡民谋福利的义务。六是,定期聚会,以便共商事务、联络感情或施行赏罚。定期聚会表现为“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而且“会集之日,相与推举其能者,书于籍,以警励其不能者”,以期褒扬先进,警示落后。七是,乡约修订相对容易,“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只要获得了乡民的同意即可修订乡约。
(三)《吕氏乡约》的内容
《吕氏乡约》内容丰富,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德业相劝”,对“德”进行了解释性的列举,认为“德”有二十三种表现。将“业”分为两种,即“居家”表现和“在外”表现,并延伸至“读书治田”等其他领域。二是,“过失相规”,规定“过失,谓犯义之过六,犯约之过四,不修之过五”。三是,“礼俗相交”,规定“一曰尊幼辈行,二曰造请拜揖,三曰请召送迎,四曰庆吊赠遗”。四是,“患难相恤”,规定“患难之事七”,列举了七种可以请求乡人帮扶的患难类型。《吕氏乡约》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对每一个方面都做出了细分和解释,可操作性很强。但可惜的是,《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没有多久,北宋就被金人所灭,随之被时人所遗忘。不过,到了南宋中期,朝廷在南方的统治逐渐稳固,随之开始思治,《吕氏乡约》又重回精英阶层的视野。有此情势,《吕氏乡约》被理学大师朱熹所注意到,并考证出主要作者是吕大钧,据此还编写了《增损吕氏乡约》。由于朱熹在宋明理学上地位至尊,影响极大,被尊称为“朱子”,经其研究和提倡,《吕氏乡约》在诞生百年之后,又盛名远播,声誉日隆。
三、明清时期:乡规民约的官方色彩逐渐增加
(一)明初对乡规民约的提倡
到了明朝,乡规民约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提倡。元朝的暴虐统治和元末明初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乱,使百姓流离失所,严重动摇了基层社会的治理秩序。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名臣解缙向朝廷建议“仿蓝田吕氏乡约及浦江郑氏家范,率先于世族以端轨”,以求淳化风俗、教人向善,以期重塑基层社会的治理秩序,该建议被朝廷采纳。明初,朝廷颁布了圣谕六条,即“主之以三老,家临而户至,朝命而夕申,如父母之训子弟。至成祖文皇帝,又表章家礼及《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继而“颁降天下,使诵行焉”。
(二)《南赣乡约》和《乡甲约》的概况与影响
由于朝廷的提倡,地方官府推行乡约也热情饱满,其中以王阳明在1518年颁布的《南赣乡约》最有代表性,该乡约“发挥底层精英作用,彰善纠恶,能够使人做‘良善之民’,营造出‘仁厚之俗’”,[10]所以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南赣乡约》都影响颇大。到了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朝廷着力推广王阳明的做法,史称“嘉靖间,部檄天下,举行乡约,大抵增损王文成公之教”。
除了王阳明的《南赣乡约》,明代还有数位大儒对乡约制度的研究很深入,尤其以明末吕坤的贡献最为突出。吕坤对《吕氏乡约》做了进一步发展,他制定了《乡甲约》,把乡约、保甲都纳入到一个组织,“约一乡之人,而共为社仓、保甲、社学也。社仓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学是民信事”,藉此对基层社会进行综合治理,颇有成效。《乡甲约》对后世影响极大,不仅设计严密,而且施行缜密,在当地建了一百二十处“乡约所”,“以一里为率,各立约正一人,约副一人,选公道正直者充之,以统一约之人。约讲一人,约史一人,选善书能劝者充之,以办一约之事。十家内选九家所推者一人为甲长”,而且在各个乡约所之外,还有一个监督管理机制,官府通过它监管“乡约所”,继而施行赏罚。可见,《乡甲约》组织极为严密,增强了官府对基层社会的统治。到了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商州知州王邦俊在城乡共设四十处“乡约所”,进一步推动了《乡甲约》的普及。有明一代,不仅文人、学者在理论上对乡约制度颇有研究,而且某些儒臣或当地精英也以《吕氏乡约》和《南赣乡约》——尤其是后者——为蓝本制定了适合本区域实际情况的乡规民约,且身体力行地予以践行。所以,乡规民约在明朝“经过一系列的演变,它作为民间规约的意义越来越淡化,却变成了朝廷强令推行的一种活动;作为一种组织实体,它也越来越失去了民间自治的性质,逐渐成为乡村基层行政机构的名称。”[11]较之《吕氏乡约》,《南赣乡约》已有了根本性的嬗变,正如社会学家杨开道对其所作的对比——“一个是民治的胚胎,一个是官治的传统”。[12]
可以说,《吕氏乡约》与借鉴《吕氏乡约》而制定的《南赣乡约》《乡甲约》,对后世影响极大,为现代乡村自治提供了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样板。明朝发展的这一套以乡约、保甲、社学、社仓四者为一体的乡治系统,一直延续到清朝甚至是民国,被历代统治阶层所认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乡规民约“由此根系向上生长、与国家法规制度相结合而产生的制度理性”,[13]使之契合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明清时期,乡约发展到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域,被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誉为中国人的“精神宪法”,可见其地位之崇高,影响之深远。
四、晚清到民国:乡规民约发展趋于停滞但却存续日久
(一)乡规民约发展趋于停滞的原因探讨
萌芽于北宋,盛行于明清两朝的乡规民约,在官府推动、精英主导与乡民参与之下发展形势一片大好,最终却限于停滞,并没有发展成具有现代理念的基层民主自治,颇为可惜。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乡约推崇的是贤人政治,即便具有一些民本思想,但与现代民主思想仍然有较大的差距,面对官府推动、精英主导的制定与实施格局,广大乡民只是按部就班的参与其中,主观能动性始终有所欠缺,而且乡约的内容也主要服务于修身齐家与邻里帮扶两个方面,难以反映民主诉求,也难以对官府权力进行制约,这与当下的乡规民约的意涵相差甚远。二是,我国民众的识字率一直不高,直到清末“新政”时期,我国的识字率也不过才20%左右,而以《吕氏乡约》为蓝本而制定的众多乡规民约,由于是以基层精英为主导,其文言气息显得较为浓厚,对于普通民众尤其是对识文断字有难度的民众而言,能够准确理解乡约的含义并非易事。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只要不违反乡约规定即可,以贤达乡绅作为人生楷模以及教育子女的榜样,则是较为普遍的做法,至于热心公益、相互扶持,倘若经济成本太大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并不容易,凡此种种,都极大的限制了乡规民约发展成为具有现代民主观念的基层自治章程的可能性。三是,明清时期,以《吕氏乡约》为蓝本制定的《南赣乡约》《乡甲约》等乡规民约,使基层社会秩序平稳运转,对于民风民俗也多有教化之功,但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服务于朝廷对基层社会的间接统治。本来是服务于乡民修身齐家、邻里帮扶,并带有乡民自治色彩的乡规民约到了明朝中后期,却开始异化为官府管控乡民,强化皇权统治的产物,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回望历史,从北宋的《吕氏乡约》到明朝的《南赣乡约》《乡甲约》,在官府默许甚至提倡之下,有赖于乡村精英甚至是当世大儒的主持,使萌芽于《周礼》《礼记》和《孟子》之中的“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等零碎的思想以成文的乡规民约这一形式体现出来,并且内容丰富,可操作性较强,确实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进步,也确实有一些乡民自治的色彩。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乡规民约通过道德教化和相关惩罚机制的约束,使传统的乡村社会得到了有效治理。而且,乡规民约之中也确实有反映基层民众的某些诉求和传统美德的规定。例如,贵州省贵定县石板乡腊利寨现存1919年的寨规碑中就有“贫穷患难亲友相救”“勿以恶凌善,勿以富吞穷”“行者让路,耕者让畔”等内容,这对于淳化风俗、教人向善,当然也是有效果的。
(二)乡规民约虽然存续,但其反动色彩日益加强
但从内容上看,乡规民约涉及的面其实很窄,基本上只有两个——修身齐家和邻里帮扶,这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贤人政治的一种体现,与具有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基层群众自治相比,在本质上相差很大。而且从明朝晚期开始,以《乡甲约》为代表的乡规民约,尽管依然传承了《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理念,但却异化成了便于官府加强对基层社会进行统治的产物,带有一定的反动色彩。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乡规民约继续得以传承,但在质上并未有太大的突破,各地虽然也有一些探索,但囿于战乱不休、外敌入侵的不利环境,乡规民约并未随着社会变革的大潮而成功实现自下而上的革新。在此期间,国家也对乡规民约进行了由上而下的改革,但本质上往往是为了扑灭基层的革命火种,或是为了加强政府对基层的统治,因此乡规民约的嬗变在总体上趋于停滞,一直未有创新性的、实质性的进步。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将统治的触角向基层延伸,从而便于扑灭工农武装革命,在基层推行带有反动性质的保甲制度,这在名著《白鹿原》之中也有反映,在该小说之中,作为“总乡约”的田福贤和作为白鹿村“乡约”的鹿子霖,行使的便是国民党政府所赋予的对基层进行统治的公权力,但在其行使权力之时,却受到了族长白嘉轩及其所代表的基层精英和乡村自治传统的消极抵制,但“总乡约”“乡约”官职的出现,就已说明当时的乡约制度在国民党政府的改造之下,具有了更加浓重的反动色彩。
五、从沉寂到重生:乡规民约作为法律规范重要补充的角色定位
(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乡规民约进入沉寂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或解放区的广大民众在党的领导下,也制定了一些适合形势需要的乡规民约,发挥了抗日救国或支持革命的积极作用。例如,抗日爱国公约、防奸公约、支前公约等。新中国成立后,乡规民约虽然确实也反映了民众的一些正当诉求,弘扬了邻里帮扶的良好美德,但毕竟是基层精英和乡绅自治的产物,所以“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时间里,一系列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乡规民约被作为封建枷锁受到批判,相关研究近乎停滞”,[14]当然,传统的乡规民约也确实存在一些不符合法治精神的糟粕,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例如,族长有权对违犯乡规民约的村民动用私刑、肉刑,这些都与今天的法治理念格格不入,如果乡规民约的糟粕不祛除,即便是作为法律规范的补充性或辅助性的规则,也难以与之进行良好的衔接和互动,更遑论服务于今天的基层群众自治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的公权力急速的伸向基层,打破了数千年“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局面,实现了国家强有力的统一,那么,作为古代官府对基层社会加强统治的产物即旧式的乡规民约,自然难以继续存在了。此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基层社会尽管也制定过一些村民公约,但由于其内容极富政治性,基本上就是一些政治口号,与之前在基层社会所存续的传统乡规民约存在着质的不同,因此不宜将其当成乡规民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发展。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是乡规民约的沉寂期。
(二)改革开放之后乡规民约又获重生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鉴于传统的乡规民约确实有一些有利于增强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做法,也反映了民众的一些正当诉求和对某些传统美德的期许,而这恰恰也能与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所秉持的意识形态相兼容,乡规民约随之又得到了国家的正视。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乡规民约在宪法与法律上也有了一席之地,成为了基层社会治理和群众自治的重要载体之一,使之在城镇和农村都得到了相应的恢复和发展。时值当下,“传统村规民约得以复苏并呈现出两种形态,即部分村规民约被改造后虚化为一种形式化的文本,形同虚设;部分村规民约则转型为法律、政策的地方化版本,重获新生。”[15]对于后者,其进化或“升格”成了“国家法”,有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无论是革故鼎新还是深入施行都没有太大的阻力。对于前者,其在本质上依然是“民间法”,应将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与国家推进基层群众自治的新形势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国家法”的有益补充,同时在基层政府的支持和村委会或居委会的推动下,增强其施行能力,使之能起到维护民众合法权益的作用,继而服务于当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宪法和法律对乡规民约的规制
1982年《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以此为依据,1987年通过、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施行,并于2010年修改的《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第27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同时,1989年通过,并于1990年实施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5条规定“居民公约由居民会议讨论制定,报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备案,由居民委员会监督执行。……居民公约的内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可见,《宪法》24条规定和以其为依据而制定的《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我国实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众依法享有自治权利的法治保障。由《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出台的时间可以看出,国家在基层推行群众自治之时相当谨慎,该法1987年通过,于次年开始试行,但直到十年之后的1998年,才由第9号国家主席令予以公布并正式施行,前后经历了近十年的试行期,国家才开始在农村推行基层民众自治。相对而言,国家在城市推行居民自治要迅速的多,这主要得益于《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经过近十年的试行,使国家看到了基层群众自治是一项符合国情的好制度。有此情势,“村民自治章程作为乡规民约的高级形式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但其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嬗变”,[16]较之传统的乡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可以看作是一种都被改造的、新形式的乡规民约,使之作为法律规范的有益补充而服务于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这应该是其在当下中国的正确定位。
(四)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根据《宪法》《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与《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各地的基层民众在村委会(包括居委会,下同)的主导之下,普遍制定了乡规民约(包括居民公约,下同),有力推动了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施。无论是《村民委员会自治法》还是《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都明确规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这是乡规民约在制定与实施之时,绝对不能跨越的一条“红线”。《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第27条第3款规定,如果村规民约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的话,“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虽然《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无此规定,但街规民约如果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的话,基层政府应有权责令改正,这也是维护国家法治尊严的必要手段之一。同时,乡规民约作为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施载体之一,除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之外,还应体现和维护基层群众的合法权益,所以“在挖掘传统乡规民约基层社会治理价值、促成其现代价值转换时,应当克服传统乡规民约漠视乡民主体权利的倾向,充分保障乡民权利;应当克服乡民诉讼意识窒息的倾向,注重提升民众的法律意识”。[17]尽管乡规民约不属于我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村委会也不属于我国政权的组成体系,但无论是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规民约及其制定与实施者即村委会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下的乡规民约,应注意抓好两个着力点:一是在制定之时村委会应发挥好主导作用,同时基层政府做好备案工作和合法性审查工作;二是辖区村民应积极参与,村委会也应做好组织工作,使广大乡民尤其是基层精英能有序参与其中,继而使乡规民约的制定能吸纳民意,其实施也能得到民众支持,而且还要想方设法的增强乡规民约的执行能力,使之成为发扬基层民主、推进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有效载体。
六、结语与展望
时值当下,即便是“国家法律法规日渐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调整规则,村规民约的存在和发展受到空前限制”,[18]但其适用仍有拓展的空间与可能,毕竟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之中法律并非总是万能的,有时也需要一些民间规则作为补充。正因如此,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治理步入正轨,国家对于乡规民约重新予以正视,根据1982年《宪法》第24条相继制定了《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与《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两部法律赋予了基层民众制定乡规民约的权利,只要遵守“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这一前提即可。当今中国的乡规民约与从宋代延续到民国时期的乡规民约存在质的不同,前者是法治社会的产物,反映了民众的诉求和基层群众自治的需要,对于村委会既是赋权,同时也是限权,对于国家在基层的治理所起的作用是补充,而不像传统的乡规民约的存续,是为了间接的服务于政府对基层社会的管控。当然,两者也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都反映了民众的某些正当诉求和对一些传统美德的期许。面对《宪法》第24条与据其所制定的《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与《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数量众多的乡规民约,可以看出,我国在群众基层自治方面已形成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治理体系。而同时,“作为乡村治理的有效形式,乡规民约是获取村民信任的最为有效的手段”,[19]那么,乡规民约在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应体现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唯有如此,乡规民约才能获得民众的关注、重视和信任,其执行能力随之才会有保障,这一点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从北宋的《吕氏乡约》到明朝的《南赣乡约》《乡甲约》,到新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根据地或解放区制定的抗日爱国公约、防奸公约、支前公约,再到《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各地据此而制定的乡规民约,一晃已有千余年,乡规民约屡屡兴衰,却存续不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同时期的乡规民约确实反映了基层民众的某些正当诉求和对一些传统美德的追求。无论社会局势如何,诸如“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一些传统美德却始终富有生命力,穿越时空,流传至今,即便当下的法治建设再向前推进,但乡规民约经过改造和扬弃,总是可以作为法律规范的有益补充,使之服务于今天的基层民众自治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创一个乡规民约发展的新时代。2014年10月,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20]这一论述为乡规民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道路。
时值当下,要注重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乡规民约进行改造和扬弃,保留精华,祛除糟粕,乡规民约必然能焕发出勃勃生机。乡规民约萌生于陕西关中的蓝田县,发源于北宋,兴盛于明清,延续于民国,千百年来,深深扎根于国人的心中,即便我国的法治建设日益完善,但乡规民约始终能在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那就是作为法律规范的有益补充,服务于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构建法治中国的伟大征程中,既要用“国家法”为乡规民约的新发展建好顶层设计,又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规民约发展的新风尚,同时强化乡规民约的执行能力,使乡规民约免于沦为一纸空文。唯有如此,才能从乡规民约中汲取满满的正能量,充分挖掘乡规民约之中的“德治”因素,使之与现代法治相结合,早日实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大治局面。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6.
[2]姜裕富.村规民约的效力:道德压制,抑或法律威慑[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2-66.
[3]周家明,刘祖云.传统乡规民约何以可能——兼论乡规民约治理的条件[J].民俗研究,2013(5):65-70.
[4]周俊华,刘素燕.研究者视角下乡规民约的理论发展与演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26-134.
[5]周铁涛.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J].求实,2017(5):89-96.
[6]杨建华.传统基层社会治理文化的现代转型[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5):90-94.
[7]沈费伟.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33-140.
[8]李如冰,宋代蓝田四吕及其著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3.
[9]徐红映,孙琼欢.村民参与乡规民约的影响因素及激励机制研究——以宁波市为例[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党报,2017(2):100-106.
[10]余治平.乡规民约与美政风俗——儒家乡村社会治理中以礼化俗的维度[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5-15.
[11]刘笃才.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引论[J].法学研究,2016(1):135-147.
[12]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10.
[13]耿波.乡规民约治下的社区传统与城镇化调适[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3):26-30.
[14]刘志奇,李俊奎.中国乡规民约研究80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40-146.
[15]周铁涛.村规民约的当代形态及其乡村治理功能[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49-55.
[16]周铁涛.法律多元视角下乡规民约的嬗变[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1):97-101.
[17]黄霞.传统乡规民约的基层社会治理与现代转换价值[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28-132.
[18]范忠信.武乾.余钊飞,等.枫桥经验与法治型新农村建设[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20.
[19]刘志奇,李俊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规民约的创新与重构——以河北省林西县为例[J].河北学刊,2018(1):212-216.
[2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