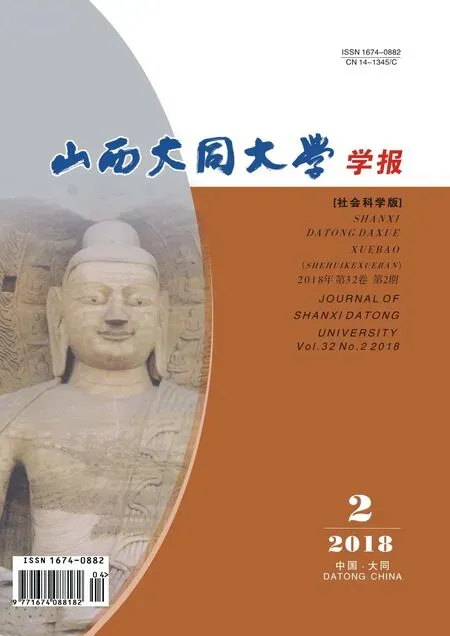西方的理性与哲学理性
孙 卓,常 江
(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一、理性的本质
理性源于代表本源“逻格斯”一词的“本一”,从而形成了寻找这个“本一”的一个无穷无尽的探索过程。理性历经理性主义的曙光、神学时代、文艺复兴与启蒙、工具理性及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从对事物的否定与怀疑,再达自粗到精的总结。所以,探求本质是原初的一个无形的“逻格斯”,又在不同的时期产生的一次飞跃的一个形而上学的演进。后现代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但其非理性地探索理性的方法依然是形而上学式的探索理性的探索。
首先,鉴于理性的发展历史,理性在不同的时代因有其局限性从而导致其概念的特殊性。但显著标志是:后时代的理性是进步的理性,后时代人们对理性的理解超过前时代人们对理性的探索。理性是与生产力相连接的,没有生产力的时代发展,便没有理性的进步。
其次,具有初步生产力的社会的城邦时代,是一个依据于城邦的文化模式从而使个体和公共的精神理念逐渐进入人的头脑时期,理性的探索是集体的公众精神高于个体,且在道德上追求一种公众的善的理念。国家建立时的理性探索是一个追求正义、自由和正当的现实国家秩序的管理步入理性的理念;工业革命时代的理性是一个具有科技掩盖文明精神价值和过度崇拜科技的理性;现代的理性是人们对工具理性的反省,又是一个各学科分离又相交的科技理性,理性不再仅仅是公平、公正、自由的探索和工具科技的盲崇,而是两个领域的综合。理性是精神文明价值倡导下的科技时代进步,各学科交融的一个时代理性。
从而观之,理性是一个时代超越对先前理性的认知和否定。理性是形而上学去寻求“本一”而实现的一次蜕变,又是需要辩证统一的指导从而寻找飞跃的理性。理性是对先前理性的批判、否定,与之相比的辩证、理智和超越。
二、西方理性自身的演进
(一)西方理性在曙光后的自我否定 万物的真正发展都离不开否定之否定的理论模式。在西方公元前500年后理性的自我否定时期,人们对理性的探讨是以否定理性的具体到抽象的理论,其目标是再寻求一个与所否定的具体理性不一样的具体的理性。进而通过对自我的否定来寻求理性的本质。
首先,人们对世界的生成本质与理性曙光时期的理性的理论争论。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数纳入了理性,提出数是构成万物的本源,开创了对理性曙光时期的否定。泰勒斯的水是万物本源的理念和赫拉克利特的火本源说及阿纳克西美尼的气本源等是理性曙光时期探索理性的代表。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本源,对理性的深层探讨,从实质物之间的关系的抽象数理论原则解释事物生成本质,提出有限空间对无限空间的添加来限定空间无限优于有限的非实质物质本源的学说——本质归一为数。数字是先于事物而存在并构成事物的一个基本的单元。理性曙光后的自我否定,是一种以理性的自我否定,来看待理性认知的进步性的内在否定。如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的形式产生于“一”的万物之本,巴门尼德的形而上学的论证形式的探索事物本质规律,恩培多科勒时期的物理、自然和科学等知识类别的划分,均是知识理性的进步发展。古希腊人以他们擅长的原创性优势将所学的东西转化成新的东西,能够以原创性特点来批判地继承先前的理论知识智慧,是理性自我否定的证明。如水本源说、无定说、气本源说和火本源说,是理性曙光时期的最高的本体理性形象物质的本源,并没有抽象思维的辩证的形而上学。当“逻格斯说”与“生成辩证法”到来,才有了初级的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理论来讲,“本一”既是“逻格斯”作为本质规律的概念和生成辩证法的演变,标志着理性的新探索。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本源学说倡导人们,学习各种事物必须从数的演进中寻求最高的善的本质,更是一个抽象的寻求真理的进步。道德的本质需要实践,而道德“好”的概念最终也就是到柏拉图“善”的理念的形而上学中去探索。即何为“善”?善是在形而上学的思考中寻求最终理性的本质。当良心、价值、好坏等德性开始形成人们对其把握程度与认知理性的时候,人们对理性的充分认识度也明显提高。当理性在伦理与实践上的把握已经有了科学进步的时候,无论毕达哥拉斯将数纳入科学的理性,逻格斯说,生成辩证法,柏拉图的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或是伦理学的形成,都是对理性曙光时期理性的自我否定的一个尝试。理性从合理的肯定到其自我否定及经过否定之后又探寻的还是理性。人类只是在寻找、否定与批判的过程中探求真正的理性。
其次,智者运动对理性自我否定的影响。早期哲学家以寻求真理为要务,但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智者派们以否定唯一真理和提出相对真理的标准,把知识与真理归为因人而异的观点。“理性的见识所具有的真理对所有的人是相同的,但是,人自身所是的真理,使人的信念清澈明晰的真理,却在人与人之间各不相同。”[1](P67)即人对真理的思考是不相同的,且“拒斥任何以外部权威而强加给他的信仰与信念。”[1](P67)必然就会有精神信仰的变化,正印证了人们对以往真理的认识转变。由此智者们的智者运动片面扩大感觉的相对性与主观性,文明在理性的自我否定时代就会有文明危机,而“危机体现为对信心的缺乏”,[1](P62)人们的道德在城邦时代到底是没有一个最终统一的概念。城邦是一个不能像国家一样,用统一的思想执行的权利和权威来驾驭人们的伦理实践的一个集体,这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00年的城邦文化的限制。显出人类对当时理性信念的否定意识的印记,也必然为以反理性而寻理性起铺垫的作用。且“另一种关于世界的运动”,[1](P5)使人们有一个对现实表象世界的形象之外的探索,因为表象世界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普通的理性信念的拥有,也不能满足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支撑。所以予以一个现实的表象世界,人们也开始有了一个理性的世界,才会有另一种关于世界运动的探讨,关于人们见到的表象世界之外的理性世界的寻求,是对现实理性自身的否定而寻求进一步抽象的理性认知。“他们自己的时代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同于它之前的时代”。[1](P5-6)
再次,人们不能达到对理性认知的中和而过犹不及。西方出现了理性的自我否定时,又必然在人们的不同否定中走向统一而进入神学时代。因为“以一种形式的分离到另一种形式的分离”,[1](P9)那么,前一种分离是理性到自我否定,后一种分离是理性自我否定后的发展形式。古希腊人运用原创性,将所学周边民族的优越文明以其自身创造的风格而独树一帜,以否定批判先前的理性而发现理性。自然、科学、物理、生物、伦理、政治等,都在形成一个城邦文化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由于没有统一的思想权威理性共识的城邦文化的局限,一个个具体的理性认知的科学概念并不能形成一个与其不一样的抽象具体。善恶是个人善的牺牲来充实集体的善,是个人善与恶的测评,还是集体价值的善恶的估测?在形而上学自然科学理性的光辉下,人们能不能有一个理性认知的思考呢?即科学是真正的中和与变通的,而非一味地形而上学的探索从而导致越过中和的进步的理性。
由此观之,这时期的理性不是单一的有组织的合作,而是有了个体自我主体性认识的理性的自我否定,是形式的新颖且富有时代创新的转换,但所有的个体主体性的不同,证明神学占用理性的时代的到来是一种趋势的必然。
(二)经院神学理论对理性的遮蔽与时代作用 公元1世纪,神学因人们对理性探索的局限而渗透人们的精神世界并形成一股力量。“基督教就这样渐渐地颠覆了统治阶级赖以延续的那种自成一体的异教精神”。[2](P193)宗教神学开始作为一股统治力量崛起并遮蔽理性。因此“基督教在一片衰败中出现了,践踏那些值得延续的观念。”[2](P193)即人对理性的认知。人们曾对理性进行自我否定的认知,又在善与恶中对终极的善陷入迷惘且受到恶的干扰,希望在理性下拥有理性的自由、思想、良心、欲望、善、价值等。当人在这些方面形成了形而上学的困惑时,神学经院理论开始宣传意志自由的信仰和道德。这也是神学能在几个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在基督教兴盛的一千年里,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人类研究的对象总是上帝。”[2](P194)渐渐地神学时代的经院神学理论对理性进行严重压制,教会开启了主宰中世纪的现象。虽然,卢梭直言道:“为了使人类恢复尝试,就必须来一场革命。”但是这革命的力量还不能使理性重登舞台。
第一,神学对理性的遮蔽压迫。中世纪是神学统治的黑暗的中古时代。基督教从被迫害者变成了迫害者,开始了对异教的破坏和对异种学说的压制。凡是与基督教教义思想相异的学说,即便是先进的科学思想均受到基督教的践踏。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布鲁诺的“日心说”、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等,因与教会的教义相悖而遭受经院神学的压迫。在受柏拉图理念主义的影响维实在论优于唯名论的年代,主张普遍、一般是真实的真理先于个人而存在。个人的精神价值必须服从公共的神学主题精神价值,人们在维实在论的理念下,寻求先于个人的一般的统一的普遍的公众的主题,而具有经院神学理论的基督教则穿过这一缝隙,走向统一人们思想的维实在论理念。个人先于一般与普遍的“维名论”还不占主流地位,个人的智慧被扭曲,新的理性的科学被压制。经院神学宣传的信仰、精神、虔诚、善都是损害个人自由意志来渲染教义的德性。道德是教会在个人没有能力评估自己的好与坏的概念下的教会精神。自由只是经院神学理念下的神学的自由,是先于个人自由而使人并无自由的选择,且只有对上帝崇拜的唯一自由意志。
第二,经院神学时代所体现的另一面。虽然中世纪神学遮蔽着理性,以其思想统治着西方几个世纪,但理性并没有消失,且神学也是在变相地继承与利用理性来使神学顺应那个时代,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在后来的若干个世纪里,基督教也是一支建设性的文明教化力量,其积极作用远远大于启蒙哲人所承认的程度。”[2](P196)因此,中世纪神学世纪有其遮蔽理性曙光的一面,但也发挥着人类文明的另一面作用。而且,理性只是处于被遮蔽的状况,是一个类似于观察者的温和角色的身份站立着的,以一股蓄力待发的势力等待着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的到来。
(三)人们对工具理性的“盲崇”和反思 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到来,宗教神学渐渐地失去了其统治者的地位。在承上启下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开拓下,人类的文明更为开化,直至后来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从哲学走向了科技。然而在几次的工业革命后,人们对工业创造物质的满足导致对工具理性的盲崇,同时,工业革命的创新导致学科的分立,更是向工具理性的目标迈进,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愿望而创造一种所谓的工具理性,此时的理性并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是一种盲崇。
第一,个人先于普遍的唯名论思潮的兴起。当唯名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战胜维实在论而占据时代主流思想的时候,个人先于一般和普遍而存在的理念强调人的主观能力和特点,人对自由的追求就应运而生,并倡导开创性与自由性。个人的优先性就是自由的优先性,伴随工业革命的工具理性也就是这个时代的自由的创新的理性。人们自由地创造出先进的科学工具,满足自己的物质文化需求。生活、交通、军事、医疗等领域都有科技的理性,创造了古代与中古时代不可想象的财富。人们开始享受这些由科技理性创造而来的财富,并开始一味地欣赏和依赖科技理性,从而丢失了人类本应有的一种信念。
第二,拜物教的演进。当人们盲目崇拜科技理性的光芒而享受物质的时候,一个迈向金钱至上的拜物教的趋向在此时的欧洲已经蔓延,人们渐渐地丢弃了古典时代的理性探索,甚至彻底丢弃中古时代神学理念的价值,完全投入到对科学工具的依赖与崇拜。其最终结果是:工具理性在人们的头脑中大于伦理下的道德律,大于哲学意义上的理性的形而上学与辩证的探索。
第三,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当人们沉迷于工具理性带来的物质文化充足的享受中时,违背自然的反面威胁应运而来,众所周知的工业革命时代的伦敦雾霾,科技军事扩张带来的战乱绵绵,与其说两次世界大战是军事较量,不如说是科技的工具理性的滥用带来的人类灾害。在科技理性带来方便、先进、快速的时候,人们并没有用古典主义的传统理性去指导科技的工具理性。一个没有正义的规范下的自由,只能是功利主义,必然是工具理性的科技盲目崇拜。
总体讲,工具理性是在理性的复兴下延伸出的科技理性,导致人对工具理性的盲崇。人们对工具理性盲崇的结果并没有将所有的不一样的先进成果进行“和而不同”的创新与融合,反而为寻求科技工具的满足而导致了过犹不及,结果必然是理性的反思。
三、中国当今的发展对理性的把握探索
我国倡导市场经济一体化、国际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理性的把握,必须予以怀疑式、否定的理性态度去看待事物。我国在探讨寻求理性时就必须与时俱进地寻找新时代的理性,从而实现对过往时代理性的超越,在新时代中把握理性的本质。针对后现代主义的优势与缺陷的总结,我国可尝试探索后后现代主义,即继承后现代主义的相对原则去看问题,又要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去探索理性的本质,那么后后现代主义就是一个以相对方法寻找“非非理性”去实现一次理性的飞跃,又以形而上学式的对理性加以分析、思考,从而做到相对的统一,进而探索一个后后现代主义的新的理性。
(一)摒弃科技工具理性的盲崇 科技是生产力,是伴随生产力的脚步而发展的,不顺应这一潮流势必被时代的车轮所淘汰。但是,我国不能忘记西方曾经对工具理性过度依赖而受到自然的惩罚的前车之鉴。倘若我们只是崇拜科技带来的辉煌,势必有拜物教的盛行从而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与浪费和环境污染难以治理的困境。工具理性在理论层面讲,会在自然学科的各个领域有一个提升,毕竟是科技引领的一种理性的科技文化。但从现实发展实践的层面讲,工具理性的过度会导致对物质的要求过度、对资源的索取过重,其结果是索取未来。
(二)我国经济的发展需以辩证的“非非理性”去实践 后现代主义倡导非理性去实践,其目标还是寻求探索不一样的理性。而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我国既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又要做好国家的宏观调控的杠杆作用。然而在国家的杠杆发挥与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又要在国际市场的体系中,怎么能够将国家管理与市场机制二者合一而有效运行?这不仅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理性的价值的深思。纵观西方传统理性的发展与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的利弊,将二者的融合就是我们经济发展而尝试的“非非理性”,“非非理性”是一个以形而上学探索理性的方式,既尊重主体价值的主体性又不失辩证探索的真理性。
(三)我国倡导“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与理性的探索相结合 现如今,中国的社会大力倡导“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战略工程的建设中,我国对于在实践中理性的把握至关重要。我国面对“四个全面”的工程建设,可以学习后现代对先前理性批判的精神去探索一种后后现代主义的理性,从而把握理性的本质,实现一次超越。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凡是理论引导神秘主义方向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P135-136)这个神秘的东西就是我们在探索过程中需要寻找的理性。“四个全面”的战略工程就有了理性的指导,有了实践过程中的理性的监督。
一个新的理论总结,一个新的精神境界,一个新的发展蓝图,这三者的综合点就是探索后后现代主义的新时代中的真正的理性。
参考文献:
[1](德)雅斯贝斯著,王德峰译.时代精神状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美)盖伊著,刘北成译.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