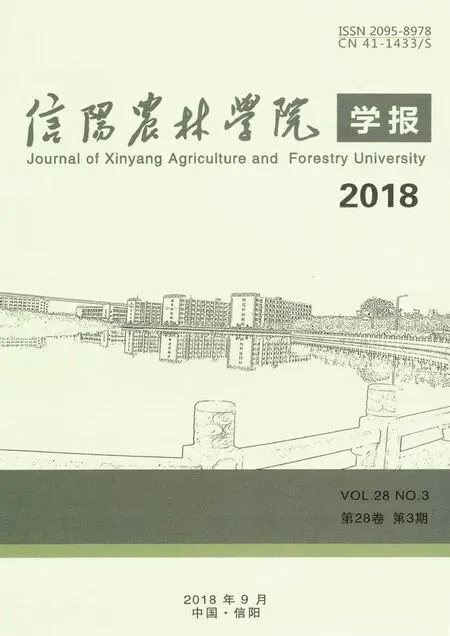女性主义翻译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以《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杨 姝
(西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从翻译研究历史来看,人们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起步较晚,谈到译者时,对于其性别一直默认为男性。且在传统翻译理论背景下,原文和原作者被视为中心,而译文与译者则处于被动地位,造成了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现象。但自女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崛起以来,就有倡导女性主义思想的前人提倡摒弃传统的翻译理念,认为“翻译不是简单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无限的文本链与话语链中的意义的不断续的延伸。这样翻译就如同彰显了译者主体性的写作行为,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改写行为。当翻译研究逐渐转向文化后,译者主体逐渐获得更多关注,成为翻译研究的新焦点”[1]。之后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主义与翻译理论进一步结合促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女性主义翻译观,弘扬“创造性叛逆”及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到翻译实践中[2]。本文旨在从女性译者的主体性,即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下的译者主体性视角,针对文本《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不同性别译者的汉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来研究女性译者在翻译作品中区别于男性译者的译者主体性的具体表现。
1 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人文品格、自觉文化意识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是其基本特征。”[3]在文学翻译的直观过程中,作者为创作主体,读者为审美主体,而译者既是审美主体又是深层次上的创作主体;文本细分为原文本和译本。作为翻译焦点的主体,译者的作用在于对原文进行审美阅读和理解,并将这种体验通过创造传达给译语读者。
历史上,17世纪的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泰特勒曾针对译者主体性提出了相关翻译原则,即译作无论是风格、思想还是表达都应尽量向原作靠近;而18世纪普希金与别林斯基则都认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于译者翻译上的灵活,而不是逐字面译;尤其是法国的德·阿伯兰库着重强调在表达原作意思的前提下,可大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色彩,与当时重视原作者主体性权威的传统译论大相庭径。总体而言,译者在翻译研究史上长期受到忽视,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直到“文化转向”的出现,该问题逐渐得到了关注。
长期以来,在传统翻译理论支配下的话语都带有明显的性别和等级化色彩,而后现代的翻译理论,如女性主义翻译论的出现则要推翻这种话语,并扩宽对译者主体的界定,加深对其的认识,尤其是对译者主体的文化身份和“双重作者”的责任的认识。女性主义写作要求发挥女性写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在与翻译结合之下,更加要求突出女性译者的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赋予译者主体性方面的独特性,一方面在于其将以往受到忽视的译者性别因素列入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范畴,并对这方面进行新的阐述,以揭示性别在翻译中的作用及影响;另一方面在于女性译者通过宣扬其自身译者主体性,从而达到将翻译重写的目的,以反抗以男性为中心和对女性带有歧视倾向的文本传统译论,突显女性在翻译文本中的地位,以此影响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界定[4]。
2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曾针对传统译论中译者的“隐形”提出质疑,要求重新界定翻译行为的主体——译者。更有激进的前人学者戈达尔德发表言论:“在女性主义理论的话语中,翻译是生产,不是再生产。”[5]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突出自己对文本的操纵,她们提倡“重写”(rewriting),在翻译文本时进行大量的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和色彩的干预及改写。具体涉及到的翻译策略主要有三种:一是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例如,在戈达德的翻译中,她在前言中解释原文意旨并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让读者充分了解并关注其女性身份;二是增补(supplementing), 即针对原文本语与译者语之间的差异进行翻译上的增补,在此过程中基于自己的性别前提进行创造性改写,例如HuMan中用大写M来强调译者想体现的原文的男性中心主义;三是劫持(hijacking),指女性译者针对原文本中出现的不符合其自身观点和表达的地方进行符合自己主观意图的翻译改写。如哈伍德(Hardwood)所言:“我的翻译是一种让语言为女性说话的政治活动,如果一部翻译作品有我的署名, 就说明我已采用了一切翻译手段让语言女性化。”[6]在这种思想引导下,女性主义译者对原文的劫持策略使用是不可避免的。
3 《了不起的盖茨比》两中译本对比分析
本论文选取的第一译本的女性译者林慧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第二译本的男性译者姚乃强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译著有《红字》 《了不起的盖茨比》等。选择《了不起的盖茨比》两个不同性别译者的中译本进行对比分析,目的在于从译者主体性发挥的角度出发,挖掘女性主义译者与男性译者在文本翻译上的不同,主要落实到女性主义译者对比男性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如前言和脚注、增补、劫持等,从而挖掘出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具体表现。
3.1 加写前言和脚注
3.1.1 前言
在对比分析女性译者林慧及男性译者姚乃强的前言过程中,发现两者都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的翻译策略和意图,都将视角着重放到了对原著内容、背景的介绍上。但从具体描述来看,在前半部分,女性译者林慧在前言中对原著人物的性格和象征意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介绍,体现出女性相对于男性译者更为微观细腻的一面,从而更为丰富地传达了女性译者试图向读者传达其对原著中隐含的抽象概念的理解,例如:“小说中, 盖茨比经常以神话的、诗化的形象出现,菲茨杰拉德赋予了他太阳神阿波罗的特征”,“菲茨杰拉德也把盖茨比和基督教神话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被欺骗的亚当,最后从他的伊甸园中堕入人世的现实”[7]。而男性译者姚乃强则着重从宏观上分析该著作的背景由来,以及表象后反映的作者的中心思想,例如:“从表面上看,《盖茨比》只是‘爵士时代’的一个画面或插曲……但是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直觉地感受到菲氏对于二十年代表面繁荣的忧心……”[8]。
在后半段,两位译者都共同将视角转移到对“美国梦”的介绍和文章中主人公体现其概念的分析上。 女性译者林慧在结合原文本内容的前提下,进一步抒发了自身对于该概念于当下时代的深层理解,体现出女性译者的细腻分析角度,着重将“美国梦”这个概念联系小说中人物所处的背景、盖茨比的心理活动、个人经历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延伸引发了对小说背景下新的物质消费主义理念的讨论,如:“菲茨杰拉德把盖茨比和黛西的浪漫爱情建筑在消费文化的氛围之中。爱情在这里被贪婪的物质占有欲所玷污”。而男性译者姚乃强则主要立足于文本对此概念进行分析,没有更进一步进行自我解说。姚乃强在结合“美国梦”分析主人公经历的部分,只是简要地表达了他看到的小说中体现“美国梦”的地方,如“盖茨比年轻时写下的自勉箴言实际上就是富兰克林等人的教诲和美国梦……在黛西身上,盖茨比的梦想变得有血有肉……盖茨比一心向往的未来已不复存在,他那个在农业社会里培育的梦想——美国梦——已经烟消云散”。
在最后部分,女性译者林慧与男性译者姚乃强都涉及到了原著中东部西部地理位置间的象征意义差异,以及东埃格村和西埃格村代表的象征意义的不同。在具体观点阐述上,女性译者林慧在抒写前言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向读者展示自己对文章理解的分析过程,倾向于结合自己对人物性格特征的了解来分析文章具有象征意义的背景,如:“东埃格代表的是老牌贵族,而西埃格则是暴发的新贵。在菲茨杰拉德笔下,西埃格的新贵们庸俗、华丽、招摇,缺乏风度和品味,例如盖茨比……相反,老贵族们则有教养、有风度、有品味,就像布坎南家装饰雅致的住宅,以及黛西和乔丹·贝克尔飘拂的白色衣裙”。而男性译者姚乃强则直接指出文章背景的象征意义,从此角度分析小说中出现的背景,如:“东埃格村和西埃格村,纽约市和灰土谷……两者隔着一个海湾对峙着,‘一交锋便撞得粉身碎骨’。这个冲撞代表了新旧两种财富拥有者之间,梦想和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东、西埃格村,埃格村(egg)在英语里是‘鸡蛋’之意,它表示脆弱易破,不堪一击”。
3.1.2 脚注
加写脚注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同前言一样同样会采用的策略,由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上的不同,外国文学中时常会出现许多中国读者难以理解的典故、俗语及地名等,需要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帮助理解。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加写脚注,有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原文意图。而该策略在女性译者林慧的译本中得到了更多体现。
例1 原文:“I graduated from New Haven1 in 1915…and a little later I participated in that delayed Teutonic migration2 known as the Great War.”[9]
[林慧译本]:“我1915年毕业于纽黑文①,距我父亲毕业刚好二十五年,稍后,我参加了那场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类似推迟的条顿民族大迁徙②的战争。”
①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南部港市,为耶鲁大学所在地。
②条顿族为上古时期居住在欧洲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交战双方德国、奥匈帝国和英国、美国的军队大多可称作条顿族后裔而被戏称为“推迟的条顿民族大迁徙”。
[姚乃强译本]:“我一九一五年从纽黑文①毕业,恰好距我父亲毕业晚四分之一个世纪,稍后我参加了被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被推迟了的条顿民族大迁徙。”
①纽黑文,美国康涅狄格州海港城市,耶鲁大学校址所在地。
从中可以看出,女性译者林慧在脚注上相较男性译者姚乃强更为细致,针对国内读者可能大多不了解的“条顿民族大迁徙”进行了详细的脚注注释,介绍了其含义以及历史由来,而姚乃强则没有添加脚注解释。
例2 原文:“They are not perfect ovals——like the egg in the Columbus story1, they are both crushed flat at the contact end…”
[林慧译本]:“它们并非标准的椭圆形——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①一样,与大陆相接的地方都被压成扁平状了…”
①指西方广为流传的一个传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返回欧洲后,有人贬低他的作为,说任何人都会驾船往西发现新大陆。哥伦布便请此人将一个鸡蛋立于桌上,此人屡试屡败。哥伦布遂将鸡蛋的一端砸破,立在桌上,以此说明在他演示之后,别人才会驾船西行。
[姚乃强译本]:“它们并不是正椭圆形的,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一样,在与大陆连接的那一端给敲碎扁平形了。”
从中可看出女性译者针对文本中涉及到的传说典故增加了脚注,并进行了详细的故事讲述,方便读者了解背景中的文化知识,而男性译者则没有加脚注进行解释。
上述两例说明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相较男性译者更倾向于运用脚注的翻译策略,通过对原文的补充说明,向读者传达有关译者自身对该文本的理解过程,建立起从作者到译者再到读者的认知联系,体现了女性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更加彰显了女性译者“译者主体性”的概念。
3.2 增补
“增补”是针对两种语言间的差异进行信息修改的翻译策略。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倾向于针对原文本中体现男性中心主义和男权思想的地方进行修改性质的翻译,以替换或补充原著中存在的性别差异,来唤醒人们在性别压迫上的认知。
例1 原文:“‘We’ve got to beat them down,’whispered Daisy, winking ferociously toward the fervent sun.”
[姚乃强译本]:“‘我们得打败他们。’黛西轻轻地说,眼睛对着晚霞猛眨。”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在翻译“we’ve got to”这种在文中展示出女主人公黛西态度的表达上,女性译者林慧通过“我们一定要”这样坚定的语气表达,较男性译者姚乃强更为精髓地翻出了黛西的内心活动。对前文汤姆所提到的《有色帝国的崛起》书中“如果我们白人不警惕的话,我们白种人就会被彻底淹没”的观点,黛西表达了对自身高贵白人身份的认可的同时,也反映了她对其他有色人种的蔑视。后半句对太阳眨眼睛的动作描述,女性译者用程度副词“狠狠地”刻画出了黛西当时受汤姆言论影响,表现出的坚定态度。这种以女性视角对书中女性角色内心活动的增译描写,正是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的表现,突出了角色的性格和心理活动,是男性译者未曾注意到的。
例2 原文:“‘Ten o’clock,’she remarked, apparently finding the time on the ceiling.‘Time for this good girl to go to bed.’”
[林慧译本]:“‘10点了,’她说,好像从天花板上看到了时间,‘我这个乖女孩要去睡觉了。’”
[姚乃强译本]:“‘十点钟了,’她说道,好像在天花板上看到了时间,‘乖女孩去睡觉了。’”
从中对比可发现两位译者差异在于后半句对“good girl”的翻译上。女性译者针对这种涉及到女性、女孩且带有正面评价的词汇,在翻出其本意“好女孩”的基础上,在前面又增补了第一人称字词“我”,以突出“我”这个“好女孩”的身份,意图将角色的女性主义身份在此放大强调,显现出了译者本人想要提高女性地位的倾向,发挥了其译者主体性。而男性译者只是按照原文字面意思逐字进行翻译,并没强调文章中女性身份的存在。
从以上例子可看出,虽然男性译者在翻译原著中没有明显的压迫和轻视女性的表现,但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相对而言会更加重视在原文本中对女性角色的心理刻画,比如以“增补”这种策略来凸显女性形象,传递给读者原著以外被赋予的新的女性主义视角的情感。
A厂NOx原始值300~350 mg/m3,正常工况下,烟气再循环比例控制在15%~20%,在不采用SNCR的情况下,烟囱入口NOx浓度可控制在250 mg/m3以下,达到GB 18485—2014的排放要求。图4为一段时间内不同循环比例对应的锅炉出口NOx浓度(SNCR不投运)。从图4可知,随着再循环比例的增大,NOx的浓度明显降低,循环比例达到20%时,1#炉 NOx低于 200 mg/m3,达到欧盟2010/75/EU的NOx排放要求。
3.3 劫持
“劫持”指的是女性主义译者对原作的挪用,如针对一些不符合女性主义思想,或对其具有蔑视性的表达进行“重写”或赋予更具备女性化的表达的翻译策略。具体参见以下例子[10]。
例1 原文:“Not even the effeminate swank of his riding clothes could hide the enormous power of that body…”
[林慧译本]:“甚至那套有些女性化的花哨的骑马装也藏不住他身体里巨大能量……”
[姚乃强译本]:“即便那套带有女性爱招摇味的骑马装也无法掩饰那魁梧壮实的身躯。”
首先原文涉及到的女性描述词汇“effeminate”本义为“柔弱的、女人气的”,两位译者对其翻译在意思上一致。然而在对形容女性的词汇“swank”的翻译中,女性译者选取了该词中较为中性化的意思“花哨的”,而男性译者采取将其直接翻译成带有贬义色彩的“爱招摇味的”。由此可看出不同性别译者翻译的出发视角有所不同,女性译者采用了“劫持”的翻译策略,对女性主义的正面性进行宣扬,而不像男性译者从其自身男性视角出发,对涉及女性词汇的翻译带有稍微轻视女性的色彩。
例2 原文:“There was a touch of paternal contempt in it, even toward people he liked…”
[林慧译本]:“即便是对他喜欢的人,他也用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口吻……”
[姚乃强译本]:“他说话的声音里有一种老子教训儿子的轻蔑口吻,甚至对他喜欢的人也是如此……”
从译者林慧的版本可看出针对原文本中涉及到男性中心词汇“paternal(父亲的) contempt”的翻译,该女性译者同样采用了“劫持”的翻译策略,避开了表达带有男性色彩的翻译,而是以形容该行为的方式“居高临下的”传达了文章含义,消减了文章中的男性主义色彩;相比之下,译者姚乃强则是将该词“paternal”中包含的父系社会色彩转译出来,翻成了“老子教训儿子的轻蔑口吻”,通过“老子”和“儿子”两大具有浓厚男性主义色彩的词传达了其男性译者的主体性。
总而言之,从以上两例子可看出女性译者在文本中涉及男性中心主义的表达,或者在涉及到贬低女性地位的表达上,会通过采取转换原文意思或避开任何不利于女性主义性别意识宣扬的翻译,赋予读者对女性主义的意识,打破男性话语的专制权,来发挥自身的译者主体性[11]。
4 结语
该文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下译者主体性视角出发,通过对《了不起的盖茨比》两汉译本中不同性别译者的翻译策略对比研究,发现女性译者相较男性译者在译者主体性发挥上有显著的不同。女性译者受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思想引导,在述写前言和脚注部分比男性译者倾向于更多地表达自己对文章人物内心的刻画或对原作核心内容的看法;在翻译过程中,女性译者倾向于通过“增补”策略添加体现女性主义中心的词汇,如通过第一人称词“我”强调女性地位、添加程度副词形容词等来着重描写文中女性角色的内心活动和性格特征;对文章中贬低女性主义的表达进行“劫持性重写”,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达到提高女性译者主体及女性主义思想在读者心中地位的目的。而在这“改写”的翻译过程中,女性译者在原著中有时会过于倾向只关注对文中女性角色的刻画描写,而忽视了对非女性角色内心活动的描写,从而造成文章人物意思传达的不完整理解。 笔者认为,无论是女性译者还是男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培养性别意识,可取得更完美的翻译效果。但同时也要对不同性别代表的理念进行批判吸收,避免性别意识单方面引起的主观偏激思想,将女性主义与男性主义进行适当融合,从而促进翻译理论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