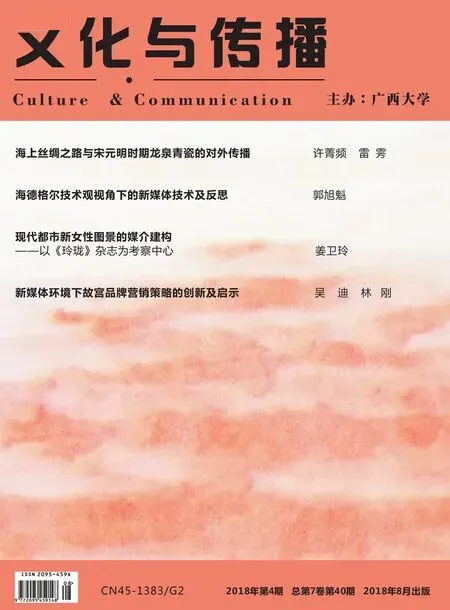从典籍到报章:晚清媒介转型中知识文本的传播偏向研究
阅读报章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报章出现之前中国士林群体阅读的知识文本以圣贤典籍为主,而且这样的阅读习惯绵延了千余年,已经内化到士人身心意识之中,渗透到社会文化之中。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在报章媒介刚刚出现时,晚清士人缘何对于报章所刊载的知识文本采取一种抵制的态度:“社会间又不知报纸为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阅报为子弟勖者。”[1]从阅读典籍到阅读报章转型中的种种争议,恰恰反映了典籍和报章两种媒介传播偏向背后的理念之争。①在伊尼斯在“传播偏向论”中,媒介被分为偏向时间传播与偏向空间传播两类。偏向时间的媒介,譬如镂于金石、刻于泥版上的文字,因为媒介保存性强,可以流传久远。但这种媒介形式十分笨重,运输相对麻烦一些;与此相对偏向空间的媒介,如羊皮纸、莎草纸等媒介形式轻巧,易于空间运输,远距离传播,但这种媒介形式讯息传递效用只局限于短时间之内。这样的总结或许并不那么严谨,却有利于我们来审视媒介的不同特质。其实报章媒介之所以对典籍媒介的书写观念造成巨大影响,与报章传播的媒介偏向有很大关系。见[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7.此中不但牵涉到中国人日常阅读习惯的变化,而且还牵涉到中国社会知识文本的传播路径变化,牵涉到中国士人书写观念的转型问题。
一、典籍媒介与知识文本的纵向传播
传统社会的阅读群体与现代阅读群体有着迥异的文化性征。这与传统典籍媒介的文本生产有关。在传统社会中,只有达官贵人、士人群体才有闲暇和财力阅读典籍,由此阅读也形成了一种等级化色彩的小群体、精英主义的倾向。拜赐于此种典籍媒介时代知识文本的阅读方式,中国的士林群体逐渐形成了纵向传播的“知识共同体”。
1.典籍媒介时代的阅读方式
早期的文本书写,无论是“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之盘盂”,都属于贵族阶层才瞩目的事务,普通人很少接触到这些知识文本,即使后来拜赐于纸张而出现的手抄本,也仅仅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播。从抄本到印本的出现,是基于中国纸和印刷术发明的非凡产物,印本书籍形式扩展了文字著作的受众和内容,使它们更易于知识文本的迁移和传递。吴澄曾经描述雕版印刷对古代士人的影响:“古之书在方册,其编衷繁且重,不能人人有也。京师率口传,而学者以耳受,有终身止通一经者焉。噫!可谓难也已。然其得之也艰,故其学之也精,往往能以所学名其家。纸代方册以来,得书非如古之难,而亦不无传录之勤也。”[2]虽然没有“耳授之艰”“传抄之勤”,但书籍的传播还只能停留在士人之中。
儒家典籍不仅仅是提供知识的一种媒介渠道,而且也是士林群体自我认同的身份象征。报章出现之前,古代的书籍生产多以圣贤典籍为主,其余皆为医疗、种植等实用书籍,或者小说、戏曲等娱乐性书籍。而这些医疗、种植等实用书籍,士人不愿读;小说、戏曲等娱乐书籍士人也不屑读。因此,中国士人阅读的知识文本一般是固定的以儒家文化典籍为中心而展开的,包括《诗经》《尚书》《周礼》《春秋》等等,这些知识文本共同构成了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的经学一元知识谱系。中国士人以孔子为“万世师表”,因此需要熟习儒家经典,正如皮日休所言:“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定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白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3]可见,士人的阅读文本选择范围非常狭窄,不可与报章时代的阅读同日而语。
2.纵向传播的“知识共同体”
《墨子·兼爱》有言曰:“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也?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中国典籍是古代文化的书面载体,通过各种复制技术和阐释方式,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积淀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传教士裨治文对中国人有着很深的理解,他在《中国丛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人对语言和典籍知识的尊重:“只有在他们的语言中才存在统领与调和世界的礼仪和原理,上古时代的圣人们己经把革新的理论通过文字传给他们,他们必须将这些宝贵的遗产代代相传。”[4]
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儒家典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知识结构体系,而这种知识文本因为士林群体的代际传承,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阅读方式和传播现象。孔子时代将典籍所承载的知识通称为“斯文”。《论语·子罕第九》有言:“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将之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这里“斯文”指代的就是上古的典籍传统,后来发展包括书写、言行等方面的传统。士人要掌握这些传统,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以其自身的学术成就和文学写作对之阐幽入微。士林群体像孔子先前通过把斯文当作一种累积的传统加以维系,他们就顺应了事物的自然秩序,接续了上古的文化遗产。这就是儒家典籍所讲的“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承命姿态。在传统媒介影响下的典籍文化中,士人们必须经常阅读《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儒家典籍,这反映文献典籍、礼乐知识等已经成为儒家社会的普世价值,成为士人群体共享的特殊知识。千百年来,传承儒家道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韩愈曾经将道统传承描述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5]之后,诸如韩愈、李翱、皮日休等诸多士人都有着继起斯文的观念,而后世历代士林群体阅读儒家典籍都是继起斯文的行动罢了。
其实,士人阅读文化典籍是一种小范围的知识传承,与大众无关。然而正是如此历代士人通过阅读典籍、解读经书而形成一个儒家的“知识共同体”。这种典籍文献知识,在中国古代只有士人群体才得以学习、分享、传承的,它与民间社会流通的日常生活知识不同。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知识的区别,这里援引曼海姆“日常知识”和“秘传知识”的分类予以解析。曼海姆在探讨知识分子的性质时,谈到知识有两种:“日常知识”和“秘传知识”。“日常知识”是在日常经验的连续过程中,个人总是被迫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当这些问题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出现的时候。他在一些知识的帮助下去对付这些问题,这些知识是他自然地、偶然地、或通过效仿,而不是以自觉的方法得到的。这样积累起来的信息形成了工匠的技艺、生活的经验和处世的手段。士人拥有的不是这种日常知识而是一种秘传知识。我们以孔子的一段话来了解。《论语》曰:“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孔子在这里并非妄自菲薄,他是认为种田、种菜等稼穑知识都只是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生产知识,而士人掌握的是一种士林群体独享的“秘传知识”。所谓“秘传知识”指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产生于秘密的传递渠道中,这种传递渠道在社会形态更复杂的某些国家变成了“教育”的载体。这些秘密传授的世界观不是自然获得的,而是刻意的努力和养成的传统的产物。[6]这种秘传知识,通过士人的引经据典、阅读书写,形成了一个纵向的传承关系,形成一个以圣贤典籍为中心的“知识共同体”。①有人也将这种“知识共同体”称为“文人共和国”。参见[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
二、报章媒介与知识文本的横向传播
现代报刊的出现,打破了典籍媒介时代的知识文本传播状况,也打破了传统社会的阅读方式。报刊媒介日益侵入晚清士林群体的日常生活,即使那些抨击报刊书写的保守文人也不得不通过阅读报刊获取新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更为重要的是,报章媒介时代的知识文本传播已经不再垄断于士林群体之内,而是逐渐扩展到社会大众中间,造就了知识文本横向传播的“信息共同体”。
1.报章媒介时代的阅读革命
作为一种出版工业,报章需要拓展销行渠道,降低经营成本,加快报章流通速度。晚清邮政、运输技术的发展,对报章的发行网络的搭建做出了很大贡献。报馆纷纷设代销点,建立销售网点,报章则极大地提高了发行量和发行空间。譬如《申报》创刊时在上海设了22个代销点,并请人给商号上门送报,雇用报童等措施提高销量。而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对于发行网络的搭建更加重视,借用官方与民间两种力量推行报章,各地官员也都饬札购买《时务报》。譬如两湖总督张之洞要求全省文武大小衙门、各局、各书院、各学堂都要购买《时务报》。《时务报》在中国20多个地区设立197个分销店,并且在海外如日本、槟榔屿、新加坡等地也设有分销处。《申报》、《时务报》等都是上海报章,但销售从上海到遍布全国各地,有的还传销海外。有人如是描述报章销售的盛况:“沪上自风行报纸后,以各报出版皆在清晨,故破晓后,卖报者麋聚于报馆之门,恐后争先,拥挤特甚。甚有门尚未启而卖报人已在外守候者,足征各报销畅之广。”[7]报章媒介的空间化传播,导致人类阅读方式发生了革命。在销行网络的推动下,报章日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传统的书籍生产成本比较昂贵,文字书写也相对古雅,阅读群体自然是小范围的士林群体。而报刊文章是一种廉价的、大众化的印刷品,从士人阶层到下层民众都有财力购买报章进行阅读,也因此阅读报章已经逐渐成为晚清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梁启超有言曰:“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9]缘何如此?因为阅读报章已经成为士人获取世界知识、了解天下大事的重要媒介。正如时人指出的:“别说是做生意的,做手艺的,就是顶呱呱读书的秀才,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坐在家里,没有报看,好像睡在鼓里一般,他乡外府出了倒下天来的集体,也是不能够知道的。”[8]而且报章的种类也满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学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9]
晚清社会的信息传播越来越倚重于报章媒介,因为它每天都为人们提供着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重要信息。譬如综合性大报要“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致夜郎自大,坐普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鳗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力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致抱八股八韵考据辞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9]
典籍媒介时代,圣贤典籍等知识文本可以反复阅读,而周期出版的报章提供的不再是需要含英咀华的知识文本,而变成日新月异的信息文本。报章提供的信息文本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及时的信息,以备日常生活的信息需要。例如,商人经商需要对市场价格信息有的及时的掌握,报章提供了帮助:“苏州商市行情涨落,大致悉依上海市价为准,苏沪商业一气联络。《新闻日报》、《申报》各载省商务类志一项,所有商货行情,随时涨落,立即登报,朝发夕至,近今宁沪铁路货车开行,尤为捷速,是以一切市面与沪市不相上下。”[10]商人依靠报章获取市场信息,而士人则依靠报章学得新知。包天笑在描述自己购报阅读的经验时说:“常常去购买上海报来阅读,虽然只是零零碎碎,因此也略识时事,发为议论,自命新派。也知道外国有许多科学,如什么声、光、化、电之学,在中国书上叫做‘格物’,一知半解,咫闻尺见,于是也说‘中国要自强,必须研究科学’。”[11]
阅读报章不仅改变了晚清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社会公众的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阅读报章可以让士林群体和社会公众感觉到与社会、与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正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有人如是描述看报的习惯:“自出了这《京话日报》,把我害的成了话痨,天天一过了晌午,坐在家里,一语不发,呆呆的盼报,真比上了鸦片烟瘾还厉害,报纸来了,赶紧看完,赶紧对人去说。”[12]已经习惯阅读报章的人倘若一天不读报章,就会产生与世隔绝的失落感觉。中国士人自孔子便养成了“信而好古”的观念,喜欢追慕历史先贤,以历史来考当下,而报章使得国人的思维发生转变,从历史转向现在。
2.横向传播的“信息共同体”
“甲午之后,为吾国社会知有报纸之始。”[13]姚公鹤在梳理上海报业史的时候如是说。何出此言?因为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字林沪报》等报章即时传递了1894-1895年间中日甲午海战的战况信息,借助于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与范围的增加,报刊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制造出了全国上下共同关注、讨论的话题。报刊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和社会场景的传统关系,营造了一种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可以互动的“信息场域”。切特罗姆引用一位报人的话道出报章的横向互动性:“新闻业注定比以往更有影响,及时报道的新闻将给大众的意识带来更多的活力。重大事件的迅速传播将在社区的群众中引起对公众事务的强烈关注—整个国家在同一时间内关注同一事物,从国家的中心到边陲将保持着同一种感情和同一个搏动。”[14]任何一种媒介都会制约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形成特定的知识结构。加拿大媒介研究学者麦克卢汉指出:“书籍是一种个人的自白形式,它给人以‘观点’。报纸是一种群体的自白形式,它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15]传统典籍适合时间上的纵向传播,知识个体的典籍阅读给社会大众以排斥感和隔离感,而报章打破“个人的自白形式”而成为“群体的自白”。根据报刊媒介的传播特征,它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报章造就的是共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儒家典籍的阅读书写造就的是历时的关联,彼此间构成纵向继承系统。
机械印刷、周期出版、大众传播的报章出版使得人们的阅读发生了革命,转型一种横向的空间化传播。报人吴恒炜在《<知新报>缘起》中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16]传统的阅读方式都是一对一的单向阅读方式,阅读者没有多少互动的机会。而报章的阅读者的数量也不受限制,可以同时拥有成千上万的阅读者。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说:“人民阅报之习惯业已养成,凡具文字之知识者,几无不阅报。偶有谈论,辄为报纸上之记载。盖人民渐知个人以外,尚有其他事物足以注意。本来我国人对于‘自己’之观念甚深,而对于社会国家之观念甚薄。‘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之消极人生观,实为我民族积弱之由来。今则渐知自己以外,尚有社会,尚有国家,去真正醒觉之期不远矣。”[17]报章时代的阅读已经从知识的传播转型为一种新闻信息的互动传播。人们每天关注报章可能只是为了通过报章获得信息,改变了观察的视角,将报章放到时间-空间的整体中,报章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存在,形成了一个横向的信息共同体。
报刊传媒改变了传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国家、民族意识的成长。报刊兴起给晚清社会带来的种种变化,其实都是因为它的通上下、达中外的“舒筋通络”功能所造成的。正如《时报》中所说的:“近年来,民智渐开,人心日辟,报馆之创立,时有所闻,报纸之销数日见增广,遇有公共团体之事业,一经报张登载,则遍传全国,加之爱国志士极力提倡,开演说会,以布告同胞,于是通国闻风响应,无不慷慨激昂,是非国民得有长足进步之征验欤,是非近日报章提倡之力欤!”[18]在报章出现之前,很多政治问题只是执政者与上层士人关注的问题,下层群众不会关心。正所谓:“国家之政治,惟天子得主持之,惟公卿、大夫、士得与闻之,而民人则丝毫不能干涉,既不能与闻国事,即只能随国家为转移。”[19]“国家兴亡视为一姓之家事,于多数国民无涉也。”[20]通过报章阅读传播,国家上下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话语空间,不管士林群体还是社会大众都能够对国计民生问题提出的意见参加讨论。可以说,报刊媒介在晚清中国的兴起,适应了当时国家危机存亡之中社会动员的需要,也促成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形成。
三、传播偏向与文人的书写观念调适
从典籍时代到报章时代,媒介转型影响下知识文本的“传播偏向”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从纵向传播的“知识共同体”到横向传播的“信息共同体”,报刊媒介的诞生普及改变的不但是知识文本的传播路径,而且也改变了士林群体的书写观念。士人群体在典籍媒介时代追求“立言不朽”的书写观念,而报章时代已经转变为面向大众的“广而告之”的书写追求。[21]这种书写追求也导致晚清报人做出了引导舆论、顺应媒介的书写调适。
1.引导舆论:晚清报人书写的自我追求
典籍占主导的媒介时代,士林群体的阅读书写是文人圈子内的交流,形成的是一种纵向的“知识共同体”,而到报章时代的写作的空间化迅速传播,使得书写文本面对成分复杂的公众。可见,借用不同的媒介形式,其书写文本的传播效应,包括普及程度、持久程度、准确程度以及可信程度,都会有所不同。徐宝璜也曾经表述报人书写对一国舆论的影响:“在教育普及之国,其国民无分男女老少,平时有不看书者,几无不看新闻纸者,言论行动,多受其影响。至对其记载者,多所怀疑,对其议论,为肯盲信者,固不乏人;然其势力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之上,实为社会教育最有力之机关,亦为公论之事实。自各国民权发达以来,国内大事,多视舆论为转移,而舆论又隐为新闻纸所操纵,如是新闻纸之势力,益不可侮矣。”[22]从典籍到报章,晚清报人书写观念也在逐渐转型。报章的传播可谓“一纸飞行,万众承认”,因此有人将报章成为“社会的公共教科书”,将记者成为“社会的公共教员”,报人的书写也被赋予很高的地位,认为是主持舆论,可以导向国家的前途:“若夫主持舆论,阐发政见、评议时局,常足为一国前途之导向方针也,砥柱也。”[23]在报章出现之前,士人影响社会靠“清议”。所谓“清议”即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臧否人物。钱穆曾经如此阐释“清议”的兴起:“士人在政治、社会上势力之表现,最先则为一种‘清议’。此种清议之力量,影响及于郡国之察举与中央之征辟,隐隐操握到士人进退之标准。而清议势力之成熟,尤其由于太学生之群聚京师。”[24]这种清议在古代受到士人和朝廷的重视,但是它还只是一种小众型的舆论形式,无法覆盖到社会大众。
从典籍时代进入报章时代,士人也逐渐将清议搬到报刊平台上来实现。中国以前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报刊媒介,传统士人的写作往往毕一生之力,汇其所学完成一本著作;古代的“邸报”只是传达信息,却不会刊载士林的清议评论。中国本土最早出现的报纸大多是传教士报章和商业报章,它们为了传教或谋利,尽量不去谈论政治。政论报章兴起是在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之后。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里认为,“迨光绪二十一年,时适中日战后,国人敌忾之心颇盛,强学会之《中外纪闻》与《强学报》,先后刊行于京沪,执笔者皆魁儒硕士,声光炳然。我国人民之发表政论,盖自此始。”[17]借助于报刊媒介,报人书写可以尝试在传统权力系统之外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些报章的政论于阅读者,使得全国信息交流,产生共鸣,由此更促进报人有着“一吐为快”的欲望。在梁启超等报人影响下,士人心有所感,学有所得,常常随机在报章发表,以供知识界共同讨论。士人的思想付诸报端,就会引起士林群体的关注阅读,并会激发士林群体的对话交流,而晚清知识群体批评对话的公共空间也会由此逐渐生成。检视晚清报人群体的思想观点,他们对报章书写都有着“求通”、“合群”的追求。譬如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就谈到报章书写的“去塞求通”之功能,一个国家上下、内外的传播畅不畅通,会影响了国力的强弱。而中国处处充满“壅塞”,想要使得一个国家肌体的血脉畅通,“报馆导其端也”。[9]严复创办《国闻报》,与梁启超有着相同的看法:“《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25]
对报章“求通”的认知也是士人对自我书写价值的调整重构。报章可以通过空间化传播影响到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的人,由此也就形成了新的舆论生态空间:“夫新闻为舆论之母,清议之所从出,左挚国民,右督政府。有利于社会者则鼓吹之,有害于社会则纠正之。社会所疑,昭而析之;社会隔阂,沟而通之。有所褒,则社会荣之,有所贬,则社会羞之。此新闻纸之良知良能也。”[26]《时报》曾经刊发论说,探讨报章传播的舆论效果:“近年来,民智渐开,人心日辟,报馆之创立,时有所闻,报纸之销数日见增广,遇有公共团体之事业,一经报张登载,则遍传全国,加之爱国志士极力提倡,开演说会,以布告同胞,于是通国闻风响应,无不慷慨激昂,是非国民得有长足进步之征验欤,是非近日报章提倡之力欤!”[27]《苏报》发表的一篇时评深入地分析了现代报刊为中国社会开启公共舆论空间的问题:“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舆论何自起,必起于民气之不平,民气之不平,官场有以激之也。是故舆论者,与官场万不能相容者也,既不相容,必生冲突。于是业报馆者以为之监督,曰某事有碍于国民之公利,曰某官不能容于国民,然后官场所忌惮或能逐渐改良以成就多数之幸福。此报馆之天职者,即国民隐托之于报馆者也。”[28]
2.顺应媒介:面向大众的书写调适
既然报人以主持舆论来自我认同,他们就需要探索舆论生产的规律,进而通过报章书写去引导舆论、操控舆论。在报章书写实践中,报人们逐渐认识到报章书写与典籍书写有着不同的书写规则,理性的文章虽然说理至深但应者寥寥,情感激进的文字才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反响。梁启超在晚清报界之所以赢得很大的声望,造成“举国响应”的社会影响,乃是其抓住了报章时代的大众传播规律,善于“笔锋常带情感”的书写。作为执晚清言论界牛耳的新锐报人,梁启超对此并不避讳,他曾经以“极端之议论”为表率,认为“虽稍偏稍激焉耳不为病”。客观来说,粗疏偏激的言论是一种盲目偏信而导致的修辞行为,而在梁启超笔下则是一种自觉的有意为之的修辞追求:“彼始焉骇甲也,吾则示之以倍可骇之乙,则能移其骇甲之心以骇乙,而甲反为习矣。及其骇乙也,吾又示之以数倍可骇之丙,则又移其骇乙之心以骇丙,而乙又为习矣。如是相引,以至无穷。所骇者进一级,则所习者亦进一级。”“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某以为报馆之所以导国民者不可不操此术。”[29]从梁启超的“报馆之所以导国民不可不操此术”话语中,我们出梁启超对于大众传播规律有着清晰的把握,用说理的方式,只能让人明白道理,而用情感化的书写去激发读者,不追求人“坐而思”,但使人迅速“起而行”。
晚清时期,报人蒋智由曾经就报章书写的大众传播规律进行过探讨,他认为有报章书写模式有“冷的文章”与“热的文章”,热的文章“其刺激也强,其兴奋也易,读之使人哀,使人怒,使人勇敢”,而冷的文章“其虑也周,其条理也密,读之使人疑,使人断,使人智慧”。[30]对于“冷的文章”和“热的文章”传播效果的现实认知,让一部分报人开始在报章写作中追求一种激情化、煽情式的修辞方式。这其实也是报人书写中一种自觉的读者意识的体现。所谓读者意识,是指“作者在写作时充分考虑到读者的爱好和需求,并以此来指导,制约自己的写作。”[31]因为报章的空间化传播,报人书写所要面对的对象出现了变化。传统的书写与阅读都是一种私人性的活动。而报章时代的书写,需要面对成分复杂的大众。大众就是传播过程中信息知识的接受者。在传播学中“五W”模式中,接受者是知识文本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尽管是以被动接受者的身份出现,但通过市场消费反过来也影响着传播者的文本生产规则。因此投身报业的士人在报章书写中也要增强对受众趣味的关注。
如果说报章出现之前,士人的书写受道统和正统的影响;而到报章时代,因为报章出版渐渐受到一种商业市场规律的支配,士人的书写需要迎合大众。可见,报章时代的士人书写摆脱政治束缚,但他们在得到书写自主性的同时,也增加了被控制规训的新型规则和隐形力量。作为一种现代大众传媒,报章的出现不单单使得社会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深远的变革,使社会与知识界由于报章而紧密地联系起来,报刊传媒改变了知识的生产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知识圈子,使得士人开始面对一群潜在的陌生而广大的读者。报刊写作因为考虑读者的爱好兴趣,士人的思想情感、态度、行为等方面都相应发生了变化或反应,开始考虑市场意识,读者左右报章书写的现象日益突出。士人开始被看不见的人所控制,书写形式和书写观念也在受到大众影响。不是士人在操纵大众习惯,大众也在操纵着士人。其实,报人书写从私人化书写走向公众书写,要引导大众,但不能顺从大众,当士人惟大众兴趣是求时,也就失去了书写的自我意识。因此有报人如此呼吁:“我们与其以感情的言论,刺激读者的神经,毋宁以有用的智识,开拓读者心胸;与其发表未成熟的主张,使读者跟着走错路,毋宁提供事实的真相,给读者自作主张的底子。换一句话说:我们是舆论的顾问者,而不敢自居舆论的指导者。”[32]
结 语
晚清之季是中国从典籍文化到报章文化的转型时代,投身报业的士人书写始终伴随着一种深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表现为,在顺应报章书写需求、面向大众书写的同时,又留恋传统的典籍文化书写模式,甚至反抗、批评大众化的报章书写观念。报章书写的有效时间短暂,但追求空间化的横向传播,由此也塑成了晚清报人在书写中有着通上下、通内外的“求通”观念。在书籍占主导的媒介时代,书写与阅读都是小众化的,易于培养士人的个体独立化的自我认同,建构了士人群体的纵向“知识共同体”。但报刊媒介的空间化传播,使得信息可以迅速共享,使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个体都能够接受到这一信息,被拉入了一个横向的“信息共同体”中。典籍媒介时代的个体化的书写方式被一种同步互动的书写方式所取代,士人写作不再面对自我或士人群体,而是面对成分更加复杂的大众群体。在晚清中国自典籍到报章的阅读转型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晚清士人书写观念转型的一个具体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