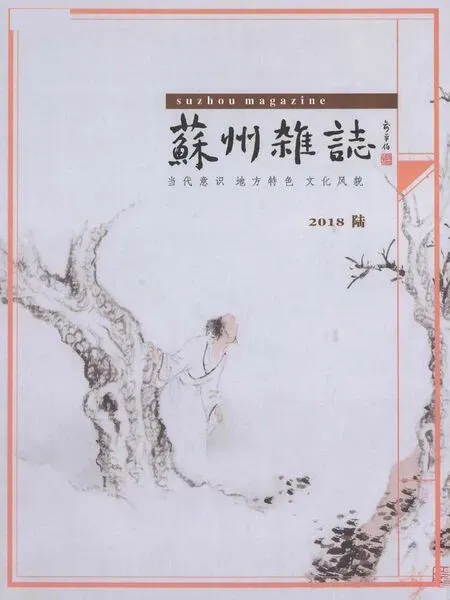旧瓷碎片文字暖
张新文
2016年江苏省太仓市致和塘的一次清淤,可以说改写了太仓的历史,因为,樊泾村元代遗址出土的瓷器量之大,令人叹为观止,从此,太仓不仅仅只是“天下粮仓”,也将拥有“天下瓷仓”的美誉。
太仓是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自古就有“六国码头”之称,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但是记载文字的主体是人,人,又是有个人感情和喜好色彩的,换句话说人对某件事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给他人,或是流传于世的时候,记载与事实往往会出现偏差。可是,樊泾村元代瓷器大量出土与面世,作为物证:太仓的“六国码头”之称谓就当之无愧了!更为惊喜的是,经专家考证如此庞大的瓷器储备库里,存储的全是次品,或是报废的瓷器,按次品的百分之二的比例,由此,可以想像正品的、合格的、好的瓷器量更多,说堆积如山应该是有过之而不及。人们不禁要问,那么多的好的瓷器去了哪里?答案只有两个:除了民用外,大量地通过我们太仓的浏家港都销往了海外。最早销往高丽(朝鲜半岛)、琉球(日本)、中东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明朝郑和下西洋,瓷器远的到达非洲。至今,非洲肯尼亚帕泰岛上有部分人承认自己是中国的后裔,说他们是郑和下西洋的水手与当地人通婚的后代,一个谢姓婆婆手里捧着的碗,动情地诉说着600多年前的这只碗,代代相传,带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体温,一种亲情和温暖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中国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也就是说,我国瓷器的出现至少已经有3600多年的历史。而元代名贵大型青花瓷器精品得以保存下来的极其有限,据说全世界不足200件,所以,本次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实用型的瓷器,供观赏的虽有却极少,而且龙泉窑的产品为主角。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旧瓷碎片,离我们的生活很近,特别是那些碗、盘底部上的字更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从这些瓷器的底部看,元代瓷器明显地厚、重、古、拙,“厚”即胎厚;“重”即体重;“古”即古朴;“拙”即不精细,这是从做工的角度来说。假如藏友在收藏的过程中,如果买入做工精细的元代碗、盘,那就要考虑藏品的真伪了,由于现代电脑技术的应用,仿冒元代瓷器会做得比真品还要“真”,太过精细,就是仿品了。元瓷的造型风格,突出一个“大”字,这与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民族高大、豪爽的性格刚好吻合。另一方面,元代的造瓷业无论从规模到质量较宋代还是衰落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与连年的战争有关。好在元代统治者重视商业,手工业(当然包括制瓷业)和沿海港口的设立,促进了海外贸易;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制瓷业的发展,樊泾村出土的瓷器,也正好说明了这一观点和结论。那么,今天的我们又将如何解读600多年前,这些旧瓷碎片中带着温暖的文字呢?
有的说元代瓷器不落款,理由是元代时期瓷器属于私营手工业范围,没有官窑那么规范。其实,元代后期还是在江西的景德镇设立官窑的,其落款为“枢府”两字。一般来说,瓷器落款有6种:纪年款、堂名款、人名款、吉语款、图案款以及其他特殊款。无论是私窑还是官窑,每个窑口烧出来的瓷器,总要有自己的标识,说明这是我家生产的,而不是他家的产品。
所以,我们从樊泾村元代遗址出土的这些碗(盘)底部的文字,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有些文字和图案,就应该有一枚枚形似印章的器物,在坯胎干、湿适度的时候,一一按一遍,于是就有了“福禄”“和合利市”“福鹿 (禄)”“金玉满堂”“仁山”“仲夫”“叔安”;有的似乎是工匠用篾签所写,有一定的随意性,如“张山”“刘宅”。
更进一步地说,这些文字多是祈福语和吉语,如“福禄”“金玉满堂”“天下太平”等,有的,在碗盘底部,印有双鱼图案,寓意“年年有余”。有的文字应该是窑主的名字,如“仲夫”和“叔安”。古人往往把兄弟从大到小排序:“伯”、“仲”、“叔”、“季”,所以,“仲夫”可能是老二的窑口,“叔安”是老三的窑口。又因为“仲”也是姓氏,如果有人提出,说是“仲”家窑口,恐怕那也不为过。而“叔”虽是姓氏,其仅仅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后没有任何文字可考,《百家姓》亦未列入其中,所以这里的元代“叔”肯定不是姓氏了。一般来说,我国大部分地区,孩子辈称比父亲小的弟弟为“叔叔”,也有一部分地区嫂子称呼丈夫的弟弟为“叔叔”,如潘金莲唤武松就带着挑逗的口吻喊:“叔——叔——”举出如上例子,说明元代瓷器上的“叔安”二字,非“老二”窑口莫属。试想,瓷器是商品,字又有一定的寓意,晚辈买“叔安”碗送给叔叔尚可理解,如果是嫂子特意买个“叔安”碗送给夫之弟,未免暧昧多多,不可理喻了。
至于“张山”和“刘宅”看起来没有用模具印制的字体规范好看,但是从收藏的角度,手写的更具有收藏价值。“刘宅”碗、盘,在销售的对象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刘姓其他姓氏就不会去买了,这也可能是一批应销售商而特殊定制品。
细看落款“张山”两字的这个碎片,不仅瓷厚,表面还坑坑洼洼,做工粗糙至极。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叫张山的工匠随意而为之,并非窑主的刻意安排的行为。造瓷和泥离不开水,所以瓷窑一般建在河流的两岸,“夜阑惊起还乡梦,窑火通明两岸红”(清·郑风仪),在没有电的时代,窑火的通明更彰显了造瓷业的兴隆。瓷业的兴起,吸引了大批天南海北的劳动者,每个漂流在外的人,还乡的唯一通道就是梦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清·沈嘉徴),他们背井离乡,舍弃妻子儿女,来瓷窑讨生活,每天面对着颜色比琼玖的瓷器,他们不羡慕、不动心;他们更多的是思念家乡、牵挂亲人。所以,这个叫张山的工匠,可能是思乡心切,一时起兴居然把自己的名字(也或是自家孩子的名字)写在了瓷器的坯胎上,他没有想到600年后的今天,他的“张山”两字居然神奇般地重见天日,而且将久远地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