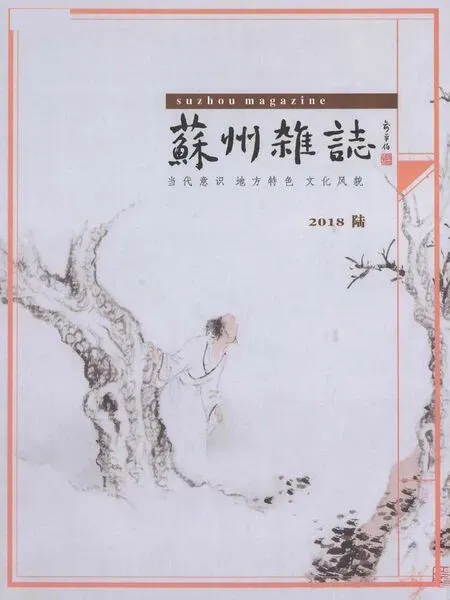易代之际无路可逃
——读《浮世悲欢》
沈慧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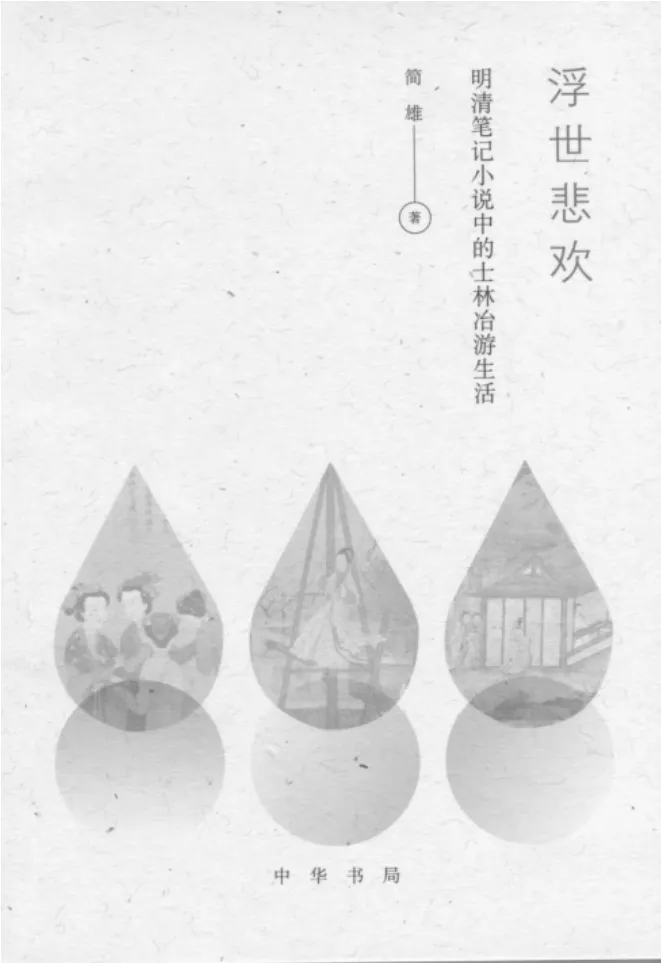
清光绪年间,住在苏州的沈秉成、李鸿裔、顾文彬、吴云等官员们退隐林泉,过着潇洒率性的生活,他们以真率会之名举行雅集,游园赏花、鉴别书画、吟诗作对,推盏换杯之间自然少不了风月场中的女子助兴。她们以侑觞、茗谈、文艺交流的方式活跃气氛,张之万戏赠名为双凤的美姬一联:”双手撩人春十笋,凤头勾客月如弯”,顾文彬嫌其俗气,改为“双手弹筝春十笋,凤头蹴鞠月初钩”;顾文彬为美姝蕙卿撰写嵌字联:“戏评花谱题红蕙,细拣箫材选绿卿”;盛康的侧室因为他另纳欢场女子而河东狮吼,搞得颜面扫地……
士绅们的文艺活动、冶游生活以及支付这些女子的出局费用都被顾文彬一一记在日记中。这些人物的“正史”中绝不会出现这类风流韵事,但纯属私人的文字里留下了他们的另面形象。
日记是个体生活的实录,较之笔记之类更为可信,然笔记之类的作者如果不带个人好恶、以其亲历见闻来客观描述人物与事件,且有相关文献互为印证,那么笔记完全可以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且更为生动地呈现大历史背景下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和庸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使历史更具纵深度与横断面,更接近事实本真。日记、笔记之类如同一面哈哈镜,照射出社会与个体的多面形象,构成社会活动的完整内容,丰富历史画面与个体印痕。
简雄先生在研读七十余种明清笔记的基础上,详加考据,从中提取寇白门与朱国弼、杜韦与范允谦、李成梁与郝文姝、吕宫与蒋四娘等人物故事,继《浮世的晚风》后再次推出新著《浮世悲欢——明清笔记小说中的士林冶游生活》,借助浮世之际的悲欢离合描写各式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命运沉浮,易代之际的艰难抉择与醉生梦死,世风日下后的士林分化与价值取向,生动展示了明清士林冶游生活的真实图景,无情揭示了封建皇权下士林精神的日趋没落。
自古以来涌现无数烈女、节妇,她们作为传统优秀女性的代表载入史册,被后人铭记与颂扬,尽管她们的酸甜苦辣绝不是一座牌坊和一段文字所能概括的。与之相反的一群女性——娼妓,作为道统的批判对象,入不了主流社会,挣不来贞节牌坊,却获得主流社会及其边缘的士林阶层青睐,她们身边不乏追随者,也因文字因缘,不少美姬如贞节女子般名垂青史。世人熟知的秦淮八艳之外还有不少有名或无名的美姝在时人的文字里留下印记,或许她们没有柳如是、董小宛、陈圆圆那样显赫的声名,但她们的命运何其相似,绝大多数人以从良为人生最高目标。

简雄手稿
作为从事出卖色相或才艺的特殊人群,她们依附男人而“合法”存在数千年,相互依存,各取所需;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她们并非孤立的群体,总是不由自主地被时代裹挟而淹没在岁月的尘埃里,但由于文人骚客的推波助澜,尚且遗留些许影子。西方一位哲人说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里暂且不用当下的道德评价体系讨论娼妓存在的合理性,先说说封建社会,其实这是一个知识结构单一、上升通道狭窄而导致文青过剩的时代,读书士子可以通过科举成功而封侯拜相,既可为官做文两不误,更可以成为诗词名家、学者史家,纵然成不了苏轼辈的大家人物,他们也会用笔记录耳闻目睹或亲历之事,以至自古以来留下的诗文、笔记、小说汗牛充栋,士林冶游的故事得以流传。诚如简雄所言“名姬背后的推手是名士”,她们的成名得益于这些时代过剩的文青们。
简雄认为“明中叶以降,士林充分利用自己受教育的背景,通过著书立说、交游结社、清议雅集等形式,以及标新立异、张扬狂狷的做派,深刻影响了社会风气和社会变迁。”确实,士林通过他们的言行,试图掌控社会的话语权、文化的主导权,甚至左右朝堂的决策权,东林党等民间社团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们通过醉卧花丛的形式张扬个性,自我肯定,追求身心解放,寻求心理的慰藉与成功的满足,深刻影响着社会风尚。
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像唐僧的紧箍圈一样自小被套在读书人的头上,“学而优则仕”是他们不懈的终极目标,一旦“货与帝王家”既可以实现人生理想,又能进入主流社会。但现实是残酷的,历朝历代仅有少数人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官场。大多数读书人铩羽而归,十年寒窗付诸东流,即使步入仕途,一不小心就遭罢免,甚至招来杀生之祸。清代诗人沈德潜六十七岁得中进士,生前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宠,死后受文字狱牵连而遭到平坟的“待遇”。
士子们失去上升空间,或开馆授徒,或做个幕僚,或悬壶济世,或热衷于书画艺术、文学创作,诗词笔记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英雄总有用武之地。中国自古文人有狎妓的陋习,女性是他们解忧消遣的尤物,是他们卖弄才情的对象,抑或成为他们的红颜知己,弥补家庭生活缺乏的情趣。他们讴歌中意的风尘美眉,宣传她们的才华,从她们身上折射出他们的另一种面相。
尽管娼妓这个营生并不光彩,但士林阶层或者显贵之家并没有完全轻视她们,有的甚至娶她们为妻妾,如保国公朱国弼迎娶寇白门,晚明名将李成梁纳郝文姝为妾,并视其为得力的秘书;有的在她们落难时想方设法营救,如才子袁枚为名妓金蕊和戴三而求助苏州、镇江地方官员;康熙年间发生陆元公纳妓为妾却被诬告强占人妻案件,富有浪漫情怀的苏州知府杨朝麟以一首格律诗作为判词,将诬告之人“枷号示众”;更有性灵派的袁中道为帮助新安少年纳妓为妾代写打动人心的书信……
从《浮世悲欢》梳理的诸多事例中可以得知,风花雪月和红袖添香是士林冶游生活的重要内容,当道给予包容与“包庇”的态度。作为一个奇特的组合,士林与美姬本质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都想练就十八般武艺,一个渴望货与帝王家,一个千方百计获得“恩客”的青睐,因此他们相互依赖与欣赏,切磋文艺,并观照到彼此内在的脆弱。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鲜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依附于封建皇权生存,以与其的远近亲疏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以“立德、立功、立言”严格要求自己,他们的眼光始终关注高高在上的庙堂,即使身在江湖,风月场是他们暂时逗留休憩与宣泄情感的驿站而已。一旦遇到朝代更迭,带给他们的则是毁灭性打击,男人的气节与女人的贞操一样重要,始终作为评判黑白、是非的标准,降清的文学大家钱谦益终究没有逃脱被列为“贰臣”打入另册的结局,从这点讲失节的士林与失贞的美姬没有两样。
数十年后,曾经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志士们的后代也如先人们那样,胸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走上大清的考场,追逐“货与帝王家”的梦想,先人誓死抗清,后人则积极合作,与现实握手言欢。清初人们强烈反抗留发不留头的苛令,及至民国初年遗老们宁愿拖着“猪尾巴”似的辫子以示对大清的忠贞。不同的时空下,面对性质相同之事,人们已是截然不同的心态与选择,就如意义重大的“气节”两字也是有时间节点的。时间是最好的药剂,可以治疗一切伤痛。士子们在封建强权长期驯服之后,即使心有不甘,也只得以标新立异的方式行走江湖,以诗酒美姬聊以自慰,实现庙堂与江湖、士林与风月的和谐共存。
因此,对士林阶层来说,如果不能在庙堂立功,就在江湖立言。他们吟几首诗,填几阕词,著几篇文,手中有几个钱,无须书号,就可以刻印流传,显满腹才华,纾心中块垒,发失意之愁,抒家国情怀,寻个人兴趣,重要的是还能博得美名传千古。官场不得志的俞樾一生埋头著述,成为一代经学大家,留下传世之作《春在堂全集》。余怀是简雄关注与研究的重要人物,对其晚年隐居苏州的时间、地点、交游等作了翔实而细致的考证,《浮世悲欢》多处引用余怀所著《板桥杂记》的内容。余怀晚年十分看重自己作品的刊行,作者认为他隐居吴门,“以卖文为生,著述自娱”,设法出版,既有出于生计的考虑,也有“立言留世”的愿望。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目标中,人们总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一款。余怀无疑是士子们的缩影。
《浮世悲欢》以明清士林冶游生活为研究主题,呈现了光鲜的历史画卷背后的另一番景象:庙堂之外士林驰骋江湖的侠骨柔情和英雄气短,美姝倾城背后的自在洒脱和凄惨命运,封建强权之下与时代嬗变之际任何个体如蝼蚁般任人践踏而“无路可逃”。在盛世的边缘,即使“英雄多情”“风月侠骨”,他们“琴画诗酒””娱乐至死”,终究“江湖水深”,在无可抗拒与揣测的时代激变面前,有的抗争而死,有的隐逸江湖,有的合作妥协,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是一种无法回避而又徒唤奈何的痛彻心肺的选择。美姬们多数以悲剧收场,士林也好不到哪里去,时光终究不能倒流,庙堂只有一个,而旗号一直周期性地更换,无法立功建业的士子们除了沉沦还是沉沦,而“士林精神的式微首先是因为政治的黑暗与堕落”,简雄如是评说。
——任士林字号、籍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