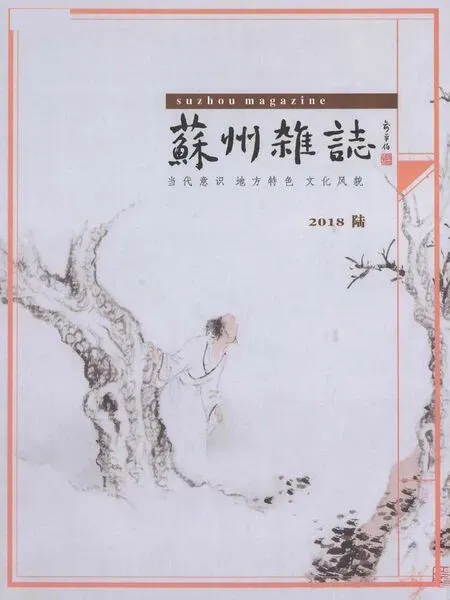《苏州杂志》三十年

点点滴滴在心头
范小青
1988年《苏州杂志》创刊,我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身份》,里边写了一个绰号叫“老隔年”的人物。老隔年的意思就是隔年没死的蚊子。因为一般的蚊子是活不过冬天的,可是这只蚊子活过了冬天,而且不知道活过了多少个冬天,就称之为老隔年。
这个人物就是隔了年的老蚊子,老而不死,活着也不知道自己几岁了,也许他自己是知道的,但他不高兴说出来,就不说。别人不知道,就很稀奇,巷子里多管闲事的人多的是,他们很想知道,千方百计地打听。因为在这条巷子里,老隔年是最早出现在这里的,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来到这条巷子的时候,老隔年已经在了,用他的话说,是早已经在了。
但是自始至终也没有人知道老隔年到底几岁了,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几岁了。
三十年过去,时间也蛮长了,我把这篇小说找出来看看,有点感动,也有点怀疑,感动的是三十年前的小说居然也写得蛮不错的,怀疑的是,这三十年的努力创作努力攀登,难道都是在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写小说这个事情确实蛮难说,无法保证一篇更比一篇好,一年更比一年强。比如像现任的《苏州杂志》陶主编就经常打击我,他好多年前就对我说,你这辈子最好的小说早已经写出来了,你再写,再卖力,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不如不要写了,白相相。
可惜我不是个白相人,我是劳碌命,命苦得溚溚渧,无论好不好,写总是要写的,一直是要写的,所以不会受到任何打击和影响,我继续写我的文章,一直到今天,还在写。
现在回头看看1988年给《苏州杂志》投的这篇稿子,至少是用心写的,至少是很卖力的,是想在《苏州杂志》创刊号上出个风头的。
《苏州杂志》创刊后的好几年,我经常在《苏州杂志》上发表小说,不敢说每年都有,但至少一年隔一年都会有,1990年是《门堂间》,1992年是《白鱼阵》,1994年是《牵手》,总之不算少了。后来好像《苏州杂志》不发表小说了,我就改投散文了,投得比较多,所以有点记不太清了,反正,写苏州的,平江路,山塘街,东山,西山,老宅,街道,茶叶,等等,关乎苏州的,几乎什么都有。最近的一篇好像是《茶有西山一记红》,下一篇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现在在写的这一篇吧,我打算起个题目叫《点点滴滴在心头》。
我作为一个作者,和《苏州杂志》的关系就是这样不离不弃不间断的。
在漫长的岁月之中,也曾经有几年,我的角色换了一下位,做了《苏州杂志》的编辑,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留下的记忆却是深刻而永恒的。
记得那时候我是这样说的:“许多年来,和许多杂志打过许多交道,几乎每天都有各种杂志从全国各地寄来,但杂志与自己的关系,似乎永远只有固定的两种关系,那就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读者和编者的关系。从来没有想过,会不会有朝一日,一个作者一个读者变成了一个编者?这个事实今天却突然而至了。”

担任编辑工作的短短几年,深深体会到了办好一本杂志的种种艰辛不易。《苏州杂志》的同仁们始终记住老主编陆文夫老师的一句话:不要东张西望,坚守与创新并举。
拉拉杂杂,说了一堆,好像把自己都给说糊涂了,因为主题不甚明确。不过反正好在就是写写和《苏州杂志》有关的事,就随心所欲一点了。现在微信里天天在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人老了,要善待自己,要心疼自己,要怎么怎么怎么,总之意思就是,爱咋咋的。
人老了,文章也就老了,主题不够鲜明,思路不够清晰,想来别人也会多多谅解。
相比之下,《苏州杂志》还很年轻,太年轻了,才三十岁,三十岁的《苏州杂志》,风华正茂,经验和精力皆俱,一定能够走出自己的新征程,一定能够攀登自己的新高度。
旧时月色
亦然
无意中发现网上有孔夫子书店出售我三十年前写的约稿信。信写于1988年9月5日,是给散文作家石英的。信中说《苏州杂志》创刊号将于十月下旬出刊,正在组明年第一期的稿子,“您曾来过苏州,还望支持新生的《苏州》杂志,不吝赐稿,若能赐下与苏州(或江南)有关的作品则更好了。”
我有点疑惑,为什么当时没有把“杂志”二字写到书名号里去呢?也许当时的刊名初拟《苏州》,而不是后来的《苏州杂志》?
约稿信写在“苏州市文联文艺编辑室”的信笺上,信封也是“文艺编辑室”的信封。那时处于由《苏州文艺报》改出《苏州杂志》的过程中,办公地点还是在文联里面的小院子里,年底前搬到平江区少年宫里办公,因为文联要拆旧房子造楼了。
在平江区少年宫一年多才搬到修缮一新的青石弄。少年宫里有个学小提琴的小孩老是在窗外拉《新疆之春》,还挺入耳的。他的老师告诉我,其实拉到这个程度只要一年半就可以了。
《苏州杂志》创刊后影响蛮大,电视台来拍专题片,我写解说词的时候,还在结尾时把少年宫所在的大井巷借题发挥了一下,说大井巷里有一眼苏州文化的深井呢。
有件事印象挺深。创刊后有一次在南林饭店吃饭,席间有位市领导向我指出有个校对错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陆文夫马上就接过话题,说这很正常,无错不成书嘛。他还说在苏州报工作的时候,连报头都印错了。当时叫《新苏州报》,工人把四块锌版位置放错了,成了《苏州新报》,居然校对、编辑、值班总编都没看出来。陆老师真是护犊子啊,我蛮感激的。那天同席的还有歌舞团编导马家钦,市领导问她最近有没有新作品,她就把另一桌的皇甫菊含叫出来比划了一段,是与刺绣或者与做针线有关的舞蹈。
有一天,有位叫王华的作者到少年宫找我,带了一本《散文》杂志和一封退稿信。《散文》里有他的散文《黑白》,退稿信是我写的。信里说,稿子没能在《苏州杂志》发表是因为写的外地知青生活,与本刊宗旨不合。然后建议他,这篇散文写得挺好,可以投到《散文》一类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去。于是王华就投了《散文》,很快就发出来了,很开心,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特意找过来告诉我。
之后王华常来找我玩,无关写作,只是下棋。在他下放的地方,围棋叫“黑白”。有几年苏州作家中喜欢下围棋的经常聚在一起比试。又是许多年不联系之后,王华带着一沓厚厚的书稿到文联找我,要我为他的散文集写序,他还听取我的建议,就把《黑白》作为书名。后来他又写了不少围棋史中与苏州有关的文章,我还推荐给陶主编发表过。
都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当年文联小院里有两棵非常耐看的树,一棵海棠,一棵桂树。春天海棠花开了,满院子纷纷扬扬,亮得耀眼。我曾经在办公室窗棂上记下哪天开了、何日谢了。可惜有一年文联跟风办三产开小饭店,油烟把靠近的海棠熏死了。桂树还在,而且树形越长越漂亮,苍劲而飘逸。我经常把它推荐给写生画家。
归来仍是少年
平燕曦
我一直以为,上世纪的80年代是中国最具人文情怀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时期。陆文夫创办《苏州杂志》之初,便提出了“三不搞原则”——不搞吓人倒怪,不搞赤膊女人,不搞“广告文学”。30年过去,这些原则仍然被坚守着,殊为可贵。
杂志创刊于1988年,我与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它的前身《苏州文艺报》。作为“文青”的我刚回到苏州,常为这张报纸写稿。当时苏州的轻纺织工业还没有遭遇到外来产品的冲击,效益很好。“四大名旦”带动了一批苏州著名产品享誉全国,苏州于是成立了企业家艺术家联谊会。
我所在的肥皂厂是联谊会的发起单位,厂长老顾是陆文夫的好朋友,做了会长。而陆老是副会长。我因此结识了陆老和朱红等老编辑,有事没事就往杂志社跑,写作也更加勤奋。终于,在1991年,我被调入苏州杂志社,成为一名编辑。
杂志社的社址是叶圣陶先生的故居,一位苏州女企业家出资10万元作了装修,所以环境非常美。春有玉兰,夏有芭蕉,秋有石榴,冬有白雪。不大的地方居然还配备了淋浴间,这在当时洗浴业尚不发达的苏州显得很高大上。于是,我夫人常带着蹒跚学步的儿子来这里玩,顺便洗个澡。感觉很温馨。
我在杂志社的3年间,采编业务这块一共有四五位老编辑,算上陆老,里面居然有两个半右派——陆文夫和朱红自不必说,还有半个是朱衡先生,写得一手让人叹为观止的蝇头小楷,学识也是十分了得。两位老朱时常跟我们讲些右派经历,豁达而淡然,仿佛在说着别人的故事。
陆文夫大约是中国最早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之一。所以杂志社一开始就是用电脑编辑的。作者来稿大多是手写,即使是电脑写作,也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发电邮,所以我们要一一对原文录入,再做修改和提交。这可苦坏了老编辑们。五笔字型录入快,但入门较难,所以编辑部里经常会有人高声询问某个字怎么打?然后大家就在各自电脑上试着操作,提供准确的答案。我最年轻,领悟快,所以常常被请教。
虽然是电脑编辑,但编读往来、与作者的沟通却都是用手写信函的方式。杂志社初期的老作者老读者,很多都是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名人,比如冯英子、苏雪林、冒舒諲等。每每有来信,大家便会围拢过来,欣赏点评一番。那时编辑与作者的关系非常融洽,我一年至少要给作者和读者寄出上百封书信。我手头就保留着一封尹瘦石先生要求订阅杂志的亲笔信,他太喜欢这份杂志了,后来还专程来杂志社走访过。
我在杂志社,主要负责《今日苏州》《人生之旅》《吴中风情》等几个栏目的编辑和采写。写过河道整治、民居改造、人文阅读、滑稽戏、邮票市场这样的题材,也写过谭以文、吴兆基、蒋风白等苏州文化名人。由于比较了解杂志的定位和陆老的胃口,我的文章基本上是“免检产品”。只是有次我写观前美食的稿子,被他先发后毙了,他写了很长的批注给朱红说明看法,令我备受启发和教益。
杂志创办后,因其独一无二的文化风味得到了海内外的一致好评。慕名而来的文化名人也很多。我印象里就有叶至善、章克标、冯英子、章品镇等人。后来,我在杂志上开办了《青石小憩》栏目,以主持人的方式,讲一些编辑部的故事,这在全国还不多见,很受读者欢迎。
我还有个任务,就是每期要拿一些编好的文章去给苏州的两位画家——张晓飞和顾曾平先生配插图,画好了再去取回来制版。两位画家的画为初期的杂志增色不少,我因此跟他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去年我在编另一份文化杂志时,又辗转找到这两位画家。顾先生对再度合作非常开心,而晓飞先生则因年高多病,几乎认不出我了,让我不免唏嘘。
在杂志社3年的,每每要出新刊时,我都要和副主编朱红先生一起,骑自行车去很远的吴县县前街附近的印刷厂制版、监印。这是一件很细致的活。当时的印刷技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要先制作成软片,然后将标题、插图、正文和装饰线等分别用剪刀裁开,再仔细贴到另一个版子上制版,来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高度近视的朱红老用小直尺校正距离和水平,鼻子几乎贴到纸上,常常弄得眼睛充血。如今,我的家就住在县前街上,时不时还会想起这些,感慨岁月的流逝和城市的变迁。
杂志创办之初,除了苏州一些企业家的鼎力相助外,陆老创办了“老苏州茶酒楼”,请来几位国宝级的大师掌勺,以期通过茶酒楼的良性运营为杂志社造血。但文人开店毕竟艰难,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不过每逢年关,杂志社全体人员都会在“老苏州茶酒楼”吃个团年饭。陆老和朱红的酒量很好,大家谈笑风生,其乐融融的场景至今难忘。
我在1994年离开了《苏州杂志》。原因很简单:虽然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虽然这是我人生中很重要很美好的时光,但杂志社的收入仍不足以养活一家三口。陆先生很赏识我的能力,不希望我离开,但出于对我的理解,仍然豁达地“放行”了。
离开之后,我每年春节都会去陆先生位于带城桥的家中看望他,直到他去世。记得最后一次春节去看他,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我拿出相机提议拍照留念,他慨然应允。但只为他拍了两张单人照,相机就没电了,与他的合影便成了永远的遗憾。稍感欣慰的是,我为他随手拍的那张照,他双目炯炯,非常有感染力,算得上是精品了。
3年与30年,都是沧海一粟。有时路过十全街,我会去青石弄5号转转,看看那里的玉兰、芭蕉和石榴,与杂志社的编辑们聊聊过往。昔日一起工作过的陆老、朱衡、华群和迟我进社的王宗拭都已作古,而我,也已年过半百。不由得想起那句没有出处的诗:“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这句,赠于30岁的《苏州杂志》,共勉。
以社为家
朱红梅
2003年7月,我毕业以后到苏州杂志社当了一名编辑,从此以社为家。
“以社为家”,不是表决心,而是实情。为了照顾我这个编辑部新来的年轻人,杂志社把青石弄5号院子里一间空置的客房给我做了宿舍。
客房进门右手是个小小的卫生间,房间里几件简单的桌椅。两张单人床,床腿因为年久潮湿,已经腐朽。索性敲掉,两个床板一叠,刚好做一个床架。自己添置了一张床垫、两只书架、一个简易衣柜,就算安了家。
从宿舍到办公室,步子迈大点,三五步就到了。平时上下班的便利自然不消说,周末闲暇时更有一种好处,打开房门就见草木扶疏,搬张藤椅坐在廊前,手里拿本书,三心二意地,看两行,发发呆,听听鸟鸣与虫声……享受这于喧闹街市中独得的一份惬意与宁静。
在老宅子里生活,也经常有些小意外,遭遇蛇虫鼠蚁是常事。我曾经在《青石弄5号》一文中,记录下这些琐碎的细节:
……比如,办公室闹老鼠。晚上坐在电脑前面,经常有一只胆大的老鼠在老式的储物柜后面,探出头来望着我。起先,我冲它吆喝一声,或者手臂划拉一下,它也就遁走了。后来,老鼠的胆子跟着日子渐长。它大概也看出了我的色厉内荏,慢慢不再理会我的呼喝,自顾自活动了。我对这灰头土脸的家伙其实也并无恶意,由着它去吧。
只有一次晚上,我走出办公室。大概是轻手轻脚的缘故,迎面窜来的一只老鼠不及提防,“砰”一下直直地撞在了我的足尖上,扑倒。我至今仿佛都还记得那“砰”的一声响。想是撞懵了,那老鼠顿了顿,定了定神,才转身狂奔而去。就像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角力,我有点占了对方便宜的歉意。
……
老房子困扰我最多的还是漏雨:
最初搬进去,墙面雪白,刚刚油漆过。后来,经过梅雨季节和多雷阵雨的夏天,屋角渐渐出现了霉斑。多经历一场风雨,随着雨渍渗透范围的不断扩大,霉斑也跟着变大。墙体渗水,一开始只是西面一堵墙,发展到后来,北面的墙也开始渗漏。2008年5月中旬,一场暴风雨来袭,这次可不是简单的墙面渗水,亮晶晶的水流在白色墙面笔直游动,淋到贴墙而放的衣柜上,发出“笃笃”的叫唤声。我气急败坏地挪开柜子,看着水淋淋的屋子,觉得生活就像饭局结束后的杯盘狼藉。外面还是雨狂风骤,有人发来一条短信:保佑四川的同胞,要平平安安!我忙里偷闲回了一条:本人正在灾区抗洪抢险,勿扰!
……
这些曾是当年生活里的小困扰,如今却似隔岸观火,生出点别的兴味来。
我在青石弄5号一住六年多。这期间,我在杂志上编发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篇文章《嘤鸣之思》,把一篇五六千字的长文删减成1300字,陆文夫老师在发稿单上写道,“编得好”。羡慕杂志社的编辑们都有写作专长,我也学习着采访和写稿子,幼稚是难免的,大家也都看我是小字辈,鼓励包容。青石弄5号既是我曾经的蜗居,也是我起步的地方。
离开青石弄5号,我不再做编辑了,但还是要跟文章打交道,跟写文章的人打交道,也没有隔很远。
答卷
黄恽
《苏州杂志》迈入了而立之年,我来到杂志社也整整十八年了。从下岗工人到杂志编辑,我就这么走过来,脸刻皱纹,鬓添星霜,一晃已经是五十朝外的“老伯”。
记得当年每到送审稿子的日子,打印好作者的稿子,同时也呈上自己的稿子,填好发稿单,等待陆文夫老师最后的审核。然后,心情略有紧张地等待陆老师审核的结果。
陆文夫老师的审核结果有四等,通常是用2B铅笔批在送审单上,随打印稿一同发下来:不发、发、好、很好(或写得好)。不发的原因多种多样,是写得不好,或者未必是不好,很可能只是不合适《苏州杂志》,如果是编辑自写的稿子,他还会三言两语要言不烦地写上不发的理由。后面三个却是等第,发,相当于合格;好,相当于良;很好或写得好相当于优。
在拙作的送审单上,上面这四种批语都得到过。当遇上“不发”时,我会仔细看看陆老师的批语,想想他是基于什么考虑,是写得不好,还是内容不合适;当遇上“发”时,会稍稍松一口气,总算合格了;当遇上“好”或者“很好”时,虽然只是一字之褒,也会略有一点高兴,是那种努力得到认可的喜悦,比发几百块奖金快活得多,文坛前辈、主编的赞赏会激励我更加不辍向上。
《苏州杂志》是双月刊,每两个月,我都要经历一次考试,收获一份批改后的答卷。
2005年6月,我在《万象》杂志六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周瘦鹃之死》,病床上的陆老师知道了,我看到他赞许的笑容。
2005年7月,陆文夫老师去世了,我感觉他并没有离去,每次写文章都会停下来想一想:陆文夫老师看了会给我的“答卷”一个什么等第?
三年后,我出版了书话集《蠹痕散辑》(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2年,我出版了《古香异色》(海豚出版社);
2013年,我出版了《秋水马蹄》(金城出版社);
2014年,我出版了《燕居道古》(新星出版社)和《缘来如此》(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7年,我出版了《舞文詅痴》(东方出版社)和《钱杨摭拾》(东方出版社);
2018年,我出版了《萧条异代》(东方出版社)和《难兄难弟》(东方出版社);
每当出版一本新书,我都会想,如果陆老师还在的话,我把新著呈到他的面前,这是我的答卷。我依然会有些紧张:对此,他会批上一个什么批语呢?“发”?“好”?“很好”?我希望他脸上有温厚的笑意和一个宽慰的表达:没有辜负他的提携和栽培。
我明白我的答卷有些寒碜,还远远不够,在今后的日子里,必须继续努力,不断地向他呈缴答卷,为了报答他对我的那份知遇。
站台
顾俊
1988年,我还在念初中,《苏州杂志》创刊。那时候,只知道苏州有个写小说的陆文夫,他的《围墙》在课堂上读过。在他的小说里,还听说了美食家这个词汇,嘴馋口刁竟也能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品位。后来听说这位小说家又办了一本可以吃的《苏州杂志》——老苏州茶酒楼。当年门楼上有副对联:天涯客来茶当酒,一见如故酒当茶。秋风起时,十全街的法国梧桐,黄叶子落了一地。每次上学,缩着头颈踩着自行车路过,都会望几眼,只觉着亲切,有一股暖暖的人情味。清淡软糯的日常生活,原来也可以有酒的豪气。茶与酒际遇,或许给知味知趣的小说家平添了不少灵感。
对一个从小听着吴侬软语,枕河人家长大的少年,那个年代的变化,乃至一切细微的见闻,都是能带来无穷遐想的。我问过很多人,对于苏州的印象大多停留在80年代末。然后呢,觉得时间越来越快,日新月异,信息终于多到来不及接收。嘴里嚼个不停,还谈什么回味?大约,真的需要一本杂志来记录了。苏州很多留存记忆的博物馆,差不多也是在那个阶段开建的。
1998年,《苏州杂志》10周年,陆文夫主编写了篇文章,题目叫《十年树木》。
文章开头,老主编就感叹,这本杂志居然也满了十年,真使人有点喜出望外。为什么?他接着说:“创刊之初深知办刊之艰难,自忖能办五年也就满足了,因为前人办杂志有的只办几年、几个月,甚至只办一期也是屡见不鲜……”
就是怀着这样一种敬畏,《苏州杂志》走过了十年。彼时的我已进了工厂,社会经济转型加速,影响着每个人的观念和生活。现在想想,在那么浮躁的环境下,一个小年轻,工余能静下心来来读读《苏州杂志》,是什么吸引了他?或许是一种含蓄包容,隐忍自省,不事张扬的底气。这本杂志当年就有这个怀抱,有这个特质。
2005年,《苏州杂志》办了一百期的时候,老主编陆文夫去世。我在苏州杂志社已经当了几年编辑。
2008年,《苏州杂志》又迎来了20岁生日。范小青主编让我们每个编辑在杂志上写几句话。我当时写下一段采访中的真实经历,说某次在街头巷尾寻访老宅,踏进一户人家,问主人宅子的来历,他语焉不详,但肯定《苏州杂志》上有。我告诉他,自己就在杂志社做事,他不假思索来了一句,那你们陆文夫肯定知道。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信任。数十载的坚守,在很多老苏州眼里,《苏州杂志》已成了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
2018年的今天,《苏州杂志》30周年。我也从一个风中看落叶的中学生,变成了一个每天跑菜场的中年人。30年的光阴,足以让一本杂志沉淀下来,也足以让青丝变白雪,知交成古人。有时想起一位久未联系的老作者,去函问候,信却被退了回来。时光飞逝,曾经受教共事的师友,因文结缘的作者,不少相继凋零,如果列个名单,会是长长的一串了。
带城桥路口有个站台,距离杂志社最近,好多年了,一直在那。这次杂志30年,陶文瑜主编又关照大家写几句话,算作纪念,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站台。
曾有个专程来送稿的老者,走路颤颤巍巍且目力不济,天知道他一个人怎么走到青石弄的。接稿之后,我怕他路上有闪失,便搀送他去站台。本来几分钟的路,感觉走了半个钟头。他当时围着一条五彩斑斓极其艳丽,艳丽到和他的年龄根本不搭的围巾。我忍不住问他,您觉得这围巾好看?他摇摇头,用手指指自己近乎失明的眼睛,叹道,鲜亮,别人才能看得见我。
我目送一抹亮色消失在站台上,觉得有点恍惚,这么多年下来,年长的师友或是外地来的作者,都是在此送往迎来。人一个个走了,站台却还在。对于这个站台而言,所有的人都是过客,也只是过客。但对于每一个人,这里就是到达或者出发,从前是,将来也是。杂志于人,何尝不是如此。
读书怀人
刘家昌
时光荏苒,陆文夫老师于2005年7月9日离世,屈指算来十多年了。他生于1928年,今年是他诞辰九十周年。
“读书怀人”是我纪念陆老师的为佳选择。
陆老师生前说,他是个“写写文章的人!”陆老师的佳作《陆文夫文集》载入了文学史册。为后人留下极其珍贵的文化财富。
《人之窝》(长篇小说),《美食家》(中篇小说),专题写的“住”和“食”。他说过,要写全“衣、食、住、行”作品,还有“衣”和“行”要写。其实,在他的著作里,可以看到写“衣”和“行”,当然不是专题作品。
说来话长,陆老师在上世纪40年代就读苏高中,他常去山塘街河畔莲花斗姨母家,现在已变迁。很想找机会看看山塘街变化。为体力不支未如愿。
记得那是2003年吧,一天我和顾俊同志去了山塘街景区采风,也是为陆老师去探路打“前站”。到了山塘街,得知景区有个“服饰展览”就进展馆看看,是否有可取“素材”,向陆老师作推荐。结果仅见到一般的服饰陈设,历史性也不足取,只得作罢。

今重温陆老师的《壶中日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内有一篇《苏州人到广州》,其中有一篇写“穿”,顿觉得可以对上号,那不是写的“衣”吗?这段文字,一开头就说,“到广州来之前,就存心要看看广州人的衣着,特别是青年男女的衣着和发式。”因为在苏州听说,苏州某工厂的领导,为了加强对青年人政治思想教育,便在大会上宣布:“从明天开始,凡穿喇叭裤留长发的不许进厂!”就是怀着一种惊诧心情,到广州见识一下。
想象中,广州靠近香港,新式衣着有可能先由国外到香港,再由此传来的。广州人的衣着一定很“洋”。谁料“一看之下,发现‘合理的形象碰了壁’,广州人一般地衣着都很朴素,朴素之中,还显得有点随便”。陆老师在这段文字里,分析青年男女的服饰变化:“如果有个穿着新奇服装的人,从街上走过,青年人盯着的时间往往要比中老年人看的时间长些。”那不太看得惯的式样,就会出现在他们身上。对衣着的偏见“不许进厂”不近情理。在无穷的岁月里,衣着和时代同步,不停地变化和发展。“时装展览”创新设计的推动,适应青年人的衣着思变心理。衣着也是生活不断变好的标志。
再就是写“行”的作品。又从《壶中日月》找到一篇《林间路》。文章一开头就是:“我熟悉一条林间之路,经常在这条小道上走来走去,这小路蜿蜒曲折,高低崎岖,他从大路旁一个很不显眼、灌木丛生的地方岔向深山里去。”说它几乎不能称之为路:“实在难走啊!”随即对两边的自然精致作描述,又写为什么不在林间修一条比较好走的路?林间之路有引人入胜之妙处,却人们都不愿意走“我也不愿意走”。“如果有高速公路或登山电缆的话,我还是很愿意乘坐,他毕竟能节省时间,增加办事的效果。”陆老师当年写这篇作品时,各地交通、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如今,现代化进程建设的高架、高速、高铁,已是星罗棋布,人们的“行”进入了新的时代!
重读陆文夫老师的作品,为了纪念,也是学习,细细品味其中的深邃内涵。
三十年
陶文瑜
《苏州杂志》三十年了。
二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调到苏州杂志社工作。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去向———苏州滑稽剧团。老陆第一次和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去滑稽剧团。我说我去了以后,怕人家叫我小滑稽,待我老了人家再叫我老滑稽,我的儿子人家说是小滑稽的儿子,我的孙子人家会说是老滑稽的孙子,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称呼。老陆说你不肯去也没有办法,要么你到我这里来吧。
十八年前的这个时候,从前杂志社的一个工作人员开了一家饭店,邀请大家一起去吃中饭,结果却是很简陋的饭菜,我记得第一道是虾仁炒青豆吧,这个刚当上老板的前同事还拖着老陆一次一次合影。我当时有点不舒服,装着开玩笑的样子说,这样的饭菜我也打发不了的,何况老陆?老陆对我眼睛一瞪说道,闲话不要多。这件往事让我学会了体谅和宽容别人,所以我一直记着。
十二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的膝盖痛得不能走路,去医院一查是膝盖骨退变,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老陆打电话来慰问,过后在杂志社会议上还说起过两次。老陆说,你这个毛病是吃出来的,谁谁也是这个毛病,结果痛风进到脑子里了。谁谁是一位不久前过世的前辈。所以我有点不高兴,告诉他我这个主要是少了锻炼,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不要来送了,不过最好写篇文章纪念一下。老陆有点无奈地摇摇头。后来有过好几次,他一定要将自己的自行车送给我。这是一辆进口车,之前几年他一直骑着锻炼,渐渐身体弱了,车子也有一两个零件要修理了。我生来不好动,也比较怕修理之类的麻烦,就婉转表达先放在他那里。隔一阵遇上老陆,他又提起要送我自行车的事,我只好明确说不要。
今年的这个时候,我和烹饪学会的华会长说起老陆,我们商量着把老陆生前交往过的厨师请到一起,由他们烧一两道老陆偏爱的菜,大家边吃边谈,这是一种很修旧如旧的纪念。华永根先生十分赞赏并且大力支持,说得月楼是老陆生前常去的地方,要不就放在得月楼吧。
华永根说,我们要为这个活动起个名字,我想了想,要不叫“美食家——陆文夫尝过的滋味”,或者加上追忆吧,追忆两个字,使句子丰富起来了,也有了距离感。
这一天我要和华会长商量活动的事情,正好叶老的家人顺便来青石弄杂志社探望老宅。一行人说说从前,看看现在,我一直陪着。这时候华会长来了好几通电话。叶老的家人说,你有事情早应该说起的呀。我说你们原来是这儿的主人,现在我在这里上班,是反客为主,我对叶老有感恩之心的,陪你们是一种表达方式。
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文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身边有熟人先走一步了,二是经常会想起那些离开的老师和朋友。写文章的人相对比较脆弱,想起从前旧事,心底里总有些挥之不去的借景抒情。
——由《苏州杂志》解读陆文夫的三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