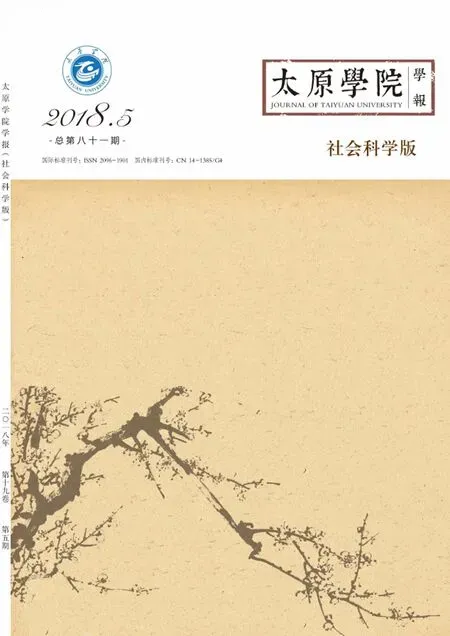走向荒野的碎片
——再论“乌青体”诗歌
赵 晓 敏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阳泉分校,山西 阳泉 045000)
最近央视的大型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正式落下了帷幕,这档节目用“和诗以歌”的形式将传统诗词经典与现代流行相融合,由数十位经典传唱人用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重新演唱经典诗词,并充分利用电视媒介、网络平台将诗歌以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大众推广。这个节目的播出无疑又引发了大众对于诗歌的一种回归,仅从诗歌向大众推广的现代化表达上看,这档节目与之前大火的“乌青体”诗歌似乎隐含着某种相似之处。诗歌已不再是少数文化精英的特属,而是变成了人人可参与的一种文化现象,“乌青体”作为一种更加直白的诗歌表达,就像《经典咏流传》中将诗歌以现代流行的韵律、节奏相伴,必要时插入现代白话歌词进行传唱一样,让诗歌更加通俗,进一步回归生活本身,建立起大众对于诗歌的接受度。在此,“乌青体”诗歌表现的语言的口语化、经验的碎片化等特点又得到了体现。之前,有些批评者已将其看作是语言的自然化选择、形式的突破、诗歌的一次冒险等等。随着大众审美的改变,连经典诗歌的表达都如此通俗大众,更何况是当代诗?那么这是否就表明,在此背后隐藏着一个预言——文学界需要重新审视它的价值,给予它一定的位置,或者说“乌青体”作为新的诗歌形式在完成一次诗歌命运的冒险探索。在此,我们不得不再次对“乌青体”诗歌进行重新关注和评价。
一、语言的口语化
对于“乌青体”诗歌,人们争论的焦点无疑是其作为“废话”是否能够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被谈及最多的有《对白云的赞美》《鸡很难过》等篇目。《鸡很难过》这样写:这时候一只鸡/走过来/说我很难过/鸡很难过/我也很难过。在争论的同时,也掀起了“仿写风”的高潮。很多围观者以嘲讽的姿态看待“乌青体”,表示对其语言的不屑和唾弃。但不论从围观群众还是诗人、诗歌评论者,对“乌青体”的态度还是发生了些许改变——从2012年绝大部分的贬低、否定到2014年部分的支持与肯定。就像乌青自嘲地说,“骂我的人的比例已经下降,大约由90%降到了60%。”[1]
看到乌青的诗歌很容易被他语言的口语化所“震撼”,就像杨黎说的,“诗,就是废话”[2],我们也正是被乌青的“废话”所震撼。这里的“废话”,是针对于传统的诗歌语言来说的,而不是对于生活。他的诗歌里不仅没有丰富贴切的形容词,没有华丽的修辞手法,也没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并且几乎是简单直白的生活用语的分行、堆积。如《买水果》:我挑水果/就挑那些看上去舒服的/苹果要像苹果/梨要像梨。《我看见》:他们两个人/像情人一样/走在街上。陈仲义说:“过分强调所谓的原生态、无技巧、现象学,过分强调呈现就是一切、呈现就是最高内容,过分追求快感和一次性消费,使得随性的‘说话’成为普遍‘诗意’。诗歌的正常‘质地’正在被无遮拦的口水淹没。”[3]2012年乌青体与“梨花体”“羊羔体”以及网络上出现的大量类似之作共同营造了2012年及之后“口水诗”的创作盛况。这些作品对诗歌的发展最终没有产生太大的意义,很快成为了网络泡沫。但在两年之后乌青体再次回到我们视线的时候,我们开始关注乌青其他的作品,如《我比你孤独》《奶奶的镜子》《跟乌青一起去奔跑吧》等,并且韩东、蒋方舟和一些网友对这些诗给予了肯定。在《我比你孤独》里这样写:我不想和你比/因为我什么都比不上你/只是心里觉得/我比你孤独/我也不想跟你多说/因为我无话可说/无话可说/自己的孤独是自己找的。这首诗看起来很平常,它没有浓烈的感情抒发,也没有讲求文词的华美,只是简单的几句口述性话语,但当我们朗读的时候,又隐隐约约在其中读出了某些“孤独”。语言简单无障碍,诗句简短,读起来有些缓慢的分句格式,似乎还有些无聊。另一方面这种简约也造成了语意的空白,语意的空白给了我们想象的余地和经验认同的发掘,也有了一种失语的寂寞和无奈。再如《跟乌青一起去奔跑吧》这样写:如此秋天的天气/为什么不到街上去奔跑/嘿,小孩/把钥匙挂在脖子上/跟你乌青哥哥一起去奔跑吧/不要盯着漂亮姐姐的乳房/久久不放,看前方/道路是那么清爽/我们就这样奔跑/多么愉快啊/你看你看/那只小牧羊犬如果不是绑着/早就跟我们一起奔跑了/嘿,小孩/明天是你乌青哥哥的生日/怎么样/买块巧克力意思一下吧。这首诗的语气是欢快的,并且有些童气。他们要去街上奔跑,“到街上去奔跑”本身就是孩子的专属,诗中又用了“小牧羊犬”和“钥匙”等意象,带出了童年欢快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毫无顾忌的,在现代的生活中恰恰又是人们缺失的。尤其在最后,生活化的语言让其充满幽默感,让整首诗都充满了对欢快自由的渴望。
当然,在乌青的诗集中有些诗歌也泛着文字游戏的味道,但如上所举的例子也是处处可见,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诗歌语言口语化过程中显出的十足韵味。其实,早在“第三代诗歌”到来的时候,它们就已经打破了诗歌语言的神秘和晦涩,试图从语言开始进行诗歌的革新。他们在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屏障上凿出一个洞口,否定了诗歌意义的崇高及艰涩。2001年在郑敏、吴思敬关于“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的对话中,郑敏先生说新诗还没有形成一种传统,也就是没有一种规则的形式,他从诗歌的格律和音乐性分别对此做了分析。从当下来说,不论是现代人重做古体诗,还是对格律和形式的研究,在体现当下诗歌的包容性时,也体现了我们对于传统的保守思想,我们仍然无法摆脱经验对我们的束缚。但我们做的每件事又都是背离传统的,打破运用“典故”“对仗”的古体诗,朦胧诗语言的晦涩和现代性精神的独立,以及“诗到语言为止”的第三代诗歌对朦胧诗或整体诗歌崇高意义的否定,他们仿佛时刻都在准备打碎套在身上的枷锁,无休止地追求着诗歌的自由。从一次次的变革中可以看到,形式在削弱,诗歌的神秘在消失,当这一切一步步前进,到现在为止,在时代的交错中,“乌青体”的出现也就不再是一个偶然。那么这样看,“乌青体”中部分诗歌也可以当成时代的先锋,是对诗歌新领域的大胆冒险和探索。
“废话诗派认为:生活中充满了官话、套话、假话,诗歌就是‘让人说人话’。废话,不是通常所讲的毫无意义的废话,它被定义为一个中性词,是指一种对普通惯常意义的消解,是一场语言的实验。‘比喻’‘文采’只代表绝对的人类自卑,口语的、不修饰的废话诗才是自信的诗。”[4]依据现状来看,大众也逐渐喜欢语言的朴实、幽默及其生活性的诗意和这简短的诗句带有的一种凝练的情感。当然这种口语化语言转变为“诗性”语言的过程或使用限度是难以把握的,不小心就成为模式写作或语言游戏,这也是一些评论者为其担心的“冒险”行为。
对于网络上的争论,乌青并不以为然,他说,“这些跟我写作没有关系,我不是公众人物,我甚至对发表诗歌都兴趣不大,这是网民自己在玩儿。”[1]人们热议“乌青体”,主要是由于网络媒体无意识的围观,对新奇事物评头论足的惯性行为,并没有对诗歌本身产生多大的影响和思考。于是我们也不必再对此争论下去,或者非要分出个青红皂白,谁是谁非。回到事情的原始状态,只是一个名叫乌青的人实践着自己的诗歌理想——打破诗歌的语言屏障,将其带入生活。正如他自己说的,“当下的诗歌已经和大众产生巨大阻隔,用强势方式去推广不太可能,用相对温和、偶然的方式,进入他们的生活,可能会更好。”[1]正如央视《经典咏流传》的播出,不也是用一种大众更易接受的方式去表达和推广诗歌吗?人们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也就在说明,他的诗歌已经渗透进生活,或者“乌青体”遭受大众的拷问,正等待得到正视与承认。乌青生活化的诗意表达,不仅使用了口语化的语言,还运用了易于被接受的经验碎片。当然这种经验的碎片可能并不是乌青刻意营造的,就如同网络信息时代到来时出现的微写作,是大众审美的一种自然选择。从默默无闻到产生反响,可以说这也是“乌青体”与大众审美的一次重合。
二、经验的碎片化
乌青的诗歌简短明了,一首首诗歌只是一个个没有前因后果的现象描述。当然这些现象都是来自于生活中无数的现象,并且彼此没有联系,构成了散漫的、直观的碎片形式。这样的书写方式,仿佛让生活每一处都可以转化为诗歌的存在,整个生活无处不充满了诗意。比如,《天上的白云真白啊》诗集中,有二十多首以“有一天**”命名的诗歌,并且“有一天”的数字排列也并不是严格按照顺序依次而来;其中还有很多题目十分相似如,《少女小欣之烦恼》《中年维特之烦恼》《青年六回之烦恼》,及《女人消失在某小区》《女人消失在拐角处》《女人消失在大海边》等。对于诗歌的独立与完整来说,这些相似的题目便构成了彼此的解构,或者成了多种可能的描写,而不是独立的、完整的系统塑造。与此同时,这些题目也将引出更多的题目,它本身就赞同了生活的碎片形式及其书写的细节化、现象化。当然这些相似性题目的出现是诗人对生活的主观感受,诗人自身迷失在生活的旋涡中,找不到生活的整个系统,而在他的经验里生活只是偶然的“有一天”或不同具体场景的存在。当然在此之外,还有一种诗歌内容里关于生活的碎片。这也是大众在接受时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生活片断的场景化。如《如果我是一道雷电》:如果我是一道雷电/我就一下子劈死/这个叫乌青的人/不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一道雷电/很酷的雷电。这首诗简答的表述是,他想劈死乌青,并且这件事没有发生,没有原因,当然更加没有结果,只是单纯的一个想法的表达。这可能是生活中在每个人身上层出不穷的、数之不尽的想法中的一个,然而他只是在表述这个想法。如《有一天·66》:爸爸回来说/今晚看电影/妈妈做饭的动作就加快了/他们忘记了工作的疲惫/使今夜变得快乐美好/吃过晚饭夜幕降临/我们一家人整装出发。这首诗看起来再平常不过,就连“快乐”也变成了简单的直观的描述,是对“快乐”本身进行的描述而不是去营造快乐的气氛。2011年“中国先锋诗歌二十年研讨会”上评论家陈超用“日常生活中泛诗歌气质的弥漫化”来形容新世纪以来类似的诗歌状态,并在整理文章中表示,“大大小小的广告、短信、博客,甚至最不可能产生诗的求职材料中都会看到几句诗,这对诗歌写作提出了新的考验,要有自己的语言秘密,不能等同于泛诗歌语言或资讯语言。从写作姿态看,新世纪以来虽然各类诗人的写作方式有很大差异,但有一个背景比较一致,就是都放弃了对形形色色的绝对本质和终极家园的追寻,诗人们普遍不再认为自己的心灵和语言可以真实、准确地反应基础、本质、整体和终极,诗歌话语不必要也不可能负荷这些东西,所以先验设定的超时间超历史框架失效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生活细节成为新的出发点。诗人们都在表达个人经验。”[5]不论是诗人的个人经验碎片进行了诗性表述,还是生活细节成为整个生活书写的碎片,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模式似乎已经被大众接受。除了研究者,很少人会花费专门的时间来研读严肃文学,就连篇幅不长的诗歌在“短讯时代”也变得冗长,再加上丰富的修辞和辞藻更是让大众读者煎熬。这种现象早在我们讨论“严肃文学边缘化”“诗歌边缘化”时就成了公认的事实,可能是因为“时代先锋”与“消费文化”的对立,或者是因为代际之间的隔膜与断裂等原因。
以传统诗歌的写作手法来分析乌青诗歌的内容,乌青并没有在诗歌中表达出基本的情感色彩或主题意蕴。而至于大众能否从这种直观的简单的语言中感受到情感的存在是由当下大众的审美决定的,与理性的分析和传统的诗歌形式并无绝对关系。这也是当下信息化、碎片化生活中大众的审美倾向。易彬在面对诗歌存在的口语、废话、日常化、娱乐性等状态的时候,借用了卡尔维诺“轻逸”的概念,并且他对此的阐释也是一种要求,他说,“诗歌如何以一种更为轻盈的方式来摹写生命,进而更为广泛地覆盖生活,而不仅仅是对于娱乐新闻、黄色段子、日常废话的拙劣模仿与简单挪用,乃是摆在当下的写作者面前的一个艰难的、无法回避的诗学命题。这种写作大抵如卡尔维诺所称,要的是一种‘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而不是‘轻举妄动的那种轻’。”[6]易彬没有贬低诗歌口语化,或许他还对此有些青睐,与此同时提出的要求也是极具现实性的,并且这也是评论者在面对“乌青体”及其他口水诗时所担心和极力批判的。他们害怕诗歌为了迎合大众流俗的审美口味而改变诗歌高洁、先锋的姿态和身份,使数千年建立的诗歌殿堂崩塌毁灭。这也是为什么尽管诗歌处于边缘化,但面对这一新的探索和挑战时仍然畏首畏脚的原因。
诗歌的形成也是诗人完成自我价值的过程。从当下来看,诗人在实现自己诗意人生的时候,就像张清华说的,“写作者完全可以使用分裂的方式——‘上帝’和‘市民’的不同方式,他有这样的权利,只‘用笔来写作’,而不会让人生太多地参与其中。”[7]10乌青也是一个基于生活的人,和弟弟六回一起经营“这里有诗”。无论是出于崇高价值的实现,还是利己主义对物质的追求,最关键的是,他们还有一些关于诗的想法,他们的心中仍然是诗。他们在经营着“诗”,并且所经营的“诗”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对于诗歌来说,这似乎在昭示着它的末路。诗歌的末路不光如此,就像诗歌的“边缘化”还包括诗歌的私人化写作。在80年代诗歌出现了“向内转”的现象,“诗歌‘退出所有人共有的领域,而进入主观主义的封闭圈’,或者诗歌因为是一种‘内在活动的表述’而变为‘小小的孤独练习’。”[8]当然这里我们不必讨论诗歌的本质到底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只阐释一种变化的现象。对于“诗”的经营,诗歌自身的独立价值确实是走向边缘,走向了末路。但相对于何同彬说的“向内转”、私人化写作来说,乌青对于诗歌的想法——让生活充满诗歌,却仿佛完成了又一次的公共写作。这种公共写作,是对于公共性生活经验的描写。这些简单琐碎的生活碎片是几乎每个人的生活中共同拥有的经验,尤其“口语”的使用拉近了大众与诗歌的距离。这里有一首《一个人的好处》:一个人到底有什么好处/我想了想,没想出来/因为没有女人/所以想了想一个人的好处/我想不出来,但想到了/一个破罐子的好处/是可以破摔。还有《给妈妈的诗》:妈妈,我送给你一首诗/礼轻情意重/看见它就笑一笑/你最美。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诗歌,那它就是以生活为底色的诗性碎片。当然还有很多人并不想把它跟诗歌放在一起,那它也是以诗意为韵味的生活。韩东、周亚平、蒋方舟等人在支持乌青的时候,也是从其诗歌语言的简洁性和诗性生活的书写来赞美、支持的。也就是,许多批评者在担心这是一次冒险的时候,在担心诗人难以平衡诗性的简洁与文字的戏谑时,他们其实也肯定了乌青对于文字的掌握和操控能力。
三、重新审视与评价
张清华在讨论网络诗歌写作与评价标准时说,“文学历来是有标准的,不止当权者会制订标准,而且写作者和接受者之间也会有默契,会遵守那些基本的规则;但另一方面,无须堆砌同时也还因为这种标准是多元和不断变化的,不能当作是现成和单一的律条。在今天我们其实很清楚,文学的标准仅是一个内心化的经验,是一个人心的法则,一个社会的契约。它在不同语境、不同条件下的内容,又应该是相对和多元的。”[7]88-89就像周星驰电影的重新上映,虽然重新上映没有对影片做任何改动,只是简单的二次播放,但之后的放映却比首映得到了更大的收益和反响。在同一地域内,我们不宜用一种文化的滞后性来看待此种现象,一种新的文化从生成到繁荣再到蜕变是属于自身发展过程内的。“乌青体”可能不只是于媒体上的一时喧哗,更可能它的发生恰恰是写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那种默契,并且我们也看到随着大众的审美发生变化,时代语境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整个文学界是否也要重新审视乌青的诗歌,或者给予相应的理论评价。吴思敬在《心灵自由与诗的超越》里说,“在这个空间里,诗人的思绪可以尽情地飞翔,而不必受权威、传统、习俗或社会偏见的束缚。”[9]当然这一定不是绝对自由的空间,并且也没有绝对自由的空间,因为诗人形象的成立已受到了“诗人”形象所带来的规约与束缚。我们总是要受到“诗”自身的束缚,并且这种束缚会随着“诗”的变化而变化。这仿佛已经构成了一个自我矛盾。
诗人对于诗的写作方式和呈现过程应该拥有自己的自由,但先锋性的表达往往都要受到传统的形式的规约或权利者的打压。仿佛人很容易做“叛徒”,诗人也是这样,这或许是所有人存在的局限性。我们在赋予诗歌自由的时候,又往往在经验的圈套里给它以规则、枷锁,并且在实践这种自由时又很容易陷入无节制的宣泄、侮辱、践踏,尽显贪婪与傲慢,直至放弃了我们对自由的想象,最后变成罪恶。似乎诗人、诗歌及其诗歌的评论也不得不陷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我们在无休止地争论时,不论是批评家扼杀了自由的权利,还是诗人阐释自由时发生了畸变,这成了对自由、对自我的背叛,潜移默化做了叛徒!那么这样解释下去,一切将步入虚无的循环中,永不得其意。具体到这里的诗歌,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在给予诗歌足够自由的同时,也要防止诗人滥用自由。批评一个诗人、一首诗歌,还要要求我们判断其是否属于诗歌范围的诗性表达,并且这种诗性表达的界定不能只遵守当权者的标准,还要考虑到接受者的审美要求。那么乌青诗歌的讨论就不再只是对于乌青个人及其乌青诗歌能否得到文学界重新审视和进入公正评价体系的问题,还是继“第三代诗歌”之后对诗歌语言更大胆的试验,对诗歌能否回到公共空间、走进具体生活的先锋性探索和冒险,更重要的是又一次以变革的姿态来拷问整个评价体制和传统的诗歌内涵。
在这个开放包容的时代,“乌青体”诗歌于当下的意义在于充分利用“对汉语诗性潜质的勘探,对‘榨干了意义’之后的语言效果的充分实验”,[10]将诗歌与现实进行融合,让生活处处充满诗意,诗歌不再处于边缘状态而是与大众的审美协调一致,并重新建立起诗歌与读者沟通的方式,让诗歌再度走进公众视野并得到流行和推广。虽然受到了种种争议,但是,即便是争议也是代表了人们对于诗歌的关心。毕竟,在这个泛娱乐化的时代,有人关心诗、讨论诗、并尝试着去写诗,也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