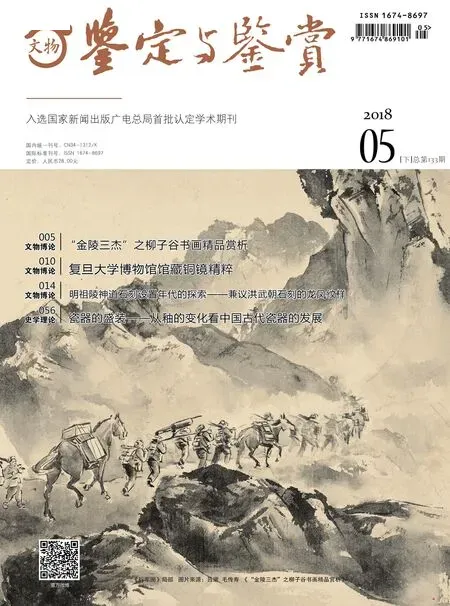北朝青州及其他地区佛教造像的彩绘问题
陆一
(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北京 100029)
1 北魏时期
现藏于青州市博物馆的多座北魏时期的造像碑及单体造像,造像上残存彩绘痕迹。北魏佛像多雕刻褒衣博带式袈裟,以北朝晚期(386—534)的一尊石雕单体佛立像为例,造像上有用红、绿二色彩绘的田相,胸腹部带结现呈淡蓝色,脸部及胸部裸露部分贴金。此外,在部分背屏式造像碑的身光部分也是用现可见为红色、青蓝色的颜色绘制,且这种造像彩绘的习惯延续至青州东魏北齐时期。
西安灞桥附近发现了一批北魏青石彩绘造像(编号S-001/04~S-007/04),在部分造像上肌肤裸露的部分(如颈面、前胸、脚部)有金箔残存,菩萨像的衣褶有白、蓝、绿等彩绘,璎珞上用金箔装饰,坐佛袈裟用大片红色彩绘表示。根据物质成分的检测分析,西安这几件造像可能是先以白色为底,第二层再敷彩饰金。袈裟的红色颜料成分为朱砂,造像上的绿色所用矿物为孔雀石,衣物边的蓝色成分为佛青(群青、青金石)[1]。这种造像彩绘的方法似也可见于甘肃泾川出土的一件北魏造像碑上,以白灰打底再加上彩绘,所用绿色颜料为石绿[2]。北凉北魏时期的敦煌壁画中的服饰,有的是直接着色,有的则是先托白底再涂色[3]。这种先用白(灰)色打底,再敷彩表示人体及衣饰的方法是否在当时是一种成式,是一种绘画与造像皆用的方法。
中原地带的石窟开凿完成后,也会用统一的大批彩绘装饰,石窟的造像上仍有彩绘残留,但经过后世重装很难判断彩绘的时期,此时科学检测的介入便是极有帮助的。云冈东部、中部洞窟内采用的颜料也多为天然矿物,窟壁彩绘也是用白色石膏打底再施彩绘[4]。巩县石窟的飞天、伎乐供养人、帝后礼佛仪仗造像的衣物都有已经褪色的部分彩绘残留。石窟内的塑像与上文提及北魏佛教造像的彩绘是否为同一种方法还需进一步对比研究。但也可说明东魏北齐时期佛教彩绘艺术并非是在某地一蹴而就的,而是基于北魏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2 东魏北齐时期
此时期的青州地区贴金彩绘塑像可说是大放异彩,东魏至北齐时期造像的造型也逐渐发展成熟。无论是菩萨还是佛像的雕刻,大多体态柔和有凹凸感,比例匀称。青州市博物馆收藏的大多北齐菩萨像的宝冠、项圈、璎珞、手钏、等饰物部分贴金,周身披帛、僧祇支、下裙主要有红、绿、蓝三色。北齐造像上佛衣的制作较之前期更加贴合身体曲线,多用以下几种方法表示佛衣:U形阴线平行双刻或仿泥条贴塑法表示衣物垂坠感;通身未做过多雕刻,突出衣缘部分(类似寻常衣物的领口处);在以上的雕刻基础上红、绿彩绘(田相)袈裟,衣缘多用淡蓝色。李森先生提出青州龙兴寺有部分造像的贴金彩绘可能是后世重妆[5],故在考察这批造像彩绘时,应注重选择并结合参考其与周边地区造像彩绘的关联性。
河北邯郸临漳地区附近近年来出土大批北朝造像,其中东魏北齐时期造像中也存在不少贴金彩绘造像,虽然体量不及青州造像,但佛衣的制作可与其进行对比研究。同样是U形阴线平行双刻、红色涂绘袈裟的有东魏武定五年(547)僧略造释迦像、道智造释迦像、立佛像等。而雕出衣缘部分,周身无衣纹雕刻,以红、金间绘田相袈裟的方法多存在于邺城北齐着袒右式袈裟的佛像上。造像肌肤裸露部分处(脸部、胸部)可见有金色残存。虽然邺城地区菩萨造像的体量规模明显不及青州地区,多以背屏式造像的组合出现,但从残留的颜色亦可见宝冠、项圈贴金,下裙彩绘红色等特征。河北其他地区也出土了北朝晚期的彩绘造像,如灵寿县幽居寺塔出土的三尊着半披式袈裟的白石坐佛像、白石弥勒坐像,具有与上文提及的雕刻佛衣特点:贴体,阴线双刻衣纹,强调衣缘。但除了有淡蓝色衣缘的红色袈裟之外,还表现了一种红色衣缘、淡蓝色通身袈裟的佛衣,主尊左侧弟子着淡蓝、红色两件法衣,右侧弟子着红色衣缘、淡蓝色法衣。这种红蓝二色的佛衣彩绘在邺城北齐造像中也有出现。定州博物馆收藏的一尊着敷搭双肩下垂式法衣的白石弟子像,在阴线雕刻的贴体两层袈裟上用红、金绘制田相。
河北邺城东魏北齐造像与曲阳、沧州、定州等地的造像可能均出自一系。虽然青州地区北朝造像与邺城周边地区造像在体量、组合形式上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其在上文所述的彩塑技法层面的共通性不容小视。
3 高齐辖区造像彩绘背后的历史问题
东魏北齐时期,轻薄叠褶的雕刻方式出现在高齐辖区下的诸多造像的佛衣表现中,而学界普遍持有的观点是受印度笈多王朝艺术的影响[6]。邺城数座同时期周身光滑、只在袖口处雕刻的造像则也可能与印度萨尔纳特佛像的雕刻有关。邺城、青齐地区在贴体佛衣上彩绘似乎是一种自身的艺术变通方式。
《十诵律》中提及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真金色,项有圆光”[7]。佛有真金色身,故而给佛像肌肤的裸露处贴金。而关于僧侣服装的用色,《摩诃僧祇律》中记:“若比丘的新衣,当三种坏色,若一一坏色青、黑、木兰。”这里的“木兰”色可能是一种暗红色。宋代赞宁的《大宋僧史略》中记到:“案汉魏之世,出家者多着赤布僧伽梨,盖以西土无丝织物,又尚木兰色并干陀色,故服布而染赤然也。则西方服色亦随部类不同,萨婆多部皂色衣也,昙无德部绛色衣也,弥沙塞部青色衣也。着赤布者乃昙无德僧,先到汉土。耳后梁有慧朗法师,常服青纳。”[8]北朝时期在汉地无论是本土还是西方僧侣衣着用色可能多为青、黑、赤红三色,在北朝佛教造像的衣物也多为这几种色彩(或间有黄色)。其时现实法衣的穿着可能影响到了造像的塑造,造像上的佛衣制作也不太可能为了追求奢华而太过违背戒律。
《洛阳伽蓝记》述:“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东魏北齐崇佛之风尤盛,邺城作为都城汇集了大批高僧名匠,其时邺城地区造像的水平与风格应已是北方地区的翘楚,曲阳、沧州、定州等周边造像均出一系。北魏晚期,河北流民多散于青州,宿白先生认为青齐(今山东)地区东魏北齐时期造像与河北、邺城地区相近的原因应该考虑到河北流民中的工匠[9]。但杨泓先生却觉得青州造像并不是仿自河北地区[10]。青州造像形成的原因复杂,可能是多重历史原因造成,多种影响融合。
从最初用象征物来表示佛,至后期允许偶像的崇拜,佛教传入中国也被称为“象教”。中土的单体造像彩绘在北魏时便已经存在,经北魏后期太和改制北方地区造像可能受到南方造像风格的影响,至东魏北齐随着类似印度笈多佛衣雕刻风潮的再传入,轻薄贴体佛衣在青齐(今山东)、河北地区流行,其上彩绘的艺术空间也随之放大,并影响隋唐乃至之后彩绘造像的营造。■
[1]荣波.北魏青石彩绘造像的颜料分析研究[M]//2005年云岗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保护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2]梁嘉放,夏寅,张勇剑等.甘肃泾川出土5件佛教造像彩绘分析及相关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6(4):97-104.
[3]马玉华.北凉北魏时期敦煌壁画的技法及色彩构成[J].敦煌研究,2009(3):18.
[4]李海,陈顺喜,解廷凡等.云冈石窟彩绘颜料初步分析[J].文物,1998(6):87-89.
[5]李森.试析青州龙兴寺造像贴金彩绘并非均系北朝装饰[J].世界宗教研究,2008(2):44-49.
[6]宿白.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J].文物,1999(10):47.
[7]十诵律[M]//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出版地不详:河北省佛教协会,出版年不详.
[8]赞宁,富世平.大宋僧史略点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5.
[9]宿白.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J].文物,1999(10):46.
[10]杨泓.关于南北朝时青州考古的思考[J].文物,1998(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