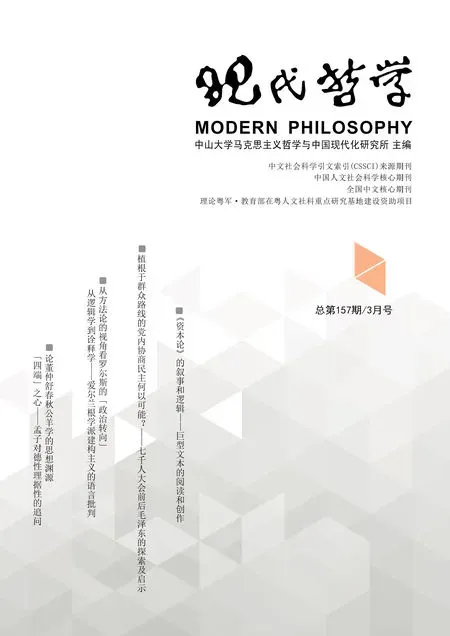基础存在论之此在的有限性根基
——基于《康德书》的分析
李日容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要建立的是一种基础存在论。它作为有根的存在论是在存在而非存在物(das Seinende)的层面上,对存在物之存在这个传统形而上学之基本问题的回答;而此在(Dasein)的时间性(Zeitlichkeit)是其核心,在《存在与时间》中是通往存在之意义的必然准备。海德格尔认为,基础存在论作为“人”或此在的形而上学*在《存在与时间》和《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海德格尔都将哲学确定为属于人之本性的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一词在这里也不像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那样,仍具有正面的含义。孙周兴指出:“后期海德格尔几乎不再提‘存在论’(Ontologie),也忌讳用‘哲学’一词来标识自己的思想。”(参见[德]君特·菲加尔:《海德格尔》,鲁路、洪佩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0—131页;孙周兴:《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07页。)是一种必然发生着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并不是从此在之外强加给此在的,毋宁说此在生存着就必然是形而上学地或存在论地生存(Existenz)。那么,为什么形而上学必然是此在的形而上学,换言之,基础存在论的“必然性”到底根源于何处?本文将通过对《存在与时间》和《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KantunddasProblemderMetaphysik,以下简称《康德书》)的考察(尤其是后者)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书》是《存在与时间》的“历史性”导论。正是通过前者,他澄清或“辩护”了后者中的基础存在论乃是一项严肃的存在论之奠基的事业,而非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只是一种“肤浅”的哲学人类学。作为《存在与时间》之“前传”的《康德书》从根柢上揭示了此在的时间性与其有限性的本质关联,因此缺少对这一“前传”的分析,我们既无法深入理解和把握《存在与时间》中的基础存在论思想,也难以真正洞悉海德格尔存在之思的深刻的哲学意图。
一、《康德书》中本质存在(Wesen)*鉴于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阐释主要是他的基础存在论思想的又一(或“历史性”)阐发,因此笔者一般将Wesen与“此在”同等使用,在不同的语境中,为了表达方便或顺畅,有时用“本质存在”,有时用“此在”代之。关于Wesen的含义及其翻译,参见[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7页,译者注①。 的有限性与超越论想象力(transzendentalen Einbildungskraft)*对超越/超越论的(Transzendenz/transzendental)概念的澄清是理解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乃至海德格尔哲学的关键,王庆节指出“它是理解和把握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以胡塞尔为开端的现象学哲学传统的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口”。transzendental在康德哲学中一般翻译为“先验的”,意为先于经验并作为经验的先天条件之意,但是鉴于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哲学的存在论解读,笔者赞同王庆节的观点,即在海德格尔哲学以及海德格尔的康德阐释中将其翻译为“超越论的”,以强调这个概念在康德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不同意涵,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为认识论(康德)与存在论(海德格尔)的区别。在本文中,“transzendental”一词如果在康德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笔者按照一般的译法将其翻译为“先验的”;如果在海德格尔哲学的意义或海德格尔的康德阐释意义上使用,笔者将其翻译为“超越论的”。具体的分析与原由已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可参见王庆节:《超越、超越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11—12页,译者注③。此外,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的存在论改造与其基础存在论的构建密切相关,或者说是《存在与时间》中此在之时间性思想的“历史性”阐发,但鉴于本文的侧重点主要是从海德格尔的视角出发来讲他眼中的康德,因此,本文仅着眼于论题本身的进程来论述海德格尔的康德阐释,而不强调或对比两者在想象力思想上的具体异同。王庆节已经对此作了非常清晰的梳理,可参见王庆节:《先验想象力抑或超越论形象力——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概念的解释与批判》,《现代哲学》2016年第4期。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是一部认识论(正如新康德主义者所解读的那样)而是存在论的著作,即它不是探讨真正的知识的定义及其“构成”的,而是探讨知识的发源及其存在论基础。由此,康德的“哥白尼转向”就不在于知识与对象两者谁符合谁的问题,而是在于存在物之存在或知识对象的生成是如何得以可能的问题。换言之,这个“转向”不是从“知识符合对象”到“对象符合知识”的反转,而是从“知识如何构成”的静态层面转向追问知识如何得以可能的生成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形而上学或存在论的一次奠基,而具体地阐释这一奠基或者说将康德没有想到但却在其思想中已经包含了的东西阐释出来,就是海德格尔康德阐释的核心任务。
存在论或一般形而上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存在物之存在是如何得以可能的,而使得这个“可能”得以可能的就是“超越”(Transzendenz)。在海德格尔这里,所谓“超越”是指超出存在物并使得存在物之存在得以可能的那个境域,它实质上是存在物从“无”到“有”的过程。“有”不是在自在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在存在物获得了某种意义因而能够对人“显现”出来的意义上说的;同样,“无”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在存在或超越意义上的“有”。“虚无意味着:不是一个存在物,但依然还是‘某物’。它‘仅仅用来作为关联物’,也就是说,依照其本质,它乃纯粹的境域。”*[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117页。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出了存在物的存在法相(Seinsverfassung)即先天的时空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它们作为经验对象构成的必要元素,就是存在物之为存在物的“原因”或“根据”,它们的源始统一使得经验对象的生成得以可能,因此存在论知识的内在可能性就在于知性与感性的结合,即超越论的演绎或者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如此,要追问存在论知识的内在可能性,就要弄清楚先天综合判断的本质,而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就意味着先天的“超越”如何可能,也就是说,“综合”意味着“境域”的生成。这表明存在论的知识就是纯粹直观与纯粹思维的统一所“生成”的那个源始境域,就它们的统一活动所形成的境域使得经验对象乃至知识得以可能的意义上,存在论的知识就是超越论的。如果存在论的知识是超越的,那么它们就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个使得知识得以可能的境域。由此,海德格尔将康德的先验知识结构之统一阐释为存在论或超越论的知识,即“纯粹知识的系统整体是对超越的形象”。*[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118页。
然而,“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存在的最大困难,就在于纯粹理性的先天知识如何可能与后天的感性经验相结合。康德虽然没有彻底地解决这一“难题”,但无疑给出了十分重要的“线索”。他认为知性与感性两者最终得以统一,是由于先验想象力所发动的纯粹综合活动及其活动结果的图式亦即时间图型(或先天的时间规定)这个沟通感性与知性的中点;如此,要探讨存在论知识的内在可能性就要回溯到那使其得以可能的“胚胎处”,亦即超越论想象力来澄清知识的“源泉”;而之所以最终会回溯到这里,在于人类知识的有限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纯粹理性批判》之所以是存在论或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在于康德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将人的有限性置于哲学的开端;而之所以有“哲学”,就在于人是有限的。人的有限性首先体现在人只有感性直观而没有理性直观,即人的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概念(人的认识同样需要思维)与直观,两者缺一不可。相比之下,神具有源生性的直观,存在物是由它自身所创造的(通过神成形发生),因而它无需思维也不需要感性就能完全通达它。问题是,作为有限的本质存在,人如何能够“通达”并不是它自身所创造出来的存在物?这对于并不能创生出存在物从而必须“依赖”于已然的存在物而存在的有限的本质存在来说,不可不谓是性命攸关的。传统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主体性哲学)是建基于主客二分的基础上的,即主体与客体的存在对于其而言是不言自明的。问题在于,诸如主体与客体如何能够“存在”或者其生成的根源何在这样的更根本性的问题却被“忽略”过去了,导致了以主客二分为根基的主体如何通达客体的问题注定是“无解”的。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人类知识之有限性本质的强调无疑与他的存在之思是“遥相呼应”的。如果人类的认知本身无法创生出存在物,那么人如何能够将在它之外的存在物看作是它的存在物?由此,作为主体与客体生成之基础的、居于人与物之间的更为源初的“关联域”便提上了哲学的“议程”。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之所以能够将作为“他者”的物看作是它的物*根据王庆节的研究,海德格尔在前期的此在的生存论哲学中并无严格的“他者”概念(因为物之意义虽然不是意识主体所给予的,却是作为生存主体即此在的上手交道对象而存在),而在后期哲学中使用的“会死者”这个概念才隐含了一个真正的他者概念,这个他者就是“不会死的诸神”(die unsterblichen Goetter)。笔者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后期海德格尔对传统西方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进一步克服。(参见王庆节:《道之为物:海德格尔的“四方域”物论与老子的自然物论》,《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第19—57页。),在于“人”能够创生出与其的存在“关联”,“人”创生出何种存在的“关联域”,存在物也就如何来相遇照面,即已然的存在物才能取得它的存在意义从而对有限的本质存在显现出来,而这个“关联域”在《康德书》中就是本质存在的超越论想象力之纯粹综合活动的结果。正是其使得纯粹思维与纯粹直观两者能够相互依存与合一,从而形成超越的境域外观或成像境域亦即式-像(Schema-Bild),如此才会有经验对象乃至知识的产生。也就是说,超越论想象力作为有限的本质存在的一种“能力”,使得本质存在的有限性能够是超越的。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其进一步生存论化为此在的时间性,正是此在的时间性使得此在的有限性能够在其中得以生存。那么,超越论想象力如何创生出与已然存在物的存在“关联域”呢?澄清这个问题,是进一步阐明此在之有限性与基础存在论之必然性关联的基础。
二、“我思”的“本质”:超越论想象力作为源始的时间性
超越论想象力作为有限的本质存在的“能力”之所以能够形象出超越的境域外观或成像境域,在于它具有使得纯粹概念感性化或图式化(Schematismus)的形象能力。这意味着在纯粹直观中就存在着概念的综观(Syposis)作用,唯有如此,纯粹直观才能是正在领受(hinnehmen)着的自己给出,即给出境域外观从而使得有限的本质存在与对象的相遇得以可能。这恰好说明纯粹感性就是有限的直观,其有限性就在于它不能直接创生出存在物,而只能源生出存在物能够来相遇的境域外观一般,而纯粹直观的可领受就是对关联物一般的领受,或者感性直观的可领受活动与关联物一般的形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它是自发着的领受活动。在超越论想象力之纯粹综合活动的过程中,依存于直观的概念成形并将对象带将出来,也就是说范畴以源初的和本真的概念成像一般而显现出来。因此,以图式化的方式所进行的概念的感性化过程作为统一之表象只是就赋予规则的功能而言的,而非是现成概念的普遍性对个别性的统摄,这也表明概念不是由知性所产生的(因而其综观不是来自于知性的综合作用),而毋宁说概念的综观或产生是源初地植根于以超越论想象力作为基础的纯粹直观与纯粹知性的源初为一的结构整体之中。换言之,范畴源初地依存于纯粹综合与纯粹直观,它们的成形发生与有限的本质存在能够遇上某个“对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此,它与时间有着本质上的关联,从而成就了超越。范畴“伴随着‘让对象化’一起成长形成,因此,它从一开始,当某个有限的本质存在遇上对象之际,就规定着对象,亦即存在物”*[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81页。。由此,超越论想象力不是与纯粹直观以及纯粹思维相并列的本质存在的另一种“基本能力”,而是作为知识两枝干的“根柢”,作为本己的能力形成了知识的两个纯粹要素的统一。对于这三者的关系,一方面既不能从经验的一元论亦即本源与派生的角度来把握纯粹想象力与思维和直观的关系(尽管在海德格尔看来,后两者在本质上都可以被“回溯”到前者),因为在形成境域外观的过程中,超越论想象力同样离不开思维与直观这两个纯粹要素,必须是三个能力一起才能形成超越的结构;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这三者看作是灵魂的三种现成性的能力(仿佛它们的“结合”只是既定元素的外在“相加”似的),而是要把植根于超越论想象力的思维与直观的内在合一看作是一个动态生成的结构整体。在这样一个结构整体中,超越论想象力之所以具有更加源初性的地位在于它是“源”,“源”使得思维与直观合一从而成为“构”,即三者一起才能达到“源构发生”。而“源构发生”之所以可能或者说超越的本质结构之所以能够形成,其根本的“秘密”在于时间。在海德格尔看来,纯粹知识三要素的源初统合正是纯粹综合的三种模式(即纯粹统握的综合、想象再生的综合以及概念认定的综合)在时间中的源初为一,即它是通过时间之三个向度(当前、过去与将来)的源初合一而发生的。
这如何理解呢?首先,纯粹统握的综合是在经验的直观中发挥作用的,而经验直观就是对感性杂多的直接领受,“杂多”体现为彼此相继而有意义。如果我不能区分一个个“现在”,就不能对一个个的感性杂多进行“辩认”,也就无法领受杂多。因此感性杂多必然是存在于前后相继的“现在”时间之中的,唯有如此,才有“流敞”和“集拢”的印象。如果经验直观在“先后相继的现在序列的境域中”恰好把握到它自身所提供的一个个外观即图像,那么它就是“直接的映像活动”,即抓取到“当前在‘现在’中的存在物”。这说明经验直观在每一个瞬间所把握到的就是一个个包含着杂多的外观,因此直观本身就是综合性的。这之所以可能在于纯粹统握着的综合,只有它才能形象出时间的表象即纯粹的直观。简言之,任何一个经验直观都包含着杂多,而杂多要能够被表象为杂多,首先需要心灵能够“在印象的彼此相继中区分时间”*[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也就是说,对经验杂多的领受要以时间的区分为前提。因此,纯粹统握着的综合作为形象出“现在和现在序列”的纯粹综合的活动并不在时间的境域中进行,相反,它是形象出时间境域的东西。唯有如此,“才使杂多成为这样的杂多并被包含在一个表象中”*[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前揭书,第128页。,也就是说,经验直观总是当下的关于存在物的直观。这之所以可能,在于纯粹统握的综合形象出“现在之一般的直接外观”,即形象出“现在”的时间,这样它才能把握杂多以及存在物本身。“纯粹直观着的呈现活动(作为给出外观的形象活动)所制造(作为创造活动的形象活动)出的东西,就是现在本身的直接外观,即总是当今的现在之一般的直接外观。”*[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170页。如此,纯粹统握的综合本身就是“时间性地形象着”,即意味着它具有时间特性。因此,从本质上说,作为自发着的领受活动的纯粹直观就是超越论想象力,而前后相继的现在时间序列及在其中的境域必须建立在纯粹想象力之上,如此纯粹统握着的综合就必须作为纯粹想象力的一种模式而得到理解。又鉴于前者本身就是时间性地形象着,如此,超越论的想象力本身就具有纯粹时间的特性。
那么,纯粹再生的综合呢?康德认为,想象力再生的综合意味着心灵能够表象以前出现过但现在已经不再的表象,唯有这样,心灵才能获得一个完整或统一的表象。如果先前表象过的东西不能再重现,来了新的就忘了旧的,那么一个完整对象的产生就是不可能的;如此,人们在当前所遭遇到的东西就总是一个一个的“新物”而无法对其进行“识认”,人就无法认识任何事物。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某物,在于已经预设了再生的综合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心灵能够将过去的表象保存下来,并且能在当下中再生出来。这之所以可能,首先需要“心灵”能够“识别出诸如‘先前’‘当时’这样的东西”,即它能够区分出“过去”与“现在”的不同的时间向度,这样它才能将“过去”经验到的存在物保存下来,并在“当下”将其再现出来。“再生模式中的经验综合要成为可能,就必然在事先已经有一个‘不再现在本身’能够先于一切经验地被重新提供出来,并且,它还能够被整合到当下的现在之中去。”*[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172页。这个“不再现在本身”必须通过纯粹再生的综合才是可能的,因此作为再生模式的纯粹综合就形象为曾在本身,这表明纯粹再生的综合就是时间性地形象着。如果说想象力再生的综合是经验的,那么纯粹再生的综合的想象力就是越超论的,“纯粹想象力就是时间性地形象着”,“它完全展开了可能的返回活动的境域——曾在,并且因此把这种‘后面’本身‘形象出来’”*[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173页。。所谓“‘后面’本身”是指纯粹再生的综合活动对“不再现在”进行的、保留着的形象活动总是在“现在”那里整合自身。这样,纯粹再生与纯粹统握的综合就是统一的,前者形象出曾在,后者形象出当前或现在,二者统一才能让过去的“当前”来到当下。如此,“每一个‘现在’都是刚刚经过了的现在”,也就是说“现在”中同时有“曾在”。这表明纯粹统握的综合之所以能够形象出统一的现在之外观,还需要“曾在”能够在当下“重现”,如此综合就不可分割地体现为统握与再生这两种模式的统一,亦即超越论想象力的纯粹综合活动形象出时间之当前与曾在的统一。
那么,它又如何通过作为纯粹认定的纯粹综合来形象出时间的“将来”呢?首先,要使一个统一的对象的显现得以可能,就需要将过去的东西与现在在场的东西设为一个统一体,亦即心灵必须能够将再生的综合所产生的东西与当下显现出来的东西设定和保持为同一个东西。这就需要直观统握与想象再生这两种综合已经事先指向那“同一个”的东西,亦即事先指向那个“统一体”,否则就不会有(统一的)对象产生。而那个早已走在“前面”的“统一体”,事实上就是概念的综合,因为概念正是作为统一的表象而“适合于众多”的自一的东西。如果没有统一的概念的综合,那么杂多、我们逐渐直观到的东西、还有再生出来的东西就不会被结合成一个表象。因此,概念的综合就是首要的综合,它导引着直观统握与想象再生的综合,能够为这两种综合之一般“找到某种存在物意义上的完整范围,在这个范围里,这些综合有可能将它们提供出来的和遭遇到的东西仿佛作为存在物显现出来和加以领受”*[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176页。。康德把概念的这种综合看作是概念认定的活动,它首要地使得对存在物的经验直观得以可能,但是作为经验性的综合,它必然以某种纯粹的认定或综合的可能性作为前提,否则存在物的经验直观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纯粹的认定活动预先形象出的就是“可持驻性之一般的境域”,这就是想象力的纯粹-前像的活动。鉴于它在本质上比其它两种同时共同隶属的模式更为优先,所以它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将来”这种时间样式在时间性的统一中是优先的,时间的最源初的本质就是从将来到时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纯粹综合的三重模式具有内在的时间特质并且其本身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时间统一体,由此表明超越论想象力就是源生性的时间。作为源始的时间性,它形象出时间之三个向度亦即当前、过去和未来的合一,从而使得纯粹综合能够形象出存在论知识之整体的超越。鉴于超越论想象力就是源生性的时间,作为有限的本质存在的自身性就是时间性,因而“自我”在本质上就是超越的,经验主体及其经验性的时间规定性均以此作为前提条件。如此,作为“自我”的时间与“我思”就不是“互不相容或异质反对”的东西,而是具有源初的自一性。康德之所以认为“我思”与时间是不相容的,在于他混淆了源初的时间性与存在物的时间规定性。在后者的意义上,“我思”不可能是有时间的,毋宁说“我思”就是源初的时间性本身。“正因为自我在它的最内在的本质中源初地就是时间自身,‘我’才可能被不作为‘时间性的东西’(Zeitliches),在这里即是时间内的东西来把捉。”*[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186页。也就是说,唯有自我源始地就是时间性本身,实体意义上的无时间的自我才是可能的,不仅如此,超时间、非时间、在时间之中等都只有在源初的时间性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三、基础存在论的必然性:此在的时间性使其有限性得以“生存”
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本质根据进行发问,就是对人之基本的“心灵”能力的统一性即对人本身进行发问。康德认为理性的一切旨趣可以归结为三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为第四个问题: 人是什么?那么,它们在何种意义上被归结为第四个问题呢?“能够”、“应当”或“希望”这些字眼总意味着发问者自身的有限性,神从来不会追问或关心他能够、应当或希望什么或怎么样,因为它是自足无限的,外在的东西它统统不需要,它无须为自己的“存在”“操心”;而对“我能够、应当或希望……”进行发问的东西,意味着它在本质上就是有限的。这说明对于有限的人类理性来说,它最内在的兴趣总是关联到它自身的有限性,并且对于它来说,至关紧要的并不在于消除这种有限性,而是将这种有限性确定下来并在这一有限性中保持自己。正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它才会追问前三个问题;也正因在“有限性”的意义上,它们才与第四个问题内在地关联起来,也就是说才能够最终被归结到这个问题上。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是什么”的问题或人的本质有限性作为形而上学奠基的真正成果,是对形而上学的本质根据性进行追问,也就是把对人之有限性的本质进行发问与形而上学的奠基内在地关联起来。尽管康德由于被问题本身所迫而走到了超越论想象力亦即源始的时间性面前,但他却因为它过于“幽暗”而在此道“深渊”面前退缩了(在某种程度上说,仍然局限于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康德必然会在这一“深渊”面前退缩),正是此道“深渊”使得人之有限性的疑难成为了问题。如此,就预示着基础存在论亦即关于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的必然出场,并且“只有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才能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导言第2页。。
那么,如何将作为人之本质的有限性规定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况呢?或者说,存在本身与人之本质的有限性关联何在?在《存在与时间》中,超越论想象力的图式化或作为源生性时间的超越论想象力的结构,被进一步生存论化为此在的时间性结构,但人的有限性都是作为形而上学奠基的“拱顶石”而出现的,人总是与存在物相关联。但这种“关联”之所以可能,在于此在之“超越”即此在的存在领会。人之有限性使得它必然发生存在之领会(存在之领会是人之有限性的最内在的本质),从而使得它能够生存,因此它才能作为它所是和所不是的存在物,亦即才能与存在物有关联。“如果存在之领会没有发生,无论人被赋予了多么奇特的能耐,它绝不可能作为他所是的存在物去存在。人是一种在存在物中间的存在物,这样,他所不是的存在物以及他自身所是的存在物,在那里总是一起被公开出来。人的这种存在方式我们称之为生存。惟有在存在之领悟的基础上,生存才成为可能。”*[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217—218页。此在本质上就存在于世界之中,这是由它对存在的领会所决定的,因为此在是有限的,它不得不发生存在的领会,不得不在世界之中。正如有限性是此在的本质结构,因此“在世界之中”就是此在最基本的生存论结构。所谓“在世界之中”,意味着此在通过它的存在领会或它的世界来建立起与自在的存在物的“关联”。因此,此在在世界之中就是存在物之为存在物的根据与前提条件,它通过它的存在领会开展出世界,通过它的世界开展出存在物之存在,即赋予自在的存在物以意义,使得它们通过它的世界而得到“彰显”。这表明建立在存在之领会的基础之上的生存是区分存在物的基础,但是要使得“存在物是其所是和是其如何而是”,人又必须是那个作为被抛的存在物而存在,亦即此在首先和通常总是作为常人而存在,或者说此在的存在总是此在这个存在物的存在。因此,作为常人的此在总是从操劳着的东西,即从现成的存在物方面来领会它的存在,也才会有对存在的遮蔽性。于是,从康德形而上学奠基的成果出发,海德格尔达到了此在的操心结构亦即“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一世界)中的-作为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物)的存在”,以及它的时间性之意义即“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的统一性,此在作为时间性的存在总是时间性之绽出境域图式的整体到时,亦即此在源初地就是一个生存论时间的统一体。*[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372页。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形而上学奠基的复返任务,就是从人的有限性疑难出发,“在亲临-存在的自身过程中(im Da-sein als solchem),将时间性澄清为超越论的元结构”*[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232页。。而康德在形而上学奠基的进程中被逼迫着超过流俗的时间概念,退回到将“我思”作为时间性的“我思”,最终使得存在论知识的本质统一性或纯粹理性的感性化得以可能,也就是说以纯粹想象力为基础的超越的本质存在源初地建基在时间性之中。可见,“时间与超越论想象力的本质统一性”不在于时间是纯直观的形式(它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一开始就被如此阐释),而是完全由于此在的有限性所必然导致的存在之领会必须是以时间性的方式进行。
此在总是时间性地领会它的存在或者说此在总是以时间性的方式生存,反过来说,此在的存在之领会又体现了此在本质的有限性,或者说使其有限性能够实现出来。“惟有当存在这样的东西在,而且它必须在,有限性才会在那里生存。”*[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前揭书,第218—219页。此在的有限性或时间性是人之“最普遍”或人之最源初的“本质”,也就是说它比现成性的人本身更加“根本”,如此,“人是什么”的问题就获得了规定性。由此,有关存在物之存在这个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就从这里重新出发,它的奠基活动必然被建立在一种此在的形而上学亦即基础存在论之中,在通向存在之意义的路途上,它既基本又初始。换言之,形而上学的发生乃是出于人的本性,人的有限性使其得以可能和成为必然。由此,人之本质的有限性在哲学史上首次获得一种真正的存在论的意义,而人之有限性也就越发地从根柢上彻底地被暴露出来。这对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义乃至人本身的界限来说不可不谓是最深刻的“警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许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直到今天仍然振聋发聩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