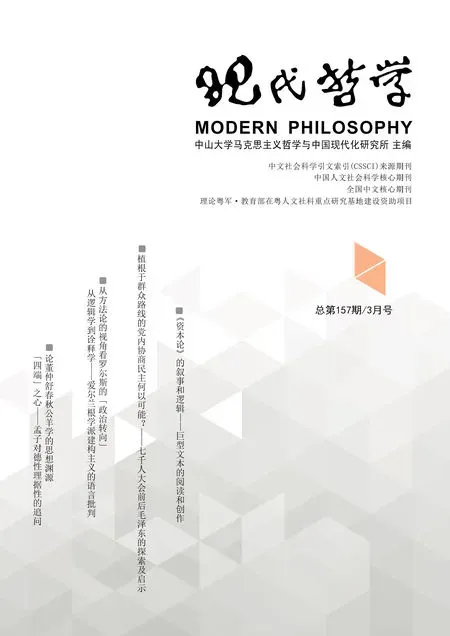在罗尔斯和诺齐克之间
——略论洛克财产理论的当代位阶
徐 峰
借用博登海默的说法,洛克的财产理论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博登海默曾经对“何谓正义”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可随时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参见[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厘清其理论真相一直是思想史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C.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p.100-130; Jeremy Waldron, The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8, pp.23-45; John Dunn, “Justic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ocke’s Political Theory”, in John Locke: Critical Assessments, ed. Richard Ashcraft, Routledge, 1991, pp.43-63; Barbara Arneil, “The Wild Indian’s Venison: Locke’s Theory of Property and English Colonialism”, in America. Political Studies, 1996:44(1); Matthew Kramer, John Locke and the Origins of Private Prop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55-96.。本文无意辨别这些研究成果得失,而是尝试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视域中思考洛克的财产理论。细言之,将他的理论同两位旗帜人物——罗尔斯与诺齐克——进行比较。罗尔斯被认为复兴了当代政治哲学,其“作为公平的正义”理念为达致一种平等社会作了强有力辩护。诺齐克则为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张目,认为财产再分配与个人的自由权利完全不相容。因而,罗尔斯与诺齐克代表了两种相悖的财富分配立场。
有趣的是,二人都试图从洛克那里寻找思想资源。诺齐克自认是洛克的继承人,坦言“关于政治哲学的思考都汇聚于洛克……现在正遵循令人肃然起敬的洛克传统”*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Inc., 1974, p.9.。罗尔斯坦承洛克的思考方式“为他们所处时代的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会继续阅读他的著作,并发现他的思想具有启发意义的原因”*John 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03-104.。然而本文试图证明,洛克的财产理论既不是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式的(right-libertarianism),也不是罗尔斯的自由平等主义式的(liberal-egalitarianism),而是锚定在他们二人的理论之间。对这三人而言,理论的歧见背后透射出对“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 right)命题的不同态度,进而生发出不同的财富分配观点。本文首先描述洛克证成财产权的基本策略,而后在同诺齐克和罗尔斯的比较中澄清理论分歧,由此勘定洛克的理论坐标。
一、洛克证成财产权的策略
在洛克的权利体系中,财产权同生命权、自由权一起,构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权利。财产权如何获得?需要满足哪些约束条件?又要遵守何种限度?洛克的回答主要集中在《政府论(下篇)》的“论财产”一章中。通篇来看,他的证成策略分为两步,首先是讨论货币出现前在“自然状态”中的初始占有,然后分析货币出现以及进入“政治社会”的合法持有(包括占有和转让等)。
在自然状态中,人们从出生起就对自己的人身享有某种所有权,这是自然法赋予的。为了维持生存,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将“身外的”自然资源“拨归私用”。在洛克看来,外在的自然资源本来就是上帝给人类所共有的东西,“上帝既将世界给予人类共有,亦给予他们以理性,让他们为了生活和便利的最大好处而加以利用。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给人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舒适生活的”*[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7页。。“拨归私用”让人们可以通过劳动占有果实,但其间必须遵守一系列约束条件:
第一,占有时要给其他人留下足够多且一样好的资源(Leave Enough and As Good to Others,下文简称“E&AG条款”)。洛克解释说,虽然个体劳动能使自然资源脱离原先的共有状态,但是占有时若不给他人留下足够多且一样好的资源,这种占有就是不正当的,是对其他人占有权利的侵犯。洛克生活的时代远达不到现代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渴求,这从他对土地占有的描述可见一斑,“这种开垦任何一块土地而把它据为己有的行为,也并不损及任何旁人的利益,因为还剩有足够的同样好的土地,比尚未取得土地的人所能利用的还要多”*[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前揭书,第21页。。
第二,占有后要以享用为度,不能糟蹋或损害所占资源(Spoilage Condition,下文简称“损害条款”)。洛克认为,自然资源本是上帝厚赐给人们享用,人们有义务保存好上帝的恩赐。“如果它们在他手里未经适当利用即告毁坏;在他未能消费以前果子腐烂或者鹿肉败坏,他就违反了自然的共同法则,就会收到惩处。”*[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前揭书,第24—25页。
在自然状态中,初始占有至少要满足上述“E&AG条款”和“损害条款”,才能称得上是正当占有。由正当占有所获得的物品资源,构成人们的合法财产。财产权受自然法的保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一旦人们签订契约,宣布离开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后,财产权的论证随之发生变化。
在政治社会中,由于引入货币和人们的(默示)同意,“E&AG条款”和“损害条款”的效力似乎有些式微*西方学界关于“E&AG条款”和“损害条款”在政治社会是否依旧具有效力争论不休。弗雷切特(Kristin Shrader-Frechette)曾简要梳理这一争论。Cf. Kristin Shrader-Frechette, “Locke and Limits on Land Ownership”,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 1993, 54(2).。这是因为一是外在资源已经不如自然状态中那般丰富,占有后很难继续留给他人足够多且好的东西,二是货币的出现使得财产的贮藏成为可能,不会出现自然状态中资源储藏过久而腐坏的状况。而且在政治社会中,人们以“同意”为基础赋予金银以价值,又通过明文协议同意确立彼此的财产所有权。这样的结果是,个人财产的严重分配不均成为可能,而这种分配不均看起来还是建立在彼此同意的基础之上。以土地占有为例,洛克曾直言:“这就很明显,人们已经同意对于土地可以有不平均和不相等的占有。他们通过默许和自愿的同意找到一种方法,使一个人完全可以占有其产量超过他个人消费量的更多的土地,那个方法就是把剩余产品去交换可以窖藏而不致损害任何人的金银;这些金属在占有人手中不会损毁或败坏。”*[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前揭书,第31页。麦克弗森据此批评说,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承认不平等的财产占有,本质上最终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奠基和辩护的。*C.B.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p.100-130.
本文并不认同麦克弗森的结论,而是相信“E&AG条款”和“损害条款”在政治社会完全失效的说法只是夸大其词。我们可以找到文本证据,表明洛克仍然希望这两个条款行之有效。譬如他在论及窖藏时说:“的确,窖藏多于他能使用的东西是一件蠢事,也是一件不老实的事。”*[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前揭书,第30页。笔者认为,洛克的本意只是坚持正当的财产都要受法律保护,他同样不希望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接下来,澄清洛克与诺齐克的理论差异之后,会发现洛克的财产理论不仅不会导向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反倒体现出平等主义的色彩。
二、诺齐克式的“弱的约束”
诺齐克在其代表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辩护了具财产权观点。他不像洛克那样区分“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而是引入资源持有的两个环节:“初始占有”和“自愿转让”。
论及初始占有时,诺齐克指出洛克的“E&AG条款”可以有“强的约束”与“弱的约束”两种解读。“强的约束”是指不仅使他人失去通过任何一种占有来改善自身处境的机会,也使他人不再能够自由使用先前能使用的东西;“弱的约束”是指仅仅使他人不再能自由使用先前使用的东西,却不包括其它内容。“弱的约束”意味着,只要一种初始占有没有使得别人的处境变糟,即便使得别人无法继续使用之前的常用之物,这种初始占有仍然是正当的。举例来说,一个人圈定一片肮脏破乱的公共沙滩,在一番精心打理和装扮之后宣布占为己有,并对光临这片沙滩玩耍的人们收取1美元门票,否则不准入内。若依对“E&AG条款”的“强的约束”,这种占用公共沙滩的行为当然不正当;而依照“弱的约束”,只要人们在沙滩玩耍获得的快乐值大于超过1美元门票的价值,那这种占用公共沙滩的行为就是正当的。
洛克本人在阐释“E&AG条款”时语焉不详,诺齐克认为洛克既可能主张“强的约束”,也可能主张“弱的约束”。考虑到“强的约束”对占有要求太过严苛,容易遭受“回溯论证”的反驳,进而永远不可能生成财产权*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Inc., 1974, p.176.,所以诺齐克相信只有“弱的约束”才更符合现实。如果接受以“弱的约束”为标准,只要占有行为没有使他人的处境变糟,哪怕他人不能一如既往地使用某类特殊资源,这个占有仍然是正当的。那就自然推理出奉私有制为圭臬是最好的选择,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能够让人们的处境变得更好。诺齐克直截了当地说:
通过使生产工具掌握在那些能够最有效率地使用它们的人手里,它增加了社会产品;因为随着由不同的人控制资源,一个怀有新主意的人不必只有说服某一个人或一小伙人才能进行实验,实验由此得到鼓励;私有所有权通过使某些人拥有不是用于当前消费而是用于未来市场的后备资源,保护了未来的人们;它为那些不随和的人提供了就业的门路,让这些人不必去说服任何人或任何小团体来雇佣他们,等等。*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Inc., 1974, p.177.
根据同样的理路,诺齐克坚定支持土地的完全私有化,因为即便土地集中在小部分人手里,带来的结果可能比其它时候更好。诺齐克在此面临一个棘手的挑战。这里的“比其它时候”是指何时?这关系到福祉比较的基准问题。有些人主张设置较低的比较基准,譬如同私有制出现以前相比*Leslie Francis, John Francis, “Nozick’s Theory of Rights: A Critical Assessment”,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76, 29 (4).,或同资源已被占有的某个特定时期相比*Michael Otsuka, “Self-Ownership and Equality: A Lockean Reconciliation”, in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98, 27 (1).,好处是容易证明施行私有制是惠及人们的善事。有人提出应当设置较高的比较基准,即有且只有其他人能够从单个特定的占有中获益,这个占有才是正当的*G.A. Cohen, Self-Ownership ,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76.。与较低的比较基准相比,较高的基准肯定会使私有制在证成上更加困难。遗憾的是,诺齐克在此着墨不多,从他的有限论述看,他似乎倾向于接受较低的基准,以使得证成私有化变得更加容易。
拥护私有制是诺齐克理论逻辑的直接结果,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侵犯正当占有的个人财产。完成初始占有后,就进入到第二个环节:资源(财产)的自愿转让。诺齐克认为,持有财产的人自愿向他人转让自己的持有物,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是公正的。他以篮球运动员张伯伦为例,任何对自愿转让的阻止和干预,都侵犯人们自由行使财产权。据此,诺齐克认为罗尔斯等人的再分配方案是一种包含了侵犯人们(财产)权利的严重事情,“任何带有平等主义成分的分配模式都会被个人的自发行为所颠覆;每一种令人满意以致实际上被设为分配正义之核心的模式化条件,也是如此”*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Inc., 1974, p.164.。
可以说,诺齐克是财产私有制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拥趸。除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外,他认为私有制不会支持任何更进一步的分配平等观念,人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抱怨自由市场带来的收入差距和贫富之别。“如果持有的状态是正当产生的,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一种以分配正义为根据的更多功能的国家。”*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Inc., 1974, p.230.正是在此意义上,诺齐克甚至认为“对劳动所得征税等于是强迫劳动”*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Inc., 1974, p.169.。
三、从洛克到诺齐克:断裂的平等叙事
诺齐克自诩洛克的继承者,但是二人在财产权的证成逻辑上大相径庭。上文已言,洛克在解释“E&AG条款”时语焉不详,以致诺齐克认为“弱的约束”才更为合理,进而得出结论自由放任的市场才是最佳选择。但下文将表明,即便搁置颇有争议的“E&AG条款”,我们也可以从洛克的相关论述中找出依据,证明洛克不仅不会置贫富不均于不顾,反而可能支持财富的平等分配。
1.“损害条款”一直发挥着作用
本文第一节业已表明,除“E&AG条款”外,在证成财产占有时“损害条款”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损害条款”要求,我们应以享用为度,不能超过实际所需,避免糟蹋或败坏上帝的恩赐。洛克清晰明了地说道:“谁能在意见东西败坏之前尽量用它来供生活所需,谁就可以在那个限度内以他的劳动在这件东西上确定他的财产权;超过这个限度就不是他的份所应得,就归他人所有。”*[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前揭书,第20页。“损害条款”不同于“E&AG条款”,后者一旦遭遇资源稀缺的处境便捉襟见肘,而“损害条款”更准确地说属于“内在性约束”,它和占有者的行动意志有关,重点是强调资源的占有不能超过实际所需,和外在资源的多寡关系甚微。有文本证据表明,在进入政治社会后,“损害条款”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例如洛克在“论财产”一章的末尾写道:“一个人据为己有的那部分是容易看到的,过多地割据归己,或取得多于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是既无用处,也不诚实的。”*[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前揭书,第32页。而且除《政府论》外,洛克还在其他一些地方阐述过类似观点,比如在论述德育时就说“人们拥有财产本身并不是恶,只是超出所享用的范围才会成为恶之源”*John Locke,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NuVision Publications, 2007, pp.87-88.。所以,在洛克看来,无论在自然状态还是政治社会,占有过多的财产占有都不符合他的本意,是一种毫无意义且不道德的行为。
诺齐克只字不提“损害条款”,其逻辑是:无论持有的财产是不是超过现实所需,只要它们符合正当占有或自愿转让,都是持有者的应得,受到法律的保护。可以设想,洛克断然不会认同诺齐克的结论。即便洛克认为私有财产需要加以保护,但仍谴责那些占用超出自身需要的行为是不诚实的。
2.上帝的存在与自然法的支配
作为虔诚的基督徒,洛克预设了上帝的存在,认为世间万物皆由上帝创造。他从这一预设出发,推导出一系列有关自然法的要求。“自然法是所有人、立法者和其他人的永恒的规范。他们所指定的用来规范其他人的行动的法则,以及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行动,都必须符合自然法、即上帝的意志,而自然法也就是上帝的意志的一种宣告。”*[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前揭书,第135页。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是永恒的存在,是高悬世间万物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自然法会如何规制自然资源来保护上帝的子民呢?这可从洛克关于“自保”的论述当中见端倪。他指出,每个人都是创世主的创造物,自然法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保存自己,不能擅自改变他的地位”,“基于同样理由,当他保存自身不成问题时,他就应该尽其所能保存其余的人类”*[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前揭书,第4页。。洛克的意思很明确,自然法要求人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保存他人,比如保存他人的生命、自由、健康或物品等。若是不平等的财产占有威胁到他人的保存时,那这些占有很可能得不到证明。
不仅自然状态如此,洛克对政治社会的思考,包括权利的确证和政治的推理都充满着基督教的假设*John Dun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n John Locke: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rgument of the “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26-30.。他虽未直言平等,但是可以合理地推测他对分配平等的呼吁。因为平等的意义在于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发现上帝的存在、履行上帝的义务。洛克始终要求人们“基于自然的平等”遵守“互爱义务”*[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前揭书,第3页。,要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人,使他们免于糟糕处境的困扰。
对诺齐克来说,他当然不可能设定洛克那样强烈的神学背景。他只是援引康德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原则作为论证的起点。诺齐克也强调“自保”,却不是洛克那种要求一种“兼及他人”的自保,而是主张每个人应该独立建构生活的意义,“既然一个人无法事先预知别人会不会接受其生活方式,所以允许别人追求他自己的生活观念也是符合你的自我利益的”*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Inc., 1974, p.50.。根据诺齐克的理解,道德上唯一允许的是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除此之外都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3.共同体的假设
洛克说,上帝创造的自然之物是留给人们共同使用的。言下之意是世间万物在未占之前都是有主的,属于世间的每一个人。这同他支持土地划归私用时的说法相得益彰:
一个人基于他的劳动把土地划归私用,并不减少而是增加了人类的共同积累。因为一英亩被圈用和耕种的土地所生产的供应人类生活的产品,比一英亩同样肥沃而共有人任其荒芜不治的土地要多收获十倍……我试问,在听其自然从未加以任何改良、栽培或耕种的美洲森林和未开垦的荒地上,一千英亩土地对于贫穷困苦的居民所提供的生活所需能否像在德文郡的同样肥沃而栽培得很好的十英亩土地所出产的同样多呢?*[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前揭书,第24页。
表面上看,私人占有更好是因为私有制的生产率更高,但生产率高、产量增加又是为什么?洛克这段话中提到了“人类的共同积累”,也提到是为了“贫穷困苦的居民”,他的表述背后暗示着有这样一个“共同体”*Maurice Cranston, John Locke, London, 1957, pp.210-211.。其中,人们共享着世界资源的所有权,产量的增加能够使更多的收益分予所有人,尤其是那些没有足够土地的人,这样就没有人会因土地稀缺而处境变糟。如果说这个“共同体”拥有某些权力的话,用洛克的话说,“他们的权利,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众福利为限。这是除了实施保护以外并无其他目的的权力,所以决不能有毁灭、奴役或故意使臣民陷于贫困的权利”*[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前揭书,第84-85页。。
难以想象诺齐克会在他的理论建构中预设所谓的“共同体”。因为他笃信只存在个体的人,不存在拥有利益的社会实体,“谈论社会整体利益就(故意的)把问题掩盖起来了”*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Inc., 1974, p.39.。对他来说,财产有且只有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形式得到证明,它跟任何社会实体没有关系,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如果笔者关于上述三方面的描述无误,我们可以指出洛克和诺齐克在财产权的证成上有着根本性差别。洛克从“损害条款”的效力、上帝的存在与自然法的支配,以及共同体的假设等方面出发,认为国家或政府需要对财产分配及贫富差距加以调控,不平等在道德上很难得到证明。诺齐克却坚持最低限度的国家,认为任何再分配都是对个人的掠夺,对财产权的侵犯。质言之,在财产权的证成上,从洛克到诺齐克有着一个断裂的平等叙事。
四、迈向何种平等:洛克与罗尔斯的分殊
根据罗尔斯著名的正义两原则,诺齐克设想的社会并不能保障公平与正义,至多是实现“前途向才能开放的平等”*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7.。罗尔斯直言不讳地批评诺齐克裹挟着洛克为自己站台背书:“今天,许多观点都被成为‘洛克式的’,但它们与洛克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关系。一些提出各种形式的财产权,但却不提供洛克提供的那种依据的观点——如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的观点——也常常被说成是‘洛克式的’。但是,对洛克及其当代传人来说,这种宗教背景是根本性的;忽视这一点就会冒严重误解他们思想的危险。”*John 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1.
根据罗尔斯的解读,洛克的财产理论不是诺齐克理解的那样,而与他的正义两原则更具亲缘性。“作为公平的正义”论证缘起原初状态,是人们在无知之幕背后达成契约、一致同意的结果,这与洛克在离开自然状态后通过契约进入政治社会的说法异曲同工。罗尔斯在《政治哲学史讲义》的“洛克讲座”中高度赞扬了洛克对财产权进行的某些限制:“它不是一种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的权利,也不是这样一种权利:我们对自己财富的使用不管给他人带来何种影响都无所谓。”*John 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47.他直言,与其说洛克接近自由至上主义,不如认为和自由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走得更近。*John 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50.
虽然在“洛克讲座”中罗尔斯甚少提及他的同洛克的理论差别,事实上在有关平等问题的思考上,尤其是达致实质平等的方式上,罗尔斯要比洛克要更加“激进”。如前文所述,洛克的财产权论证建立在作为上帝之法的自然法基础之上,但罗尔斯明白,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证明财产权不可能再诉诸非公共的进路,只能诉诸公共的政治正义观念,即在所有人都认定是正义的条款基础上,每个人都同其他人进行政治和社会上的合作。*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7.换言之,无知之幕背后深谋远虑的公民一致同意每个人都有平等的道德地位,每个人不仅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形式平等),还应该享有公平的机会平等(实质平等),而且如果不平等不可避免,那也要首先保障社会最弱势的群体的最大利益(不平等的限度)。
从洛克的角度看,他大概会同意罗尔斯的部分内容。例如,洛克认同人们生来就毫无差别地享有自然的平等,但囿于社会时代差别,自然的平等仅仅包括司法权力和自然权利的平等,不可能包括诸如性别平等之类的现代问题,而且这种自然的平等还潜藏着等级制的可能。*John 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51-152.此外,洛克还积极捍卫个人的私有产权,但又意识到要对财产施加某些限制,避免因无节制的占有破坏社会正义。如拉斯莱特所言,洛克甚至暗示,最贫穷的人也有足够多的理由需要社会予以保护。*Peter Laslett,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A Critical Edi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pparatus Critic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105.
但是没有理由相信洛克将同意罗尔斯的全部结论,尤其不会同意正义原则中的第二个原则的内容:公平的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这肇始于罗尔斯对平等主义理论的推进和贡献。他既体认到古典自由主义以降形式平等的重要性,还察觉到实现社会正义与实质平等的内在勾连。一般而言,出生于较高社会经济阶层或拥有较多天赋的人,会比出生贫穷家庭或较少天赋的人在能力和激励方面具有更多优势。无论是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都将这些优势当作自然之事。罗尔斯却反对说,人们出生的社会经济阶层或个人的天赋完全不应当影响其职业的成功。他把每个人最初的社会经济阶层和天赋的分配看作是偶然的和随机的,正确的做法是“把天赋的分配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共同资产,可以共享由这种天赋分布的互补性带来的较大社会与经济利益”*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7.。他用“公平的机会平等”取代古典自由主义秉持的“自然的机会平等”,以消除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试图使“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3.。
完全的经济平等当然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不平等”已然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洛克对不平等的限度的表述比较模糊。当把财产理解为物质占有物时,洛克看起来完全尊重一个人持久地占有另一个人的劳动产品、主人占有奴仆的劳动产品*Peter Laslett,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A Critical Edi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pparatus Critic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105.,但他又不断提醒人们,通过正当的方式获得财产,既要坚守不多占的道德律令,又要关心贫苦大众的糟糕处境。相比之下,罗尔斯表达出斩钉截铁的态度,差别原则允许的经济不平等必须要最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者,必须要从最差的经济地位的立场去评价社会分配方案,不平等不能以损害社会最不利者为代价。可以说,在允许经济不平等方面,罗尔斯的分配原则比洛克更体现出“互惠”与“博爱”的价值。
就“互惠”(reciprocity)而言,它不是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合作博弈中指认的“相互获利”(mutual advantage),而是预设了公共规则框架下的正义合作体系,以及由此确立的各种合法期望。“互惠”介于公共无私和相互获利之间,被视为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达成正义条款的重要观念。虽然“相互获利”同样可能提升人们福祉水平,但是只有“互惠”才能够吸引人们对社会弱势群体福祉的最高关注。罗尔斯强调“互惠”意在表明没有人应得在自然天赋分配中所占的偶然地位,社会也不应当为那些最初较有利者做最好的事情。
就“博爱”(fraternity)而言,它无疑包含一种公民友谊和社会团结的意义。说差别原则体现出博爱的观念,是因为它支持这样的主张:如果不利于促进处境较差者的利益,社会成员就不应该增加任何利益总额。虽然前文说过洛克的理论暗含“共同体”的假设,但罗尔斯强调的“博爱”观念不是一回事。根据罗尔斯的描述,良序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首要美德便是“正义感”,以拥有“正义感”来参与社会的公平合作体系,这是洛克理论中所阙如的。此外,“博爱”的观点要求建构某种公共的政治正义观念,这与洛克式的独树一种特定的广包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s)建立起来的“共同体”是非常不同的。
五、解构“自我所有权”
本节将深入财产权的内部,通过发掘自我所有权命题来分析洛克、诺齐克与罗尔斯之间的根本差别。在洛克看来,财产权的基础与根据正是自我所有权,即“每个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前揭书,第18页。。每个人都拥有自己身与心,“劳动”作为跟自我有意向性联系的行为,在完整意义上也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以自我所有为起点,人们通过劳动占有身心之外的物品,拥有相对其他人的排他性的(财产)权利主张。
诺齐克尊崇自我所有权的重要价值。他认为,洛克的所有权观念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把人们说成是对自己和自己的劳动拥有所有权的人。他们把每一个人都看做是拥有做出决定权利的人,即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成为什么,以及看做是有权利收获自己行为所带来利益的人”*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Inc., 1974, p.171.。在他看来,以自我所有权作为边界约束权利,体现了康德主义“人是自在目的”的根本原则。对他来说,不仅要坚持个人对身心进行控制的这种严格的权利(自我所有权),还必须坚持个人用其劳动或他人自愿转移而得的财产具有严格的权利(财产所有权)。简言之,诺齐克的自我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是一体两面、内在同一的。我们不妨将这种自我所有权称作“完全的”自我所有权(full self-ownership right)。
相较之下,洛克的自我所有至多是一种“敏于事实”的自我所有权(fact-sensitive self-ownership right)。“敏于事实”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自我所有与对财产所有是不对称的,财产所有权只是自我所有权的派生产品,二者不具有同一性;二是人们不再对身心或财产拥有始终如一的控制权,而会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调整。从本文对洛克的分析能看出,无论在自然状态,还是在政治社会,洛克都暗示需要对私人财产做出的某些必要的限制。例如,不符合“E&AG条款”的占有就是不正当的,拥有太多的私有财产也是“不道德”的。这种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调整财产分配的方式,正是“敏于事实”的自我所有权的内在要求,目的是使社会分配趋向更加公正的模式。
对“自我所有权”的不同理解,构成洛克与诺齐克在理论分殊的原点。“完全的”自我所有权是逻辑上最强版本的自我所有权,这既体现在权利的广度上,如包括了对自己身体完全的控制和要求赔偿权等,还体现在对这些权利的严格度上,如任何时候这些权利都不能被侵犯。“敏于事实”的自我所有相对温和得多。我们设想洛克会这样批评诺齐克:“完全的”自我所有权既不能与关于上帝的信念相一致,又会与契约中的公平精神相冲突。
吊诡的是,罗尔斯虽与诺齐克一样,主张自己的理论作康德主义的解释,却只字不提自我所有问题。他巧妙地说:“我把作为一个本体自我的个人选择假设为一个集体的选择。”*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26.这里集体的选择肯定不是指个人利益让位于集体利益,而只是意味着原初状态中的每个人都会一致同意正义两原则,在这种一致同意中表现出每个人自我的统一。罗尔斯如此处理自有苦衷。依日常观念来看,自然禀赋这些本属于个人所有之物,却被他认为是纯属偶然分配的产物,没有人应得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之外的自然禀赋和社会优势,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将这些偶然因素当作社会的共同资产。如此设定,罗尔斯再去提及自我所有就显得不再必要。
罗尔斯不提自我所有,也就不像诺齐克一样将此概念与财产所有缠束在一起,不要求无条件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从他的基本自由清单中能找到蛛丝马迹。依罗尔斯所言,正义第一原则用来保障公民基本自由,这些自由包括“政治上的自由与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个人的自由;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以及依照法治的概念不受任意逮捕和没收财产的自由”*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3.。这些基本自由中包括持有财产的权利,表明罗尔斯认可私有财产是重要之物。但他又接着说,拥有某些财产(如生产资料)的权利被排除出基本自由清单,不受第一原则的保护*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4.。这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的财产权不是“根本的”和“不可让渡的”,国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根据平等或公共利益进行必要的限制。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罗尔斯才会说,他的正义理论(财产理论)是开放性的,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能够与他的正义原则相兼容。
至此,我们解构了洛克、诺齐克和罗尔斯三人的自我所有权命题。诺齐克主张“完全的”自我所有权,坚持个人对身心和财产都具有严格地不被侵犯的权利,从而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罗尔斯不诉诸自我所有权,而是在全体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将自我所有转换成集体所有,进而建构
他的自由平等主义的理论。洛克既不像诺齐克那样抱守“完全的”所有权,又不同于罗尔斯那样存而不论,而是主张“敏于事实”的自我所有权。洛克既认识自我所有权的重要性,又察觉到自我所有和财产所有并不是一回事,在他眼里,政府的目的绝不仅限于保护(消极)权利,我们要对政治的要求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六、结 论
本文将洛克的财产理论置于当代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如果前文论证无误,可以认为洛克的财产理论既不是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式的,也不是罗尔斯的自由平等主义式的,不妨将他的理论锚定在罗尔斯与诺齐克之间。洛克的立场既不会导向纯粹的资本主义,又和自由平等主义社会,甚或社会主义社会维持适宜的距离。在此,笔者同意扎克特的论断:“洛克的权利理论像是‘金发女孩’一样的东西——既不支持‘大政府’,也不支持‘小政府’,而是支持正好合适的政府。”*Michael Zuckert, Launching Liberalism: On Lockean Political Philosophy,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p.329.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洛克的财产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也不应期待它成为一种阐述完备、论说严密的财产学说。正如后人评论的那样,这反而会充满着混乱和不妥。*James Tully, A Discourse on Property: John Locke and His Adversa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32-234.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承认,洛克所勾勒的财产理论是一种原创性理论。当代人没有选择一种统一的定义和解读,而是从同样的位置出发,沿着不同的方向起航。自洛克以来,理解财产权就成为理解政治与社会的钥匙。